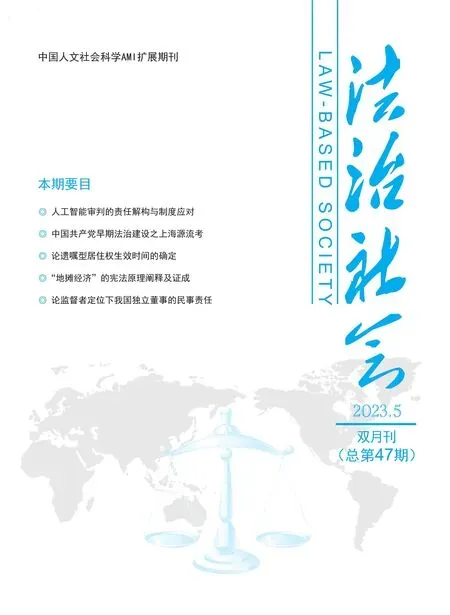罪与刑的线性不相关:美国大规模监禁罪刑关系的理论迷思
劳佳琦
内容提要:一般认为,罪为因,刑为果。理想的罪刑关系应该是高度相关的线性关系。然而,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大规模监禁作为罪刑关系的样本却显示,罪刑之间并不存在如此直接和即时的线性相关。以美国大规模监禁罪刑关系的三个迷思为抓手,本文发现犯罪率的消长只是监禁率变化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其全部根据,甚至不是主因。监禁率的变化对于犯罪率的消长而言也并不存在立竿见影的效果,犯罪的潮汐涨落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的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探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注定了罪刑关系的复杂性,直觉式的罪刑关系想象既不符合现实,又会给现实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美国大规模监禁的惨痛教训提醒我们,必须用一种复杂数据模型的思考方式去代替直觉式的罪刑关系想象,只有观念发生变革,才能带来犯罪控制模式的革新。
一、大规模监禁:罪刑关系的美国样本
1973 年,美国著名刑法学家Alfred Blumstein 和Jacqueline Cohen 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 《刑罚稳定理论》 的文章。基于美国1925 年至1973 年间监禁率稳定维持在低位的现实,两位作者乐观地预测,无论未来犯罪率如何变化,美国的监禁率将始终保持稳定。①Alfred Blumstein and Jacqueline Cohen, A Theory of the Stability of Punishment,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Vol.64,Issue 2,1973,p.198.
不幸的是,这篇文章的发表似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现实迅速朝着与预言截然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自该文发表当年起,美国的监禁率就开始一路狂飙,持续近40 年之久,直至2009 年才开始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②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The Growth of Incarc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Causes and Consequences,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14,p.34.据统计,人口总数仅占世界人口总数5%的美国,其监禁人口却占了世界监禁人口总数的近14。美国从一个标榜自由民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监狱国家(prison state)。学者将这一史无前例的现象称为大规模监禁(Mass Incarceration)。据测算,即使未来美国监禁率一直保持下行趋势,按照目前的速度来说,至少需要花费75 年才能减少一半的监禁人口。③Nazgol Ghandnoosh, Sentencing Project, Can We Wait 75 Years to Cut the Prison Population in Half?,8/3/2018,https://www.sentencingproject.org/app/uploads/2022/08/Can-we-wait-75-years-to-cut-the-prison-population-in-half.pdf,1/7/2023/.
从某种角度来看,大规模监禁如同一场疯狂的刑罚实验,虽然发生在大洋彼岸,却有着超越特殊性的普遍意义。一般认为,罪为因,刑为果,犯罪与刑罚应该是高度相关的线性关系。犯罪态势严峻,国家投入的刑罚资源就应该随之增长;犯罪态势随着犯罪控制的加强有所回落,国家的刑罚投入又应该随之减少。这种线性相关的罪刑关系高度符合大众的逻辑与想象,也成为不少学者常用的叙事逻辑。然而,当把美国大规模监禁作为样本展开深入观察,我们发现,现实中罪刑之间的关系展现出了复杂的面貌,不能用罪刑关系的应然想象去简单诠释与推测。其中,美国大规模监禁罪刑关系存在的三个迷思特别值得深入探究,所寻得的答案或许能为我们深入理解罪刑关系提供生动的素材,也可能丰富甚至改变关于犯罪治理的某些常规理解。
二、罪涨刑增:理所当然?
如果说大规模监禁对于美国社会而言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噩梦,那么在这个噩梦开始之前,另一场噩梦早就先一步降临,这场噩梦的名字叫犯罪。
美国的犯罪率自1961 年起大幅增长,暴力犯罪与财产犯罪率持续全面上扬。据统计,财产犯罪率自从20 世纪60 年代起不断走高,在1979 年达到峰值,暴力犯罪率的上扬趋势则一直持续到了20 世纪80 年代中期。20 世纪60 年代具有政治性的暴力逐渐演化为通过无端伤害他人来发泄个人愤怒的街头犯罪,危及生命的严重暴力犯罪在全美范围内频频发生,特别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并不认识的陌生人犯罪比例显著增加,④Franklin E.Zimring and Gordon Hawkins, Crime Is Not the Problem: Lethal Violence 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62-63.广泛引发了公众对于犯罪的恐慌情绪。1968 年,盖洛普公司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高达81%的受访民众认为美国的法律与秩序已经崩坏。⑤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The New Press,2012,p.46.为了安抚民众不断增强的恐惧情绪,美国的刑事政策自20 世纪70 年代起开始惩罚性转向,美国的监禁率随之不断飙升,美国大规模监禁就此拉开帷幕。
(一)并非必然
高犯罪率导致高监禁率,这一十分自然的叙事逻辑与罪为因、刑为果的罪刑关系想象高度贴合,因而非常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然而,历史经验表明,高犯罪率并不必然会导致高监禁率。
从纵向来看,太阳底下无新事。早在20 世纪60 年代以前,美国同样经历过类似的社会动荡与犯罪率飙升。在19 世纪和20 世纪早期,成千上万来自爱尔兰和南欧及中欧的移民到美国大陆寻找新生活。除了少数人留在了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农场,绝大部分人都涌入了位于美国工业带上的各大城市。在这些移民之中,贫苦的青年男性是主体,他们国籍不同,信仰各异,聚居于美国工业城市的贫民窟后,为了讨生活争夺街道的控制权,结成帮派互相争斗。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变迁作为大背景又放大了这种不安定。宗教和种族分裂、年轻人过剩、巨大的经济风险和社会变革,这些因素的混合不可避免地掀起了美国社会的第一次犯罪浪潮。⑥William J.Stuntz, The Collapse of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8.尽管欧洲移民潮导致当时犯罪态势一度恶化,美国的刑事政策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惩罚性转向,也没有过度依赖监禁这一手段来控制犯罪。
从横向来看,20 世纪60 年代犯罪态势的恶化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事实上,当时犯罪浪潮几乎席卷了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犯罪问题时,最终只有美国转向了严刑峻法,少有国家采取类似的做法(英国有跟随美国亦步亦趋之嫌,但是其刑事政策严厉化程度远远不如后者)。有的北欧国家在面对不断增长的犯罪率时,甚至还降低了监禁率。统计数据显示,在1960—1990年间,美国、芬兰、德国的暴力犯罪率均增长了2~3 倍,其中凶杀率均增长了1 倍,但是就监禁率而言,美国增长了3 倍,芬兰下降了60%,德国则保持了相对稳定。⑦储槐植、江溯:《美国刑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292 页。另一组数据的对比则充分凸显出美国这一阶段罪涨刑增的异乎寻常。1970 年,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8 个西方发达国家之中,美国的监禁率为97/100000,虽位居第一,但是仅比位居第二位的加拿大高7%(90.3/100000),比位居第三和第四位的澳大利亚(82/100000)和英国(80/100000)高约15%。2010 年,美国的监禁率飙升至500/100000,比位居第二位的英国高227%(即使英国此时的监禁率相较于1970 年来说也近乎翻倍),比位居第三位的澳大利亚高270%,超过其余五国监禁率的总和。⑧See Franklin E.Zimring,supra note ④,p.4-5.仅仅用了40 年的时间,美国触目惊心的高监禁率就使其成为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异类。
综上所述,无论是美国之前的政策选择还是其他西方国家的同期做法均显示,犯罪率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监禁率的攀升。罪涨未必刑增。
(二)事出有因
那么,为什么美国会在20 世纪70 年代罔顾西方同侪的做法,抛弃以往应对犯罪的策略,不顾一切地走上大规模监禁之路呢?
原因一是舆论。在犯罪态势恶化的时候,民众就会下意识地要求政府采取严刑峻法,这并非新事。然而,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两个巧合的出现如同催化剂,加速与强化了美国民众把对于犯罪的恐惧转化成对政府刑事政策的不满。其一,美国犯罪率全面增长的时期正好处于美国刑事政策比较轻缓的阶段。这一期间,美国减轻了对许多犯罪的刑罚,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判决来限制警察的权力,保护刑事被告人的权利。很多民众将犯罪率的上升归因于执政当局对犯罪的软弱(soft on crime)。其二,全美犯罪率迅速增长又正好发生在约翰逊总统大力推行伟大社会项目(The Great Society Program)的阶段,该项目秉持了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这一精神,但是受到越南战争的拖累导致效果不彰。这一巧合令当时的美国民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试图通过增大公共投入、发起各种社会福利项目以期从根本上解决犯罪发生的原因,这种治本策略并不能有效减少犯罪。犯罪的根源在于犯罪者堕落的个人品质,而不在于社会环境的不公。不少反对者甚至认为,正是这些社会福利项目催生了犯罪率的增长,因为它们培养了病态的人格和一种依赖文化。⑨See Franklin E.Zimring,supra note ④,p.4-5.在这两个巧合的推动之下,美国社会刑罚民粹主义(penal populism)高涨,要求严刑峻法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原因二是党争。自20 世纪50 年代起,犯罪问题就牢牢占据了美国公众话题的中心位置,随着20 世纪60 年代犯罪态势的恶化,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能否在犯罪问题上给出令选民满意的方案是成为执政党的关键。当时,执政的民主党对于犯罪问题的认识与公众的情绪明显不太合拍。一些民主党人认为民众对于犯罪的恐惧是误导性的犯罪统计数据与政治作秀的产物,犯罪问题给公共安全带来的实际威胁远比媒体和保守派人士所宣称的要小;另一些民主党人虽承认犯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们认为犯罪问题主要是种族和公民权利的问题,仍然主张运用治本策略来控制犯罪。⑩Se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upra note ②,p.113-115.民主党分裂而不合时宜的立场被解读为应对犯罪态度软弱,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共和党趁机反其道而行之,在各类选举中大力将犯罪问题种族化和政治化,承诺以严刑峻法来应对犯罪,讨好广大选民特别是南方白人和北方工薪阶层的白人。这一策略非常奏效,共和党迅速在各类竞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在民意压力和对手竞选策略的影响之下,民主党候选人为了赢得选举也纷纷投身于严打犯罪的 “军备竞赛” 之中。两党以严刑峻法为卖点竞相讨好选民,美国刑事政策持续出现惩罚性转向,铺就了通往大规模监禁的道路。
三、刑增罪落:确有因果?
自20 世纪90 年代开始,美国持续高位的犯罪率出人意料地开始 “大跳水”(The Great Crime Decline)。美国各地均持续经历了令人欣喜的犯罪“退潮”,几乎所有类型犯罪的犯罪率均一致呈现出不断走低的趋势。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公布的数据显示,1993年至2018 年间,美国暴力犯罪率持续下降51%,财产犯罪率持续下降54%。⑪需要说明的是,美国暴力犯罪率总体趋势虽不断下降,但是下降过程中略有波动,2004—2006 年和2014—2016 年两个阶段有小幅回升。数据来源参见: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10/17/facts-about-crime-in-the-u-s/,2023 年7 月18日访问。对于这一意外之喜,各路专家纷纷尝试给出解答。一些人认为,20 多年来美国犯罪率持续、全面、大幅的下降应当归功于大规模监禁,前者充分证明了扩大监禁规模在犯罪控制方面的有效性。
上述刑增罪落的归因逻辑十分符合罪刑关系的应然想象,但是这种理所当然却并未获得太多的证据支持。目前,美国学界主流意见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大规模监禁可能在减少犯罪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并不大,大规模监禁并非美国犯罪率“大跳水” 的主因。⑫Se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upra note ②,p.337.
(一)并非唯一因素
美国犯罪率的持续走低是诸多因素复杂互动导致的结果。如同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监禁率猝不及防迅猛增长一样,90 年代后美国犯罪率的“大跳水” 同样不在意料之中。以至于在全美犯罪率连续数年出现大幅下降后,仍有一些知名学者坚持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美国的犯罪率特别是暴力犯罪率很快会反弹回来,并且迎来新一轮的暴涨。⑬这些知名学者包括但不限于James Alan Fox、James Q.Wilson 和John Dilulio 等。
在预测被现实狠狠打脸之后,各个领域的学者们纷纷对于这一令人迷惑的现象给出了五花八门的解释。总结起来看,迄今为止,被认为对美国犯罪率下降有显著贡献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警力的增加,警方治安策略的提升,监禁规模的扩张,枪支管控法律的严格化,允许携带隐蔽武器法律的通过,死刑适用的增加,堕胎合法化,毒品市场的变化,人口结构的老化,90 年代经济繁荣带来的收入提高、消费者信心、通货膨胀,等等。⑭Steven D.Levitt, Understanding Why Crime Fell in the 1990s: Four Factors that Explain the Decline and Six that Do No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8,Issue 1,2014,p.165-168.
尽管学者们对于哪些因素真正对犯罪率下降有显著贡献以及各个因素对于美国犯罪率下降的实际贡献大小存在争论,但是他们一致认为,90 年代后美国犯罪率的持续大幅下降并非由单一因素所导致,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学因素、政策因素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形成的合力才促成了这一广泛而剧烈的变化,大规模监禁即使是导致犯罪率下降的因素,也不是唯一因素。
(二)实际影响不大
研究显示,大规模监禁在减少犯罪方面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大规模监禁主要通过隔离和威慑两大机制试图取得减少犯罪的效果。所谓隔离机制,就是通过将犯罪人关押在监狱之内,客观上阻绝其在监禁期间回归社会继续犯罪的可能性。所谓威慑机制,一方面指通过监禁使得犯罪人饱尝刑罚之苦,促使其审慎进行得失权衡,从而在主观上打消其出狱后继续犯罪的念头;另一方面指以监禁犯罪人的方式 “杀鸡儆猴”,让其他潜在的犯罪人深刻了解犯罪的代价,从而在主观上抑制其他人实施犯罪的冲动。前者是特殊威慑,后者则是一般威慑。简而言之,隔离机制致力于使人不能犯罪,威慑机制致力于使人不敢犯罪。隔离机制减少犯罪的效果实现于监禁期间,而威慑机制减少犯罪的效果(特别是特殊威慑)则主要实现于监禁结束以后。
2014 年,美国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大规模监禁的研究报告。在全面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该报告指出:其一,关于隔离机制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尽量延长监禁时间,让尽可能多的犯罪人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与社会隔绝,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减少犯罪的效果。然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一般会随着其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除非能够精准隔离那些高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否则隔离机制的效率会很低。鉴于实践操作中旨在精准隔离的选择性隔离模式已被普遍性隔离模式逆向淘汰,美国大规模监禁的隔离机制一直处于低效运行的状态。其二,关于威慑机制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刑罚的威慑效应主要来自刑罚的确定性而非严厉性,提高被捕的风险远比加重定罪之后的量刑更有威慑力。因此,大规模监禁通过延长监禁刑期所能获得的增量威慑效果(The Incremental Deterrent Effect)并不大。⑮Se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upra note ②,p.4-5.
另有一些研究致力于从整体上探索监禁率对犯罪率的影响,这些研究的结果同样表明,大规模监禁在减少犯罪方面的实际效果远远低于预期。其中,最乐观的结果显示可归因于大规模监禁的犯罪减少量在犯罪下降总幅度中的占比不超过25%,最悲观的结果则显示这一占比仅为3%。⑯See Michelle Alexander,supra note ⑤,p.236.
(三)边际效用递减
通过扩张监禁规模来控制犯罪还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大规模监禁对美国犯罪率下降的贡献即使存在,也在不断减弱。根据边际效应递减的原理,当监禁率处于低位时,扩大监禁规模能够明显起到减少犯罪的作用,但是随着监禁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作用达到峰值之后会逐渐变小,乃至趋近于零。如果把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考虑在内,那么之前大部分的研究结果可能还是高估了大规模监禁对美国犯罪率下降的实际影响。
2015 年,纽约大学法学院布伦南司法中心以1980—2013 年间美国各州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回归分析排除其他因素对犯罪率下降的影响,在考虑监禁规模扩张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下发现:其一,大规模监禁确实是导致美国犯罪率下降的影响因素之一,但这种影响只体现在财产犯罪率方面,影响程度也远低于预期。20 多年来,可归因于大规模监禁的犯罪减少量在财产犯罪下降总幅度中的占比不超过7%,暴力犯罪率的持续下降则基本不受大规模监禁的影响。其二,随着监禁规模的不断扩大,大规模监禁在犯罪控制方面的效用不断下降,这一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早在1980 年之前就初现端倪,在1990 年后愈演愈烈,2000 年以后,监禁规模的继续扩大对于犯罪率下降的贡献基本为零。从大规模监禁对财产犯罪率下降的实际贡献来看,20 世纪90 年代,监禁规模扩张带来的犯罪减少量占犯罪率下降总幅度的6%,进入新世纪后这一占比不足1%。在美国目前超高监禁率的情况下,“更多的监狱” 早已不能带来“更少的犯罪”。⑰Oliver Roeder,Lauren-Brooke Eisen,and Julia Bowling, What Caused the Crime Decline?,12/2/2015,https://www.brennancenter.org/our-work/research-reports/what-caused-crime-decline,1/7/2023.
(四)同侪对照存疑
一些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惊奇地发现,与20 世纪60 年代犯罪浪潮席卷西方发达国家类似,20世纪90 年代起犯罪率的 “大跳水” 也并非美国独有,而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情况,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像美国一样大幅度提高监禁率。比如,加拿大的监禁率远远低于美国,而且数十年来增长很少,其犯罪率自进入90 年代后却和美国一样出现了全面显著的下降:财产犯罪率于1991 年达到峰值,为每10 万人6160 起案件,之后持续下降,2013 年这一数值降至每10 万人2342 起;暴力犯罪率于1991 年达到峰值,为每10 万人1084 起,之后持续下降至2013 年,这一数值仅为每10 万人766 起。⑱Franklin E.Zimring, The Necessity and Value of Tran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Some Preaching from a Recent Convert,Criminology and Public Policy,Vol.5,Issue 4,2006,p.615-622.同样的,西欧国家在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其暴力犯罪率特别是致死的暴力犯罪率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然而,这些西欧国家的监禁率无论是变动幅度还是既有规模均更接近于加拿大,而远远小于美国。⑲Graham Farrel,Nick Tilley,and Andromachi Tseloni, Why the Crime Drop?,Crime and Justice,Vol.43,2014,p.421-490;Michael Tonry, Why Crime Rates Are Falling Throughout the Western World,Crime and Justice,Vol.43,2014,p.1-63.
这些发现跳出了聚焦美国的视野局限,对大规模监禁刑增罪落的归因逻辑提出了最为有力的抨击:若将20 世纪90 年代起美国犯罪率的全面下降主要归功于大规模监禁政策,为什么其他没有采取大规模监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会同步出现类似的犯罪率 “大跳水”?这一问题是美国大规模监禁政策的拥护者无法回避也无法回答的。
这些发现也揭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20 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国家犯罪潮汐的涨落似乎有一个统一的大趋势,是某种历史规律的体现,并不受某一国家特定刑事政策的左右,其关键成因尚未进入我们的认知范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无法将20 世纪90 年代后美国犯罪率的 “大跳水”主要归功于大规模监禁。简而言之,刑增未必罪落,罪落恐有他因。
四、罪落刑减:何以迟来?
按照罪刑关系的应然逻辑,犯罪态势有所回落,国家相应的刑罚投入也应该随之减少。然而,吊诡的是,在犯罪率持续下降的同时,美国的监禁率却依然一路狂飙,直到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才首次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诚然,刑罚的调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国家很难根据犯罪态势的变化即时迅速地调控刑罚资源的投入。可是,20 世纪90 年代全美犯罪率就开始持续全面下降,全美的监禁率却直至2009 年才出现缓慢下降的势头,为什么在罪落近20 年后,刑减的趋势才姗姗来迟?
(一)意愿缺乏
一个国家监禁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对犯罪的反应方式而不是犯罪本身。正如20 世纪70 年代,舆论和党争推动了美国刑事政策的惩罚性转向,美国的监禁率才会一路狂飙,而犯罪只是触发因素。进入90 年代后,尽管犯罪率持续下降,舆论和党争这两大因素较之先前却并未发生太大改变,民众依然对犯罪问题忧心忡忡,政客也就依然试图通过摆出严打犯罪的强硬立场来攫取竞选胜利,美国社会及时降低监禁率的意愿驱动明显不足。
犯罪率下降并没能显著扭转民众的态度。社会公众关心犯罪问题,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关心只是门外汉式的看热闹。他们对于刑事司法体系如何运作知之甚少,对于政府公布的犯罪率的涨跌也并不敏感。相比枯燥的统计数据而言,新闻媒体上耸人听闻的犯罪案件或者身边人口口相传的被害经历更能吸引民众的注意力,也更能影响他们对于罪与罚的基本认知与态度。因此,公众对于犯罪的认知往往与事实真相不符。盖洛普公司一项针对美国民众的调查结果显示,2001 年至2014 年间,尽管美国官方公布的犯罪率特别是暴力犯罪率一直在持续下降,但是大部分受访者坚持认为美国的犯罪率仍然在不断上升。持此意见者的占比在2009 年曾高达74%,之后虽略有回落,直至2014 年这一占比仍然高达63%。⑳Justin McCarthy, Most Americans Still See Crime Up over Last Year,Gallup,21/11/2014/,https://news.gallup.com/poll/179546/americans-crime-last-year.aspx,1/7/2023.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犯罪问题上,美国选民常常表现出低信息量、高敏感度(low-information,high-salience)的特点,他们并不太关注常规的、日常的事实,而只是根据一两个特别令人震惊的案件进行投票,这些案件很突出,但很可能没有代表性”。㉑J.F Ptaff, Locked In: The True Causes of Mass Incarceration and How to Achieve Real Reform.Basic Books,2017,p.169.
民众对犯罪问题的认知与态度没有太大改变,以严打犯罪为卖点的竞选策略就会一直被两党沿用。这种打法在犯罪率飙升的时代有效,在犯罪率持续下降的时代也依然有效,因为民众对犯罪的恐惧依然存在,对严打犯罪的需求也依然强烈。尽管犯罪态势正在不断向好,但是为了赢得在犯罪问题上“低信息量、高敏感度” 选民的选票,对政客而言,继续摆出严打犯罪的立场有益无害,根据犯罪率的变化主张及时采取宽和的刑事政策却存在现实的风险。
作为不完美的人造之物,刑事司法系统的运作有可能产生两类不可欲的错误:假阳性问题(false-positive problem)和假阴性问题(false-negative problem)。用通俗的话来说,假阳性的情况包括:逮捕本不该逮捕的人,起诉本不该起诉的人,给无辜的人定罪,把不该投入监狱的人关起来,把罪不该死的人判死刑,否决本该减刑假释罪犯的申请,等等。假阴性的情况包括:该捕不捕、该诉不诉、该判不判、该关不关、该杀不杀、不该提前释放的提前释放。不难理解,严厉的刑事政策容易导致假阳性问题,宽和的刑事政策则容易产生假阴性问题。对于国家或者整个刑事司法系统来说,显然假阳性问题更值得关注,因为滥用刑罚会侵犯公民个人权利、浪费国家司法资源。但是,对于政党和政客来说,假阴性问题却更需要警惕与避免,因为假阳性问题往往不容易被发现,假阴性问题的后果却一目了然,一旦爆出,会对竞选产生不可挽回的损失。在这一点上民主党曾吃过大亏。1988 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Michael Dukakis 在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期间曾支持(甚至不是创立)了一个司法改革项目,该项目允许被挑选出来的罪犯在服刑期间短暂离开监狱,以便其出狱后更好地复归社会。这个项目一度运行得非常成功,被允许短暂外出的罪犯都按时返回监狱。但是在1987 年,一个名叫Willie Horton 的罪犯获准休假出狱后犯下了强奸、抢劫和攻击等多项重罪,震惊全美。于是在总统大选期间,当时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老布什就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指斥Michael Dukakis 宽纵罪犯以致多人受害,成功将后者一举击溃。自此以后,这次竞选产生的“威利霍顿效应”(Willie Horton Effect)警钟长鸣,对于美国的政治生态影响深远。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两党各路候选人最理性的做法就是在犯罪问题上继续坚持严打的立场,即使在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之后犯罪态势已经不断缓和。这种做法完全出于政治上的趋利避害,并不因其是否了解刑事司法实际情况而改变。很多参选的检察官、法官尽管完全掌握了犯罪率在不断下降的情况,他们也不得不采取这一立场。因为现实早已证明,冒着葬送自己大好政治前途的风险主张宽和的刑事政策来降低监禁率,往往吃力不讨好。
(二)能力不足
除了没有足够的意愿驱动之外,美国刑事司法的两大特点决定了其不具备根据犯罪率及时下调监禁率的能力。
美国刑事司法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去中心化。与我国单一的中央领导地方的刑事司法体系迥然不同,美国并非只拥有1 个而是拥有51 个独立运行的刑事司法体系。除了联邦政府的刑事司法体系之外,美国50 个州也拥有各自独立的刑事法律、刑事法院系统和监狱系统。首先,联邦政府的刑事司法系统与各州的刑事司法系统并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甚至不是平行关系,而是补充和被补充的关系。在刑事司法领域,各州为主,联邦为辅,而非相反。这一点并未随着罗斯福新政后联邦政府权力不断扩张而有所改变。以监狱系统为例,美国监禁人口的绝大多数都被关押在各个州的监狱里,而不是被关押在联邦政府的监狱里。被关押在各州监狱中的犯人数在全美监禁总人口数的占比曾长期居于90%左右。㉒Franklin E.Zimring, The Insidious Momentum of American Mass Incarcer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p.7.因此,当刑事政策要做出重大调整时,美国难以采用中央命令地方的方式来上行下效。仅仅在联邦层面入手降低监禁率,很可能收效甚微。据估算,即使现在将关押在联邦监狱中的所有犯人都立刻释放,美国的监禁率也依然位居全球第一。其次,50 个州的刑事司法系统各自独立,难以统一协调。以监禁率为例,各州之间就存在极大的差异。据统计,在1978年到2009 年美国监禁率持续上扬的阶段,美国总体的监禁率增长了288%,但是各州监禁率的增长幅度却差异显著。举例来说,北达科他州监禁率同期增长了629%,密西西比州同期增长了567%,而北卡罗莱纳州同期却只增长了85%。在2009 年后全美监禁率开始缓慢下降的时期,各州之间的情况也大不相同。据统计,在2010 年至2014 年间,全美州立监狱监禁总人口下降了4%,事实上,只有25 个州的州立监狱人口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另外25 个州反而出现了上升趋势。其中,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州为这4 个百分点的下降净值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㉓See J.F Ptaff,supra note ㉑,p.14.概而言之,去中心化的特点意味着美国刑事司法缺乏强有力的主导,联邦弱势,各州各行其是,难以及时针对犯罪态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刑事政策调整。
与去中心化相关,美国的刑事司法历来还具有地方化的特点。如前所述,美国各州在刑事司法方面拥有极大的自主权。相类似的,在各州之内,各个郡县在刑事司法事务上同样拥有极大的自主权。事实上,郡县一级的刑事司法体系是美国监禁人口最主要的产出地。这一特点决定了我们在研究美国刑事政策时仅仅将关注点从联邦层面转移到州的层面是不够的,需要将目光进一步下移到美国3144 个郡县。显而易见,3144 套刑事司法体系的运行显然比51 套刑事司法体系更难取得协调一致,美国刑事司法体系深层次的松散混乱与各行其是为全面迅速推行以降低监禁率为主旨的刑事司法改革设置了重重困难。与此同时,地方化的刑事司法体系更容易受到刑罚民粹主义的影响与裹挟。相较于联邦层面,地方选民与地方刑事司法体系的联系更为紧密,对后者关键职位人选所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郡县的警长、检察官以及一些法官候选人(特别是检察官)为了赢得地方选举,常常会摆出严打犯罪的立场来吸引选票。赢得竞选之后,他们也必须继续采取这一立场来兑现竞选承诺,以便为之后的选举积累更多的政治资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做法除了能让地方司法长官们自己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之外,并不会过多消耗地方资源,增加地方纳税人的负担,各郡县定罪量刑的犯人都会被送去州立监狱关押而不是地方看守所,州政府而不是郡县承担了所有的监禁费用。正因为这种免费午餐式的制度设计,各地方的司法长官得以源源不断地将犯人输送到州立监狱服刑而不用考虑成本。这种制度错位也使得美国的监禁率易升难降。㉔See Franklin E.Zimring,supra note ㉒,p.52.
五、犯罪治理:从观念到模式
在大众的想象中,罪为因,刑为果,罪刑两者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既合理又合法。然而,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大规模监禁却显示,罪刑之间并不存在如此直接和即时的线性相关。㉕Se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upra note ②,p.44.事实上,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罪刑关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单一因果关系,相反,现实犯罪控制模型里混杂进了太多的其他变量,舆论环境、竞选文化、党派斗争、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刑事司法体系设置,甚至堕胎法案出台等都会对犯罪与刑罚同时产生深刻的影响。以半个世纪为时间跨度,罪刑关系的美国样本充分显示,犯罪率的消长只是监禁率变化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其全部根据,甚至不是主因。监禁率的变化对于犯罪率的消长而言也并不存在立竿见影的效果,犯罪的潮汐涨落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的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主张用一种复杂数据模型的思考方式去代替高度线性相关的罪刑关系想象,不仅因为后者过分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与驳杂的现实相去甚远,更是因为这种观念会产生实实在在的巨大危害。
一方面,高度线性相关的罪刑关系想象会力主在犯罪态势恶化时加大刑罚资源的投入,这种水涨船高式的犯罪控制模式其实就是“治乱世用重典” 思想的体现。这种重刑主义的思想一来仅将犯罪率上升归咎于刑罚资源投入不足,而不能全面认识到其背后的复杂原因;二来盲目信任严刑峻法的力量,忽视了刑罚本身就是一种恶。在这种双重错误的观念指导之下,犯罪控制的效果往往事倍功半,国家的刑罚资源在被大量浪费的同时还会制造出更多的社会问题。在过去的50 年里,美国大规模监禁给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公民贴上犯罪人标签,但在降低犯罪率方面却被证明收效甚微。大规模监禁在批量生产犯罪人的同时,也批量制造了破裂的婚姻、单亲家庭以及无家可归的孩子,其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从刑事司法体系不断溢出,巩固和扩大了社会的不公,侵蚀与改变了美国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最终在国家和社会层面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伤害。㉖参见赵希:《重刑主义的教训:美国大规模监禁的源流、反思与启示》,载 《刑事法评论》 2020 年第1 期,第390-391 页。这一触目惊心的美国样本足以说明这种思维模式的现实危害。
另一方面,高度线性相关的罪刑关系想象也会阻碍决策者在犯罪态势缓和以后及时降低刑罚力度,因而造成国家刑罚资源的无谓浪费。对于罪刑关系的简单化理解建立在对于刑罚效用的盲目乐观之上,笃信治乱世用重典,必然会恐惧刑不足而世又乱,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种观念模式之下,即使犯罪浪潮逐渐退去也往往无法及时带来犯罪控制模式的调整。一来犯罪率的下降会被视为高监禁率的胜利,在行之有效的错觉之下继续维持原来的政策会成为一种路径依赖。二来犯罪率下降的趋势究竟能够维持多久是一个未知数,对贸然放宽刑事政策很可能会重新导致犯罪态势恶化的担忧会成为政策转向的最大障碍。因为在刑落和罪涨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完全符合公众的直觉,这种归因一旦被提出,对于主张宽和的决策者来说就是政治生涯不能承受之重。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刑事政策惩罚性转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公众将始于60 年代犯罪态势的恶化归咎于当时民主党在犯罪问题上过于软弱,民主党因而在各级竞选中连连吃瘪,最后不得不采取和共和党一样的严打立场。在美国犯罪率持续下降近30 年之后,尽管美国全社会对于大规模监禁深恶痛绝,两党在必须采取刑事司法改革问题上取得了空前的一致,但是大刀阔斧的宽和化转向却并未真正发生。目前美国监禁率下降的势头还在,但是速度缓慢,背后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此。
观念决定行为,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也如此。罪刑之间高度线性相关的关系想象与人的直觉高度贴合,这种观念之下产生的严打犯罪治理模式因此得以长盛不衰。然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注定了罪刑关系的复杂性,直觉式的罪刑关系想象既不符合现实,又会给现实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需要时时警惕并尝试摆脱。用跨学科的视角来理解犯罪与刑罚问题,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来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改造犯罪知识论,在犯罪控制模型中引入足够的自变量,才有可能跳出 “严打犯罪”(tough on crime)的模式,进化到“巧打犯罪”(smart on crime)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