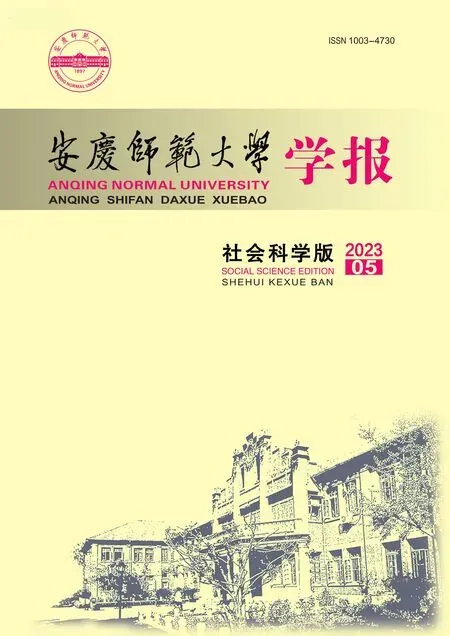桐城派的另一面:姚鼐舆地之学初探
沈志富,何敬坤
(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桐城派号为“清代文坛盟主”,辞章最盛。作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亦以古文宗师及其文论“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称名于世。目前学界对于姚鼐的研究,亦主要从文学角度展开,然其学术成就远不止此。姚鼐一生所学甚广,著述颇丰,计有《惜抱轩文集》《惜抱轩文集后集》《惜抱轩诗集》《惜抱轩九经说》《惜抱轩尺牍》《惜抱轩笔记》《惜抱使湘鲁日记》等十余种,内容涉及经学、文学、史学、天文、训诂、书数等诸多方面。姚氏治学以诗文为主,兼及经学、子史,舆地亦为其中之一端。
随着桐城派研究的深入,有关姚鼐研究的视阈也在不断拓展,比如其史学研究就取得了一定的进展①参见董根明《桐城派名家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4-126页。。至于舆地学方面,已有论著中亦偶有涉及,如车锡伦、萧宝万从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两个方面对《登泰山记》所载的中、西、东三谷进行考证,指出了姚鼐在叙写这三条溪谷时的部分失误之处;王立群将《登泰山记》归类为以记载地理知识、有利于地理考订为主的地学游记,并对其进行深入剖析,探讨了其地学游记特征;王达敏从清代学术的大背景出发,将姚鼐一生的治学经历分为三个时期,对其考据思想的发展进行了剖析,并对于地理考据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郑素燕在探讨姚鼐的史学思想时亦简要述及姚鼐地理考据的成就②参见车锡伦,萧宝万《姚鼐〈登泰山记〉所述泰山南麓三谷订正》,《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第78-80页;王立群《姚鼐的〈登泰山记〉与地学游记》,《语文建设》,2004年第4期,第36-37页;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8-21、213-236页;郑素燕《试论姚鼐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2020年3期,第9-18页。。不过,以姚鼐舆地学为主题、系统论述其舆地学的论著暂付阙如。本文着眼点即在于此,尝试通过对姚鼐舆地学著述的分析,探究其地理考据之法与舆地学思想,以勾勒桐城派学术思想的另一侧面,并就教于方家。
一、古地考辨与今地书写:姚鼐舆地学著述大要
受乾嘉时期学术思潮影响,姚鼐曾致力于考据,著有数量较为丰富的考据之作,其中用力最深的乃是舆地之学。学者谓“姚鼐早年从戴震治学,对地理一门别有会心。后来,他所写有关地理沿革方面的文章甚多,并以此自负”[1]213,当为写实之照。姚鼐在舆地学方面的著述主要集中于《惜抱轩文集》《惜抱轩文集后集》《惜抱轩九经说》《惜抱轩笔记》等。综观这些著述,其在舆地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古史地理考辨。针对史上热点舆地问题或典籍中的某些舆地内容,姚鼐并不盲从,而是从史料与史实出发,详加考辨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复谈孝廉书》提到的秦郡数目及具体名称问题,自古多有讨论之人,迄今尚未形成定论。姚鼐认为,“自秦并六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2]296乃秦始皇二十六年之事,并将黔中郡、陈郡、东海郡、河内郡、济北郡纳入其中,而桂林、象郡、南海三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列,为此后所置,“迄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2]379。然钱大昕认为桂林三郡在秦初三十六郡之列,二人因此曾有过学术争论,最终不了了之。此后,谭其骧作《秦郡新考》时曾对二人有过较为中肯的评价:“钱氏大昕考证经史,深邃绵密,古今殆罕其匹,于此独拘泥于《班志》三十六郡目,置史汉纪传于视若无睹,啁嘐再四,终难自圆其说。姚氏鼐识解最为通达,所言皆中肯綮,惜未能勤搜博采以证实之。”[3]1不难看出,谭其骧所赞同的乃是姚氏之论,但对其考证方法稍有异议。再如《项羽王九郡考》,全祖望、刘文淇、钱大昕都曾有过相关论述,但谭其骧却认为“姚鼐《项羽王九郡考》之说为是”[3]98,即“砀、陈、东郡、泗川、薛、东海、东阳、鄣、会稽,是云九郡”[2]308。而且,姚鼐还点明了自己作如此说法之地理原因:“固天下之膏腴平壤矣”[2]308。也就是说,姚鼐认为项羽选择这九郡作为封地的动机就在于这一区域地形平坦,土质肥沃,乃是天下间之优质土地。再如《三江说》。关于《禹贡》“三江”,自古纷争不断,韦昭有“松江、钱塘、浦阳”说、郭景纯有“松江、钱塘、大江”说、庾阐有“娄江、松江、东江”说、徐坚有“彭蠡、岷江、汉江”说,而姚鼐认为以上说法皆谬误失实,他认为班固的观点最为正确:“《汉》《地理志》曰:芜湖县中江出其西南,东至阳羡入海。吴县南江在其南,东入于海。毗陵县北江在其北,东入海。《禹贡》之三江具是矣”[4]38。其原因就在于,班固之说是依据西汉人的著作而来,而此人有可能亲眼见过三江的遗迹。此后地理形势发生变化,“南派湮失,人疑所不见,而说乃日纷”[4]39。此外,如《郡县考》之郡县本不相统属,《九江说》之《禹贡》九江在“湖北黄州府、九江府之间”[4]41,《盘庚迁殷说》之“盘庚迁殷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亳”[4]49等,皆为持论鲜明、论证有力的观点。
需要注意的是,在《九经说》中,姚鼐就相关问题提出观点时,对先贤之非偶有驳论。如上述《九江说》之驳韦昭、郭景纯、庾阐等人,《盘庚迁殷说》之驳司马迁“盘庚自河北迁河南,从先王之居亳,至武乙乃去亳”[4]48,等等,既展现了姚鼐治学与前贤之间的“互动”、论有所本,也表明了姚氏不迷信权威、敢于超越的科学态度。
其二,经史典籍舆地内容的正讹考补。姚鼐博览群书,著有《惜抱轩笔记》,其笔墨涉及《诗经》《春秋》《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隋书》《客座赘语》等多部古籍。对于这些典籍,姚鼐或正谬,或考补,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舆地学方面,姚鼐的正讹工作分为两个部分:其一,纠地名之谬。古代典籍中对于地名的记载,或由于传抄、或由于作者舆地功力不足等原因存在诸多谬误,如《笔记五·史部二·三国志》“汉丹阳本治宛陵,汉末徙治曲阿”一条。姚鼐认为“孙翊为丹阳遇害,孙何驰赴宛陵,此宛陵乃曲阿之误”[5]302。姚氏从地理位置上分析,认为谋害孙翊(时为丹阳太守)之妫览、戴员乃吴郡太守盛宪所荐,曲阿距吴郡较近,故孙翊可礼致之;而宛陵距吴郡较远,邀妫、戴二人前来较为不便。且曲阿距京城更近,所以孙何可“闻乱即至”[5]302。再则,妫、戴二人请扬州刺史刘馥前来接应时使其驻历阳,正与曲阿相对,而宛陵在曲阿之西,刘馥驻历阳对于宛陵影响甚小。是故,“宛陵乃曲阿之误”[5]302。再如《笔记五·史部二·晋书》“慕容兰屯汴城”一条,姚鼐认为此“汴”乃鲁郡卞县“卞”之误。其原因有二:一是原文中提到,荀羡开挖渠道直达东阿,然后斩杀慕容兰,如此一来此“卞城”当在东阿附近。倘若是汴梁之“汴”,则在河南,与事实不符。二是王羲之曾有贴言到:“荀侯定居下邳,复遣兵取卞城”[5]307。两下印证,当知姚鼐所说为真。其二,正地理史实之误。古籍中遇有一些地理记载含混不清之处,姚鼐常予纠正,如《笔记四·史部一·国语》“谷洛斗”条。韦昭为之注,称“谷在王城东入瀍,至灵王时盛,出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毁王城西南,王欲壅之使北出”[5]272。姚鼐认为韦昭之说为误,因为按照韦昭的说法,灵王只不过是使谷水回到正常的河道上,没有什么问题。姚鼐推断,谷水就是涧水,在王城之西,瀍水在王城之东,二水皆流入洛水。灵王之时,谷水大涨,乃与洛水斗。灵王为消弭隐患,堵塞谷水使其东流,致使王城形势遭到破坏。根据《水经注》“谷水出渑池,下合涧水,得其通称,或亦指之为涧水也”[6]363,姚鼐的说法似更为合理。再如《笔记四·史部一·汉书》“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一条。何焯认为西海郡乃王莽“持金帛诱羌豪献地为之,非改金城旧名”[5]285。姚鼐亦认为:“此郡临羌县下,固云西海,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古仙、西一音,此仙海即王莽之西海”[5]285。即,古时“仙”与“西”同音,“仙海盐池”就是“西海盐池”,所以西海郡应是根据当地地理特征而设,而非改金城郡之名。
除纠正谬误外,姚鼐还对典籍中地理内容语焉不详之处进行补充说明。如《笔记四·史部一·史记》中“赵良说商君,言百里奚相秦五年而东伐郑”一条,姚鼐认为此“郑”乃是京兆尹之郑,秦穆公所灭三十国之一,而非郑国之“郑”。盖因秦国僻居西隅,若想东出,须打通东向之路。而京兆尹之郑位于秦国东方,“得此则通于关东,其势益大”[5]278。如此功劳,才有夸耀之资。倘若只是“秦、晋围郑”之前一次普通的攻打新郑之事,那么与“百里奚相秦五年”的功劳则不太相符,没必要如此称赞。在这里,姚鼐以百里奚相秦五年之大功为准,从而推断出此“郑”乃京兆尹之郑,使得这句话更加精确。再如《笔记六·史部三·辽金元史》对辽之上京、东京、中京、北京、南京,金之上都、中都、东都、西都、北都、南都,元之上都等地理位置都作了解释说明,如:“辽之上京即西楼,当在今热河之上流,多伦诺尔之西”,“元之上都,似与辽上京相近”[5]311。
其三,山水游记创作中的舆地书写。姚鼐热衷于游览山水,曾在《左仲郛浮渡诗序》中说道:“他日从容无事,当裹粮出游,北渡河;东上太山,观乎沧海之外;循塞上而西,历恒山、太行、大岳、嵩、华,而临终南,以吊汉、唐之故墟;然后登岷、峨,揽西极,浮江而下,出三峡,济乎洞庭,窥乎庐、霍,循东海而归,吾志毕矣”[2]326。因而,姚鼐于后世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游记。这些游记与纯粹的文学游记不同,皆属于地学游记,即“以记载地理知识,有利于地理考订为主”,“重视区域疆划、地理方位、山脉走向、水流聚分、地理沿革等地理知识的记载”[7]。具体来说,姚鼐的地学游记名篇有《游媚笔泉记》《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游双溪记》《观披雪瀑记》《万松桥记》《游故崇正书院记》等。
在这些山水游记之中,含有大量舆地信息。譬如,姚鼐重视所游之地空间方位的记载。在上述几篇游记中,几乎篇篇都有关于景点地理位置的描写。如《游灵岩记》中,灵岩之在“泰山北”,其地“在长清县东七十里,西近大路”[2]508;《观披雪瀑布记》中,披雪瀑布“南距县治七八里,西北距双溪亦七八里”[2]511。其中尤以崇正书院的地理位置描写最为细致,“江宁城西倚山,古因其势作石头城,今古城尽变,而石头之一面不改也。石头城内清凉山巅有翠微亭,南唐暑风亭址也。亭下稍西有僧寺,南唐所为清凉寺也。寺之左,明户部尚书耿定向为御史督南畿学时,建正谊书院(即崇正书院)于此”[2]699。先由江宁城入手,次及江宁城西之石头城,再及石头城内之清凉山,再及山巅之翠微亭,由翠微亭而至其西方之清凉寺,进而由清凉寺而至崇正书院,“寺之左”为崇正书院。姚鼐将地名与方位相结合,步步相因,层层深入,详细地指出了崇正书院的地理位置与交通路线,而字数又仅有八十五字,可谓言简意赅。而上文所述“七十里”“七八里”等语,亦足见姚鼐在地理位置方面考据之详确。再则,姚鼐重视周边地理环境的记载。在其游记作品中,既有关于地理形势的描写,如《游媚笔泉记》之“桐城之西北,连山殆数百里,及县治而迤平。其将平也,两崖忽合,屏矗墉回,崭横若不可径”[2]505,将桐城西北的地形及西北山区至县治一路的地形变化交待得一清二楚;又有关于植被的记述,如《登泰山记》之泰山上“少杂树,多松”[2]507,《游媚笔泉记》之龙溪旁“多奇石、蕙草、松、枞、槐、枫、栗、橡”[2]506等。既有关于山川形貌的记载,如《游灵岩记》之“其状如垒石为城墉,高千馀雉,周若环而缺其南面”[2]507;又有关于气象变迁的生动记录,如《登泰山记》之“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2]507。以上,足见姚鼐在地学游记方面的眼界之宽、观察之细。
二、检讨乾嘉与兼采汉宋:姚鼐舆地学研究方法
舆地之学以考证疆域、政区、山川河流之沿革演替为主要内容,这决定了治舆地之人须善用一定的考据方法。考据法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治学者的学术倾向。姚鼐“学行继程朱之后”,遵奉宋儒,故其所采用的方法亦与乾嘉学派不同——主要采用宋儒解释古籍时常用的揆情度理之法,但又不拘一格,兼用音韵训诂与排比文献之法,显示出汉宋兼采的特点。除此之外,姚鼐的舆地研究还重视开展实地考察。
第一,善用理证法考辨古史地理问题。姚鼐在治学上主张不应存门户之见:“夫为学,不可执汉、宋疆域之见,但须择善而从”[4]377。不过,他也反对一味堆砌材料的繁琐考据,认为那样只会导致“搜求琐屑,征引猥杂”[2]588,缺少对史料的批判运用。相反,他更欣赏宋儒的考据方法。宋儒在笺注古籍时,“揆情度理,从辞章、义理角度诠释本文”,此法“得到姚鼐的肯定”[1]36。是以姚鼐考据地理常采用理证之法。在《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中,姚鼐于讨论南朝梁所置晋州、湘州时曾言道:“此虽于《梁书》纪传无明文,而推寻事理形势,固有可意会耳。”[2]307也就是说,梁置晋州、湘州虽在《梁书》中没有记载,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势进行推求寻索,某些论断是可以得出的。据“事理形势”以“意会”,此正为理证法的具体体现。后世史学大家陈寅恪在考据时所主要采用的事证法与此有相似之处,“所谓事证即从许多事物的相互联系,判断某一事的真伪,考订某一事的发生、变化和发展,而不偏重于字句的比勘”[8]。
在《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中,姚鼐曾分析庐江郡跨有大江南北的原因:“庐江之在江南古矣。汉景帝时,庐江王赐以通越徙王江北,为衡山王,而庐江改为汉郡。夫赐既以过徙,汉盖不尽予以衡山王勃之故地。勃之故地,盖颇分数县附庐江郡;庐江一郡遂跨江南北矣”[2]305。据姚鼐分析,庐江首先在江南,衡山郡在江北。文帝时,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然而因七王之乱之故,刘勃因功内徙为济北王,而刘赐则因过徙为衡山王,其庐江国则改为庐江郡。如此一来,刘赐既然是因有过错而徙为衡山王,那么其封地则必然不会如同之前刘勃的衡山国一样,其面积必然会有所减少。所减少之县则改属庐江郡。如此,庐江郡就跨有大江南北了。在这里,姚鼐几乎没有征引任何文献,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围绕“过”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汉庐江郡最终跨有大江南北的原因。其推论环环相扣,合情合理,尽管没有使用大量的文献征引,同样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体现了姚鼐对理证法的娴熟驾驭。这样的舆地考据,在《惜抱轩笔记》中更是比比皆是。如上述“赵良说商君,言百里奚相秦五年而东伐郑”条亦是对推寻事理之法的运用。
第二,通过音韵训诂与排比文献以证地。如上所述,姚鼐的地理考据除采用理证法之外,亦时有采用音韵训诂、排比文献方法考证地理的情况。运用训诂之法考据地理如“孙叔敖举于海说”条。众所周知,春秋之楚国地不接海,既如此,为何有“举于海”一说?姚鼐认为“薮泽亦谓之海”,“古之方言,有谓薮泽曰海者”[4]230。“海”有大湖之意,“薮泽”亦指水草茂密的沼泽湖泊地带,姚鼐的考证当无误。以排比文献法考据地理者如《笔记·史记》“传《易》者,楚人馯臂子弓,传江东人矫子庸疵”一条。姚鼐认为“江东”乃郡名,其理由在于“范蜎言: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江东虽小,地方千里”[5]279。在这里,姚鼐通过排比《史记》中《甘茂传》与《项羽本纪》中的相关文献证明了“江东”为郡名的可能性。
第三,强调“目验”与文献相结合研究舆地。总的来说,上述各种舆地考据方式,大体皆本于文献而来。然舆地之学比较特殊,倘若单单依靠文献记载进行考据,就有出现舛误的可能。故而,姚鼐强调在治舆地学时,还应注重“目验”。在《与刘明东》一文中,姚氏指出,“地理乃史学中之一端,须足行多所历,方能了了”“若止于史志上,终不能分明也”[4]305。而舆地学之所以特殊,就在于一个“变”字,姚鼐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他才提出“山壑形或消长,不可执今形以决古事”[5]317的观点。也就是说,地理形势有变化之可能,不能以今天的地理形势来因循古时的典籍记载。与此相侔,治舆地学之人倘若刻舟求剑,执着于历史上地理文献的记载,以比附彼时的现实情况,其产生舛误的可能性同样不言而喻。故而,姚鼐认为治舆地之学在览阅文献的基础上还应重视“目验”,即实地考察。
在姚鼐看来,天下间的地志之所以“率与实舛”,原因就在于其作者胡乱引用古籍记载,以之记述现实中的地理状况,忽略了地理形势的变化,却没有进行实地考察。如此一来,时间越长,地志谬误越多,因而他才有“病天下地志谬误”之语。针对这种情况,姚鼐认为只有实地考察方能解决地志谬误的问题:“设每邑有笃好学古能游览者,各考纪其地土之实据,以参相校订,则天下地志何患不善!”[2]544倘若每一地都有人对该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形成文字,再互相传阅参考,以实况验证文献,那么地志中的失误之处当会减少许多。虽然姚鼐的想法有些脱离现实,然而这确实不失为解决地志失误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姚鼐不仅在思想上重视实地考察,而且在现实中也身体力行以纠正一些地志中的失实记载,这一点在《惜抱使湘鲁日记》中多有体现。如去往湖南途中,在经过确山县附近的明水时,姚鼐得知在当地风俗中,“以明水为淮水”,而《方舆纪要》竟以此为据称确山县境内有淮水,姚鼐特指出“非也”[5]369。
在强调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姚鼐进一步提出目验地形今人不如古人的观点:“夫说经义理,后人容有胜前人者,若目验地形,则古人得者多矣。愈古,则其得愈多”[4]40。姚氏提出这个观点的原因就在于,地理环境是极有可能发生变化的。那么,同一地理现象的记载,在其变化前后就可能会有所不同。后世之人面对现实状况,当发现与前人记载不符时,自会在文字记载上有所改动,并做出新的解释。如此一来,舛误便出现了,且时间愈向后推进,谬误愈多。故而,姚鼐才有目验地形今人不如古人之说。此言与乾嘉名家钱大昕之语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言有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已矣”[9]253。
三、经世致用与文史贯通:姚鼐舆地学研究之遵循
无论治何种学问,治学之人必是在一定的思想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姚鼐生活在乾嘉时期,作为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时又与乾嘉学人颇有交往,故其治学原则与乾嘉学派有所联系而又有其特点。围绕姚鼐所治舆地学,其治学指导思想大致有三:
第一,舆地之学当“佐当世之用”。儒家提倡“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思想,其经世传统影响深远、从未间断。逮至清朝,由于政治、经济、学术上的原因,乾嘉学人埋首故纸堆做学问,经世之志逐渐消亡。而提倡“义理”的桐城派学人却承接这一余绪,形成了其一以贯之的经世传统。桐城派诸人,自方苞、刘大櫆、姚鼐,至于刘开、姚莹、曾国藩等,均有以天下为己任、文章经世之思想,即使桐城派衰落后,“其文学理论的探索和经世致用的精神仍然超越了朝代和古文的界限”[10]。这种精神,潜移默化中成了姚鼐治舆地学的指导思想之一。在《荷塘诗集序》中,姚鼐就指出诗人应先做人再作诗,而做人的标准就是应具有“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2]332。在姚鼐看来,为人准则之一就是需存经世之心、具经世之才。显然,在经世思想影响下,姚鼐认为治学亦当以为世所用为目的,其治舆地学亦以通经致用为指归。姚鼐曾言:“夫通古今之谓儒,漕运,经国之重务也。是以皇上既尝亲莅河堤,指示方略;至雨泽小有不时,必上轸宸虑,咨命河臣,毋敢怠忽,意至切矣。然则考稽川渎,讲求利病,几一得以佐当世之用,亦儒者事也”[2]418。姚鼐认为漕运乃关系国家命运之重物,因此皇帝才会亲自指示治河方略;运河但出些许问题,都会引起皇帝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儒者就应该发挥自身的责任感,以自身博古通今之能,对重要河道开展调查考证,以明其利弊,并使考据之结果用益于世,为运河治理提供借鉴。
姚鼐不仅在思想上认为地理考据应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在实际生活中也加以实践。嘉庆八年《庐州府志》成。其中,分野、疆域、形胜等内容为姚鼐所亲纂:“《庐州志》刻出矣,然唯《沿革》一门出于鼐手。”[4]339在志序中,姚鼐认为:“庐州居江、淮之间,湖山环汇,最为雄郡”,“若以地势宽平,原隰雄厚,控扼南北之要言之,安徽大府建牙,未有宜于合肥者也”[2]546。显然,姚鼐作出合肥宜设省会的判断,并非出于地域之私、门户之见,而是基于对庐州山川形势、政治地理、空间结构的客观认识和综合判断的结果。这一观点与现今安徽的实际情况不谋而合。此处不仅体现了姚鼐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而且也显现了姚鼐敏锐的地理眼光。
第二,地理考据应“尽其真”,亦即实事求是。在《礼笺序》中,姚鼐认为金榜“其所服膺者,真见其善而后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尽其真也”,对金榜虽然崇奉郑玄、但郑氏之说有不当之处时亦不加隐讳的实事求是行为表示赞赏,并称金氏为“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342。姚鼐在进行地理考据时,亦和金榜一样,以实事求是为指导。姚鼐的这一治学思想,或许也受到了乾嘉学人的影响。鉴于宋明理学的空疏弊病,乾嘉学者更加注重探寻文史典籍的客观真相,追求实事求是便成为其治学的思想原则之一,如漆永祥所说:“实事求是为汉儒治学传统,乾嘉学者承此学风,论学立说,讲求有本之学,注重证佐,无征不信”[11]98。而姚鼐与乾嘉学人多有交往,甚至欲拜戴震为师,从这一点看,其治学思想受到乾嘉学派的影响是可能的,也是存在的。具体来说,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在进行地理考据时,姚鼐不因桐城派的身份而偏袒宋儒,亦不因排斥时之汉儒而对汉儒先贤全盘否定。
《九江说》就是一篇专门驳斥朱熹关于禹时九江地理位置观点的文章。在文章中,姚鼐开篇明义,指出禹九江的地理位置,并以《汉书·地理志》为依据:“禹九江处今湖北黄州府、九江府之间,今黄州黄梅,汉寻阳县。故《地理志》曰:‘寻阳,《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是也”[4]41。紧接着便指出朱熹“以洞庭当禹九江”[4]41的失误之处。然后从五个方面驳斥了朱熹的观点:其一,湘水、沅水注入洞庭之时,洞庭之水尚未流入长江,所以不能称之为“江”。其二,清时之黄州、安庆地在秦时为九江郡,此名沿袭殷、周,汉昭、宣时为庐江郡。禹时九江之地曾进贡大龟,而汉褚少孙曾说庐江郡常有大龟出现,没有从洞庭湖得到过大龟。故洞庭不是禹九江。其三,禹九江自黄州、安庆而下,流经东山,东山称“东陵”。而后人却以与九江延伸之地甚远的“巴陵”为东陵,这又是一失误之处。其四,朱熹认为禹时九江有九条分支,那么就会有九块水中陆地,寻阳一地可能涵盖不了如此大的区域。姚鼐则认为,彼时黄梅、宿松数百十里内尽皆水中泽国,所以朱子所疑不是问题,且又有司马迁目验禹九江为证。其五,从“过”与“会”的区别,指出洞庭不是禹九江。姚鼐从以上五个方面进行论证,指出朱熹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误之处。可见,姚鼐并没有因自己尊崇程朱而对朱子进行粉饰,而是实事求是,力求真确。再如《三江说》中,姚鼐称“说禹三江者,莫详于《汉》《地理志》,莫善于康成之注书”[4]38。郑玄乃清朝乾嘉学者极为推崇的人物,被称为“汉之素王”。对于郑玄,姚氏亦实事求是,没有因他的汉儒身份而刻意歪曲。
第三,“考据”与“义理、辞章”并重。在实事求是的考证基础上,姚鼐所采取的考证结论呈现方式即体现了这一点。姚鼐认为治学者“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2]387。三者之中,义理自不必说,尊崇、阐述、发扬程朱义理乃是桐城派一以贯之的信念。关于这一点,乾嘉学派与桐城派有其一致之处,如戴震“一生论学无论如何变化,大旨则以义理为首,以考证为次,以辞章为末”[1]168。如此一来,姚鼐的舆地考据与乾嘉学派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对“辞章”的处理上:姚鼐重视辞章之学,乾嘉学派则视之为细枝末节。
漆永祥曾指出:“乾嘉学者对词章、小说、戏剧、书法、绘画等皆持轻视态度,认为此皆非学之要务。”[11]318然乾嘉学者对辞章采取如此态度,除了理念上的原因外,还有客观因素在起作用。漆氏曾对乾嘉学派的主要考据方法进行总结,而“以经解经、以经证经”即为其中之一法,“宽泛地讲就是运用最直接、最可信的材料,来证明自己想要证明的问题”[11]103,如钱大昕在对谈泰解释自己考秦三十六郡时言“仆所据者,班孟坚《志》本文,以《志》解《志》”[9]630。再加上乾嘉学者讲求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了增强论点的可信度,自然会广征博引。如此,其最后所呈现的作品就会繁冗破碎,有史料堆砌之嫌,这样的文章自然也就没有艺术性可言。以江藩《六安州沿革说》为例,其文共计一千六百余字,自始至终,所阐释论点之处必有所引,《春秋》《左氏传》、班固《地理志》、司马彪《郡国志》、司马贞《史记索隐·黥布传》、《太平寰宇记》等相关引文充斥全篇。如此一来,姚鼐批判乾嘉学派为“搜求琐屑,征引猥杂”也就不足为怪了。
相对来说,姚鼐的舆地学考据作品则兼重“辞章”,呈现出雅洁的特点。刘季高在《惜抱轩文集前言》中曾对姚鼐的考据文章作过点评:“其考据文之佳者,如《笔记四·史部一·史记》,证据确凿,断语下得干净利落,并未繁征博引,却解决了历史上的疑团,堪称考据文典范之作”[12]。这句话亦可视作姚鼐地理考据文章总体特征的概括。以《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为例,文本可分为三部分,第一、二部分以建置沿革表为界,先叙沿革,再行补注,第三部分交代文章创作缘由。第一部分总叙汉朝庐江、九江二郡的沿革,自秦灭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开始,按时间顺序,历述楚汉相争时期、文帝时期、景帝时期、武帝时期“庐江”“九江”二郡所在地的建制沿革,剥开建制沿革的表象,以历史事件的演进为线索,层层递进,将二郡的沿革并庐江由地跨南北到移于江北交代清楚,最后总结指出汉二郡的地理方位及地域形态。整个过程只有引文二处,简洁非常。文章第二部分,则是对第一部分的注释说明,即对表格中庐江郡的相关问题展开论述,对其进行解释说明或纠正谬误。其余舆地考据之作如《项羽王九郡考》等,亦是如此,行文明快,无琐碎冗长之象。推及其余地理之作,如《登泰山记》更是被称为“义理、考据、辞章”并重之范本。
姚鼐之所以这样处理舆地著述,除重视辞章外,还有另一重原因,即姚鼐虽认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皆不可废,但对它们的重视程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夫以考证断者,利以应敌,使护之者不能出一辞。然使学者意会神得,觉犂然当乎人心者,反更在义理、文章之事也”[2]542。如此,姚氏在考证之时会有意识地对考据过程加以限制,“只是提供准确的基本事实(最突出的还是地理知识)以作为其抒情达意的背景,且必须服务于‘义理’表达的需要,因此不会完整呈现考证的全部证据和过程,常常只能简单介绍考证的部分结论或结果”[13]。这种做法自然也影响了姚鼐的专门性考据作品的创作,最终形成了考证雅洁的特点。
四、余 论
关于姚鼐的学术性著述,历来非议者颇多,如《九经说》,翁方纲就认为姚鼐“不当自立议论”[14],李慈铭也说姚氏“虽讲求经术,然颇为异论”[15]。从二人的批语中不难看出,姚鼐在学术上的一些观点确实是颇异于当时的。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些非议者的言语,又恰好肯定了姚鼐在学术上的贡献。姚氏的创新无疑给当时的学界带来了一股新风,给后世带来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以姚鼐的舆地学成就而言,至少有两方面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其一,为后世学人所资鉴。如上所述,姚鼐的各种学术观点,颇有创新之处,舆地方面也不例外,是以后世多有借鉴之人。如李慎儒《禹贡易知编》中《三江既入》一文就将姚鼐的《三江说》纳入其中,进行探讨。王先谦所著《汉书补注》、王鎏所著《四书地理考》、张应昌所著《春秋属辞辨例编》等书,都曾引入姚鼐的相关观点,或为借鉴,或为鉴戒。及至当代,姚鼐的某些舆地学观点依然为学人所关注,如谭其骧就认为秦初三十六郡之“陈郡”便是由姚鼐最先发现的,“《汉志》缺,姚氏鼐始补出”[3]5。所以说,无论姚鼐的学术著述存在怎样的非议,其人在学术史上的贡献确是不容抹杀的。其二,姚鼐在舆地学上所体现的“义理、考据、辞章”并重思想为嘉道之际的折衷汉宋思想导夫先路。明末清初之际,时之学者如顾炎武等人惩明末学术空疏之弊,虽重汉学但尚无门户之见;乾嘉之际,汉宋之争逐渐兴起,且门户之争日益剧烈;嘉道之际,由于国家内忧外患,清朝之学术风气又走向经世致用、汉宋调和。而姚鼐虽亦有鄙薄汉学之意,却积极折衷汉宋。姚鼐在治舆地学中所采用的汉宋兼采方法、考据与义理辞章兼重论对于姚门弟子的汉宋兼收思想有所启发,用姚莹的话来说,“实后学所奉为圭臬,无异辞者也”[16]。更进一步,姚门弟子还“顺应了当时学术兼收的大势”[17]。从这里即可看出姚鼐的学术兼收思想似是后来学术大势的先导之一。虽然说姚鼐“义理、考据、辞章”并重思想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然而这一思想最初的实践对象便是舆地之学(如较早的《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其后的各种著述如《九经说》《惜抱轩笔记》等,舆地学的内容都一以贯之。所以说,姚鼐这一思想的来源及实践皆与舆地之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当然,姚鼐所治舆地学也有其不足。首先,姚氏在舆地考据内容上存在某些失误之处。如《笔记四·史部一·史记》“魏文侯十七年,伐秦至郑而还,筑雒阴合阳”一条。姚鼐认为《史记》“表作洛阴”是错的,当为“入渭之雒”[5]278,而不是河南之洛。根据虞万里的研究,自殷周时洛水之“洛”便从“水”作“洛”,后至战国之时文字异形,秦汉时出现了以“雒”代“洛水”之“洛”的情形[18]。所以,“洛阴”本就为正确的写法。而且,《水经注》亦有言:“河水又南,洛水自猎山枝分东派,东南注于河。昔魏文侯筑馆洛阴,指谓是水也。”[6]97可知姚鼐这一番考据其起始便存在认知失误的情况,至于其结论更是可想而知。其次,其理证法也有所不足。乾嘉学人考据旁征博引,固然导致文章繁细苛碎,但论据较为充足;姚鼐之考据方法,虽然使得文章雅洁,但却有凿空之嫌,且论据较为单一。上述谭其骧对于姚鼐与钱大昕关于秦朝三十六郡争论的评价就体现了这一点。虽然说在这次辩论中,姚鼐以桐城派的身份与乾嘉考史大家钱大昕相颉颃而不落下风,却掩盖不了其“未能勤搜博采”的事实。再如其《地舆(附)》中关于江东“丹杨”更名的考证,姚鼐认为晋时犹作“丹杨”,而后来的书籍或作“阳”,或作“杨”,“此殆陈时因北朝杨氏日盛,忌以其姓加于吾之都,故写作‘阳’耳”[5]320。从史实上来说,南朝陈时北隋强而南陈弱。南陈因忌讳“杨”隋而将其都城所在地“丹杨郡”改为“丹阳郡”,这是符合情理的。然而这一条推论却是没有任何史料支撑的,完全出于姚鼐的主观推断,他自己也知“于史无记”[5]320,其可信度自然大打折扣。所以乾嘉学人批评姚鼐凿空并非全无道理。
综上所述,姚鼐所治舆地学有得有失,然就姚鼐之思想顺应当时之总体学术大势来说,应是得大于失的,刘守安也曾说姚鼐的考据“结论也多正确”[19],同时亦从一个视角反映了桐城派学术研究内涵的丰富性。关于姚鼐的舆地学及其相关联的清代学术视域下桐城派地理学整体研究,尚存很大的拓展空间。
——论《江格尔》重要问题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