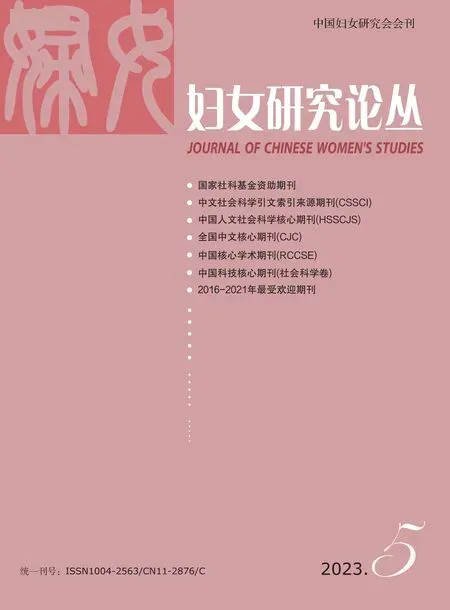更宽广的革命叙事光谱
——以《漳河水》为线索试析延安时期的女性叙事与社会变革
刘 卓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20世纪40年代的北方解放区文学创作在女性叙事上有诸多突破,推其根本来说,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战革命与边区民主建设带来的妇女地位的变化。虽然人物形象、情节脉络、文体样式各有不同,但居于叙事核心的都是女性成长的“新”“变”,或者说“翻身”“革命”,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依托同一时期正在生成中的革命话语。每部作品的讲述方式各有侧重,它们在不同时期的接受程度各有不同,其中产生了不少争论。比如,革命叙事与女性叙事何者为名,何者为实?这在经典作品《白毛女》的阐释中尤为明显,喜儿的形象是“空洞化的表象”[1],还是具有“历史多质性”,因情节上不局限于“婚姻”与“家庭”而得以承载更多超越性别的普遍代表性?把握《白毛女》文本的关键,“并不在于‘阶级’叙事如何掏空并替换了‘性别’叙事,而是‘阶级’叙事如何从‘性别’叙事中生长,或者说,有关‘性别’的叙事如何可以与‘阶级’的叙事结合起来并融入其中”[2]。革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它是席卷近现代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阶级叙事只是它的叙事路径之一,并且阶级叙事也多与其他情节结合在一起呈现为不同的表现路径。事实上,北方解放区女性叙事作品中的大部分情节与婚姻、家庭有关,即使延伸至拥军、生产等情节,也仍然是关联着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自主意识的转变。本文以《漳河水》为线索,勾勒、对比边区围绕生产、生活展开情节的一些女性叙事作品所触及的不同层面,从更宽广的“革命”光谱来理解这些作品中展现的女性力量和女性解放之路,以此来把握延安时期通过抗战动员、政权民主建设、大生产运动、民众教育等多重途径推动的深刻的社会变革。
一、以女性生命史为基底的革命叙事
《漳河水》写于1950年,通过荷荷、苓苓、紫金英三个姑娘的婚姻、家庭经历反映了漳河边土地改革和民主运动的时代变化。《漳河水》沿用了当时延安易为接受的民歌体,不过它突破了传统民歌的抒情程式,以扎实的叙事、灵活多变的曲调塑造了鲜活的女性人物形象,也因此被茅盾称赞为“长篇叙事诗最早的成功之作”[3](P5)。《漳河水》中三位人物荷荷、苓苓、紫金英,与《白毛女》中的喜儿是差不多的年纪。在《白毛女》中,喜儿作为阶级苦难的象征,在八路军到来后获得拯救。对比来看,《漳河水》中的三位女性人物更具有主动性,参加生产互助组、土地改革带来的变化使她们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也看到了自身的力量,最后冲破落后的观念束缚,掌握了生活的主动权。在一定程度上,两组人物状态的差异与情节设置相关,《漳河水》以婚姻、家庭作为叙事的主要场域,更内在于女性的生命体验,有助于正面呈现她们的变化和主动。质疑也会由此产生:以女性生命经验为主脉络的讲述,是否是私人性的、局部的、特殊群体的,因而不足以承担革命叙事?
这个问题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脉络中回答。《漳河水》的作者阮章竞是广东人,1936年前后辗转来到晋东南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十多年时间都在太行根据地工作,太行山的革命和人民是其写作生涯中的重要部分。对于这一段革命、战争的亲历者而言,妇女解放以整个革命语境为大前提,不过,她们的解放并不仅是民族抗战故事、阶级斗争故事就能够完全涵盖的。对比“太行山的人民”,“太行山的妇女”的解放任务是双重的。在《漳河水》小序中,作者这样写道:“太行山的妇女,过去在封建传统、俗习的野蛮压迫下,受到了重重的灾难。但随着抗日战争,减租减息,解放战争,土地改革,这两个时期的伟大斗争,她们获得了自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10多年来,她们忍受着难以设想的重负,支持人民解放事业;并不断地和封建传统习俗作斗争。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生产,获得妇女彻底的自由解放。她们的丰功伟业,在祖国解放的史诗中,占着光荣的一页。”[4]从遥远南方而来的阮章竞能够与太行山人民、太行山妇女感同身受,这不是因为写作技法的高超,而是因为他们同为革命者,有着共同的不可磨灭的记忆和情感。《漳河水》以女性、婚姻为主要切入点,从女性境遇的复杂性,更为深入地碰触20世纪革命中带来的社会关系变革中潜藏的诸多不同层面的新/旧变化。它是女性叙事,更是以女性的生命史为基底讲述了一个从“往日”(全诗的第一部分)经由“解放”(第二部分)到“常青树”(第三部分)的革命故事。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主题在《白毛女》中是依托阶级叙事呈现的,有清晰的现代史时间脉络。《白毛女》开篇即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1934年。这个时间点设定在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之前,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杨白劳的年关躲债、喜儿的命运都被更为清晰地指向阶级压迫——“旧社会”。《白毛女》写于1945年,它没有把情节设定为与抗日战争相关,而是以恶霸地主/农民为主要情节,在效果上诉诸剧场中唤起观者的道德义愤,更为契合解放战争时期的动员需求。不同于20世纪40年代大量出现的翻身戏,《白毛女》在叙事上更为自觉,喜儿、杨白劳、黄世仁、八路军等一组形象及其情节中彼此关系的设定,都使得这一段阶级压迫的故事更精准地契合此时延安对于近现代史的回顾。从延安整风运动到党的七大这段时间,回顾、整理共产党的历程、书写近现代史是党的工作的重要部分之一,初步形成了以党的视角来叙述的近现代史脉络,每一个时间点的政治意义都有着充分的讨论和论定。作为党的七大献礼作品的《白毛女》,它的情节、人物和时空场景都有效地铺垫了八路军作为喜儿拯救者、新社会开创者的双重身份。它成功地为文学如何书写历史进程探索了一个叙事方案——新/旧转变,包括《漳河水》在内的解放区大部分文艺作品都呼应了这一模式。
不过,《漳河水》中的时间脉络有所不同。在开篇的唱段“漳河小曲”之后,长诗用了一个时间模糊的开端:“漳河水,水流长,漳河边上有三个姑娘:一个荷荷一个苓苓,一个名叫紫金英。河边杨树根连根,姓名不同却心连心。低声拉话高声笑,好说个心事又好羞。”(1)参见阮章竞:《漳河水》,《阮章竞文存:诗歌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本文中《漳河水》的诗句均引自该版本。什么时代都会有三个姑娘,什么时代的姑娘都会有这样的心事,这是一个没有明确时代感的开头。再加上民歌体“漳河小曲”的唱段,以漳河两岸的风光作为起兴,使得长诗的叙事时间进入一种自然时间状态。妇女承受的苦难是漫长的,婚姻家庭领域的陋习超出了现代史的框架,对读《漳河水》的太行版本的开头能够有更为鲜明的感受: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往日的凄惶也诉不完。百挂挂大车拉百挂大车纸,大碾盘磨墨也写不起。黄连苗苗苦胆水奶活,甚时说起来甚时火。枣核儿尖尖中间粗,甚时提起来甚时哭!(2)《漳河水》最初发表于1949年5月《太行文艺》第1期,“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收录的是太行文艺版,后来作者做了修改,1950年发表于《人民文学》。
太行版的开头直接进入“苦”的倾诉状态,这个“苦”不是在近现代语境中获得确认的阶级压迫,它不是抽象的命名,而是在讲述中直接地调动了身体感受、自然物象,这是一个贴合女性自身经验和感受的讲述方式,它的自然物象是和人物的内心情感息息相通的。修改后的开头更为优美: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层层树,重重山,层层绿树重重雾,重重高山云断路。清晨天,云霞红红艳,艳艳红天掉在河里面,漳水染成桃花片,唱一道小曲过漳河沿。[4]
两个版本有不同的历史情境,基调也有所不同,不过从总体上看仍保持民歌体式,都是内在于女性的经验感受,对苦难的抒发没有持旁观的态度。人民文学版中有许多修改为研究者所称道,被认为更具古典诗词美感(3)作者阮章竞确实具有这样的才能,比如1950年的《小桥》:“榆钱片片水上漂,做巢的燕儿吱吱叫。烟霞横沫的柳林中,驮粪的驴儿成对过小桥”,如诗如画。不过,要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万象更新的历史环境中来看这种新的抒情风格的发生,而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向传统的复归。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古典”来解“民间”的并不在少数,这并不是仅仅因为接受者的知识背景不同而产生的误读,“古典”视野的误读背后有积极的认同,同时“民间”脉络中的修辞和风格也有生长;另外,“古典”和“民间”都被放在了“人民性”的视野之中,并且作为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理解文学遗产、贯通文化传统的一种努力。这一努力不仅在理论层面,也是创作者隐约的自觉融会。。单纯从形式上来看,这样的阐释不无道理,但过于倾向于古典诗词的视野和审美传统,会覆盖民歌体叙事诗在当时历史语境中的意义和形式突破。已有研究者反思这一“古典化”的修改和阐释,指出“《漳河水》从‘歌’变为‘诗’的修改过程,则折射出革命诗歌的‘民间性’特质在文学体制的规范化过程中逐渐被收束的过程”[5],因此强调民歌体的“民间性”,不仅仅是恢复民歌体的诸多特质,更为重要的是把握它的变革,在传达妇女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心声的过程中,突破了传统民歌的苦难循环的模式,也更新了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美,融为革命话语的重要部分。
在传统民歌中,苦难的讲述是最为常见的主题,虽然以抒情为主,不过讲述中融进了社会百态,平凡琐碎、幸福苦涩、命运无常,包含着普通百姓对社会的体认,很难看出严格意义上的抒情和叙事的界分。大部分民歌叙事中多是同类生活表象的铺陈,虽然有助于情绪的堆积和释放,但叙事架构相对简略、单调。常见的叙事结构方式是以月份(或者四季、五更)为次序结构全篇。《漳河水》每一章开头和结尾的唱段部分,最为接近传统民歌体式,以自然景物起兴,情绪反复吟咏。传统民歌的叙事结构来自日常生活,天天、月月、年年的设定不仅是出于叙事简便、便于记诵,也有情感上的层层递进、加深,更契合穷苦日月的漫长和心理状态上的无奈。传统民歌的结构是循环的,而《漳河水》的叙事结构是新/旧之变。全诗有三章,“往日”这个部分被纳入后续的“解放”“长青树”之中,由唱段构成的外在框架中暗含的循环往复的时间感一下子被打破了。在传统民歌中,与叙事结构上的重复与循环相关联,苦难得以被控诉,然而得不到解答,只能在想象性反抗的解决方案(自杀或者复仇)中被反复延宕,以至于封建习俗的陋习在诉苦中被“自然化”为“命”,诉苦和认命不过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漳河水》不同,女性对于自身苦难的讲述,被置于现代的、革命的视野中,“苦”不再是“命”,而是社会问题,它作为“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本相被凸显出来并指向最终解决。
从内容上来看,《漳河水》中“苦”没有直接被归因于时代环境,它从小儿女心事入手:“荷荷想配个‘抓心丹’,苓苓想许个‘如意郎’,紫金英想嫁个‘好到头’”,而后随即点明,“毛毛小女不知道愁。断线风筝女儿命,事事都由爹娘定”[4],与喜儿一样,她们对未来的命运一无所知。《白毛女》中,喜儿处在温暖的家庭和邻里呵护中,从效果上来看,更有助于凸显恶霸黄世仁的恶。《漳河水》没有设定这个理想状态,“爹娘盘算的是银和金,闺女盘算的是人和心”[4]。“爹娘盘算的是银和金”与“断线风筝女儿命”两句,前一句写尽了亲情为金钱关系彻底绞杀,而后一句是将不合理的现状习俗化。在阶级叙事中,通过地主与佃农之间“谁养活谁”的算账,以经济范畴的“剥削”揭示地主/农民关系的实质,由此唤起农民的反抗并奠定了农民反抗斗争的正当性基础。但是,在女儿们来说,“爹娘盘算的是银和金”无须现代知识话语提醒,是她们从自己和姐妹的经历中早已认清的实质,由女性口中说出“断线风筝女儿命”,这是比农民群体的认命更为深重一层的清醒的自伤。家庭内部的不平等,特别是父母与女儿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直接套入阶级反抗的视野中的。换个角度来看,《漳河水》第一章“往日”中集中呈现的家庭婚姻问题,更多呼应了“五四”时代的主题。
“五四”一代走出大家庭,大多数来到城市,固然可以说是观念的影响,比如子君“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更重要的也是社会空间的开创,大城市中有学堂有工厂,可以暂时支撑以“恋爱”构想的微小共同体。这些虽然并不足以铺开“娜拉走后”的真正出路,但暂时性地在否定的层面上使得女性向前迈进了一小步,摆脱了原有的社会身份和自我认知。对于困在农村的荷荷、苓苓、紫金英来说,即便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也不过是从一个家庭走向另一个家庭,婚姻、家庭不意味着任何意义上的个人、自我、私人空间,而是社会关系的底层链条。她们对自身处境一直有着清醒的感受和认知,民歌是她们的表达方式之一。“往日”这一章是很明显的传统民歌的诉苦方式,这与其说是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不如说是自觉采用了传统民歌的女性叙事路径。三个小姐妹的性格不同,苓苓温和,紫金英哀怨,荷荷更为勇敢、泼辣。“哪年才把头熬到?漳河你为甚不出槽?给俺冲条道!”[4]荷荷已经完全不在意传统美德,不过这个更为勇敢的“给俺冲条道”的表达,也并不是自觉地打破原有家庭关系,她们的意识还没有到那样的程度。无论是哀怨还是泼辣,都是以自然物象作为倾诉的对象和想象性的解脱:
漳河流水声呜呜!戏鼓冬冬响连天,唱尽古今千万变。唱尽古今千万变,没唱过俺女儿心半片!恨咱不能拔起山,把旧规矩捣成稀巴烂!万代的脚踪要踏出路!千年的水道看流成河![4]
这一段既是荷荷的声音,也是三个小姐妹共同的心声,她们是彼此倾诉的对象,也是彼此情感上的支撑。很难说这个声音是集体性的力量,它仍然只是不具有干涉现实力量的“心声”。《漳河水》中并没有采用《白毛女》结尾中“群众”齐声控诉的环节,但是在民歌的复沓体式和修辞中,个人的声音借助自然意象“漳河流水声呜呜”开始具有了超越个体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漳河水》中的女性心声有着它的普遍性。妇女并不是没有声音,也不是没有反抗的行动,哪怕改变现状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哪怕控诉最后变成仅有自己能够听见的回声,指向自身的毁灭,她们也是有声音的。民歌体的讲述天然带有从身体经验出发的对于现有言语秩序的反抗以及群体性的共同认知。优美、清新并不是民歌最宝贵的特质,它的美德在于真实。
长期以来,延安时期的民歌体叙事诗作品最受质疑的一点就是真实性:反抗的声音是知识分子代言还是女性群体真实的声音?然而,由谁来讲出,由谁来写定,都无法否认女性被压迫这一事实。理解民歌体叙事长诗创作的关键,不在于借用谁的语言,也不在于喜闻乐见的民间样式,而在于能否打破传统民歌体的回声感,使它从女性声音成为革命话语的一部分,从革命的潜藏力量到成为推动社会关系变化的力量。《漳河水》对妇女诉苦从“心声”到“自由歌”(长诗第二章“解放”的开头曲调)的变化,给出了非常形象的刻画:“漳河水,九十九道弯,毛主席领导把天地重安。写在纸上怕水沤,刻在板上怕虫咬。拿上铁锤带上凿,石壁刻上支自由歌。”[4]“写在纸上”“刻在板上”“拿上铁锤带上凿”都是行动性的形象,这一段“兴”之后引出了边区实际发生的变化:“共产党,毛泽东,光明福根遍地种。抗日本,保家乡,除‘秃蒋’,大解放!减租减息闹土改,妇女飞出铁笼来!漳河发水出了槽,冲坍封建的大古牢!”[4]与前一段的起兴相比,这段更近于写实,毛泽东、共产党同时出现在虚、实两个部分中。这一段中将共产党、抗战、解放等重大的政治事件融入女性的解放叙事之中,“毛主席领导把天地重安”是“妇女飞出铁笼来”的前提。不过更需指出的是,这个大的前提并不是在原有的现代史框架中被理解,而是经由自己的声音、以与自己的生活相关联的方式被讲述出来。在这个讲述方式中,“新社会”/“旧社会”的划分并不直接关联于政治时间划分,而是更依托个人的体验、生活中的变化,以个体的心理、情感层面的真实作为基础。
《漳河水》以女性的生活变化、成长为线索,不再以日常生活的时间次序、劳动中的节奏感(如劳动号子),或并列式的结构铺陈各种类型的苦难,而是以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翻身故事为血肉,以真实人物的生命经历为架构,这不仅打破了传统民歌中的诉苦的循环,并且丰富了革命叙事的多种样态。《漳河水》的第二章“解放”在开头的“自由歌”之后分别以荷荷、苓苓和紫金英为主题讲述了她们三人如何走出旧有的婚姻状态,除“自由歌”的部分保留了鲜明的民歌特色外,以三人为主题的讲述部分更像是以韵文的方式写的小故事。茅盾称赞《漳河水》优于《王贵与李香香》的理由之一即在于“人物有性格”,运用歌谣形式多样,“因此音调活泼,便于描写”[3](P5)。在歌中讲故事、写人物,是阮章竞在20世纪40年代常用的方式,他的很多作品如《圈套》(1946)、《送别》(1947)以及更早一点的演唱诗剧《柳叶儿青青》(1943)都有这样的特点,从这个脉络中能看到作者不断的积累和推进,人物形象和情节逐渐成熟。基于扎实的人物和情节,它没有落入当时翻身民歌中常见的苦难到歌颂的简单翻转的套路,它的新/旧转换植根于人物成长中,以女性成长之变来写革命之变,它提供了一种女性生命史为基底的革命叙事;从另一角度而言,它也说明延安时期民歌体叙事诗中产生的突破与创新,关键之处并不在民歌体,而在于叙事性。
二、劳动生产与女性叙事中社会空间的开创
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女性叙事作品中,《漳河水》这样以女性生命史、生活变化为脉络并不是孤例,还有田间的民歌体叙事长诗《戎冠秀》(1945)、《孟祥英翻身》(1945)等。长诗《戎冠秀》源自戎冠秀的个人事迹,依托于“英雄母亲”这一形象,把苦难经历纳入农民/妇女翻身的叙事路径;《孟祥英翻身》的故事原型是边区劳动英雄。取材于真人、真事,叙事结构聚焦于个人成长之变,在情节上也有重合之处——劳动生产,这个情节来自延安时期妇女解放进程的一个重要节点——“四三决定”。“四三决定”鼓励妇女参加生产,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涌现了孟祥英、马杏儿等一大批劳动女英雄。当时的政策方向和新闻报道中多集中在“劳动英雄”,而文学作品《孟祥英翻身》和《漳河水》更多着力于生产之于家庭内部关系的挑战,妇女翻身之后如何面对传统伦理陋习,成为“劳动英雄”只是妇女争取权利的一步。
近年来对“四三决定”的讨论多聚焦生产与家庭的矛盾,反思从单一生产取向阐释“四三决定”作为政策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单从鼓励生产的视角来看,妇女被视为新的劳动力来源,以此推导下去不仅与妇女解放背道而驰,也会误解党的政策制定基础。有研究文章作驳论式的辨析:“‘四三决定’后妇女政策的调整与转向,并非向传统乡村社会父权制作出妥协与退让,更非背弃妇女解放初心以求赢得战争胜利,而是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框架之内,通过‘妇女参加生产’助力连接起家庭与社会两个端点,促成多方利益在经济发展与性别协商中协同共进,走上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和历史实际的妇女解放之路。”[6]万军杰的文章侧重点在于把握党的妇女政策的出发点,并描绘了参加生产以构建新式民主家庭的远景,不过,初心和远景都无法回避当时历史情境中仍存在的生产与家庭冲突。文学研究领域围绕赵树理作品《孟祥英翻身》《传家宝》的分析都是在回应这一问题(4)相关研究参见贺桂梅:《人民文艺中的婚姻家庭叙事与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3期;黄锐杰:《“翻身”与“生产”——细读1943年前后边区的妇女“翻身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董丽敏:《“劳动”妇女解放及其限度——以赵树理小说为个案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孟祥英成为边区劳动英雄之后,开始有了翻身做主人的感觉,不过这并没有改变她在家庭中的地位,更无从改变婆婆和丈夫的观念,受限于边区政策,成为劳动英雄后离婚更难。贺桂梅通过这个案例反思“四三决定”的妇女发展方向,指出“这就显示出女性通过劳动生产而在父权制度家庭内部获得主导权的‘边界’所在”(5)参见贺桂梅:《人民文艺中的婚姻家庭叙事与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3期;贺桂梅:《“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问题的历史思考》,载《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研究反思的是“四三决定”的边界、限度,并不是否认劳动生产之于妇女解放的意义,因此也出现越来越多具有平衡感的论述,如董丽敏通过梳理延安妇女政策的变迁,指出“通过‘生产’这一社会化的方式,为支撑战时的家庭经济/社会经济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既在家庭内部取得了可以与父权制进行性别协商的机会与空间,同时也在此过程中建构了自己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位置并锻造了通往解放之路的能力”[7]。这篇文章的重点落在家庭内部的协商,参与生产劳动毕竟赋予了女性与父权制抗衡的机会与空间。这些研究都不以静态的眼光来看待矛盾的不可调和(如现实中的孟祥英选择离婚),期待劳动生产能够毕其功于一役解决妇女解放的问题,而是历史地、辩证地检视孟祥英的突破与困境,贴近历史语境来把握政策与实践中的冲突、磨合并不断发展的过程。
这些基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其着眼点与其说是性别视角,不如说是中国革命进程的历史特殊性。20世纪40年代延安出现的围绕妇女参加生产而产生的家庭与生产矛盾,究其根本,并不是公共领域与家庭领域的社会分工层面的矛盾,而是“新观念”与“老规程”的冲突,这也是当时的革命文艺作品已然充分意识到并呈现出来的。与《漳河水》的叙事时间一样,《孟祥英翻身》也并没有选取现代时间——比如以孟祥英翻身做“人”——作为起点来讲述她的故事。《戎冠秀》采用了这样的方式,以“英雄母亲”的身份回溯、重构了戎冠秀的一生。赵树理在小说开头就将时间推远,“这地方是个山野地方,从前人们说,‘山高皇帝远’,现在也可以说是‘山高政府远’吧,离区公所还有四五十里。为这个原因,这里的风俗还和前清光绪年间差不多;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8](P195)。小说的叙事时间起点不是孟祥英的生命时间,但同时它又确实是如“孟祥英”这样千百个受欺凌的媳妇的集体生命时间。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不是将这个风俗作为“旧事”来描写,它是当下仍然存在的封建陋习——“山高政府远”,赵树理模糊了具体的时间,这个四五十里外的“区公所”也许是国民政府,也许是边区政府。对于孟祥英的人生来说,决定性的新/旧转换不是“五四”,也不是抗战,而是参与生产劳动,是“四三决定”之后的边区环境。即便这是有限度的,它也使得孟祥英翻身做人了。赵树理不仅是在小说内容层面呈现了这个限度,在叙事层面也有着充分的自觉,他从“孟祥英”们的生命经验入手,以边区在生产、民主政治层面的变化作为她们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环节,并为小说保留了开放式结局。这个形式设定中暗示着妇女的生命历程与政治进程的交汇与分歧,妇女解放之路虽然依托于外在的政治变动为条件,然而它始终是一个不曾失去其自身主动性的持续努力的进程。
从写作时间上看,《漳河水》(1950)晚于《孟祥英翻身》(1945),它的故事时间也要晚,一个是边区劳动英模会时期,一个是“土改”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在情节上有连续性,边区大生产时期推动形成的劳动互助组继续支持了荷荷成长为劳动带头人。荷荷、苓苓、紫金英在婚姻家庭中的经历可以看作孟祥英困境的三个变奏:荷荷离婚重组家庭,苓苓教育丈夫争取家庭内平等,紫金英参与互助组劳动不再嫁。社会变革中价值观的转变往往首先体现在婚恋中标准的变化,荷荷离婚后选择丈夫时这样选:“自由要自由个好成分,荷荷待见的是庄稼人;自由要自由个好劳动,荷荷待见的是新英雄;自由要自由个好政治,能给群众办好事。”[4]在荷荷的例子中,一方面,男女双方都认同新价值观,它可以说是自由恋爱,“针连线,线连针,自由的对象恩爱深”[4];另一方面,荷荷的再婚家庭依据边区生产和革命战争的需要形成了新的内/外模式:“男人前方运军粮,妇女保证地不荒。七人小组自由碰,荷荷当了领导人。”[4]荷荷走出旧家庭当了互助组的领导人,而新家庭是内在于革命分工的小家庭。荷荷的例子是相对理想的状态,它支持了“四三决定”作为妇女解放新方向的可能性。在苓苓的婚姻中,被“妇女不劳动”的旧观念绊住的是丈夫二老怪。而在紫金英的例子中,被“寡妇”的旧观念绊住的是紫金英自己。三个人的故事是就同一个问题给出的三条不同出路,《漳河水》并没有都写成美满的结局。不过,三个故事中有一个共同点:劳动生产不仅是作为女性摆脱封建观念桎梏、自我赋权的实践之路,也作为一种价值观投射到男性身上,作为挑选丈夫、改造丈夫的标准,可以说,在当时的边区通过“劳动英雄”等机制,劳动生产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内化为个人的自我认同。
苓苓的故事,与其说是以苓苓为中心,不如说是以丈夫二老怪为中心展开。全诗的大部分笔墨,第二章“解放”中的“苓苓”部分和第三章“常青树”都是落在教育、改造“二老怪”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新观念”与“老规矩”的几个回合,这几个回合的发生是在苓苓走出家门、参加互助组之后。此时,村庄里已经开始出现新风尚,“花钱再娶犯法令,自由谁敢上我家门?不准打,也不敢骂,动她根汗毛也犯法!哎呀呀,老规程吃不开,二老怪碰到了新朝代!”[4]这个“新朝代”仍停留在村子层面,还没有到家庭内部。二老怪不赞成苓苓出门劳动,威胁要“写休书”:
苓苓抿嘴微微笑:“你要休我没条件!俺又不知道你今天回,上地劳动也有罪?”
“猫捉老鼠狗看门,锅台炉边才是女人营生!客马也想上大阵?不准上我地瞎闹腾。”[4]
第一个回合发生在苓苓与二老怪之间,“上地劳动也有罪?”的新观念说服不了二老怪的老规程“锅台炉边才是女人营生”。不过,老规程也约束不了新观念。老规程不仅是观念,它伴随着家庭暴力和生产资料权(“不准上我地瞎闹腾”),新朝代的法令禁止老规程中的打骂行为,也给了苓苓在劳动生产光荣之外更多的革命道理,这里带出了劳动生产的第二层含义——算账:
“土地证上俺两人有份。”“别吃我饭你另支锅,明天咱就各自过!”“后天另过也不忙,还得跟你算算帐(账):去年穿俺五对鞋,一对就按五工折,两身布衫一身棉,至少不算个十万元?去年俺织了十个布,一个值钱两万五。卖了俺布买驴回,草驴该俺有三条腿。洗衣做饭都是我动,一年算三月九十个工。男女平等讲民主,谁不民主就找政府。”[4]
经过“土改”,女性也拥有了土地所有权,这从制度上消除了二老怪的“上我地瞎闹腾”的旧观念基础。苓苓与二老怪的“算账”,不同于贫雇农与地主论理“谁养活谁”,贫雇农的算账指向经济剥削和阶级斗争,苓苓的算账是为了使家务劳动变得量化、可见,以劳动价值意义上的平等反驳老规程中的家庭内部分工的不平等。家庭关系不同于贫农与地主的关系,家务劳动的分工上也许不可能完全达到实质平等,然而尊重和情谊能够稍微弥补这一点。苓苓要的不是离婚,而是家庭内部的平等。算账虽然能够使得妇女对于家庭的贡献变得可见,能够逼得二老怪哑口无言,但经济平等未必能保证家庭美满。《漳河水》中在“苓苓”的故事结尾这样写道:
封建社会能糟蹋人,胡捏出来套老规程:“母猪不敬神,女人不算人,养孩儿抱蛋,洗衣裳做饭,”不想想俺们是占一半,盖房要靠柱和梁!不想想男女是心连肝,谁离开谁都没时光![4]
这一段唱中传递的是对于家庭关系、夫妻关系融为一体的认识,家庭不仅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意义上的最小生产单位,也是伦理意义上身心安顿之所。近代农村社会中家庭内部的关系已然被深重地裹挟进社会大环境的剥削和压迫关系中,这从女性的处境看尤为明显,这一段唱有着鲜明的性别视角和反抗意识,这是孟祥英的“哭”“自杀”中无法明说的“理”。黄锐杰分析孟祥英的例子时指出:“旧家庭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非源于差等秩序的‘专制’,而在于这种严格的差等秩序背后有‘理’,这是老规矩的‘规矩’一词揭示的。这种家庭内部的差等秩序以‘爱、慈、孝’等基本家庭伦理为家庭正义的核心……孟祥英为什么要哭,要自杀?因为她‘从小当过家,遇了事好说理,不愿意马马虎虎吃婆婆的亏’。自杀对于她而言是一种寻求家庭正义的基本手段。……自杀这一极端手段将‘理’背后的情感诉求彰显了出来——‘满理的事,头上顶个血窟窿,也没人给说句公道话’。老规矩的真正变异在于‘理’背后的‘情’已经不再能发挥作用,‘情’成了私情,不再是连接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这时候的‘理’必须求变。”[9]孟祥英与《漳河水》中三个姑娘所处的是同一个时代境况,从前有“理”作为支撑的家庭内部差等秩序日渐失衡,变成“爹娘盘算的是银和金”,变成丈夫奴役打骂是常态,“女人不是人”。孟祥英和荷荷、苓苓村外的大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难道恢复了旧有差等秩序的“理”,就是孟祥英想要的吗?或许可以不自杀,但是离“女人也是人”还很远。换言之,并不是“四三决定”鼓励妇女参加生产之后才对边区家庭形态产生威胁,而是家庭关系早已崩坏。事实是,正是妇女因为参加生产得以翻身,才挽救了家庭形态中的“一半”。如果“四三决定”有历史局限性,那么这也是在朝向妇女解放的进程中的局限性,它的限度是劳动生产能够使孟祥英、苓苓在公共领域翻身做主,但暂时还不能使其在家庭内部也得到尊重和爱戴。“四三决定”中想要兼顾生产和家庭,固然有因应边区现状而做出的妥协,但这不也是孟祥英和苓苓内心对于新生活的向往吗?孟祥英最后选择离婚,是因为无法改变丈夫和婆婆的旧观念,这与其说是家庭与生产的矛盾,不如反过来理解,她依然相信翻身生产带给她的力量和价值感,要靠自己的双手继续努力,为自己挣得一个重建家庭的可能性。
对比而言,孟祥英的故事与荷荷的故事相近,与苓苓的故事不同。孟祥英得到的支持来自革命队伍中的女干部,她被拔擢为“劳动英雄”,“正月,大家选她为劳动英雄,来参加专署召开的劳动英雄大会。会后她回去路过太仓村,太仓妇救会主任要她讲领导妇女的经验,她说:‘遇事要讲明道理,亲自动手领着干,自己先来作模范’”[8](P209),由自己生产渡荒发展成为村里公共事务的公家人。这与《漳河水》中荷荷的位置类似,她帮助苓苓改造二老怪,鼓励紫金英摆脱怯懦、自怨自艾的状态,荷荷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不仅在于她们的姐妹情谊,而是因为有了互助组。1943-1945年前后边区互助活动蓬勃发展,从组织生产的角度看,延安时期互助组采用的是变工、扎工等基于亲戚、朋友、邻居关系的劳动互助形式,家庭是互助模式中生产和核算的基本单位。互助组的意义不仅使农村的生产模式发生变化,正如毛泽东1943年11月26日在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和生产展览会上所作《组织起来》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互助组同时推动乡村社会政治关系和农民生活、观念在不同层面发生了变化。苓苓得到了荷荷、互助组姐妹的支持,她们的力量和想法都参与到苓苓教育说服二老怪的过程中,与妇救会主任带动孟祥英相比,荷荷带动苓苓是内化于村庄中的力量。在《漳河水》中,劳动互助组既是一个未充分命名的姐妹群体,也是新生成的社会关系,它是依托于生产的组织方式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空间。在互助组中,姐妹情谊不再是私人情谊,她们的“心事”“悄悄话”在革命话语的支持下开始具有了改造现状(教育丈夫)的力量。上文所引“苓苓”故事结尾的那一段唱,不是“苓苓”自己的声音,而是姐妹们的声音,“荷荷的办法灵验快,一夜治服了个二老怪。夜训班要多多地开,姐妹高兴得唱起来”[4]。在《漳河水》第二章中“苓苓”的故事部分,互助组作为女性集体力量、新的社会空间的意味要大过单一的生产组织形态,它推动了新的小家庭的生成。
苓苓与二老怪的家庭与荷荷的再婚家庭稍有不同,它作为劳动生产的基本单位的意义不明显,作为边区新式民主家庭的意味更重。这一点在《漳河水》的第三章“常青树”中表达得尤为明显。从一般的故事讲述而言,从“往日”到“解放”就可以承担起旧社会/新社会的叙事任务,为什么还要加一段“常青树”?“常青树”这一部分“歌颂妇女闹生产以及丈夫‘二老怪’观念的转变”,它的着力点不再在苓苓与二老怪之间,而是扩展到整个村庄。这一部分没有直接歌颂“土改”之后村庄里的新风尚,而是借助“张二嫂”的视角,从这一段旁观的、讽刺的、老年女性的语气,“年时时兴土地改革,今年时兴娘儿们改革,真是了不得!”[4]开始引出一长段唱,讲出村庄仍然普遍存在的偏见。这可以说是改造二老怪过程的第三个回合。这一次与旧观念的对峙既不在家庭内部,也不在男女性别之间,最终成功改造二老怪的是边区民众教育——“二老怪上了夜训班,好似骚骡上了嚼,不敢哼气不敢跳”[4],是新的基层政权力量——“支书批评他不应该,村长说隔天要把会开”,是妇女生产互助组的生产成果,使得他最终心服口服。在这个整体变化中,妇女的互助组不是独立的性别空间,凸显的特征不是性别身份,而是平等观念。在这个氛围中,荷荷不会因为离婚再嫁受到歧视,新社会中她的才华被看到,“工作好,有能耐,要表有表才有才,谁不喜,谁不爱?”[4]紫金英不会自伤于寡妇的坏声名,勇敢地独立生活。《漳河水》将转变的最后情节设定为二老怪的自我反省与向苓苓“赔情”:
“把我编歌写成戏,登报批评我都愿意。咱的脑筋有封建,哥儿们姐儿们多提意见!”
“男女本是连命根,离开谁也万不能。去给苓苓陪(赔)个情!”荷荷笑着下命令。
举手额前脚立正,二老怪今天像个民兵。苓苓捂嘴低声啐:“出什么洋相讨厌鬼!”
“出什么洋相讨厌鬼!”孩子们学着苓苓嘴。人人都笑出欢喜泪,惹来山雀转圈飞。[4](PP147-148)
这个情节中可阐释的地方很多,比如用民兵来形容改造好的二老怪,下命令的是荷荷,围观的是孩子们而不是老人们,等等。不过更为核心的是二老怪向苓苓“赔情”,这是孟祥英在旧家庭的“理”的秩序框架内要不出的情分。苓苓的参加生产、说理,最后抵达了“情”,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说是对于“四三决定”的另外一个注脚。《漳河水》留下了一个比《孟祥英翻身》更明朗的结局。这是作者的乐观,还是为了歌颂边区而对家庭与生产的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
苓苓的故事中给出了边区政权、劳动生产、民众教育等合力改造二老怪的一系列过程,如果没有村庄中的整体变迁,“赔情”的情节即便写出来,仍然可能是陈旧的套路,可能是私人空间中夫妻关系的想象性翻转,是偶然的个例,读起来受鼓舞但仍不觉得可信。这些情节来自延安时期行之有效的实践[10],来自阮章竞1949年回太行参加妇女工作会的见闻:“是妇女互助组唱的,她们在歌唱自己的翻身,歌唱自己的劳动,歌唱自己的快乐……自从听了歌声以后,萦绕脑中。找人口述,录下些片断(段)的歌儿,自己又模仿着编了些,组织成现在的样子。三个女主人公到底是哪个村的,没打听出来。群众说好多村都有这样的故事和大同小异的歌儿。”[4](P101)《漳河水》并不直接取材于真人真事,但它来自阮章竞与太行人民十多年的革命经验,来自太行山剧团中在一次又一次的剧本创作中所积淀起来的认知和感觉。荷荷、苓苓、紫金英不是天生的革命者,但战争与革命的酷烈程度既磨炼了边区人民,使他们变得勇敢、智慧,也重新锻造了文学创作过程。仍然需要再一次强调,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此处的“真实”,并不尽然是修辞和情节上的严格符合真人真事,它指向的是创作与革命进程的血肉相连。作为延安时期革命文艺创作的总体性特征,它的内涵远远不同于文学理论中用于表述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诸多范畴,如再现、摹仿或寓言。作者的积淀赋予了叙事诗基本的情节架构和人物性格,并且因民歌善于言志、直抒胸臆的方式优于小说的第三人称讲述,使得人物性格更为凸显,更具感染力。《漳河水》中三个女性的故事,不是对现实处境的美化或者想象性解决,而是延安的历史实践与叙事实践中结出来的果实,是有生命力的“常青树”。
三、女性解放故事就是革命故事
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边区革命文艺实践的整体氛围中,女性力量与主动性是相对普遍的现象,而“喜儿”形象中的被动性则相对要少。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农民为对象的革命文学作品相对照,40年代经历了全民族的抗日动员之后,革命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和他们展现出来的力量逐渐增强,并且很少引发暴力、非理性等负面阅读效果,而是作为中华民族新生的力量被认知。《漳河水》仍然是不同的,在情节上它并没有直接触及阶级压迫与革命反抗,它的女性形象也并不是最具反抗精神的。新出版的《阮章竞文存》中收录了作者的一句话:“也许有人以为诗中没有写到荷荷等三人在旧社会中反抗的行动,是一个缺点。”[4](P149)这句话没有标注时间,也没有解释原因。推测来看,应该不会太晚。《漳河水》于1949年3月完成初稿,12月改定,而后发表于《人民文学》,也就是此后的通行版本。在这段不短的修改时期中,他应该也看过《白毛女》,但依然保留了这样的写法。谢冕在《中国新诗总系·50年代卷》中收入了《漳河水》的全文,除称赞其艺术上“把新诗写作的民族化,推向一个成熟的、经典化的高度”外,尤其指出“要说革命是狂风骤雨式的,但阮章竞先生所表现的革命的胜利,是更深刻的、更深邃的,那是钻入人心的,……那三个女性的对立面,那几个男人,他们带有旧时代的一种被奴役,受创伤,求解放这个痕迹的。所以阮先生他笔下这些长诗所展现的,是革命带来更深刻,更内在的成果:那就是人的改变,人的命运的改变”[11],这是有洞见的评论,应该也是切合作者心意的知己之言吧。
是否将女性形象写得更具主动性、反抗性,以及怎么样才算是写出反抗性,并不仅仅是写作技法问题,甚至也并不仅仅是性别问题。女性形象的主动还是被动,正如同文学叙事中农民形象的主动与被动,它指向的是对于共产党革命中党群关系的理解。对于阮章竞来说,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农民形象源自他的历史经验与认知。让我们再次回到《漳河水》诗前“小序”:
太行山——我的第二故乡,太行山的人民和全华北人民一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自己,并和自己的子弟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从自己的家门口,先打走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又打走了一个美蒋匪帮军队,建立起一块自由幸福的新天地。太行山的妇女,过去在封建传统、俗习的野蛮压迫下,受到了重重的灾难。但随着抗日战争,减租减息,解放战争,土地改革,这两个时期的伟大斗争,她们获得了自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10多年来,她们忍受着难以设想的重负,支持人民解放事业;并不断地和封建传统习俗作斗争。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生产,获得妇女彻底的自由解放。她们的丰功伟业,在祖国解放的史诗中,占着光荣的一页。[4]
这一段表述中,读来最为鲜明的印象是主语清晰,“太行山的人民”“太行山的妇女”,句式中主动性强,“解放了自己”“和自己的子弟兵”,“获得了自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它没有使用常见的客观化的表述,妇女的参与革命也并不是被表述为“伟大斗争”的附带性后果,而是被认知为自我解放的“丰功伟业”。这是阮章竞对党的领导、对妇女解放一以贯之的理解。“领导”的另一面并不是单纯的“被领导”,这个关系之中有强制与服从,但并不抹杀农民、妇女群体的主动性。在创作《漳河水》之前,阮章竞写过不少女性人物。1942年《姜四娘》写的是日军扫荡太行山时牺牲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日军“抉剔清剿”来到武乡县胡蛮岭,姜四娘被俘,没有透露八路军任何消息,最后饿死在山上。这首短歌只剩下一些零散的段落:“胡蛮岭,姜四娘,挺立高岩腰不弯。”1963年重访太行时,作者追忆起姜四娘,从乡亲们记忆的一些段落中,补全了这首诗,并补跋:“追忆下这首诗,以缅怀姜四娘那样,许许多多宁死不屈又没有留下名字的太行山普通农家妇女。”[4](P18)这首诗清晰地表明了阮章竞对于抗战中女性的态度——是赞颂,不是同情。她们确实是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姜四娘”们没有丰功伟绩,她们沉默,没有名字,没有声音,而战争的局势不容任何人旁观、等待被拯救,她们后来组织起来,前线后方都有她们的默默付出。她们绝不仅是被拯救者,她们是反抗战争的重要力量。
这也不仅仅是《漳河水》单一作品的态度,而是那一时期文艺作品的整体基调。田间于1945年写作的长诗《戎冠秀》中有这样一段:“老人好比一盏灯,八路军给她火,她亮了,她又照八路军。”[12](P2)诗中以“灯”/“火”来形容戎冠秀与八路军之间的关系。这一比喻要比“军民鱼水情”中表述的子弟兵与革命母亲的关系更多了一层意思,戎冠秀老人原本就是一盏灯,她不是被动的蒙昧者。不难发现这一比喻对于启蒙与被启蒙关系的改写。这一共同基调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赞颂党的领导,而是一种历史认知,理解个别的群体的改变,要从党与人民的关系、从社会关系的改变(即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的脉络来把握,党与群众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关系,只有放置在具体实际的事情之中才能够获得更为具象化的理解。与此相应,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人物的主动性、力量感反过来佐证社会关系的巨变,以及准确地理解共产党的一些表述、提法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新意。从这个角度来看,妇女或者农民群体的“主动性”需要越写越实,从边区的新事、从关系中获得具体的支撑。《漳河水》虽然没直接写阶级斗争和大的政治事件,但它恰恰是从妇女地位和认知的转变过程的真实性抵达了社会革命最深层的脉动。女性的解放不以外在的观念为衡量尺度,在它自身的意义上,每一步小小的推进都镌刻着反抗,它在情感、经验层面的复杂层次,不能全然在主导的革命叙事路径中获得充分表达。那些最激烈的挣扎甚至是无声的,正如同《漳河水》中阮章竞在“紫金英重新再做人”这一句前面写道:“天没雨,地无风,清明没来为甚春雷动?”[4]女性解放的故事就是革命故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