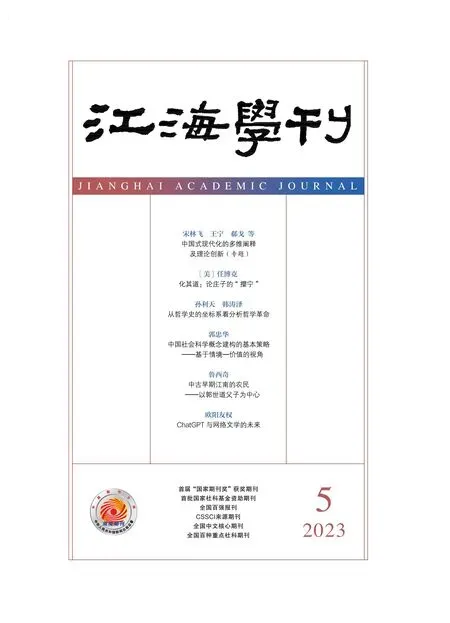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双重进路与未来愿景
王 宁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语境中的一个全新命题,同时也是全球现代性大语境中的一个全新命题。当然,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必然,现在提出这一命题可谓恰逢其时。但是这个命题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有着广博的国际理论资源和深厚的本土积淀。中国式现代化涉及方方面面,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文化,无所不包,这就得追溯到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形成。此外,中国式现代化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全球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中国式现代化更具有中国本土的特色,它与现代性在中国的诞生以及中国现代性的本土特色有密切的关系。虽然现代性这个概念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现代化也是率先在欧美国家实现的,但是现代性一经进入中国,也如同其他西方引进的概念一样,与中国的本土因素发生碰撞进而交融,最终产生出一种新的变体,也即所谓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在这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因而中国的现代性中掺杂着儒学的因素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主要从文化现代性的视角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儒学的传承和在新的全球语境中的重构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脉络,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中国的现代性和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特色。
旅行的现代性:从西方到中国
笔者在过去讨论现代性及其在中国的不同形式的著述中,始终将其界定为“翻译过来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并在涉及中国的现代性时使用了复数的现代性(modernities)形式,(1)我的一本英文专著的题目就用了复数的现代性,参见Wang Ning, Translated Modernities: 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Ottawa and New York: Legas Publishing, 2010。其意在说明,并不存在所谓大一统的“单一的现代性”,尽管我们可以将全球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统称为总体的单数的现代性,但由于各民族/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现代性的形式也就各有千秋,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如中国的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性也有着很大的差别,(2)这方面可参见拙作《全球化进程中城市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北京民俗论丛》2013年第1辑;《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上海摩登(现代性)和上海后现代性》,《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8期;以及英文论文“From Shanghai Modern to Shanghai Postmodern: A Cosmopolitan View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elos, Vol.180, 2017, pp.87-103。因此用复数的现代性来描述其在不同民族、国家甚至地区的形态是十分恰当的。
由于现代性作为一个旅行的概念,从西方出发并旅行到世界各地,期间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产生出不同的变体,这样便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带有本土特色的复数的现代性。这便使我想起美国已故的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的著名概念“理论的旅行”(traveling theory)。他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论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评家》(TheWorld,theTextandtheCritic, 1983)收入了他的一篇著名论文——《旅行中的理论》(Traveling Theory)。这篇文章最初于1982年发表于《拉利坦季刊》(RaritanQuarterly),后收入论文集。赛义德在文中试图通过卢卡奇的“物化”(reification)理论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翻译和传播以及由此而引来的种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理论有时可以“旅行”到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地方,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原初的那种理论会失去某些原有的力量和叛逆性,并产生出一些新的变体。因此,按照赛义德的描述,这种旅行便呈现出四种形式:
首先,它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整套起始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念才得以产生或进入话语之中。其次,有一段需要穿行的距离,也即一个穿越各种语境压力的通道,因为观念从早先的起点移向后面的时间和地点,使其重要性再度显示出来。第三,还须有一系列条件,我们可以称之为接受条件或作为接受所不可避免的部分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得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类,最终都能被引进或包容。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包容或吸纳进来的观念因其在新的时间和地点的新的位置和新的用法而受到某种程度的转化。(3)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226-227.
这就表明,赛义德试图赋予其“理论的旅行”之概念以某种普适的意义。某种理论概念,例如赛义德自己建构出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作为一个原创的概念旅行到世界各地,在这一过程中它产生出若干个变体形式,一方面使原有的理论概念为更多的人所分享,另一方面则通过该理论概念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的接受丰富它本身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是如此:在苏联的传播与当地的环境相融合进而产生了具有苏俄特色的列宁主义,在中国则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西方被称为毛主义,Maoism)。若将其运用于中国现代性的形成,我们大概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乃至现代汉语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种西方文化理论思潮通过翻译旅行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本土元素相交织融合的一个产物。由此可见,“理论的旅行”这一论点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赛义德对此虽十分明白,但仍想在适当的时候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加以修正和发挥。他在2000年出版的论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中收入了写于1994年的一篇论文《理论的旅行重新思考》(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在这篇论文中,他强调了卢卡奇的理论对阿多诺的启迪,接着指出了它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关系,其中介就是当代后殖民批评的先驱弗朗兹·法农。(4)Edward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51.可以说,赛义德本人以东方主义文化批判为核心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在第三世界,尤其是在中国产生的共鸣和反响证明了他的这种“理论的旅行”说的有效性,(5)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参见生安锋:《理论的旅行与变异: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文学理论前沿》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164页。同时也影响了后来的学者对现代性的研究。
无独有偶,和赛义德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共事的华裔文学研究者王德威也对现代性问题情有独钟,并在讨论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现代性时,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按照王德威的看法,长期以来人们所认为的中国现代性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实际上可以再往前推至19世纪后期的晚清,因此现代性在中国的语境中是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6)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虽然王德威的这一看法引来了诸多争议,但至少能够自圆其说,并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认可。可见学界对现代性在中国的发轫还是有不同看法的,而且现代性在中国的不同地区确实也有着不同的形式。
笔者通过西方文化译介到中国这一视角来考察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现代性生成,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五四时期的话,那么在此之前,现代性就已经通过世纪之交的大规模翻译西学的运动进入了中国,大量西方文化理论和文学作品通过翻译蜂拥而入,对既定的文化格局以及语言表达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客观上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奠定了语言文化基础。因此,将中国的现代性发轫期推至上一个世纪之交还是可以说得通的。就文学艺术而言,曾经占据19世纪西方文学艺术主流的现实主义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崛起于19世纪下半叶的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和流派形成强有力的潮流,并开始逐步向世界其他地方旅行。随着19世纪后半叶中国国门被洞开、清王朝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后的崩溃和走向共和运动的高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艰难启动。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起始正是从封建帝国向民国过渡的时期。
儒学的旅行与新儒学的重构
客观地说来,现代性的引进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启动,使传统儒学首当其冲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是任何文化上的变革都不可能全然摒弃其早先的传统,而应该是一种扬弃。由于儒学的巨大影响,不少人往往会将其混同于传统中国文化。确实,儒学一般指儒家的文化和思想,有时甚至被当作一种宗教教义,也即被称为“儒教”。儒学同时也专指以孔子为代表并得到每一代哲人传承的一门学问,在古代一直流行并占主导地位,但在新文化运动(1915—1923)期间受到严厉的批判。在这场运动中,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钱玄同、李大钊等重要思想家和学者发起了“反传统、反儒学、反古文”的思想文化运动,试图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可以说,儒家学说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经历了曲折多变的发展历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甚至被认为是反对中国文化现代性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一股力量,因而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批判。诚然,与另一个重要而有影响力的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学说——道家学说相比,儒学更接近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无论是儒家还是新儒家,都主张积极地参与社会改革,干预政治,治理国家。相比之下,道家学说则在观察社会变革和动荡时,态度冷漠,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享受自己的生活,而不干预社会改革和治理国家。此外,儒家思想还以其封建思想和男性中心主义倾向而闻名,因而儒家思想并不受女性欢迎。根据儒家的思想教义,中国女性更应该恪守封建礼教所规定的“三纲”“五常”,这是封建道德行为的主要原则,任何违反这一原则的女性都将受到惩罚。因此,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长期受到女性的挑战和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学的这一教义尤其受到男女知识分子的批判。
因此,人们很可能会感兴趣的一点便是传统儒学与新儒学的差别。首先,传统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中庸之道”,也就是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事态度。因此,儒家思想的主要宗旨是仁义,即以义、仁、孝治国,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由孔子的弟子们发展并总结出来的,同时也指随后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逐步发展起来的教义。这种思想体系是由孔子创立的,孔子将其描述为自我修养,注重与周围的人建立和谐的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便表达了对整个人类的关怀。因此,儒家的核心理念要求个人注重修养并具有治理家庭的能力。当然,中庸之道并非意味着什么都不做,而是一种把握阴阳的大智慧,它特别强调处理人事和世俗事务的灵活性。既然一个人不能同时掌握整体,那么达到中间就可以了。它就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仁慈是一种平衡心灵的方式。它还试图平衡家庭和社会问题,也即一个卓越的领导者还应该具有保持他家庭关系和谐等良好的品质和美德。在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时,应该找到各方的共同点,这样便能使每个国家都能在不损害其他国家或民族利益的情况下受益。诚然,儒学并没有给个人主义留下任何空间,因此,在考虑个人和社会利益的新儒学那里,它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节制。儒家学说是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学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代表在海内外得到发扬光大。因而毫不奇怪,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基本要义就在于坚持尊重他人,特别是尊重老人、照顾弱势群体的立法原则,坚持“礼”,倡导“以德治国”,重视“以仁治国”。因此,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长期以来被封建统治者们奉为正统。在儒家占据上风的时期,其他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如道家思想等,则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人们谈论中国传统文化时,便不能不想到儒家思想,因为儒学确实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精髓。
儒学中的“礼”是其核心要义,其基本含义有较大的张力,因而使得不同的人对“礼”的理解或定义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自己所属的行为规范,因此,在传统社会时期,国家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性。人们很可能会认为儒学反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在受到西方发展模式影响的新文化运动期间受到强有力抨击的原因。儒家的“礼”也是法的一种形式,这是基于对父权等级制度的维护,任何人违反了“礼仪”规范,都将受到惩罚。当然,后来儒学由于过分强调等级制度,这一规范便得到新儒家的调和。
儒家主张“德治”,这一理论主张体现在以仁为基础的道德应该用来影响和教育人。儒学认为,无论人性如何,都可以根据善的标准来影响和教育人们。这种教育方法会带来心理转变,使人们的心灵变得更为善良,比如,消除自私或利己的心态,知耻而无恶灵。这是最彻底、最基本、最积极的方法,可以采取道德制裁。儒家的“以德治人”思想体现在重视观念,它认为人是可变的,可以对“人”的主动性和伦理道德进行管理。因为传统儒学认为“人格”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此基础上,进而发展成为极端的“人治”,如“政治人”“人治,无法治”等。由于儒家格外强调人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呼吁出现善良的、德高望重的统治者,也即所谓的“青天”或“清官”。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1893—1988)以“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著称。他自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八版自序中承认,“这书的思想差不多是归宗儒家,所以其中关于儒家的说明自属重要”。(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页。可见他创造性地将孔子等儒家学说与西方哲学融为一体,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此外,他对现代世界文化也有总体的把握,将其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和印度文化均有别,比较持中。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应该是人类文化最终的理想归宿:“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75页。对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他却颇不以为然,并且不无讥讽地指出:“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那只有如我现在所说可以当得起。”(9)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88页。虽然梁漱溟是本土产生的新儒家,但在海外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在海外中国学者林毓生(Yu-sheng Lin, 1934—2022)看来,梁漱溟应与鲁迅并列为“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10)卫小溪:《问题中人梁漱溟》,《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10月17日。确实,梁漱溟不仅有自己的思想理论,同时也注重实践,试图在实践中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并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11)参见《两个儿子深情回忆:“问题中人”梁漱溟》,《广州日报》2006年1月2日。另一些新儒家,如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新儒家在当代的复兴作出了贡献。
不可否认,儒学在现代中国经过曲折的道路之后,得到了近几代中国领导人的认可并发扬光大。国外的不少人认为,中国政府决定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数百个孔子学院,不仅旨在恢复传统的儒学,更在于推广中国的思想文化,因此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的尝试首先受到西方国家的抵制,它们认为这是在帮助中国政府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思想。其实在我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从孔子学院的组成人员来看,它建立的初衷并非如此。(12)孔子学院的任务一般有这样两个:其一是在国外教外国人学汉语,承担这一工作的主要是一些刚刚毕业的对外汉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或志愿者;其二则是不定期地邀请资深文化学者用英语或其他主要外国语言讲授中国文化和思想。笔者有幸应邀在欧美和拉丁美洲多所大学的孔子学院就中国文学和文化发表演讲。“孔子”在这里只不过是传统中国语言文化的一个象征性符号,他的教义早在五四时期就受到过猛烈的批判,其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更为激烈的“口诛笔伐”,其原因在于它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反现代性的话语力量。在当代中国,我们首先要看这种信念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并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样看来,传统的儒学在当今的复兴正好与党和政府建立和谐社会的既定国策相吻合。但是儒学在当代中国绝不只是简单的“复活”,而更应当得到新的理论阐释和扬弃,从而经历某种程度的“变形”:弘扬其人文主义的教义,摈弃其陈腐和封建保守的传统。因此,有选择地并批判地“复兴”传统儒学的伦理价值观念在当今时代是十分有益的,而在全球化时代重建一种新的后现代新儒学话语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新儒学的巨大影响早已超越了中国乃至中华文化传统的疆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话语。在这方面,杜维明、成中英、牟宗三等海外华裔知识分子进行了长期的不懈努力和尝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仅强调指出仍然健在的两位海外新儒家为推进儒学在当代的复兴所作出的贡献。
杜维明这位已在中国定居的新儒学大师不仅经常在国内各主要高校发表演讲,而且还在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接受采访,以便向更广大的电视观众宣讲新儒学的教义,他的努力不仅使新儒学具有了广泛的普及性,同时也使其得以与那些已经被新一代中国青年广泛接受的西方文化理论和道德准则共存和互补。既然后现代主义和新儒学都具有解构性,也即既消解了现代性的整体和专断性话语的权威,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具有东方和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那么这二者完全可以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层面上进行有效的互补和对话。
毫无疑问,在众多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中,杜维明的影响力最大,同时也最为广泛。他本人对后现代主义也颇有兴趣,(13)1998年3月,我应傅高义(Ezra F. Vogel,1930—2020)先生邀请,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演讲后杜维明教授专门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交谈,其间他建议我从后现代的理论视角研究一下新儒学,并送给我他的两本中英文专著。我读后深受启发,写了一篇英文论文,先是在学术会议上宣读,后来又应成中英教授邀请,为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季刊》编辑一个关于后现代与新儒学的主题专辑,我的文章就被收录在该专辑中,参见拙作“Reconstructing (Neo)Confucianism in ‘Glocal’ Postmodern Culture Context”,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37, No.1, 2010, pp.48-61。在此特向两位海外新儒学大师致谢。在他看来,我们并不需要从传统儒学中汲取直接参与政治的精神,而更重要的是其人文精神,因为当代新儒学所召唤的是“具备一种更为深沉的人文主义视野,而非像人们所广泛设想的那样,仅仅适应于政治上的参与。儒学为其自身的发展和人类社群理想的实现而具有的象征性资源,不仅体现于政治上,同时也体现于宗教伦理上。实际上,他们对‘政治’的感觉不仅体现于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来管理世界,而且也在教育和文化意义上改造世界的同时促使其政治领导地位扎根于社会良知中。儒学知识分子也许并不积极地寻求官职来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但他们始终通过其诗学的敏感性、社会的责任性、历史的意识以及形而上的洞见在政治上积极地介入对现实的变革。”(14)Tu Wei-ming, Way, Learning, and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fucian Intellectua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reface”, pp.ix-x.杜维明本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近十多年来奔波于中美两国之间,为在海内外普及儒学进而建构一种与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并行的新的普适性理论话语而努力。应该说他的努力尝试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经过改造和扬弃的“新儒学”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学以及其后的宋明理学,而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现代性理论中的“一元”,它既不想征服或涵盖其他话语力量,也无法为别的话语力量所替代。它完全可以作为产生自中国本土并吸收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的新儒学与西方的现代性理论进行平等的对话。
成中英作为另一位著述甚丰并十分活跃的新儒学代表人物,不仅在汉语世界大力推广新儒学,而且还利用自己主编的杂志和丛书,发表他的全球化时代重建新儒学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思维模式,因而更容易与后者相融合并进行对话。他还对当代社会的政治权力与德行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发,在他看来,“对儒学而言,一个人一旦成为统治者或公众的官员,也不应当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德性。倒是与其相反,内在的私有德行常常会变成服务于外在公共社会和政治德行和权力中的个体的基础和灵感的来源。我们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充满美德的儒家哲学完全有可能被看作并实际上作为具有双重方向的民主化的积极中介而发挥作用:成为权力的美德,同时也成为美德的权力”。(15)Chung-ying Cheng, “Preface: the Inner and the Outer for Democracy and Confucian Tradi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34, No.2, 2007, p.154.即领导者要以德治国才能取得成效,因为作为个人来说,应该具有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就如同作家在从事创作时,明知道充满乌托邦的想象不可能实现也偏要发挥非凡的想象力,进而将虚构的故事讲得真实可信。可以说,成中英的研究既保持了传统儒学的积极进取和入世精神,同时也摈弃了其专断的排他性,使之成为一个可供后来者阐释和建构的开放话语体系。
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海外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重新建构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在当前西方社会物欲横流、人文精神备受挑战进而发生危机的时刻,呼唤儒学的复兴并以此将中国文化精神在全世界弘扬,应该是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因此我们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应采取积极的对策。海外新儒学在中国的复兴,除了上述两位华裔学者的贡献外,贝淡宁(Daniel A. Bell)的贡献也不容忽视。贝淡宁是加拿大人,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和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近年来,作为新一批儒学的代表人物,贝淡宁提出了一种“贤能政治”策略,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但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实际上,贝淡宁并不否认西方一人一票制度的优点,也没有否认民主的好处,但他认为,一人一票制度或许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贝淡宁考虑应该如何将民主与尚贤制度结合起来,以便创造一条更适合中国的道路。在他看来,中国有人口多、领土广袤等特性,因而据此制定一种“下层民主,中层实验,高层尚贤”的方式也许是一种特有的中国模式。贝淡宁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他认为,面对民众的支持率不断下降的境况,新加坡政治领袖已经重新将其执政的意识形态描述为“仁慈的贤能政治”。与李光耀不那么谦卑的政治话语相反,现任总理李显龙强调,政治领袖必须谦逊地为人民服务,做正确的事,把事情做好,但永远不要自以为是和傲慢。谦逊也意味着政府并不是对所有问题都有答案。(16)关于贝淡宁的“贤能政治”的讨论,参见徐倩:《贝淡宁的贤能政治思想探析》,《理论观察》2020年第1期。但总之,秉持以德以仁治国对于新儒家来说仍不失为一种策略。
实际上,我们在当今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也可以觅见许多出自儒学的元素,例如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说、“和为贵”的外交策略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等,这也说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海纳百川,可以包容一切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文化,并且尤其注重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正能量。具体说来,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后现代和全球性的视角对传统的儒学进行改造、批判、扬弃并加以重构,使其成为当前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则从全球化时代的新儒学的视角对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进行质疑、批判和改造,从而使得重新建构的后现代新儒学成为世界文明和多元话语共存之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与后者平等对话。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重新继承儒学的优秀传统建构中国文化学术话语无疑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依据。经济的腾飞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不仅要对全球经济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应该为世界文明和新的全球文化格局的形成贡献自己的理论和智慧,但这一切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话语建构
如前所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真正开始启动并取得长足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确立,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曲折过程,即使在改革开放时期也是如此,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好在我们始终有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我们不断地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直至通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成功之路。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也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一种理论学说,在这方面,许多先驱者为之进入中国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李大钊之前,就有熊得山、朱执信等人大力译介马克思著作。后来李大钊在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时加进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但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经过一段时间对中国国情的适应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选择,最终走上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从而生成了一种新的东西,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体体现为毛泽东思想以及后来发展延续下来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因此,与现代性或现代化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概念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的长足发展,也经过了这样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才得以实现,即它必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胜利。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直接的产物。虽然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毛泽东深知,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因此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来进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国文化和文学也不同于苏联的文化和文学,不能完全效法苏联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原则。由于笔者主要从事中西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因此在这一部分,主要梳理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发展历程。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长期以来被国内外学界看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纲领性文献,不仅对于我们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对全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理论思想,它的许多精辟思想在今天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的进程中仍没有过时。在当今强调世界文明互鉴的新形势下,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应该得到发展,才能更为有效地指导新时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这样一种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被赋予其时代特征和本土特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确实也如同从西方引进的其他哲学和文化思潮那样,是一种从西方和俄苏“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译者能动的理解和创造性建构与阐释,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一些中国元素,例如儒学及其他传统中国文化的元素一直渗透在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中。在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中,《讲话》不仅对国内的文学艺术研究起着指导性作用,还对当今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文化建设,尤其是对国外先进文化和文学的借鉴。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十分重视世界文学,对一些欧洲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发表了许多十分精辟的见解,后来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学观,逐步形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这其中也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17)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的详细论述,参见拙作《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前沿》2014年第12辑;《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学术前沿》2020年第21期。作为一个文学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卓越的诗人,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的文学艺术,但是他在号召作家艺术家学习外国的东西的同时,也反对那种不加分析批判地盲目地“全盘西化”的实践。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坚持文学艺术的民族方向,但是他始终不忘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主张洋为中用,推陈出新。(18)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伴随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毛泽东的著述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以及毛泽东思想(在西方被统称为毛主义)的被深入阐释。应该指出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毛泽东的国际声誉及影响已经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可。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整个20世纪,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相比。毛泽东思想不仅影响了阿尔都塞、萨特等法国左翼理论家,即使对波伏娃这样的女权主义思想家也有极大的启迪和影响。(19)这方面参见拙作《启示与建构:法国文学和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French Theori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79, No.3, 2018, pp.249-267。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结构主义理论家和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多年后再次来访中国,在谈到毛泽东以及新中国的成就时,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她于1974年首次访问中国时的观感和对中国的好奇与兴趣。(20)参见尹庆红:《〈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聘任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教授为编委仪式暨学术座谈会纪要》,《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3卷,2010年第2辑。
此外,毛泽东的学说也吸引了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他每次来中国访问讲学,都要设法寻访毛泽东的足迹,以便表达自己对毛泽东本人的敬意。在今天的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毛泽东的崇拜者更是数不胜数。这不仅与他的个人魅力有关,更是因为他的思想和理论对这些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有重要的启迪和影响。
当然,要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性影响,得有具体的数据支撑。几年前,我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期间,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指导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她应我要求专门以毛泽东著作的英译为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并顺利通过了答辩。在广泛深入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中国的所有外译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中,毛泽东著作的外译数量无疑最多,所涉及的语种也最多。据不完全的数据显示,除中国之外已有数十个国家建立了近百家专门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机构。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出版的毛泽东研究论著已达1600多部、论文超过了一万篇。中国的外文出版社也不遗余力地在全世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各种版本,但是大多数毛泽东著作的外译是由国外学者主动发起并承担的。他们之所以关注毛泽东及其著作,主要是为了通过对毛泽东的了解来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进而从中国社会的实践来看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另外根据不完全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共达853种,其中《毛泽东选集》48种,单篇本、文集、汇编本、语录等805种。(21)参见邓海丽:《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英美国家的译介和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1年博士论文。
时至今日,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早先的统计。除了中国外,全世界还有54个国家和地区也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有39个国家和地区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诗词》,全世界有20种文字、35个版本的《毛泽东语录》。这一切都已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世界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并进行研究的一个现象。(22)参见李君如:《毛泽东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国外学者评毛泽东〉(修订版)序》,《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旅行的思想教义,在中国的发展路径是双向的:通过中国接受者的译介和阐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然后通过全世界接受者的译介和阐释又开始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已经成功地被几代领导人继承了下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继承了毛泽东的精神遗产,也都是由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这是我们今天从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和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因此,毛泽东的精神遗产不仅属于中国共产党人,同时也属于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由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建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表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绝不应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和发展的,需要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践来不断地加以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获取的成功经验也对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作出了中国的独特贡献。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当然,毛泽东思想并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方面,邓小平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由于文学艺术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因而也受到他的高度重视。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文学艺术观,强调文艺的人民性。(23)这方面可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编:《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贯穿在历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一系列著作和讲话中。在这方面,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不同的场合都对之有所阐述,他们的思想理论分别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而著称。
在几代中国领导人中,习近平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最为重视,这与他本人谙熟世界文学不无关系。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天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温他的讲话,可以发现这篇讲话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并且更加强调文学艺术的时代特征和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功能,同时也强调了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和民族性,以及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也表达了习近平等新一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将中国的成功经验传播推广到全世界的决心和信心。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将其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如果我们比较这两个讲话,就不难发现,二者都体现了各自所处时代的精神:毛泽东的讲话更强调的是民族性,而习近平的讲话则尤其强调中国文学艺术的国际重要性。
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应当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不仅在全球政治和经济方面应该这样,在文学艺术方面,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也应该有所作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价值和意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艺术观点,也将越来越得到世人的重视。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对全球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贡献也将越来越得到世人的认可。
习近平并没有简单地把文学分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而是将其整体视为世界文学,他不仅关注西方文学,同时也重视东方文学,并在谈到东西方文学的巨大成就时,自觉地将中国的文学看作是世界文学宝库的一部分。这无疑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先进的世界文学理念。在习近平看来,世界文学不仅包括前面提及的那些西方文学艺术大师的作品,东方国家的文学也对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就告诫我们,即使是研究世界文学,对中国学者来说,也应该坚持中国视角和观点,这样才能赢得国际学界的认可。(24)这方面可参见拙作《世界文学研究应有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光明日报》2023年8月30日。
在习近平看来,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的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到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的魅力,从而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2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5月19日。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一致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有58处提到文化,可见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占据的分量是举足轻重的。确实,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中国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在全球文化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应该有何作为呢?毋庸置疑,整个20世纪我们都在致力于引进各种国外的尤其是西方的文化观念和人文学术理论思潮,因而我们的几代人文学者都能够娴熟地运用西方的理论观念和话语阐释中国的现实。而全球化的进程发展到今天,我们更关注的一个焦点已经出现了转向: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何以成功地实现海外传播。这也许是我们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应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