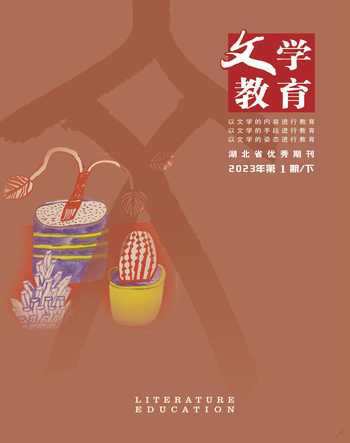比较文学两份经典文献的误读与正解
内容摘要: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上经常被引用的两份经典文献——克罗齐的《比较文学》和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被认为是击中了法国学派的要害,开创了学科发展新局面。实际上,上述文献体现出的中心思想是神学——形而上学对实证主义哲学的敌意,体现出二者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上述文献实际上是站在欧洲传统思想的立场上彻底否定法国学派的思想合法性,彻底否定法国学派的文学研究实践。可以说,我们通常理解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可能实质上是两个学科: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
关键词:克罗齐 韦勒克 《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的危机》
在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上,有两篇经典文献——克罗齐的《比较文学》和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被屡屡提及,它们被认为是击中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要害:误把历史研究的理念与方法运用到文学研究之中。它们还被视为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转折点:美国学派在批判法国学派中拨乱反正,将比较文学拉回文学研究正轨,比较文学因此度过了所谓“第一次危机”,继续向前发展。这听起来很有道理: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定义为“国际文学关系史”,将实证主义历史学的观念与方法运用于“跨界”(跨越国界、国语等)的文学现象研究,只关心作品在社会上流传与接受的各种“外部”事实,没有接触到文学作品的“内部”本质——文学性、审美特性,所以法国学派的研究成果如果不是可有可无的话,那也最多是还算凑合的初级产品,而美国学派则是学科的应该具有的高级形态。实际上,这是对上述两篇经典的误读:克罗齐的《比较文学》看上去谈文学,实际上是在谈历史学;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看上去是在谈比较文学学科发展问题,实际上是在谈文学研究问题,核心主张是否定比较文学提供的文学研究方法。克罗齐的《比较文学》否定了比较文学在历史研究领域内的合法性,韦勒克否定了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合法性:合而言之,法国学派手持历史学研究的门票不能进入文学研究殿堂,甚至连历史学研究殿堂也不能进入。
首先,让我们看看克罗齐的《比较文学》如何否定了比较文学在历史研究领域内的合法性。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是,在1903年刊出的那篇著名的檄文里,身兼历史学家、美学家、文学评论家多重身份的克罗齐其实是在谈论“历史”问题,确切来说,是“比较的”文学史与“总体”文学史的关系问题。他说:“比较的历史是某种与文学史概念不可分割的东西。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文学的比较史应该看成是充分说明文学创作及其全部关系、处理总体文学史的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历史,必须把它与作为它的存在理由的联系和准备工作沟通起来看。”意思似乎是说,历史研究必须是全面研究、整体研究,如果是研究某个作家作品,那就必须将作家作品的前世今生各个方面都考察到,既然如此,号称研究国与国之间文学关系的“比较(文学)史”实际上本来就是“文学史”应该涉及的内容。因此,克罗齐断言:“我看不出单纯的‘文学史与‘比较文学史之间有什么差别”;“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把比较文学变成一个专业。”[1]
需要指出的是,克罗齐看上去是在承认“文学史”概念合法性的基础上否认(应该)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比较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其实不然,他认为文学没有发展史,换言之根本就不存在文学史。克罗齐认为作品与作品之间不能建立“内在的”联系,而内在联系恰恰是“真正的”历史具有而编年史缺乏的东西;换句话说,只有沿着时间轴罗列的文学作品集,不可能有文学史,因为要被称为“历史”,必须显示出诸多事实在时间之流中的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克罗齐赞同以下观点:“在艺术的历史中,不能引入统一和进步,而应以断续的方式视艺术家的作品为宇宙生活中的众多片段”,[2]308“真正历史性的、活的和完备的研究是个别诗歌人物的思想和批判”。[2]112韦勒克将上述观点总结为:“克罗齐完全排斥了撰写一部诗歌演变史的可能性。只有众多诗人存在——人品与作品——而且他们并不形成一个序次,一个环节或系列。克罗齐予以认可的只有专著和文章。文学史继续存在仅仅是由于学人和学者需要博古通今。”[3]326否定“文学史”,是因为克罗齐持“艺术即直觉、直觉即表现”的艺术观。该艺术观以“个性”的不可同约性否定艺术品之间的历史联系。该观点认为,任何一件配得上“艺术(品)”称号的作品都是独创的、个性十足的、独一无二的,因此要在两部作品之间建立联系,称一部作品因另一部作品而产生,或者用一部作品解释另一部作品,诸如此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克罗奇说:“诗歌史的结构(应该)……抛弃文学中的文明史结构,这种外在于诗歌的模式,适宜挤压并歪曲艺术作品,并迫使艺术作品脱离情感与判断,相反(应该)建议另一种建构方法,即审美上个体化的方法,自由地考察作为诗歌的一部又一部作品、一首又一首诗的个性,没有任何一首诗的个性可以完全还原为另一首诗的个性……诗歌史应当这样并且恰恰这样展开,根据其真谛,因此不能同政治、社会、道德或哲学的发展的叙述相连……任何其他(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保守派、革命派或自由派)的模式,无一例外地都外在于诗歌。”[4]115相信文學艺术原则上只有个性没有共性,即使有共性,那共性也不存在于历史之中而在心灵之间,这才是克罗齐拒不承认“比较文学”学科/专业合法性的真正原因。否则,克罗齐就不会认为,“包括考据在内”的“真正的历史的阐说方法”也不过只能在文学杂志上“撑撑市面”而已。
实际上,克罗齐不仅否定了“比较”文学史,否定了文学的“历史”,还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客观的、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历史”。他持一种所谓绝对历史主义的历史观。该历史观认为不存在所谓“客观的”历史,“历史”归根结底是体现在历史编撰过程中的(自由)“思想”。克罗齐说:“历史就是思想……人类真正需要的是在想象中去重现过去,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回到已死的过去”;“真正的历史总是现实的、当代的,它总是为了伦理——政治行动而解释我们当下的处境。”[5]144哲学家梯利将其观点概括如下:“克罗齐解释历史为出现在哲学的历史学家头脑中、关于历史的了解和解释的当前的有创造性的过程。历史不是单纯的关于僵死的过去的事实的再造,而是在对历史过程有创造性和想象的解释的意义上的编撰工作。”[6]659海登·怀特认为,克罗齐之所以对历史持这种看法,是因为作20世纪最初25年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文化的代言人,克罗齐一心想要维护个人主义价值观,所以他将历史呈现为可以无限展示个性的舞台,任何想要寻找客观规律的愿望,以及将人视为社会的人、集体的人的企图都被认为是对人类自由和个性的冒犯,怀特总结说:“克罗齐反对……任何社会科学程序,因为在他看来,这种程序代表着一种用因果关系来决定‘自由精神产物的努力。”[7]577
其次,让我们看看韦勒克如何否定了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合法性。坦率来讲,韦勒克宣读于半个世纪后的《比较文学的危机》存在诸多偏颇。
偏颇之一,韦勒克将比较文学的兴起归因于反对“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学术研究倾向,这是错误的。韦勒克说:“在反对各国文学史进行孤立研究的错误中,比较文学建立了巨大的功绩。”[8]262“比较文学的兴起,是作为对19世纪学术研究中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反动,是对法、德、意、英等国许多文学史家所持的孤立主义的反抗。”[8]265然而法国学派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反对”国别文学史,而是希望“帮助”国别文学史研究。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家“往往依附于本国文学观念的目标”,“地道的比较文学”的位置在“本国文学史旁或后面”,[9]137-138因为国别文学史家都“只能握住联系索的一端”,因此不能不求助于比较文学家;此外,“那些影响的问题往往带到一些本身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作家”,这类作家,国别文学史家“绝对不会注意或绝无机会注意”的。并且当时的国别文学史研究中也没有韦勒克夸大其词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以法国学派代表人物为例,与巴尔登斯贝格并称“法国比较文学研究创立人”的阿扎尔在《书,儿童与成人》中以“笛福征服了法国”作为一节标题,还特别指出:“对于儿童,并不存在思想的海关,对于作者、地域、民族与国家不感兴趣。”[10]183戴克斯特在比较文学第一部博士论文《卢梭与文学的世界主义》的结论部分强调指出,他不同意斯达尔夫人关于“一个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其自然天性,对于外国的模仿无论如何都意味着缺乏爱国主义情怀”的说法,认为该说法极其“轻率”,因为模仿不等于放弃自己,主动向邻居借鉴思想并没有抹杀法国文学的原创性。[11]371-372更为重要的是,比较文学与国别文学研究之间并不存在韦勒克所说的巨大分歧,它们的共性是主要的,即都致力于建设一门学科,一门至少要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科学态度”的文学学科。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从历史中寻求答案,成为一切知识与思考的重要维度;19世纪又是自然科学的权威迅速提高的时代,它带来了一种科学观,该科学观“奠基于以下这些因素之上:研究方案的可重复的条件,相似研究中心中受过训练的可信赖的研究人员,可公开供专家们批判性审查的研究结果,整个学科对证实、批判的广泛接受,以及在职业杂志上刊发、查验、修正的可供同业互查的结论……有鉴于史料的那种事件细节详尽但又不可化约的本质,以及历史研究最终表现形式始终是叙事,则科学足以容纳历史,尽管只是一块边缘地域。”[12]5“文学史”被视为文学研究科学化、专业化、学科化的途径,被国别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共同采纳,是不足为奇的。基亚要求比较文学工作者具备的首要“装备”是“成为一位历史学家(文学的历史学家)”,需要了解文学赖以产生的“总体背景”;“应该懂得多种语言”被排到了第三位,低于“各国间文学关系的历史学家”。[13]4-5梵第根倒是把“通许多种语言”放在第一位,不过其目的却是为了推进文学史研究,让文学研究具有“历史科学的特质。”[9]4
偏颇之二,《比较文学的危机》以“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名,却以“文学研究”的“危机”开篇,以讨伐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为主要内容,好像“比较文学”的危机就是“文学研究”的危机,比较文学应该为文学研究的危险处境买单。这不是思维混乱,韦勒克的意思只能是:比较文学为文学提供的一套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因此,文章的标题《比较文学的危机》就应该理解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给文学研究带来)的危机”,或者干脆改为《文学研究的危机:比较文学方法批判》。不过,要论述“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给文学研究带来)的危机”这个问题,按照惯例应该回溯历史,检讨历史上其他文学研究方法的优缺点,在对比之中给比较文学的药方一个公允的评价。但是,文章没有这么做,大概是因为在比较文学将实证主义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引入文学研究,尝试着将文学现象做科学化的研究之前,西方并没有类似的尝试。
偏颇之三,《比较文学的危机》以反对“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学术研究倾向定义比较文学,但随后的一系列论述又离开了“跨越性”,围绕着所谓的“文学性”展开,好像比较文学跨越的不是“民族”而是“文学(性)”。这显示出韦勒克最为在意的是“文学性”被法国学派所主张的“历史性”破坏了,“非文学”——作家、读者、社会等“外部因素”——篡夺了“文学”的地位。但是,韦勒克所谓的“文学性”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韦勒克绝对不是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者,请看他为新批评辩护时所说的一段话:“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所指的任何意义上的形式主义的罪名加在新批评派上是根本的没有切中要害。新批评一味偏重的是一部艺术作品的意义,偏重态度、调门、情感,甚至偏重其中传达的最终意在言外的世界观。……新批评派想望使批评变成一门科学的说法在我看来更加荒诞不经……其实新批评是科学的对头。科学之于泰特乃是历史罪人,它已经摧毁了人类的相通之处、搅乱了古老的有机的生活方式,为工业化铺平道路,把人类变成了在本世纪里蜕变成的那种异化、飘零无根、不信神明的生物。”[14]254-255可见韦勒克看中的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内容”(态度、调门、情感、世界观)。韦勒克为文学研究开出的药方是:就目标而言,是“保存”和“创造”“人类最高价值观念”。[8]272这清楚表明,韦勒克心目中的“文学性”归根结底是“价值观”,如果说它和我们通常以为的以“虚构性”(“想象性”)为中心的“文学性”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韦勒克所谓的“整体论”概念——“将艺术品视为一个千差万别的整体,一个符号结构,然而却是一个隐含着并需要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8]271用“符号结构”代替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形式”概念,而支撑点仍然在“意义和价值”之上。比照克罗齐对“历史(事实)”——编年史所记录的事实——与“(史学)思想”之间关系的阐述可以帮助理解韦勒克的上述观点。克羅齐认为“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15]8“历史是一种精神活动”,[15]9“历史就是思想”,[15]42“‘反历史的哲学……之所以是反历史的,乃是因为它是反精神的,因为它是自然主义的。……那种哲学没有接触到关于精神的概念,因而也没有接触到关于人道、自由和进步的概念,人道自由和进步就是精神的各种面貌或同义语。”[15]151
更进一步说,韦勒克的“文学性”具有意识形态特征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问题还在于该意识形态是“历史性”的还是“非历史性”——永恒的、超验的、不以社会和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问题上,韦勒克坚定地站在“超历史的绝对价值”一边。他借泰特的话表明自己对所谓“让历史去评判”说法的鄙夷:“倘若我们等待历史去判断”,如同它们所呼吁的那样,“那将永远没有判断可言”。[14]248借着评价新批评,韦勒克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学作品具有超历史的、永恒的价值标准“信念”的忠诚:“我无意掩饰自己的信念(:)……一部艺术作品……相对而言(是)脱离它的渊源和效果而存在的。……裁决艺术的优劣始终是批评回避不了的职责。倘若屈从于中立的科学主义和超然的相对主义,或者听任由于政治灌输而要求的强加于人的外来规范,人文科学就会放弃其在社会上的功能。”[14]264可见,既然韦勒克的“文学性”是具有超验性的意识形态,那么,为了维护该意识形态的超验性,就必然要回避历史,回避社会。因为一旦引入历史、社会的维度,就意味着打着“文学性”幌子的意识形态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因而就不是无条件的,是会变化的。这样一来,该意识形态的超验性、神圣性就被剥夺了。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法国学派所提倡的比较文学在克罗齐和韦勒克看来,为什么如此罪大恶极,必欲除之而后快了。因为“文学史”概念被认为是实证主义在历史学中的体现,历史是问题,但关键问题却在实证主义。在反对实证主义这个问题上,韦勒克和克罗齐是同一战壕的亲密战友。克罗齐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大师之一,“主要地是从唯心主义立场反对此前西方风靡一时的实证主义思潮。”[16]126韦勒克说对他的基本观点几乎全盘接受,他说:“克罗齐对类型说的攻击几乎处处令人信服。他认为每一部艺术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从而否定了艺术技巧、步骤和文体风格,甚至拒绝将它们作为文学史的论题。在许多人看来,这恰恰摧毁了整个进化论的基础。克罗齐曾预言并希望文学史将完全由论文和专著(或手册和资料摘要)组成,他这种预言和希望正在成为现实。”[17]53和克罗齐一样,韦勒克也不承认文学现象的历史性,他们把文学作品看作神来之笔、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福音书。他们根本反对史学的观点与方法介入文学,即反对历史研究的所持的观念与方法——客观性追求与事实的可查证机制——应用到文学研究中,将文学现象间的“关系”研究界定在由作者、读者、时代、社会、文化等因素参与构成的“历史”之中,因为这样会亵渎他们赋予文学的神圣使命——留存和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福音书。
综上所述,克罗齐的《比较文学》和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这两份经典文献体现出的主要是形而上学——神学包装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实证主义哲学的敌意,体现出二者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如果承认法国学派为比较文学学科设定的内涵,就不得不认为美国学派主张的实际上是另一个学科——很可能是文学理论,并且在书写比较文学史的时候,将这两份否定比较文学学科的文献清除出去;如果认同美国学派定义的比较文学概念,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区别只存在于本质相同相近的文学现象呈现出的具有“跨界”性质的不同表现,法国学派势必被全盘否定,它们的历史就成为学科前史,或者学科发展的一段歧路。换言之,我们把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当成同一个学科——比较文学——下面的两个学派可能是错误的,它们实质上是两个学科: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
参考文献
[1][意]克罗齐.比较文学[A].王锦园译,张廷琛校对.中国比较文学[J].1988(2):91-94.
[2][意]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M].王天清译,袁华清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意]克罗齐.自我评论[M].田时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意]卡洛·安东尼.历史主义[M].黄艳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6][美]梯利.西方哲学史[M].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8][美]雷纳·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A].批评的诸种概念[M].罗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9][法]梵第根.比较文学[M].戴望舒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5.
[10][法]保罗·阿扎尔.书,儿童与成人[M].梅思繁译.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
[11]JOSEPH TEXTE. 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the Cosmopolitan Spirit in Literature: a Study of the Literary Relations between France and England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 trans. J. W. Matthews. London: Duckworth & Co.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899.
[12][加]南希·帕特纳.现代性与历史学[A]. [加]南希·帕特纳、[英]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13][法]基亚.比较文学[M].颜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14][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八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15][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英]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譯,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6]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7][美]雷纳·韦勒克.文学史上的进化概念[A].批评的诸种概念[M].罗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毛明,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中西生态文学与文化比较、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海洋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