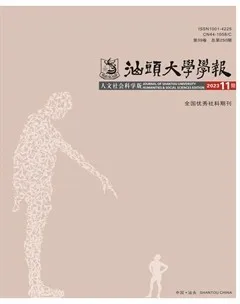探究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
——协同引入“恶意补足”规则与“国家亲权”理念为视角
朴永春,罗世琦
(延边大学法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引言
2023 年9 月16 日,一篇关于山西大同两名九岁儿童,常年凌辱同班同学的新闻引起了社会广泛讨论。两名九岁儿童对同班同学实施暴力殴打、强迫舔舐其肛门以及生殖器等极其恶劣的行为,让民众很难想象是如此低龄的儿童所为。由于两名九岁儿童的行为太过于极端,年龄之低但手段之狠毒,该事件在短短的一天里,在我国主流媒体的讨论度高达671.5 万且仍呈上升趋势。于9 月26 日,广受社会关注的山西大同未成年人欺凌事件通报了处理结果:“对涉事的两名九岁男孩,予以训诫”。对于该处理结果央视网发文“年龄不应该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①参见央视网:年龄不应是违法犯罪挡箭牌_中国网(china.com.cn)。,广大群众也对此处理结果难以接受[1]。但依据我国现行的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我国没有法律依据对该施暴儿童进行刑事责任的追诉。
基于此事件,我们不难联想到2019 年10 月,13 岁大连男孩杀人案②参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750355。,虽然根据当时的法律该男孩无法承担刑事责任,但此案件成为推动惩治未成年犯罪的关键节点,基于此案我国于2020年10 月13 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正式提出了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做个别下调,该草案于2021 年3 月正式生效,该草案的生效是我国惩治未成年犯罪的实质进步。对于山西大同事件能否适用大连男孩杀人案来处理,答案是否定的。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与青少年的心智成熟度成正比关系。如果只是一味降低个案刑事责任年龄的标准,对降低我国青少年犯罪只是治标不治本,很难达到“感化、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
其次,山西大同事件与大连男孩案件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两件案件的损害结果大不相同。山西大同事件未造成死亡等严重损害后果的也无法理依据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使其承担刑事责任。“恶意补足”规则通过公诉机关对低龄嫌疑人(造成严重损害结果)恶意的补足来弥补低龄儿童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无法负刑事责任的现状,“恶意补足”规则的引入可以概括性地解决低龄儿童的恶性犯罪事件,既保证了追责低龄儿童的效率,也对恶性低龄儿童犯罪行为起到警示作用。而对于类似山西大同事件,低龄犯罪者并未造成严重损害结果的情形,如果一味地推崇“恶意补足”规则便直接违背了我国对于未成犯罪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于未造成严重损害结果的低龄犯罪者既不能加重其承担刑事责任,也不能完全放任由家长自行管理,将“国家亲权”融入“恶意补足”制度便是解决此情形的最优解,对于触犯刑法但未造成死亡等严重后果的低龄犯罪者由国家充当该低龄犯罪者的第一负责人,对低龄犯罪者进行统一教育、管理既能体现我国对未成年犯罪教育为主的方针,也能体现我国对打击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心。
一、将“国家亲权”融入“恶意补足”制度的理论探究
(一)“恶意补足”制度的理论发展
“恶意补足”规则始于英美法系国家,经过近700 年的发展该制度在预防和惩治低龄儿童犯罪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规范体系,其理论核心在于假若有足够且充分的证据证明某种不法行为是特定年龄段缺乏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故意或没有正当理由实施的,那么其欠缺刑事责任能力的法律推定将被推翻[2]。“恶意补足”规则最早出现于5 世纪中叶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时代①公元410 年,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Alaric 攻陷罗马,罗马官员也接着离开了不列颠,于是在5 世纪下半叶日耳曼部落纷纷涌进了不列颠,建立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当时教会法在设置了12~14 岁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同时规定了额外的低龄儿童是否构成刑事责任能力的灵活性判断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单纯以刑事责任年龄“一刀切”的规则模式,在14 世纪30 年代,英国的主导思想为“11 岁和14 岁的人可能同样狡猾”,为“恶意补足”规则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全盘依据刑事责任年龄划分是“一刀切的”“死板的”规则,英国法学家Black stone 教授②威廉·布莱克斯通是英国18 世纪著名法学家,出生于伦敦的哲普赛德。著作有《英国法分析》《英国法释义》等。提出“7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通常应被视为缺乏犯罪能力的,但控方有充分的证据及理由证明未成年人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恶意的,那么缺乏犯罪能力的推定将被推翻”。
直至17 世纪,适用“恶意补足”规则的年龄上限被调整为14 岁。进入20 世纪后半期,“恶意补足”规则在美国少年司法系统里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 世纪初期,美国掀起了“家长主义”的浪潮,早在1899 年7 月1 日,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少年法庭在芝加哥开庭时所依据的法案中,首次全面而明确地宣布了这一原则,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家长主义”一直为治理青少年犯罪的最高理论依据,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感化”为主的“家长主义”模式已经无法应对美国青少年暴力犯罪的现状,随着青少年暴力犯罪与恶性杀人事件的频发,美国各州不约而同地改革司法体制,制定严厉的刑事政策来治理青少年犯罪[3]。美国法学家Marvin D.Krohn 教授③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Myles Dworkin,1931 年12 月11 日~2013 年2 月14 日),出生于美国麻省沃塞斯特。著名哲学家、法学家。提出,美国各州少年法院的法官可以在审理过程中放弃对刑事责任年龄的斟酌权,可以将严重恶性犯罪的青少年从少年法庭转移至成人法庭,打破了单纯依靠年龄确定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规定有刑事责任年龄的例外规定,具体分为将少年犯移送至成人刑事法院,或在刑事法院将一些恶性少年犯按照成人刑事诉讼程序提起公诉。使“恶意补足”规则在美国未成年诉讼程序中得到了实质的发展。20 世纪80 年代,美国有42 个州的法律允许法官对犯谋杀罪的未成年人判处终生监禁(LWOP),其中29 个州颁布法律明确规定适用LWOP 判决排除对个人罪责评估,将青少年等同于成年人,不再应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予以特殊的诉讼程序,不再以未成年身份成为其减免罪责的理由。
时至于此,“恶意补足”程序在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该程序的适用大幅降低了美国青少年恶性犯罪的参与率。21 世纪后,美国恶性青少年犯罪率大幅下降,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也逐渐较为宽松,2010 年,最高法院在Graham 诉Florida案中明确适用了未成年罪犯不得因非凶杀罪由被判处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LWOP)。“恶意补足”规则在美国未成年诉讼程序中的适用既能保证对恶性严重犯罪低龄儿童的处罚,又能避免过于放纵的归责原则,引导青少年在社会中降低犯罪危险,在现如今的美国诉讼程序中至于不可或缺的地位。
(二)“国家亲权”的理论发展
“国家亲权”主义最早起源于英格兰,为了巩固君主对封建王朝的统治,“国家亲权”主义应用而生,最初“国家亲权”主义的对象主要分为两大类,精神病患者和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早在1540 年就有法院介入“国家亲权”的相关记载。1540 年的监护法院(Court of Wards)①起源于1066 年诺曼征服后引入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主要涉及国王对未成年继承人及其土地的监护权。主要的任务是处理封建租赁的相关事宜,其中包括领主对租户未成年子女的监护问题,此后随着《1660 年保有权废除法案》的颁布,衡平法院开始介入国家亲权案件,并成为了君主亲权的代理机构;将衡平法院对儿童的监护看作是一种信托,但此衡平法院对儿童的管辖权旨在财产,而非人身属性[4]。
1804 年的“曼德维尔诉曼德维尔以案”中正式扩展了“国家亲权”的范围,虽然英国早期的“国家亲权”主义存在许多弊端,但也从根源上推动了“国家亲权主义”的发展。17 世纪后期,“国家亲权”在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1846 年美国法学家Lord Chancellor Cottenham②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1870 年—1964 年),是美国20 世纪著名法学家。是“社会学法学”运动的奠基人,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提出:“法院代表婴儿进行干预的案件应不止局限于有财产的案件,法院干预婴儿案件作为婴儿的保护行为,凭借的是国家作为父母的特权,这一权利的行使不需要任何委员会的授权”,这一制度的提出打破了英国“国家亲权”只针对财产而非人身属性的枷锁[5],使“国家亲权”主义的管辖范围近一步扩大,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对于惩治青少年犯罪推崇“保护、预防以及教育”的政策,基于对青少年的保护,美国形成了福利性未成年司法程序,基于“国家亲权”家长制及教育为主的方针,依托福利性少年司法程序,“国家亲权”在20 世纪初迎来了质的跨越。
1971 年的“麦克维尔诉宾夕法尼亚州一案中”③首次提出否认少年犯享有陪审团审理的权利,被誉为国家亲权体现的第一案。,法院停止了对少年犯宪法权利的进一步扩张,否认了少年犯享有陪审团审理的权利。此案件被视为“国家亲权”在少年司法程序中的明确体现。20 世纪80 年代,美国未成年恶性暴力犯罪率急剧提升,国家开始转变福利性少年司法程序,转而代之的是“严罚”少年司法程序的出现,“恶意补足”规则与“司法移送”成为当时社会处理青少年犯罪的主流程序。“严罚”性少年司法程序的适用大大阻碍了“国家亲权”的发展,在此阶段“国家亲权”发展趋于停滞。21 世纪后随着青少年恶性犯罪率的下降,“国家亲权”又逐渐回到少年刑事司法程序中,经过近百年“国家亲权”已经发展成为青少年司法程序中的中流砥柱,当父母管理不当或无管理能力时,国家有权直接行使监护职责,保护少年的合法利益以及规制社会中的青少年犯罪。
二、将“国家亲权”融入“恶意补足”制度的理性分析
(一)将“国家亲权”融入“恶意补足”制度的必要性
1.我国低龄儿童犯罪率逐步提高
2023 年6 月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根据白皮书所示,从2020 年至2022 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情况来看,2020 年至2022 年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分别为37681 人、55379 人、49070 人,2022 年受理审查起诉人数较2020 年上升42.8%,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占比上升,2020 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14 至16 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为5259 人、8169 人、8710 人,分别占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总数的9.57%、11.04%、11.1%。基于犯罪主体与犯罪行为的正比关系,我们不能回避低龄儿童犯罪逐渐增加的客观事实,同时佐证,合理规治我国未成年犯罪尤其是低龄儿童犯罪问题的紧迫性、必要性。
2.我国现有未成年诉讼程序的滞后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①2020 年7 月23 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开幕词,参见:https://www.gov.cn/xinwen/。,我国处理未成年犯罪问题始终落实“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及“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近几年,高频发生的低龄儿童犯罪事件将我国未成年诉讼程序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于大众视野。从大连13 岁儿童杀人案、湖南益阳12 岁吴某杀母案②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36535。到9 岁山西大同儿童恶性霸凌事件。由于社会发展增速与青少年心智成熟度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与综合国力的提升,青少年的低龄犯罪率只会越来越高,这是我国规治青少年犯罪不得不面临的现实存在。根据相关数据总结得出,20 世纪90 年代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已经比70 年代提前了2—3 岁。短短二十年降低2 岁,如此快速的未成年人年龄递减率让人瞠目结舌。然而基于我国现有的规制,未成年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并未将此发展趋势考虑其中。
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关规定,我国已经针对特别严重犯罪的犯罪行为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 岁,这无疑是我国追诉未成年罪犯刑事责任的重大飞跃,但法律存在滞后性,根据上文提及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中数据可知,我国低龄儿童犯罪是一个大趋势,《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关规定是基于大连13岁儿童杀人案为导火索促进了相关规定的制定与落实,那么不禁让人产生相关质疑,如果日后出现11 岁儿童杀人案、10 岁儿童杀人案,我国现行法律仍无法规治,一味的通过刑法修正案去补正刑事责任年龄,必定不是长久之策,这种行为没有真正发挥刑法最主要的预防作用,同时还破坏了刑法的预测性与稳定性,违背了刑法作为惩治犯罪、保护国家人民和人民利益的有利武器的初衷。
针对我国未成年犯罪呈现出低龄化的现状,笔者提出引入“恶意补足”规则,通过统一恶意认定的标准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严重的恶性未成年罪犯,由公检机关搜集恶意的认定证据,补足其年龄上的缺口。该规则既能高效地处理我国低龄儿童的犯罪现状更主要的是可以增强青少年对自己行为不利后果承担的心理预期率,真正起到预防先于惩治的治理模式。
3.单一适用“恶意补足”制度的片面性
根据《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③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强化“四大检察”融合履职打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组合拳”。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犯罪并非集中于一个或一类犯重,犯罪行为的多样化、犯罪客体复杂化是我国未成年犯罪的现状。2022 年检查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居前五位的分别是盗窃罪20966人、聚众斗殴罪9677 人、强奸罪9122 人、抢劫罪6983 人、寻衅滋事罪6190 人,占比共达67.4%。而对于前五个罪中并非都造成严重的人身损害。
且以强奸罪为例,只有强奸致人死亡等结果加重犯才有可能打破固有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则原则,如果忽视损害结果这一前提,对所有的低龄犯罪都以“恶意补足”规则处罚的话,势必从根本上违背了我国以“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会使我国重新走上美国20 世纪80 年代“严罚”制度的老路,这即违反了国际上对儿童保护优先的原则也会因为“严罚”从而扩大司法惩戒的财政支出阻碍我国经济平稳有序的发展趋势。对于未造成严重损害结果的低龄儿童犯罪行为,依据我国现有的规责体系,仍是以家庭教育、训诫为主。正如本文提到的山西大同案,由于该案的两名施暴者既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又未造成严重的人身损害后果,最终只能对两名施暴者予以训诫的处罚。对于这样的处罚,无疑是无法使民众信服的,违法犯罪成本过低会变相增强未成年人的犯意,尤其是对于有前科劣迹的青少年来说,快速、高额的回报率与低的犯罪成本,加之青少年正处于涉世未深的学习阶段,在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多次犯罪趋势正在我国青少年犯罪中逐渐显露出来。
分析《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数据得知,2022 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中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为1737 人,占同期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总数的2.2%,同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于,对于低龄犯罪嫌疑人且未造成严重人身损害后果的是不起诉的,加上该因素,我国青少年重复犯罪率应远不止于此,这也从侧面佐证了我国青少年犯罪类型趋于多样化。单一的“恶意补足”规则无法应对我国现存的复杂情况。结合我国本土国情,笔者提出“恶意补足”规则与“国家亲权”相结合的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的治理模式。针对低龄犯罪嫌疑人且未构成严重损害结果的由国家作为该犯罪嫌疑人的第一监护人,国家对此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统一管理,整合我国现有的“矫正教育”制度,配合“工读学校”或“专门学校”对此类低龄犯罪嫌疑人进行教育、培训。既能有效增加低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成本又真切落实我国“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切实保障我国青少年健康成长。
(二)将“国家亲权”融入“恶意补足”制度的可行性
1.符合“罪行法定原则”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罪行法定原则”最早起源于1215 年的《大宪章》①800 年前的6 月15 日,在英泰晤士河畔的兰尼米德草地,英国国王约翰被迫与25 名男爵签署《大宪章》是中世纪人们试图用法律的形式限制王权的第一次尝试。,其内涵在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结合引入“恶意补足”规则与“国家亲权”,均在我国现行的《刑法》内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予以定罪处罚,符合法律预期。本案所提及的山西大同事件中,多数人提出对未尽到监管义务的父母给予刑事处罚,此观点正是违背了“罪行法定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并无任何关于未成年犯罪而由父母承担的刑罚制度,这样的规定不光违背了刑法的预测原则,使公众对自己的行为丧失了合理的预期。更反映了严苛的惩罚机制,与我国刑法推崇的立法原则相驳,故不适用。
18 世纪60 年代,启蒙运动在英、法两国如火如荼的扩展,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在启蒙运动中首次提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随着1789年《人权宣言》的发布,“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正式确立。“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启示我们惩治犯罪要结合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把握罪行与犯罪各方面因素综合体现社会危险性,从而确定其所承担的刑事责任,适用相应的刑罚[6]。
“恶意补足”与“国家亲权”的结合正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外在体现。对于未成年主观恶意重大,造成严重人身损害结果,人身危险程度高、社会危险性大的犯罪,适用“恶意补足”规则,表明我国惩治犯罪的决心从而遏制低龄儿童用年龄当挡箭牌的假想;相反对于有一定的主观恶性,但未造成严重的人身损害后果的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国家亲权”便是最好的规治手段。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免责并不代表无罪,并不能以此大大降低此类低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成本,缺乏年龄要素而无法追责的情形并不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本意使然,刑事责任年龄以刑事责任能力作为设定基础,而刑事责任能力以辨认与控制能力为判定依据,那么引入“国家亲权”,由国家对此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管理、教育,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客观要求与导向。
2.符合我国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的整体价值取向
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产生了由年龄来制定相关处罚的规定,《曲礼上第一》中曾写到“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体现了我国从古至今对未成年犯罪都予以更大的宽容。时至今日我国未成年犯罪问题始终保持着教育先行,惩戒辅助的主体地位。从教育和挽救的角度出发,努力帮助未成年人重塑性格品格,更好地融入日后的生活。我国刑罚规定的两大功能为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
治理未成年犯罪问题属于刑罚中的子集,势必治理未成年犯罪有其固有的特性但也不能忽视刑罚中的共性及惩治犯罪。我国结合引入“恶意补足”规则与“国家亲权”主义,便是对此价值取向的最好诠释,面对所有的未成年犯罪行为不论犯罪客体的属性、不论损害结果的大小都应该树立起国家规治的决心,坚决不能让刑事责任年龄这一因素成为追责此类犯罪的护盾。
不能忽视未成年犯罪问题中的独特性,刑事责任年龄是客观存在的,会必然影响每一个未成年犯罪问题。因此,对于惩治未成年犯罪问题尤其低龄儿童犯罪问题,不能简单粗暴的适用美国20 世纪80 年代盛行的“分流制”,将所谓“恶性案件”直接移送成年法庭审理,这将会使我国治理未成年犯罪走向另一个极端,而结合“恶意补足”规则与“国家亲权”主义便兼顾了我国刑罚中惩戒的共性,又凸显“教育、感化、挽救”的特性,符合我国针对未成年犯罪问题的总体价值观。
3.分层规治、教育与降低未成年犯罪率的正比关系
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曾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定罪可能性和惩罚轻重两个因素的增加都可以导致人们认为“违法不合算”而减少犯罪,同时通过经济学分析法得出惩罚轻重与减少犯罪并非呈正比趋势,分析实验犯罪模型发现当惩罚重于可预测范围,犯罪率不降反升,犯罪者基于“破窗效应”心理,不适当的过重刑罚反而增加了罪犯的犯意。单一引入“恶意补足”制度,对于未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未成年通过补足恶意,而承担相应刑事责任是不可取、不合理的。将“国家亲权”融入“恶意补足”制度,分层规治、教育才能有效遏制未成年犯意,合理规治未成年犯罪问题。
多数人曾对引入“国家侵权”主义提出如下质疑:“单纯由国家担任犯罪青少年的监护人,仅通过统一的教育管理而非监禁的方式能否起到惩戒未成年犯罪的作用”?Nikhil Jha 教授所做的“提高入学率以学校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与犯罪率”的调查研究回答了此质疑。该调查提出减少犯罪的政策是规治犯罪的重中之重,然而影响犯罪率降低的因素各不相等。
青少年表现出的高犯罪倾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因此,减少青少年犯罪活动干预措施反而有更大的好处。Becker 教授提出的关于犯罪理性分析的模型,得出从犯罪中得到直接回报的学生可能会提前辍学,如果将学校边缘学生强迫留在学校,他们从事犯罪的时间或机会就会减少。同时,此调查参考的教育类型不限于学校普通教育,青年学生可以追求职业教育和培训(VET)①VET 是Vocational Education Training 的缩写,全称为职业教育培训,主要目的是培训学员提高相关专业实践技能,进入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或提高其现有的职业技能。流,为了鼓励边缘学生的参与,提高离校年龄需要与“外部”选择或其他形式的强制性参与相结合。
强迫不合群的人留在学校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犯罪学家Billings 和Phillips 研究中发现高风险学生的集中度增加了犯罪,关闭此类学生行为不端和教育表现低下的学校,可以减少净暴力犯罪[7]。从而也佐证,对于低龄犯罪青少年不能仅由未成年父母或普通学校进行管理,否则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最后调查指出,提高国家教育的统一管理结合职业培训或就业等有意义的参与途径,有助于预防青年人可能脱离教育或劳动市场,同时也能减少潜在的未成年参与犯罪活动。基于此将“国家亲权”融入“恶意补足”制度,势必成为推进治理未成年犯罪体系化、效率化和制度化的重要环节。
三、将“国家亲权”融入“恶意补足”制度的中国化道路构建
(一)明确将“国家亲权”融入“恶意补足”制度的适用范围
英美国家“恶意补足”的适用范围并未形成统一明确的标准,20 世纪90 年代,美国在未成年诉讼程序中引入“婴儿期辩护结构”,该结构推定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如果年龄介于7 周岁—14 周岁,在审查起诉时由公诉机关证明7 周岁—14 周岁的被告人在起诉前所构成了犯罪意图,但随着美国未成年犯罪率的降低以及美国固有的政治分权体制,使得“恶意补足”在年龄适用设计上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内华达州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8 岁、得克萨斯州为15 岁而纽约州为13 岁,均不相同。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指导全国的建设,在我国的政体下明确“恶意补足”规则与“国家亲权”主义是推进两种规则本土化的必然之需。
1.明确两种制度的年龄适用范围
引入“恶意补足”与“国家亲权”年龄适用范围为8~14 岁。年龄是适用“恶意补足”与“国家亲权”主义的前提与基础。如果未明确年龄的适用范围,就意味着两种规则的适用范围0~14 周岁,未成年的心智变化较快,看似短短几年的时间实则是未成年人身心发展变化最复杂的阶段,简单以全阶段的适用范围势必是不合理、不可取的。
Piaget 教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认识程度的划分提出了“认识发生论”的观点,他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动作,动作是感知的源泉和思维基础。美国心理学家Piaget 教授①让·皮亚杰是儿童心理学、发生认识论的开创者,开辟了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对当代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将儿童的认知发展过程分为4 个主要阶段:感知运动阶段(0~2 岁)、前运算阶段(3~7 岁)、具体运算阶段(8~11 岁)和形式运算阶段。由此可知,在具体运算阶段(8~11 岁)青少年的自我评价逐渐趋于成熟,自我意识的强度和深度不断增加,能够产生是非观与对错行为的选择。由辽宁省儿童青少年健康人格评定与培养协同创新中心,所做的“4~8 岁儿童公平认知与公平行为差距”实验中,得出结论“4 岁组、6 岁组儿童在认知获得数量显著少于认知任务,8 岁组儿童在实验中认知获得数量与认知任务无明显差异”由此可知,儿童只有到了8 岁,才能稳定将公平原则应用到实际行为中,儿童的公平认识与公平行为才趋于一致。
根据上述实验分析,将我国引入“恶意补足”与“国家亲权”规则的年龄控制在8~14 周岁,是符合当下儿童心智发展趋势的,同时公平、正义是我国法律始终追求的价值目标,实验表明8 岁儿童就能将公平原则运用于社会实践中,进一步佐证,8~14 岁的儿童已经能清晰地认识到是非观念,在此基础上让8~14 岁违法犯罪的儿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无可厚非。《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统计得出我国低龄未成年犯罪主要集中于13 岁左右,将“恶意补足”与“国家亲权”范围确定为8~14 岁,既有利于集中主要力量打击低龄犯罪,又可以对更低龄的犯罪行为起到未雨绸缪的预防。
2.明确两种制度的罪行适用范围
“恶意补足”与“国家亲权”两种规则的内在法理是不尽相同,“恶意补足”规则是打破刑事责任年龄,突破我国对未成年犯罪整体保护的方针,注重对严重、恶性低龄未成年人罪犯行为的惩戒性。故限制“恶意补足”规则的适用范围关乎着“恶意补足”这一程序能否真正在我国未成年诉讼程序中适用。
我国适用“恶意补足”的范围,是否能像美国以“严重的恶意犯罪”为笼统的标准,笔者认为不可照搬,美国少年司法程序中对未成年的规治以保护处分为主搭配教育或社会劳动,且美国有独立管辖权的少年法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已经形成了一套适用本国国土的体系,故美国规定以严重的恶意犯罪笼统规定并不会直接损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与人权。
我国尚未形成独立的少年司法程序和独立的少年刑事处罚体系,且我国对于达到审查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罪犯,都以惩戒为主,假若以笼统的适用范围势必会造成我国治理未成年犯罪严厉有余而宽缓不足,违背我国规治未成年犯罪的方针与理念。结合我国未成年刑事犯罪的现状,笔者建议延续《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特别个案中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范围,即“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从2021 年开始实施通过2 年的时间检验,特别个案中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范围已经广泛被大众接受且产生良好的司法效果,“恶意补足”规则延续该罪行适用范围,首先是通过实践检验的产物更好的融入我国本土化特色,其次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没有增设群众对该规则适用的额外预期,提升“恶意补足”规则的适用率[8]。不可否认“恶意补足”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增设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负的责任,突破了我国固有的法律规则,加大了对恶性未成年罪犯的惩罚性。综上所述,只有适用于最为严厉的罪行范围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我国现有未成年治理体系的损害。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特别个案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罪行范围,是所有犯罪中恶性强度最高、损害结果最大的。笔者建议将此类罪行纳入“恶意补足”的调整范围,也是我国比例原则的集中体现。“国家亲权”是对我国现有未成年追责程序的有效补充,面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未造成严重损害结果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国家不能放纵不管,落实国家第一监护责任制,是有效规制此类犯罪的有利手段。“国家亲权”符合我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最大限度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的治理总方针,是我国治理未成年犯罪的常态化机制,基于此,“国家亲权”调整的范围应该是补充性的,对于不符合未成年诉讼程序管理的行为以及“恶意补足”规则以外的行为,均由“国家亲权”规则进行管理,真切落实国家对未成年违法犯罪行为的管理以及对管理未成年违法犯罪问题的全覆盖。
(二)将“国家亲权”融入“恶意补足”制度中恶意的认定
早在我国唐朝时期就出现了对“恶意”的解释,魏征曾在《谏太宗十思疏》诉:“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第一次系统地将“恶意”解释为:邪恶,与善相对。现代汉语词典中将“恶意”解释为:不良的居心、坏的用意。“恶意”作为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很难用科学手段将其清晰划分,不同国家历史背景、文化习俗的差异,使得不同国家对“恶意”的认定各有不同。英国法庭通过调查未成年人与受害人的特定关系、犯罪前后的行为表现、经验阅历、受害者损害程度等综合因素来判定未成年是否具有恶意。
美国规定如果控方能够证明处于10~14 周岁年龄段的行为人以前实施过同类犯罪行为,就可以推定行为人主观具有恶意[9]。将“恶意”的认定本土化是推进“恶意补足”规则的核心环节。同时,“恶意”认定的核心在于未成年人能否正确地认识到行为具有严重的非道德性和违法性。在此概念上笔者基于我国特有的司法程序,建议结合犯罪后的心理状态与详尽的社会调查综合判断“恶意”。
1.对未成年犯罪者犯罪后心理状态研究
研究表明,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常常伴随着紧张、恐惧还存在一种异常的兴奋感。在犯罪时,激情和应激的状态下容易产生危险的失控行为,这使得犯罪者在犯罪时并非处于完全理性状态,而多数犯罪者在情绪平复后,都会明显表达自己在当时的情绪失去控制,对自己先前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后悔情绪,尽管他们所产生后悔情绪的原因不尽相同[10]。
不可否认,有极少数的犯罪人在实施完犯罪后会产生得意、满足感或麻木的心理状态,多数观点将此类犯罪者归纳为反社会人格。美国生物学家提出“恐惧感缺乏说”,即此类犯罪者感觉恐惧的阈值高于绝大多数正常人,从而可以解释此类犯罪者犯罪后平静、麻木的心理状态。美国心理学家Andrews 总结了反社会人格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又称无情型人格障碍(affectionless personality disorder)或社会性病态(sociopathy),是对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类型。的一些典型特征,不计后果、反社会认知或亲犯罪情感(缺乏良知)、几乎没有罪责感等[11]。美国犯罪学家Dodge 和Frame 教授认为,所有的孩子都会形成引导他们行为的行为脚本:反社会型儿童形成了反社会型或攻击型的行为脚本。
在此类儿童观念中,攻击行为是合法正当的、攻击力的提升可以为此提供权利。由此可见,反社会人格并非仅存在于成年人犯罪者中,反社会型儿童也同样暴露出极高的社会危险性和人身危害性;同时上文提到的研究表明,犯罪后的心理状态是犯罪者最客观、理性的情绪表达。同时恶意的评估应该是多因素的,基于此笔者建议我国应把“恶意”的认定分为四个主要标准:①精神疾病测试,如反社会、偏执或自恋型人格障碍和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②行为倾向,如对武器的喜爱;③参考此类主体实施犯罪的方式及内容,如具体犯罪目标、方法或时间;④保护性因素,如暴力行为后所做的预防措施。结合我国犯罪心理测评,从而对未成年犯罪者罪后产生的心理进行评估,以悔罪态度、是否属于反社会型人格为主要切入点由专业的心理学家与群团组织(关工委)共同协作,从而评估其是否具有“恶意”或“恶意”程度的高低。
2.运用好我国固有的社会调查制度
“恶意”的认定是一个主观价值的具象体现,任何法律都无法对“恶意”给予一个标准答案。“恶意”的认定不仅是关乎一个未成年人是否受到刑法的追诉,更关乎着一个家庭的幸福、一个国家的未来。我国对于“恶意”的认定一定要坚持赋予公诉机关最少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的范围认定。美国犯罪学家指出,当代引起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是多样化的,主要归纳为:性格缺陷、家庭结构的影响、学校教育制度的缺失以及社会风气等[12]。
启示我国对“恶意”的认定也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原有的客观情况下进行主观价值判断才能更好地避免自由裁量权带来的不利后果。我国的社会调查制度便是解决此问题的最优解。社会调查是特定主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家庭结构、监护教育等情况所进行的调查行为。我国多数观点将社会调查报告评价为英美证据法中的品格证据。社会调查的核心是人格调查,涉及对未成年人的品格评价以及被调查人危险性的评估,并以此作为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做出决定或判断的重要参考制度。
基于此,我们不难推断出,社会调查制度与“恶意”的认定,在调查范围与调查目的上存在高度契合性。如果将未成年调查报告这一现有制度完善并应用于“恶意的认定过程”,这势必满足“恶意”认定应在收集多样化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的前提,结合我国社会调查制度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我国司法的利用效率。
(三)将“国家亲权”融入“恶意补足”制度的程序运行
“恶意补足”制度,通过主观恶意的补足,从而打破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对造成严重损害结果且主观恶意大的低龄儿童进行惩戒,配套适用我国固有的未成年刑罚制度,进行管理规治。对于未造成严重损害结果的低龄犯罪儿童,“恶意补足”制度的规治力存在空白。将“国家亲权”融入“恶意补足”制度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利益,由国家担任未成年犯罪者的第一监护人,对未成年犯罪者的自治行为做出限制。实践证明“国家亲权”的立场是符合当代青少年健康发展的,也契合对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只有结合我国现实刑罚程序才能更好地将“国家亲权”融入“恶意补足”制度,去治理我国的未成年犯罪问题特别是低龄儿童犯罪现状[13]。
1.结合矫治教育制度与工读学校的共同协作
教育矫治的前提条件在于“必要时,可以由政府专门教育矫治”,而且相关规定明确指出,家庭具有管教能力的,一律不予教育矫治。根据收集未成年犯罪案例,总结得出对于未成年犯罪的行为家长一般分为缺乏管教能力和缺乏管教意愿。当一个未成年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我们就有理由推定父母无能力履行、不积极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监护职责,应由国家统一行使监护权。而教育矫治的前提条件增加了此规则的适用阻碍,绝大多数的家长基于私心会证明自己有管教能力,但由家庭直接教育的未成年犯罪者重新犯罪率极高,在他们看来低成本犯罪后果完全不足以对未成年犯罪者形成恐惧规治的作用[14]。而多数家庭对于此情况由于无专业的教育管理能力,往往无能为力。如果全盘套用教育矫治制度,很难对低龄犯罪者起到良好的警示作用。
其次,矫治教育是具有司法保护性的,优先考虑由收容对象的家长管教,是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体现。当然,我国不能为了增强治理未成年犯罪问题能力而忽视我国管理未成年犯罪的总体方针。通过调查数据得出,大多数家长尽管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仍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矫治教育的主要原因在于,认为矫治教育的名称给未成年学生贴上了“坏孩子”的标签,会对他们日后的就业学习带来负面影响。
基于此,结合我国工读学校的治理模式,《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工读学校毕业的未成年人在升学、就业方面,同普通毕业的学生享有同等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由此可以大幅降低未成年犯罪者家长的担忧,有效推进国家统一治理的运行[15]。同时,笔者建议融入“国家亲权”的目的在于教育而非惩戒。工读学校致力于实施小班教学、职业教学、就业指导,重教育、矫正,因人施教,这才真正有利于把问题少年培养成守法公民和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美国也有类似于工读学校的替代学校[16]。美国法学家Micheal Benza①迈克尔·贝勒斯(Michael D·Benza),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哲学教授,代表作品为《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也阐明:替代学校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有不良行为的孩子培养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员。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工读学校对未成年犯罪者的感化、挽救作用。结合矫治教育的强制性和工读学校的保护性,既满足融入“国家亲权”作为我国青少年犯罪补充的罪行适用范围,又增加了社会特别是未成年犯罪者家长对该制度的接受度,真正做到对未成年犯罪者警示治理与保护教育相辅相成的局面,是结合我国实践的产物,是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建设的有利推手。
2.落实社会帮教制度
有数据表明,在15 项影响未成年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因素中,是否落实帮教与重新犯罪的关联度最高,无社会帮教的未成年重复犯罪率高达56.9%,而帮教基本落实的少年犯重新犯罪率仅为12.8%,“国家亲权”的目的是更好地教育、管理以及引导未成年犯罪者内心价值观的重塑,促进他们能以良好公民的姿态参与社会建设当中。通过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与基层法治部门相互结合的模式,落实好对未成年犯罪者的社会帮教工作,从而有效减少青少年重复犯罪率[17]。个体的认知结构是由经验结构形成的,当未成年罪犯体验到除家庭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的支持与帮助,他们便会逐渐形成“自己被社会所接纳”的意识,从而积极地面对、构想自己的未来。从而真正做到对未成年罪犯“教育、感化、挽救”的核心要义。
结语
“恶意补足”制度与“国家亲权”主义,都是英美国家追诉未成年犯罪、未成年诉讼程序中的制度结晶。当前我国现有的未成年诉讼程序已经很难全面应对未成年犯罪问题尤其是低龄儿童犯罪问题,如何完全适配我国本土司法实践,真正做到将“国家亲权”融入“恶意补足”制度,需要我们进一步上下求索,为我国未来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保驾护航。
——从虐童事例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