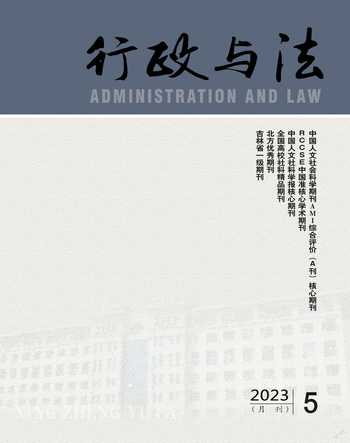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涤除的实践困境与规范重塑

摘 要:在法定代表人登记涤除纠纷中,法院往往在受理、裁判、执行的各个阶段面临困境。公司与法定代表人“同一人格”理论以及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因身份重叠而形成的“权责核心”地位,使商业实践与司法实践忽视了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真实关系,使审判陷入困境。基于公司意思表示的可分离性及公司治理分权制衡的特点,法定代表人是具有登记外观的代理人,其功能是对外代表公司,而不是掌控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形成平等主体之间的委托关系,公司享有设立多名法定代表人的自治权。
关 键 词:登记涤除;委托关系;同一人格;法定代表人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3)05-0119-11
收稿日期:2022-12-15
作者简介:黄晓林,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商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青岛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现状及优化对策”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QDSKL2201144。
近年来,法定代表人要求退出公司的纠纷层出不穷,诉讼请求通常表现为变更法定代表人。因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不仅是公司内部的变更,也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相应信息的变更,所以,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实际上就是法定代表人登记事项的涤除。在司法裁判文书网上搜索案由为“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的文书,以关键词“变更法定代表人”为限定条件,截止2022年共搜到1528件裁判文书,其中2012年1件、2013年4件、2014年5件、2015年11件、2016年28件、2017年55件、2018年102件、2019年258件、2020年378件、2021年388件、2022年298件,10年的数据显示此类纠纷逐年上升,且从2019年开始数量陡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法定代表人变更后,公司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如果公司不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因为登记外观将面临限制高消费等法律风险。然而,对于如何处理公司不变更法定代表人的问题,现行立法并没有完善的规定,加之商业实践和司法实践对法定代表人法律地位的误读,使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纠纷的审判实践陷入重重困境,亟须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厘清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本质,重塑法定代表人规范,以便能够顺利解决法定代表人退出公司的问题。
一、法定代表人登记涤除审判实践纵览:问题汇总
自然人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原因主要有三种情形:⑴冒名法定代表人,大多因身份证件丢失或被盗等原因,被公司登记为法定代表人;⑵挂名法定代表人,不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基于亲朋好友等情谊关系同意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⑶与公司有实质关联的法定代表人,此类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公司董事或经理等职务,实际掌握公司内部与外部事务的经营管理权。冒名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关系中,法定代表人系非自愿而成为具有登记外观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原因是非法的,主要依据侵权责任法解决,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关联性极弱,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挂名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有关联性的法定代表人,这两类法定代表人均基于本人自愿而与公司之间建立了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公司法》中法定代表人产生的规范基础,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原因是合法的,在法定代表人变更纠纷中具有更大的争议性,占据了此类纠纷的绝大多数,本文对审判实践中相关问题的梳理即围绕后两类纠纷展开。
通过梳理诸多案例(见表1)可以发现,法院处理法定代表人登记涤除纠纷时,所面临的困境贯穿于审判实践的全过程:受理阶段、裁判阶段和执行阶段。每一个阶段,不同的法院对于事实类似的案件往往会有不同或相反的处理决定,且不同观点所依据的理由在不同的审判阶段似乎也有所差异。如在案件受理阶段,认为法定代表人登记涤除纠纷不属于司法管辖范围,其理由是此类事项属于公司自治范围。在卢某请求变更法定代表人一案中,法院认为公司章程对变更法定代表人有规定,卢某是否担任法定代表人,属于公司的自治事项,应由公司作出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决定后,登记部门履行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故卢某请求的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①。與此相反的判决则认为,王某请求终止其与公司之间法定代表人的委任关系并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该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②。在审理裁判阶段,法院支持变更法定代表人请求的理由,主要从保护现任法定代表人的角度出发,认为虽然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属于公司自治范畴,但是公司内部治理失范,一直未办理变更手续,直接影响了张某的征信和日常生活的便利性,司法可以有条件地介入并提供救济③。持有类似观点的裁判不在少数④。也有法院以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无实质关联性为由支持变更请求,例如,孙某是不持有公司股份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已经从公司离职并办理了退工手续,其与公司已无实际关联,如果继续由其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背立法的初衷和本意⑤。在判决执行阶段,绝大多数登记机关拒绝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理由是公司没有推出新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登记涤除纠纷所面临的的困境贯穿于案件受理、裁判乃至执行的审判全过程,表面看来争议的焦点问题各异,但仔细梳理和归类后发现,各个阶段争议的问题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登记涤除纠纷的本质为何?是公司自治范畴的事项,还是平等主体之间法律关系?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视为公司自治事项的裁判中,有的以自治事项为由拒绝受理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请求⑥,有的以公司内部治理失范为由支持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请求⑦,同样都是将法定代表人登记涤除视为公司自治事项的裁判,却作出了不同的判决。另外,在商事登记部门拒绝协助执行生效判决的案件中,登记机关的理由是无新法定代表人,也是将法定代表人变更视为公司自治事项,因为法定代表人的产生需要经过公司内部程序,并且要向登记机关提交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材料。与此相对的观点则认为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公司与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关系,遵循委任关系的法律规则即可⑧。可见,司法实践对此类纠纷的性质认定存在巨大分歧。为了统一裁判规则,维护司法权威,应当从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的理论基础与规范的解释适用出发,分析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发掘分歧产生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二、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法律关系解读
从《民法典》《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及众多的司法判例可以看出,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涉及两个面向:对外代表公司实施法律行为和对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一)“同一人格”理论下公司外部关系中法定代表人的权限与责任
⒈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的概括代表权限。公司作为社团组织,无法自行实施相关行为,必须由自然人代表公司实施。根据法人本质实在说的观点,代表人的行为即法人的行为,代表人是法人的机关,法人与其代表人是同一个人格,虽名二而实一,不存在两个主体。[1]《民法典》采纳了该学理观点,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立法并未详细列举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实施活动的具体范围,其代表权原则上被视为一种概括性的权利。[2]同样,公司立法也未明确列举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范围。
依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属应当登记事项。一旦登记并向社会公示,法定代表人即具有外观属性。对交易对象而言,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公司自身的行为,基于该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公司承受。《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代表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第五百零四条规定:“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的合同原则上对公司发生效力,乃至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也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
⒉法定代表人因公司行为而面临的责任风险。“同一人格”理论的本旨在于解决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后果归属问题,但这一理论却在不经意之间强化了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同一性”,不但公司要承担代表行为的后果,而且法定代表人也要对公司法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公司欠税或者被强制执行,法定代表人个人会被限制出境或者实施高消费行为①,而不区分公司的非法行为是否与法定代表人有关。如在一起执行案件中,王某以自己只是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没有参加公司的实际经营为由,请求解除限制其高消费的措施。但是,法院认为公司未履行生效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法定代表人负有直接责任,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王某不符合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条件②。该案中,即使王某仅为挂名法定代表人,也无法摆脱为公司不执行生效判决而承担责任的命运,因为他是具有登记外观的公司“负责人”。
(二)身份重叠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权限与责任
对于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公司法》并没有明确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的义务与责任,但因该法第十三条规定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使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具有了重叠性,且该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一百四十八条、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以及违反相关义务时对公司的赔偿责任。据此,审判实践普遍认为法定代表人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自然而然地将法定代表人与董事、经理等掌握公司管理权的主体不加区分地捆绑在一起。如王某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字,之后该笔交易失败而导致公司受损,法院认为其没有对公司尽到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应当赔偿公司所受损失①。在该案中,公司受到损失的原因,究竟是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导致的,还是在经营决策中违反忠实义务或勤勉义务而致公司损失,裁判文书中并未明确区分。显然,司法实践直接将法定代表人等同于董事或经理,将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扩展到经营决策领域,形成法定代表人的权限“无所不包”的认知。实践中,因法定代表人兼具董事或经理身份,违反作为经营管理者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而造成公司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理论层面上应当清晰区分法定代表人与掌握公司经营决策权的董事、经理等人员的义务与责任。换言之,由于《公司法》没有将法定代表人列入高级管理人员的范畴,如果公司章程也未将法定代表人界定为“高级管理人员”,那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一百四十八条中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能否适用于法定代表人,自然就有了商讨的余地;即使可以适用,也只能是参照适用。
虽然《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享有经营管理权,但其他立法中隐含了这样的意思。《破产法》第十五条②规定了法定代表人在破产程序中的义务,因怠于履行相关义务而造成公司或者公司债权人利益受损,要对破产债务承担清偿责任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下简称《建筑法》)第四十四条也规定法定代表人对建筑企业的安全生产负责。此外,国务院发布的一系列行政法规、规章,更是强化了法定代表人独揽大权的地位,如将法定代表人具体化为“行使职权的签字人”。2022年实施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所规定的法定代表人的任职资格,与《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相同,更加印证了“法定代表人与董事、经理等同”的观念。学界也有观点认为法定代表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和业务知识,甚至直接将其划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范畴。[3]总之,由于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及商业实践和审判实践的解读,公司法领域形成一种普遍的认知:在大部分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中,法定代表人拥有对外概括代表公司签订各类经营合同的签字权和代表公司参加诉讼活动的权利,对内掌控公司经营管理事务,包括财务在内的主要管理决定均出自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处于公司治理的权力与责任核心位置,本文将其将简称为“权责核心”。
三、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對登记涤除纠纷的影响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责核心”地位,源自于我国国有企业的 “厂长经理负责制”。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负有全面责任,拥有广泛的权限:代表企业从事交易活动和参加诉讼,控制公司财务,权限渗透到企业的全部活动中。[4]由此形成了法定代表人大权独揽的“一长制”的企业领导理念和文化。这一理念渗透到公司法领域,法定代表人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核心地位被移植到公司实践与立法中,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一样拥有几乎“无所不包”的权限。法定代表人的“权责核心”地位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保障交易的安全和效率。同时,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也引发了诸多纠纷,与“同一人格”理论相互作用,遮盖了公司与法定代表人之间的本质关系,使法定代表人登记涤除纠纷的审判陷入困境。
(一)法定代表人“权责核心”地位引发诸多纠纷
法定代表人的“权责核心”地位意味着法定代表人既要掌握公司的控制权,又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前者引发控制权争夺纠纷,后者成为法定代表人退出纠纷的缘起。一方面,法定代表人掌握公司内部管理大权和外部代表权,对外是公司商事交易活动的最终授权者,对内通过管理印章、签字、财务资料等方式最终控制公司财务,[5]相关纠纷层出不穷,如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印章控制人之间的冲突、不同代表人之间的冲突、不同印章控制人之间的冲突等。[6]另一方面,法定代表人也是“责任核心”,需要为公司的非法行为承担责任,俗称“背锅”。如公司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被强制执行时,法定代表人会被限制高消费、出境自由,由此引发法定代表人退出公司的纠纷,被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请求变更登记。在此类纠纷中,部分法院认为,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属于公司的自治事项,法院不能强制公司作出决议变更法定代表人,亦无法直接代替公司变更其法定代表人,因而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①。甚至法定代表人仅为挂名,并未实际参与经营管理,也受到公司非法行为的牵连,被限制高消费,法院也以法定代表人的任命及变更为内部事项为由驳回变更请求②。如果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一直不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内部变更后不及时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手续,企业公示信息系统中公示的法定代表人就会一直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法定代表人在公司中的实际地位差异较大,有的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有的不参与经营管理,公司不执行法律文书的行为可能与法定代表人有关,也可能没有关联性。那些挂名法定代表人或者已经从公司离职的法定代表人,未曾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与公司的非法行为并没有关系。
(二)“同一人格”理论遮蔽了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同一人格”理论的旨在解决代表行为的后果归属问题,原则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代表行为即公司行为,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在“同一人格”理論的涵摄范围之内。然而,这一理论在解释适用过程中,与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中的“一长制”的理念共同作用,使立法和实践产生了“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认知。一方面,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具有实质关联性①;另一方面,法定代表人的唯一性,民法学界将法定代表人解释为“一般由公司的董事长等正职担任,为唯一确定的自然人,享有当然的代表公司的权利”。[7]由一名自然人担任法定代表人与由多名自然人担任相比,前者更能契合“同一人格”理论,也使该理论的解释适用更加圆满。法定代表人与公司的实质关联性、唯一性,将二者捆绑为一体,遮盖了二者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使审判实践对法定代表人变更纠纷产生认知分歧。有的法院认为二者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②,有的法院则认为二者系公司组织内部关系③。不同的认知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的结果。此外,法定代表人的唯一性,也是判决执行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登记机关拒绝执行判决书的理由为“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登记行政法规,涤除法定代表人后必须要有人员接替不能缺少法定代表人登记事项……”④,如果法定代表人由复数自然人担任,协助执行机关就不能以此为理由拒绝办理涤除登记。
四、重塑法定代表人规范,破解涤除登记的实践困境
近年来,法定代表人变更纠纷频繁发生,司法裁判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均与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的理念和实践认知有非常大的关联性,预防并顺利解决纠纷的关键在于厘清法定代表人的地位,重塑法定代表人规范,为审判实践提供清晰的思路。
(一)法定代表人权限的去“核心化”,回归“代表”的本质功能
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权力与责任的核心位置,集代表权与经营管理权于一身,公司的意思形成与意思表达均为法定代表人完成,加之商事登记的外观,在公司外部与内部形成了“法定代表人=公司”的简单而粗糙的逻辑认知。之所以形成这一认知,是没有认清法人的意思表示的特点。法人的意思表示与自然人不同,自然人意思形成与意思表达由一个主体完成,公司的意思形成与意思表达在形式上是分离的,分别由决策机关和表达机关完成:股东会、董事会以决议方式形成公司的意思,通过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代理人对外宣示披露公司的意思。[8]虽然在小规模公司中,代表机关和意思形成机关往往是重叠的,但二者在理论上依然有着清晰的区别。既然公司实施法律行为时的意思表示具有可分离性,从学理的角度而言,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应当仅为公司的“代言人”,经营管理权并不是法定代表人本有的权限,而是在身份重叠的情形下,作为董事长、执行董事、经理所享有的权限。[9]
基于公司意思表示分离的特性,应将本属于董事、经理等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权从法定代表人“无所不包”的权限中剥离出去,法定代表人回归其“代表者”的本质,使公司的代表权与决策管理权“桥归桥,路归路”。法定代表人去“核心化”的结果,一方面,能减少争夺公司控制权的纷争,同时防止法定代表人承担超过其代表职能的责任,无由为公司行为“背锅”,减少和预防纠纷的发生;另一方面,能够打破公司与法定代表人“同一人格”的魔咒,厘清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
(二)拨开“同一人格”的迷雾,厘清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本质关系
法定代表人的“权责核心”地位被纯化后,作为单纯的公司意思表达机关,其与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对于解决“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问题至关重要。可以从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的性质入手,厘清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我国学理上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的性质有代表说和代理说两种解释。
代表说以“同一人格”理论为基础,认为代表与被代表人同属一个人格,代表人实施的法律行为即被代表人的行为。[10]然而,对“同一人格”理论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有学者认为,法定代表人是自然人,而公司则是区别于法定代表人的由人和资本构成的独立主体,二者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会存在利益冲突,“同一人格”是不切实际的假想。[11]还有学者认为,不区分法人与自然人,将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均视为法人的行为,可能导致法人需要承担越权代表行为的后果。[12]代理说则认为代表与代理在规范来源、登记与否、权限范围等形式方面有差异,但二者在行为要件、法律行为后果归属上并无本质区别,法定代表人制度可以视为代理法的特别法,是一种特殊的代理。[13-15]既然“同一人格”的理论不能贯彻始终,代表制度独立于代理制度也就失去了支撑,其实只是一种特别的、适用公司领域的代理,法定代表人是通过法定系统公示的代理人,其真正独特之处在于登记制度。[16]对“同一人格”理论的种种质疑至少说明该理论并非行之四海皆具合理性,代理行为的后果归属与代表并无不同,且二者均以代表人或代理人执行职务为构成要件,实际上代表人或代理人均具有独立的人格。
既然公司授予法定代表人代理权,法定代表人为公司实施法律行为,那么,依民法学理,二者之间必然存在来源法定或意定的基础关系。[17]法定代表人的产生、消灭源自公司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其权限来自章程规定,同时章程也会对其权限施加一定的限制,因而公司与法定代表人之间关系并非源自法定,而是双方意定的结果。公司内部决策机关选定法定代表人后,公司与被选之人协商,征得其同意即形成平等主体之间的委托关系。部分法院也持相同观点,“王某请求终止其与公司之间法定代表人的委任关系并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该纠纷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①。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的规定,作为受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有权随时解除委托关系,双方对任职期限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从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本质关系出发,法院解决法定代表人变更纠纷时,应当采取以下思路:首先,应当受理平等主体之间的委托合同纠纷;其次,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解除双方的委托合同,终止代表关系。委托合同双方均享有任意解约权,可以随时、无条件地解除委托关系,但是应当赔偿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然而,大部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并没有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裁判,而是将审查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⑴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是否存在实质利益关联,如“一个与公司已无实质关联的人,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某已从公司离职,并办理了退工手续,其与公司已无实际关联,如果继续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违背立法的初衷和本意”②。其实,法定代表人接受公司“代言”的委托,与参与公司管理、签订劳动合同等所谓“实质关系”,是两类不同的法律关系,有各自不同的处理规则。当然,基于意思形成与意思表达的内在逻辑性,实践中由作出经营决策的机关代表公司实施法律行为,更加符合商事交易安全和效率的要求。⑵权利主体是否需要救济。如“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选举、任命和登记,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畴,司法一般不应予以介入。但是,当公司内部治理失范,且有证据证实已对相关权利主体利益造成侵害或者发生侵害的可能时,司法可以有条件地介入并提供救济”③。诚然,法定代表人的任免需要履行公司内部程序,属于公司自治范畴。但公司内部选定某人作为法定代表人,仅仅是公司单方意思,还必须征求候选人的意思,双方达成合意才对双方发生法律效力。公司与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委托关系与公司内部任免决定,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范畴,分别依据《民法典》和《公司法》处理,只有公司和法定代表人的双方意思或单方意思才能影响委托关系的效力。
(三)打破法定代表人“唯一性”的禁锢,赋予公司设定多元代表模式的权利
《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法定代表人,该条款反映了我国法定代表人范围的法定性和人数的单一性。法定代表人的单一性是公司治理中“权责核心”地位形成的重要前提,同时,单一的法定代表人也不适应事务繁多的大规模公司的经营管理需求。因而,解决相关纠纷的关键在于打破法定代表人的唯一性,使法定代表人的地位回归本质。
与我国有类似代表制度的大多是大陆法系国家地区,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78条,《瑞士债务法典》第716条(B)、第811条、812条,《韩国商法典》第389条等。与我国的法定性、单一性相比,这些立法有以下特点:⑴公司代表人的范围比较广泛,全体董事、经理乃至股东等其他人均在代表人候选范围之内;⑵代表人的人数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数人;⑶立法充分尊重公司自治,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对代表人的确立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英美法系国家采法人拟制说,法人不具有行为能力,因而公司法中没有代表人的概念,不存在代表与代理的区别,公司与董事、经理之间的关系通常认为是代理关系。[18]从代理的角度而言,英美国家公司的代表人的范围更加广泛、公司的自治性更强。
域外法定代表人制度的这些特点,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且不会与现行制度相冲突。关键是扩大公司确定法定代表人的自治权,这一观点目前被学界多数学者所接纳。我国公司只能在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中选择一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自治权限有限。所谓扩大公司自治权。我们多数学者也主张扩大公司确定法定代表人的自治权。[19]首先,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多人的共同代表或者一人的单独代表的模式;其次,公司可以自由选择代表人,各国的主流做法是由董事会或其成员及经理作为候选人,甚至《瑞士债务法典》规定股东乃至非股东的第三人也可以担任代表人。实际上,在厘清代表人的法律地位,将其限定为公司“代言人”角色的基础上,代表人不一定必须由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可以扩大到公司认可的其他主体的范围。当然,基于意思形成与意思表达的内在逻辑性,实践中,由作出经营决策的机关代表公司实施法律行为,更加符合商事交易安全和效率的要求。当然,基于意思形成与意思表达的内在逻辑性,实践中由作出经营决策的机关代表公司实施法律行为,更加符合商事交易安全和效率的要求。
此外,我国的诉讼实践对法定代表人唯一性的僵化规定已有所突破,如《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法定代表人须代表法人进行诉讼,实践中往往因为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产生纠纷而无法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对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解决措施是:首先尊重公司自治,章程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章程没有规定的,由股东大会协商;协商不成的,法院在副董事长、其他董事、监事会主席或执行监事、其他股东中指定①。司法实践为法定代表人制度的重塑开拓了思路。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第五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132.
[2]朱广新.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J].中外法学,2021(3).
[3]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88.
[4]方流芳.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权利和利益冲突[J].比较法研究,1999(3).
[5]刘俊海.现代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495.
[6]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课题组.公司意志代表权争议的现状与问题解决思路[J].法律适用,2013(5).
[7]江平主编.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49.
[8]蒋大兴.公司意思表示之特殊构造[J].比较法研究,2020(3).
[9]朱锦清.公司法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266.
[10]梁慧星.民法總论(第五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132.
[11]袁碧华.法定代表人的制度困境与自治理念下的革新[J].政法论丛,2020(6).
[12]王利明.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92.
[13]迟颖.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效力与责任[J].清华法学,2021(4).
[14]董俊峰.董事越权代表公司法律问题研究[J].中外法学,1997(1).
[15]蔡立东,孙发.重估“代表说”[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6).
[16]殷秋实.法定代表人的内涵界定与制度定位[J].法学,2017(2).
[17]李永军.民法学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128.
[18]杨汝轩.论中国公司代表人制度的改革—以两大法系的比较为视角[J].河北法学,2012(11).
[19]刘斌.公司治理视域下公司表意机制之检讨[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2).
(责任编辑:赵婧姝)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legal representative registration to settle disputes,courts often facedifficulties in each stage of acceptance,judgment and execution.The theory of“the samepersonality”between the company and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as well as the“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core”position formed by the overlap of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s status in thecorporate governance,make the commercial practice and judicial practice ignore the tru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and the company,making the trial into a dilemma. Based on the separability of the expression of the company's will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the function of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is to represent the compa-ny externally,rather than to control the company'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A deleg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and the company is formed as an equal subject,which is an agent outside the registra-tion. The companyhas the autonomy to set up multiple legal representatives.
Key words:registration and elimination;identical personality;same personality;legal represent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