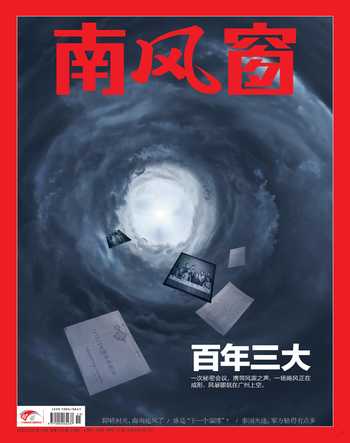毛泽东思想,于此萌芽
赵义

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湖南,中共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央工作,参与筹办中共三大。毛泽东先到了上海,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驻地迁往广州,他又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一起“经沪赴粤”。
6月,毛泽东在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成为五位中央局委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还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按照规定,当时中央的文件需要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签署才能发出。
毛泽东时年30岁,刚入而立之年,论职权已经是党内事实上的“二把手”。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毛泽东在国共两党都担任高级职务。一个公认的说法是,正是在广州这个大革命的中心,毛泽东逐步完成从地方革命领导人到全国性政治人物的角色转变。
当然,对当时的共产党人来说,“当官”的观念甚至连“淡薄”都谈不上,他们搞革命,没有个人私立权衡,就是要拯救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对中国革命而言,毛泽东在广州、广东这个大革命舞台上的这段经历,开始催动毛泽东思想的萌芽,真正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开始破土而出。
广州是毛泽东思想重要的萌芽地,起码是之一。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读过《毛泽东选集》的人都知道,第一卷开篇的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上世纪50年代以来,《毛泽东选集》有过数次修订,但无论哪次修订,这篇文章的位置雷打不动。这篇文章相当于毛泽东思想的开山之作。而这篇文章从酝酿、发表到修改、宣传,都是在广州。
共产党是信奉阶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给中国人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有力工具。但这并不等于就有了现成答案。就像《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第一句话说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基本原理。紧接着举的例子主要是欧洲历史上出现的各组对立阶级,没有直接谈到中国。那么,基本原理怎么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开始就把思考的出发点摆了出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思想萌芽期和思想成熟期的著作相比较,理论成熟度肯定要低一些,但其特色是简洁明快。当时的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期”,很弱小,要领导国民革命,深感力量不足,也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是要帮共产党分辨真正的敌友。文中道理看似浅显,但一下子就说到了要害上。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毛泽东是一个很少受教条束缚的人,理论在他眼里是要解决迫切问题的。
这篇文章的另一特点是,可能出自敏锐的直觉,毛泽东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的“特殊”。文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共产党人那个心头之困—他们所从事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但中国工业落后,产业工人数量有限。毛泽东并且预见到了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时称之为“中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文中道理看似浅显,但一下子就说到了要害上。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毛泽东是一个很少受教条束缚的人,理论在他眼里是要解决迫切问题的。
如果对比一下毛泽东思想成熟时对革命对象、动力、领导阶级等的论述,其基本思想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大致都具备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重要文章能在广州产生,有一定的必然性。广州当时本身就是各种主义和改造社会方案公开登场的中心之一,也是各个阶级聚集、互动的中心之一,在广州能够直接感受和观察到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复杂关系。比如商人,既有过革命的合作,又有过矛盾冲突。革命阵营里的分分合合,在这座开放城市里多次上演,历史经验丰富。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也是如此。工人阶级力量太小、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这点,一般人都能认识到。就像毛泽东后来讲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但能不能认识到要把搞革命的主要精力放在农民身上,这是另一回事。其实,共产党成立后,早期主要精力是放在工人运动上,这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很自然的选择,就连毛泽东自己,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把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估量得这么高。
周恩来1949年5月7日曾经对青年做过一次如何学习毛泽东的演讲,其中就提到:“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
在三大期间,毛泽东发言时就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有三大的代表回忆:“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们才注意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还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
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根据对孙中山亲自拟定的候选人名单的表决,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員,随后去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1925年,毛泽东回湖南养病,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再到广州后,他开展了很多与农民运动相关的研究与实践,特别是担任了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还主持编辑《农民问题丛刊》,总结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
正是在主办第六届农讲所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中心问题”的理论,思想、逻辑均已明白贯通了:“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广州和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对这个理论的形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国共合作后,国民党也成立了中央农民部。在广州和广东,农民运动天然是“合法”的。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提供了保护和支持,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有时候,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人还应请求派出军事力量支持农民运动。
这种农民运动不仅仅是经济性质的,更是政治性质的,农民组织起来接管了原来掌握在乡绅等少数人手中的权力。正如毛泽东总结的,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就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只要读读“广东农民大会决议案、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广宁普宁两个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不由得不有此感觉”。许多人不懂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细看关于广东的资料”。
如前所述,不重视农民问题的那些早期领导人,并非没有看到农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这个事实,从一般意义上也主张农民要加入国民革命,但他们更多的是只看到农民身上的弊病,比如散漫不集中、文化低下、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等,他们没有看到组织起来的农民、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农民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毛泽东看到了这些。广州和广东的革命实践,也告诉了“幼年期”的共产党这些。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把革命重心迅速转移到农村,就是必然的。正如周恩来说的,“大革命时期,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的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
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
毛泽东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同时,相对于那些以正统自居的讲马列理论一套一套的早期领导人,他身上所受的理论框框的束缚是很少的。搞革命对他而言,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等等这些东西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毛泽东支持国共合作,一点都不奇怪。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共产党的力量的确得到了迅速发展。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但能不能认识到要把搞革命的主要精力放在农民身上,这是另一回事。
同时,他又非常重视独立自主。比如,他就不同意“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主张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組织上的独立性。他甚至也不同意把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混为一谈,因为“我们是共产派”。三大的决议案就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对处于“幼年期”的共产党而言,要处理好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的关系,难度不小,往往是为了联合战线不破裂而不得不退让,退到最后就再无可退,因为新军阀举起了屠刀。就像毛泽东后来总结的,“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这两种错误我们党都犯过,经验很痛苦。”这些“痛苦”往往是在革命一线打拼的人体会最深。可以说,对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在统一战线上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是有切肤之痛的。在他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时,国民党右派如果还想和第一次合作时一样打共产党的歪主意,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搞国民革命,必然需要统一战线,这是中共三大干的事情。而在联合过程中如何既团结又斗争,又非常考验政治艺术和领导艺术。作为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在国共两党内都非常活跃的“高层”政治人物,毛泽东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是切中肯綮的。
总之,无论从阶级分析、农民问题还是统一战线等方面看,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根据广州和广东风起云涌的革命实践,提出的相关理论,的确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的起点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论,对“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解,早期就是从广州等地的革命实践中获得的。
一个深远影响历史的政治巨人,和一个大革命时期的革命中心,相互成就,值得我们反复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