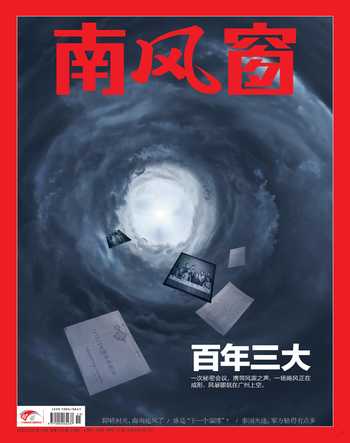狂风暴雨中的陈独秀
董可馨

1922年11月,身为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的陈独秀动身前往莫斯科—这个当时的马列主义“圣城”,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同行的,还有产业工人王荷波,翻译刘仁静。
据当时正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共旅莫支部领导人彭述之后来的回忆,陈独秀“中等身材,前额宽广,留有小胡子,牙齿整齐洁白,体态文雅,待人随和,但警惕性极高;眼神炯炯,闪耀着智慧之光”,具有充沛的生命力。
“他的仪表确是与众不同,显然是一位大知识分子型。有时他那悠悠自得的神情几近乎风流倜傥。他是一位健谈者,在不拘形式的谈话中,顷刻间就能把对方征服。他不断地旁征博引,常常是妙语连珠,妙趣横生,确实引人入胜。他能把我们所有听他说话的人逗乐了,甚至是件小事也会逗得我们开怀大笑,直到笑出眼泪来。说他是一位地道的逗人欢乐的人,并不为过。”
那时的陈独秀,40多岁,正是壮年,意气风发。他已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编刊立言的知识分子、学者,转身成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切实的革命者,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也开始有了共产党这一将之作为毕生理想来努力的实体。
可是令当时参会的中國代表感到极其意外的是,陈独秀和中国代表团,根本没有受到多少重视和礼遇,更没有受到列宁接见,只是正常参加会议,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拉狄克不留情面的“训斥”。
陈独秀本人对中国留学生谈起这次四大时,也不怎么热情,后来也没有留下什么回忆。
1922年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尴尬,是他在国民党、莫斯科之间处境越发尴尬的缩影。五四以来,陈独秀由一位西式自由民主倡导者,一变为不主张暴力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再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变为一个大革命失败时承担责任的落寞领导人,这位傲骨铮铮、性情狂飙的思想者、革命者,也许最能深切体味知与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艰难与妥协。
三个心理坎
在共产国际的会上,拉狄克对中国代表团的“训斥”是:“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
或许在陈独秀听来,这话多少有点官僚主义的自以为是和想当然,但他和共产国际真正的心理隔阂在于对方的轻视和自我期许不符的心理落差。
像他这样充满革命热情和奋斗激情的人,要处处接受遥远北方的指示和指导,还要在国共合作似乎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想尽方法来争取和保全自己的独立性,这并不容易,不仅得说服同志们,也得花力气来说服自己。
对于共产国际来说,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力量显然太弱小,不足以承担起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任务,当然,也不足以独力承担在中国进行符合其设想的革命活动。
但苏俄和共产国际自身,在1921年至1922年间,也谈不上对中国形成了多么成熟的认识,多么稳定的政策。
彼时中国国内的形势并不明朗,几大军阀拥兵自重,盘踞各方,孙中山展示出了积极的革命意志,正用心于讨伐打败了皖系、控制着北京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却也根基不稳,总是转徙于不同的投靠者和援助力量之间。
像他这样充满革命热情和奋斗激情的人,要处处接受遥远北方的指示和指导,还要在国共合作似乎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想尽方法来争取和保全自己的独立性,这并不容易。
联合谁,苏俄和共产国际也是有反复的,所以它们几乎像是在投注似的,示好过陈炯明,联系过无政府主义者,也团结过吴佩孚,认定吴具有革命性。只是到了1923年初吴佩孚对苏俄在华利益的拒绝以及屠杀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惨案”发生,它们才放弃了联吴的政策。
最后注意到国民党,这个在20年代初非常重要的具有革命性的政治力量,莫斯科给予了重视,也积极团结,并且先后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乃至加入国民党的要求。
在孙中山这边,军阀的威胁、帝国主义的欺凌、国民党内部的混乱和叛变令他精疲力竭。要完成北伐这一他后半生的执念,仅靠军力、财力尚且单薄的自己,还不足够,尤其是1922年6月,孙中山竟还被陈炯明赶出广州,势力已极衰弱,非常需要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援助。
晚年的孙中山也明显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亲近,并曾在一次演讲中表示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称为民生主义的“一个好朋友”。
但孙中山也绝不认为自己的国民党就和共产党是一回事,在1922年初,孙中山与越飞分别代表国民党与苏联政府签订协议,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声明:“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但不论如何,1922年还面临重重危险和困境的孙中山与国民党,在1923年后,积极转向,完成了联俄联共,孙中山也重返广东,终于准备迎来国民党最好的时候。
而中国共产党,则在国共合作和几次罢工运动中,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陈独秀,这位党的领导人的个人命运也随之巨变。
对于陈独秀来说,这一过程,是把自己融入党的组织,把党的组织融入共产国际的组织,把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融入世界革命之中。
个性刚烈如他,有几个心理的坎要过。
一个是,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由怀疑到信任,再到服从。
一个是,和国民党的关系,由排斥到接受合作。
一个是,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由两党平起平坐的党外合作,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
两次入狱
中国共产党是知识分子创立的党。南陈北李,一个是北大文科教授,一个在早稻田大学毕业,是北大图书馆主任,都是卓越的思想者、理论家。
他们最早的活动都是从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的,在创立党的组织前后,陈独秀延续观念革命的习惯,着重于思想启蒙,甚至并不急于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也不急于发动革命。
据和陈独秀联系密切、曾参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回忆,建党早期的陈独秀认为,在中国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还很遥远,无产阶级革命还要一百年上下,所以要慢慢来,尊重客观规律,不要妄想一步登天。
在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决议加入第三国际、组成民主联合战线之前,陈独秀对共产国际与苏俄也仍然有很大的心理距离。
当时的陈独秀主张一面工作,一面革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要第三国际的钱,因为拿了钱就要受制于人。
因此,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接触之初,陈独秀与他之间多有分歧和矛盾,一度闹得很僵。如马林提出,党的领导机关会议他必须参加,但是陈独秀不愿意答应,认为这有监护性质。马林有时和国内的共产党员联系派任务,也不经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这也令陈恼怒。
在陈独秀心中,中国的革命运动虽然与世界劳苦人民的革命运动有联系,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生产落后的国家,有自己独立的国情,也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意愿来做事,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这和急切的莫斯科并不完全同频。
不过,陈马关系在一次颇为偶然的机缘下,发生了转机。
这件事情是,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家中被捕。
其实当时警探并不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陈独秀在捕房登记时,用了王坦甫这个假名。但是,随后去陈家拜访的国民党要人褚辅成也被蹲守的暗探逮捕。在捕房,褚一见到陈独秀就拉着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结果,陈独秀的身份暴露。
陈独秀被捕入狱后,马林花了大力来营救,一边找著名律师来打官司,一边保释,打点各个环节的关系,最后,罚了一百元结案。
对于陈独秀来说,这一过程,是把自己融入党的组织,把党的组织融入共产国际的组织,把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融入世界革命之中。
陈出狱后,两人都收敛了自己,关系有所缓和。陈独秀也开始专心于主持党务工作,并且,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
陈独秀一生多次入狱,而不免巧合的是,他的上一次被捕入狱,也对他的人生改变起到某种影响。
1919年6月,正是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在北京街头散发传单,那一次,他被潜伏的京师警察厅密探逮捕,在牢狱中关了98天。
如果按胡适的说法,陈独秀这一次的被捕入狱促使他个人思想发生转向,获得一种宗教感召,接受了共产主义。显然,陈独秀被捕是他一个道路反思与重择的契机,但胡适的描述却显得太玄乎了。
而这一次,马林和陈独秀,莫斯科和中共中央,终于能坐到一张桌子上来,共商革命大事业。
形势比人强
若按陈独秀自己原本的意思,他是不愿意和国民党合作,更不愿意加入国民党的。他连远在天边,但能提供经济援助的莫斯科都敬而远之,怎么能忍受和近在身边的国民党同气相求。
但和国民党越走越近,却是形势比人强。
关于国共合作,列宁曾亲自提议。在1922年1月,列宁接见了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国焘、孙中山指派的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等人,并在会面中问二张:“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
两人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同年3月,来到中国的马林,向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想法。
这被称作“斯内夫利特策略”(斯内夫利特为马林的姓)。
根据他对中国当时社会状况的考察,马林认为,在中国还没有发生共产国际所期待的工人运动,中国的现代产业工人的人数也太少,绝大部分人口依然是农民,但农民对政治漠不关心,难以发挥政治作用。
他对国民党表达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认为三民主义“为各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所以他认为共产党也可以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但同时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
陈独秀对列宁的提议“深表同意”,但反对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
1922年4月6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发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不同意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原因:
一个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宗旨和基础不同;再有,国民党联美、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另外,在外界看来,国民党的名声很不好,是一个争权夺利的党,共产党员如果入了国民党,也要被连累了;如此等等。
但是,陈独秀并非一股脑地反对,他也做了改变。比如,他在6月份发了 《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以党的决议的方式,向外界宣告共产党邀请并接受和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社会主义团体,建立联合战线。
但是,陈独秀的底线对于国民党和莫斯科来说,仍然太高了。
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马林发指示,“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在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
8月,为了促成国共合作的西湖会議召开。这次会议过程比较激烈,据陈独秀的回忆,当时与会的几个中央委员及他自己,都反对马林的提议,认为两党的混合方案会牵制共产党,影响独立性。
面对他们的拒绝,马林最后提问,中共是否服从共产国际。
陈独秀只好表态:“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更改的决议,我们应当服从”。
随后,陈独秀也开始说服党内的反对者。在机关报《向导》上发表《国民党是什么》,其中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他的政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这和他之前对国民党的认识和说法,都不同了。
西湖会议后来被认为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石。
而在共产党员入党问题上,陈独秀则坚持要求国民党不可以保留宣誓服从党魁、打指模等入黨办法。西湖会议也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前提条件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孙中山也很痛快地答应要以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
1923年4月,中共中央迁到广州,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召开。三大的一个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服从在西湖会议上确定下来的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最后决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在陈独秀心中,中国的革命运动虽然与世界劳苦人民的革命运动有联系,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生产落后的国家,有自己独立的国情,也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
中共三大,是建党元老李大钊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又返回北京,并准备迎接接替马林的鲍罗廷。
革命的复杂性
接替马林的鲍罗廷于1923年8月底来华。
“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陈独秀语)的鲍罗廷来华后,国民党与莫斯科的关系升温,而对于陈独秀来说,他的空间则在收缩。
1924年,列宁逝世,次年,孙中山也逝世了。
陈独秀所面对的两面,内部都发生了很大的分裂与变化。在莫斯科,斯大林胜出,
国民党内,蒋介石胜出。斯大林口中的“国民党领导”,在陈独秀听来也分外刺耳了。
此时,共产党获得大发展,党员人数大增,由一个知识分子的小团体,成长为全国性的群众性政党,但国民党内部所酝酿的排共倾向,在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和之后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人数的“整理党务案”事件中,也愈发明显。
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陈独秀两度想退出国民党,但均没有得到莫斯科的同意,而他亦失了方寸,最后决定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1927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遭受重创,陈独秀的威望也急剧下降,最后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留下历史定性。
在具有离别意味的 《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检讨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坦述了自己如困兽般的处境。
他有个人的意见和意志,但每每当他的意愿和莫斯科的意见相左时,他最后都不得不“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自己的提议。而他每一次的自主意识带来的是莫斯科更大的压力,以致他终于无所作为。
这一点,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也有所表达:共产党既要发展农民运动,又不能破坏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既要实行领导,又不能变成指挥,这是特别困难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的处境和所犯的错误,也是中国革命复杂性的一种反映。
在大革命失败中淬火重生的中国共产党,则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找到了独立自主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