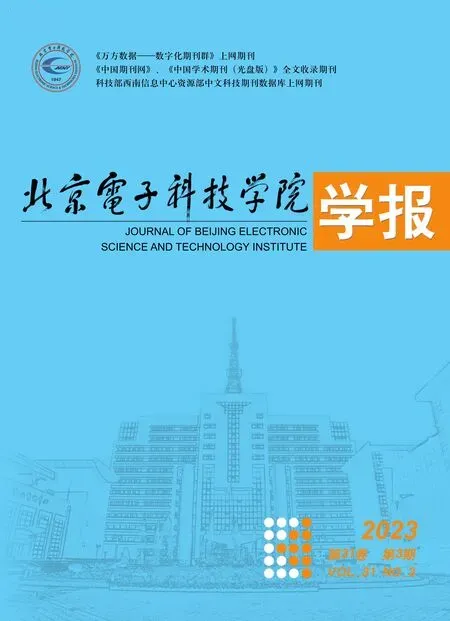苏轼的物我之思及其美育启示
马 蓉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北京市 100070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物”往往积淀着主体对宇宙、社会、人生等各个方面的体验和经验,“具有本体范畴的意味”[1]209,如何看待“物”事实上隐喻着主体如何看待自我与自身的外在境遇。 苏轼对物我关系①有关苏轼如何看待“物”的问题,学界多从其文艺观的角度进行讨论,如冷成金《从<东坡易传>看苏轼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指出,苏轼在形而下的纷纭的物象中寻求其形而上的同一性;罗书华《应物:苏轼文道的新变》认为苏轼以物为道的源泉,以“应物”“观物”“寓物”“游物”为道和致道方法;沙红兵《论苏轼的“物我平等”思想与诗艺》认为苏轼视物我都是无须任何外在根据的自身的存在,同时也通过彼此彰显自身的存在。 对本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思考极具典型意义,他融通儒释道三家,继承道家在“心斋”(《庄子·人 间 世》) “坐 忘” (《庄 子·大 宗师》)中“吾丧我”(《庄子·齐物论》),吸收佛家“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2]79,在庄禅思想的影响下走出物执而任性逍遥。 但他又否弃庄禅忘世的一面,以儒家志道济世的思想为根抵,由“格物”而“致知”,在伦理政治范畴中穷尽物的价值,从而“诚意”“正心”“修身”“齐 家” “治 国” “平 天 下” (《礼 记·大学》),将心灵的自由导向自我价值的建构与人格境界的提升,提供了一条由观物进入审美、进而指导现实的独特道路。 这一理路正与马克思主义美育“自由自觉”的精神指向一致,亦即通过诗意的审美活动,在认识和把握对象世界中认知和肯定自我,“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189美育的关键在于通过“美”的启发“培根铸魂”,从而培养“完整的人”。 如何实现“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163苏轼对物我关系的思考或许可以提供一种独特的思路。
1 破除物执:“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
《宝绘堂记》中,苏轼提出了对外物的两种态度,“寓意于物”与“留意于物”: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4]356
“留意于物”是实用的物质功利态度,主体以物足欲,则物为心执,我为物役,故有得失之患,最终为物所累;“寓意于物”则是超功利的审美态度,主体不为物滞,以物寄意,则物无不可,皆为我用。 老子以“五音”“五色”“五味”“驰骋田猎”令人陷入物欲不可自拔而言“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5]118(《道德经·十二章》),主张除基本的生理需求外摒弃一切物欲。孔子则“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6]100(《论语·述而》),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坚实人格修养基础上“游于艺”[6]96(《论语·述而》)。 苏轼吸收老子思想对物欲的否弃,后文中反对钟繇、宋孝武、王僧虔等人因留意于“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的书画而“害其国凶此身”(《宝绘堂记》)。 但他并不弃物,继承儒家思想而言“圣人未尝废此四者”。 在《书六一居士传后》一文中,针对时人提出的欧阳修怀琴、棋、书、酒、金石遗文而后安不为有道,“有道者,无所挟而安。 居士之于五物,捐世俗之所争,而拾其所弃者也。 乌得为有道乎?”他反驳道:
挟五物而后安者,惑也。 释五物而后安者,又惑也。 且物未始能累人也。 轩裳圭组且不能为累,而况此五物乎? 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 吾与物俱不得已而受形于天地之间,其孰能有之? 而或者以为已有,得之则喜,丧之则悲。 今居士自谓六一,是其身均与五物为一也,不知其有物邪? 物有之也。 居士与物均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丧于其间! 故曰:居士可谓有道者也。[4]2048
时人之误在于有“留意于物”的得失之心,因而便有“挟物”与“释物”的心理状态,物便能“累人”。 而苏轼认为,欧阳修并非自一得五,而是与五为六,心无挟释之意,则轩裳圭组与琴棋书酒也没有本质的差别,一切皆为主体“聊以寓意焉耳”的媒介。
“寓意于物”强调的是在物我关系中破除主体对物的占有欲,始终保持自我精神的独立性,其实质也不止于表层的以物寄托情志,“寓意于物,亦即他所说的‘游心寓意’,与物同游,与万物共成一个独特的体验世界。”[7]是在对物的观照中获得适情适性的审美体验,“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4]2211(《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只有对现象界的声色动静无留意之心,方能摄万物而不撄一物,“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8]863(《送参寥师》),在乘物游心中臻至审美的极致状态,在“美”与“自由”的感受中实现对外物的彻底超越。 《涵虚亭》诗云:“水轩花榭两争妍,秋月春风各自偏。 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8]642水轩、花榭因秋月春风之偏而“两争妍”,但“天全”只有在“无一物”的“坐观”中才能获得,所得的“天全”为何物? “醉者坠车庄生言,全酒未若全于天。 达人本是不亏缺,何暇更求全处全。”[8]212(《谢苏自之惠酒》),天全”便是“本是不亏缺”,指向的是圆融自足的心灵境界。审美主体在澄怀忘羁中静观默照,“万景”皆在其澄明自足的本真之心中呈现,主体也在任意纵兴中获得心无所滞的绝对精神自由,故而苏轼观山水图卷亦能不为画图拘囿,“烦君纸上影,照我胸中山。”(《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著色山二首》其一)[8]1547“赖我胸中有佳处,一樽时对画图开。”(《次韵子由书王晋卿画山水二首》 其二)[8]1681超越画图而触境自得。
如何走出物质欲念的纠缠、裹挟甚至奴役,是人类思考的永恒问题。 现代社会中,这一问题更加突出,理性化及其带来的“世界的祛魅”[9]29导致信念伦理和价值理性的消解,工具理性的单向扩展使得现代社会的价值导向变为物质主义,人逐渐被物异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3]190,作为主体的人的意义的世界几乎完全被笼入“用”的网络。 如何处理“物”与“我”的关系? 苏轼提出的“寓意于物”启示我们,走出“留意于物”的物质占有,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万物,方能明心见性,超越“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具体现象拘囿而至“庐山真面目”[8]1155的本体美境域,从而在乘物游心的审美体验中构建起自由自足的精神世界,最终实现“从自身产生出他的内在丰富性”[3]111,实现人生的艺术化和艺术化的人生。 席勒谈到美育的特点时曾说,美育便是“通过自由去给予自由,这就是审美王国的基本法律。”[10]145“寓意于物”的价值旨归正契合这一特点,指向的都是对人性自由完满至境的永恒追询。
2 心性涵养:“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
熙宁七年(1074),苏轼任杭州通判期满,改任密州知州,期间修葺州城西北城墙旧台,取苏辙建议名之为“超然台”,作为“相与登揽、放意肆志”之所。 在《超然台记》中,苏轼写道:
凡物皆有可观。 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 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 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 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4]351
事物所以有美恶之辨、小大之分,在于人“游于物之内”,主体心灵被外物拘囿而“隙中观斗”,于是忧乐生焉。 “游于物外”则是以一颗无往而不适之心应物,事物的外在差别在主体随缘任运、自适自得的审美化心灵境界中得以消弥,自然“凡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 《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便隐喻此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朦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8]404诗人以妙笔点化出山水形象背后的道思,西湖自有“水光潋滟”“山色空朦”之美,更重要的是审美主体不因晴、雨影响心灵的安适,是故目之触处,风景皆宜。
相较于“寓意于物”的不执,“凡物皆有可观”强调将主体心灵从外在现象与内在桎梏中提升出来,在自我人格的涵养中消融外物的客观差别与人为设定的主观标准,从而走向“君子广心,物无不可”[4]576(《广心铭斋》)的“燕处超然”之境(《道德经》二十六章)。 这不仅是苏轼对物我关系的思考,更是他指导现实实践的人生态度。 回到《超然台记》的写作背景,时苏轼由民丰物阜的杭州移知“民物椎鲁,过客稀少”[4]1395(《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的密州,“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4]351(《超然台记》)且当时密州“蝗旱相仍,盗贼渐炽”“公私匮乏,民不堪命”[4]753(《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4]351(《超然台记》)。苏轼曾有《蝶恋花·密州上元》一词,通过对比上元节杭密两地景象对比书写自己的心境变化:“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 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 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 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11]140可见“灯火钱塘”到“寂寞山城”的落寞情绪。 但苏轼并未消沉,而是勤于吏职,赈灾、剿匪、扶贫、济困,经过一年的时间,密州面貌得到极大改善:“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4]1891(《与灵隐知和尚一首》)。 心境也愈加安适,“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 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4]351(《超然台记》),以生命实践诠释了“凡物皆有可观”的意蕴。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轼无论谪黄贬儋,都能很快调整心态,将外在的穷达宠辱、沉浮毁誉排除出主体思维系统,以一颗超然物外、自足自适之心体认现实,打开了全新的生命境界。 黄州期间,苏轼有《定风波》一首自抒情志: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11]356
完整呈现了苏轼由风雨之行返归内心,以圆融自适的审美人格超越外在风雨的理路。 词前小序中写道“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 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上阙写雨中感受,在“雨具先去”的境遇下,苏轼不同于“同行皆狼狈”的状态,而是竹杖芒鞋、蓑衣笠帽徐行烟雨,以“游于物外”的态度看待环境的变化,故不惧外界风雨。 下阕则是对雨晴后的心理感受,苏轼在吟啸徐行中了悟,“穿林打叶”“山头斜照”都是外在的现象,无须挂碍,风雨与晴天的差别在审美主体无往而不适的心灵境界中全然消泯。 正因参透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本质,以“凡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之心看待外物与环境的变化,苏轼经七年的惠儋贬谪生涯后,在遇赦北归途中总结自己的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4]2641(《自题金山画像》)身居庙堂多年,苏轼做了大量利国利民之事,却独钟情于遭贬几死而无权签署公事的黄州与岭海时期,不仅超越了外物,更超越了主观的得失之心走向审美的人生。
在“凡物皆有可观”的思维中,“我”不仅“游于物外”获得极致的审美自由,更在“安往而不乐”中“肯定人本身在认识世界完善人格的主体作用”[12],将精神的自由与超越导向心性世界的涵养融炼,从而建构起审美的人格。 这一理路也启示着我们对“美”的价值指向的思考,“人同美只应是游戏,人只应同美游戏。”[10]86而“游戏”带来的不应只是感性上的愉悦,更应在超越现实功利的“存在”状态中“反求诸己”,在精神的自由中涵养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得至美而游乎至乐”以臻于“至人”[13]380,通过内心的涵养获得人格的提升,从而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与自我的冲突,最终臻至“大美”的境界,“游戏”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此,这也是美育以“美”启“善”的本质要求。 如何在感性的完善中启发对自我的理性思考,从而“使人的感性和理性协调发展,塑造一种健全的人格”[14]198,苏轼“凡物皆有可观”的理路值得深入思考。
3 天地境界:“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
谪居黄州期间,苏轼有《书临皋亭》一则: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 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坋入。 当是时,若有 思 而 无 所 思, 以 受 万 物 之 备, 惭 愧!惭愧!”[4]2278
何谓“有思而无所思”? “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 遇事则发,不暇思也。 ……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4]363在苏轼看来,现象界的荣辱穷通、生死得失都是外在于人的“命”,思虑过多便会生邪念,因此要“遇事则发”,抛弃对现实世界的功利考量,纯任感性,这便是“无所思”。 但“无所思”又非毫无原则的放佚,而是涵容了理性化的人生思考,“于是幅巾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 于是得道,乃名其斋曰思无邪。”[4]574(《思无邪斋铭》)“夫无思之思,端正庄栗,如临君师,未尝一念放逸。 然卒无所思。”[4]1983(《续养生论》)“无所思”建立在“幅巾危坐”“明目直视”“摄心正念”“端正庄栗”基础上,这便是“有思”。 但“有思”不是刻意的理性约束,最终要“无所见”“无所觉”“无所思”,归于人的情感。因此,“有思而无所思”便是要排除由功利考量而来的思虑私欲,将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规则化为生命情感而纯任感性。 以这种交融情理的方式观物,便是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5]350(《孟子·尽心上》)万物在“我”圆融自足的审美化心境中生成全新的意义世界,“我”也在反观自照中由“诚”而“乐”,体味到了生命的全部意义,因此苏轼“酒醉饭饱”便能“受万物之备”。
“有思而无所思”可谓苏轼对物我关系认识的最高境界,“寓意于物”的精神自由、“凡物皆有可观”的心灵自适一变而为“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4]5(《赤壁赋》)的人格自主,“我”已然成为赋万物以意义的主体。 这一审美化理念典型表现为苏轼的“无待”之心,“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迁居》)[8]2067,不仅破除了对现象界一切外物的执着,现实中的一切功利对待、人生的终极目的都不复存在,只以一颗无思无待之心感受万物、纵浪大化,当下即为永恒,过程即是本体。 《书上元夜游》中,苏轼记道:
己卯上元,余在儋州。 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西域,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糅,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 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 放杖而笑,孰为得失? 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 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4]2275
韩愈心念“大鱼”而不得,更欲走海而求,将人生的完满设定为求鱼而得鱼,自然被外物左右,得之则喜,不得则忧;苏轼则心中自有“大鱼”,对外无求无待,“我”不仅从客观外物与主观欲求中解放出来,更在“良月嘉夜”“步西域,入僧舍,历小巷”的审美化生命过程中得到人生的完满,故而苏轼观棋时有“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观棋》)[8]2130之语,人生的终极目的性被破除,生命的意义全然寓于审美化的生命过程中,观物的当下情感体验也被提升到生命本体的高度而具有了超越性的意义。
“有思而无所思”不仅是苏轼对物我关系认识的最高境界,其中也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价值建构逻辑——由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出发,不断将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应然之道化为人内在的生命情感,最终指向的是人格境界不断提升[16]。 在这个螺旋上升的开放结构中,儒家的“从心所欲,不逾矩”、道家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佛家的“云在青天水在瓶”泯然合一,人彻底由现实走向了审美。 席勒在《美育书简》说,“通过审美的心境,理性的自动性可以在感性的领域中显现出来,感觉的力量在自身的界限内已经丧失,自然的人已经高尚化,以至现在只要按照自由的规律竟能使自然的人发展成精神的人。”[10]145归根结底,美育最终解决的是由“自然的人”到“精神的人”的问题,其实质也是“有思”到“思而无所思”的过程,如何实现“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3]185,苏轼的“有思而无所思”中隐藏着答案。
总而言之,在对物的观照中,苏轼以“寓意于物”的态度走出“留意于物”的物质占有,破除物执而在乘物游心的体验中获得审美的自由;在感性的完善中启发理性的价值思考,将精神的自由与超越导向心性境界的涵养,在“凡物皆有可观”的态度中培养起无往而不适的审美人格;更在“有思而无所思”的天地境界中实现“万物皆备于我”,由现实人生彻底走向审美的人生。 苏轼对物我关系的思考,在“物欲的释放”[17]的现代世界更有重要价值。 如何由“用”走向“美”并“向美而生”,如何“以美启善”以臻于“至善至美”,最终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185,苏轼塑造了一种富有启迪意义的生命范式,启发着我们对美育何以可能、应当为何、走向何处的思考。
-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的其它文章
- 风险社会视域下网络暴力成因探析
- 高校游泳教学中大学生心理障碍的成因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