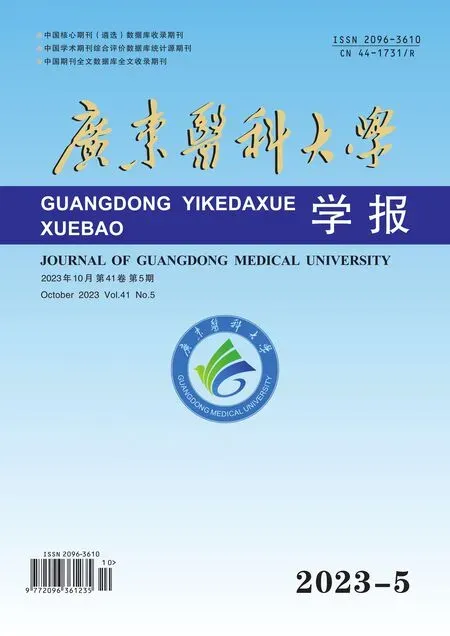我国医学传播现状及研究进展
卢泽锋,叶米真,麦思捷,杨金妹,陈欣欣,叶斯阳,陈 榆,李靖雯,王双苗*(1.广东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东莞 523109;2.广东医科大学健康促进与医学传播学研究所,广东湛江 52023;3.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广东湛江 52001;.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荷兰格罗宁根 977AA)
在我国将“健康中国”和实现“全民健康”提升至国家战略背景下,《“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指出把预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聚焦重大疾病、主要健康危险因素和重点人群健康,强化防治结合和医防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策略。医学传播作为促进全面健康的重要举措,对引导居民形成科学的健康观念、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培养具备“医防融合”素质的复合型医学人才和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对医学传播的内涵演变及现状进行综述。
1 医学传播的内涵演变
卫生传播作为人类文明史的产物,在不同时期依据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的职能[1]。在原始社会,人类出现了火的应用、织物的发明、天然草药的使用等许多卫生经验,此阶段的卫生传播主要为卫生经验的传播。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如《庄子》主张“循天之理”“虚无恬淡”的养生理念、气功养生法等思想与方法,此阶段的卫生传播主要为疾病预防与保健养生的知识传播。封建时代中国传统医药体系不断发展,《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典籍的出现,标志着中医药知识的传播成为该阶段卫生传播的主流。明清时期,随着传教士的到来,西方医学逐渐传入我国,兴起了中外医学文化的传播交流[2]。在民国时期,由于健康教育观念和理论的引进,卫生传播逐渐转变成健康教育,相关专业机构、人才及民众卫生教育等方面得到了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解决疾病丛生和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国家开始进行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宣传教育,传播与教育并重,发动群众讲究卫生,预防疾病。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继承爱国卫生运动的同时,引入了健康促进、健康素养、健康共治等新概念,健康传播事业蓬勃发展,居民的健康水平得以不断提升。
2016 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3]明确指出将我国健康工作的重心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到“以健康为中心”,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现全民健康作出了重要决策部署。全国各地积极推进健康教育,建设健康服务产业,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也逐年提升。然而,近年来居民健康素养的增幅逐渐缩减,尤以慢性病和传染病防治素养更为明显;同时,由于诸多领域的信息逐渐被“医学化”[4],公众对专业医学知识提出了更多更高的需求,医学知识普及传播发展进入了另一个新阶段,更为精准的医学传播开始萌芽。基于此,广东医科大学王双苗研究员提出:“医学传播是具备医学专业背景的传播者将医学领域相关的理念、知识、技能及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所能理解、运用的信息,借助多种途径实现精准传播,从而引导公众树立健康理念,掌握必备医学知识和急救技能,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及医学素养,形成健康生活方式,从而维护或促进健康的过程”。
2 我国医学传播现状
本文以“健康传播”“医学传播”“健康教育”等主题词在知网、Pubmed等文献库进行检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就医学传播实践与理论研究两方面综述如下。
2.1 我国医学传播实践现状
我国医学传播实践依据传播场景可以分为医院医学传播实践、社区医学传播实践和家庭医学传播实践[5]。
在一定程度上,医院医学传播的内涵与医患沟通相似,医患之间的传播内容多为疾病诊治、护理等专业知识与心理疏导信息,这是由受众群体(主要为患者及其家属)信息需求存在指向性所决定的。医务人员的学历认知、工作强度、薪资待遇、职业倦怠、患者反馈等诸多因素影响了有效传播的积极性[6-10];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水平、利益诉求、病情缓急、亲属关系、健康观念等诸多因素也影响了其参与医学传播的有效率[11-15]。国内外均有研究显示,阻碍医患之间有效传播的主要因素是双方在医患观念和医学知识储备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在疾病转归和治疗结果责任归属上存在显著的观念差异,此种差异源于医疗环境的固有特点[16-18],患者作为信息劣势方,需要通过医务人员的建议和指导来进行判断,错误的判断可能会使患者做出错误的选择并带来更高的风险;同时我国人口基数大,医疗资源紧张,医务人员相对不足,工作负担大,尽管医院的传播矩阵[19-21]、医务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医务人员医学传播的职能,减轻了医务人员的压力,但仍无法满足患者及其家属对医学信息的需求。
社区医学传播是指在社区内对受众人群进行精准医学传播,其中社区是指人的集合体[22],由特定地理或行政组织划分的区域内的一群人或将人们按照工作、学习或其他日常活动情况予以划分的社会单元(如学校)。受众人群分为健康及亚健康人群、确诊患者和患者家属,受众群体存在动态转化,其人口学特征、心理因素、现实障碍、信息处理能力等诸多因素均会对医学传播效果产生影响[11,23~26],因此社区医学传播需要针对受众人群的变化及时调整传播策略。受众对传播内容和渠道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的态势[27],如患者及其家属对疾病相关医学信息需求更高[28],健康及亚健康人群的需求主要由自身体验与近期热点决定[29],农村老年人仍多通过电视获取医学信息等[30]。社区传播内容分为健康常识类、疾病预防类、医学辟谣类、急救技能类、就医指导类、家庭照护类、心理疏导类及政策解读类医学知识;传播介质可以分为示现、再现和机器媒介[5]。在现实中,受众人群的需求是多样的,传播策略须针对不同受众人群的需求不断调整和更新,以提供定制化的医学传播知识服务。其次,基层医务人员作为传播主体的主要人群,受管理制度[31]、薪酬待遇[7]等原因限制,在进行社区医学传播时仍无法避免出现专业水平有待提升、积极性不高等现象[32]。
家庭医学传播是全科医生、家庭医生与社区内相关人群之间在诊疗、照护、健康宣教等日常工作中进行医学知识的传播[5]。家庭医学传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传播主体的匮乏和受众的特殊性,其中传播者匮乏的主要原因是多因素导致的全科医学发展缓慢和被现实因素冲击的家庭医生制度不完善[33-34],而家庭医学传播的受众主要为失能人群及其家属,医民双方对医学传播的认识程度不够、居民存在重治轻防的观念、医生精力待遇不佳等障碍越发明显,导致家庭医学传播效果不佳;其次,大部分失能人群由于其生理能力与心理认知的不匹配[35],传播者可采取的医学传播策略相对单一。
2.2 医学传播理论研究现状
在医学传播中,医学生、医生与医疗机构是医学传播的主体,其处于信息传播链条的首端,对信息的内容、质量与流向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魁玉兰等[36]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医学生的医学传播参与意愿高,但由于学业繁重、知识储备不足等诸多因素导致医学传播实际参与度不高。张茜等[37]对广东省在校医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广东省医学生参与医学传播的积极性较高,但是由于知识储备不足等因素,传播形式、渠道单一,内容、场所、受众相对局限。目前,我国对医学生参与医学传播的研究仍多局限于实践调查方面,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王丹等[38]发现乡村医生由于管理制度、薪酬待遇等原因导致其开展医学传播积极性较低。马一琳[39]针对新浪微博TOP 医生博主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力价值较高的TOP医生博主多聚集在一线地区。Hanneke等[40]对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公共卫生学院的12 名教职员工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发现教师会不计回报地主动通过多种形式向不同受众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比可以发现,经济水平与个体的差异也会影响其开展医学传播的积极性。美国学者Park等[41]采用知识—技能—能力(KSA)模型制定了健康传播能力评估量表(CHCS)。尹琳等[42]采用拉斯韦尔5 W模型形成了医务人员健康传播能力评价指标体系。CHCS量表与国内健康传播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均由于其传播内容不同,对传播者医学传播能力的适用性也不强,导致医学传播能力评估工具的应用较为局限,缺乏被国内外广泛认可的工具,且尚无适用于后疫情时代的指标体系,同时针对医学传播能力的培训体系也未达成统一,相关重点仍停留在医患沟通等培训上。国内学者对传播群体或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院的医学传播模式的实践与探索,江苏省人民医院[19]、北京协和医院[20]等通过不同模式的医学传播模式探索,提出了不同思路,但仍缺乏对已有医学传播模式的推广验证,在全国范围内鲜有统一且有效的标准模式。
传播内容由相互关联的有意义的符号组成,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进行交换,以达到互动的目的。自2015 年《健康科普信息生成与传播指南(试行)》[43]后,国内对传播内容的研究较为集中,主要围绕健康科普信息传播原则与要求进行详细研究,不断补充原则与要求的内涵,健康科普信息传播原则包括适用性、可及性、积极性原则。王胜源[44]从“伪健康信息”这一概念入手,总结了新媒体背景下伪健康信息在议题、文本等方面的特征,以健康科普信息传播要求的科学性进行分析。周欢等[45]发现在线健康平台的科普文章通过构建文本关联网络来发现其中的知识内容,受欢迎的文章更注重主题词项之间的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健康科普信息传播原则的可及性。Larsen等[46]通过体育项目进行医学传播,发现受众的参与积极性较高,并更容易记住相关的健康知识,与健康科普信息传播原则与要求的经济性不谋而合。夏江胜[47]提出医学传播内容应根据具体受众而定。《医学传播学理论与实践》[5]在健康科普信息传播原则与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医学传播内容应具备科学性、合法性、有效性、通俗性、艺术性和公益性等六大特质,以打破医学知识艰深晦涩的壁垒,缩小知识鸿沟。
传播介质作为传播内容的搬运者,是链接传播链的纽带。传统媒体是早期医学传播的主要载体并不断发展,国内学者以传统媒体角度进行了医学传播相关研究,通过分析传统媒体的局限性,提出新媒体的融合。刘娟[48]以《大公报·医学周刊》为研究样本,考察其传播内容、特点、策略及功能,虽然发现卫生传播客观上促进了医学事业的发展与国民生活习惯的改良,但是通过传统媒体进行传播效果不好。刘新艳[49]提出医学专业期刊唯有在新媒体时代突破传统媒体,应用各种途径进行科学普及,才能既突出医学期刊的专业特点又推广科学成果,让更多人受益。林春香[50]提出科技期刊要在智媒体时代提升自己的传播力与影响力,需及时回应科技前沿,增强对新媒体的理解力与运营能力,增强媒介融合,破除学术壁垒,扩大科学知识的分享与普及。部分学者通过新媒体视角,分析医学传播的优劣。Breu[51]提出社交软件推文可以为各级传播者提供了与数百万潜在受众互动的新机会。Dhoju等[52]通过对媒体进行分析,发现媒体之间开展医学传播存在显著的结构、主题和语义差异,有助于打击在线健康虚假信息。王耀斐等[53]提出医学类网红科普短视频仍然面临表现形式单一等问题。杨咏雪[54]分析了短视频环境下医学类科普的选题、创作方法与传播机制等;Han等[55]通过对艾滋病知识传播平台的评估,发现其受众对平台的整体评价、可读性、功能评价、设计和结构以及交互性方面表示高度满意。以上多数研究发现新媒体渠道仍存在诸多问题,如交互性强导致舆情危机的产生、信息超载等诸多问题,因此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交替背景下,由于两者均存在各自的优劣,在医学传播中两者缺一不可。
传播受众作为医学信息的接收者和反应者,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医学传播不仅涉及医学知识的传播,还涉及医学观念的传播,以及医学观念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如何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理解并接受现代医学知识,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让医学知识更好地传播,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医学传播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和社交性,使受众不再被动接收信息,而能够更主动地参与,但由于受众与传播者之间存在知识鸿沟,受众在接收医学传播时仍存在诸多问题。Aumpanseang 等[25]发现尽管医学信息的交换互动是合作共享的,但受众仍然会由于时间、资源不足等限制和障碍影响其接收程度;Briand 等[26]发现在COVID-19 流行等卫生紧急情况下,受众无限制地获取医学信息可能会造成混乱并影响行为,主要原因是受众的信息处理能力不足以解决信息超载;由于受众群体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如收入、教育水平、年龄、性别、城乡差异等,导致其参与医学传播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现阶段仍少有对指定受众群体进行医学传播内容需求和偏好的相关研究。
传播效果是医学信息被受众接收后对其认知、态度、行为等层面引发的反馈。现有的医学传播效果研究数量较少,学科背景单一,效果评价体系不完整,重过程、轻总结评估,理论框架缺失,如梅雪芳[56]虽然发现婚孕前开展健康教育,能够改善夫妻不良情绪,提高其优生优育健康知识知晓率及配合程度,减少不良妊娠结局,降低新生儿发病率,但是对干预效果的评价局限于医学领域;Świątoniowska-Lonc等[17]提出健康教育是心衰患者治疗的一个影响因素,良好的健康教育能提高患者自我护理水平和对治疗建议的依从性。
3 展望
相较于健康传播、健康教育的学科研究,早期医学传播学科化研究较少,侧重于对传播介质、效果反馈等传播独立环节的研究;医学传播与健康传播内涵相混淆,且研究来源相对广泛,涉及医学、传播学、心理学等领域,这也导致了医学传播研究较为分散,观点较为局限。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外对医学传播的认识与研究仍局限于单一学科领域,难以取得全面的研究成果;研究视角集中于医学传播的要素,未深入探讨完整传播链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数据特别是新媒体下对医学传播效果的相关研究涉及大量的个人健康信息,数据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现有的医学传播评估工具难以全面、客观地评估传播效果等。医学传播经历了视角渗透与论域沉淀的阶段摸索,其逐渐理清自身目标,2017 年广东医科大学以《医学传播学》课程初步定义国内外医学传播研究理论体系[5],标志着正式为该复合型交叉研究领域确立了“学科化”的目标导向;此后,多个省级医学传播学会的确立及其相关的组织、教育实践,从人员筹备、资源积累等方面加速了医学传播研究的“学科化”建设发展。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医学传播研究须以“五化”路径深入建设:(1)医学传播学科化。从知识建构来看,医学传播理论研究需要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确立医学传播学学科范式,形成一批公认的代表性成果;从组织建构来看,医学传播需要获得学科合法性身份,以获取其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医学传播学科化完成组织建构后,反哺知识体系建构,遵循“内外兼修”[57]的学科发展路径,优化学科架构,并推广至医学教育行业,普及于各大领域。(2)医学传播理论化。纵观医学传播的发展,其实践发展先于理论的出现,医学传播应积累从医学传播的历史实践、哲学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来并经过检验的概念、视角和方法等,借鉴医学和传播学中的基本概念和模式进行理论建构。(3)医学传播专业化。目前我国医学传播主体是具备医学背景的人群,而鉴于医学传播评估工具与培训体系的不完善,其与医学传播专业化仍有一定距离,因此医学传播专业化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具备“医防融合”素质与医学传播能力的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实现人才制度建构。(4)医学传播规范化。医学传播依据5W模式形成了完整的传播链,然而大部分研究仅局限于某一传播环节,环节间的交互作用尚不完全明确,因此对医学传播链进行传播制度建构,形成统一的医学传播参考规范,才能更好地达到最优的医学传播效果。(5)医学传播精准化。现阶段仍少有对指定受众群体进行医学传播内容需求和偏好的相关研究,学界应加强相关研究,以明确受众具体需求,进行传播内容建构,实现医学传播精准化。
总之,我国医学传播的发展既具有理论层面上的可行性,也具有实践层面的可行性,仍需要从医学、传播学、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运用实证研究手段,完善医学传播理论体系,指引实践,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服务人类全生命周期健康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