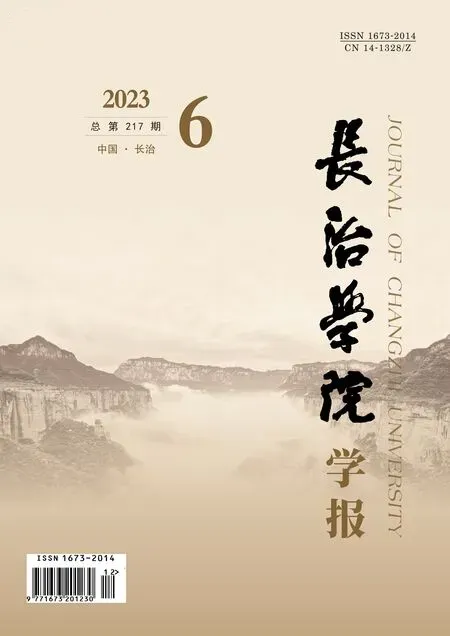鲁迅、赵树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耿传明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071)
鲁迅与赵树理都是决定并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方向的关键人物,他们的文学、文化选择方向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演变、发展趋势使然。一般而言,鲁迅呈现为现代文学开创期的创世性的克里斯玛先觉者形象,而赵树理则呈现为现代文学深化期的道德守恒性的克里斯玛形象,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不同演变、发展阶段的领军人物。鲁迅代表的是现代文学诞生期的席卷天下、并吞八荒的开天辟地的创新开拓者的气象,而赵树理代表的则是现代文学实践期由精英下沉到民众的道德守恒者形象,前者写作的是一种作者重心型小说,而后者写作的则是一种读者重心型小说。以下对两者之间的深层差异做一简要的分析。
一、文化性格、审美气质和文学理念的差异
作为文化创世者的鲁迅具有一种开天辟地的文化英雄的性格。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并不是一般人都能担得起文化英雄这个称号,他必须具有南宋陈亮所说的“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文化创世气魄,是像拜伦、雪莱一样的“未冕的世界立法者”。废名曾说一个大作家必须兼具“天才”“豪杰”“圣人”三种禀赋、品质,才能成就,是有其道理的。所谓“天才”者,指的是卓越的才能、智慧;“豪杰”者,指的是敢于“重估一切价值”的勇气和特立独行,不合众嚣的大独人格;“圣人”者,指的是博大之爱心,宽阔之胸怀,能够达到“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天地境界。以这些标准来衡量现代作家,的确只有鲁迅能庶几近之。鲁迅的伟大和杰出主要来自于“心力”的强大,他是一种主观意志力极为强大的人,兼具古人所讲的“剑气”“奇气”“侠气”“豪气”之类创世英雄的人格气质,这是他能够成为开一代风气的文坛巨人的重要原因。自清末以来,龚自珍就开始呼唤拯救衰世的豪杰人格的出现,他极端强调的就是“心力”的作用,他在《壬癸之际胎观第四》文中认为,“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其后谭嗣同的“以心力挽劫运”、章太炎的“自贵其心”也都是这种呼唤的继续,鲁迅可以说是近代以来这种浪漫主义英雄文化的发扬光大者,他以别开生面、撼动人心的刚健之作,一扫衰世文坛的萎靡绮丽之态,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振衰起敝的作用,为中国文学的新生开辟了道路。
克里斯玛一词源自《新约》,意指神授的能力,是追随者用来形容诸如摩西、耶稣之类具有非凡号召力的天才人物的用语。马克斯·韦伯认为克里斯玛人格是历史中富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有着这种人格的人物以传统的名义出现,却是传统大刀阔斧的改造者。由于有了克里斯玛人物,传统以一种同以往不大相同的形式与实质而延续下来,它是一种对传统的创造性的改造与再生。“超凡魅力”用于指称个人的某种品质,正是由于这种品质,他被看作不同寻常的人物,被认为具有超自然或超人的、至少是特别罕见的力量和素质。这些力量和素质为普通人所不可企及,所以被认为是得到神助、天赐的人物,在“轴心期”文明中一般都把这些人物看作“最伟大的”英雄、先知和救世主。这类人物也就是鲁迅早年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中所呼唤的英哲大士。马克斯·韦伯曾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归结于三种:传统型权威、魅力型(克里斯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他认为只有摈弃情感、习俗、偏见的法理型才是民主社会追求的目标,因为法理型的认同对象不再是人格化的君主或精英,而是非人格化的法典,似乎这更符合现代民主的契约精神。但是,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克里斯玛人物的出现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现代性的初创期,没有克里斯玛人物的“英雄造时势”的主观能动性,是无法突出传统的重重包围从而别开生面的,所以现代最具政治影响力,最具传播力的都是“克里斯玛”型领袖。这也正是造成现代性进程波澜壮阔、起伏不定的吊诡之处,后发外源的国家的现代性离不开克里斯玛人物,而对克里斯玛人物的完全依赖又会迟滞、妨碍法理性权威的确立。两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重要的还是寻找信仰与理性之间、克里斯玛人物和法理性权威之间的平衡,偏于前者易流于失控,偏于后者易流于失活。正如辛弃疾《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中所言:“物无美恶,过则为灾”,重要的是因应实势,根据需要、对症下药的问题。
鲁迅的时代是一个思想的时代、怀疑的时代、也是一个凸显个人、革故鼎新的时代,他所面临的文化现实是传统作为一个河道已淤积严重,因此迫切需要清淤疏浚,所以他是以一种精神上的清零重启的方式来展开其文化工程的,犹如把杯子里残液倒掉才能品尝新的美酒一样,他所要造就的是一种接纳新世界的空杯心态和开放胸怀。这种文化上的精神再生努力与传统儒家所讲的复性、道家所讲的返璞归真、佛家所讲的回心,以及李挚所讲的童心等都是在深层相通的,都是一种在文化迷失之时返回内心、复归本性、找到真我的功能,这种心灵重光的过程正如宋朝柴陵郁禅师的《悟道诗》所言:“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青山万朵。”[1]鲁迅《狂人日记》的开端即是:“今天晚上很好的月亮,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月亮”在这里显然扮演了触发他的本性觉醒的“灵媒”的作用,主人公约莫三十多岁,而不见此月亮也是三十多年,也就是他是在童年才见到过这样的月亮,也就是说只有以一颗纯真的童心,才能看到这样的月亮,龚自珍有一首诗:“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2]讲的也正是这种童心、本性的可贵。也就是说鲁迅是以这种做减法的清零方式回归到一种心灵的自由,从而使得陷入困境的文化重新恢复了活力和创造性。
赵树理与鲁迅的情况差别极大,他比鲁迅小十五岁,在北方内地偏僻的山西农村出生、长大,在山西一所师范学校毕业,从未留过洋,读过些新文学的书籍,深受其影响,但也深感新文学对于农村、农民的隔膜,因此早就有意促成新文学走入底层民众、走入乡村,实现新文学的普及化。就赵树理所担负的文化角色而言,他是一位跨越了新旧文化之间的界沟,实现了传统德性与现代德性、新文学与旧文学的精神对接的人物。据他自述:“我出身于一个有宗教关系的下降中农兼手工业者的家庭。我的祖父原是个杂货店的会计,改业归农后才生我父亲,晚年入了三教圣道会,专以参禅拜佛为务。我从六岁起,由祖父教念三字经和一些封建、宗教道德格言,不让我和其他孩子们玩,并且要我身体力行能为我所理解的那些道德行为,例如拜佛、敬惜字纸、走路不左顾右盼、见人要作揖、吃素等。……在这一阶段,从祖父那里学来了一些‘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法、敬师尊……’‘不履斜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封建或宗教守则,同时又造成了个瘦弱的体格和不通世故的呆气,从父亲那里学来了农业和手工业的一些技术,但因为身体关系,有巧无力,没有学好。在祖父死后的三年半中,我和农村的文化娱乐有所接触(我父亲也好这些,但以前为我祖父所反对),学了些地方音乐和书词、戏本。”[3]206也就是说,赵树理的文化底色主要由其祖父所传授给他的传统伦理文化以及乡土民间文化构成,这些构成了他接受其他文化的前理解。他的传统文化素养在高小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高小毕业的那一年,买到一本江神童的《四书白话解说》。这本书,后来听说是一位老古董先生用他孙子的名字出版的。这位老先生接受过王阳明的学说,同时又是个信佛的,还著过《大千图说》,其思想是儒佛相混的。这恰好合乎我从祖父那里接受的那一套,于是视为神圣之言,每日早起,向着书面上的小孩子照片稽首为礼,然后正襟危坐来读,并且照他在《大学》一书中的指示,结合着那些道理来反省自己。我从高小毕业后,又教了二年初级小学(那时候高小毕业可以教初小),连同毕业之前的一年共三年,对这部书的礼读没有间断过。……在这一阶段,我以学习圣贤仙佛、维持纲常伦理为务,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人看来,以为是好孩子,可惜‘明书理不明事理’。”[3]207-208这是一位典型的少年乡村儒者形象,与时代处于一种脱节状态。
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是在考入师范学校之后:“因为我不通世故,初级小学也教不成了,才于一九二五年暑假期间考入山西长治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这个学校幸未受同学欺侮,只是由自己的落后思想指导着的怪行动(如吃素、敬惜字纸)引起了一位有先进思想的同学的非议。在初入学的一年中,经过这位同学把我的江神童思想体系打垮,才算打开了学习其他东西之门。那个学校,偏重于教古文,不能满足有求知欲望的人——那个学校当时有求知欲望的人却也不少。我经过那位同学的启发,得到课外在图书馆中借些书读,不过所读之书杂乱得很,同时可以接受互相矛盾的书——例如对科学与玄学的东西可以兼收并蓄——而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者则为反礼教、反玄学的部分。就这样乱读了二年,后一年偏重在文艺和教育学方面,但同时也接受了一点共产主义的道理。第三学年第一学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入了共产党,同时在学校赶上了驱逐腐败校长的学潮(不是党领导的,但党也赞成)。在这运动中,我被选为一名学生代表(共十人),并且终于取得另委校长的胜利。到第二学期(一九二八年春)因国民党反共,波及学校,我遂离校逃亡,但至次年春仍被捕入狱。在这一阶段,我的思想虽然有点解放,但旧的体[系]才垮了,新的体系没有形成,主观上虽抱下了救国救民之愿,实际上没有个明确的出路,其指导行动者有三个概念:①教育救国论(陶行知信徒)②共产主义革命和③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艺术至上,不受任何东西支配),并且觉着此三者可以随时选择,互不冲突,只要在一个方面有所建树,都足以安身立命。”[3]208对于赵树理这种把灵魂、理想看得高于一切的人物,信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仰行为本身,信仰就是相信和敬仰,没有信仰意味着受制于欲望与他者,失去精神自主性和人生方向。所以他是急需一种新的信仰来提升自己,使自己不至于成为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
他在政治上的进步和成熟则来自于他出狱之后:“我在被捕之前,虽曾有过将近一年的逃亡生活,可是那时候还以为是暂时的,并未做长期打算。被捕以后,开始觉悟到再不能在旧政权下做什么安身立命的打算。这便是我流浪的理论基础。出狱之后遇上了比我高明的一些懂马列主义的同志,又和王春打垮我的江神童思想一样,很艰苦地打垮了我另一些糊涂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格至上’(在这以前,我以为革命的力量是要完全凭‘人格’来团结的)和‘艺术至上’。这对我的帮助是有决定意义的。”[3]209换言之,他已经意识到革命不能像传统道德那样靠个人人格发挥作用,而是要动员群众、发动群众,靠阶级斗争来取得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否定或彻底抛开传统美德对于人的成长的价值和意义。例如他在写到他极为推崇、认同的共产党的好干部、实干家潘永福时,第一节的名字竟然是带有宗教慈善色彩的“慈航普渡”,写的是参加革命之前的潘永福已经是一位颇受众人尊敬的见义勇为、舍己为人式的好人,小说在讲述了潘永福早年在河中救人的英雄事迹后,还特意发了这样的议论:“像潘永福同志这样远在参加革命之前就能够舍己为人的人,自然会受到大多数人的尊敬,所以他走到离别十八年之久的地方,熟人们见了他还和以前一样亲热。”[3]147在传统美德和现代美德之间,赵树理做了一个无缝对接,传统的好人也就是现代的好人,好人就是在群己关系上认同群重己轻的人,在应然和实然之间站在应然一边的人,在道义和功利之间站在道义一边的人。总之,普通大众的是非爱憎、喜怒哀乐也就是他的是非爱憎和喜怒哀乐,所以他的文化特性不像鲁迅那样的独持我见、特立独行,而是善与人同,如盐溶于水,化于大众,一种融入民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日常世俗状态。
二、作者重心型写作和读者重心型写作的差异
现代小说源于现代自我的发现,正如本雅明所言,现代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现代作家与古代小说中的那种讲故事的人愈行愈远。从深层来说,这种源于西方的现代小说文类的产生代表着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全新的思想、心理、感觉方式的出现,其哲学根源是建立在主客对立基础上的“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由此改变了传统人们看待、感知世界的方式。如果说传统文学的基本精神是文以载道,那么现代文学的基本精神应该说是“文以载我”。“我见”的扩大、主客对立的“我”的思想、感情、心理体验成为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中心内容。这种自我的发现导致现代小说与传统相比发生了全方位地、深刻地改变。从小说的潜作者和小说的叙述者和人物、读者之间的关系上来看鲁迅小说与传统小说已有很大不同:传统小说的作者多以“说书人”的身份出现,作者设想自己在说书场这类的公共场合面对听众讲述故事,其身份本身带有公共性,是以一种公共见解、公众立场为基础来讲述故事,这是一种非个体性的讲述。现代小说的叙述人抛开了“说书人”这个面具,将小说的拟接受情境由书场、街头转向了密室、案头这样的一对一的独处空间,作家与读者的交流也不再需要“说书人”这一中介,而变为一种个人之间的交流,与读者进行心灵之间直接的沟通和对话,因之更能起到“撄人心”的效果。像《狂人日记》这样以高度个人化的“狂人”以及“日记”这样的袒露个人心迹的私密性文体写成的小说,对于自我的发现、现代个人意识的形成都有推动作用。他在人生经验传达的直接性、客观性、逼真性、强烈性方面远胜于古典小说。
但赵树理并没有按照鲁迅指出的方向继续向前走,而是倒过头来,向传统和民间叙事方式回归,其主要原因在于历史的担纲者已由思想启蒙时代的英哲大士向普通民众转移,普通民众成为创造历史的主力,而服务于普通民众也就是听从于历史的召唤,使自己融入时代的洪流之中。所以“五四”作者重心型小说所立足的主客二元对立模式已不再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对于鲁迅也就出现了接着讲而非照着讲的问题,启蒙小说表现出的是一种凭高视物、以自己之所是为标准,裁决一切,论断一切的倾向,其优点在于打破了传统的权威,将理性视为唯一的标准;正如狂人所言“一切都须研究,才会明白。”但理性只能判别知识上的真伪,与人的价值判断无关,真伪不可能成为人生存的最高需要。启蒙者急于救世,往往把自己的主观成见加于被启蒙者,呈现的是被自我编排、加工过的他者,而这种伪他者只能加大启蒙者和启蒙对象之间的距离。据说在师范读书时的赵树理曾把鲁迅的《阿Q 正传》读给父亲听,这本启蒙农民的小说对于这位真正的农民没有任何的触动,反而感觉作家写的不是农民、与己无关。的确,向阿Q 向吴妈求爱时说出的“我要和你困觉”之类的场景显然不会出现在一个真正了解农民的作家笔下,只要对于民间俚曲等稍有了解,也会知道农民并不欠缺谈情说爱的本领,并不会像小说中所写的动物求欢似的简单、粗野。在启蒙者小说中出现这样的描写并非是现实如此,而是启蒙者的主观化的逻辑推演,也就是说他认定阿Q 是还未进化成人的动物,所以只能按动物的本能行事,而这显然是有悖于现实的。在赵树理的笔下,是显然不会出现这样被凝视、被裁决、被物化的农民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不是站在农民之外为农民写作,而是自己就作为农民来写作。这种与写作对象融为一体的创作理念是赵树理独到之处,也是他由“五四”时代的作者重心型写作转向读者重心型写作的根源。由此出发,他也就在写法上做了一系列的尝试来推进其创作意图的实现。以往有人认为是赵树理不会写新文学式的小说,所以才走的民间文艺路线,实则不然,赵树理对于“五四”新小说的写法有充分的认知,掌握熟练,他是有意识、自觉地对其加以规避、改造的,他曾这样写到:“中国民间文艺传统的写法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呢?我对这方面也只是凭感性吸收的,没有作过科学的归纳,因而也作不出系统的介绍来。下面我只举出几点我自己的体会:一、叙述和描写的关系。任何小说都要有故事。我们通常所见的小说,是把叙述故事融化在描写情景中的,而中国评书式的小说则是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的。如《三里湾》第一章写玉梅到夜校去的时候,要按我们通常的习惯,可以从三里湾的夜色、玉梅离开家往旗杆院去写起,从从容容描绘出三里湾全景、旗杆院的气派和玉梅这个人的风度仪容——如说‘将满的月亮,用它的迷人的光波浸浴着大地,秋虫们开始奏起它们的准备终夜不息的大合奏,三里湾的人们也结束了这一天的极度紧张的秋收工作,三五成群地散在他们住宅的附近街道上吃着晚饭谈闲天……村西头半山坡上一座院落的大门里走出来一位体格丰满的姑娘……’接着便写她的头发、眼睛、面容、臂膊、神情、步调以至穿过街道时和人们如何招呼、人们对她如何重视等等,一直写到旗杆院。给农村人写,为什么不可以用这种办法呢?因为按农村人们听书的习惯,一开始便想知道什么人在做什么事,要用那种办法写,他们要读到一两页以后才能接触到他们的要求,而在读这一两页的时候,往往就没有耐心读下去。他们也爱听描写,不过最好是把描写放在展开故事以后的叙述中——写风景往往要从故事中人物眼中看出,描写一个人物的细部往往要从另一些人物的眼中看出。二、从头说起,接上去说。假如我在第一章里开头这样写:‘玉梅从外边饱满的月光下突然走进教室里,觉着黑古隆冬地。凭着她的记忆,她知道西墙根杈材零乱的一排黑影是集中起来的板凳……’这样行不行呢?要是给农村人看,这也不是好办法。他们仍要求事先交代一下来的是什么人,到教室里来做什么事。他们不知道即使没有交代,作者是有办法说明的,只要那样读下去,慢慢就懂得了;还以为这书前边可能是丢了几页。我觉得像我那样多交代一句‘……支部书记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便到旗杆院西房的小学教室里来上课’也多费不了几个字,为什么不可以交代一句呢?按我们自己的习惯,总以为事先那样交代没有艺术性,不过即使牺牲一点艺术性,我觉得比让农村读者去猜谜好,况且也牺牲不了多少艺术性。”[3]赵树理把新文学侧重的视觉性叙事重新扳回到听觉性叙事,把共时性进行时变为历时性过去时,把书面语变成口语,把淘汰了的说书人重新请回到小说中,其目的都是为了“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东西”这个目的,可以说赵树理的确通过他的写作达到了这个目标,所以也可以说在文学上他度过了无憾的一生,提供给文坛以真正的新质。对他留下的宝贵遗产,我们要抱着接着讲而非照着讲的态度,继承其视人如己,心系大众、植根大地、埋头实干的精神,在新的时代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