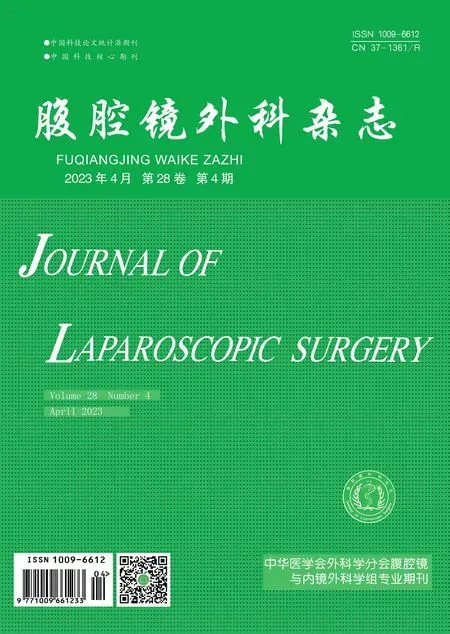腹腔镜左半结肠切除术不同手术入路的效果分析
孙大伟,孙军席,于 晨,井 楠,王昭顺,张凡沛,刘永光,郭 澎
(潍坊市人民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山东 潍坊,261000)
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变化及早癌筛查意识的加强[1],结直肠癌发病率也在逐年上升,2020年全球估计新发结直肠癌(1 931 590例,占10.0%)居第三位,新发结直肠癌死亡病例(936 172例,占9.4%)居第二位[2],其中左半结肠癌发病率相对较低[3],腹腔镜手术虽已成为治疗结肠癌的主流术式[4],但腹腔镜左半结肠切除术的手术入路、淋巴清扫范围等争议较多[5]。本文现回顾分析腹腔镜左半结肠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及部分手术录像,以探讨采用不同手术入路行腹腔镜左半结肠切除术的临床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分析2019年7月至2023年1月我院结直肠肛门外科收治的左半结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完成腹腔镜左半结肠切除术,无中转开腹及难以控制的出血;(2)不伴腹膜转移、远处转移。排除标准:(1)术前行新辅助治疗或伴梗阻;(2)术中发现腹腔严重粘连;(3)术中有胰腺、脾脏或其他脏器联合切除;(4)重度肥胖(BMI≥37.5 kg/m2)。共纳入92例患者,根据手术入路分为经中间入路组(n=31)、经外侧入路组(n=43)与经网膜囊入路组(n=18),由4名具备丰富腹腔镜手术经验[6-7]的主刀医生完成,三组患者年龄、性别、BMI、肿瘤病理分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临床可比性,见表1。

表1 三组患者临床资料的比较
1.2 手术方法 采用气管插管全麻,患者取改良截石位,常规术野消毒、铺巾,脐下缘2 cm处穿刺10 mm Trocar作为观察孔,建立气腹,压力维持在12 mmHg,流量维持在20 L/min,探查腹腔,确定肿瘤位置及邻近器官、肝脏转移情况。(1)经中间入路组:于平右髂前上棘内上2横指水平上方2~3 cm处穿刺12 mm Trocar为术者主操作孔,脐上5 cm平面交右腹直肌外缘处穿刺5 mm Trocar为副操作孔,对应左侧穿刺两枚5 mm Trocar为助手操作孔。术者站位见图1a,调整患者为头低臀高位,将小肠、大网膜推向上腹腔,乙状结肠牵向外侧,展平乙状结肠系膜,沿血管投影打开腹膜进入Toldt间隙,显露肠系膜下动脉,清扫血管周围脂肪淋巴组织(图2),切断左结肠动脉与乙状结肠动脉第一支,夹闭离断左结肠动脉,向外侧、尾侧继续拓展游离,切开乙状结肠腹膜形成贯通,完成尾侧游离。调整站位(图1b),将患者调整为头高臀低位,横结肠、大网膜推向头侧,降结肠推向外侧,显露肠系膜下动脉起点与屈氏韧带连线并切开腹膜,进入Toldt间隙,向外侧及头侧充分游离,由屈氏韧带下方向外侧分离,夹闭离断肠系膜下静脉,显露胰腺下缘、脾下极血管(图3)。沿左结肠旁沟切开侧腹膜向上至脾曲,离断脾结肠韧带;切开胃结肠韧带左侧部分,沿胰腺上缘向结肠脾曲游离,经过脾下极与外侧汇合,完成脾曲游离。于左侧腹切开5~7 cm切口,提出已游离的左半结肠,于肿瘤近端5 cm处及肿瘤远端10 cm处裸化肠管,置入吻合器完成端侧吻合。(2)经外侧入路组:患者体位、术者站位、Trocar布局、肠系膜下血管及左结肠血管的处理同经中间入路组。打开降结肠外侧腹膜,沿左结肠旁沟向头侧游离降结肠至结肠脾曲(图4),游离切断脾结肠韧带,将大网膜及横结肠内翻,打开胃结肠韧带(图5),沿胃网膜血管弓外游离切断,向中线裁切,沿胰腺表面向内侧拓展Toldt间隙(图6),离断肠系膜下静脉,切断大网膜及横结肠系膜,左右贯通。(3)经网膜囊入路组:患者体位、术者站位、Trocar布局、肠系膜下血管及左结肠血管的处理同经中间入路组。游离脾区时有所不同,暴露胃网膜血管弓,于血管弓中点处切开胃结肠韧带(图7),暴露胰腺尾部(图8),切开横结肠系膜后叶与胰腺下缘附着点(图9);向左游离至降结肠,将降结肠向右翻页,沿左结肠旁沟向结肠脾曲游离,与内侧贯通汇合,完成脾曲游离[8];后续操作同经中间入路组。

图1 穿刺器放置示意图 图2 肠系膜下血管裸化 图3 中间入路进入网膜囊

图4 外侧入路游离至脾下极 图5 离断脾结肠韧带 图6 沿胰腺表面拓展间隙

图7 网膜囊入路切开线 图8 向下暴露胰腺 图9 暴露胰尾上下会师
1.3 观察指标 记录术中、术后相关指标: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肿瘤大小、淋巴结清扫数量、术后首次排气排便时间、术后进食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等。

2 结 果
92例患者均顺利完成腹腔镜左半结肠切除术,无中转开腹及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标本切缘均为阴性,3组手术时间、淋巴结清扫数量、术后住院时间、首次排气排便时间、首次进食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中间入路组术中出血量较经外侧入路组(P<0.001)、经网膜囊入路组(P=0.010)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中间入路组术后未发生并发症;经外侧入路组发生4例,其中感染3例,吻合口漏1例;经网膜囊入路组发生感染3例;3组并发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三组患者手术指标的比较
3 讨 论
脾区游离是腹腔镜左半结肠切除术的难点,容易出现脾脏撕裂、胰腺损伤[9]、脾血管损伤、结肠吻合口漏、术后胃瘫等;部分患者结肠脾曲位置较高,操作孔布局不合理会影响手术操作,导致深层面的视野显露困难,三毛牧夫[10]曾提出将副操作孔由剑突下追加穿刺,以降低脾曲的显露难度;或将术者操作孔向中上平移并适当增加患者头高左高角度,以利术野的暴露。经中间入路法更符合恶性肿瘤的根治性原则,是目前采用较多的术式[11],尾侧的游离与腹腔镜直肠前切除术类似,脾曲游离采用“三路包抄”法[12],沿Toldt间隙向上拓展,在十二指肠空肠曲外侧于肠系膜下静脉根部结扎离断,探查清扫结肠中动脉,沿胰腺下缘向脾曲游离,拓展该间隙时离断横结肠系膜根部并入网膜囊,对侧为脾门,内有丰富的血管丛,避免误伤;头侧游离起点为胃网膜血管弓外的胃结肠韧带,离断胃结肠韧带进入网膜囊,到达脾曲时如果层面良好便沿脾下极血管向外侧游离,并离断脾结肠韧带,避免外侧游离时过度牵拉,脾结肠韧带的牵拉是脾脏撕裂伤的主要原因[13],脾结肠韧带附近存在脾下极血管,游离脾曲时经常造成损伤[14]。高位切断肠系膜下静脉游离脾曲时,以胰体表面为标志向胰体尾前间隙寻找正确平面比较容易,术野更易显露,对于肥胖患者优势更加明显。外侧入路则更符合传统开腹左半结肠切除术的操作习惯,由外向内翻页式游离,可较好地避免损伤腹膜后脏器(如肾脏、生殖系统血管、输尿管等),同时还能保持肠系膜的完整性;但外侧入路步骤繁琐,手术风险高[15];游离至内侧处理血管时,肥胖患者容易因层次分离困难造成血管误伤,甚至误入肾后间隙[16];肿瘤血供未阻断,游离过程中的挤压存在肿瘤播散的风险。有报道认为[17],经中间入路容易进入胰腺后方的错误间隙,而推荐经网膜囊入路,打开胃结肠韧带进入网膜囊后优先暴露胰腺,通过胰腺更容易辨识横结肠系膜根部,从而循胰腺表面切断横结肠系膜,达到左半结肠系膜的完整切除。老年人、肥胖患者发生脾损伤的风险最高,其主要机制是因术中过度牵拉导致脾包膜、脾门撕裂出血,首先完成头侧游离可减少后续操作中对脾脏的牵拉。王锡山团队腹部无辅助切口经直肠切口拖出标本的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同样选择经网膜囊入路,选择保留大网膜,保留其免疫、润滑、防粘连及预防肠梗阻的作用,降低取标本的难度[18]。但沿胰腺前间隙向下拓展,切断横结肠系膜根部、胰腺下方筋膜后与下方会师时难度较大(图10),容易误伤肠系膜下血管。

图10 结肠脾曲膜解剖关系[10]
左半结肠血供主要来源于肠系膜下动脉,其分支包括左结肠动脉、乙状结肠动脉、直肠上动脉,其次来源于来自肠系膜上动脉的结肠中动脉,有25%的人群存在副结肠中动脉[19],需清扫No.222lt组淋巴结[19-20]。结肠中动脉与左结肠动脉的初级血管弓吻合处存在缺如或薄弱,离断左结肠动脉后容易造成吻合口缺血,结肠中动脉血液无法形成弥补性供应[21];罗兰弓是结肠中动脉与左结肠动脉或副结肠中动脉与左结肠动脉之间的次级吻合弓,存在脾曲结肠缺血风险存在时,罗兰弓能形成侧支循环从而改善吻合口血运,但其发生率仅为7.5%~27.8%[22],术前可行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术中仔细观察吻合口肠管血运、小动脉搏动、切缘渗血情况,以减少吻合口漏的发生[23]。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分析,样本量较小,有待更多中心、大样本量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4名主刀均为有经验的结直肠外科医生,遵循全直肠系膜切除原则,足以应对脾曲癌手术的挑战[20],但主刀的异质性无法完全排除,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偏倚,如果能精确至脾曲游离部分的手术时间,三种手术入路的对比可能更有意义。
手术入路的选择更多需要结合术中实际情况及术者经验,而非拘泥于某种操作路径,通过三种手术入路的比较可加深对膜解剖的理解,形成更全面的手术思路,使腹腔镜左半结肠切除术更加安全、简化、微创。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