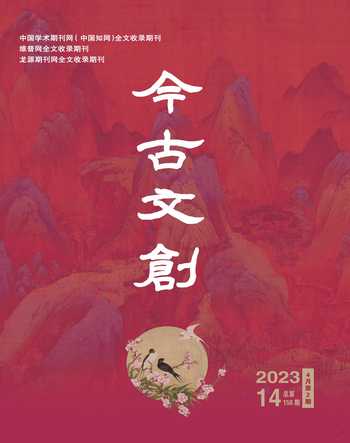卡萨诺瓦“民族主义文学”的内部观照
姜程铭
【摘要】 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共和国》中关于缺乏文学资本于文学世界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民族,将赫尔德理论提出的通过民族主义文学实现文学资本的积累作为进入文学世界的新方法。在此情况下作为对政治具有强烈依附性的文学,因现实主义文学在追求写实的同时对其虚幻属性的隐藏,使与大众化语言相结合的现实主义写作成为国家、民族塑造民族特性的最佳武器,而曾经具有相同含义的“人民”与“民族”,也在民族主义文学和阶级文化的发展中,逐渐具有不同的含义,即“人民”是“民族”中阶级的组织部分,并不等同于民族主义文学。
【关键词】 文学与政治;现实主义;人民;民族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4-005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4.016
一、缺少文学资本的国家、民族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在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共和国中,部分国家和民族由于缺少足够的文学资本,在文学世界里处于劣势地位。这种文学资本既能给一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历史及文学的合法性”,又能为全世界所认可。他提到这种文学资本是“独立于民族意识形态之外的”,因此是超越国家、民族和历史的存在。但他又通过语言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展现出来,“语言往往是民族的”,它既服务于国家事务,又为文学所使用的,因此“文学的资源必须在民族的篱笆内产生”。两者通过语言“相同奠定,相互加强,相互促进”。这种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为缺少文学资本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积累文学资本的方式与力量。
(一)经由语言连接政治与文学
卡萨诺瓦所划分世界文学空间起源里,法国的杜贝莱所发出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是初期阶段的坐标,16世纪由于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拉丁语的权威性,法语在法国被视为下层语言,而杜贝莱的宣言意味着以语言为首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对抗,该阶段即“拉丁语垄断性使用阶段向通俗语言在知识分子中广泛使用的阶段”,并发展为“各类其他文学对抗古代辉煌文学的年代”。这一发展方向的本质是以法国为首由于缺少文学资本而在文学世界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和民族与依靠拉丁语及其所具有的文学资本在文学世界称霸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抗衡。因此杜贝莱提议进行“资本转移”,即“用法语对大量拉丁语修辞学成果进行置换和改造”。在充实完善法语的同时,用新的法语进行文学创作以证实新法语的优越性。
卡萨诺瓦将以语言为中心的“资本转移”的成果落脚在法语成为文学语言,强调了这并不能归结为“政治集权化必需的一个简单的‘传达指令”。但在他所描述的法国的语言改革中不乏政治的参与,正如上文所述,这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以语言为开端的对抗,语言所具有的政治属性以及由语言所联系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使法语在取代拉丁语及其所创作的文学的地位的同时,带来了人们对法语以及其身后的法国的崇拜,法国的声望也由此提高。这一运动的背后是国王与以拉丁语为宗教语言的教皇之间权力争夺,法国国王借助具有世俗特性的新法语,通过质疑教皇使用拉丁语垄断宗教阐释的方式否定教会的神权。国王的作家队伍既“负责提高(通过法律、编年史形式的构建)王家语言的政治和外交威望的同时,还负责‘增加王家语言的文体、文学及诗歌丰富性。”与此同时,法国王朝获得了对地方封建特权的统治,这也意味着文化领域上的统治,增加了新法语的辐射范围。[1]
(二)“人民”与“民族”作为展现民族特性的主题
19世纪,欧洲的贝内迪克特·安德森等学者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认为“民族‘被发明、‘被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建构物,‘民族主义也只是‘一个虚构的政治团体意识”。[2]卡萨诺瓦在“赫尔德革命”一节中以安德森及该时期产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引入后续内容,显示出他所认知到的“民族”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对法国的语言变革的叙述中,也显现出“民族”与“政治”的模糊与区分。
由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在法国于文学世界称霸的情况下,世界文学空间起源进入中期阶段,即“欧洲新民族主义的产生”,“新民族主义的产生和民族语言的‘创造和‘再创造紧密相连”,赫尔德理论在此时因反对法国强权而在欧洲得以传播。他认为应当在民族和语言之间建立必要联系,各民族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评判标准,“有独立于其他文化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各民族应当获得政治和文学存在上的平等。据此赫尔德提出与杜贝莱的“资本转移”不同的方法使处于文学世界弱势地位的国家和民族得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其中一个途径即“人民”。通过给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与他人平等享有存在和尊严的天然原则……赫尔德认为“语言是‘人民的镜子——‘语言是文学的储存器和内容。”将文学与民众本身联系起来,“民众传统的重要性或真实性”是衡量文学的重要标准。通过这种方式将会帮助国家和民族積累起新的文学资本,而这种文学资本使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与政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世界文学空间起源的后期即“去殖民化阶段”,一些被排除的世界文学空间之外的国家和民族也开始参与竞争。这些国家和民族由于缺少政治上的独立,“民族文学空间为了能作为民族空间而存在”,就要获得政治上的独立。
二、作为民族主义文学形式的现实主义
卡萨诺瓦认为世界文学空间将出现一种对立局面,即最具有自主性的一端文学资本丰富,文学领域已然形成,另一端文学资本匮乏,文学空间依附于政治民族机构。根据赫尔德理论为缺乏文学资本的国家和民族提供的积累途径——人民,以及处于弱势的文学对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力量的依附性,使这情况下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构成“民族或民族主义形式的政治化”特点。作家在创作上要以民族和人民为主题,同时在思想上要“批判”“阐述”“维护”和“阐明”民族的事务,卡萨瓦诺在这里有意识地将民族同人民相区分,但两者同样都被用来说明弱势国家的文学对于政治的依附性,“文学是一种斗争或民族抵抗的武器。”这种依附性使得现实主义为其所用,“排除任何形式的文学自主并使得文学创作服从于政治主义功用”。
(一)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与虚幻
乔伊斯认为现实主义是“民族及民族主义作家始终难以摆脱他对人民的‘虚幻之爱”。卡萨诺瓦据此将现实主义表述为“现实主义的”以及“虚幻的”,并用罗兰·巴特的“真实效应”与歇尔·里法泰尔的“真实神话”进行说明。在1850年以后法国文学的“零度写作”出现之前,古典写作作为法国唯一合理的写作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风格,完全适合于准确地反映现实。”但巴特认为法国的古典写作并不是真正的真实,而是服从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3]他认为古典写作所反映的现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神话”。在其后出现的“零度写作”则跳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局限,处于各种社会阶级之中但并不介入。这种“新闻式”的写作与古典写作讲求修辞学不同,呈现出脱离人的价值与意义的客观现实。但巴特认为“零度写作”并不是远离意识形态,而是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它处于为反对服务于各种社会阶级意识形态的写作而产生的历史中。[4]
这些对现实的追求在意识形态的干涉下成为“现实与想象的最终结合”,从中“诞生的现实主义是与政治目的和利益最相关的学说。”因此现实主义是用以服务于政治的最佳形式,而二次世界大战后聚焦于普通人,尤其是无产阶级人民的贫困的新现实主义美学与“民族化”“平民化”语言结合起来,这种民族性、大众性的文学是“处于政治监护下的文学世界的作家文学他律性最完美的表现。”与卡萨诺瓦相呼应的是巴特对这种追求现实的文学写作受意识形态控制的观点并不止步于此,他认为“历史对文学写作的制约性往往通过语言结构对写作的制约性表现出来。”而语言结构同时是服务于权力的,尤其体现在其“断言的权威性和重复的群体性。”作为声明追求现实的现实主义,与其他并不标榜“现实”的写作相比,更能将虚幻的性质隐藏起来,将其受意识形态等因素控制所创作的实际上融合了选择性现实与幻想、理想的“现实”展现给众人,说服众人去信任。当其与大众化的语言相结合,无论从主题还是语言更紧密地与民族联系,这种民族性的文学是文学世界处于弱势地位而依附于政治,国家与民族政治上需要文学的“声援”时最符合实际的武器。
(二)功用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学与其外的形式主义和“纯文学”
与弱势国家和民族所需要的文学现实主义相对应的是强势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形式主义,当前者的文学资源经过合并,赫尔德理论所强调的民族的独特性经由民族主义文学创作显露于国际时,后者从文学实用功能主义、文学外部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关注转向对文学内部的各种选择、大众与民族主题消失的非政治化、纯文学化,“参与发展形势和源于各种非特定因素形式的研究,参与剔除文学中所有非文学化观点的辩论。”这是文学对政治已经没有强烈的依附性时的一种文学自主。卡萨诺瓦通过卡夫卡对意第绪语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弱势国家这种民族主义文学的理解。
在论及部分学者对卡夫卡该思想的错误解读时,他着重提到了德勒兹和瓜塔里对弱势国家和民族文学创作的看法:“这样的文学成为少数文学是一种光荣,即对任何文学他都是革命性的”;“‘少数不再指某些文学,而是指所谓的大文学或者所有已存文学内部的革命因素。”由此卡萨诺瓦从弱势国家里在政治上最民族化的文学延展开去,论述了卡夫卡意识到的民族文学运动中作家个人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复杂而丰富的关系,以此来展现民族文学在文学世界可能产生的效应和自主性。他强调了民族文学运动中的两端,即政治上最民族化的作家和支持完全国际化自主立场的作家。以哥伦比亚文学运动为例,他展现了处于两端诉求的作家以及处于中间的作家的精神与创作交汇所形成的弱势国家和民族的文学盛况,这是一种远离文学世界中心的独立体系的灿烂。同样也显示了弱势国家内部文学和政治存在的复杂关系以及其中的撕裂。[5]
三、“人民”与“民族”含义从相同到互相区分
自赫尔德提出弱势国家和民族可以通过进行以人民、民族为主题的文学创作来进行具有民族特性的文学资本积累以来,“人民大众”与“民族、国家”的含义被等同起来,与现在“人民”的政治化含义相对比这一时期的“人民”更符合作为“民族”具象化要求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并帮助弱势国家凭借自己的民族性文学创作进入文学世界。卡萨诺瓦认为19世纪德国为“人民”一词所设定的“属于民族范畴的就是人民的。”在表明“人民”几乎与“民族”等同的同时,也显露出两者之间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关系,属于民族范畴的是人民的,人民在一个国家、民族之中,抒写其中的人民大众的确可以归于在书写民族中的存在,但是否可以等同于书写整个民族的特性,被视为民族在文学中应当出现的唯一形态,是存疑的。十九世纪后期由于阶级分化和矛盾的加剧,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的蔓延,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而言,何为人民大众,民族文学中所指定书写的人民大众为怎样的群体这些问题愈发清晰起来。因此19世纪末,“在民族(或者民族主义)定义之上,又加入了‘人民的(此时的人民被看作社会‘阶级)这个社会观念。”“人民”与“民族”含义的划定不再是以往的等同,而是逐渐明确两者之间的差异。“人民”既可以是为积累文学资本所重新利用、书写的作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最能体现民族特性的传统农民神话,又可以是现在阶级分化下“民族”这个被统称为人民阶级的组成部分。
之后,“人民”的民族主义定义逐渐受到质疑,卡萨诺瓦以爱尔兰文艺复兴为例说明了在这一时期人民从民族的观念改为人民是一个阶级的观念的转变过程。由于爱尔兰对民族独立的追求,爱尔兰的民族文学与爱尔兰的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政治上的脱离和独立相同的是,爱尔兰在民族文学上同样表现出一种脱离和对立的形式。该时期英国的现实主义往往围绕资产阶级进行创作,以展现城市里的“上层阶级”的社会风貌,也被称为“客厅里的文学”。[6]而爱尔兰在民族文学的创作上将这一现实主义创作转变为对乡村、农民、工人的现实风貌的展现,先后出现了科克所提倡的乡村现实主义,以及肖恩·奥凯西突出的工人现实主义、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等。这是爱尔兰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所确定的“人民”,一种不同于国家、民族中的上层阶级的中下层群众。在朝鲜这种以无产阶级为主导政权的国家和民族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的文学形态中出现了书写他们所承认为人民的无产阶级文学以及与民族主义文学两个不同的类别。
四、结论
根据卡萨诺瓦关于文学世界内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国家的论述中展现出的文学通过语言与政治建立起来的互助、依附的关系以及提到的赫尔德理论中以民族为主题的民族主义文学是文学资本积累的新解法,本文通过结合历史进一步阐明了作为民族主义文学最好的创作武器——现实主义因其能够以真实地反映现实为“口号”隐藏自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趋向,并在其中渗透其思想倾向,当其使用大众化的语言,以及将人民大众作为主题进行书写时,比起其他文学形态更能塑造出弱势国家、民族想要在文学、政治世界展现出的民族特性与姿态。作为民族主义文学主题的民族、人民与大众,也经历了一个从能够互相替代的关系到分化为是民族和政治不同层面的存在的过程,即人民是在现代阶级发展分化下的一个政治阶级概念,是民族中阶级的组成部分。民族主义文学的创作主题因此也更为丰富和复杂。在民族主义文学之外文学创作者在文学对政治具有强烈依附性的时期对民族主义文学的认同与反对所产生诸多思想和作品,也可能使一个弱势国家、民族的文学在远离文学中心的文学世界获得自己的文学独立与世界认可。
参考文献:
[1]蒲雯.法国近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特点分析[J].黑龙江学院报,2016,7(05):171.
[2]梁志芳.文学翻译与民族建构——形象学理论视角下的《大地》中译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22.
[3][4]龙佳解,陈磊.论罗兰·巴特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从“神话学”到符号学的转换[J].西南民族大学(人文社科版),2017,38(10):167-168.
[5]方瑛.诗歌之国 群星闪烁——哥伦比亚文学掠影[J].语文学刊,1994,(02):29-31.
[6]方茜.何以为爱尔兰:论爱尔兰文艺复兴中“爱尔兰特性”的论争与嬗变[D].武汉大学,2017.
[7]孙伯.叶芝的戏剧理念:去殖民化的诗学[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01).
[8]陈仪.卡萨诺瓦“文學世界共和国”研究:论文学评价机制的演变[D].华东师范大学,2019.
[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