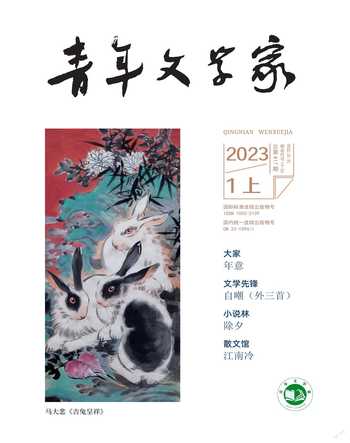浅析白先勇《台北人》中的上海书写
刘钰
上海,这个在近现代中国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城市,时常被纳入作家的创作视野。在白先勇的笔下,上海这座城市也被反复提及。在其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白先勇以他的童年经验为基础,诠释着他心中的上海。在他笔下,上海虽是繁华的现代都市,但这种繁华也有其畸形的一面。同时,在白先勇《台北人》的上海书写中,又展现出上海独特的象征意义。由此,它突破了地理空间的界定,变成了客居台北的上海人的心灵寄托,成为乡愁情结的载体。因而白先勇通过《台北人》中的上海书写,不仅展现了上海二十世纪的城市风貌,还彰显了其对“文化乡愁”的思考。
一、繁华都市的影像
白先勇在散文《上海童年》一文中书写过他记忆中的上海影像—“大世界”的哈哈镜、车水马龙的静安寺路、上海滩头到处播放着的周璇的歌、霞飞路上通宵不灭的霓虹灯。白先勇在1946年至1948年居住于上海,不过此时的白先勇尚处于孩童时期,对于这段上海生活的童年回忆恰如他自己所言,“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白先勇《树犹如此》)。在他小说集《台北人》的诸多作品里都存在着对上海这个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繁华生活的描写。在白先勇的笔下,霞飞路、静安寺路等代表上海的道路,与百乐门、国际饭店、大光明剧院、兰心剧院、天蟾舞台等标志性建筑皆成为其勾勒繁华上海的工具。
《台北人》的开篇《永远的尹雪艳》就是以上海作为基础背景的故事。此篇对上海都市风情的渲染全然凸显了其现代繁华的一面,无论是尹雪艳在百乐门舞池里跳着摇曳生姿不失自己步伐的快狐步,还是王贵生和尹雪艳在国际饭店里享受的华美消夜,抑或是洪处长和尹雪艳在法租界居住的花园式洋房,包括台北新尹公馆的格局布置、文中时不时出现的京沪小菜、尹雪艳的穿着打扮等等,都带有明显的繁华上海特质,更不必说在众人眼中的主人公尹雪艳就是上海百乐门时代的象征。“繁华”“荣华”是作家给上海这座城市贴上的最鲜明的标签,也正是这样的上海才能吸引尹雪艳周围的“旧雨新知”不断地回望与迷恋。
对上海繁华的书写不仅存在于《永远的尹雪艳》中,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游园惊梦》等篇中,白先勇也对上海的繁华着墨较多。上海的繁华是金大班一直念念不忘的百乐门,当她用老上海话狠狠地唾弃着夜巴黎的舞池不及百乐门的厕所宽敞时,百乐门的气派已在无意中彰显。此外,上海的繁华也是静安寺路为朱焰执导的电影而车水马龙的景象。只有在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才会有电影院这类现代的场所。无独有偶,在《游园惊梦》中钱夫人对在上海天蟾舞台看张爱云演《洛神》的经历之回忆,也在同等程度上表现着上海无与伦比的繁华与现代。只有在上海这类现代大都市才会因为电影的开映而车水马龙,才会出现专用于演出的高档剧院。
上海在二十世紀的繁华一直被人们惦念。白先勇通过《台北人》中的上海书写,复现了他儿时的上海印象,留下了那“最后一抹的繁华”。繁华的上海有着南京路、霞飞路、静安寺路等宽敞开阔的马路,在这样的马路上,车马飞驰而过,人群来往不息,豪华的汽车上还载着时髦的都市女郎。马路周边建筑物耸立,既有享有“远东第一高楼”美誉的国际饭店,也有享有“远东第一乐府”艳称的百乐门,还有大光明剧院、兰心剧院、天蟾舞台等摩登建筑。将白先勇在《台北人》各篇中对于上海都市风貌的描绘汇集观赏,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跃然纸上。
二、繁华背后的畸形
“上海的繁华是异常畸形和脆弱的。”(李俊国《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作为“外国飞地”,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异常迅速,西方历经三百年左右的现代化转型却在短时间内还处于小农社会的中国上海快速架构,这无疑是一种囫囵吞枣式的“复刻”。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使上海由一个昔日的小渔村摇身一变成为一座繁华的现代化大都市,也难免导致繁华背后的畸形。
棉纱财阀王家的少老板王贵生开着崭新的凯迪拉克在百乐门门口等候,载着尹雪艳去国际饭店吃夜宵的场景;金大班在上海“百乐门时代”和小姐妹玩转上海滩的风头;朱焰执导的《洛阳桥》在上海大光明放映时静安寺路车水马龙的情形;蓝田玉和钱志鹏在上海天蟾舞台看张爱云演《洛神》的经历……白先勇笔下的这一幕幕都市剪影,都和消费、娱乐、享受等物质化生活紧密相关。物质化的享乐追求和消费性的快感体验,已成为这群上海人脱离上海后还依旧延续着的生存模式。
在《永远的尹雪艳》中,来到尹公馆的宾客们就是当初为她在上海百乐门舞厅捧场的那群“五陵少年”。他们之所以追寻尹雪艳,就是因为尹雪艳周身散发着上海繁华的“麝香”。她的公馆看似仅用来招待“旧雨新知”,打打麻将借以消遣,实际上恰恰潜藏着这群人对往昔上海纸醉金迷之繁华生活的无限沉迷,这点从尹公馆精妙的布局就可略见端倪。尹公馆宽敞的客厅里布置着桃心红木家具,塞满湘绣靠枕的老式大靠背沙发,专供打麻将的麻将间里摆着设计精巧的麻将桌、麻将灯,各个房间格局布置得井井有条。房间内夏有冷气,冬有暖炉,四时供养着时令鲜花。无论是午点、晚饭还是消夜,都备有精致的吃食,大战方酣时有雪白的冰毛巾揩面醒脑。牌局结束后,尹雪艳还会差人叫好出租车将其一一送回家。这些体贴入微之举,显然会让来到尹公馆的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从某种层面上说,这恰恰也是物质享受到极致的一种表现。老朋友都把尹公馆当作世外桃源,就是因为被上海的繁华熏晕的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舒适的生活,这是在台北无法体验到的。只有在尹公馆里,他们才能变回往昔在上海高高在上的成功人士,才可以享受到如同上海那般极度享受的物质生活。繁华都市生活背后奢侈无度的生活恶习,被这群达官权贵一如既往地延续着,他们仍过着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沉迷于对往昔上海繁华生活的种种想象与复刻中。
《台北人》还潜藏着一种较为隐蔽的对上海繁华背后奢靡生活的暗示性描写,那就是尹雪艳、金大班这类交际花形象。《台北人》中赫赫有名的交际花大体上都有一段上海出身的个人背景,而交际花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现代都市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欲望”特质。在白先勇的笔下,此种看重物质、无视情爱的交际花意识,更是被她们延续至台北。尹雪艳到台北后,还是把尹公馆建成了一个如同百乐门般追求物质享乐的交际世界;金大班在秦雄、陈发荣之间,还是选择了更有资产的陈发荣;云芳老六到了台湾,最后还是选择到五月花上班,其实也在说明她们习惯于将身体作为一种商品,去换取她们最基本的生存资本。这种习惯性,或者说是被上海的物质生活培养出来的商品意识,已经成为她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市繁华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与精神堕落的生活相连,最终产生了上海繁荣的畸形一面。
三、都市想象与作家胸臆
白先勇的上海书写固然出自上海经验,或多或少有着他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个性化思考,但他在《台北人》中描述的上海似乎仅停留在大众认知的层面,这就难免构成了《台北人》中上海书写的某种缺失。
在白先勇笔下,上海的现代与繁华,足以激发读者对上海的想象,但是他对繁华上海的描摹,只是从那些代表性建筑入手,用一些形容词进行简单勾勒,却很少描摹这些建筑的具体模样与内部构造。这种书写,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对上海这个城市的简单描绘,但缺乏作家对于上海的城市肌理与内在底蕴的细腻刻画。综观《台北人》整部小说集,这种体现出某种缺失性的上海书写,恰巧与白先勇想要在《台北人》中凸显的主题密切相关。
上海自开埠以后,逐渐成了中国现代程度最高的城市,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为国人向往。这种向往也因上海这个城市的特殊性,令国人产生一种矛盾心理:国人既钦羡上海繁华、物质条件丰硕,又在一定程度上畏惧着这种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对原有生活模式及道德传统的颠覆。在《台北人》中,白先勇构建的上海形象恰恰切合了国人对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向往。
“一个城市的文化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首先是它的各处地名,各个景点,各条街巷名所代表的一长串历史,一系列记忆,当这些地名、景名、街巷名被识名性地描写出来的时候,其所代表的历史与记忆自然就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朱寿桐《论现代都市文学的期诣指数与识名现象—兼论上海作为都市空域的文学意义》)白先勇在《台北人》里所构建的上海形象,正因这种强调“上海感”的识名现象,反而强化了国人对上海的共同想象,引起读者对那段历史的识记与追寻。虽然不那么切入上海的特定肌理,却在一定程度上使读者更深刻地体悟到“台北人”为什么会迷失在“上海记忆”里。也正因如此,读者才能更深切地体味白先勇小说里想要表达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的主题。白先勇在《台北人》中表达的“文化乡愁”,以及对于类不可避免的生存困境的个性化思考也因之凸显。
“白先勇写地域空间而不是真正地写地理风貌,而是在多地中探求人性。”(韋霁琛《离散与乡愁—白先勇小说的多地性研究》)他想彰显的不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繁华生活和城市肌理,而是想理性地探讨人的生存困境,即这群离开上海的台北人,为何一如既往地追求着繁华上海的梦境。欧阳子曾言:“《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欧阳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虽然小说题名为台北人,但是这群台北人实际上是客居台北的异乡客,由此上海和台北也形成了今昔对照。在《台北人》中,台北是白先勇主要刻画的城市形象,人物的故事都发生在台北。上海并不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书写,而是作为人物历时的背景生活经历被提及。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展现着回望上海的姿态,但上海生活已经成为昔日的“光辉岁月”,给人以“无可奈何花落去”(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之感。他们生活在台北,却逃避着现实,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对上海生活的思念,内心渴望“似曾相识燕归来”。上海已经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更是人们心灵上的归宿,由此上海也成为这群客居台北的上海人寄予乡愁的某种载体。
诚如余秋雨所言:“时间上的沧桑感和空间上的漂泊感加在一起,组成了这群台北人的双重人生幅度,悠悠的厚味和深邃的哲思就从这双重人生幅度中渗发出来。”(余秋雨《世纪性的文化乡愁—〈台北人〉出版二十年重新评价》)通过客居台北的上海人对上海繁华生活的种种追忆式书写,白先勇以一种悲悯情怀思考着人类不可避免的生存困境,深深震撼着读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