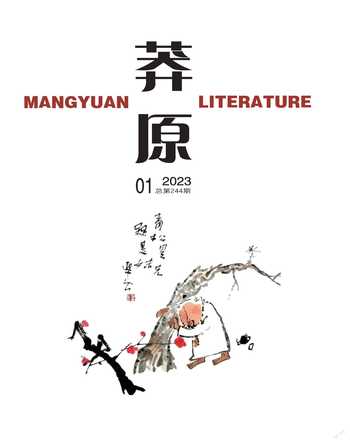胎记
刘诗伟
沔水的老人们都记得:三十年前,别大魁在县城出过一次名。
别大魁出生于沔水乡下,当年大学毕业分回沔水县,在沔水师范学校做语文老师。因为之前念书下了功夫,脸上没肉净显得颧骨高,眼睛小又熬得眼眶很大;也不讲形式主义,一头小偏分,穿件半新不旧的咖啡色夹克,不如大院的干部庄重,不及医院的医生体面,也不同于人民广场上小青年的花哨;给人的印象是个不打眼的小个子,一上台就说夹生普通话,比如“灰(飞)机灰(飞)到百(北)京城”。
其实,他还有别的特点,隐藏在屁股上。
他的屁股左边上方有一个胎记,图案很奇特。怎么奇特呢,不大好讲,在他的屁股被披露后,学校流传着关于这块胎记的种种嘀咕,都是犯忌的正面意象,譬如像沔师校长的脸,不宜深究。
正是这个胎记,让别大魁回沔水的第一年就出了名。
这事跟学校食堂的工友王小胖有关。王小胖是别大魁的发小,小时候两人赤光着身子在河沟游泳,他见过别大魁的屁股。本来,王小胖作为县里最高学府的工友,地位不俗,又有油水滋润,早已忘记分道扬镳的别大魁。可偏偏这家伙大学毕业又回到沔师,每天在食堂窗口把大瓷碗咣当一送,朝他嬉笑,还净点最贵的荤菜。两个月后,王小胖去学校门卫室抽烟,谈天说地间,巧妙公布了别大魁屁股上的胎记;并且补充:那是千真万确的,当年,小学校长还批评过别大魁的父母,说他们生孩子太马虎太不严肃。
故事如此高级,自然一传十,十传百。起初,人们对别大魁胎记的看法分两派:一派觉得把学校领导的“正面意象”放在屁股上实属亵渎;一派认为屁股上出现“正面意象”反映了高贵的遗传。好在大家都有一定的觉悟,多半是逗乐子,乐呵一阵,道理讲不下去,当场就归于和谐。只是,各自回头想象这胎记,越想越离谱,又生出许多新的趣味。
有一次,别大魁出了校门,身后的俩人隔着裤子看他的屁股。别大魁听到动静,回过头去,那俩人赶紧抿住笑,跟他招呼。
这事给别大魁带来的破坏不小。沔师附小有一位身材高挑的青年女教师,别大魁很是心仪,打算跟人家处对象,已经相约去河堤散过步了,可胎记的事一经流传,再约时,女教师就以忙着备课为由推辞了。不久,别大魁又喜欢上县医院一位妇产科女医生,托人说媒,媒人回来摇头,别大魁问咋的,媒人支吾道:女方听说是你,捂起嘴咯咯笑着直摇头。别大魁不由愤骂:我操!
两年过去,别大魁还是单身。校长毕竟宽宏大量,有意帮他,提议由他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不料,别的校领导不知出于何意,看着校长,光笑不表态。别大魁晓得了,照例愤骂:我操!遂去找到校长,婉言谢绝了校长的好意。
到年底,沔师全体教职员工去酒店聚餐,语文组教师坐在一桌。酒到酣时,席上有人替别大魁的胎记打抱不平,别大魁被煽动得忍无可忍,嚯地起身,作势要解裤带褪裤子,嘴里大喊:我叫你们看看,你们看吧!可毕竟大庭广众之下,又有女同事在座,当众露出屁股是不雅之事,更有失教师身份。有人阻止,有人却不甘,于是,派代表跟别大魁去了厕所。别大魁褪下裤子,撅起雪白的屁股,代表们的目光抖了一下,缓缓聚到一处——原来那胎记毫无意象,不过是一枚硬币大小的乌青色斑!语文组的同仁就愤怒了,当即到隔壁餐桌,质问王小胖何以诬陷别老师。但王小胖耍赖,说他说的是别大魁小时候的胎记。
自此,胎记的事不了了之,别大魁恋爱结婚,老婆竟是那个妇产科女医生吃了回头草。新婚之夜,别大魁看到女医生的屁股上也有一个胎记,就哂笑说,对象对象,不像哪能对得上!
待儿子出生,别大魁把王小胖带到家里看儿子的屁股。王小胖认真看过,讪讪地笑:这胎记没什么特别呀,难道当年我看错了?别大魁笑笑:记得哦,下不为例。
此后,王小胖专心打菜,别大魁安心教书,日子祥和平顺,彼此相安无事。
时间一晃三十年,世上风气流走,人事来去,一年一花样,沔水县改成了沔水市,当年的沔师校长也升任了沔水市长。其间有一年,学校要给别大魁一个教务处的职务,被别大魁作揖谢绝。别大魁已年过半百,身材越发矮小,形象依旧潦草,单是胖得厉害,脸上的肉多了,眼窝儿已经填平了。
不料,没过多久,别大魁又出名了。
这回不是因为胎记,是因为写小说。别大魁业余写小说多年,每年都能发表两三个中短篇,在沔水市的文学圈里小有响动。上年末,有一个中篇,写市长捉小偷的故事,被市长夫人读到,推荐给市长看,市长觉得不错,由于小说背景很像沔水市,就向人打听,得知作者正是别大魁。不久,在一次文化工作会议上,市长特意提到这篇小说。这样,别大魁就放了卫星,一日博得大名。
来年春天,别大魁加入了省作家协会,接着又参加省里举办的创作高研班。春天还没过完,本市传出成立市作家协会的消息,好像也是冲着别大魁来的。一天,市文联写歌词的老白请别大魁下馆子,约了六七个文友作陪。席间,觥起杯落,都说大魁兄小说写得好。不知谁冒出一句:沔水市作协主席非别老师莫属。众人就跟着起哄,大有逼他就位的态势。别大魁欢喜得稀里糊涂,不慎将烟灰抖落在汤碗里。
老白右手边有一个眼镜青年,嫩红的脸,一直沉着平静。老白拍拍他的肩:超魁老弟咋不说话?眼镜青年连忙回应:我,我赞成大家的意见。别大魁是敏感的,主动跟眼镜青年搭讪,得知他全名叫王超魁,在沔水报社工作,是沔师工友王小胖的儿子,按辈分应该叫他魁叔。别大魁想到王小胖给儿子起名超魁,不禁心里哂笑,这老家伙,自己比不过我,就拉儿子上阵,一时间竟有点儿同情这孩子了。
两个月过去了,成立作协的事没什么进展。
突然有天晚上,老白在微信上给别大魁发来一篇网文的截图,文中指责别大魁屁股上有一个胎记,像“某市领导”的脸,“极不严肃,极其低俗”。别大魁并不以为意,问:你信吗?老白回:不信。别大魁送出一串大拇指和呵呵笑。
又一天,一个陌生电话打来询问胎记的事。别大魁说自己屁股上是有一个胎记,却并不像谁,更不像哪个市领导。几天之后,网上就传出他不敢亮出真凭实据;别大魁跟了个帖子,说自己那个胎记其实很小很淡,根本没有象形的特征,网上马上开始写他含糊其辞;别大魁大骂“我操”,网上就写他已经恼羞成怒了。
别大魁没想到情况会越来越复杂,实在没法子,干脆对陌生电话与短信一概不理。
别大魁老婆是在三十年前上过当的,这回决不罢休,很快組织一干亲友用匿名去网上应战,从生理、文化、法律和社会道德的角度,进行猛烈驳斥、嘲讽和怒骂。一时间,网上热闹非凡……眼看就要演变成了舆情。别大魁苦闷多日,终于被逼出灵感,对妻子说:要不这样,我脱掉裤子,你拍一段屁股视频发到网上去?妻子嗤道:那也没用,脸都可以化妆,屁股就不能?谁信啊?
又过两个多月,沔水市文联牵头筹备成立市作协,初拟了三个主席候选人:别大魁、王超魁、老白。文联主席找别大魁谈话,先说明来意,再询问网上的事,别大魁摆手一笑,当即表示他坚决不当主席,并竭力推荐老白当。等文联主席一走,别大魁就串通老白,恳请老白一定替他顶上,不然就让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了。
秋天,市作协成立,老白任主席;王超魁同志因为是行政科级干部,按政策不能在协会任职,组织上让他兼任作协党支部书记。那天,参加作协成立大会的人不多,别大魁拿出稿费请大家喝酒庆贺,王超魁也到了。酒喝到一半,王超魁把嘴附在别大魁耳边,说:魁叔,你不该推辞的,蒸熟的馒头让别人吃了……别大魁已是半醉,听见“蒸熟的馒头”,把王超魁看成了他爸王小胖,甩着指头哂笑:记得哦,下不为例。
谁都没想到,网上又不干了,画风突变,大量帖子为别大魁落选抱不平,言辞之激烈,跟别大魁妻子先前的驳斥、嘲讽和怒骂不相上下;而且有人披露,说某某是受某某唆使炒作别大魁胎记的……眼看又是一轮舆情。别大魁一点也无所谓,去阳台的月光下抽烟。
有一条消息没参与炒作,发在了别大魁手机上,是出版社编辑发来的,希望为别老师出版一本小说集。别大魁回:谢谢,缓缓吧。对方回:不能缓——要趁热咧。别大魁心里哂笑,不再应答。
一连几天,别大魁枯坐在书桌前,心思飘忽。妻子进到书房,关心地说:主席没当上,咱又不差钱,还写吗?别大魁愣愣地看看妻子,不由心头一乐,笑了,想说老婆你也有一个胎记咧,终又没说。
责任编辑 刘钰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