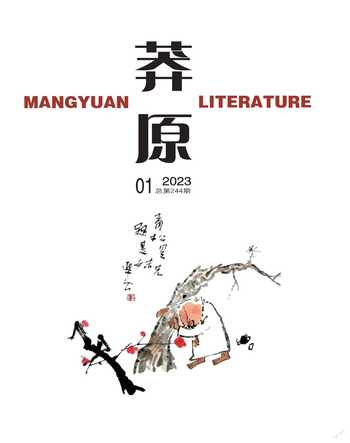晒阳坡
李剑鸣
小镇叫狼谷口,却从未见过狼,四面被铁桶似的群山围定,楼就傍山而建,一圈一圈往当中旋。当中留空儿,成了中心广场,广场上长满遮天蔽日的大树,把天上的亮光掰成了碎碎的花影,小镇就再也见不上囫囵太阳。
镇上的人都跟树一样老,一年四季穿夹衣,外面披张塑料雨披,缓慢地在树下蠕动,像爬虫。雨从年头能下到年尾,下雨的时候,悬帽咀上就聚起一团白雾,像一口怨气似的悬着,终年不去。一年里难得晴好的那几个日子,悬帽咀上的烟雾终于散尽,人们脱下霉湿的塑料雨披,缓慢爬上山坡去将军坟上晒日头。
将军坟是小镇北边的一个土包,从下到上拢共一百零八级石阶。顶上是一块平地,不生树木杂草,像秃子的脑壳。人们坐在小马扎上,黑压压一片,像天上飘飞的鸦群,抑或秃头上的虱虫。胡古月和马大力混迹其间,日头晒着他们暗黑色的皮肤和稀疏的白发,晒着他们日渐霉烂的躯干和锈迹斑斑的骨骼。他们像老旧的机器,经年累月的磨损以后,疲倦和衰老如浓重的湿气,浸入骨髓,短促的日头根本无法烘干。
胡古月六十七,马大力六十九。出事的时候,胡古月看到悬帽咀上起了烟雾,说,天要变,日头晒不成了。那时晌午刚过,原本太阳很大,不多时水汽凝聚,天就慢慢沉下来。胡古月缓缓站起,伸手去摸屁股下的小马扎,摸了半晌没摸到,却对着虚空嘿嘿笑起来,说,你也来啦?
马大力随口问,谁?
胡古月张了张嘴,话未出口,人就栽在地上。
雨淅淅沥沥地下,像一场看不到头的长途奔袭。葡萄和番薯坐在病房里,听着窗外的雨滴滴答答。胡古月睡在靠窗的那张病床上,是半昏迷状态,偶尔动动眼皮,眼睛却从未睁开过。值班医生偶尔进来一趟,翻眼睑,摸脉搏,摸完了就摇头,食指和拇指捻着白大褂的衣角。时候不多了,把人弄回去吧,准备准备。医生这话是对葡萄和番薯说的。葡萄和番薯相互看一眼,再没有任何表示。他们连夜从几千里之外的地方赶回来,脸上写满焦虑。
葡萄和番薯是马大力打电话叫来的。葡萄在北京,番薯在广州,都成了家,租住在大城市那窝棚似的小房子里。马大力对葡萄说,老胡怕是不行了。葡萄说,真的?马大力说,真的。葡萄愣了半晌,说,还能坚持不?马大力没言语,把电话掐了,又给番薯拨过去,说,老胡怕是不行了。番薯说,还能坚持不?马大力想了想,说,天晓得。
空气里散发着草木霉烂的气息。窗外是一面石崖,长满青苔和灌木,一群白头鹟隐匿其间,唧啾唧啾地叫。葡萄和番薯坐在凳子上玩手机,偶尔抬头看胡古月一眼。从白日到黄昏,天总是阴沉沉的,像要塌下来。葡萄手机没电了,对番薯说,我去吃饭,回来换你。到了夜里八点,葡萄还没回。番薯饿了,打电话过去,葡萄说,你不会叫外卖啊?番薯骂骂咧咧地摁断电话,站在床边看胡古月。胡古月仍旧保持着那个姿勢,死了一般,一圈白发从鸭舌帽的边沿挤出来,像褪了墨色的羊毫秃笔。番薯把吊针管的碾子掐到最小,也走了。
后半夜,胡古月醒来,吊瓶滴干了,血回了老高,大半截管子变成了血的颜色。胡古月先睁眼看窗外,窗外不是石崖了,是翘脚的屋脊,白色的鸽子站成一排,咕咕地叫。胡古月眨眨眼,鸽子飞走了,屋脊变成了长满绿植的坡地,身穿铁甲的将军站在那里,背上扎满箭镞,花白的须发上粘着绿苔和浮藻,红色的铁锈顺着湿漉漉的裤脚往下滴。将军手持一柄布满绿锈的铜剑,慢吞吞地去砍一棵老树,树叶把阳光挡得死死的,将军感到烦躁。砰——砰——砰——铜剑砍在树干上,树却没有丝毫变化,连叶子也没颤。看了半晌,胡古月说,老哥,歇口气,吃根烟。他舌头僵直,说话不利索,呜呜呜的像吹喇叭。将军侧过头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脸上沾满泥浆。胡古月说,你是坟里的那个将军吧?我知道你。将军不语,手拄铜剑站住,像一尊雕塑。胡古月挣扎着要坐起,却没有力气,叹了口气,说,老了啊。
将军抬头看天,有几丝日头的亮光从密密匝匝的树叶间穿透,散落在地,像一面摔碎的镜子。将军赌气似的把铜剑一扔,坐在树下掩面沉思。树下聚了一团白雾,把他裹在当中,雾气在胡须和发梢上凝结成细碎的水珠,一粒一粒往下落。将军浑身瑟瑟抖动,背上十几根箭镞也跟着抖,像一头豪猪在打冷颤。将军站起来,重新捡起铜剑,砍了些带刺的灌木枝拢成堆,从腰间摸出火镰打火。四溅的火星子引燃了火绒,柴草冒出阵阵浓烟,却终究没有起焰。将军被熏得双目流泪,最后无奈地摇了摇头,颤颤巍巍地爬进一个山洞里,再也没出来,只有风刮过的灌木枝还在轻轻地颤,抖落三五滴雨露来。
胡古月从病床上爬起,扯掉输液的管子,不顾手背上还在渗血,就一颠一颠下了床。他的半个身子僵硬,几次瘫软下去,最终靠一只手抠住窗台板立起来。他拉开窗,外面漆黑一片,巨大的石崖横在眼前,石崖光溜湿滑,连苔藓都难站住。胡古月看了半晌,再看不到将军的半点影子,大约他已经走远了。
胡古月在病床上躺了七天,七天里葡萄和番薯轮番守着,马大力也偶尔过来,拎一串香蕉或几个橘子。值班医生不再提张罗后事的话,改为动员病人出院,医保要超限的。雨断断续续地下,天一刻未晴。马大力说悬帽咀上又起雾了,很重的一团,风吹不散雨化不开,这雨怕是要下到明年。悬帽咀挨着将军坟,也是一个土包,也是一百零八级石阶,道路湿滑,没人愿意上去。老人讲,悬帽咀上有一个天坑,大无边,不见底,雾气就是从天坑里冒出来的。悬帽咀上起雾的时候,天就要下雨。悬帽咀上几乎一年四季都笼着白雾,所以小镇上几乎一年四季都在落雨。
马大力剥根香蕉送到胡古月枕边,胡古月摇头,马大力就自己吃,边吃边讲,前天夜里从外头开来一辆牵引车,火车似的长,车上拉一台绿色的挖掘机,轰隆隆地就把南边的那一排老房子扒了,要起新楼。镇上的人都跑去看,一窝蜂似的,身上套着五颜六色的大号塑料袋,或站或坐。雨断断续续地下,开挖机的师傅换了三班,看的人雷打不动,一看就是一天。天黑了,挖机熄了火,人才慢慢地散。胡古月说,还在挖?马大力说,挖,说着以手作铲,舞出一套挖机挖地的手势。胡古月眼里闪出亮来,他的言语只有马大力听得懂,连蒙带猜,虽然费些劲,但总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外面一阵吹打声,是铜管乐队在演奏歌曲,第一首是《世上只有妈妈好》,第二首是《父亲》,第三首是《今天是个好日子》。三首曲子奏完,小号似在调音,又呜呜叫了几声,终于安静了。胡古月指了指窗外,问是迎亲还是送葬?马大力想了想,说,结婚不到医院来的。那是小镇里唯一的一支铜管乐队,几个老头老太太自个儿凑的,谁家婚丧嫁娶都去请,来了就三首歌反复吹,早上一遍,晌午一遍,晚饭前又一遍,有时候天黑了还吹一遍。小镇里隔三岔五就有人咽气,铜管乐队吹吹打打,能从年头热闹到年尾。
出院那天,葡萄推来一辆轮椅,把胡古月放在里面。轮胎忘了打气,在石板路上颠来荡去。胡古月感觉罩在塑料雨披下面的身子要散架,尤其僵掉的那一半,已然与他脱节。屋在一楼马路边,本是铺面,没人租,胡古月就自己住。番薯借来一把角磨机,把家里的门槛切了,方便出入。
葡萄做了一桌子菜,还起了瓶酒,没人喝。番薯吃了三碗米,马大力吃了两碗,胡古月和葡萄都没怎么吃。饭后,葡萄把一大堆衣裤塞进洗衣机,洗好了,经幡似的挂满屋,又把玩手机的番薯叫到屋外,嘀咕半晌,回来了。葡萄立在床边,隔着蚊帐对胡古月说,我得回。胡古月不语。葡萄说,让番薯先照看你。胡古月不语,番薯扁了扁嘴。
葡萄走的第二天,番薯对胡古月说,我也得回。胡古月不语,尿片子湿透了,裤裆里黏糊糊的,难受。番薯指了指马大力,说,让老马先照看你,钱我和葡萄对半出。胡古月呜呜呜地嚷,嚷了半天,番薯没听懂,回屋收行李去了。天明,番薯要走,走前对胡古月说,父愁子妻,子愁父葬,我的事你愁不上了,但你的事,我愁。
外面阴沉,屋里也黑漆漆的,大白天还要开灯。马大力戴一副老花镜,把胡古月裤子扒掉,给他换尿片。马大力把尿片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瞅了半天,总算弄明白了哪里是屁股哪里是肚腹。马大力说,你抬腿。胡古月就抬腿,一条腿撑着下半身,腰和屁股拱起来。马大力把旧尿片扯了,砰地砸在地上。胡古月撑不住,屁股跟着塌下去。马大力说,你再抬抬腿。胡古月就抬,咬紧牙憋住气,把屁股和腰拱起来,挣得眼里泛起了泪花花。味儿很冲,马大力擤了擤鼻子,把尿片塞进胡古月的裤裆,还顺带瞅了眼稀疏的灰色毛发当中那面条样耷拉着的物件儿。粘好了贴扣,两人都长吁了一口气。
转天一早,马大力烧了一大锅红薯稀饭,一人喝了一碗,就推着轮椅去镇子南边看扒房。人很多,一层一层把挖机和房子圈在当中。房是砖房,顶上长满绿苔和瓦楞草,木头柱子上密密麻麻尽是虫眼。绿色的挖掘机像只巨大的野兽,铲斗只轻轻一拍,烟尘四起,一间老房子瞬时倒了大半,又一铲斗压下去,整间房子就变成了废墟。
胡古月看到被烟熏得黑乎乎的墙砖瓦解了,残砖断瓦的下面,一只被压扁的竹筛,像一顶土灰色的帽盔。将军呆坐在废墟上,手撑住下巴,两眼望着那只竹篩,似在沉思。将军!胡古月失声惊叫,但四下里喧嚣异常,人们惊叫连连,没人听得懂他含糊的言语,也没人注意到灰头土脸的将军。铲斗朝将军所在的地方一扣,一勾,又一刨,将军就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下面,想往外爬,爬不出来,五指粗壮的手在徒劳地抓扯,指甲缝里填满血泥。胡古月脸色惨白呼吸粗重,他虚弱地闭上眼,浑浊的老泪在密布的皱纹间肆意横流。
那天夜里,胡古月梦到了李副。李副还是四十岁的样子,生过葡萄和番薯,赤裸的腰身上赘肉嘟噜噜颤,屁股硕大如盆。胡古月说,来了?李副不语,只是笑,还不住地撩头发。她的头发留到了腰上,烫着波浪大卷,还染了栗子色,左耳戴个项圈似的大耳环。胡古月说,渴。李副把床头柜上的杯子拿给他看,沾满茶垢的杯底子是干的,像被火烧过的焦土。胡古月说,葡萄和番薯都来了。李副不语,掀开被子,看他枯柴一样的肉身和松弛的皮肤,看他裹在尿片里的裤裆,看着看着就笑,手虚捂着嘴,没有声儿。胡古月想把被子拉过来,把身子苫住,却拉不动,就苦笑,说,他们忙,顾不上我,你坐。李副没坐,笑渐渐僵硬,变成了哭,仍旧没有声,只有眼泪汪在眼窝里。胡古月嘴巴嗫嚅,说,莫哭,你莫哭啊。说得自己心里一阵难过,也抽噎起来。
胡古月是被自己的哭声吵醒的,醒来时还在抽噎,不见李副的影子,枕头湿了大片。他用手揩泪时,看到手背上那个黑痣似的瘢痕,心里一阵酸楚。李副是胡古月的发妻,八十年代初的那个国庆节,他以一台半导体、一块老上海手表、一辆凤凰自行车和一对梨木板箱的绝对优势,成功将她迎娶回家。那时他是机械厂的工人,造磨面机和脱粒机配件,到了周末,就换上白衬衣,自行车后座上载着李副,嘘着口哨四处逛。李副能舞弄点文墨,在县委报道组,上头一正一副两个老组长。她是组员,三天两头跟着领导往乡下跑,回来就熬夜写报道。
结婚第四年,李副当上了副组长,时间上有些余闲,便生了葡萄。葡萄三岁,李副从报道组调去文化馆,当了副馆长。文化馆工作轻松,平日喝茶看报,李副把毛衣织了一件又一件,总穿不完。逢年过节就组织文艺晚会,手头有大把的演出票,送亲戚朋友有面子。日子像泉里的水,一眼能看到底。再坐上几年冷板凳,织满一大板箱毛衣,兴许她就能熬出个正职来,日子便见底了。
葡萄五岁那年一个礼拜五的夜里,胡古月去单位澡堂子洗澡回来,见葡萄还在外面玩,就拉李副进屋,把灯灭了。李副不情愿,也不拒绝,说,那个,那个措施。胡古月说,好,低头舞弄了几下,就动起来。动了几个来回,李副突然一个打滚,一脚蹬掉胡古月,把腿夹得死死的,说,不对,我觉着不对。开了灯,果真就看到胡古月光头不戴帽的狗样子,翘在那里,像一根红头火柴。李副说,你要害我。胡古月干笑两声,说,不能。
葡萄是个闺女,胡古月不乐意,天天念叨要个儿子。李副把腿夹得针插不进,把眼珠子瞪得像灯泡,说,双职工,超生都得开。胡古月说,那能咋?李副说,你说能咋?胡古月说,别闹,你抬抬腿。李副说,你莫想。胡古月说,你逼我?李副说,是你逼我。胡古月哼了一声,说,鸡巴的事儿也有人管了!李副说,等两年再说。胡古月摸了摸自己谢顶的脑袋,说,再等我就秃成和尚了。李副说,那就拉倒。胡古月有些恼,说,你他娘还过不?李副把被子往身上一裹,背过身去,说,爱过不过!
日防夜防,李副还是怀孕了。李副的生理期不太准,有一搭没一搭的,自己也不当回事,等肚子一天天鼓起来,才觉得不对劲,去医院一查,坏了。回到家,哭天抢地地骂胡古月,骂毕了,一抹眼泪,把存折拿出来,要把定期取了,要去打。临出门,李副看到茶几上放一截绳,一瓶敌敌畏,一把尖刀,胡古月脸色铁青坐在旁边。胡古月把牙咬得咯咯响,说,害他的命,就是要我的命。李副说,你是要我的命。胡古月嘴一歪,眼珠翻出一片白,说,都甭活,说着拧开瓶盖,要把敌敌畏往嘴里灌。李副尖叫一声,一把把瓶子刨地上,撕心裂肺地嚎,嚎毕了,也就妥协了。
遮遮掩掩几个月,终于生下番薯,是个男孩,活蹦乱跳的。胡古月很高兴,把那对梨木板箱抬出来,仔细擦洗一遍,漆成了喜庆的大红。接着是四处托关系送礼,工作总算是保住了,但处分还得背。番薯满周岁,胡古月的处分先下来,罚一千六,回铸工车间开车床。那时机械厂效益不好,车床不车铁件儿了,车些锅把子捣蒜杵一类的东西卖。闲时,胡古月就给番薯车陀螺和弹珠,后来又打出一把铁叉。幼年番薯扛着它在野河边叉癞蛤蟆,后来还叉死过一条虎斑蛇。李副被罚了三千六,背个处分,从此前途被冻结,到死也没提上正职。李副死前还记挂着身上背的处分,对胡古月说,你把我害了。胡古月说,命里该你有八两,砸锅卖铁不够斤。又说,你这名儿起得也是,不吉利。说到名儿,李副一双眼睛死瞪着胡古月,眼里尽是仇恨。李副的爹就干了大半辈子副手,老来得女,取名李副,是自嘲,多半也是心病。
屋里漆黑一片,没有一丝亮,也不透一丝风,又闷又潮像口棺材。胡古月摸到了灯绳,一扯,终于亮堂了。水杯就放在床头,马大力走时忘了添水,干得跟梦里一样。肚子胀得如一面大鼓,打出院到现在,他没解过大手。在医院时,胡古月想着卧床只是暂时的,也就心安理得地吃喝拉撒,除了躺着解手经常使不出劲儿,费些力气也能对付。出了院,胡古月才知道自己害的是偏瘫,估计得瘫到死,心里顿时横出一道坎,怎么迈都迈不过。
胡古月把能动的那条腿蜷起来,往外撇,然后吸一口气,慢慢使劲。人老了,疲乏是从心底里生出来的,从头到脚都透着酸软无力的感觉。小腹上使着暗劲,像挤牙膏,大半天,人累了,汗珠子从额头滚到耳根。歇歇停停有一个钟头,裤裆里热乎乎软乎乎,人还是觉得不畅快,像鱼刺卡了喉咙,便作罢了,也只能作罢了。胡古月想到了马大力,天亮了他准来,越想浑身越难受,就用那只能动的手去解尿片,解开了,一扯,要往地上扔,劲儿使过头了,黏糊糊的东西甩得到处都是。
天明,马大力拉开卷帘门,就呕。那气味像粥,闷了一夜,越闷越稠。马大力用棉球塞了鼻孔,拿着抹布到处擦,边擦边埋怨,老胡,你咋能这样?胡古月不高兴,便不说话。马大力叹了口气,说,遭这个罪,你图啥?胡古月不语。马大力跟了胡古月大半辈子,打从穿开裆裤起,到死还跟着,死跟。他跟着他进城,跟着被机械厂招了工,跟着下了岗。龙龙消失后,胡古月赌气,回到老家狼谷口。没两年,马大力也跟回来了。而今自己屈辱地躺着,而他却直挺挺地站着,像座山。那年月日子过得清汤寡水,腊月里,天黑了,胡古月上山打野物,马大力跟着打下手。枪一响,马大力和狗一齐往出窜,谁捡到兔子就嗷嗷叫,回家连夜煮了,吃个满嘴油。胡古月的枪打得好,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在省运会射击比赛上拿过奖,有持枪证的。
马大力每三天熬一锅稀饭,吃罢了,不用洗涮,再续一锅。早上,给胡古月盛一碗稀的,放床头,分三顿喂。饭送到嘴边,胡古月有时拒绝,有时抿一口,是自弃,或者赌气。他挨过饿,有经验。小时候生产队修梯田,一口杀猪用的大锅熬白菜和荞面疙瘩,清汤寡水,一人一碗,吃了还得搞农建。起初上顿挨不到下顿,就死挨硬挨,后来习惯了,肚皮塌到后腰上,喝口水也能对付,没水的时候,咽口唾沫也能压住饥荒。
空气里有一股子浓重的鱼腥草的味道。不出一月,胡古月眼看着瘦下去,瘦了又胖,是肿了,皮肤变得透明,像一条要吐丝的蚕,看得清五脏六腑的轮廓。继而开始发烧,大多数时候人在昏睡,或者装睡,但脑子还不糊涂。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将军时的情形。那年,葡萄念到高中,番薯才进小学。有天放学回来,番薯要花环,红色风筝纸糊的那种。胡古月熬了个大半夜,糊了一个。过几天,番薯跟着学生队伍去游街,一边挥舞花环一边铿锵地高喊:庆祝庆祝,热烈庆祝……喊完没几个月,胡古月就下岗了。
胡古月下岗那天,一口气喝了一瓶烧酒,睡到天黑,便背着枪出门,去打山,破例没叫马大力。翻过两座山头,矿灯忘了充电,灭了,就摸黑,高一脚低一脚地瞎撞。撞了一夜,身上尽是树枝刮拉的伤痕,天明时,看到烟雾缭绕的一条山谷,半晌才认清是老家狼谷口。山谷里正站着将军和他的队伍。那时将军比现在年轻,约莫六十出头的样子,骑在马上,铁甲锃亮,花白的须发随风飘动。将军身后跟着一队士兵,个个满脸倦意。打头的挑着两面旗,左面写“常胜”,右面写“威武”,旗子耷拉着,人也耷拉着。突然,鼓角声四起,烽烟弥漫,无数箭镞像雨点一样射向将军和他的队伍。将军坐在马上左右躲闪,同时挥舞长剑格挡,终于还是被箭镞扎满后背。
箭镞射到晌午才歇,那时狼谷口几乎被箭镞淹没,将军也已滚落马下,大半张脸埋在泥地里,箭镞插满脊背宛如一只豪猪。天快黑时,四下里依然没有动静。胡古月悄然下坡,来到将军面前。将军奄奄一息。将军对胡古月说,我中计了。胡古月说,嗯。将军说,我明知道会死,还是来了。胡古月说,嗯。将军说,我老了,我是慷慨赴死。胡古月说,嗯,老了。將军最后说,狼谷口湿气太重,我的骨头痛得厉害,死后要把坟修在阳坡上,多晒晒日头。胡古月没点头,也没摇头,扽出袖子为他把脸上的泥水揩了。
此后多年,胡古月每次见到将军时,他的身上总插满箭镞。胡古月看着将军一天天衰老,须发蓬乱,四肢僵硬,铠甲上的铁锈越来越厚,像旧年的血迹。那副强壮的身板缩了水,渐渐干瘪下去,这让他看上去像只被铁甲困住的老猴。
雨下个没完,空气中散发着朽木头的味道,衣裳粘在身上,像一层蜕了半茬的皮。胡古月又在床上躺了大半月,感觉一天比一天虚弱。每天一大把五颜六色的药片,是医生开好了,马大力配的,但一个疗程吃下来,总会多几粒或少几粒,很少匀乎过。好在胡古月自己想得开,马大力更想得开,反正药总归是吃到了肚子里。吃罢药,有时会头晕,有时会烧心,也有时会想吐,但都没什么,到了这个年纪,人像一条被岁月凿沉的船,也就不指望什么了。偶尔,马大力会把他绑在轮椅上,推出去看挖机扒房。那排老房子扒得差不多了,已经看不到压在瓦砾中的旧物件,只有一些残破的矮墙,被刨平,压实。挖机也不再挣命似的干,慵懒得像个晒阳坡的老头,偶尔伸手碾死个蚊虫。
番薯和葡萄隔三岔五打个电话回来,有时候说两句,有时候说三句,无非是吃了吗喝了吗睡了吗之类的,胡古月呜呜地连比划带说,马大力做翻译,或者根本用不着翻译,只需嗯嗯应承。胡古月悲哀地意识到,这种局面恰好颠倒过来了,以往是他说话,葡萄和番薯嗯嗯点头。葡萄大专毕业那年,赶上分配制取消了,工作要考。胡古月问,考得上?葡萄咬着下唇,说,嗯。胡古月说,考不上咋办?葡萄想了想,说,嗯。一旁的李副叹气,说,也是赶上了,是命。葡萄说,嗯。李副对胡古月说,都是你害的。胡古月不说话,葡萄说,嗯。
葡萄连考带跑两年,把胡古月和李副的棺材本搭进去了一小半,也没个眉目,就出去打工。先去深圳,在电子厂干了两年,又去北京,在饭店干了两年,就结婚了。葡萄头婚嫁给河北人,生了个儿,一年后离婚,把小孩留老家,给胡古月和李副带。外孙子叫龙龙,长着跟他爹一样的大鼻头,高眉骨,鲶鱼嘴,胡古月打眼一瞧,说,有龙相,不是一般人。龙龙六岁,番薯暑期回家,带了个充气瓢虫。龙龙拿瓢虫当皮球,拍来拍去。番薯说,不对,不这么玩。那时番薯在南方念技校,学的机械修理,学校周边到处都是河,天热了就跟同学下水游泳,晒得像头黑熊。番薯把龙龙带到河边,说,你看着,说完脱了衣裤,在黛青色的河水里游了几个来回,瓢虫跟在身后,游累了就摁住歇气。
秋后的一个晴天,李副吃罢午饭去外头练广场舞,龙龙举着瓢虫在屋里嗡嗡飞,胡古月在躺椅里晒日头。不冷不热的天,胡古月躺着躺着就迷瞪过去了。醒来时,龙龙不在屋里,瓢虫也不见了。胡古月等到下午,龙龙没回,天上飘起雨来,他披个塑料雨披出门去寻,先从周边寻了一圈,不见人,便越寻越远。后来寻到河滩上,上游正挖沙,河水浑浊,到处都是水潭,却不见瓢虫,也不见龙龙。胡古月突然又看到将军,将军浑身湿漉漉的,独自坐在河边,望着河水出神。胡古月走过去,站在他身后,看到他的铁甲上沾满河泥。将军手握铜剑,在淤泥上划拉,划拉毕了,胡古月去看,是八个隶书的老字:龙腾致雨,露结为霜。胡古月想,这是什么启示呢?想了一宿,没想明白。
第二日,胡古月和李副发动所有亲戚朋友四处寻,寻了三天,还是没寻到,便给葡萄打电话。葡萄二婚,怀着肚子回来,只嘤嘤地哭,哭罢了,指着胡古月和李副说,你们把我给害了。胡古月说,也怪番薯。李副指着胡古月的鼻子,说,你就是个害人的鬼。胡古月红着眼珠,说,葡萄,你说,我害你了?葡萄不语,仍是哭,断断续续,哭得瘆人。天快亮时,李副拍了拍葡萄的肩,说,莫哭了吧,是儿不死,是财不散。胡古月说,不对,龙腾致雨,露结为霜。李副突然声嘶力竭地对他吼,闭嘴,滚!胡古月愣了半晌,默默收拾几身衣裳,真就滚了。他回到老家狼谷口,在老房子后墙上开门,改出一间铺面,搭个小柜台卖烟酒。半年下来,五条烟卖出去三包,剩下的受了潮,只能自己抽,呛得鼻涕眼泪肆意横流。
雾气浓重,日头像消失了。胡古月骶骨上生了褥疮,鸡蛋大一个,天天嚷着疼。马大力瞅一眼,嘻嘻笑,说,大腿上扎刀子,离死还远呢。说完就用刀子把疮挑了,研一把止疼片撒上去。肉一疼,胡古月脑子就灵醒了,要马大力推他出去走走。外面的雨还在下,说是雨也不确切,那种半雨半雾的东西,是些肉眼难辨的水珠子,在空中荡着,逢人便到处乱钻。胡古月觉得雨雾从他珊瑚绒睡衣的裤脚钻进去,寒气顿时就从肚腹升起来,直冲脑门。
街上人很少,很安静,只有三五结群的白头翁和麻雀在行道树间唧唧喳喳叫。沿老街走到头就是河滩,几台采砂船立在河心,轰隆隆地叫嚣着,从河底淘沙。在河滩边上看了会挖沙,从另一条街往回走,老远就听到喧嚣声。胡古月以为马戏团又来了:一辆篷了顶的卡车,拉一车红男绿女,随便找块空地搭个帐篷,音响一开,几个露肚子的姑娘就上台扭,高跟鞋踢踢踏踏,把木头台阶上的浮土踢飞起来,呛得台下的人咳嗽连连。走近了才弄清楚是办丧,灵堂前搭了舞台,挂着白幡和遗照,写着永垂不朽流芳千古的话。仍旧有几个露肚子的姑娘扭,扭罢了,换个人,唱歌,翻跟头;再换个人,唱歌,扭屁股……小镇里的人不看挖机扒房了,都跑来瞧办丧。马大力也挤进去,大半天才回来,对胡古月说,现在的姑娘可真白啊,比馒头还白。胡古月说,能吃?马大力说,光瞧就解馋,又说,到时候,也给你弄得热热闹闹的。胡古月嘿嘿笑,说,多臊脸啊。
天暗下来,雨又来了,不大。胡古月四下里瞅,没看到将军,倒是看到了李副,也混在那几个姑娘当中,也扭。李副的腰身比那群姑娘粗了两圈,扭得格外卖力,一边扭,一边瞧着胡古月笑。那双眼睛炽热如火,撩得胡古月心里难受。胡古月闭上眼,尽量不去想她,尽量去想将军,但他竟记不起将军的样子来了,只记得一副移动的盔甲,锈迹斑斑,沾满草屑和泥浆。
李副突发脑溢血死去的那年,整理遗物时,胡古月在一份文稿上看到了将军的事迹。那份文稿用毛笔抄写,是工整的蝇头小字,落款是一个叫吴子虚的姓名,成文时间是大宋靖康二年。胡古月借了本文言字典,连蒙带查半个月,总算弄明白了个大概。纸上所述的将军,英武勇猛,是当朝第一勇士。那时天下初定,人心不稳,戎族屡屡进犯。將军设下奇计,把戎族十三万人的军队困在狼谷口,巧破西牛潭大堤,引潭水水淹七军,致戎族死伤惨重。将军以一万人轻而易举歼敌十三万,赢得了天朝数十年的稳定。那是将军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平步青云,紫袍加身,每一根须发上都射出熠熠的光。
将军的一生几乎都耗在与戎族的战斗中。六十七岁那年,将军在狼谷口遇袭,不是偶然,是早有定数。将军年轻时战功赫赫,百战百胜,诸葛丞相被他压着,二十年才等到了出头日。而今将军老了,已不适合带兵打仗,戎族的进犯却又开始了。诸葛丞相向皇帝力荐他挂帅出征。将军略一犹豫,便答应了。两军交锋,未见胜负之际,戎族军队突然不战而走。此时,将军接到诸葛丞相的手令,只有四个字,追而歼之。孤军追出百十里,将军接到丞相的第二道令,还是那四个字,不知是不是信使弄错了。进入狼谷口前,将军已预感不祥,写一封绝命书,差信使带给妻儿。将军在死前看到了丞相的第三道令,这次只有三个字,死亦足。将军死后,谣言四起——他意图投敌,却反被诱杀。谣言和证据一齐摆在皇帝面前,皇帝说,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从此,史书上再查不到半点有关将军的事迹与生平,只知道将军的无头尸葬入将军坟,首级被戎族取下,连同帽盔一齐悬在悬帽咀天坑边的一棵老树上。那些日子,鸦雀盘旋在天坑的上空,将军的头颅被飞扑分食,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头盖骨。再后来,那颗乌黑的头骨坠入天坑,荡然无存,从此世上再无将军,只有那顶帽盔还悬着,日久年深,人就把这地方叫了悬帽咀。这是那份文稿上的所有内容,鬼话连篇,漏洞百出,但胡古月看完后,还是出了一身冷汗。
空气里散发着生蘑菇的味道,被褥湿乎乎又冷冰冰,像一堆烂泥。胡古月一天换三回尿片,裤裆里还是湿得难受。换尿片时,马大力总会弄疼他骶骨上的疮口。疮口一直没长好,嘴巴似的张着。以往,胡古月要骂他,而今虎落平阳,不骂了。顾忌着换尿片子遭罪,一过晌午,胡古月就不喝水了,把棉签弄湿,渴了就沾沾唇,实在难熬时,就把棉头里的水咂干。马大力不落忍,劝他,不急在这一时。胡古月不语。马大力说,差一时不生,差一时不死,天定的。胡古月说,屁。
马大力坐在床边,缓缓点一根烟,塞到胡古月嘴里。胡古月猛吸一口,很苦,很呛,一连串地咳嗽。自打患了病,他没吸过烟,大概已经忘了烟的味道,现在反而不适应。马大力看他一副遭罪的样子,嘿嘿笑。他给自己也点一根,慢慢吸,火光一明一灭,像眨眼。半晌,马大力嘆了口气,说,老了啊,打小我就爱跟着你,而今一辈子到头了。胡古月不语。马大力说,那时候你有枪,打了兔子,就让我和狗一块儿去撵。胡古月笑,马大力也笑,把一口烟喷在胡古月脸上,说,你说,我咋就那么爱跟你呢?胡古月笑,笑得有些僵硬。马大力说,到头了,还是我守着你,你要死了,我总不能也跟着去吧?胡古月不语,眼里泛出泪花花。马大力站起来,说,你欺负了我大半辈子,可我就喜欢给你欺负,现在你不欺负我了,我倒觉着活着没意思。胡古月不语,死死咬着下唇,眼睛翻出一片白。马大力嘤嘤地哭,一拳一拳擂在胡古月胸口,说,你倒是起来啊,你倒是骂我两声啊!胡古月木然躺着,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滚。
后来,马大力拉了灯,把卷帘门闭了,就走了,走时忘了给胡古月换尿片。屋里一片漆黑,胡古月睁着眼,睡不着。他想,人活着,大概就是熬,熬到死,就好了。
往后的几天,胡古月开始犯迷糊,老睡不醒,醒了也睁不开眼,搞不清是活着还是死了。马大力有些慌,都想给葡萄和番薯打电话了,硬生生煎熬了两日,胡古月又醒了。胡古月已经有日子没看到将军了,却总看到李副。李副坐在床边,笑眯眯地看他,有时还撩起被子往里看,似要坐上来。胡古月暗自好笑,自打生下番薯,李副就和葡萄挤一屋,到死也没和他睡过一张床。那个深夜,胡古月推开虚掩的门,看到李副正用钢笔在白纸上描画儿。画上是一匹骏马,马背上坐着身穿盔甲的将军,李副正犹豫要不要在将军的唇上描几绺髯口。猛一回头,看到胡古月穿着一条大裤衩站在身后,吃了一惊。胡古月嬉皮笑脸,伸手欲揽她的肩。李副一躲,再一戳,笔尖就扎在胡古月手背上,顿时渗出个血珠子来。李副喘着粗气,指了指门,说,出去。胡古月捂着手,不语,也不动。半晌,胡古月突然扯过桌上的画纸,撕了个粉碎。此后,直至李副突发脑溢血死去,他再未踏进过她的屋门。手背上被戳出的小洞后来变成了一个麦粒大的黑点,像长了颗新痣。
现在倒好,一切都反过来了。现在是李副坐在床边,又撩头发,又扭屁股,搔首弄姿的。胡古月觉得浑身不自在,想坐起来,竟真坐起来了。他伸了伸手脚,手脚都活泛,似乎没有病过,似乎重新活过来了。屋里异常昏暗,他与李副并排坐着,说,我想晒日头,日头出来没有?李副说,你瞅这天,哪有你的日头晒?胡古月不语,伸手去揽李副的肩,却抓了一把空。
天还是一如既往的阴沉,雨如蛛丝,雾气涎水似的黏重。胡古月嘤嘤地哭,说,十七十八人人爱,老了就把阳坡晒,我老了,连个阳坡也晒不上。李副说,莫怕,你就要死了,死了埋个向阳坡,天天晒日头。胡古月竟破涕为笑,幸灾乐祸似的,说,你已经死了。李副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胡古月说,这篇课文我念过。李副说,不是课文,是一首诗。胡古月说,干湿我都念过。李副叹了口气,半晌,哀怨地说,你把我害了,你是狗。胡古月不语,浑身一软,人又塌在床上,似乎病痛和衰老又一齐来了。
弥留之际,李副一直在他床边守着。有一天,胡古月迷迷瞪瞪地念叨,有日子没看到将军了。李副说,将军?胡古月摆摆手,说,你不懂。李副说,坟里的将军?胡古月不语。李副嘻嘻笑起来,说,那个故事,是我编的。胡古月说,莫瞎说。
李副说,那几年发展旅游,我们县底子薄,资源稀缺,就自己造,造历史,造名人。我三十来岁背了个处分,不服,还想搏一搏,就编了许多故事。将军戎马一生,死在了狼谷口,有噱头,只是证据造得少了,有些人不信。我本该再弄一些战戈和箭镞来佐证,但文物不好弄,费钱,就算了。好在狼谷口经常下雨,悬帽咀上的烟雾终年不散,我说那是将军的怨气所化,人都信了。
胡古月说,莫瞎说。
李副嘻嘻笑起来,说,我编的故事很多,数这个最拿人。
胡古月也跟着嘻嘻笑,说,你说的是你那个将军,我说的是我这个将军,两码子事。
李副不接茬,叹了口气说,只是后来狼谷口的旅游到底没搞起来,我到死还是个副手,你把我害了,你是狗。
胡古月不语,摇头,叹气,过了许久,又嘿嘿地笑出声来,说,我把你害了,我是狗。李副说,你就是狗。胡古月起身,身子骨还像年轻时那样活泛,他打开那只红漆剥落的梨木旧板箱,从箱底摸出一只塑料袋来。胡古月告诉李副,那年月,是他把保险套的尖儿戳了豁儿,生了番薯。说着扯开塑料纸,一堆褪色的保险套散落在地。李副愣怔良久,终于干笑了两声,就消失了,彻底消失了。李副消失后,胡古月才想起来,忘了告诉她,那敌敌畏瓶子里,是他灌的自来水,瓶子他刷洗了几百遍,早有准备的。就在李副彻底消失的同一时刻,马大力拨响了葡萄和番薯的电话,说,这回真不中了,人昏迷了七天,吹喉音了。葡萄说,当真?马大力说,千真万确。番薯说,你可别哄我。马大力说,哄你是狗。
胡古月最后一次看到将军时,已经虚弱得眼皮都抬不动了。他看到了年轻时的将军,面色白嫩,下巴颏上连一根胡须也看不到,白马银盔,长枪在手,万军阵中杀个七进七出,面不改色心不跳。那时太阳很好,照在将军身上,盔甲熠熠放光。白马在无边的绿野上疾驰,将军的红色披风随风飘舞,将军英武逼人。只一眨眼,将军老了,又坐在树下沉思,又拿起火镰打火,欲点燃潮湿的树枝,几缕青烟过后,便绝望地埋下头去。
将军活到六十七岁,而今铠甲上铁锈斑斑,胡古月名义上也到了这个年纪,但他马上就要死了。事实上,他是七十一岁,当初为了参加工作,转户口时虚写了几岁,就改不回来了,没人知道这事。六十七就六十七吧,他已经是个死人了,不计较这些。
胡古月咽最后一口气时,葡萄和番薯赶来了,铜管乐队也赶来了。铜管乐吹吹打打,先是《世上只有妈妈好》,接着是《父亲》,最后是《今天是个好日子》,葡萄和番薯哭得撕心裂肺。
殡仪馆的运尸车停在门外,待胡古月咽气后,化几张倒头纸,人便被送进停尸间,再吹吹打打几天,让露肚子的姑娘们尽情地唱歌扭屁股,让葡萄和番薯哭丧。扭够了哭够了,就把他填进焚化炉里烧,烧得皮肉骨头都不剩,只剩一把灰。
责任编辑 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