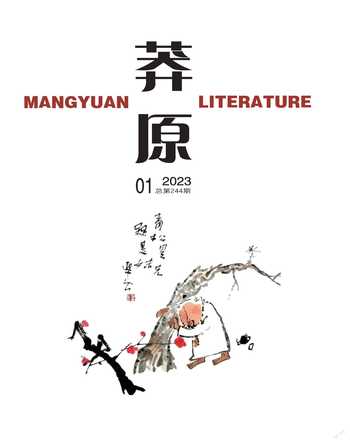从清明到端午
孙希彬
一
天擦亮,顺通就起来了,他要早早把艾草插到门头上。
端午节采艾插艾,老风俗了,为的是驱瘟避邪。采艾有讲究,早不好,晚不好,一定要在端午节到来前两天;插艾也有讲究,一定要在端午这天早上太阳露脸前;顺通更讲究,掐着点儿采艾,头天采,二天插,图个新鲜。
新鲜的艾草摆在石凳上,绿莹莹白茸茸,好大一捆。顺通优中选优,挑拣了枝干粗长叶子宽厚的艾草,走向大门。抽门闩时,他闻到一股子臭味儿,心里就有些疑惑,等拉开大门一看,头“轰”一下炸了:大粪!大门上,门槛上,石阶上,全是黑乎乎、臭烘烘的大粪——天呐,大门被人泼粪了!
“我日……”顺通刚想破口大骂,遽然止住了——被人暗算,奇耻大辱,这样的事情,咋能声张呢?他迅即作出决断:埋住,先埋住。
顺通压低嗓子隔窗叫麦花,麦花出来一看,拍屁股就要跳脚,顺通伸手捂住她嘴巴,低声呵斥:你想让全村人都知道啊?麦花呜呜地说,那咋办?刷洗,赶快刷洗。一边说着,提来水,找来扫帚、铁锨、抹布,夫妻俩手忙脚乱刷洗粪便,连呛脑仁儿的恶臭也顾不得了。清洗着粪便,顺通忽又想起葡萄园,嘴里禁不住冒出一句“葡萄……”听见顺通说“葡萄”,麦花也想起了葡萄园,急声说你赶紧去看看葡萄吧,这儿我弄。顺通叮嘱麦花几句,撒腿往后角门跑。
葡萄园就在宅院后边,打开角门就到了。可角门却打不开。顺通明白了,是有人在外边做了手脚。掉头回来,从大门往外跑。顺通像枪追的兔子一样,从大门奔出,顺街往葡萄园跑。远远的,看见葡萄园了,仍是绿茵茵一片,并无异常;待跑到跟前,弯腰仔细察看,一下子像掉进冰窖里:葡萄树被人从根儿铲断了……他两眼一黑,栽倒在地上……
顺通醒来,躺在医院里。
他急火攻心,导致大脑出血。幸亏送医院及时,除了说话有点不伶俐,左腿走路有点不利索,并无大碍。住院的日子,身体动得少,脑子动得多,反复推想琢磨,试图理清前因后果……
二
祸根,应该是清明儿那天埋下的。
清明儿那天上午,上罢坟,夫妻俩来到葡萄园。活儿还没上手,麦花就打开了话匣子,说早上赶集时碰见一个卦摊儿,顺便算了一卦,先生说了,咱家近日有点小灾,得谨慎些。顺通嗡声说你这是没事找事,有那闲心,还不如看蚂蚁上树哩。麦花说算卦先生的话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顺通嗤了一声,说:真要有命,信是它,不信还是它,你算它干吗?麦花说那不一样,我不跟你抬杠,小心没大差……正说着,三在来了,大老远呢,尖尖的猴腔就先传过来了:
“四叔四婶!忙啊您!”
顺通不耐烦三在,嫌他人懒嘴尖脸皮厚,不愿搭理他,别了脸只管鼓捣葡萄树。麦花心说这鳖儿,明知今儿个清明节,上坟要割刀头肉,怕是赶饭食儿来了。
三在边走边夸葡萄长势好,走近了,瞥见顺通脸色冷,就跟麦花套近乎,说:“四婶呀,我见好多人都去赶集了,您没去?”
麦花说:“人家赶集就赶么,我不买不卖的,赶啥集呀。”
三在嘻嘻笑着说:“四婶调门好低哩,叫我说四婶您得天天去赶集。”
麦花问:“凭啥?”
三在说:“您家瓷实呀。”
“你听哪个放闲屁,说俺家瓷实?”顺通抢过话头,声音嗡嗡响。
“四叔,别人说您家瓷实,是好话不是孬话,这年头,谁富谁光荣么,多少人想瓷实还瓷实不了哩。”三在说着走近顺通,压低嗓门问,“四叔,您家请二冲了吗?”
顺通脖子一梗:“我凭啥请他?”
三在说:“咦,都请了您家不请?连王支书都请了您家不请?”
麦花一旁听见了,勾过头问:“支书真的请了?”
三在说:“那还有假?王支书最先请,接着是村干们,再接着是有头有脸的,排着号呢……”
“听你这么说,我还真请不起哩。我不是村干,也没头没脸,正轮倒轮也轮不着我。”顺通打断三在,又说,“三在呀三在,你干点正经事不中?成天游手好闲,跑这儿叨叨跑那儿叨叨,有意思吗?”
三在讨了个无趣,没法待下去了,说:“四叔四婶您忙吧,我有点事走了啊。”边走边嘟囔,“俺不就想给您提个醒儿嘛,真是的,好心落个驴肝肺,我这是图啥哩?”
看三在走遠了,顺通黑着脸对麦花说:
“这种少脸没皮的货,以后少招惹。”
麦花说:“谁招惹了?人家来咱园里了能不说句话?你不想理他也就罢了,生那么大气干啥呀?”
顺通瞪一眼麦花,说:“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你也不想想,平白无故,他来这儿叨叨二冲干啥?别人请不请二冲,关他屁事?”
麦花看一眼顺通,说:“真要是三在说的那样,人家都请了,咱也别拉下。”
顺通斩钉截铁:“不请。凭啥请他?他一个地痞二溜子,刚从拘留所出来,咱就得请他?有功了他?”
麦花说:“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那二冲是啥人你不知道?书记为啥请他?那么多人又为啥请他?要是人家都请了咱不请,得罪了他,不值。”
顺通说:“别的事都好说,唯这事万万不行。好歹我当过兵去过前线,立功入党,也算经过大阵势,一个地痞出狱了,我给他接风洗尘?我还活不活了?”
麦花嘴一撇说:“再别提你那光荣历史
了,当个村委还叫人挤兑掉,还好意思说。这年头不兴你这一号了,孩子们都不在家,咱俩也上岁数了,安稳过日子就好,别瞎逞强。”
顺通说:“我逞啥强?不请他二冲就是逞强?”
顺通一时烦躁,丢下葡萄树,也不跟麦花打招呼,甩袖子走了。
一开始,顺通并不清楚自己要去哪儿,只是要避开麦花,不想再吵吵了,可等走进大奎家里,才明白,自己是想找大奎说话来了。
大奎正在剁猪草,看见顺通进来了,咧嘴笑笑,说烟在窗台上,自己拿。顺通掏出烟,点上两支,自己叼一支,塞到大奎嘴里一支,然后寻了木凳坐下,看大奎剁草。
村里几千号人,顺通就跟大奎对脾气,有啥话也愿跟大奎说道。年轻时,两人都是好饭量,粮食少,饥一顿饱一顿,熬渴得受不了,听说部队能管饱饭,还有肉吃,两人一商量,一起报名当兵。体检过关了,政审过关了,大奎却突然退出了。顺通几番质问大奎,大奎光笑不说话,气得顺通好长时间不理大奎。后来才知道,不是大奎不愿去,是大队干部不让他去。那年,村里几十个人报名,层层淘选,到最后,剩下三個合格的:顺通、大奎、民兵营长的侄子。三人合格,就俩指标,淘汰谁?民兵营长的侄子自然不能淘汰,大奎退出了,那个名额也就给了顺通。
两人抽上烟,顺通就发牢骚,说这年头真是没路数了,坏人嚣张,好人受气,遇到事了,还真没人给你论公道。大奎光笑不接话。顺通提起三在,说像三在那号人,好吃懒做,少脸没皮,还偷鸡摸狗扒人家墙豁儿,这样的人,咋还能在村子里仰头竖脸呢?又说,还有那个二冲,更邪门,欺男霸女打打杀杀,哪朝哪代都得是镇压对象,现在倒成了人物了……还说起方圆左近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一个骂骂咧咧,一个摇头叹气。
顺通问:“听说那个啥……有不少人请二冲?”
大奎噢了一声。
顺通又问:“听人说,书记也请了?”
大奎又噢了一声。
顺通再问:“有头有脸的轮着请?”
大奎还是噢了一声。
顺通朝地上唾了一口:“这年头,四六不论啦。那你呢?你家请不请?”
大奎笑了笑,说:“我?轮不上。”
“要是轮上了呢?”顺通说。
“轮不上。”大奎说。
“要是轮上了,你请不请?”顺通逼了一句。
“我仨闺女出门俩,剩下一小闺女,也出去打工了,家里就俺老两口,空落落的,要啥没啥,就算我请,人家也不会来。”大奎说,“不过,你可不一样。”
“我咋不一样?”顺通问。
大奎吸了几口烟,说:“你有俩儿子,做生意的做生意,上大学的上大学,宅院盖得又出亮,还种着葡萄园,在村里也算瓷实户,破财消灾。”
顺通从大奎家出来,村里村外转了一大圈儿,回到家里,麦花早擀好了面条捣好了蒜汁,臊子也炒好了,专等他回来面条就下锅。可是今天,顺通端上饭碗,却没一点胃口,搅搅,往嘴里扒几口,再搅搅,像个挑食的小娘儿们。
麦花瞪他一眼,问:“臊子没做好?”
顺通没接腔。
麦花又问:“蒜汁没捣好?”
顺通还是不接腔。
麦花恼了,说:“你这是咋回事?跟谁怄气哩?”
顺通说:“我哪里怄气了?”
麦花说:“不怄气咋这样?”
顺通说:“我啥样?”
麦花说:“啥样你自己知道。爱吃不吃,最看不得你这副样子。”
站起身来,噔噔噔,到院里去了。
不舒坦,真不舒坦,转一大圈,听到的全是不想听的,这让顺通很是闷气。麦花这娘儿们,哪儿都好,就是没眼色,看人不畅快,不说话不中?顺通闷头抽了两支烟,心气稍稍平了,端过海碗,一看,面条已经坨住了。顺通浇进些面汤,搅开了,再吃,味道早已大变,黏蜡一样。胡乱扒拉一通,吃下小半碗,连碗丢在桌上,又把烟点上了。
大门吱呀一响,有人进院来了,听声音又是三在:“四婶您才吃啊?”
只听麦花闷闷地“啊”了一声。
三在又问:“俺四叔哩?”
没听见麦花应声,就听见三在朝屋里来了,边走边喊“四叔”。
三在进屋了,带进来一股酒气。这是个出了名的酒迷瞪儿,没钱买酒,也难得有人请他喝酒,谁家有红白喜事了,他喝蹭酒过瘾。
“四叔,我有事找您呢。中午二冲请我喝酒,他说了件事儿,我吃不准,您帮我拿拿主意……”
顺通冷眼瞥瞥三在,没有接腔。三在酒喝高了,兴致更高,也不看顺通脸色,只管喳喳,喷得五脊六兽。听着听着,顺通听出蹊跷来了——原来不是二冲请三在喝酒,是有人请二冲喝酒,恰好街上碰到三在,顺便捎上了……真是个没脸皮。顺通正想训斥三在,三在说出一件事情来——喝酒的时候,二冲告诉三在,村里要成立治安小分队,二冲当队长,问三在愿不愿参加。
“四叔您说我参加吗?”三在脸红红的,眼也红红的,浑身都在抖动。
三在那副孬模样,分文不值,可“小分队”的信息,顺通不得不重视:村里为啥要成立“小分队”?“小分队”都啥人参加?二冲能当队长?
“四叔!您见过世面,给我拿拿主意,我参加不参加?”三在又问。
顺通明知三在巴不得参加,也知道他不是来请教是来显摆,一肚子不快,说出的话就带了刺:“参加嘛,参加了有酒喝嘛。”
三在一拍大腿,说:“四叔您算说对了。二冲说了,只要跟着他,吃香喝辣。”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来,啪,弹出一支递给顺通,又弹出一支自己叼上,“人家二冲就是气派,出手又大方,喏,一撂,就撂给我一盒。”
顺通没吸三在的烟,点着自己的“喇叭筒”,说:“你那烟太高级了,我享受不了。”
两个人各吸各烟,冷了一会儿,三在忽然把头伸向顺通,说:“四叔,二冲问您忙啥哩,说他回来多天了,好多人都见了,就没见您。”
顺通“哦”了一声。
三在接着说:“我说您这阵儿太忙,得空了要请他哩……”
啪!一声脆响,顺通把一只茶碗摔碎在地上,脸青得吓人,大声吼:“我啥时说过要请他?你为啥瞪眼说瞎话?”
三在吓坏了,结结巴巴说:“我想着、我想着……”
“你想个屁!我凭啥请他?我欠他?不请他还要犯法坐牢不成?”
三在看看眼前阵势,知道大事不好,慌慌张张跑走了。
麦花从院子里回到屋里,弯腰捡拾茶碗碎片,埋怨顺通:“你今儿是咋啦?真吃枪药啦?三在嘴上没门儿,他要是把你的话翻给二冲,可不把他得罪了。”
顺通冲麦花吼:“随便。他就是狗屎,咱不蹅它,还能咋?”
麦花呆了呆,说:“算啦不说啦,咱小心点就是。”
三
这就是清明那天的事,当时的确叫人不舒坦,不过顺通也没往心里放,睡一觉就过去了。
过了几天,村口突然贴出一张告示,上面写道:
根据上级有关精神和广大村民强烈要求,为了打击村匪村霸,加強社会治安,特成立治安小分队。经研究,每人交治安费5元,三日内交齐……
告示引来了不少人,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人说:一人五元,一家就是几十元啊。有人养几只鸡才多少钱?这还得养个小分队了?有人说,想得美,谁弄的小分队谁养,干吗叫老百姓掏钱?有人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就是羊,你不出谁出?有人说:小分队刚成立,就跑快活林吃吃喝喝,原来又瞄住老百姓腰包了……
顺通没有去看告示,看告示的人却聚到顺通家里来了。顺通当过兵、当过村干,正直不怕事,所以,村里人都想听听他的高见。顺通总是比别人有高见,同样一件事,他说出来的,合情合理,还符合政策,不由人不佩服。几年前村里想加收提留款,大伙抗交成功,顺通就起了关键作用,从此成了大家的主心骨。麦花劝顺通别瞎逞能。顺通说这不叫逞能,这是讲政策讨公道。麦花说全村两千多号人,人家都不懂政策不要公道?遇事你往前头站,就你能?顺通说不是我能,可遇事总得有人往前站。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话正应到顺通身上。他听大家说完,想了一会儿,一本正经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事有两点要弄清:第一点,成立小分队,是不是上边的意思?第二点,就算是上边的意思,那治安费呢?上边同意收不同意收?没弄清楚之前,先不要慌着交。大家说对对对,你说得太对了。顺通说成不成立小分队咱没有发言权,掏不掏钱还是咱说了算。自己的钱,你不往外掏,谁还敢抢?
听顺通这么一说,大家一个个表态拥护。大家一拥护,顺通更来劲了,进一步批讲道:中央一直反对乱摊派,小分队真要维护治安,费用也该由村里解决,村里留有机动田,就是应付这些事的。众人纷纷赞同:就是就是,村里留机动田当小金库,还向老百姓乱摊派……
等人们散去后,麦花开始数叨顺通,说议论小分队就议论小分队,说治安费就说治安费,你提机动田干啥?顺通说那是事实,咋不能提?麦花说村干部知道了,又该说你挑腾事。顺通说二十多亩地在那摆着,我不说就没有了?麦花说人家都不说你说,就你能?你以为人家真都不知道?顺通说既然都知道了,我说说有啥错?麦花说知道是一回事,说出来又是一回事,你得管管你这张嘴。顺通说你这老娘儿们,我看你才该管管自己的臭嘴……
两个人吵了一架,一整天谁也不理谁。
三天后,小分队开始挨家挨户收管理费。谁都不想交,都想看看再说。有的说没钱,有的说等等,胆大的还当面指责小分队乱摊派,胆小的干脆家门一锁,躲了出去;只有胆小好说话的,交三块、五块应付。
顺通不躲不藏,就在家等,他早想好了应对的办法。
小分队却没到他家来。第二天也没来,以后几天都没来。
顺通判断,一定是大家的抵制起了作用,小分队收回成命,不再收费了。他由此得出结论:到底邪不压正,只要大家都站出来了,歪门邪道就没有市场了。
治安费没收起来,小分队还是照样拉起来了,十几个年轻人,臂扎红袖标,手提白蜡棍,白天晚上沿街穿巷巡逻,很像回事。顺通心里涌出一股子酸,不过也就那一股子酸,呸了几口就干净了,然后就一门心思去侍弄自己的葡萄园。今年风调雨顺,葡萄长势好,看着葡萄一天一个样,心里满是喜悦。
顺通沉浸在喜悦中,没留意三在啥时来到身后了。
“喊几声您都不应,四叔不想理我了?”三在说。
“啥事?”顺通说。
“没事,我来给您捎信哩。二冲说他要请您喝酒,问你啥时有空。”三在说。
顺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停下手脚,问:“你说啥?”
“人家二冲要请你喝酒,叫你定时间。”三在说。
“二冲要请我喝酒?”顺通盯住三在,问:“他凭啥请我喝酒?”
“这我哪儿知道?他叫我捎信我就捎信,捎信没啥错吧?”三在说。
顺通一时语塞,看了看三在,扭头就走。顺通背手在前边走,三在在屁股后跟,两人一前一后,绕葡萄园转了大半圈儿了,三在憋不住了,高声问:“四叔您说句话啊,我得跟二冲回话哩。”
“你没看我正忙?没眼色。”顺通说着,干脆钻进葡萄丛里,把三在晾在路边儿上。
三在走了,麦花来了。
麦花提着水壶来到顺通跟前,问:“我来时碰见三在,气呼呼的,跟他说话也不理,咋回事?你又日骂他了?”
顺通说:“有口气我还暖暖心哩。”
“没有就好。老了老了脾气得改一改,别总是跟人说话一斧子两镢头的。”麦花说。
“他跑来说二冲要请我喝酒——嘿,笤帚疙瘩戴个帽儿,充成人物了。”顺通道。
“啥?二冲请你喝酒?”麦花一听就急了,开始埋怨,“看看,我说嘛,随大流多好,你不听,这不明摆着,人家给你没趣哩!”
顺通掏出烟点着,道:“我就是觉着不对劲儿,才没有应承他。”
“可这总是个事呀……我看干脆趁坡下驴,请他一回算啦。”麦花说。
“胡说!我说过不请就不请,娘们家哪恁多废话?烦不烦?”顺通又发火了。
日压西山的时候,顺通从葡萄园里出来。摸兜抽烟,发现剩最后一支了,打火燃上,吸着,朝快活林走去。
快活林盘在村口路边,为方圆左近独一家饭馆,主要吃客是村干部,上边来人、村里说事、开会解馋,统统在快活林解决。除了干部,村里有头有脸的,家境富裕的,来了贵客,也到快活林摆排场。虽是独家生意,究竟地处偏僻乡下,生意一直不旺。小分队一组建,情形大变,一伙子年轻人臂戴红袖标穿街走巷吆三喝四,天天都有公干,吃喝招待全在快活林,快活林迅速火爆起来。
杂货店设在快活林的一角,顺通买烟的时候,听见餐厅那边闹闹哄哄,知道村干部又在摆酒场儿了,不愿久留,付过账,赶紧离开。刚走几步,一个声音追了上来:“四叔!”
又是三在!
顺通装作没听见,不扭脸,紧步走。
三在小跑抢到前面,拦住顺通。顺通搭眼一看,很是惊讶——三在还是那个三在,穿着也还是原来穿着,可分明精神了许多。他心里叹道:入官场不入官场真是不一样啊,三在不过给官场当当腿子,啊,给腿子当当腿子,竟就人模狗样了。
“四叔,二冲队长让我过来喊您,今晚有酒场儿,叫您参加哩。”三在说。
顺通那一刹有些茫然,脑子有些转不动了,他想,这个二冲,咋就缠上自己了呢?
看他不言语,三在又说:“去吧四叔,一会儿王支书也过来哩。”
一听“王支书”,顺通一激灵,连连摆手说:“不啦不啦,我还有事……”
说着,甩步就走,任凭三在再喊也不应声了。
四
要说事儿,就是这些了,从清明到端午,除了跟二冲这点龃龉,顺通再也没有和其他人发生过任何纠葛。可是,不请人不吃人请,也算不了啥事啊,咋能惹来这么大的祸呢?
顺通从部队复员回乡,正是赶上农村大发展,他如鱼得水,把几亩责任田拾掇得妥妥帖帖,养了猪,养了牛,小日子眼见着红火起来。接着,又娶了媳妇,当上了村干,差一点就当上支书,在村里也算个人物了。可惜好光景不长,渐渐的,顺通感觉不舒服了——他跟村支书王秀海尿不到一个壶里,主要是看不惯王秀海软塌塌扶不上墙的做派。就说那个二冲,偷鸡摸狗,蛮横霸道,王秀海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二冲请他吃喝,他只管放任自流。顺通给王秀海提过意见,但没用,王秀海太软了,胆小怕事,而且好喝酒,顺通感觉自己没法干下去了,干脆撂挑子。
王秀海比顺通大一岁,个子没顺通高,精明顶顺通仨。俩人从小一起玩,吃亏的总是顺通。只有当兵那次,顺通总算赢了一回。王秀海也想当兵,可他是鸭子脚,体检不过关。顺通复员回乡,王秀海已当上了村支书。顺通在前线立功授奖,是党员,王秀海把他拉进了村委会。顺通为人正派不自私,威信倏倏往上蹿,换届时,就有不少人支持顺通。王秀海当然不想让,就摆了一场酒席请顺通,让村干们作陪。酒过三巡,王秀海开门见山地说,顺通你上过前线,立功授奖见过世面,能力不用说了,像你这样窝在村里亏死了。这个村支书,你也不会看眼里,是不是?你要愿当,直接给我说,我立马让贤,可不能争来争去伤和气。顺通急忙辩解说自己没有这想法。王秀海追问:真没有?顺通表态:真没有。王秀海脸一紧,破口大骂:是哪个乌龟王八蛋造谣,说你要跟我争,你要没这想法,就说句明白话,省得叫那些乌龟王八蛋钻空子……顺通只得连说了好几个没有。就这样,众人都知道顺通不愿当支书了,既然他不愿当,谁还再去得罪王秀海呢?可顺通心里窝囊得很,不知不觉让人牵着鼻子走,走来走去还是走不出人家的手心,再后来,连村干也给弄丢了……
不当干部了,顺通一门心思经营小家庭,他相信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干,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开始几年还不错,粮食高产,猪牛养得好,又弄个葡萄园,收入还算可观。后来形势越来越不妙了,摊派越来越多,化肥、农药越来越贵,种粮食养猪越来越不划算了。乡下养不住人了,人就往城里跑,青年男女都到城里打工去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顺通看出问题严重了,就鼓励儿子们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落户到城里。大儿子不是读书的料,高中没上完就天南海北乱倒腾,三拳两脚下来,居然在城里站住了脚,买房买车,穿西服扎领带,都被人叫成“总”了;小儿子书念得好,被大儿子接到城里,说城里学校正规,他要供弟弟上北大、清华。小儿子果然争气,虽没有进北大、清华,也考上了北京的名牌大学,让顺通很风光了一阵子。小儿子上学走后,大儿子要接顺通老两口到城里去,顺通坚决不去,他可不愿去城里当吃货,想自己和麦花年纪不算老,身体又扎实,只要本分勤俭,会有日子过。
可日子却过得很不顺溜。
牛丢了。牛就在院子里拴着,说丢就丢了。顺通去报案,派出所说这事太多了,不好查;又说破案追查是马后炮,主要还得靠自己好好看管。顺通被噎得半死,发誓不养牛了。
猪又丢了。两头猪,大的百十来斤,小的五六十斤,头天晚上还在圈里呢,一夜起来没有了,消失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顺通不再报案,生了几天闷气,也不再养猪了。
不养牲畜了,除了种地,顺通的精力全都放在了葡萄园里。开始几年,葡萄还真卖钱,后来种葡萄的人越来越多,卖不上价了,一季下来,赚不了几个钱,弄不好还得赔钱。还好,这时候大儿子已经在城里站住脚了,顺通也就不指望葡萄赚钱,侍弄它就图个喜欢、图个踏实。可是,葡萄园咋就叫人给毁了呢?门口还泼了大粪,是谁干的这伤天害理的事呢?顺通把村里人想了一遍,其实也不用多想,除了二冲,不会有别人——二冲从拘留所出来后,别人都请了,只有顺通没请,这就是不给人家面子;再者,二冲成立治安小分队,摊派治安费,又是顺通带头拒绝缴纳,二冲能不怀恨在心?但无论如何,顺通也是当过兵打过仗的,也是有血性的,他打定主意,不管是谁,不管多难,一定要把欺侮自己的王八蛋挖出来。
出院那天,顺通让大儿子直接把他送到葡萄园。
夕阳下,葡萄园叶枯藤干了,一片狼藉。顺通看着眼前的惨状,回想着往日满园勃勃的生机,突然大号起来:嗷呵呵——嗷呵呵——凄厉的含糊不清的嚎叫,让整个葡萄园都颤抖起来……
顺通开始挖罪犯。
當村干时,顺通分管治安,知道路数,就按路数开始挖。他先去村部找支书王秀海。
自打辞掉村干,顺通第一次来村部。王秀海很意外,赶紧让座递烟。顺通落座,却不接烟,直通通提出要挖罪犯,还把事先写好的几页纸递了上去。王秀海看着顺通,满脸同情,嘴里啧啧慨叹:哎嗨,咋弄成这了?哎嗨,咋弄成这了……又把那几页纸看了两眼,为难地摊手摇头,说顺通你也当过干部,应该清楚这种事不好查,很不好查。再说又过去这么些天了……顺通耐着性子听完,说那我去乡里了,起身就走。
顺通来到乡里,找到乡秘书。秘书姓董,老乡干了,与顺通相熟,看着顺通的模样,既同情又惋惜,却也无法满足顺通的要求。但董秘书有水平,说这是刑事案件,应该去派出所。顺通说我知道该去派出所,可我总得先跟乡里打个招呼吧。董秘书笑了,说到底是老村干了,懂路数。
顺通当年管治安的时候,经常跟派出所打交道,熟门熟路,与所长老郑更是熟人。没想到值班的却是一个年轻公安,面生得很。顺通迟疑一会儿,问:“老郑在不在?”
年轻公安看一眼顺通:“你有啥事?”
顺通说:“我来报案。”
年轻公安指指面前的一把凳子,说:“坐下说吧。”
顺通坐到凳子上,顺便又问:“老郑不在?”
年轻公安不高兴了,说:“你是来报案还是找人?”
顺通赶紧说:“报案,报案。”
听顺通啰里啰唆说完案情,年轻公安批讲道:“你这个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只是过去这么多天了,恐怕查起来很困难。”
又责备顺通为啥不早来报案。顺通解释说他气病了,刚刚出院。
顺通把大门上泼大粪、葡萄园被毁的事说了一遍,又问:“啥时去破案?”
年轻公安说:“回去等着吧。”
顺通问:“要等多长时间?”
年轻公安不耐烦了,说:“你这人咋这样子?全乡几十个村,案件一个接一个,派出所就这几个人,大案要案还办不过来哩,总得一个一个办对不对?啥事也得讲个先来后到对不对?”
正不可开交,一个年岁大的公安进来了,顺通一见,带哭腔喊:“老郑……”
熟人就是不一样,老郑劝顺通坐下,还给顺通倒了一杯水,听顺通说了案子,老郑皱眉搓手地说:“门上泼粪是挺气人的,可这属于道德方面,顶多算治安案件,算不上刑事案件。再说粪也叫你给洗刷了,没法查了。毁葡萄园是刑事案件,抓住得判他个鳖孙。可过去天数多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很难破。”
顺通就把自己的猜想说给老郑听。
老郑说:“你这是怀疑,破案不能靠怀疑,得靠证据。”
顺通说:“那该咋弄?”
老郑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先回去,我腾出手就去你们村。”
顺通一把抓住老郑的手,说:“老郑你可快点去啊!”
五
老郑真够意思,没有让顺通久等,隔一天就去村里了。先找村里了解了情况,再把顺通、麦花和几个邻居叫去做了笔录,然后察看现场。同去的除了支书王秀海,还有二冲和几个小分队的红袖标。
来到葡萄园,看着惨不忍睹的现场,老郑忍不住破口大骂:王八蛋!查出来,我收拾死你……骂归骂,毕竟天数太多了,又下过几场雨,作案的痕迹一点儿都没有了,查起来难度太大,或者说根本无法查。老郑问为啥不及时报案,顺通愣怔着答不出话来。王秀海解释说顺通一气就病倒了,一病半个多月,只顾住医院了,哪还顾得报案?老郑说村里呢?村里干啥呢?不是有治安小分队么?
二冲的脸色就阴下来,说:“小分队刚刚成立,业务还不熟悉。”
王秀海也跟着打圆场,说:“就这帮青皮蛋子,哪里会办案件?”
老郑说:“不会办案,报案总会吧?”
王秀海一拍脑袋,连说失职失职;又说我也有责任,只顾抢救病人照顾病人,把报案这事给忽略了。老郑说事情弄到这地步,该咋办?王秀海说案件的事,你说了算。
绕着葡萄园走了一圈儿,老郑严肃地对王秀海说:“根据受害人的陈述,村里、邻居们也都证实,受害人既没有仇人又没与人发生纠纷,搞破坏的人应该是出于嫉妒,这叫仇富心理;现在这样的案件很多,城里乡下都有,以后可要多加防范。”
王秀海听了,频频点头称是。
老郑又说:“根据现场勘查,案件已经难以侦破了,受害人损失惨重,虽然是自己看管不严,但村里发案前防范不力,发案后失职不报,也应负一定责任。”
王秀海愣了一下,随即说是的是的,郑所长说得对,村里有一定责任。
老郑说:“光嘴说负责还不够,得负担相应的经济损失。”
王秀海说是的是的,村里本来就有这方面的义务,无论哪家哪户天灾人祸,该救济救济,该照顾照顾,顺通又是老村干老党员,更应该照顾。
老郑点点头,说:“具体数额嘛,村里研究一下,看能负担多少,拿个意见出来。”
王秀海说:“好好,我们很快就研究。”瞅瞅满脸发紧的顺通,又悄悄拉拉老郑的衣襟,小声道:“郑所长一路辛苦,到村里就马不停蹄办案,连口水都没喝。喏,天不早了,村里安排了便饭,咱先去吃饭,吃着说着。”
一边说,拉起老郑就走。老郑谦让不过,只好顺从。
二冲和几个红袖标尾随其后,一干人奔快活林方向去了。
葡萄园里,剩下呆愣的顺通和麦花,还有几个看热闹的小孩子。
第二天夜里,王秀海亲自登门,向顺通传达了派出所的处理结论:案发时间过久,所有作案痕迹已经消失,案件已无法侦破。看看木呆的顺通和哀伤的麦花,王秀海换口气说:
“考虑到你家损失重大,又考虑到顺通是老党员,曾为村里做过贡献,根据老郑的建议,村里商量了一下,决定除了免去治安费外,再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
顺通有些不解:“治安费?什么治安费?”
“哦,你住院那些天,全村治安費已全部交齐了,只你家没交。这次,给你免了。”王秀海说完,看着两人,问:“你们看——”
麦花叹口气说:“让王支书操心了。”
王秀海松了口气,起身告辞。
顺通却突然大声叫喊:“我不要补偿,我要罪犯!”
六
葡萄园被毁,村里人唏嘘几声,议论几天;郑公安来村破案,村里人议论几天,唏嘘几声;然后呢,该干啥干啥,日子很快恢复常态。在别人看来,葡萄园事件就算过去了。
可顺通过不去。没有挖出罪犯,就是案件还没有破,案件没有破,怎么能说事情过去了呢?顺通为此跟不少人抬杠,还认为所有跟他抬杠的人都有问题——不是水平问题就是立场问题,惹得人家老大不高兴,除了大奎,都不愿再上门了,在街上碰见,也不似往常热乎了。顺通很郁闷。麦花想劝慰顺通,刚一开口,就被顺通喝止:糊涂虫!全是糊涂虫!
顺通拒不接受村里的补偿,也不听麦花、大奎等人的劝说,坚持到派出所索要罪犯。开始,老郑耐心劝说,三番五次,终于不胜其烦,态度由客气变冷淡,最后干脆躲着不见他了。顺通在派出所找不到人,就跑到乡政府找书记、乡长;书记、乡长不在,就向董秘书控告派出所,说派出所不作为。董秘书对顺通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对顺通控告派出所却不以为然,说:人家老郑看老面子,专门跑到村里去破案,还协调村里赔偿部分损失,已经做得很到位了,你应该感谢才是,咋能反过来死缠烂打告派出所呢?又说:你也是老村干、老党员了,应该懂得规矩是吧?顺通眼瞪得溜圆,说我咋不懂规矩?我哪儿不懂规矩?董秘书一看不对劲儿,忙说我这儿还有事,改天再说,对不住了啊。说着,手忙脚乱忙起来,不再理顺通。顺通待了一阵儿,只好怏怏离去。
那天上午,董秘书把杂务处理完,刚在办公桌前坐定,端起泡好的茶,还没喝进嘴里,电话响了。董秘书拿起电话“喂”了一声,脸上的表情倏一下僵了——原来,顺通认为乡里态度消极,跑县里去了。
顺通来到县公安局,说乡派出所的技术不行,连个小案子都破不了;又说派出所不作为,他要告他们。公安局一个女领导接待了顺通,问得倒是详细,一邊问一边记,问毕,让顺通去一边等。顺通很听话,坐在一边,等着女领导给他解决。长等短等,没等到女领导,却等来了董秘书和郑所长。
郑所长自不必说,回到公安局就算回家了;董秘书与公安局打交道多了,也是老熟人,见了女领导笑脸一献,连说:“感谢领导感谢领导,多亏你通知了我们。”
女领导却绷住了脸,对郑所长正色呵斥:“你们工作咋做的?矛盾解决在基层,防患于未然,维稳是首要,你们就这样干工作?”
郑所长经验丰富,知道这时候自己就是个出气筒,训也好骂也好悉听尊便,只要不记录在案,就算成功,要不然给你来个“一票否决”,自己可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女领导脾气发过瘾了,才换副脸说:“算啦,看在你们在基层工作也不容易的份上,这次不记录了,但必须保证此人不再上访。”
董秘书和郑所长都拍胸脯作了保证,点头作揖说友情后补友情候补。告别女领导,二人把顺通架到车上,说声:“快走。”
出了县城,来到一处僻静地方,董秘书让车停下,他掏出香烟,自己叼一支,递给顺通一支,老郑赶忙替顺通点上。吸了几口,董秘书压着嗓子问顺通:“老哥,俺俩没得罪你吧?”
“没有呀?”顺通很奇怪。
“那你为啥害俺俩?”董秘书嗓子高了些。
“我咋害您俩了?”顺通更奇怪了。
“你跑县里上访,还说没害俺俩?”老郑说。
“我不是上访,我是让上边给我破案。”顺通说。“你破不了案子,我让上边给我破,咋就害您俩啦?”
“你跑到公安局告人家老郑的黑状,还说没有?”董秘书质问。
“我知道派出所警力不够,让公安局派人给我破案,咋能算告老郑的黑状?”顺通急得拍大腿。
“哼!”老郑生气地别过脸去。
“老哥呀,案件已经结了你咋还这样?你这不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吗?”董秘书说。
“案件没有了结,罪犯都没抓住,咋能说案件结了?”顺通说。
“给你说多少遍了,这案件根本没法破,你咋恁不清楚哩?”老郑说。
“我给你提供有线索,你不按线索去摸啊。”顺通说。
“你那纯粹是怀疑、是猜测,这种事哪能靠猜测?弄不好人家反诉你诬告,咋办?”老郑说。
“那你说我家门上的大粪就白泼了?我家葡萄园也白毁了?”顺通说。
“没有啊,不是让村里给你补偿了吗?”老郑说。
“我不要补偿,我就要罪犯!”顺通说。
“我靠……”老郑气得鼻子都歪了。
董秘书拉拉老郑,换一副笑脸,对顺通说:“你也是老党员了,也当过干部,咋不知道轻重啊?你这一趟,差点剥了老郑的警服,也差点敲了我的饭碗。我们为你跑腿受累,没吃你没喝你,够意思啦,做人得讲良心吧?”
“我要破案就不讲良心?我要抓罪犯就不讲良心?”顺通大叫起来。
董秘书与老郑互相看看,都不说话了。僵持一会儿,董秘书掐灭烟头,对老郑一努嘴:“走,去村里。”
回到村里,董秘书让顺通在家等消息,自己和老郑一起去了村部。
与上次不同,见到村支书王秀海,老郑劈头一顿猛训,让王秀海猝不及防莫名其妙。看看董秘书,董秘书也一脸铁青,故意不跟他接茬儿。王秀海软是软,可毕竟跟乡里交道打得多了,立刻明白有麻烦了,而且麻烦不小,不然的话以老郑的处世为人,不至于对他这么耍态度,董秘书也不至于冷眼旁观。王秀海转了转脑子,拿出多年练就的招数,小心陪两个乡干周旋。谜底很快揭开了,王秀海松了口气,心想我当啥大不了的事哩,原来是小鸡尿湿柴火——小事嘛。扫一眼两个上级,提嗓子说道:
“要说这事我有一定责任,顺通是我的村民么。可顺通是个大活人,人家到哪儿去是人家的自由,我能管得了?把责任都推给村里,不大合适吧?”
“不是推给你,根本就是你分内的事。”老郑说。
“就因为我是村支书?”王秀海问。
“属地管理你知道不知道?一票否决你知道不知道?他是你村村民,不是你的事,难道是书记乡长的事?”董秘书说。
“我又不指望提拔,一票否决碍我屁事。”王秀海冷笑一声,道,“属地管理么,是有这一说,可一个村该管多少事我心里有数,我胳膊再长,总不能揽到乡里去吧?”
老郑咳了一声,盯住王秀海:“没揪出罪犯算我无能,难道村里就没有责任?”
王秀海反驳:“要说责任么,不能说村里一点没有,忘记报案,错过破案时机,就算你郑所长说得对吧。可现在案件已经在你手里结了,全村人都夸你郑所长处理公道会办案哩,只有顺通本人不接受,他脑子有病了,谁劝都不听,我有啥办法?正好,您俩上级来了,指示指示,村里该咋办?”
董秘书沉吟一下,说:“其他事情还好商量,唯有这事没有余地。你是老支书了,能不知道厉害?一句话——严防死守!”
“村里不是有小分队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该知道咋办。”老郑道。
“有乡里指示,村里才能采取措施。不过,人可不是锅台,看住一个大活人,有难度啊。”王秀海说。
“你就别耍滑头了,这点小事,还能难住你这老狐狸?”董秘书说。
“老哥你就别绕圈了,这事你办妥了,老弟这儿友情后补。”老郑也给王秀海拱手。
王秀海脸上堆出笑来,说:“郑所也别太外气,我一定尽力。又说,两位领导乡里县里两头儿跑,够辛苦了,昨晚刚弄了一条狗,两位不尝尝?”
董秘书、郑所长互相看看,呵呵笑了起来。
七
顺通这么从乡里到县里折腾了大半天,累坏了,回到家往床上一躺,闭眼不说话。
麦花慌了,摇他的胳膊,问:“到底出啥事了?”
顺通胳膊一甩:“你邪乎啥呀?没事。”
“我当你出事了呢,吓死我了……”麦花说。
“你是光想我出事呀?我出事了你高興是不是?”顺通呵斥。
“你咋这样说话?我劝你多少次都不听,你就不能消停消停?我早说过咱近来不顺,你就是不听,非惹出大事来你才安生?”麦花劝说。
“你这娘们,我跑了大半天,又累又饿,你不倒茶递水做饭吃,瞎邪乎啥呀你?”顺通怒道。
麦花这才意识到自己失职了,赶紧倒杯热水放到床头桌子上,再去灶房做饭。
麦花手脚麻利得很,三下五除二就把饭端上了桌。顺通一看,还是蒜面条,眉头一皱:就不会做点儿别的?麦花很委屈,说我想你爱吃这个……那你说想吃啥?我再做去。顺通是心里不痛快,看啥都不想吃,仔细想想,还是蒜面条可口。看着顺通大口吞面条,麦花心里舒展了不少。
顺通挖罪犯,麦花跟着受累。不是身子累,是心累。顺通心一横,不管三七二十一,从乡里跑到了县里,村里人咋议论,他根本听不到,也不会去听,麦花不一样啊,她在家里待着,左邻右舍脚跟脚来家里串门,言来语去的,麦花能听出来些蹊跷。村里人已经开始咂嗑顺通了,说顺通不近人情,人家郑所长帮他,他还告人家;说顺通不知足,村里恁困难还想法补助他,他还嫌少;说顺通只顾自己,孩子们恁孝顺却给孩子们添麻烦……麦花心里很不是味。原本被人害了,大家都同情他们,弄着弄着咋变味了呢?麦花给儿子打电话商量咋办,儿子说你能劝他到城里来,啥都解决了。麦花左想右想想出个计策,决定试试看。
等顺通吃完了,麦花不忙收拾碗筷,坐在一边赔着小心跟顺通说话。她说老大媳妇打来电话,说他俩太忙,孩子照看不过来,叫咱去城里住一段儿,帮他们照看照看孩子。麦花说媳妇打电话而没说是儿子打电话,是想让顺通不好拒绝。
顺通吸着烟,没有接腔。
麦花接着说:“我说等你回来,商量商量……”
顺通猛吸烟,还是不接腔。
“孙子也说想咱了,你看……”麦花又说。
“看啥?不去!”顺通打断了麦花。
“眼下家里也没啥要紧活儿,孩子们忙,孙子又小,咱去替他们照看照看,也是正经理儿嘛。”麦花说。
“要去你去,我自己在家。”顺通说。
“那会中?你不去我能去?”麦花说,“听我一回吧,咱把门一锁,都去,省得在家里心烦。”
“我知道,你们是一心不想叫我再追,不追能中?我被人害了,葡萄园毁了,还往门上泼大粪,就差挖祖坟了,你说说,还有啥比这欺负人?我要是连这都伸脖子咽了,我还有脸活么我!”顺通说。
顺通说话不流利,涎水却流得欢畅。麦花看了,用手里的毛巾去擦。顺通却不领情,一把推开麦花的手,弄得麦花眼圈又红了。顺通看一眼麦花,说以后你就别再瞎喳喳了。你跟孩子们说,叫他们也别再瞎操心。你们说啥都不中,谁说也不中,我非要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不可。顺通说着,把烟蒂塞到脚底下,狠狠地踩。
歇了一宿,一大早起来,顺通感觉精气神不错,打算进城。经过思考,顺通已经明白,乡里不会再管他的事了,派出所也不会再来破案了,他们思想不行技术也不行,就是想把事情糊里糊涂了结算了。顺通当然不能接受,他要去找公安局,找那些思想好技术高的人来破案,替他挖出罪犯。他想这不是难事啊,咋会挖不出来呢?一定能,县里公安局思想境界高,技术水平更高,一定能够破案。
顺通从家里出来,一路想着心事,往村外走。来到十字路口,在路边站了,等待载客的三轮车,快捷又便宜,村子离城不算远,一顿饭工夫就到了。路口那边是快活林,顺通看它不顺眼,宁可离它远一些,就在这边等。
刚刚站定,快活林里突然抢出两个人来,臂扎红袖标,径直向顺通奔来。顺通还没回过神儿,就被红袖标们拉住了,一边叔啊伯啊叫着,一边连拉带架把他往快活林里拖。顺通大嚷大叫,喝骂两个红袖标胆大包天竟敢白天劫人。红袖标也不恼,说让他去喝口茶,吸袋烟,只管往里拖。拖到屋里,三在从里间出来了。
三在一副小头目的做派,命令一个红袖标把屋门关了,才笑嘻嘻地跟顺通说话:
“四叔,一大早,您是往哪儿去呀?”
一见三在,顺通怒不可遏,高声骂黑心狗、白眼狼,竟然敢跟他来这一套。三在也不急不恼,拿一把凳子,让顺通坐。顺通不坐,说:“老子要进城去,没工夫跟你们瞎叨叨。”
“四叔您身体不好,坐下歇歇总该吧?”三在说。
“快让我出去,耽搁了我的事情你负责?”顺通喊。
“那责我负不了,我只负责不让您出村。”三在笑道。
“龟儿子,你这是绑架知道不知道?谁让你干的?谁给你的权力?”顺通喊。
“队长。”三在说,“我是小组长,小组长得听队长的,队长叫干啥干啥,这叫服从命令听指挥。”
“哪个队长?”顺通问。
“四叔您真是糊涂了,谁是队长您都不知道?二冲啊。”三在说。
顺通突然哑了,看着三在发起愣来。
“四叔,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拦住你不让你出村,是二冲的意思,他给我下了死命令,不准你走出村子,我只听二冲的。”三在说。
“二冲是你的队长,可不是我的队长,你听他的,我不听。”顺通说着,又向门口走。“我不回去,我要进城……”
三在赶紧起身挡在门口,说:“不中啊四叔,放你走了,我可该倒霉了。这样吧,我们几个送你回去,把你交给四婶。”
三在说罢,命令几个手下架起顺通就走。
进城受阻,被三在“护送”回家,顺通如同遭受了奇耻大辱。三在算什么东西?居然敢在大白天明目张胆绑架他,还胡说什么是“护送”。这叫什么事啊,蛤蟆老鼠都成精了。
三在不理顺通,俯在麦花耳根儿说了几句话,然后把手一挥,率领手下扬长而去。麦花惶惶地送红袖标们出门,怕顺通往外追,随手把大门从外边插上了。顺通追骂三在,一拉大门,拉不开,大怒,一边骂,一边手脚并用奋力晃门。麦花就在门外,不开门也不吭声,任凭顺通咣当。她了解顺通,没有人在场,他很快就会消停下来。果不其然,晃了几下没反应,顺通就势一出溜,坐在地上呼呼喘粗气去了。
坐在地上,顺通想,你们看我一时,还能看我一世?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哩,不信你们就不眨眼。
但顺通没有想到,他是一个人,二冲手下却有好多人。只要他一出家门,红袖标就跟上了,他走,红袖标也走,他停,红袖标也停,他走到哪儿,红袖标跟到哪儿。顺通不出村,红袖标就只跟不拦,只要顺通往路口一站,准备拦三轮车,红袖标立马冲过来,两个架,一个推,把顺通往村里弄。顺通挣扎,没用,叫骂,也没有用,红袖标只是赔着笑脸把他往村里拉。奇怪的是,拦截顺通的事,二冲一直没有出面,主要是三在领着人干。
走不出村子,顺通当然不会罢休。要想出村,就得避开红袖标,要避开红袖标,就得选择时机。夜里人要睡觉,红袖标也要睡觉,他们总不会夜间也盘在路口吧?只是夜里出村,没有三轮车,只能步行进城……步行就步行,先出村再说。
凌晨三点,整个村子静悄悄的,除了几声狗叫,没有任何动静。顺通走出村子,刚来到通往县城的大道边,王秀海、二冲、三在和两个红袖标就在那里等着他了——原来是麦花告的密。
麦花醒来,一摸身边没有了人,喊了几声,没人回应;起身来找,屋里屋外都找不见。看大门又开着,她一下子慌了,披衣下床,一路小跑把情况报告给了三在。三在安慰麦花,四婶,没事的,你先回去吧,我这就安排人去找。果然就在村口堵住了顺通。
“嘿,中啊四叔,跟我玩战术哩不是?”
一个硬硬的声音,扎进顺通耳朵里,顺通扭脸一看,看到了三在。
“四叔,你才出院不久,身体还没康复,不好好在家休养,三更半夜乱跑个啥?半路发病咋办?不要命了?”三在说。
“我睡不着,想出来散散心,散散步,这也是康复哩……”顺通声音虚虚的,自己听了都觉得不真实。
“装,你就给我装吧。”三在说。“四叔啊,你都一大把年纪了,折腾不起啊。”
三在手一挥,两个红袖标架起顺通就往村里走去……
回到家里,顺通把麦花骂了一顿,麦花赔着笑脸,只是好言相勸,顺通没了脾气,吸着烟,蹲在地上想心思。他想,二冲那样的痞子,他算什么东西?还有三在那样的小混混,也人五人六的了?肯定是王秀海的主意。想到王秀海,顺通麻利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你又往哪儿去?”看见顺通往外走,麦花拽住了他的胳膊。
“找秀海。”
“找他干吗?”
“我去问问,是不是他下的指示。”
麦花知道劝不住顺通,拴了大门,跟在顺通身后,亦步亦趋。
王秀海不在村部,顺通头一扭,去他家找。
王秀海果然在家。见顺通进门,忙叫家人搬凳子倒茶水,还给顺通让烟。顺通不坐,也不接烟,问:“二冲绑架我,你知不知道?”
王秀海说:“顺通兄弟,你先坐嘛,坐下好说话。”按着顺通坐下了,才缓缓说,“老弟啊,你说二冲绑架你,不会吧?二冲刚刚还在我这儿哩。”
“是三在,二冲给三在下了命令,我刚到村口,就被他绑架了。”顺通说。
“老弟,那不是绑架,是劝阻,最多叫拦截。”王秀海说。
顺通原本以为王秀海不会承认知情,没想他回答得很干脆,盘算好的思路就被打乱了。
“我又没犯法,凭啥限制我的自由?”顺通质问。
“你当然没犯法,也没人说你犯法,村里是怕你出去惹乱子啊。你想想,乡里有乡里的工作,县里有县里的工作,领导们各忙各的,你这横插一杠子,知道的你是去办事,不知道的,会说你寻衅滋事呢。”王秀海说。
“我是去县里报案,提供线索揪坏蛋,不是去寻衅滋事。”顺通说。
“这我知道,乡里郑所长、董秘书也知道,可你去县里,人家知道不知道?谁都不认识你,万一产生误会咋办?”王秀海说。
“你这是胡搅蛮缠!”顺通又气又憋屈,脸都涨紫了。
王秀海看看麦花,又看看顺通,说:“老弟你可是明白人,你想想,报案是不是得一级一级报?你已经在乡里报过案了,又要去县里,这不是越级上告吗?县官不如现管,县上能管了你这事?还不是得让乡里管?听我一句劝,把照顾金领了,多少是个意思,安安生生养身体,别再到处跑了,自己劳累不说,别人也跟着劳累,一把岁数了,何苦哩?”
“不中,我要挖罪犯,罪犯挖不出来,我决不罢休!”顺通呼一下站了起来。
王秀海苦笑一下,说:“顺通啊,看在咱从小一起玩的份上,我再劝一句,别为难自己了,也叫村里作难。挖罪犯这事,还是交给乡里郑所长吧。你往县里一报,上边咋看郑所长?轻了说他懒政,不作为,重了说他渎职,叫郑所长背个处分你心里老美?”
见顺通不吭声了,王秀海又对麦花说:
“顺通糊涂你可别糊涂,看紧点儿,别叫他乱跑啦,万一出啥漏子了,村里可替他包不了。”
麦花客套几句,赶紧拉上顺通告辞。
八
那天以后,顺通像变了个人,不发脾气了,也不出大门了,就是坐,一个人静静地坐。麦花害怕他憋出大病,故意跟他逗弄,说大儿子、小儿子的事,说孙子的事,顺通倒也有来有往地应着,看起来都正常。顺通安生了,麦花心里一下子宽展了,说话脸上有了笑,连睡觉都踏实了,还专门给儿子打电话报喜讯呢。
麦花哪里知道顺通心里的憋屈,人家那么欺侮他,他却没有一点办法。也不是没办法,他去县里找公安局破案就是办法;可是,王秀海的一番话让顺通犹豫了——万一真因为他,让董秘书、郑所长背了处分甚至丢了公职,那他下半生就没法做人了。跟董秘书、郑所长的公职相比,他顺通的脸面算不了什么,那二亩葡萄园更算不了什么。可顺通还是咽不下那口气,他在集中精力思考下一步的行动哩。大路不通,只能走小路,反正不能就这么结局。顺通首先想到的,就是以牙还牙,你往我大门上泼粪我也往你大门上泼粪,你把我的葡萄园毁了我也把你的葡萄园毁了。又一思考,不行!大门上泼粪,毁葡萄园,太下作,不是正人君子干的事。自己是老党员了,这么下作的事不能干。想来想去没有好法子,正发愁,一只硕大的老鼠从墙根儿窜过,提醒了顺通——往人家大门上泼粪,毁人家葡萄园,正是鼠类才干的事,用老鼠药治鼠类,正好……
主意有了,实施起来,才知道并不简单。老鼠药不难弄,快活林就有卖。但顺通知道他不能在快活林买。到村外买,自己不能出村,也没法买。那就等,等着货郎进村。以前的货郎是杂货挑,现在是杂货车,卖的杂货五花八门,也有老鼠药。当然,也有专卖老鼠药的,边走边喊“老鼠药,老鼠药,老鼠夹子老鼠胶……”等了半个月,顺通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老鼠药,卖老鼠药的问顺通要不要老鼠夹子老鼠胶,顺通摇头,说老鼠太大,老鼠夹子老鼠胶治不住,卖老鼠药的说那你得多买几包,顺通一下就买了十包。
有了老鼠药,下一步就是毒杀了。在满村游走的时候,顺通已经把目标、地形勘察得清清楚楚,大街几步小巷几步院子几步,了然于胸。顺通认定,自家大门上的大粪,自家的葡萄园被毁,肯定是二冲干的,二冲从拘留所出来后,村里人都请他喝了酒,就顺通没请;二冲成立小分队摊派治安费,又是顺通不让交——二冲是啥人?天不怕地不怕的地痞呀,能不怀恨在心?能不報复?好吧,你让我蒙羞,让我受损,我要让你付出双倍的代价!
来到二冲家门口时,顺通却犹豫了。二冲家大门敞开,没有压水井,吃水要到邻家压,得手很容易,药投进水桶就行了。可二冲爹娘都是好人,出了名的大好人,要下药,说不定是老两口先被害。这就不对了,下药害好人,那不是丧尽天良吗?再说,就算是二冲泼了大粪、毁了葡萄园,那也罪不该死呀,何况,他毒死了二冲,说不定自己也要赔上性命,为个地痞偿命,划不来。不能毒人,那就毒畜牲吧,二冲家的鸡、猪,都是目标。毒死畜牲,把恶气出了,算扯平!
二冲家的大门敞开着,没有人,猪圈里有一头母猪几只小猪。看看前后,空无人影,正是下药的好时机,只需十来步,进院去,把拌了药的面条扔进猪圈里,就大功告成了。顺通一只脚迈进门槛,还没落地,却像被蝎子蜇了一样又缩了回来。他看见二冲娘从屋里走了出来。二冲娘是瞎子,六十多岁了,本分一辈子,日子过得苦,养了二冲这一个儿子,整天游手好闲不正干,四十大几了,连媳妇都没娶上,老人抱孙子的愿望眼看落空了。喂这一头母猪、一窝猪娃儿,可是一年的开销呢,就这么一把药把母猪弄死了,老人的日子咋过呢?顺通心一紧,脚退了回来,不知不觉,竟然往回走了,等回过神来时,已经看见自家大门了。
回到家里,关上大门,顺通胸腔忽然涌起一股酸水,委屈得想哭。他突然伸出双手,猛砍自己的脸,右手砍右脸,左手砍左脸,一边砍,一边骂自己:“我咋这么无用啊!我咋这么窝囊啊!我咋这么没本事啊!连个畜牲都下不了手,这仇还咋报啊……”
也不知道砍了多少下,砍得累了,脸也砍木了,顺通往地下一蹲,失声痛哭起来……
责任编辑 申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