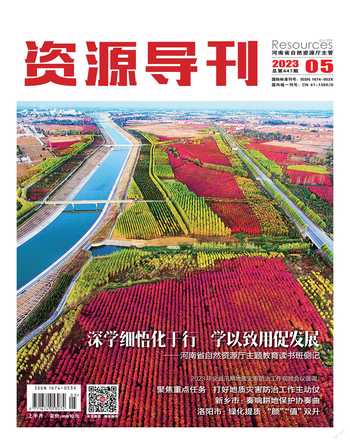重回馆驿村
王邦贤
20多年前,一辆破旧的解放卡车,穿山越岭,将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丢到桐柏山里一个叫馆驿的小山村,就吐着青烟消失在远方的山路上。什么叫寂寞,什么叫孤独,只有在中秋节升起的明月里,在新年的鞭炮声中,才可以触摸到那份忧伤。
20多年后,在桐柏县安棚碱矿遇到一个有着相同经历的朋友,惊叹于同在一个山头居住了两年却未曾相识。我们聊了很久,从草房子到钻机,到馆驿村,再到康老板、黑牡丹、许先生等等,仿佛看见了一个木讷的男生,顶着蓝天白云,对着绿树青山,沿着泥泞山路走来,身上有青紫,但眼光充满坚定。
朋友也很激动,他说一个人名,我就给他讲一段关于他的故事;说一个地方,我就给他讲我对这个地方的认知。讲了很多关于银洞坡、歪头山、围山、河坎的故事,甚至巨马河上有几块垫脚的石块,哪一块是松动的,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
于是,我们相约一起重回馆驿村看看。南阳市桐柏县朱庄镇馆驿村,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豫南重要的矿区勘查驻地,两代地质人在这里接力完成了全国最大的露天金矿——桐柏银洞坡金矿勘探找矿任务。遥想当年,钻机在群山的怀抱里轰鸣,卡车来回穿梭运送物资。山无路,人难行,钻探队员硬是靠着镐头和铁锹修成一条条勘查钻探之路;大绳拉,肩膀扛,喊着号子把一台台钻探设备拉上山。没有人喊苦,没有人喊累,地质工作者朴实无华、无怨无悔的付出,换来的是河南省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城市钢筋水泥铸造的繁华与梦想。
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村庄变迁,馆驿村没有了往日的热闹非凡,剩下的只有残缺的堆浸场地、锈迹斑斑的井台设备,还有那茅草在猎猎的风中张扬,在辣辣的阳光下清晰又闪亮,诉说着过去的辉煌与荣耀。
朋友有些失落。是啊,年轻时梦想出发的地方,现在成了荒地,谁能不伤感?朋友刚参加工作时从事的是地质调查,我是钻探,一勘一探,都在找矿。其实当时的居住条件也不比现在好多少,吃水需要山下担,通讯要靠发报机,出门需要两腿量,物资匮乏,布衣淡饭,但这一切都能用热情来弥补:对生活的热情,对工作的热情,对理想信念的热情。
我的钻探生涯始于20多年前,朱庄外围找矿、大河铜矿勘探,我一次次转换战场。记忆里,沉睡的钻机、钻杆、泥浆泵,还有高耸入云的钻塔,无一不在诉说着尘封的光荣、梦想和哀伤。刚进山的时候,老师傅总是担心我这个外表文弱的城市孩子待不了多久。伴着半箱子行李半箱书的日子里,辗转于一个矿区又一个矿区,城市孩子既没有掉队,也没有喊累,并逐渐成为钻机的顶梁柱。只是将肿胀的肩膀、擦伤的手掌、委屈的眼泪……悄悄地写在日记里。谁没有青涩年华,谁又不是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使劲前行?猛然想起搬家丢失的半箱书籍和笔记,心里还会像针扎般疼痛。
望着钻塔,品味大山的厚重,体会地球造物的神奇,想着对地下未知世界的探索。钻机黑夜里的轰鸣、震颤,神秘而又古怪的岩芯;厚重的地梁,怪模怪样的泥浆泵,钻杆单调的起落、旋转;大大的山蚁蜈蚣和游走的小蛇,以及钻探工人不分昼夜的汗水、欢笑和眼泪,一页一页重现。钻塔下数百上千米的钻杆在地下旋转深入,一节一节,在未知领域探寻矿藏,靠的是地质工作者无人知晓的坚忍、寂寞。
走下山去,田地里的芝麻花開了,一节一节,抽出绿色枝条,开出白色的花朵;坑塘里青青的蒲草,蒹葭苍苍,在水中袅娜着绿色的腰肢,等待伊人的归来。
我与朋友坐在山下国土资源所的院落里,谈了很多过去的事。一代地质人已经老去,嬉笑怒骂,云卷云舒,就像草虫一样,伴着秋雨离去。但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地质人,成为桐柏县天然碱、金、银等矿产资源勘探的动力源;无数人的青春,无数人的热情,成就着祖国工业强国梦。芸芸众生,人海浮沉;繁华都市,滚滚车流,世界五彩缤纷,而地质队员就像山塘里的一朵朵荷花,夜色里静静地开,静静地待,静静地枯萎,吸食着来自地壳深处的营养,吐露出一世芳华。
沉沉夜色,有月光升起,照在国土资源所褪色的顶楼红瓦上。世界依旧这样安静,安静得一如平常。在这样的夜晚中,回忆只剩下富于节奏的呼吸,幸福而舒畅。(作者单位:河南省第五地质勘查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