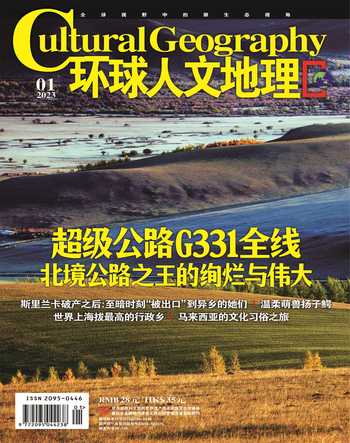斯里兰卡破产之后
史英静



岛国斯里兰卡,这颗“南印度洋上的珍珠”,经历了26年内战,满目疮痍,终于在2009年迎来了和平发展时期。然而,仅仅十年时间过去,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2022年7月6日,斯里兰卡外债突破510亿美元,最终因无法偿付7800万美元的到期债务利息而宣布破产。国内举步维艰的生活处境,导致斯里兰卡婦女们不得不背起行囊远赴中东各国,通过从事家政服务养活家庭,为国家赚取外汇。
“破产”的斯里兰卡一场积患已久的大爆发
2022年7月6日,斯里兰卡破产,对于该国的人们来说,这一天无疑是灰暗的。“国家破产”通常是主权国家由于特定经济原因或其它因素,无法支付到期债务而产生了主权债务危机。可以说,这次破产是斯里兰卡1948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这一天来得如此突然,尽管隐患早已存在。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斯里兰卡国家公共债务就逐年增加。九十年代开始,斯里兰卡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借出的长周期、低利率贷款陆续进入偿付期,斯里兰卡也掉进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尤其是2009年,结束内乱的斯里兰卡,以期通过借取外债开启自己的大建设时期,债台愈发高筑。2015年,斯里兰卡外债翻番增加到439亿美元,2017年增加到501亿美元,2019年底,外债总额更是高达546亿美元,债务占GDP比例远超60%的国际公认安全线。
斯里兰卡为何欠下巨债?
首先是斯里兰卡历来拥有严重贸易逆差,即出口少,进口多,外汇储备空虚。
斯里兰卡长期以茶叶、橡胶、椰子、肉桂、咖啡等农产品出口作为主要经济支柱,随着经济发展,服装制造业、旅游业、海外劳工侨汇也开始如火如荼。然而,斯里兰卡经济基础脆弱、经济结构单一,导致它必然严重依赖进口。小到粮食、纸张、蔬菜、食盐、牛奶,大到农业灌溉、农业电力,以及发展服装加工业需要配套的出口港口码头、用电的能源电网、内部的交通公路等基建,全都需要进口。据统计,斯里兰卡每年进口比出口额多30亿美元,这对于储备外汇相当不利。
斯里兰卡政府外债管理失当,诸多政策判断严重失误,最终推倒了多米诺骨牌,陷入无尽的死亡循环之中。由于在国际社会当“老赖”,许多国家不再愿意与失信的斯里兰卡进行贸易,这进一步压缩了斯里兰卡借债渠道,使它的债务不可持续,境况每况愈下。
逆境中,斯里兰卡企图“自救”。
首先,斯里兰卡政府希望通过减税得人心。 2019年,戈塔巴雅作为总统上台。为了博取民心进行大规模减税,增值税率由15%降至8%,并废除了其它七种税,直接导致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国家购买外汇能力降低,这样的低水平是1948年独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戈塔巴雅还要拿着微薄的财政收入维持社会福利: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粮食补贴等。超低税收,却又中等福利,相当于收1块钱花掉2.4元,斯里兰卡不合时宜地上演了一出“寅吃卯粮”。




其次是发展有机农业,禁止化肥进口。2021年,政府认为生态农业可以节省约2亿美元的外汇,便禁止全国使用进口化肥,农民只能使用有机肥料或者农家肥。到了丰收的季节,这个靠天吃饭的国家,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暴跌,国内粮食危机爆发:水稻产量下降20%,稻米价格却上涨了50%,长期稻米自给自足的斯里兰卡不得不进口4.5亿美元的大米。人们不仅吃不饱饭,甚至以往作为拳头产品出口的茶叶和橡胶也纷纷减产,国家外汇收入直逼历史最低。
风雨飘摇的斯里兰卡屋漏偏逢连夜雨。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横扫世界的新冠疫情和突如其来的俄乌战争。
斯里兰卡旅游业一直是较稳定的外汇来源。2018年,斯里兰卡接待230万外国游客,收入44亿美元,赢得了贸易顺差。然而近年来,斯里兰卡旅游业严重受挫,2020年旅游总收入暴跌至6.82亿美元,同比下降81.1%,2021年继续跌至2.6亿美元,不及2020年前的一个零头。“生态农业”的恶果使政府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不料,赶上了俄乌战争,俄乌冲突致使全球食品和能源價格飙升,斯里兰卡可以买到的药品、食品、能源越来越少,根本无法满足国内之需。
到今年3月底,斯里兰卡外汇储备只剩下可怜的18亿美元,几近枯竭,只能宣布破产。正如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报告所说:该国是“营收不足而消费有余”!
饿殍千里、冲突升级……当最基本的生活受到威胁时
斯里兰卡“破产”,遭殃的还是百姓。
2022年6月开始,斯里兰卡国内从买不起食物,走上了几乎没粮食,没燃油,经济彻底崩溃的“绝路”。 世界粮食计划署数据显示,该国约2200万人口中,逾620万人面临食品短缺,约61%的家庭不得不减少食品消费,其他如药物、燃料、电力供应等都陷入严重短缺。
因为没有电,政府规定关闭全国路灯以省电和省油,居民在晚上停电期间只能静默坐在闷热的黑暗中。33岁的罗希塔是首都科伦坡一座办公大楼的清洁工,这期间他除了清扫楼层、清理下水道,还要负责解救那些因为停电而被困在电梯里的人们。后来,斯里兰卡甚至停止向普通民众出售燃油,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首个“断油”国家。其他燃料,例如百姓们日常生活所需的燃气,价格也迅速飙升。罗希塔一家已经八个月没有使用燃气了。“我们在一个垃圾处理厂收集柴火,在狭小的露天空间里用柴火做饭,”罗希塔诉苦道。
因为没有燃油,政府下令出租车只能一次性加少量的油,致使出租车无法正常营运,部分私营巴士,甚至是火车也已停运,人们出行受到约束。“我必须在这里连续排队四天,才能在第五天领到燃油。”在科伦坡开出租车维持生计的穆罕默德·贾弗里恩说:“即便我获得了燃油,现在也很少有人愿意掏钱乘坐出租车。”有的年轻人站在火车外,紧紧抓住铁栏杆,里面的人则在拥挤的车厢里喘着粗气。斯里兰卡北部的小镇穆莱蒂武的捡鱼工也很无奈,因为没有燃料,渔船无法出海捕鱼,他没有了任何工作。而在另一边,清洁工人罗希塔因为买不起鱼而伤感:“大米、鱼等食品价格也出现了创纪录的飙升。我儿子喜欢吃鱼,但现在我几乎已经买不起了。”更有人因为无法维持生计而带着孩子投河自尽……
斯里兰卡的通货膨胀创下历史新高。




2022年3月,通货膨胀率同期相比提高了21.5%,6月直逼54.6%,食品价格飙升80%,也就是1美元可兑换高达229.99卢比。即使是物资优先供应的首都科伦坡,同样也得面对物价上涨与物资短缺的状况:鸡蛋从250卢比一盒涨到500卢比一盒;卫生纸从800、900卢比涨到2000多卢比一包,价格翻了三倍……人们纷纷减少了食品消费,比以前吃得更少了。政府甚至没有足够的外汇进口纸张,学生们的学期考试被无限推迟。甚至是缺乏医疗设施,医院里的重大手术也被推迟。在阿努拉德普勒,一名被蛇咬伤的16岁男孩的父亲跑遍了城市几乎所有的药店,但由于公立医院的抗毒血清已经用完,这个男孩不幸身亡;一名刚出生两天、患有黄疸的婴儿,在药物不足,且父母没来得及找到交通工具送她去医院的情况下夭折。
走投无路的百姓聚集在街头,开始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者既有底层劳动者,也有老师、律师……很快,抗议活动不断升级,成千上万愤怒的斯里兰卡群众涌入总统府和首相官邸,府邸里平日与外宾合影的台阶上、空中悬廊、花园、会客室里到处充斥着愤怒的民众。他们有人在会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有人在这里吹家里供不起电的空调,然后一把火烧掉了总统的私人住宅。还有大量民众在街头抗议:“我们要求改变,这不是我们应有的生活!”纵然军警不断发射催泪弹和高压水枪,但依旧无法击退愤怒的人群。
斯里兰卡一片狼藉,身处至暗时刻。
妇女们成了外汇主力远赴他乡的她们还好吗?
劳务输出一直是斯里兰卡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和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以往,斯里兰卡的妇女们会去往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从事家政服务赚取收入。数据显示,斯里兰卡每年约有20万人出国务工,女性占40%左右,超过90%的人去往中东,约90%的人从事家政行业。
受疫情影响,2021年斯里兰卡劳动输出外汇收入达2012年以来最低水平。很多女性家政工从中东国家回到了斯里兰卡,直接造成国外家政行业从业者需求增加。这次,在国家破产阴影下的斯里兰卡民众不得不“重操旧业”,一些人正想办法偷渡到印度或澳大利亚谋求生计,更多人则是排起长队申请护照,出国打工。
过去几个月里,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首都科伦坡移民与出入境部大楼被数千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起来,长长的队伍曲折蜿蜒,要花十几分钟才能找到队尾。等待办护照的人们三五成群,靠着花坛边缘和栏杆休息,或铺一块布席地而坐,缓慢地向入口处移動。
36岁的安雅娜也在队伍之列。她从20公里外的卡杜维拉县来到这里,足足等了20小时还未排到号。拿到号之后,她还得再等三四天才能办到护照。2014年,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她从科威特雇主家回到了斯里兰卡。当下的经济危机让她不得不决定再次出国打工,“这八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困难。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我们无法再满足基本的衣食所需。两个孩子在读中学,丈夫也没有稳定工作,我必须挣钱养家。”安娜雅说。
十年前,安娜雅在科威特的工资是每月50第纳尔(当时约180美元),现在,她被中介告知每月最多能拿到150第纳尔(约490美元),相当于17万卢比。这比她在斯里兰卡强太多,在国内辛苦一个月只能挣到几千卢比(约15~28美元)。
与安娜雅情况相似的妇女太多了。她们在国外从事家政的劳务收入被直接存入丈夫的账户,不仅养活了全家人,还要为深陷经济危机的斯里兰卡输入珍贵的外汇。为了增加外汇储备,斯里兰卡政府放宽了对女性出国务工的限制,将最低年龄限制修改为21岁,还给每个打算出国的人发放一本护照。
别无选择的妇女们踏上未知的道路,她们离开了饥饿的斯里兰卡,却依然摆脱不了饥饿,还得同时忍受孤独、寂寞的双重打击。家在斯里兰卡北部基利诺奇小村庄的帕米拉时隔十年再次离开丈夫、孩子,去往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从事家政服务。她离开斯里兰卡时,中介还提前给她丈夫支付了一笔12万卢比预付款。而帕米拉只能靠回家的信念支撑自己去忍耐、坚持。




在雇主家,从清晨一睁眼,她就得一刻不停歇地照顾雇主一家八口人的生活,直到午夜才能睡觉。她的辛苦并没有换来幸运,第二月,雇主就找各种借口不支付工资。帕米拉不得已重新换雇主,但情况也并没好转。新雇主是95岁且患有糖尿病的老太太,虽然工作不算繁重,但帕米拉几乎每天都在饥饿中度过,有时饿极了,她只能等雇主休息后,偷偷给自己做一点吃的,躲在厕所里吃。“我像乞丐一样食不果腹。如果雇主问我,我就说我在上厕所。”帕米拉说。两年合同期满时,帕米拉提出要回家,但是老太太的孩子却扣押着她的护照,要求她照顾老太太直到去世。
为了保护外出的劳工们,斯里兰卡通过国际、区域等多种对话机制来推动移民劳工权利保护机制的建立和实施,还更新了“回流移民”政策。然而回流归来的妇女们也并不幸福,她们会在镇上的制衣厂做缝衣工,除了几十分钟的吃饭、茶歇时间,她们都要一直站在缝纫机前工作,只为换来每月2.3万卢比的微薄收入。
(编辑 邓语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