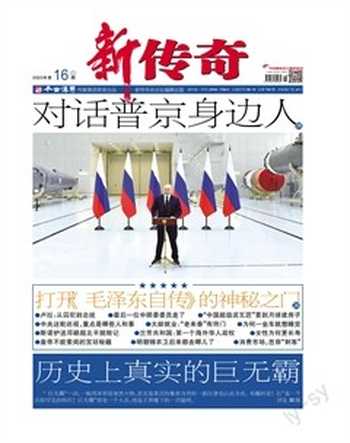如何面对“社会时钟”
有时,我们要学着做“逆社会时钟者”。这不是提倡大家与“社会时钟”对抗,而是不要把自己困在某一赛道或单一的时间维度里,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与社会提供的机遇进行匹配,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社会时钟”一般是指一种由主要生活事件排序而成的规定性时间表,它约束着个体要遵守固定的规范,常听到的“到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就是“社会时钟”的直观体现。
“社会时钟”有明显的时间标尺,当指针指向毕业这个节点时,就业就成了一些人衡量个体有没有跟上节奏的标准。在求职季,毕业生如何面对就业的“社会时钟”?
一直被“社会时钟”推着走
近日,一项有2001名青年参与的调查显示,65.5%的受访青年觉得自己一直被“社会时钟”推着走。
“从高考到上大学,再到读研,一路都挺顺利,现在却在找工作上被‘卡住了。”吳浩是南京某高校应届毕业生,他表示自己曾每一步都合上了“社会时钟”的节拍,但目前临近毕业,还没找到工作,让他有一种“没跟上节奏”的感觉。
在求职最难的时候,吴浩想过要休息一段时间,但面对时常关心的父母,他还是没有勇气停下来。他说,父母是普通工人,家里经济条件一般,“如果我停下来了,就意味着父母要更辛苦”。
00后陈小北也有“时间”上的紧迫感。去年12月,她从英国硕士毕业回国。经历了4个多月的求职,她的目标也在不断调整,从“非大厂不进”到“只要有一定规模、机制比较完善的公司就可以”。她原本计划3月底找到工作,但到目前仍在求职。在就业压力下,她不得不一直往前走。
“同辈比较”是求职者心理压力首要来源
调查显示,“同辈比较,担心落后于他人”是受访者求职心理压力的首要来源。
本科毕业的陈欣玲(化名)表示,近年来,随着硕博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的不断增多,求职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几度面试无果后,她变得很焦虑,“你会发现跟你竞争的人越来越优秀”。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韦庆旺表示,求职是一个考验心态的事情,毕业生要在同辈比较和专注自我之间做好平衡。跳出来看,你与别人不相似的地方也可能是稀缺的品质,稀缺的就是有价值的。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蒋建荣认为,当求职者的就业期待和现实情况存在差距时,如果发现自身竞争力不够,可以适当调整就业期待,先实现就业的目标,在工作岗位上提升自身的能力,再向上发展。
与陈欣玲不同,对于今年毕业的梅刻寒来说,求职中最大的困扰是“不知道想干什么”,所以什么事情都想试一下。每当心中有困惑时,她就会到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帮助。
在韦庆旺看来,求职放大了毕业生在青少年时期就可能存在的问题。家长和学校没有与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会导致孩子产生“习得性无助”(指在经历挫折后,面对问题时产生的无能为力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这需要学校和家长的长期关注。
对于学校的心理教育,韦庆旺建议,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多一点儿服务思维。一方面,提供更多的求职信息资源和求职技巧讲座,提高毕业生的求职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心理咨询工作,帮助毕业生重建自我价值、畅通求助通道,给他们更多安全感。
韦庆旺也建议家长要放下“过来人”的心态,抛开成见,真正地了解孩子、理解孩子、尊重孩子,建立起良性沟通机制,让孩子感受到关心和支持。
有时要做“逆社会时钟者”
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95后应届生张子卿认为,“社会时钟”可以让人在某些时间节点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但也容易把人限定在框内,限制了个人想法和多样性的可能。
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郑小雪一直在研究时间社会学方面的课题。在她看来,社会时钟是一种社会规范,引导个体按照社会规定的时间顺序上学、就业、结婚、生育等。她发现,在按照社会时钟往前走的人群之外,还有一群努力跳出“社会时钟”限制的人,他们自称“逆社会时钟者”。
在经过观察和深入了解后,郑小雪发现,有些选择暂停社会时钟的人会有很明确的目标。他们通过短暂的停歇,去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那些暂停“社会时钟”的人并不会停很久,一般是几个月或者一年左右,他们就会重新找工作。在暂停期间,他们也并不是那么洒脱。因为对个人来说,暂停往往意味着较高的经济成本。
今年考研失利后,95后李玉(化名)开始找工作。她计划如果到4月底还没找到工作,就再考一次研。这段时间,她准备再学学外语,把没有学透的知识点再看看,也想到全国各地转一转。
郑小雪认为,现在不少人会有时间焦虑,很大原因是只认同时间的一种可能性,比如我们经常听到“到某个时间就要做某件事情”“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再不做就晚了”等。当没有达到预期时,一些人就会产生失控感、无力感和不确定感。有时,我们要学着做“逆社会时钟者”。暂停“社会时钟”不是提倡大家与“社会时钟”对抗,而是不要把自己困在某一赛道或单一的时间维度里,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与社会提供的机遇进行匹配,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