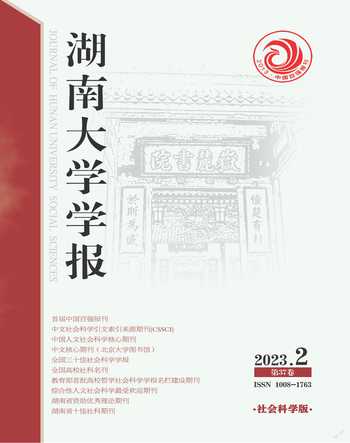继承与创新
[摘要]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形成了以萧公权和吕振羽为代表的两个研究范式。刘泽华在三十多年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以扎实的著作恢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开创了新局面,形成了新范式。他在政治思想史研究突破了以往僵化、教条的阶级分析法,但又并未完全放弃阶级分析,他认为阶级分析依然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刘泽华是从历史学进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后,他一直在努力拓展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领域,提出要加强统治思想的研究、加强社会普遍政治意识的研究和民本思想研究,以此提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属性。
[关键词] 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萧公权;阶级分析;统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 B2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23)02-0117-10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Prof. Liu Zehuas Study o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LIU Fe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732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formed two paradigms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which were embodied by Xiao Gongquan and Lü Zhenyus works. Prof. Liu Zehua resumed the subject in the 1980s and formed a new paradigm by his studies o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He made a breakthrough concerning the rigid research method of the class analysis in his study,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did not discard class analysis completely, believing this is still an effective and significant way to the study. After he published his work, A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Shang Dynasty to 221 BC) in 1984, Prof. Liu continued to extend research fields i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proposing studies of ruling ideology, general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traditional people-based thought, which will improve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Liu Zehua; Xiao Gongquan; class analysis;ruling ideology
一引言
劉泽华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专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三十多年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一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思想史在学界沉寂了三十年之后,刘泽华先生以他扎实的著作恢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开创了新局面。他重新界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并将这些方法贯彻到具体的研究当中。他在特定的时代继承并扬弃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思想史形成的两个范式,无论从思想史的研究来看,还是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来看,刘泽华建立起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的范式。对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无论在具体的观点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刘先生既有突破,又有坚守,他接续了以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
二对萧公权、吕振羽研究范式的
继承与革新
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是近代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如果以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出版为标志,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学科的历史已有上百年。在这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以1949年为界,形成前后两个阶段。在前期,尤其是二三十年代,政治思想、政治哲学的研究一度比较兴盛,出版了多部专著,如谢无量《古代政治思想研究》(1923)、陈安仁《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1932)、李麦麦《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批判》(1933)、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1932—1935)及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等。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解,在这一时期,随着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兴盛,也逐渐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范式。一是以西方政治学为理论参照,同时结合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而成的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另一个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而形成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以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代表。这两个研究范式基本产生于同一时期(吕著出版于1937年,萧著写成于1940年,1945年出版),但由于所参照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不同,这两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代表了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萧著在出版后就被奉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的台湾以及海外学界。吕著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范之作,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学界,吕著以及同类的思想史著作(如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著作)及研究方法一直代表了思想史研究的主流典范,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80年代之后,刘泽华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才有所改变和提升。
刘泽华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从《先秦政治思想史》开始的。就《先秦政治思想史》来说,确实如刘先生自己所言:“我可以自信地说:这一卷是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全面(包括‘人和‘书)、资料最翔实的一部先秦政治思想史。”[1]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之前,历史学家缪凤林在此书的审查报告中曾指出“书中叙述中国思想,只上溯到晚周。唐虞以迄西周,概从删削”[2]127,这固然也体现出缪凤林个人保守的学术立场,但他指出的问题确实应当严肃对待。萧公权当时的回答是由于文献不足征。鉴于三四十年代古史尤其是甲骨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对于殷商时期的历史与思想的研究从略,这个解释可以理解,也是现实可行的。但是对于西周的政治思想,尤其对于《尚书》的思想不加涉及,就是明显的不足,同时也有疑古过头的嫌疑了。刘泽华在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撰写《先秦政治思想史》的时候,疑古过甚的风头已过。更主要的是随着甲骨金文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对商周时期的历史、思想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几十年前的成就。刘泽华自入南开历史系之后,就在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领域学习与教学,还师从著名的古史专家王玉哲学习。这种种因素都使他有能力也有条件在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上溯至商周时期,补足之前研究的这个空缺。
其实,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从原始氏族时代开始讲起的,陶著中的商周部分虽然也利用了甲骨文、金文以及传世文献进行了叙述,但是他的研究太宽泛,商代涉及了氏族制、身份制、婚姻制度、王位继承制度等,思想方面仅涉及宗教祭祀。周代講了周人的历史发展、血缘制度、王位继承制、婚姻制、社会等级制等,思想方面涉及德刑、天人问题。总体来说,陶著更像是商周的历史与社会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的特点不明显。参见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第8-50页。刘先生书中有两章论述了商周时期的政治思想,其中商代的思想主要论述了“余一人”和王权专制思想以及“德”“礼”“民”等几个重要政治概念的出现。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卜辞和相关传世文献。西周的政治思想主要涉及了周公“尊天崇祖、敬德保民”的思想,西周中后期的政治思想,如《吕刑》关于刑的起源与用刑原则的理论、祭公谋父论德与兵、邵公论弥谤、芮良夫论王不可专利、虢文公论民之大事在农、伯阳父论和同等政治思想,以及西周后期讽刺诗的政治意义。这些内容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传世的《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国语》等。而在“三卷本”的先秦卷中,刘先生对于这部分内容又有所深化和系统化。例如对于周公的政治思想,直接以周公的“革命”思想为主题,论述了周公“顺天应人”的革命论、尊祖与伦理政治化以及明德、保民、慎罚的思想。增加了“天子”与专制主义观念一节,论述了西周时期王权神授、天子独尊、天下王有、权力王授的政治思想,这些内容是之前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所没有或涉及很少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刘泽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在不断深化。所依据的材料,除了《尚书》《诗经》等可靠的西周材料之外,也使用了部分金文材料。相较于之前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删掉了商周时期社会概况的介绍,所增加的内容特别突出了政治思想的特色。
刘泽华三十多年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基本是按照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提出的研究方法和体例不断推进的,以历史发展的时代线索为主,具体时段内以列传、流派的研究为主,同时在内容上突出统治思想,以加强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政治的特色。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通史来说,萧著“论及古来学者六十余人,皆就原作取精用宏,就政治学观点分类征引,并加以综合与分析”[3]3。刘泽华主编的三卷本,无论“古来学者”的选取,还是资料的拓展,都远远超过了萧著。这不仅是分量的扩大,更为主要的是内容和议题的延展和加深。刘泽华一面拓展思想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又极力从历史的角度,用历史的方法来增加政治思想史的政治色彩和特色。如在先秦卷中增加了综论性的百家争鸣和诸子政治理性的发展、诸子政治文化总论,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增加了儒家政治观念的经典化与社会意识化、君权的合法性理论与君权调节论等内容,同时又增加了关于谶纬、佛道教、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思想等内容,这样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更加完整,弥补了过去很多没有涉及的内容。又如关于宋代理学的政治思想,萧著对此着墨甚少,仅列有两章,且总体评价不高。其中一章是关于两宋时期的功利思想,主要讨论了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等人,可见他认为李觏等人的思想代表了宋代政治思想的主体。另一章论述了元祐党人及理学的政治思想,其中二程和朱陆仅列有一节。萧公权认为,程朱理学家的政治思想比较接近,“多零碎陈腐”,多为不切实用的高谈阔论,“因袭陈说,无多创见”。[3]490、496刘泽华的三卷本的宋代理学部分虽然在整体上也对理学及理学的政治思想评价不高,认为理学的“主体和内核是一批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过时旧物……是中国自宋明以来长期迟滞不前的主要的精神因素”[4]387,但其所涉及的内容,如理论、人性论、中和论、道统论,以及这些内容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政治价值与政策思想,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远远超过了萧著,在政治思想通史著作中达到了关于宋代理学政治思想的最高的研究水准。
除此之外,三卷本在秦汉以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叙述中有重点地强调了帝王观念与统治思想,这些内容是以往(包括萧著)所没有的,而这又恰好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应有的内容和特点。
另外,在体例方面,刘泽华也是既有承袭,又有创新。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说,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有问题的研究法、时代的研究法和宗派的研究法,而且他在其著作中也基本落实了这些研究的方法,著作的体例也是以此为据的。刘泽华从《先秦政治思想史》开始,基本遵循的也是这样的方法和体例,主要是列传式的研究、流派的研究、社会政治思潮的研究及专题的研究,但同时又作了极大的拓展。以三卷本中的隋唐宋元明清卷中的宋明时期为例,这部分既有统治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潮的研究,如“北宋时期改革政治、强化王权的政治思想”,主要内容是宋初诸帝的改革思想;也有列传式的研究,如范仲淹的改革思想、李觏变通救弊的思想、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南宋的事功思潮和邓牧的异端思想”的标题之下列传式地叙述了陈亮、叶适和邓牧的政治思想。也有流派的研究,如“宋代理学的政治哲学、政治价值和政策思想”,以道论、人性论、中和论与道统论为主要线索,叙述了宋代理学家的政治思想。
由此可以看出,刘泽华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从先秦时期开始无论是纲目的选取还是历史阶段的划分,都是尽量贴近思想本身以及中国历史发展本身。在大的阶段划分上,他既没有采取之前诸如萧公权等人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历程的不同阶段的划分标准,也没有采取历史学研究惯常用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有关社会形态的理论框架。刘泽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序言中就指出,在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按照商代、西周、春秋、战国这样的历史顺序,同时没有给先秦诸子作阶级成分的定性,采取了模糊行事的做法,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史学界对先秦社会性质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其实,古史分期问题直至今日也未解决,甚至学界对“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本身也提出了很多质疑。对于诸子所代表的阶级及给诸子的思想划定阶级属性,同样也难以达成一致的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史学界的这些重大且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刘先生都作了模糊化的处理。
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这几十年的研究状况来看,尽管冯友兰早期将中国哲学史分作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这两个阶段很有意义,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后来的其他学者和研究所接受,甚至冯先生自己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没有再采取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的划分方式,这个划分也只有在学术史的研究中才会被提及。同样,萧公权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按思想演变之大势和思想之历史背景,做了两种划分,现在也只有学术史的意义。这一现象说明,对研究对象作适当的界定,划分阶段、区分流派,在学科草创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学科的形成、研究范式的建立,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当研究持续深入开展之后,每个领域、每个问题、每个时段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之前冯友兰、萧公权等提出的划分阶段这种看法,毕竟主观性太强,难以取得公认。同时,无论是哲学史还是政治思想史,都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史学界对古代历史的分期、对社会形态的定性也有五花八门的看法。再者,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政治思想史本身也是极其复杂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问题一定会溢出既有的阶段、特点等宏观的概括,如果人为地设置一个框架,甚至会有作茧自缚之嫌。总之,出于方方面面的考量,后来出现的思想史、哲学史包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基本上都放弃了给长达几千年的思想发展作划分阶段、区分类型的努力,而是直接以历史发展阶段(朝代)这种客观的标志来划分研究时段。这种做法虽有机械等不够理想的地方,但同时也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议。从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刘泽华就自觉地放弃了前辈学者给思想史断代、划分阶段这种做法,而是直接以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标志性的节点(如朝代)来为研究作划分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是如此,后来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九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也是如此。
三对阶级分析法的坚守与突破
新中国成立之后,学术研究坚持以阶级分析法为指导是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确立相一致的。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阶级分析法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的定义和理解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政治是什么”这个问题的阐发散见于他们的许多论述中,归纳起来主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1)政治是历史范畴;(2)政治是上层建筑;(3)政治与阶级相联系;(4)经济决定政治;(5)政治有反作用;(6)国家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巨大的作用。关于其中的第三条“政治与阶级相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后来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一些教科书和发表的文章中有的就把它作为政治的定义,断言列宁认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5]21-22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历史学尤其是政治史的研究就完全被阶级斗争笼罩了。“文革”期间,阶级斗争在史学研究中又被教条、僵化地利用。这是刘泽华政治思想史研究开始的方法论背景和理论前提。
刘泽华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进入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当时整个学术界都在拨乱反正,清理僵化、教条的理论给学术研究带来的束缚与灾难。在思想史的研究中,首先就是重新反思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
和政治思想史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的是政治,但长期以来政治首先被理解为阶级,这样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受到了阶级理论的束缚。刘泽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再版弁言中指出,此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突破了用阶级理论来定义政治的“铁则”,也就是突破了把政治等同于阶级的框架。其实,在“文革”刚结束,刘泽华就通过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重新评价秦始皇等,在历史研究中试图打破理论的禁区,反思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法,以此从“文革”的桎梏中走出来。
刘泽华冲破“文革”桎梏,主要有名噪一时的三篇文章,即《打碎枷锁解放史学》《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和《论秦始皇的功过是非》。相关内容的简要介绍及影响,也可参见刘泽华:《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第254-267页。尤其是他对历史发展动力提出的某些修正,更是带动了全国史学界的大讨论,成为史学界思想解放的一大标志。刘先生后来说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他“摆脱思维定式的一次尝试”[6]268,是进一步突破与反思的结果。刘先生一直不否认阶级分析法,但他反对政治思想史主要研究阶级理论,给古代的思想家和思想体系机械地划定“阶级成分”这种在史学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僵化现象。他认为政治既有阶级性,同时也有社会性,这就给全面笼罩的阶级理论打开了一个缺口,提供了一个可供反思的契机。刘先生认为,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这部书中实行了“脱帽礼”,把戴在各位头上的“帽子”統统给摘掉了,“这在当时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1]1这样做其实就是把政治思想从阶级定性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
要理解刘先生的“脱帽礼”的学术意义,我们与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关于先秦诸子的研究做一对比。吕振羽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是主西周封建说的,因此他据此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了大致的划分,西周至战国晚期为初期封建制社会,秦统一之后至清代为专制主义封建社会。对于诸子百家,他认为老子思想代表的是没落封建主集团的政治学说,孔子思想是封建主集团的政治学说,墨子思想是农民阶级的政治学说,庄子是没落封建主的政治学说,孟子、荀子思想是没落封建领主的政治学说等。
其实,早在30年代学界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研究中国思想的时候,对于古代思想的阶级属性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如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谭丕谟《宋元明思想史纲》等著作便认为老庄道家是“封建地主阶级和旧贵族代表,主张回复封建初期的西周”,或者是“没落的封建领主阶级与贵族”,而李麦麦的《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批判》一书又认为老子是贫农,庄子为破产贵族,墨子完全代表了有产阶级。叶青认为墨子代表有产阶级,庄子代表了工商业者的革命家。陶希圣认为庄子有辩证法的思想。而蔡尚思则认为,墨子是手工业者、小有产阶级,较接近于无产阶级或农民阶级,许行是农民阶级或无产阶级,老庄道家代表的是流氓无产阶级,儒家代表的是没落的贵族地主阶级,法家代表的是新兴贵族地主阶级。[7]30-39这些观点虽然看法不一,但正如蔡尚思所指出的,很多人应用新观点的同时也有“太呆板、重公式”的教条倾向。[7]39因此,如何灵活、科学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研究中国思想,深入分析思想家及其思想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产生这种表面化的理解,是在史学界一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时候就普遍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成为学术界主导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理论与方法,思想史研究中以唯物唯心“两军对垒”的模式、给思想家与思想体系定阶级属性的做法长期存在,且教条化倾向更加明显。尽管各家划定的具体阶级成分可能有所不同,可是这种教条的、死板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改变。相比较而言,刘先生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的做法是比较大胆和超前的。
阶级分析法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但是由于长期僵化、教条地使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不但在学术研究中造成很多“冤假错案”,而且也束缚了学术研究良性、健康的发展。80年代之后,随着思想的解放,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史学界尤其是思想史的研究中,人们对阶级分析法往往采取了避而不谈、虚搁悬置的态度。人们发现,在学术研究中,不用阶级分析,不做唯物唯心的判断,也能进行研究,而且很多时候似乎还能研究得更好,成果更多,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刘泽华尽管在学术研究中经常显得桀骜不驯,但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他常说“在时下思潮的大变动中,我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仍信奉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仍然是最科学的”。
这是刘先生在他的自述与访谈中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参见刘泽华:《困惑与思索》《我和中国政治思想史》,均收入《刘泽华全集·历史认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2、44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法,尽管他在70年代末期思想界、史学界刚刚开始萌动的时候就试图突破、进行修正,但他并未放弃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法,他依然相信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在思想史研究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只是他不愿被僵化的阶级理论所束缚。同时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他也一直在试图对此继续进行“修正”。
在1999年11月举办的“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刘泽华先生提出“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说。他说:
关于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我依然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所勾勒出的社会关系,从总体上看最贴近历史,或者说解释力最强……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之外还有其他各种社会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说,社会关系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础性的阶级关系,另一类是“社會共同体”,它比阶级关系更复杂,其中既有阶级关系的内容,又超越阶级关系。共同体小到一个家庭,大至民族、国家。基础性的阶级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起着制约作用,但其他社会关系又有其存在的依据,不能全进入阶级关系之中。据此,是否可以设想一种阶级-共同体分析方法?[8]12
在刘先生看来,由于阶级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因此,阶级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中依然有其合理性。他指出:
我并不抛弃阶级分析,不过我也有修正,提出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社会共同体有大有小,小至一个家庭,大至民族与国家,现在又有世界村、国际联合体等。 阶级与共同体互相纠合,高屋建瓴的思想家们一般说来,既立足于一定的阶级,又能关注共同体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说某些思想家是社会良心,无疑有其道理。不过普遍利益也不可能是一律等量的,还有对谁更有利的问题,这就是阶级问题了。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等级、利益集团、阶层、强势、弱势等,其实这些概念的核心应该是阶级。马克思就说过古代是等级的阶级。我们考察、梳理任何思想,都应揭示其具体的历史内容,其中包括处理阶级利益的思想。泛泛说社会良心而避开具体历史内容,就不可避免地要流于空疏。时下对孔子的颂扬铺天盖地,就是缺少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尤其不谈他的思想对谁更有利,这是不符合历史的。阶级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解析社会利益问题,利益问题是人们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基本问题。人们的思想也是围绕着利益转动,到目前为止, 有比阶级分析方法更能深刻解析社会利益问题的方法吗?[9]114
在刘先生看来,阶级分析法在当代中外主流学界依然被广泛地使用。这是因为,只要一个社会中存在阶级,研究这个社会的相关现象就需要相应的分析法。他又指出:“许多学者主张改用考察利益集团的方法来分析政治同题,那么基于共同的经济地位而形成的社会群体,难道不是最常见最重要的利益集团吗?忽视乃至否认这个集团的存在是不可能深刻地认识任何重大政治现象的。阶级分析法的提出是西方学术界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大贡献。这个方法为认识历史,解剖社会提供了一把利器,其合理性内核是颠扑不破的。”[10]85其实,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研究领域,阶级分析法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简单来说,出于对僵化的、教条的阶级分析法的反感与厌恶,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迅速引进当代西方各种新兴理论和方法,其中尤其以韦伯的阶层分析理论最为流行。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阶级分析视角的边缘化,是政治逻辑和学术逻辑双重挤压的结果。从政治逻辑来讲,阶级分析曾经与极‘左意识形态紧密相连,随着政治气候的转变,这样一种历史瓜葛不仅导致阶级分析在政治上失宠,而且成为学术研究的负累。从学术逻辑来讲,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布劳和邓肯的开创性研究,社会分层理论已经发展出一整套适合‘中观社会学的研究概念、命题和方法,而阶级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思辨的社会哲学层面,在实证研究占主流的社会学中不受欢迎自然是不问可知的了。”[11]157理论永远是为现实所引导的,方法也是用来解释现实问题的。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阶级分析法又开始回归,受到学者的重视与运用。
这些现象和分析虽然是以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为主,但是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映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研究状况。刘泽华是70年代末率先走出僵化的阶级分析的理论桎梏的,但他在整体上一直没有否定阶级分析的理论价值,也没有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放弃使用阶级分析法。他后来提出的“共同体”,和社会学中韦伯提出的多元分层(按照经济、声望、政治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层),基本上是相通的。刘泽华晚年一直呼吁在历史研究以及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不能完全放弃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除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坚守之外,也与他对9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逐渐走向“碎片化”,只研究问题、不谈主义的实用主义取向的批评与反思有关。在刘泽华看来,史学研究永远不能限于描述表面现象,而是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于政治思想史来说,这个本质就是思想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只有抓住了这个问题,才算是撑起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龙头”。而在这个方面,阶级分析一直是最有效的理论工具。
四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扩展
刘泽华一生都在南开历史系,他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纳入史学的思想史研究。但同时,刘先生又有极强的政治学意识,在研究中不断突出政治的内容和政治学的特色,这使他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与一般的思想史拉开了距离。除此之外,刘先生还极力拓展研究领域,例如他在80年代就开始倡导政治文化的研究,尤其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不但要借鉴现代政治文化的研究主题,还要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政治社会化过程及中国的政治一体化这三个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必须采用多学科综合性方法,具体来说,要采取诸如整体研究、分层研究、个案研究、过程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12]16-17刘泽华在为他主编的“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写的序中说,政治文化主要研究“政治观念的文化结晶或凝固状态(如政治观念范式与情感信仰,成俗性的政治心理定式,无明确意识的政治行为准则,无须论证的当然前提,公认的政治形式、框架、套套等等);人们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人格和政治心理等等”。
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收有张分田《亦主亦奴——中国古代官僚的社会人格》、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胡学常《文化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张荣明《权力的谎言——中国传统的政治宗教》,由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此序未收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的《刘泽华全集·序跋与回忆》卷。这些看法很有理论性,和现代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行为主义等现代理论是基本相合的。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者早已对行为主义、政治系统等分析框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3]216其实,刘先生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提出的“刚柔组合结构”理论,他研究过的士人与社会、清官问题、谏议问题等,也都属于政治文化的范围。就政治思想史来说,自《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后,刘先生在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三卷本和九卷本中,又特别突出了以下三个问题,以此来凸显政治思想史的“政治”色彩。
(一)统治思想研究
按照阶级斗争的史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史学研究中對于统治阶级是持批判态度的。统治阶级是剥削阶级,是反动的,是革命的对象。但是,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来看,如果不研究统治思想,对于历史上政治之正常运转、政治之变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就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是有重大缺憾的,而且政治思想史也是不完整的。但是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由于理论所限,在这方面基本没有涉及。
其实,在“文革”结束后,刘泽华就开始探索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如何突破阶级划分,打破僵化的理论束缚,使史学研究摆脱现实政治的干扰,走到正常的学术道路上来。当时对历史发展动力的探讨、对战国时期阶层与身份问题的探讨,都属于突破“铁律”的尝试。在此基础之上,刘泽华组织南开大学历史系与云南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于1983年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地主阶级学术讨论会”。正面开会研讨地主阶级,这确实是和以往史学研究中重视具有革命性的奴隶阶级、农民阶级背道而驰的。刘先生后来回忆说:“此时此刻开地主阶级讨论会是很扎眼的事,引起种种猜测,最突出的议论是方向有问题,有为地主阶级翻案的嫌疑。”会上也确实有学者对地主阶级作了一些正面的评价。会后南开历史系的老师们又继续对地主阶级进行了一些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刘泽华和冯尔康主编的论文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版这样的论文集”。[6]252-253
在历史研究中,刘先生率先打破常规,使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不再是批判的对象,而成了研究的对象,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增加了活力。同样他在后来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从三卷本开始,有意识地加强了统治思想的研究与分量。如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就有秦始皇的帝王专制思想、汉武帝的杂霸政治术、君权的合法性理论(如君权合法性与天、圣、道、王的相通;君主称谓与帝王权威的垄断性等)、西汉后期的政治调整思潮、北魏统治集团的治国思想,隋唐宋元明清卷中有隋唐诸帝成熟完善的君道论,宋初诸帝改革体制与强化集权的政治思想,辽、西夏、金的统治思想,耶律楚材的治国思想,明代统治者强化集权、专制的政治思想,清代前期诸帝维护绝对君权的政治思想等。总体上看,这些内容都是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很少提及甚至根本未曾关注的。
刘泽华先生不仅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加强统治思想的分量,而且还对统治思想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明确的理论性认识。他指出:
统治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对现存秩序的基本模式和主要法则做出合理性解释、规范性定义、操作性指导、理想性展示和永恒性论证。统治思想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观念体系,它的核心是政治思想。[10]31
统治思想主要研究最高统治者的政见和政治倾向,统治集团的思想,各种政治习俗、政治惯例的理据,官方学说,统治阶级思想家的思想,占统治地位或影响广泛的社会政治思潮,现行制度与政策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以及社会大中普遍认同的政治观念乃至政治信仰。[10]32-36
即便如此,刘先生到了晚年依然认为,历代统治集团政治思想的研究、统治思想与各种社会思潮关系的研究等,“都还较薄弱,有的甚至还是空白”[10]24。刘先生提出的应加强统治思想的研究,也是后来政治思想史研究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在统治思想当中,中国古代的帝王观念是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刘泽华指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找不到毫不涉及帝王的政治命题。……各种哲学、伦理、教育、经济、法律、军事方面的思想,不仅离不开政治,而且几乎都通过不同途径归结为帝王论。即使‘文以载道观念支配下的文学也大多把君主政治作为自己的关切点。这样一来,与帝王相关的历史现象也就必然成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因为撇开君权、王权、皇权及帝王观念,去总体性地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伦理史、教育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学史等,几乎注定要严重偏离事实。帝王观念或帝王论无疑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10]39具体来说,帝王观念“既包括广大臣民有关帝王的各种认识及相关的心理、情感、态度、信仰等等,又包括历代帝王的自我意识和统治理念。形形色色的帝王论,即各个不同政治学术流派和思想家的有关君主的政治学说、政治思想则是理念化、个性化、典型化的帝王观念。一般来说,在文化上、理论上,界定臣民就是界定帝王,界定帝王就是界定臣民。因此,有关君主政治体系的各种政治学说、政治思想、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都属于帝王观念的范畴”。[10]38
在帝王观念研究中,张分田提出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可谓独树一帜。按照张分田的理解,中国古代帝王论(君主论)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尊君—罪君”的理论结构。除了少数无君论者之外,这个理论结构在历代统治思想及著名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普遍意义。与此相呼应的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中,也广泛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尊君—罪君”的意识—行为模式。这种普遍存在的共时性结构,根植于与君主制度相匹配的社会普遍政治意识,它集中体现着中国古代帝王观念的基本属性和主要特点。[14]1
在张分田看来,所谓“尊君”,就是认同一人治天下、治权在君的政治模式,而且系统地论证王制、帝制以及相应的君道、王道、帝道,具体表现形式有效忠君主、服从君权、崇拜帝王、期盼圣人等。所谓“罪君”,就是批评、非议君主,抨击暴君暴政,甚至指斥君主为罪恶之人,主张革除弊政、剪除无道、推翻暴君,乃至改天换地。在张分田看来,“中国古代社会不仅普遍存在着尊君的理论、观念与行为,而且普遍存在着罪君的理论、观念和行为。”[14]12而且这两种理论、观念与行为并非对立,而是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范式,即“以道义为尺度,将政治认同与政治批判扭结为一体。这就把尊君与罪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特定的政治批判模式”[10]40。
张分田详细阐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帝王观念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是为了说明:在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中,既没有一味鼓吹绝对君权的人,也没有步入民主范畴的人。以尊君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家都在理论上为君权设定了存在条件、活动范围和行为规范,并据此对不合格的君主进行过激烈的抨击。因此,找不到无条件尊崇君权的思想家。以罪君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家,除无君论者外,都认同由一人执掌最高权力的政治制度和圣化的政治权威。他们不仅从来没有提出过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反而在抨击暴君暴政的基础上设计以治权在君为一般法则的、理想化的“圣王之道”。这就无法将他们的理论体系归入民主范畴。由此可见,在尊君与罪君问题上,各种帝王论、各类思想家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所谓绝对君权论者和相对君权论者也仅是比较而言,不能将其绝对化。[14]2
(二)社会普遍政治意识的研究
在史学与思想史的研究中,过去的研究往往偏重政治史、偏重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而忽视了社会史、社会大众以及普遍的民间思想与民间意识等。针对这一偏失,在国外史学思潮的影响之下,在史学研究中,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曾一度非常繁荣,改变了过去学界只重“上面”而忽视“下面”的偏颇。在思想史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传统的政治史、思想史研究中,多强调统治階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统治思想与民间学说、精英思想与大众意识的对立,多重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有学者意识到以往研究的这种局限,因此又提出了要研究以往不太受重视的民众思想、大众意识,或者说要重视“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研究。但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思想史研究中出现的这种新思潮,在问题意识与方法导向方面又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刘泽华及其学术团队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除了加强、突出历代统治思想之外,还特别提出要进行统治思想和民间社会意识互动研究。比起简单的从重视“上面”转向重视“下面”,重点从一头转向另一头,刘泽华提出的“互动”研究更有意义,同时也更有操作性。具体来说,刘泽华提出,在方法上突破以往的过分强调统治思想与民间学说、经典思想与庶民信仰、精英思想与大众心态的简单二分的研究,而是要对此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补充,“补充以和合法”。刘泽华提出的“和合法”就是“在研究方法上把‘从上往下看与‘从下往上看结合起来,多层次、多视角、整体性地考察社会普遍意识发展变化的历史。在对统治思想、经典思想、精英思想、社会思潮、民间信仰和大众心态分别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全社会普遍意识发展史做出深度分析和系统描写”[10]24。这种研究是“将各种民间的精神现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深入剖析这些精神现象的基础上,解读经典思想、精英思想和统治者的思想,进而深化对统治思想、主流文化和全社会普遍意识的认识”[10]24。具体来说,这一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历代统治集团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研究,王权主义与各种社会权威崇拜的关系,官方意识形态与民众社会理想的关系,宗教的社会政治观念与主流文化的关系,钦定的经典思想与大众社会文化符号的关系,统治思想与各种民间社会文化典型的关系。[10]25-30
由此可见,这是将民间社会意识、普遍的政治意识放在与统治思想、精英思想的对照中来进行研究,在这样的对比、互动研究中突出普遍社会政治意识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
(三)民本思想研究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核心议题之一,自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开始,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于不同的学术目的,都特别重视民本思想的研究与开发。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传统文化研究当中,很多研究者,很多对传统持积极态度、同情理解的学者都将民本思想作为与现代民主对接的传统资源,作为传统政治文化当中君主专制的对立面,都对传统的民本思想予以高度评价。
刘泽华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特别重视、探究民本思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关于民本思想的认定方面刘泽华及其学术团队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完全不同,并且在此问题上形成了对立与争议,对民本问题的认识是刘泽华整体学术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这也是刘先生在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阴阳组合结构”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刘泽华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君”“民”都不能独立来界定,思想家、统治者都是通过界定“民”来界定“君”[10]46,“民本”与“君本”是“一物两体”的关系。因此,为了进一步证成王权主义理论,刘泽华及其学术团队都特别重视民本思想的研究与评价,“研究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关系是准确判断民本思想与专制主义的关系的主要途径”[10]47。
在刘泽华的学术团队中,真正对民本思想作了独立、深入研究的是张分田教授。张分田是把民本思想纳入统治思想中来研究的,认为民本思想“始终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中华帝制的政治原理是以民本思想为基础框架而精心构筑的庞大的思想体系”[15]1。这是他对民本思想的基本判定,也是他的最为独特的学术观点。具体来说,张分田认为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价值共识。第二,民本思想来自对政治法则和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它对中华帝制及历代王朝的制度原理、统治方略、施政原则、政治规范及实际操作有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华帝制的政治精神。第三,民本思想不仅以规范君权、制约君权、调整君权、评价君权为主要导向和重要功能,而且包含着若干超时代的政治价值。第四,“君为政本—民为国本”是民本思想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的基础框架。“君为政本”与“民为国本”源于同一理論原点,彼此互依互证,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功能完备、逻辑自足、理论圆融的学说体系。[15]2-3由此可见,张分田对民本和君本关系的理解,基本上是对刘泽华先生阴阳组合结构的具体阐发,也是对阴阳组合结构详细的证明。
张分田对民本思想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最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对于廓清一些关于民本的似是而非的看法,对于如何深入认识儒学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都提出了很多有参考价值的看法。他将民本思想看作是统治思想的一部分,民本与君本互为体用,在很多当代研究者来看来,这一看法好像是贬低了民本思想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其实,张分田对于民本思想有着客观的历史评价。他认为,民本思想中包含有超越时代的政治价值。“这表明,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很不简单,其现实的态度、缜密的构思、周详的规范、精巧的设计和理性的关切,在世界古代史上无人可与之匹敌。在总体上,民本思想所包含的理性成分之多、所体现的批判精神之强、所容许的调整思维之大,都远远超过古代地中海地区一度存在的相当粗糙的‘民主思想。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政治理论体系中,很早就蕴含着许多在现代社会依然适用的政治法则。对于这个历史现象应当给予更客观、更全面、更准确的评价。”[15]2-3张分田对民本思想的历史意义的评价,与刘泽华对王权主义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尽管他们在整体上对古代的专制主义持批评的态度,但这并不排除他们对于王权主义、民本思想在历史上起过的积极作用作明确、充分的肯定。
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综论卷中,刘泽华及其学术团队继续指出要加强民本思想的研究,因为这是政治思想史中全局性的问题。他们指出,除了研究民本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各个重要政治思想流派的民本思想之外,还要研究民本思想与大众政治意识及社会政治批判,民本思想与君主规范和治民方略,民本思想与传统政治哲学,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及民本思想的理论结构与政治功能。[10]48-49这些内容其实张分田在其著作中已经有所涉及,但是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同时也还都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
由以上论述可见,刘泽华在三十多年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开拓新的领域,笔者在这里指出的诸如关于统治思想的研究、社会普遍政治意识的研究以及民本思想的研究这三个方面,其实是一个问题,这几个方面都属于统治思想。因此,加强统治思想研究是刘泽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后一贯的学术方向,他不但对一些专门的问题作了具体的研究,如关于帝王观念、帝王尊号、君主名号的研究,儒家经典中的政治思维与统治思想的研究等,而且还具体地体现在三卷本和九卷本中,以此来加深政治思想史的“政治性”。其实,政治思想史和一般的思想史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其“政治性”,刘泽华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尽量做到了这一点。而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研究与一般的思想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区别。可以说这也正是刘泽华刻意而为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萧公权.问学谏往录[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5]陈荷夫.试论政治及政治学范畴体系[J].政治学研究,2001(1):19-25.
[6]刘泽华.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7]蔡尚思.中国思想研究法[M].上海:中华书局,1948.
[8]刘泽华.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J].历史研究,2000(2):12-14.
[9]刘泽华.理念、价值与思想史研究[J].天津社会科学,2008(3):113-117.
[10]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1]刘剑.阶级分析在中国的式微与回归[J].开放时代,2012(9):151-158.
[12]刘泽华,葛荃,刘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导论[J].天津社会科学,1989(2):12-17+48.
[13]俞可平.中国政治学四十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14]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5]张分田.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DOI:10.16339/j.cnki.hdxbskb.2023.02.016
[收稿日期] 2022-12-26
[作者简介] 刘丰(1972—),男,陕西榆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儒家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