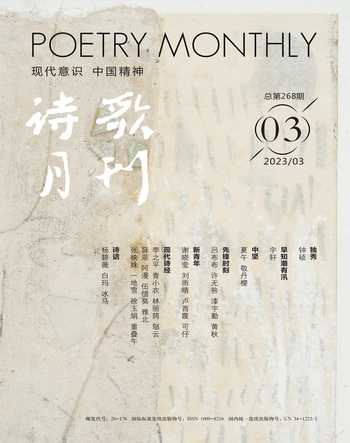小夜曲(组诗)
春日,格言集
先生,你打着口哨去了
(我只是你红砖墙上的鬼影对吗?)
为了触碰你,我早已生长得皮肤龟裂
以踮脚、以伸懒腰、以最奋力的疼痛——
喏,我发芽了!
可我春天的梦里,再也没有童年与你了
因此我一定做着别人的梦,就像
别人早已说尽了我想说的话,可能
也包括这一句
也好,当你翻开那本格言集
每一句都成为我未竟的情意,疏疏密密落晚窗
你煤炉里的烟尘,终于是我了,总有一天
我会是飞鸟掠过花苞后的一丛枯萎
那是我渴望已久的归家(或放逐吧)
更添秋衣
如此朵带泥的鲜花竟依旧地
在文艺里栖身
倚仗露珠折射天空
在荒芜的床榻上,睡衣是被谁纺成的?
绞尽力气也无法回暖的秋呵
只好歌唱一首金色的诗谣
十七摄氏度的字符缓缓流淌
流淌成那件环绕的一衣带水
绣满天高地远无穷碧
可是我自己,用真实纺成了谎言?
在狗尾巴草里烈火焚身
我的悲悯与不可说
我最后的、唯一的救赎
我最后的、唯一的——
非必要的爱
灵魂是非必要的,而必要是健康
于是我知道没有人会在这个黄昏踏进我大敞的门
这个城市够宽阔,以至于我们在街道上寻寻又觅觅、踉踉又跄跄
却无法撞个满怀
飞鱼服是必要的,自在则不然
来来往往的行人都有着必要的理由
譬如,跳广场舞
修剪头发,像修剪一丛绣球花
除了我胆小的情人
笼子外刮着必要的风雪,笼子里关着非必要的爱
爱是非必要的,我被这样教化
每年,人们只有在约定的释放日可以互相拥吻
于是我锁好了抽屉,将日记扔进炉火
我有足够的日记可以度过寒冬
在课上
规则的墙穿过这群少男少女
如同雨穿过睡与醒的间隙
下到公寓里,长出一副瞭望镜
去探听湿漉漉的足音。幻想
你有一双谁也不曾见过的手
抱起隔世的酒瓶,再让汉语赐予我
一柄木头与少许岩浆
让我完成一幅消瘦的隐喻
爱与诚,我已做到二分之一
但要描摹后来那缕青烟,还需要用尽
短则年轻的一生,长则——
望向你如马尾的眼睛
直至在其中,我可以辨認出自己
南门口
我常常想,记忆等同于真实吗?
或者等同于一只草履虫吗?
当我置身于,如此多的
校服之间,如此多的黑白之间……
怀疑是我唯一的出路,对此
你不必怀疑。我被凝固
在一支樟脑味的牙膏里
随着钟摆,摇回一个又一个
被清空的夏天。的士、公共汽车
你的本田车都是这样摇晃的
其他人,红的蓝的绿的彩色的人
也和我们一起摇晃。形同神树
的发丝,拧干我们的水分
它的使命,是控制一个隐忍的尺度——
“务必让他们偶尔痛苦,常常狂喜。”
空气里,全是透明的波浪线
加在任何一个句尾,生活
都会瞬间充满冰冷的沁甜
小夜曲
辨认天空与落叶的颜色,然后
辨认硕大的快乐,是否足以产生自然的睡意
第十个夜晚,依然会惊醒吗?
或许你在担心
没有人愿意替你醒更多的早晨
想到妈妈、黏土娃娃与童年的小板凳
要像一个人类学家
看生活如何浮沉,似喉结
还能因此期望,一封埃斯美的最终来信:
“既有污秽凄苦,也有爱。”
我们都学会一门立命的技艺
不需展览痛苦,只需——
制作蜜桃的天气。将它们挂上梢头
就会有名为“欣欣”的信使,
摇响幸福的曼陀林
刘雨晴,现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曾获“樱花诗赛”二等奖,有作品发表于《诗刊》《南方诗歌》《大学生》《华声文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