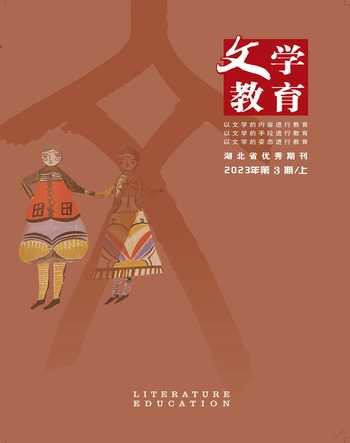鲁迅《药》的数字修辞及其主题意蕴
刘丽星
内容摘要:短篇小说《药》中的出现了187个数字,数字在小说中承担叙事功能,参与文本建构。在环境描写中“一”的重复使用,强化了鲁迅小说特有的绝望的孤独;“一”与人物动作相结合,是对愚昧无知民众的审视;不同数字间的对比,以数字命名人物,则象征着个体与群众联结的断裂。而数字的背后是国民劣根性的解剖,与民族传统中追求“天人合一”的人格结构相悖,渗透着鲁迅悲天悯人的情怀。
关键词:鲁迅 《药》 数字修辞 主题意蕴
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对于鲁迅的各类研究可谓浩瀚如海。但是目前,国内外鲁迅小说的数字叙事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除少量论文外,有分量的学术专著还没有出现,可以说该研究领域至今存在着大量的空白。目前学术界所界定的数字叙事是数字技术进入叙事领域,作为一种在线叙事,具有人机交互的性质,超文本小说、互动影视作品和人工智能写作等是目前数字叙事的主要类型。[1]而笔者这里回归文本内部,数字成为小说的一个叙事元素,用数字讲故事,承担叙事功能,进而参与文本建构。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鲁迅小说与数字研究出現了三种路径。其一,数字与经济。如《经济叙事与鲁迅小说的文本建构》一文中指出“鲁迅小说对经济的书写具体呈现为商品经济意识、相应的经济行为和具体精确的‘数字以及事件与情节的具细处理等等”。[2]其中经济数字对深入研究清末民初中国民间经济生活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其二,数字与叙事。杜贵晨教授在《“三而一成”与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兼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数理批评》中认为,鲁迅小说运用数字最突出的特征是“三而一成”,且存在于它叙述与描写中或明或暗大量运用数字以为度数的总体表现之中,具体体现为:三事话语、三复情节、三变节律、三极建构[3]。除此之外,丰竞在《鲁迅文学作品中数字的修辞分析》中通过对鲁迅小说中数字的拟实、描摹、表演与凸现的修辞分析,进一步探究作品中背后幽默与讽刺风格。其三,数字与文化。如唐帅在《鲁迅小说中的数字观念及其文化蕴涵》注意到鲁迅的《呐喊》与《彷徨》不少作品爱用数字为人物命名,具体分析了《风波》中各类人物后认为“不幸与悲哀以及死亡与哀悼,总和七字系结在一起”[4]。同时通过对《孔乙己》十九文钱的反复出现的分析,组成跳跃结构,揭示数字的文化意蕴。而集中分析《祝福》中祥林嫂的人物形象后,指出“一”背后是孤独心理的刻画,是“国民灵魂”的解剖。除此之外,魏耕原《数字十九实虚反复转化的意义——兼论鲁迅小说中的数字内涵》一文也通过追溯极数十九所经历了实虚反复转化的演变过程,用以分析孔乙己所欠的十九文钱,数字背后是下层知识分子沦为封建制度受害者和牺牲者的悲剧命运。
现有研究以鲁迅小说创作为整体,对数字与小说做了一定分析,提供一个全新的解读视角,但远远不够。除了上述已系统论述过的小说外(《阿Q正传》、《孔乙己》、《风波》、《祝福》等),值得注意的是短篇小说《药》,4523字中就出现了187个数字,其中由“一” 组成的词汇更是高达138组。其中有的数字是固定词组,如“好一会”、“一无所有”、“十世单传”;有的数字和量词结合,作为普通叙事元素,并不具备特殊的意蕴,删掉也不会影响文意,“簇成一个半圆”和“簇成个半圆”,“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和“印成个阳文的‘八字”等可以说并没有差别;但更多的数字,在小说中承担叙事功能,参与文本建构。在渲染环境和人物刻画中“一”的反复使用,赤裸裸袒露鲁迅小说特有的绝望的孤独。在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中渗透着鲁迅的生命体验,充斥着悲悯、绝望乃至恐惧。而不同数字间的对比,以数字命名人物,营造出一种象征的氛围,即启蒙者被被启蒙者所吃,个体与群众之间的联结断裂。而数字的背后是国民劣根性的解剖,与民族传统中追求“万物与我为一”的人格结构相悖,渗透着鲁迅悲天悯人的情怀。
一.数字“一”的重复
唐帅《鲁迅小说中的数字观念及其文化蕴涵》中专门提及“一”字的使用,主要集中对《祝福》中祥林嫂的论述,其认为:“《祝福》中无论是‘一个活物等相关数字‘一的表述,还是‘一件事等相关数字‘一的表述,并非所有的‘一字都带有这种特殊的文化内涵。鲁迅先生惯于将有传统寓意的数字‘一和普通叙事的数字‘一杂糅在一起,形成带有节奏感的数字串,无形中强调人物的孤独和无助。”[5]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祝福》以外,《药》小说共4523字中,由“一”组成的词组就出现了138组。通过文本细读,“一”出现最多的地方有两处,一处与环境相联,另一处则与人物的行为动作结合。从数理学角度来看,“‘一跟名量词(包括某些借用名词、动词作‘量词)结合,可用于写人,刻画情貌、心理、精神、品质等,具有很轻的修辞色彩。”[6]
1.“一”与环境
自然环境描写在文本中主要出现了三处,且这三处都采用了“一”字进行架构,每一处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且看以下三处。(序号为笔者所加)
(A)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
(B)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天气比屋子里冷得多了;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C)他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7]
胡亚敏在《叙事学》中指出“环境是一个时空综合体……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的行动形成一个连续活动体,因此,环境不仅包括空间因素,也包括时间因素。”[8]A处环境出现在开头,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短短一句话展观出观察的过程,月亮、天空逐一出现。电影般的镜头拉长,狭长的一道天浮现,而“一片”相对于删去“一”后更具有整体的空间感。“只剩下片乌蓝的天”可以是华老栓抬头目光所及之处,也可以是刽子手此时此刻所看到的天。而“一片乌蓝的天”体现出某种审视感,这就像电影中的场面调度,镜头广角形成整体。B处空间感仍旧存在,但不同的是从刚开始的空间扩大到华老栓出门走在路上空间聚焦,或者可以说空间缩小,从整体空间到聚焦于当前街道的局部空间。米克·巴尔也在《叙事学导论》中对空间感有相关分析,他认为“形成空间感知中特别包括三种感觉:视觉、听觉和触觉”。[9]视觉上漆黑街道、灰白路、狗遛街;听觉上狗未叫,寂静无声;触觉上,脚踩地,爽快走。这一切正是通过富有节奏感的数字“一”串联其中,使得空间转移得以顺利进行。其中,在触觉上叙述者写到华老栓的脚步轻快,数字串再次出现。叙述者通过“一前一后”的动态过程,与紧接着“老栓倒觉爽快”呼应。人物的心理意识流变过程,悄然发生。可以看到华老栓想到小栓有药可救,脚步不由得轻快起来。C处出现在结尾,环境描写中后半段的三个“一般”是普通叙事,固定搭配。但前半段的三个“一”却有着话语蕴藉,充盈着一种绝望的、无垠的孤独感。而且“一”本身就有“独”、“单”的含义,更是强化了鲁迅小说中特有的孤独和无助。清明坟场,一只乌鸦,一株没有叶子的光秃秃的树,偌大的空间只有两位老人上坟。短短十几个字,简单的白描,画面感极强,仿佛世界在此定格,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启蒙者已死,被启蒙者不自知,何其悲哀!一股沉重的失落感涌上读者的心头,但这绝望中又带有反抗的色彩,树是笔直的,乌鸦是“铁铸一般站着”,给人以希望。这种反抗绝望的意蕴与《秋夜》中开头异曲同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也是枣树。”[10]有学者指出:“阅读者在期待着,期待枣树这样高大挺拔、直刺天空、清醒而又坚强的‘战斗者在秋夜里多多益善。然而,‘也是枣树的结果使这一期待完全落空。”[11]一株枣树的重复牵动着读者的心绪,在阅读的过程中打破心理上既成的思维指向,造成失落感。同时,枣树“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也流露出一种“执拗的反抗绝望的完全性和倔强感”[12]。
2.“一”与人物
读鲁迅的小说常有一种观看戏剧的感觉,若把小说某一段拿去当剧本,甚至不需要修改。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13]可见鲁迅在小说中自觉借鉴戏剧艺术,淡化背景,以“人”为核心推动叙事。
《药》共四节,像是标准的四幕剧。华老栓、康大叔是唱戏者,其他人既是戏中人也是看戏者。《药》中用四个场景叙写了华家的挣扎求生:华老栓夜晚偷偷买药——华小栓服药——茶客们谈药——华大妈清明上坟。前三节通过数字“一”的重复与人物动作在三个断面展开,第四节场景转换来到第二年的清明。第三节到第四节中文本时间几乎为零,故事时间无穷大。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中首次提出了“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的概念,其中当故事的某些事件没有在叙述中出现,便会造成省略。而受戏剧舞台表演的限制,戏剧作品中也相应存在省略。
动作大于语言是戏剧表演的关键,“运用数字在次数和频率上对动作进行规定,使动作有 ‘数可依”[14]。其中《药》中最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华老栓和康大叔。
华老栓出门前“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路过一簇人小心翼翼地“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买完馒头后匆匆忙忙回到家后,满怀希望地“一面整顿了灶火,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在灶里;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店屋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店里人来人往,老栓忙忙碌碌“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尽管“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康大叔讲话时,唯唯诺诺、卑躬屈膝地伺候着“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通过有节奏感的数字串“一”的重复,对人物行为动作的刻画,无形中增加了艺术的真实性,华老栓的一举一动仿佛就在眼前上演,这一点是别的修辞手法无法替代的。鲁迅关注的是病态社会中的病态人生,华老栓不仅仅只是一位为救儿子的普通老父亲,更是国民劣根性根深蒂固的代表,概括了封建末世整整一代贫民的生活命运。作为底层民众,他勤劳、善良、吃苦耐劳,但又有着深信人血馒头能治病的麻木无知、愚昧,自甘被掠夺、被剥削。一切真诚的努力都毫无意义,在他身上,鲁迅倾注了其悲天悯人的情怀。
数字“一”与动作结合的独特手法在康大叔形象塑造中也同样呈现。随着一次怒吼康大叔第一次出场:“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康大叔作为职业刽子手,在出场时读者不知其姓名,而是连着两次写到“黑色的人”。黑色意象本身隐喻着等级地位的尊贵和威严,可以看作是“封建旧势力善用黑色的精神压力效果以此恫吓、威慑被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15]。对当权者的恐惧、卑微使华老栓立刻“缩了一半”。交换时,康大叔“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紧张、密集的动作与数字“一”搭配充满戏剧表演性质,康大叔冷漠、残酷、威严的形象跃然纸上。
二.“一”与其他数字的对比
《药》中数字“一”除了大量出现在主要人物华老栓、康大叔身上外,次要人物描写中也出现了不少数字,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形成个体与庸众的对立。我们可以看以华老栓是“一个人”,“他的两脚,是一前一后的走”;看客是“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革命者夏瑜“家中只有一个老娘”,“榨不出一点油水”,最后只留下“一座坟”。华老栓只关心自己的生活,看客是争先恐后去赏玩苦难,启蒙者是孤身一人的奋战。在鲁迅有意识的设置中,个体与群众之间的联结断裂,这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当时革命党人脱离群众的缺点。
除此之外,在鲁迅的小说中以数字命名人物的情况也有不少。《风波》中有九斤老太、七斤嫂、六斤、赵七爷等;《明天》里有单四嫂子、蓝皮阿五;《离婚》中的八三、庄木三、七大人等。具体到《药》中,这些看客们同样也没有具体名字,驼背五少爷、夏三爷、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等。可以说,他们是看客的集合体,是庸众的代表。五少爷家中排行第五,“少爷”称呼可推知其出生于封建旧大家族,而驼背这一特征正是家道中落的象征。在他的身上明显残留着纨绔子弟的生活习气,“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而二十多岁青年人的存在鲁迅特意点出其大致年龄,背后也别有深意。正处于朝气喷薄、热血的年纪,理应当更快接受新事物,有目标,有理想,对于革命有自己的判断,但他却在茶馆里游手好闲,虚度光阴。当听到夏瑜“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时,则表现出气愤的模样,麻木滑稽,显示出人性的冷漠与残忍。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药》中也出现了两次有关于钱的表述。第一次是华老栓一家准备买药的“一包洋钱”,第二次则出现在康大叔与众人闲聊提及“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一包洋钱”是数字的模糊,具体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包”字我们又可揣摩出分量绝对不少。在《孔乙己》中,“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16],“至于孔乙己所欠的‘十九个钱,则显然借用虚数所蕴含极数的意义”[17],十九文钱是虚数中的大数,压垮了孔乙己最后生存的希望。而华老栓只是开着陈设简陋茶馆,他起早贪黑、勤勤恳恳,这一包洋钱也许是他一生的积蓄。华老栓家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买药的路上谨慎小心,“又在外面按了两下”,“按一按衣袋”等细节描写又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上的困顿与窘迫。而讽刺的是,夏三爷的告密就轻松获得了二十五两白银。在这里,数字不再模糊,而是明晃晃的、雪白的实在之物。夏三爷是夏瑜的亲戚,铜钱到白银的跨越式转变,身边人为了利益不惜出賣革命者,夏瑜最后只剩下“一座坟”就显得无比落寞。
三.数字背后的文化内蕴
“一”是《药》中使用得最多的数字,而“一”的背后更多的是国民劣根性的暴露,这显然与民族传统中追求“万物与我为一”的人格结构相悖。早在春秋时期,《道德经》便蕴含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内核,而《庄子》也有“泰出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行,物得以生,谓之德”。“一”是万物之始,开启了从无到有、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一”是最小的自然数,却又是最大之数。而“医道相同”,中医也循天时之变,追求“天人合一”。在《药》里,“人血馒头”治病法是对“道”的消解,带进了鲁迅对中医的消极感受。鲁迅的一生也和各种疾病纠缠着:童年的牙痛,父亲的病与死,青年时赴日学医,中年以后饱受胃病、肺病的折磨,最后死于肺病。在《父亲的病》中,所谓名医们荒唐的药引“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对”[18]何尝不是“人血馒头”的变形?“一”所隐含的和谐、包容的内核在华老栓身上转为了愚昧落后、麻木冷漠,在康大叔的血红刀子下聚合成凶暴残忍。人血来自治病的“医生”,而华小栓一声声的咳嗽也是饱受病痛折磨鲁迅的切身体验。“人血馒头”治病颠覆着“医/患”关系,用以审视着孱弱的国民。
而“三生万物”背后蕴藉着“天、地、人”三级之道,正如鲁迅在小说叙事中的“三级建构”。[19]《药》中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华老栓,而与之对立的是以暗线形式出现的革命者夏瑜,康大叔、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老头等酒客们,便构成三级,推动故事的发展。其他数字,华老栓的“一包洋钱”与夏三爷告密所得的“二十五两”白银形成强烈的反讽。社会底层农民倾家荡产,在生存的边缘苦苦挣扎。而极端自私的夏三爷,为了保全自己和钱财,亲人的命在他眼里视如草芥。更具普遍性的看客们“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青年的热情,如此而已,看看杀人寻热闹。鲁迅不止一次在作品中提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20]青年尚是如此,他人何尝不是这般无知?鲁迅赤裸裸地控诉封建思想观念对民众身心的戕害,而在这物质和精神极度窘迫的状态下,鲁迅所发出的启蒙之音又如何能够漫延开来。同时文中的人物不配拥有名字,他们是一类人,是“吃人”的民众,更是被吃的对象。至于夏三爷、夏四奶奶这两个人物的年龄排行,细细揣摩也含有言外之意。《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一书中对于数字“四”有这样一番解读:“四”的大写字“肆”却不仅在语音上同“死”有巧合关系,而且在意义上也同“死”的观念有着不解之缘……《说文解字》释“肆”为杀死后陈尸。[21]可见夏四奶奶排行第四,而非第三,隐喻着儿子夏瑜的死。而“三”在《说文解字·三部》中释“三,天、地、人之道也”,夏三爷的无耻告密正是对道的违背。同时,《药》共四节,第四节华小栓、夏瑜已死,而清明上坟所各摆的四碟菜何尝不是对农民、革命者“死”的祭奠。
四.《药》的主题意蕴
鲁迅在谈到《药》的创作意图时曾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谁,却还要因为愚昧的见解,以为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某一私人的福利”。[22]这也可以看做是对《药》主题最直接的概括。《狂人日记》中是“吃人”更多是一种隐喻,而到了《药》中“吃人”成为血淋淋的事实,《示众》中“看 /被看”模式进一步发展为“被吃/吃”模式。
康大叔手起刀落,个人在他的世界里毫无差别,他是人性的野蛮、愚妄残忍的象征。华老栓固执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病,而这人血背后是革命者的牺牲,苦难是底层民众的生活常态,“生”的挣扎要以革命者“死”为代价。他努力求生,只想救救自己的孩子,但这一点合情合理的、微小的希望都得不到满足。在吃人的旧社会,似乎全社会都要从他这样的劳苦大众身上榨取血汗满足自己的欲望。此外,《药》中那些潮一般涌向看杀革命者的人,茶馆里无所事事的看客,他们是精神荒原的流亡者,赏玩着苦难,不自知。花白胡子老头,理应该是年龄大,见识多。而他却处处讨好迎合,称夏瑜为“这个东西”,被打也不可怜;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听到夏瑜被打后反说阿义可怜时,他恍然大悟的说“发了疯了”,其实什么也没有悟到。而夏瑜是小说中塑造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形象,虽在小说中没有过多篇幅的正面描写,但可以看到夏瑜始终存在,即使被捕后也在狱中热忱地宣传革命活动。而他做所的一切努力都毫无疑义,死后成为茶客们闲聊的谈资。他是孤军奋战,他所面对的是专封建制等级制度下制造的、早已麻木的顺民和奴才,夏瑜的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革命者不为群众所理解的悲哀。”[23]
看客的精神实质是自欺欺人、冷漠无知、残忍自私,几千年的封建思想观念、封建伦理道德是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看客形象中蕴含着鲁迅悲悯的情怀和真诚的“立人”使命,鲁迅正是借助“看客”形象显示他彻底的反封建意识和呼唤启蒙的现代性品格。而故事的最后,夏瑜的坟上凭空出现了“一圈红白的花”,乌鸦箭一般向天空飞去,这是对黑暗现实的绝望反抗,给予那些缝隙中苦苦挣扎的人们一丝丝希望。
参考文献
[1][荷]米克·巴尔.叙事学导论[M].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张德鑫.数里乾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孙玉.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4]吴中杰.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5]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吴秀明.多维视野中的百部经典(中国现当代文学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7]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葉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9]杜贵晨.“三而一成”与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兼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数理批评[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02).
[10]丰竞.鲁迅文学作品中数字的修辞分析[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03).
[11]寿永明,邹贤尧.经济叙事与鲁迅小说的文本建构[J].文学评论,2010(04).
[12]孙淑芳.论鲁迅小说中色彩语码的隐喻内涵[J].鲁迅研究月刊,2014(09).
[13]魏耕原.数字十九实虚反复转化的意义——兼论鲁迅小说中的数字内涵[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02)
[14]唐帅.鲁迅小说中的数字观念及其文化蕴涵[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5).
[15]胡亚敏.数字时代的叙事学重构[J].江西社会科学,2022,42(01).
注 释
[1]胡亚敏:《数字时代的叙事学重构》,《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2]寿永明、邹贤尧:《经济叙事与鲁迅小说的文本建构》,《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3]杜贵晨:《“三而一成”与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兼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数理批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4]唐帥:《鲁迅小说中的数字观念及其文化蕴涵》,《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05期。
[5]唐帅:《鲁迅小说中的数字观念及其文化蕴涵》,《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05期。
[6]张德鑫:《数里乾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7]鲁迅:《药》,《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3-472页。
[8]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9][荷]米克·巴尔:《叙事学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10]鲁迅:《秋夜》,《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11]吴秀明主编:《多维视野中的百部经典》中国现当代文学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12]孙玉:《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3]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14]丰竞:《鲁迅文学作品中数字的修辞分析》,《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5]孙淑芳:《论鲁迅小说中色彩语码的隐喻内涵》,《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9期。
[16]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7页。
[17]魏耕原:《数字十九实虚反复转化的意义——兼论鲁迅小说中的数字内涵》,《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8]鲁迅:《父亲的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页。
[19]杜贵晨:《“三而一成”与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兼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数理批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20]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21]叶舒宪、田大宪: 《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105页。
[22]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转引自靳邦杰、王世家:《中学语文课本鲁迅作品详解》(高中册),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6页。
[23]吴中杰:《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