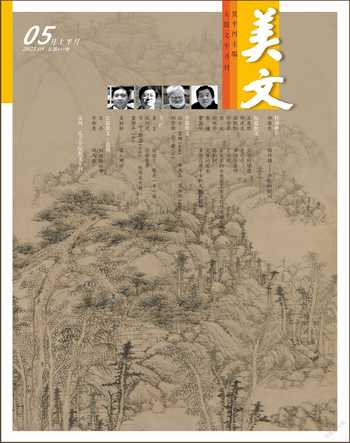乌桕树
赵艳华

乌桕树
第一次读到乌桕树,还是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六斤捏着一把豆,正从对面跑来,见这情形,便直奔河边,藏在乌桕树后,伸出双丫角的小头……”因为这些个场景,也因为乌桕树的“乌”字,在我的印象里,乌桕树树干黑色,植株高大沉重,它最适合活在近现代那缓慢的、暗沉沉的空气里。
后来又读到《西洲曲》,里面也提到乌桕树,说:“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杏子红和鸦雏色固然让人觉得青春明媚,但是日暮,加上伯劳这种叫声粗哑且凶悍的小鸟,再叠加上乌桕树,就让人顿觉苍凉孤独,高兴不起来了。《西洲曲》写的仍旧是江浙一带的风景,所以,我一直认为乌桕就是江南的树。或者说,乌桕树就是种在古老江南的山间、路边、人家屋侧的一种大树。这种树只活在诗歌里,只活在近现代,也只活在江南。
没想到,第一次见到乌桕树,却是在广州。
一
写乌桕树之前,一定要写写他。
他是岭南大山里的人,我们在广州认识,结婚的时候去他家里,我第一次见到那么深那么厚重的山,山上有那么多植物:山上的大树、小树、爬藤、灌木都糾结在一起,简直密不透风,比起四季分明的北方,这里简直是一块可以无限生长的雨林。
我们结婚,生孩子,磕磕碰碰,也不乏恩爱。他一度生病,也渐渐康复。然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年,他的病复发,事情似乎就要发展到无可挽回的程度了。但是,在无可挽回之前,疾病却是扭扭捏捏,迈着小碎步,走一下停一下,似乎还没有想好蹂躏一个人的总体计划。我们无比焦虑,却又无可奈何。我陪着他到医院求医,战战兢兢等待专家的接见,接受各种检查,寻找各种意见,如坐针毡地等待着命运一轮又一轮地宣判,同时,也经受着一重又一重焦虑和恐惧的双重折磨。
新的一学期也开始了。我的工作单位,从一个新校区搬到了一个旧校区。这是一间很老的学校,无论是树,教室,教室门前的红砖地板,校园里跑来跑去的橘猫,老校工,还是那些穿着绿色校服的学生,都带着一种安安稳稳的笃定气息。我教的班在一楼,教室门口居然难得地长了两棵大树。树很高,树干有合抱那么粗,树冠一直长到了五楼的楼顶上。下课的时候,学生在树下走动说笑,短暂的课间十分钟仿佛也被拉长了。往往到了上午第四节,对面居民楼里的饭菜香就隔墙飘了过来——总之,一切都踏踏实实,舒舒服服,都呆在自己该呆的位置上。
只有我和他的生活失了衡。
日子仍旧一天一天地过。上班、求医、焦虑、等待。站在讲台上,看着那一张张稚嫩的面孔,我经常自怜地想:这些孩子,根本不知道讲台上的这个中年人心里有多少事。她讲课,说笑,布置作业,批改作文,看起来跟任何一个语文老师没什么两样,然而,只有她自己知道,她负担了多么悲苦沉重的秘密。也许,不久之后,她的人生就要见到最可怕的场景了。
病人一开始还能坚持上班,还能偶尔在公园里跑个步。半年后,他请了长假在家休养;再后来,他只能静静地坐在凳子上,等我回家做饭了。
一个傍晚,天冷了。下了班,我去菜市场买了菜,踩着单车回家去。恰好是一段逆行的上坡。风吹过来,我一边弯腰卖力地骑,一边在脑子里算着:蒸一条鱼,鱼有营养;焗一个五花肉,五花肉有肥有瘦,加上柱侯酱,有滋味,病人比较容易入喉;再焯一个菠菜,菠菜也比较软烂……这么合计着,抬起头来,却看到天色已经昏暗,一颗孤零零的小星悬挂在天角。身边的汽车们嘀嘀地鸣着,汇成了一条急匆匆的河流,一起奔向一个光辉华丽璀璨无比的方向。只有我跟这条洪流背道而驰。路陡,我的两条腿又被车把上装菜的塑料袋子敲着,人只能磕磕碰碰地向前骑。那一刻,突然觉得悲从中来,再也蹬不动车子,只得下来推行几步,顺便把自己的眼泪擦了。那天正给学生讲《荷塘月色》,心酸之际,心里反复涌起的,居然是《西洲曲》里“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两句。当时我身边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哪有什么伯劳和乌桕呢?我能有的,不过是跟那两句里一样的苍凉和孤独罢了。
后来,教室前的树结了果子,果子掉了下来,一粒粒白白的,学生捡了来问,我才顺便知道它居然是乌桕树。原来这就是乌桕树。原来岭南也有乌桕树。我没想到,自己居然跟一棵诗歌里的树相对了那么长的时间。抚着它粗糙的树皮,我感慨万千,一瞬间,仿佛觉得自己悲凉的情绪有了一个可以寄托的地方。
是啊,我可以跟谁说呢?父母老了,不可以让他们担忧;孩子还小,他承担不了父母的哀愁;学生只是学生,他们没有责任和义务分担我的命运重担;同事们很忙碌,他们已经帮我太多,我不能过多地烦扰他们。总之,生病是可耻的,某种意义上,疾病,尤其重疾,是不可说的。说了,非但改变不了什么,还会给这个年轻的世界带来不可背负的沉重和晦暗。所以,不如不说。尤其是在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生病简直就犹如推脱了自己人生的责任,让人不自觉地自我谴责起来。
我们于是保守着这个秘密,既不告诉家里,也不告诉朋友,只是相对坐着,叹气、求医、治疗。他越来越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但也只静静地忍受着,不抱怨,也不诉苦。我就陪着,从单位到家,从家到医院,或者反之。我把恐惧和焦虑背在身上,在三个地方之间奔波来去。有时候,比如,收到极大的坏消息的时候,我也会走到楼顶,在没人的楼梯间隐忍地哭一场,然后,对着楼顶乌桕树一片一片在风中摇曳相击的青绿叶子,默然良久,等眼睛里的泪干了,再走下楼来。
命运确乎是不可改变的,说了也没什么用。在跟疾病对抗的这些日子里,我和他都明白了这个道理。
然后,某一天,一切的忍耐,背负,煎熬,疼痛都结束了,死亡带走了他,他完成了自己的一生。
我把他永远地留在了2021年。
二
今年的冬天,在公园的竹林深处,小路转弯的地方,我突然看到了一棵极美的树。
这简直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树:树冠饱满、葱茏,一树红艳艳金灿灿的叶子,夕阳几乎把所有的光芒都撒在了它身上。只要有人经过,绝对会被它那耀眼夺目的光彩吸引过去。树长在草坪上,脚下是浓密的蟛蜞菊,背后是两棵高大的木麻黄。像是为了躲避木麻黄沉重的关怀,它朝斜侧里伸出了枝条。这不经意的旁逸斜出,更给了它一种让人怜爱的姿态。这棵树,简直像一个美人:安静、妖娆、不动,却热烈,却有无限风情。
乌桕。我立刻认出了它。没错,这就是古诗中同枫叶争艳的乌桕树。
它太美了。满园肥壮的绿,只有它是一树红。每一个经过它的游人都会不由自主停下来,举起手机对着它拍个不停。后来,贪婪的游人们不满足于远观,有些人就跨过灌木丛,走到它身边去,在树下久久伫立;有的人干脆走到蟛蜞菊的深处,走到树美人的对面去,从另一个的角度去捕捉它的美。竹林浓绿的草坪被临时踩出了两条小路,这两条路,都通往美。
它的美也吸引着我。我开始频繁地到公园里来,只为了看一看它,为了能在不同的时候欣赏它的风姿:有太阳的时候,它举着自己丰满的华丽的冠,久久地浸泡在阳光里,直至每一片树叶都变成了金红色透明的琥珀;起雾的时候,竹园里的空气都变成了细细的淡绿色,它的叶子也更加清丽。有一次,我甚至在天黑后还来了一趟,自然是什么也没有看清,但看到它黑暗中曼妙的身影,就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我问自己,为什么如此关注一棵乌桕树?认真想想,大概是因为现在终于有了空闲。我的心里曾经塞满了东西。他在的时候,是焦虑、忧愁、恐惧;他走之后,是忧伤、孤独和空虚。现在,八个月后,满溢的忧伤逐渐沉淀下来——这个曾经满满当当的空间,终于可以空一会儿,闲一会儿,终于可以看见一棵红艳艳的树了。
热了又凉,凉而复热,折腾了几番后,来了一个大台风,岭南终于顺势入了冬。台风过后,温度骤降,大家都穿上了棉衣。再踏入公园,这里一切如旧,所有的树都依旧青翠。风已经停了,园子里静悄悄的,在这幽静冷凉中,桂花的香味格外清冽。鸟儿们趁着新出了太阳,在树间扑来扑去。
我迫不及待地去看乌桕树。转过弯,惊愕了半天——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风雨下来,乌桕树居然已经凋零了半边,只有朝南的叶子还挑在枝上,其他地方只剩下光溜溜的枝条了!当时满树华美丰润,现在却是一半萧条,一半荒凉。走近了再看看,剩下的叶子也全变成了焦红色,一片片蜷曲着,静静地挂在枝头,一动也不动,显出很散淡憔悴的样子来。一场冷雨,这美丽的乌桕树,现在也成了那迟暮的美人,容颜减了,只剩下那把瘦骨头了。
我仰头看着,正在感喟时光的无情,不知道哪里起了一阵微微的颤动,突然,一片叶子就毫无预兆地,轻轻地、决然地,飘了下来。它飘零的姿势那么突然、决绝,让人措手不及,根本没有办法提前预知。这一片小小的落叶,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的心在那一刻也颤动起来。这决绝的、自然的、无法更改的姿势,唤起了我的一个什么回忆。
是什么呢?我静静地站着。
周围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树一动不动,叶子也都不动,空气停滞了,只有远处一个小孩子稚嫩的声音划过,大家仿佛都在等待着一个重大时刻。一根枝条抖了抖,仿佛一个人欠伸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发生。然而,就在我定睛看着,世界仿佛陷入凝固的时候,又有一片叶子静静地、突然地掉下来。它一点留恋也没有。然后是另一片,再一片。它们飞旋着掉了下来。轻易地、轻飘飘地、义无反顾地、决绝地、淡定自然地。
就像他一样。
我想起来了,它们就像他一样。
确实就像他的离开一样:虽然很瘦弱,但昨天晚上还能自己洗澡,自己洗内衣,可是,第二天就在枕上安详疲惫地离开了。那么简单,那么容易,一下子就过去了。虽然我曾想过无数次,但我决没有想到,死亡如此容易跨过。一个晚上就是永诀。枕头上的他那么单薄,病弱,单薄的衣服覆盖着单薄的他。他就仿佛一片葉子,水分用完了,活力用完了,就轻悄悄地,抱歉地,决绝地,自然地,走了。
一个人,就像一片叶子。一片叶子,也像一个人。
一瞬间,我站在那里,泪流满面。
三
我跟他一起,在岭南度过了我们最年轻最有活力的日子。在我印象中,岭南没有死亡,岭南永远不老。这里树荫匝地,没有秋冬,只有无尽的漫长的炎夏。你看,那泼泼洒洒的棕榈,那肥硕壮大举着小黄花呐喊着冲向一切空地的蟛蜞菊,那永远常绿的木麻黄,它们什么时候老过什么时候死过?这里是插一根棍子都会发芽长大的亚热带。这里的夜晚在12点才刚刚开始。在这样的地方,他怎么在那么年轻的年龄说走就走了呢?
然而,他最终还是抱歉地走了。
然后,在这生生不息万物碧绿的岭南,在今年冬天,我突然看到了这棵会凋零的乌桕树。
在万物生长的南方,这棵华美而又凋零的乌桕树,以它的美丽和凋零安慰了我。
他离开了,但他无处不在。他和它,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告诉我同一个道理:死亡是一件极其自然的盛事,它无时无刻都在发生,谁也无法阻止它的到来。
后来我再去,剩下的叶子也一片片脱落下来,乌桕树渐渐变成了一棵光秃秃的、毫不起眼的树。它站在满目青翠的园子里,跟周围不再有边界,再没有人留意到它。
它曾经点亮了这个园子。现在,它消失在自然中了。
公 园
一
公园给我的,可能比我知道的还要多。
这个园子那么大,植物那么多,高大的植物尤其多,莽莽蓁蓁的去处也不少——一进去,我的悲伤、难过、孤独、茫然,仿佛就被稀释、被吸收了,我暂时变成了一个轻松的人。我在那一刻一无所有,只看到树、水、鸟、虫,和许多的人。所有那些烦人的、难以解决的、无法解决的东西,都可以暂时放一下,放到“公园”这个圈子之外,放在“在公园里”这个时间之外——于是,我可以跑一会儿步,出一下汗,在公园深深浅浅的绿色光芒暂时忘了自己。
公园的前身是郊区森林公园,它占地广,树多,湖泊面积大。即使是寸土寸金的现在,也仍旧罕见地保留了一些荒地,隐约可见当年的阔大荒蛮。我算了一下,公园里没有被人工充分雕琢过的荒地大概有五块,且每块面积都不小。谢天谢地,这些荒地都是我消愁解闷的好去处。
一踏进公园,就可以看到第一块荒地,它被高的桉树,矮的三桠苦、玉叶金花、鸡屎藤,更矮的蟛蜞菊和白花鬼针草占满了。低矮的灌丛植物们密密麻麻地纠缠在一起,在岭南炎热潮湿的气候里肆意生长,把这块地盖得严严实实。
我第一次走进它,是为了追看两只红翅凤头鹃。这颜色漂亮的春季过境鸟才在桉树上露了个脸,就躲到林子里去,只响亮粗哑地乱叫,却再也不出来。再听听,除了红翅凤头鹃的大叫,林子里还有一些无法辨识的怪声,那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于是,在好奇心驱使下,我试探着跨过一根颇大的枯树干,向密林深处走去。
这完全是一个孤独者的探险,小路上除了我再没有第二个人。很多枯树干横在小路上,蜘蛛丝拂着脸和头发,脚下尽是可疑的荒草团,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蛇。走着走着,鬼针草的种子就毛茸茸挂满了裤腿。公园的主干道就在几米外,一个小女孩清脆的说话声似乎近在咫尺,但我看不到她,我只能在原始雨林之中独自跋涉。转了一个弯,我正低头看脚下,却听到扑啦啦一串响动,一只羽翼斑斓的褐翅鸦鹃跌跌撞撞飞扑到园子那头去了。
走了好久好久,人声渐渐微弱,周围的高树仿佛都自动让开,只在远处俯视,独留一片空地出来,我就站在这空地中央,双眼茫茫,脚下是蓬勃无用的杂草。脚下有小虫在叫,几步外居然有一朵洁白肥大的栀子花,即使隔着口罩,我也闻到了它强悍的香味。周围荒芜复杂,只有这棵花幽幽地明艳着,仿佛给这片荒芜带来了人类世界的秩序。
站了一会儿,万籁无声。正在出神,却见一只乌鸫,伸直黝黑的翅膀,呀的一声,掠过我的头顶,直飞到高高的木麻黄树干上,跳踉两下,不见了。
荒地的中心于是愈加荒凉。桉树和木麻黄树叶子稀疏,枝条高耸,站得远远地。周围居然看不到一只红耳鹎或者白头鹎,这绿色的荒漠沉寂着。
只能向下走,路总是有的,虽然路上永远只有我一个人。仿佛走了很久很久,仿佛永远也走不出去,但是,最后,我低头猫腰穿过一片竹林,抬起头,却突然发现自己居然就站在了大路上,游人如织,正说说笑笑地经过我。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
二
对另外一个荒地的探索,同样源于一阵婉转多变的鸟鸣。正是春天,这些小鸟的鸣唱受荷尔蒙的制约,跟平时听惯的调调大不相同,所以我怎么也认不出它来。屏息等了良久良久,却只看到杜鹃花下一个模糊的小灰影子,去追它,它三跳两跳,立刻不见了。正惆怅之际,那恼人的美妙歌声又在不远处响起来了!就这样,我被它诱惑着,一步一步走进了另外一个密林。
这个林子里多是棕榈科植物,它们的叶子宽阔碧绿,把天空遮满了。树下有两条小路,一条向左边,通向林子深处;一条向右,不远处就是大路。我先试探着向右,没走两步,居然发现了一块空地。这空地干净小巧,仿佛是一个私人秘密基地,头顶还弄了一个遮雨棚。它是谁维护的,又用来做什么呢?
再略略向前,却看到一个男人肥圆的蹲伏着的背影,他拿着弹弓,正练得专注认真。子弹被这现代武士用力射出,啪啪啪地洞穿了可怜的树叶。大路上游人如织,这人却躲在小树林子里秘密练习童年绝活——想到这儿,我低下头,提起脚,赶紧掠过他,三步两步走到大路上去,让他一个人继续在小树林里练他的绝世武功。
向左分叉的那条路上的风景要精彩得多。跟第一块荒地的灌木丛生不同,第二块荒地灌木少而高树多,探路者只能在林下穿梭,很难看到完整的天空。这里的树仿佛都商量好了,一起往高里长,只要略略高过人头,它们就手挽手,连成一片,你需要穿过长长的密林通道,才能抵达它的中心。
小路的起点乃是一棵光秃秃的枯树。枯树怪枝嶙峋,高高地向天空伸展。这棵枯树,就成了这片绿色海洋当中的一个小小岛屿,鸟儿们喜欢在这里栖息。最热闹的时候,我看到噪鹃、蓝喉拟啄木鸟、红耳鹎、白头鹎、珠颈斑鸠几种鸟共处一树,大家花团锦簇,和和气气,该唱的唱,该吃的吃,该发呆的发呆,谁也不妨碍谁。
再向里走,一路曲折向下,向下,穿过树的走廊,一路向下,走到林子光线最幽暗的地方,就可以抵达荒地中心。
我为什么会认为它是中心呢?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是,一到了这里,一见到那棵巨大的黄葛树,我的感觉就告诉我,中心就在这里。这棵树树干之高,树叶之翠绿浓密,树冠之浑圆巨大,都让人咋舌。它庞大骄傲地独立着,仿佛是这块荒地的神祇,各种杂树朝它俯首,周围的生物都仰仗它的庇护。整块荒地杂乱纠结,唯有这棵大树下面,它的枝叶遮蔽范围之内,居然连一棵灌木也没有,整个宛如一个平整的环形小操场。是谁打理的这块空地?又是哪个孤独者整日在这密林深处盘桓?我同样不得而知。
我想,这个公园的荒地深处,一定有许多孤独的人,像我一样,在这荒地里寻找自己的慰藉。
作為必要的点缀,一只黑羽红眼的噪鹃一直蹲在黄葛树树顶,某个我看不到的角落,一直发出高亢苍凉的呼唤。
三
向深处走,向更浓密更杂乱更荒凉更阴暗更孤独的地方探索,这大概是我这个心事重重者一个奇怪的嗜好。我的心事既然在人烟密集之处无法解决,那么,在这些地方,我能等到什么,能得到什么,能放下什么,又能解决什么呢?
让我想想。
有时候,等的是一只鸟。比如,春天的时候,我在那几棵树前久久地屏息站立着,等待那只过路的褐胸鹟落下来。它每次都选择站在那根横枝上,站好后,用它鹟类特有的大眼睛久久地大胆地端详着我,于是我围着它左拍右拍,上拍下拍,直至几乎把相机架到它鼻子尖上。等我拍了无数张照片后,它突然又毫无征兆地飞走,我只能又开始屏息等待,觉得它还会落在相同的地方,被我久久地观察。果然,隔了很久后,它又下来了,又在那根树枝上偏着头看我。我沉迷在这捉迷藏一样的游戏中,这一等大概就是几个小时。在等待的时候,时间简直是水一样迅疾地溜过去了。
有时候,也许等到的是更浓重的荒凉和虚无。荒野之所以是荒野,就因为它少有人来,没有被用力地雕琢过。所以,荒野并不呈现优美的整齐感。它是复杂而凌乱的。一切都在自由生长:藤在奋力攀爬,企图绞杀大树;巨大的蚂蚁在树上穿梭,石楠散发着浑浊的香味,剧毒的菅兰结出了神秘的紫蓝色的果子,白花鬼针草举着小白花呼啸着,几乎覆盖了整个荒野。
有时候,我只是默默在这个园子里走着。迎面走来了很多人,他们一个个喜气洋洋,带着孩子,或者相互携着手,一边走一边追逐一边开怀地笑着。他们走向我又离开我。而我永远是怀揣心事,不知所措,只能等待未来的裁决。家里的那个病人虚弱地喘息着,皮肤苍白,下眼睑上还尚存一点血色,进进出出医院很多次了,但每一次都没有什么起色。除了绝望和焦虑,我能怎么办呢?我没有办法。他虚弱地笑着,看起来很平静,却又忍不住愧疚地安慰我说:“不要这样——医生都没有办法啊。”
有时候,比如这个春天的某一天,我会在某个奇妙的地点,集中地、眼花缭乱地看到小鸟们的总演出,看它们红的黑的绿的黄的翅膀飞起来,看它们喝水、鸣唱、求偶、觅食、晾翅。那两个小时,我每一个细胞都沉浸在喜悦中。我忘记了自己,时间,他的疾病。
当我垂下眼睛,走在回家的路上,我重新又立刻被灌注满了忧伤。
第三块荒地在一个小小的山上。傍晚的时候,我绕着这座小山跑步,山下密密麻麻的虫鸣声仿佛也可以堆叠成山。下过雨之后,蛙声骤然变得宏大响亮,虫声蛙声合奏,一阵一阵、一波一波,简直达到了如雷如鼓的效果。
夜晚让这座山,让山脚下的蕨类植物,让隐藏在草丛中的虫子获得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野气,原始的荒蛮气。天气越热,越潮湿,黑暗越浓,虫子的鸣唱声就愈大、愈澎湃。单独来看,每一只鸣虫都很小,很柔弱,但是,当亿万个它们一起用力合奏,就制作出了声音的海浪。这海浪翻滚着,仿佛永动机一样,永不止息。它们让整个夜晚湿气弥漫,瘴气丛生,让人不敢举足靠近。可是第二天清晨你去看时,它仍旧是很安静的一座小山,驯顺地展现在你面前,又质朴又亲切。一切都静静的,仿佛这个世界刚刚出现。
四
2021年4月22日,他去世了。5月的一个晚上,我又站这草丛前。草丛很深,而且有巨大的黑暗,仿佛可以吞没一切光线。空气潮乎乎的。突然,就在最黑最暗的地方,一盏小小的灯笼亮了起来。它那么柔弱,那么迷幻,就这么飘飘摇摇,一闪一灭,颤颤巍巍地朝我飞了过来。它左飞右飞,若有若无,几乎就是一小团非物质一样的存在。彼时,我的身上还沾染着浓重的死亡的气,这一小朵幽昧之光,让我仿佛看到了逝者那柔弱的灵魂。那一刻,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后来那两个星期,公园的萤火虫突然大爆发:每个晚上,每片草地,每个长满草的深沟里,都有一只两只几十只甚至一大片萤火虫冒出来。越黑的地方,它们越亮。整个五月的夜晚,我就在黑暗的草地边长久地站着,看着萤火虫们在黑暗中微弱地飘摇、寻找、熄灭、亮起。它们仿佛是那一点点希望,一点点安慰,也仿佛是来自彼岸的无言的使者。总之,这幽暗的世界里的幽暗的光芒,给我带来了多少迷思啊。
六月底,它们完成了寻觅配偶和交配的任务,就渐渐稀疏,消失了。
我亲手送走了他,这个跟我相伴了17年的人。他走之前的那几年,我每一天都跟疾病相伴。我亲眼看着他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从一个肌肉丰隆的中年人,变成了一个骨瘦如柴行动迟缓的慈祥的病人。他走之后,我每一天都在复习他的死亡。每一样事物都会使我想起他。为了稀释这种苍凉的情绪,我只能回到公园,奔跑,或者长久地观察和浸淫。公园曾经接纳了我的无限绝望,现在,我又在它的怀抱中消化忧伤。我一边跑步一边想:这个公园的一草一木、角角落落都浸满了我的思绪,这个公园俨然已经变成了我的公园——我的极大的感受之所和思想之地,而他确乎就在这里,他在每一个卑微的事物中,在这一呼一吸的空气内。
我于是更加认真地奔跑。在柠檬桉的强烈气息里,在盛夏之夜虫子的轰鸣声中,我的目光和神思渐渐从彼岸回到了此地。
(责任编辑:庞洁)

趙艳华 中原人,现居岭南。现当代文学硕士,高中语文教师。有大量自然考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