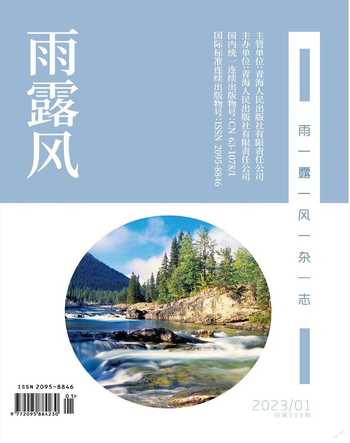从“赋体”到“言意”

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成熟标志,《文赋》集中地表达了“恒患言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个困扰历代文论家的“言”“意”关系命题。其“以赋言文”的独特话语结构形式,为言意关系的探究找到了一个特殊的入口,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甚至在20世纪末引发了“形式主义”之争。作为一个致力于文本细读的研究者,钱钟书也注意到了《文赋》特殊的话语结构形式,并在《管锥编》中分析和研究了作者使用赋体形式的原因,以及由此带来的陌生化效果和文本张力。
一、陆机与《文赋》
宗白华曾指出,魏晉六朝在政治上的黑暗和痛苦,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是共生的。在魏晋六朝以前,汉朝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王朝主流的统治思想与意识形态,这严重禁锢了文学的发展,故文学只在儒家经学的体系中打转。孔子谈论诗歌时所道的“兴观群怨”“事父”“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等都是为政治道德的现实功用服务。
如果说曹丕的《论文》是“文学自觉时代”开始的标志,那么陆机的《文赋》则表示“文学自觉时代”趋于成熟。在称之为“中古”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文学在对文学语言的理论认识和运用实践上,经历了一次称之为“文学语言革命”的范式转换,把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锻造置于文学理论的中心位置。针对这种转向,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一个为历代文论家所关注的问题: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意”即派生出“言”“象”,又是可以被言、象把握的客体,这是儒家思想无法解释的,所以陆机寻求道家思想与玄学的理论资源,丰富了《论语》中“文质观”的内容和厚度,同时也增加了其艰深。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文赋》曾一度受到形式主义的批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形式主义与西方文论上的形式主义没有太大的关联,仅在理论逻辑上略有相通。古代文论中的形式主义并不是通常所说与内容相对的那种东西,而是文章的另一因素,它就是刘勰所说的文采,形式主义实为文采主义。“诗缘情而绮靡”的提法被认为过于重视文学的形式美,开启了西晋末年的靡靡之音,这种批判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从俄国形式主义借来的词汇,但并未抓住形式主义概念本身的美学内涵。
俄罗斯汉学家在对《文赋》的研究中,认为“赋”这种特殊的对偶的结构,将读者带入一个区别于日常语言的世界, 重新构造对对象的感觉,从而扩大了认知的难度和广度,不断给读者以新鲜感和陌生感。“以赋言文”作为《文赋》这篇文论所使用的话语形式,说到底,既是“言”说形式,也是理解其陆机言意关系的一个重要入口。
二、钱钟书与《文赋》“赋体形式”解读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对《文赋》进行了文本细读,开篇就提到陆机《与兄平原书》之九:“《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在讨论“文适多”问题的同时,也间接点明了《文赋》文风繁缛、语言华丽的赋体言说形式。
此后,钱钟书又列举出陆机与其弟陆云有关赋体创作的相关讨论,如陆机《与弟云书》中:“此间有伧夫,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尔。”按卷一〇二陆云《与兄平原书》之一九:“云谓兄作《二京》,必得无疑,久权兄为耳。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语,触类长之,能事可见。”历代创作者都会对前代作品因袭和模仿,这种状态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常态。陆机作为西晋代表作家,是骈文形成时代的关键人物。其中汉代赋体传统和儒家的文艺观对陆机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文赋》中“典坟”“六艺”是指儒家经典,可见陆机注重从儒家典籍中积累文学创作素材。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陆机及其弟陆云往往表现出对功名德教的向往,作为魏晋时期蔚为大观的创作形式,赋体就是陆机实现自身抱负及文人才学的一种强有力的书写工具。
“《文选》以赋体开篇,而以《京都》冠其体;盖此中制作竞多侈富,舒华炫博,当时必视为最足表才情学问,非大手笔不能作者。故左思不惜‘构思十稔为之,而陆云亦‘久劝兄为。”钱钟书清醒地意识到赋体言说形式为《文赋》带来了全新的审美效果,也为理解《文赋》的“言意”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汉学家宇文所安对此也有相似的看法:“不谈赋这种形式就无法理解《文赋》。”赋体是魏晋时期“非大手笔不能作者”的写作形式,《文赋》中的大量隐喻、双关、互文、隐喻手法将对象从正常的感觉领域中移出,重新建构对对象的感觉,这就进入了形式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陌生化。
就文体概念来说,不同的文体之间并非界限分明,同一文体不同人使用也未必能达到相同的效果。钱钟书就在《管锥编》中引陆机《文赋》之“十体”,曹丕《典论·论文》之“四科”,《文心雕龙·定势》之“随势各配”,《雕龙·体势》之“八体”,论证了此物此志,具体到篇目上各文体名相如而实不相如的观点。
“文”在《文赋》中也是一个具有复合内涵的概念。钱钟书曾明确指出:“《文赋》非赋文也,乃赋作文也。机于文之‘妍蚩好恶以源流正变,言甚疏略,不足方刘勰、钟嵘;而于‘作之‘用心‘属文之‘情,其惨淡经营、心手乖合之况,言之亲切微至,不愧先觉,后来亦无以远过。”前人多侧重总结关于《文赋》在创作理论方面的系统阐述,事实上,其中不少非理性的关于创作感受的成分却被忽略,钱钟书“赋作文”的说法看见了《文赋》之特殊性。考虑到书写对象的复杂性与神秘性,传统的论题在应对这一书写对象的时候大多显得刻板拘谨,面对这个文体,陆机选择尝试使用赋体形式来阐释“文”。从效果上看,以繁复应对繁复显然是一个很有效用的选择,一方面保持着“颐情志于典坟”的情志,一方面又进行着“破体”的尝试,体现出陆机对于文体形式认识的超前性。
赋体在陆机所处时代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功用。左思作《三都赋》引得一时间“洛阳纸贵”;郭璞作《江赋》为世所称,作《南郊赋》获得皇帝赏识而得著作郎的职位。左思“构思十稔”,陆云“久权兄为”,魏收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可以得知自诩才力超群,跻身高位的陆机也应需要赋作来重振家族声望。
从《文赋序》中看: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尔。
陆机不仅要将长久以来先贤关于写作难以言传的经验和体会记录并加以阐释,还完成了对于赋体形式和功能的拓展和创新。这种实践一旦得到认可,陆机不仅完成了一个写作者的自我实现,也完成了一个规范创立者的自我实现,后者正是我国古代文人“立言”以垂不朽的终极追求。
三、錢钟书关于“以赋为文”话语形式解读与“陌生化”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是西方二十世纪文论中影响最为深远,且被广泛应用的文学理论之一。形式主义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形式主义者提出了他们的核心概念——陌生化,成功地将文学批评研究的视野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作为形式主义的核心内容,陌生化支撑起了形式主义文论研究的大厦。 俄国形式主义学者什克洛夫斯基在论及陌生化问题时指出:
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了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
在这段论述中,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陌生化的最终目的是重新唤醒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使得主题在感观层面感受到刺激和愉悦,从而引起主题的审美感受,如果将感受过程不断地增强,那么主体获得的审美感受也会随之增加。
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原则也同样引起了钱钟书的注意,“在《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已经运用‘陌生化原则生动地解说和剖析了从修辞练句到材料裁选以至文学鉴赏等诸多现象,或者说从诸多现象中反复印证了‘陌生化原则的普遍性”。在《谈艺录》中,钱钟书提出文体相互“侵入扩充”说,举韩愈“以文为诗”为例,引宋人林光朝评“退之则唯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盛赞“艾轩真语妙天下者”。表明诗、文、词文体相互“侵入”和“补充”中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及对文章之“革故鼎新”的作用。
钱钟书正是秉持着此种原则,格外关注《文赋》新颖的“以赋言文”的独特话语结构形式,并从中体会其“竞多侈富,舒华炫博”的非常人之所不能为而产生的特殊审美效果:“‘赋因其管用的修辞技巧,如对偶、互文、铺陈以及中国特有的‘隐喻用法,形成一种不符合线性描述的逻辑,而是由相反或者相对的观念和立场组成的套系,常常允许矛盾的因素存在,造成结构上的张力”。
四、结语
在论述表达与文体关系时,陆机强调艺术表达必须充分考虑文体的特殊限制,同时也对同一文体因时代不同和主体差异而显现的纷纭变化进行了论述,并没有拘泥于文体的界限,以发展、辩证的眼光凸显其变化和差异,体现出陆机文体观中的“打通”。钱钟书对陆机《文赋》“以赋言文”话语形式的解读中,也体现出钱钟书对其文体“打通”所产生的“陌生化”审美效果的欣赏与中西文论的“打通”。钱钟书将中西诗学话语进行互补互释,来重新认识中西诗学中那些易被误解的理论命题,具有重大的纠偏意义,也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现代诗学建构过程的认识和思考。
作者简介:王贝贝(1999—),女,汉族,河南邓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