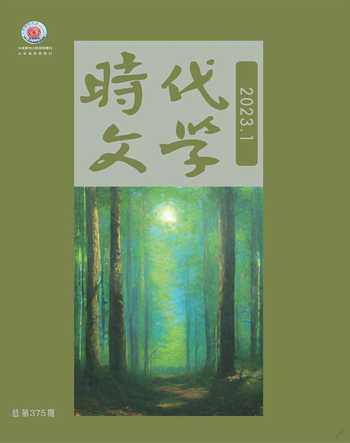醉酒的羊(短篇小说)
于芳潇
现在,沮丧的王坎坎,就像老伴出殡时那只蔫头耷脑的羊。当时,羊就那么站着,不吃不喝,雕像一样盯着灵堂里老伴的黑白遗照。它的眼珠那么蓝,很深邃,王坎坎和它对视一下,就如触了电,连忙躲闪开来,再也不敢看它。风吹乱了羊的白毛,像风吹麦浪。王坎坎眼泪滚下来,倏忽间感觉和羊贴着心。他偷偷擦去眼泪,泪珠儿又聚大了,羊变了形,老伴的遗照也变了形。
他沮丧是因为刚才求人吃了软钉子。一辈子刚强的人,没开口求过人,哪里想到老了老了,脸丢到了地上。人活着不就是活一张脸吗?脸没了,还活个什么劲儿?若是老伴看到他的狼狈样儿,会心疼的。老伴没看到,羊却看到了,蓝眼珠儿里似有万般不舍。羊看到就像老伴看到一样,有什么区别呢?他发现,老伴不在了以后,羊的举动越来越像老伴。
杰出,我试试吧!我对天发誓不添乱!王坎坎眼珠儿血红,拍着胸脯。李杰出干笑着,就像没浇水的鲜花,开得很敷衍。老头像小孩一样可爱,干不了这活。怎么回答才能不驳老头的面子呢?话在李杰出心里翻来翻去,走到舌尖又滚回肚子里,像牛反刍的烂草。
看到李杰出喉结上下滚动,王坎坎看了看羊,羊也看了看他,他们眼神里有相通的东西。是什么相通,王坎坎一时半会儿想不明白。在他眼里,羊不是牲畜,而是伴儿。羊是老伴买的,刚进家门时,半条胳膊长,柔柔弱弱,天天黏着老伴。老伴经常摸着它的头说,快点长大吧,下奶给老头喝。羊没让她失望,奶子一天比一天大,直到怀孕后,变成两个球。羊崽落地,奶子就像泉水,一挤不断地往外喷。老伴每天上山折榆树枝叶给羊吃。榆树叶是好东西,人也能吃。羊喜欢吃榆树叶,产的奶有股清香味。王坎坎喜欢喝羊奶,顿顿喝,直到喝得脸色红润,羊奶还是很旺。
说话呀!王坎坎巴掌拍红了,几乎喊着说,要急死我老汉?说个实话,钱不钱的无所谓,我不在乎钱!我老汉不缺钱,就是找个活计磨磨时间。你不知道,晚上时间那么长,黑乎乎压着我呀!咬人……喘不上气来……他看了看羊,心里的秘密似乎被别人窥去了一样。老伴走后,他在羊面前,总是坚强,倔强地坚强。
李杰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心盘算了很久,还是为难:樱桃大棚刚刚建起来,夜间管理容不得一点闪失。王坎坎干事没问题,可他不会管理技术,咋能放心让他干?
王坎坎眼巴巴盯着他,眼珠儿像久旱的田地,布着一条条深深的裂痕。李杰出身上好似爬着许多蚂蚁,干咳一声,脚尖画着地,半天挤出几句话,叔,我考虑考虑……
王坎坎不糊涂,明白考虑考虑的意思。他不怪李杰出,樱桃大棚是村里的眼珠子、命根子。手不能拿、肩不能挑的糟老头子,就是个累赘。
不给你难题了。王坎坎转过头,眼里有泪点。李杰出看到了,心里不得劲儿。
后背冷飕飕的,王坎坎憋着泪珠儿,一肚子的话想和羊叨叨。老伴走了,羊成了她留给他的念想。他心疼羊,不把它当牲畜看,而是当人看。
这天晚上,王坎坎想喝一杯酒,犒劳一下自己。犒劳什么呢?他说不清楚。他想找个人陪着喝几杯,想来想去,哪个老伙计都不合适。
老李头要照顾瘫痪的老伴,洗衣做饭,种地收拾家,手脚不沾地。王坎坎羡慕他有人陪着说话,有人说话是多么幸福的事呀!自己经常半夜说话,对着黑暗的墙角说,话像进了黑洞里,没有一点回响。每到这时,他就感觉日子没滋没味。他到羊圈里,搂着羊说半夜的话。羊身上有股好闻的味道,他会想起老伴身上的槐花香味。他闻了一辈子,也没有闻够。羊安静地吃草,偶尔轻轻叫一声,温顺得像夏天冰凉的河水或一条绸缎。它听懂王坎坎说的话了吗?只有它自己心里明白,王坎坎不清楚。
张脑袋去城里照顾外孙了。他委屈巴巴地告诉王坎坎自己不想去,讨厌虫子样的汽车,高楼要塌下来一样,人密得像蚂蚁。王坎坎看着他稀疏的白发,心里发酸,嘴上不说,心里清楚,老伙计进城是没有办法,自己比外孙还重要吗?屈着自己吧!老李头挤兑张脑袋,去照顾个外姓人,白费蜡!将来能给你上坟烧香?张脑袋被捅了屁股一样,反击道,有人倒是有儿子,但是去了外国,几年不回来一趟。嘁!还不如我的外孙。李老头白眼直翻,说不出话来。
王闷子最合适,和王坎坎投机,话能说到一块儿,能尿到一个壶里。也不行,他最近找了個老伴,天天黏在一起,村里的老头都眼红他。喊他和他老伴一起来喝酒?人多热气腾腾,热闹得很。琢磨一下,王坎坎否定了这个想法,他不想当亮晃晃的灯泡,看人家亲热,心里是个啥滋味?自己给自己上眼药!不能干这样的事。有一次,王闷子劝王坎坎也找个老伴。王坎坎瞪着他,闷声闷气地说,是人做的事吗?老伴刚走,就动歪心思。王闷子说,男人嘛,能离开女人?有人陪着说话解闷也好。王坎坎说,我有羊呢!王闷子瞪着他,半天没说话。
想了一圈下来,王坎坎的脑门痛。算了,还是自己喝吧!图个清静。老伴不在后,哪天日子不是自己熬着?熬日子,熬来熬去,味寡淡了。
喝酒前,他先去地里割羊草。把羊伺候舒服了,他才能安心喝酒。他只割嫩草,小心地挑出夹杂的枯叶和杂草。老伴活着时,每次吃饭前,都会先把羊喂饱。他也养成了这个习惯,宁肯自己吃饭晚,也要先把羊喂饱。王闷子揶揄他,是不是把羊当女人养了?王坎坎“嘁”一声,心里说,你懂什么,羊是不会说话的“人”,心里什么事都懂。这些王闷子又怎么会明白?
他想炒几个菜,安慰安慰寡淡的嘴巴。架好火,手却懒了,不想大动干戈,凑合凑合哄哄嘴巴算了。一个人活着就是这样,吃饭不是享受的事,哄肚子不叫就行了。中午做的大盆炖白菜,还剩半盆,热热就可以吃。看着切得很粗的白菜块,他苦笑出了核桃脸。老伴若是活着,断然不会切得这样粗枝大叶,她会切得很均匀,就像机器切出来的一样。
老伴做饭手艺很好,咸淡适中,合他的口味。她去世前,挣扎着对王坎坎说,最放不下的就是你。我走了以后,你再去找个人,给你做做饭、洗洗衣。有个人陪你说说话,要不你一个人在家,还不闷死?老伴那时已快油尽灯枯,火苗说灭就灭。
儿子红着眼圈说,妈,说什么死不死的,你会好起来的。女儿哭花了脸说,妈,我和弟弟还要带你和爸爸去北京看天安门,去杭州看西湖。老伴闭上眼,轻轻摇摇头,这辈子不用想了……儿女奔出门去抱着哭。
王坎坎的儿子在北京工作,女儿在杭州工作,都事业有成,一年只在春节回家三四天,有时还不回来。老伴在时,儿女不回家过春节,王坎坎没感觉少什么。老伴不在后,他下了死命令,必须回家过春节。
女儿不放心王坎坎一个人在家,花钱扯了根网线,安了个摄像头,随时看家里的情况。王坎坎不喜欢猫头鹰脑袋样的摄像头,感觉它冷冰冰的,没有温度。儿女有时会在“猫头鹰”里说话,无非是吃饭没有?钱够不够花?别不舍得花钱,没钱了就说,给你寄。女儿心细,叮嘱王坎坎,西瓜下来了,买着吃。甜瓜有卖的,买几个,不要亏了嘴。
王坎坎哼哼着,心想,土快埋到脖子了,能吃多少?能喝多少?有钱也花不出去。他很想说,带孩子回家住几天,我想外孙了。嘴上却变成了这样的话,好好工作,别总挂记家里。我好着呢,能跑能跳。要是外孙能和他说上几句话,他能高兴好几天。小家伙嘴甜着呢!
他经常拉着羊在“猫头鹰”下转圈,一圈又一圈,乐此不疲。女儿说,我只想看看你,不想看羊。王坎坎不吱声,对着摄像头抚摸羊头。女儿又好气又好笑,孤居的父亲脾气变古怪了。羊很配合演戏,淘气地伸出红舌头,眯着眼对着“猫头鹰”咩咩叫几声。它还会笑,嘴唇翻着,眼皮眯着,像个喜剧演员。女儿不想看羊,找个借口下线了。
王坎坎摸着羊头说,你看,你不讨人喜欢吧?那个不着调的儿子,几次动了杀你吃肉的念头。他知道你天天吃鲜草,肉嫩着呢!若不是我盯着,只怕你早就进他肚子里了。这时,羊低下头,在他腿上蹭脑袋。王坎坎心软软的,想起老伴刚嫁过来时的一些事。几十年前的事,就像在昨天。
儿女每年回家过年都会打算带老两口出去见见世面,天安门、西湖天天挂在嘴上。王坎坎耳朵眼磨出了茧子。但是他们离开村子,回到大城市,就会忘记这码事。王坎坎和老伴都不愿提这茬儿,孩子有孩子的事情,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他们的小日子,不能让两把老骨头拖累了。老伴眼见快不行了,还没出过村。王坎坎心里那个难受劲儿,像油煎一样。他抓着老伴的枯手,泪珠儿无声地往下掉,眼前的世界碎了,稀里哗啦的。心碎的滋味不好受,他宁愿走到老伴前头,也不愿承受这痛苦。
老伴说,你再找一个,我不怪你,只要将来你和我葬到一起,咱们下辈子还做夫妻。他听不下去了,捂着脸,跑到院子里,找个墙角,呜呜悲泣。
老伴下葬后,女儿要带王坎坎去杭州住,他连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儿子说,南方住不惯,可以去北京,孙子天天想爷爷。他的心颤了顫,孙子是他的软肋,想起来心就汪成一摊水,软软的。他差点答应跟儿子去北京,最后一刻,却缓缓地摇摇头。女儿急了,问,为什么不去?你一个人在家谁放心?王坎坎说,我还没老到糊涂的地步,能吃能喝,能跑能跳,为什么去麻烦你们?远香近臭,这个道理我明白的。离开老窝容易,再回来你们儿女脸上也无光不是?好了,不用为我操心了,我在村里就像鱼在水里,想怎么游就怎么游。在大城市,我摸不着方向,成干干鱼了。儿女都沉思不语,王坎坎说的理能站住脚。算了,强扭的瓜不甜,强逼父亲进城,憋出病来不划算。
老伴走了以后,王坎坎不喜欢待在家里。他许多次听到厨房传来锅碗瓢盆的响声,不自觉地就叫出老伴的名字。但是,没有人回应。他回过味来,老伴真的走了。空荡荡的家,没有一点人气。他经常半夜醒来,卧在被窝里吸烟,黑夜被他吸浓了。天亮后,满屋子浓烟,一地烟头。
他经常拉着羊去老伴的坟地。羊在山坡上吃草,会跑到老伴坟前,瞪着眼,站半天。王坎坎相信,羊有一肚子话要对老伴说,说不出来而已。所以,王闷子怎么会明白这些?王闷子也打过羊的主意,想把羊杀了,喝羊肉汤。想起这事儿,王坎坎就生气,想和他干一架。王闷子看他神色不对,溜之大吉。
王坎坎在老伴的坟前很少说话,枯坐坟边,听风声和鸟虫的叫声,看青草萋萋,绿树葱茏。山上的气味很好闻,青草香,甜甜的。老伴坟上长出了青草,有些弱,底气不足一样。他从来不清理这些草,认为这是老伴在出来陪他。那棵青草是她的眉毛,这棵青草是嘴巴……每棵青草他都能想成是老伴身体的一部分。
羊不吃坟上的草,也不在坟前乱叫。有时头抵在坟上摩挲,轻声低叫。王坎坎看到它眼里有层薄雾。羊想主人了吧?他心里酸酸的,对羊越发好。
有一次,他和女儿在“猫头鹰”里说话,说了羊在坟前的表现。女儿不相信他说的话,说,羊就是羊,不是人,怎么可能那么神奇?怕是你想我妈想魔怔了吧?王坎坎觉得贴心的女儿离自己越来越远,已经不懂他的心思了。女儿劝他去杭州,住不下,散散心也好。王坎坎说,我不去,我去了,羊咋办?还不得饿死?女儿生气地说,难道我和弟弟还赶不上羊?我们才是你的骨血。王坎坎很落寞,不再和女儿磨牙,要求和外孙说几句。外孙很乖巧,一会儿就哄得他晕头转向。
咱俩喝一杯!我干了,你随意!桌子对面没有人,王坎坎举着杯,对着某个虚无的目标说。老伴好像回来了,在对面坐着,默默看着他。她不是去世时的样子,而是刚嫁过来时的模样。那时穷,彩礼没多少,老伴穿的红衣服是借的。想到这里,王坎坎心里涌出酸水。老伴一辈子勤俭节约,供出两个大学生,让王家光宗耀祖。若是还活着,王坎坎一定带她去看看天安门和西湖。可惜人死不能复生。他自己去看那些光景,有什么意思?
儿子在“猫头鹰”里说话,他很长时间没说话了。老伴活着时,儿子很少和王坎坎说话,和他妈说话时捎带着他。儿子心粗,王坎坎不怪他。见他在喝酒,儿子不高兴地说,多大岁数了,能不能少喝点?万一喝个半身不遂,我和我姐咋办?王坎坎不吱声,为自己悲哀,岁数大了,是孩子的包袱。他伸伸胳膊和腿,活动自如,看来一时半会儿不能瘫在炕上。他想过将来,如果真如儿子所说瘫在炕上,就随老伴而去。
王闷子说过,人岁数大了,会越来越怕死。王坎坎不赞同这个观点,谁能不死,早一天晚一天而已。老伴先走一步,留下他苦苦熬煎着,若是真得了病,难道能让儿女请假回家照顾他?那样他心里不安,死得更快。若是儿女接他去大医院治病,他还担心这把老骨头回不了家乡,成为孤魂野鬼。他死了以后,要葬在老伴身边。他决定写个遗嘱,白纸黑字,看儿女敢不敢违背他的遗愿。
见王坎坎不说话,儿子语气软下来,问,钱是不是够花?王坎坎点点头说,够花!一个字都不想多说。王坎坎问,孙子呢?想和他说几句话。儿子说,去游乐场玩还没回家。两人冷了场,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两人之间好像隔着一层玻璃,能看见彼此,却交流不了想法。儿子找借口说手头的工作还没干完,要加班写方案。王坎坎说,写吧!工作要紧。
王坎坎的影子聚在地上,像个标点符号。抿口酒,咳嗽一声,没品出酒香来,感觉喉咙像被掐住了。他抬起头,看清楚了桌子对面没有人。他一阵伤感,埋怨老伴不陪他。
羊叫了几声,王坎坎才想起没给羊喂水。他狠狠捶了一下大腿,老糊涂了,只知道喝酒,忘了羊。他提了一桶水,摇摇晃晃来到羊身边,水倒进槽子里,羊大口喝着。看羊喝得香甜,他想起女儿刚出生时的情景。老伴担心他重男轻女,不喜欢女孩。王坎坎第一眼见到女儿,心就融化了,欢喜得不得了,自己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世界上又有另外一个自己。儿子出生后,他的世界只有两个孩子,为他们活着。孩子们慢慢长大,离他越来越远,村小学、镇中学、县高中,直到去大城市读大学。
羊抬起头,温柔地看着他,胡须上垂着晶莹的水滴。它的肚子越来越大,依王坎坎的经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该下崽了。羊奶垂挂着,像两个香瓜。下崽后,就有奶了。他喜欢喝羊奶,老伴却不喜欢,说羊奶有膻气,喝不惯那股味。自从养羊后,王坎坎很少感冒,老伴说是羊的功劳。王坎坎后悔,要是老伴也喝羊奶,说不准就不会死那么早了。唉,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人都不在了。
女儿生孩子时,老伴去杭州照顾过几个月。有一次,女儿对王坎坎说,我妈喜欢吃涮羊肉,孩子剩下的羊奶、牛奶,都是我妈喝的。王坎坎这才回过味来,老伴不是不喜欢喝羊奶,而是不舍得喝,留给他喝。他内疚了很长时间,自己太自私了,没想到老伴为了他连羊奶都不舍得喝。
羊甩甩脑袋,“咩咩”轻叫几声。王坎坎回过神来,摸摸羊的头,很滑溜。他说,你吃饱喝足了,没有烦心事。我老头子想找个人说说话都找不到。羊瞪着蓝眼看他。他说,老伴走了以后,你受苦了,我没有照顾好你。你怀孕了,我都没上心。羊围着他转来转去,蹭着他的腿。王坎坎心软如泥,感觉老伴又回来了。
王坎坎说,今天没面子呀!这么大岁数开口,人家李杰出没答应呀!人老了就格外要脸皮……所以想喝酒,没人陪呀!羊叫了一声,听明白他的意思一样。王坎坎看看羊,盯着“猫头鹰”看半天。现在,全家只有他和羊两个喘气的活物。老伴去世后,他怕黑夜。关灯后,浓墨的黑压在他身上,就像一块大铁板,很沉。他张大嘴巴,大口呼吸。梦也多,一个接一个,也是怪了,从来没梦到过老伴。醒来,就抽烟,打发很长的夜。
家里就咱俩,只能你陪着我喝酒了。王坎坎拍拍羊的脑袋,感叹自己的这个想法奇葩。他拉着羊,走到桌边,指着凳子说,坐吧!陪我喝两杯。羊站着,温柔地看着他。王坎坎拍拍脑袋说,你看我这个人,还没给你准备碗筷,就让你喝酒,我真是老糊涂了。你等着,我去拿碗筷和酒杯。羊还是站着,保持一个姿势不变,目光更加温柔。
王坎坎拿出老伴用过的碗筷,摆在羊面前。羊伸出红舌头,舔了舔嘴唇,四只蹄子轻轻磕着地面。王坎坎拿出酒杯,倒上白酒,放在桌子上说,喝吧!咱老哥俩喝一个。羊伸长脖子,粉红的鼻子凑近酒杯嗅着,然后缩回脖子,打了好几个响鼻。王坎坎哈哈笑着,直到眼泪笑了出来,喝下一口酒说,没想到你不能喝白酒。瞅瞅羊的大肚子,他自责地说,你看我这脑子,你怀孕了,不能喝白酒呀!对你的身体,对小羊崽,没好处。
羊好似听懂了他的话,无辜地看着他。王坎坎搛了一块大白菜,放到碗里说,吃吧!菜口味不好,凑合吃吧!我的手艺不如老伴。人死如灯灭,这辈子吃不上她做的菜了。说完,眼里涌上一片薄雾。羊瞪着他,嘴巴抿着,很体谅他的样子。它探头伸舌,卷起白菜吃了。王坎坎呵呵笑着问,合你的口味?可别嫌弃呀!我做菜的水平确实不行。我看你不能喝白酒,那喝点啤酒吧!
老伴生前喜欢喝啤酒,喝酒时遮遮掩掩,不好意思地说,哪有女人喝酒的?传出去不好听。王坎坎不以为意,哪有规定只能男人喝酒,女人不能喝酒的?赶集的时候,他专门给老伴买了个啤酒杯。杯子下窄上宽,高高条条,有漂亮的弧线。第一眼,他就喜欢上了,怎么看都适合老伴用。老伴埋怨他乱花钱,她用碗、用杯都能喝酒,何必去整些西洋景儿?王坎坎说,气质,这个杯子正合你的气质。老伴脸上浮起一片红云,咯咯笑着说,多大岁数了,还气质,说出去人家不笑掉大牙?王坎坎说,我就觉得你好看,别人说了没用。老伴眼里闪着光,这光在结婚时,王坎坎看到过。
老伴的啤酒杯还在,被王坎坎藏到柜子最里面,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场。他拿着啤酒杯看了半天,上面好似还残留着老伴的体温。玻璃晶莹剔透,在燈光下闪着光。他看到老伴在玻璃杯后面笑,含情脉脉地看着他。他有些不好意思,都多大的人了,目光里还有火。再一眨眼,老伴不见了。
他给羊倒上啤酒,白色的泡沫泛滥着。他说,尝尝,不能喝惯这个味?我不喜欢喝啤酒,老伴喜欢喝,我想你也一定喜欢喝。来,碰个杯吧!“咣”一声,碰杯的声音很响。羊吓住了一样,盯着破碎的泡沫出神。王坎坎说,不要不好意思,尝尝,味道应该不错,要不老伴能喜欢喝?快点,尝尝!
羊伸出红舌,舔了一下酒,抬头看着王坎坎。王坎坎说,滋味咋样?是不是好喝?羊舌舔来舔去,眼眯着,很享受的样子。王坎坎高兴地说,咋样,老汉没骗你吧?我猜老伴喜欢喝,你一定也会喜欢,我说得对不对?
羊低下头,舌头灵活地转动着,啤酒下去一大半。王坎坎哈哈笑起来,打趣说,你还真喝酒啊,我没想到呀!要是老伴看到你喝酒,也会美得要命。说完,一仰脖,酒成条直线,钻进嘴巴里,一条火蛇从喉咙直抵胃里。好不痛快!今晚的酒格外香。
“猫头鹰”响了,女儿问道,爸,又在喝酒?王坎坎看着胡须上挂着啤酒沫的羊,呵呵傻笑着。女儿声调高了,跟你说多少次了,不要一个人喝闷酒,就是不听。要是身体喝坏了,喝成个半身不遂,我和弟弟可咋办,能天天照顾你?她说的话和儿子一样,提前商量好了似的。
王坎坎闭眼唱起了京剧《智取威虎山》的经典唱段《打虎上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愿红旗五洲四海气招展,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党给我智慧给我胆,千难万险只等闲……”
咿咿呀呀,他唱的声音不大,却铿锵有力。羊变成了老伴,坐在那里不声不响地看着他。老伴系着红头巾吗?红头巾是他买的,老伴平时不舍得系。王坎坎经常笑嘻嘻地给她系好,老伴害羞地轻轻捶他胸脯。王坎坎说,我就看你好看!老伴说,没羞没臊的,哪里像一个当爷爷的人?王坎坎笑成一只大虾。
女儿在“猫头鹰”里急了,爸,爸,你是不是喝糊涂了?跟你说话听到没有?王坎坎耳朵嗡嗡响,女儿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女儿说,爸,羊咋上了饭桌?你是不是糊涂了?
王坎坎给羊倒酒,哆哆嗦嗦的,酒倒到杯外,流了一桌子。羊歪着脑袋,伸出舌头,舔桌上的酒。王坎坎大着舌头说,哈哈,我看你是喝上瘾了,没问题,酒有,就怕你喝醉了。女儿喊道,哎呀,爸爸,你咋给羊喝酒?人和羊喝酒,传出去讓人笑话不?王坎坎眯缝着眼,抿口酒说,羊咋了?羊不是人?我看羊比人好……女儿生了气,爸呀!我看你真是……怎么说……我和我弟不是你的孩子?王坎坎闭着眼,眼角有泪,女儿却看不到。
“猫头鹰”哑巴了,听不到女儿的声音了。王坎坎心里有点失落,女儿再贴心,离那么远,能陪着他喝酒?羊不会说话,但是能陪着他喝酒。不想这些了,日子反正要过,咋样不是过?闭眼过吧!
来,别客气,大口下……王坎坎举着杯对羊说。
羊腿扭出了麻花,身体左右晃着,脑袋甩来甩去,嘴巴挤出个核桃,哈喇子细长,眼睛半天才眨一下。羊醉了,王坎坎揉揉眼睛,盯着东倒西歪的羊,哈哈大笑起来,指着羊说,你呀,你呀!酒量还没有老伴的大,喝一点酒就醉了,说出去丢不丢人?羊的眼睛越来越小,猛地一瞪,眼珠儿直直地盯着王坎坎,没有恶意,能感觉到温柔、感激、挂念。
王坎坎站起来,一股热血顶上脑门,眼前一黑,差点没站稳。他扶着桌子,呼呼喘着粗气,半天才喘匀了,自言自语地说,不服老不行呀!再年轻五岁,敢和二十岁的小伙儿试试酒量。他摇摇头,两颗浑浊的泪珠儿滚了下来。
羊它慢慢倒在了地上。它肚子膨胀,急剧地一起一伏,好似要炸裂开,舌头吐出,口水流了一地。王坎坎担心羊肚子里的小羊崽会生出来。他头晕眼花,哪能照顾好羊崽?他后悔了,不该让羊喝酒。羊不是人,不知道酒的厉害。若是伤到肚子里的羊崽,他不会原谅自己。他想了很多次,羊崽下来后,是卖掉,还是自己养着?现在有了答案,自己养着,当孩子一样养。
李杰出进门时,王坎坎枕在羊身上,躺在地上睡着了,脸像着了火,通红通红的,呼出的酒气,吹的羊毛要飞起来一样。他脸上浮着浅浅的笑容,在做美梦吗?羊的舌头耷拉着,眼睛半闭着,不知道睡没睡着。
十分钟之前,王坎坎的女儿给李杰出打电话,哭哭唧唧地央求他去照看下王坎坎。看到王坎坎在地上睡觉的狼狈样儿,李杰出心里后悔了,不应该回绝他。王坎坎是个脸皮薄的人,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一般不求人。他和老伴吃过几车的苦,供出了两个大学生。孩子有出息了,却没有一个陪在身边。
叔,你醒醒!李杰出摇着王坎坎,在地上睡觉会生病的,看看你这人,我不是答应考虑一下吗?他又去摇羊的头,羊重重地喘出口粗气,他闻到了酒味。难道羊也喝酒了?这个老头,真是个怪人,能和羊一起喝酒。羊醉酒,他是第一次见。
王坎坎半天才睁开眼,愣愣地看着李杰出。李杰出说,叔,咋能睡在地上?岁数不饶人呀!万一病倒,儿女不得跟着忙活?王坎坎揉揉眼睛,说,是杰出呀!你看看你,扰了我的清梦,好不容易在梦里见到了老伴。老伴走了以后,我还是第一次梦见她。
李杰出“扑哧”笑了,说,叔,你是不是想我婶子了?赶明儿给你介绍个,陪你说说话。王坎坎坐起来,梗着脖子,眯瞪着眼说,不要你介绍,老伴在等我……羊也可以陪我……李杰出说,叔,你喝醉了,现在和你说不清楚,明天再说。
李杰出扶着王坎坎进屋上了床,给他盖上被子。王坎坎忽然坐起来,拉着他的手说,杰出,陪我说说话……李杰出倒完水,他已经打起了呼噜。
第二天一早,李杰出来到王坎坎家里。他正在喂羊,一边投食,一边说,看看我喂的羊,膘肥体壮。过几天下了羊崽,就不是一只羊,是一群羊了,我家的人口就多了,热闹了。李杰出说,叔,你昨晚喝多了?王坎坎放下草料说,我就说很奇怪,早晨坐在羊圈里,敢情在羊圈里睡了一夜?你看看,羊没有精神头呀,难道听我说了一夜的话?
李杰出笑了,能和羊说一晚上的话,真是个可爱的老头。他说,叔,给你介绍个老伴,抽时间过过目吧!另外,你夜里去守大棚吧,我把人搭配一下。
王坎坎问道,你知道羊是怎么生产的?李杰出说,我没养过羊,没见过羊是怎么生产的。王坎坎说,羊生产之前,奶子膨大像球。羊是躺着生产的,大声叫。羊崽生下来,羊会照顾它,舔它身上的羊水,舔干净后,羊崽会站起来找奶头吃奶。知道羊崽是怎么吃奶的?
李杰出说,这个我知道,羊羔跪乳嘛!小羊吃奶时要跪着。
王坎坎说,你说的事不急,等我的羊下了羊崽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