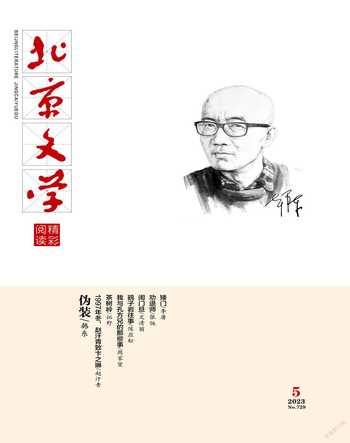我与孔方兄的那些事
周家望
大抵俗物,皆有雅称。孔方兄,就是铜钱的雅称。我的青少年时期,曾与孔方兄有过一段不深不浅的交往。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肇始,百业初兴,集邮、集币曾经热闹非凡。彼时,我一个中学生都觉得:若不躬逢其盛,那就是在辜负韶华、光阴虚掷!厕身其中,淘其宝,探其源,居其奇,方显得自己有文化、有品位。
作为我国安定门内前肖家胡同里唯一的“二百铜钱富翁”,咱也自命不凡了一阵子:遇到街坊四邻屁都不懂的小孩儿,就像那些社会名流一样,下巴上扬,嘴角下撇,眼皮斜视,腆胸叠肚儿,视芸芸如草芥,假装自己特有学问的那种。若是碰上个懵懂的小兄弟,仰着脸用清澈的大眼睛,崇拜地看我一会儿,那“满满的正能量”,搁谁也得飘飘欲仙!我当时想,怪不得谁都愿意居高临下受人瞩目呢,这感觉,搂,都搂不住。
没献成的“国宝”
那段时间,家里的柜子、抽屉、针线笸箩……常开着门儿、敞着口儿,凡是能集纳物件儿的地方,几乎都被我篦过数遍。老辈儿上留下来的铜钱,还真淘出来一大把。其中一枚“宽永通宝”,我认定它极有可能是枚不世绝品。倒不是它的品相特殊,那只是一枚楷书铜制钱,比清钱略薄。古币的断代其实很简单,看年号即可。当然其珍稀程度,要看存世量的大小和品相的成色,物以稀为贵,古币亦然。当时没有电脑或者手机查询,查年号只能翻《现代汉语辞典》附录里的“我国历代纪元表”。奇怪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多少遍,竟然没有找到“宽永”的年号!
这一下子吊起了我的胃口。隔了没几天,我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的“古币收藏”栏目,读到了一篇短文,大意是说,1970年左右,北京房山的一个废品收购站,在废品堆里发现了一枚九叠篆的“皇宋通宝”,是海内孤品,当时就价值10万元人民币。我忽然意识到,那枚“宽永通宝”,大概率也是一件国宝!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作为一名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团組织的初二学生,理所当然应该把它献给国家,让全体人民共同拥有。
怎么献呢?献到哪儿呢?通过老师或学校上交吧,我不大放心:一来不放心他们准能上交;二来担心他们抢了我的功劳。再说,万一这要不是国宝,传出去还不被全班同学笑死?思前想后,左右为难。放学的路上,看见2路车站,我一下子有了主意: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啊!上个学期,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参观过。求人不若求己,干脆,自己把“国宝”送进历史博物馆,那才是最稳当最踏实的。
暑假一放,找个光天化日的中午,怀揣着那枚“国宝”,我上了胡同西口的2路公共汽车,直奔天安门。一路上小心谨慎,“国宝”要是有个闪失,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那还得了!手在兜里攥着“国宝”,潮乎乎的,都是热汗。
下了车,一摸,硬硬的还在。赶紧过长安街,买票进了历史博物馆。高大的博物馆里凉爽无比,我的心情也跟着冷静了一些。先去古币展区核对,万一找到了相同的呢,也不白跑一趟。结果,转了一个小时,也没找到同样的一枚!
这时候,我长出了一口气:看来国家确实缺少这一枚!咱来对了!
我压抑住内心的喜悦,凑过去向展区的工作人员请教。人家很客气,直接把我领到了四楼的办公区。敲开东侧办公室的一扇木门,一位中年女同志接待了我。我表情平静地说明了原委。这位阿姨接过“国宝”看了一眼说:“同学,你这是日本钱,中国年号上是没有。”
啊?日本钱!我脸上也装不出平静了。
“那这是什么年代的?”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国一直都用这个。流入中国的外国钱币,数这个最多。”
当时,我像只泄了气的皮球。曾经的豪情万丈,嗖的一下,没了。壮志未酬的感觉,好一似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好一似冷水浇头怀抱着冰。您说,这搁谁受得了哇!
虽然没能“痛饮庆功酒”,但不幸中的万幸是,“献宝”的事儿,只有我自个儿知道,否则何以见一中同窗、全乡父老?
后来听京戏《游龙戏凤》,正德皇帝说:“有道是,龙行有宝。”李凤姐说:“有宝献宝。”正德皇帝问道:“无宝呢?”李凤姐讥笑道:“看你的现世宝!”
我腾的一下,又想起了我的“宽永通宝”!
跑丢了的秦半两
虽然“国宝”没献成,被孔方兄涮了一道,可也激发起我,与“钱”奋斗其乐无穷的热情。
为了集币,我“五路出击”:一是在家里翻箱倒柜,穷尽每一个角落找铜钱;二是到亲戚家搜罗;三是买来《钱录》《古币收藏》等书籍杂志、剪下晚报上每期“古币收藏”的文章,做知识储备;四是去官园市场、东花市早市、德胜门城楼南侧、琉璃厂古币商店等处淘宝;五是到历博、首博等各大博物馆的钱币展柜前作实物比对。有道是,不疯魔,不成活。我集古币,虽未“成活”,却已接近“疯魔”。
“如金似玉的好年华呀”,同学们都在为“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勤奋学习,我可倒好,掉进“钱眼儿”里,出不来了。
岂止出不来?我还变本加厉地拿着铜钱找班主任切磋去了!
我高中的班主任,是教历史的刘富明先生。他是北京一中20世纪50年代末留校任教的高才生,中等个儿,梳背头,气质儒雅,风度翩翩,从没见他吼过谁、骂过谁,总是那么如沐春风的夫子形象。
有一天,我带了一枚秦代“半两钱”找刘老师看。刘老师说,通过集币学历史,是个好办法。不但对我口头鼓励,还从家里找来一枚品相很好的“乾隆通宝”赠送给我。
我当时虽未受宠若惊吧,心下已把刘老师引为“同道中人”。于是心情不是小好,是大好,好得不得了!放学时分,连跑带颠儿回的家。
到了家,傻眼了:夹在课本里的那枚“半两钱”没影儿了!
放下书包和手里的“乾隆通宝”,赶紧冲出家门一路往回找。找到天黑也没找着,兀自懊恼不已。
过了些日子,又去早市闲逛,发现秦“半两钱”成盒子地在摊上售卖。看书才知道,其实“半两”的存世量颇多,并不稀罕。
倒是刘老师赠予的“乾隆通宝”,我珍藏至今。那可是老师鼓励学生培养兴趣多学知识的一份恩情啊!此恩,花多少钱也买不来。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另一位刘老师——中国交通报的副刊主任刘建斌先生。我和这位刘老师相识于1995年,在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年会上。建斌先生大腹便便、笑口常开,活脱一尊弥勒佛。和他熟悉起来是过了两年,在中国交通报的会议室里,一聊才知道,敢情《北京晚报》“古币收藏”栏目的作者“伍文”,就是他!
“八十年代,您在晚报上发表的收藏知识短文,我可是挨篇剪下来,贴在大本上了。真是相见恨晚呐!”我那个激动劲儿,跟歌迷见着巨星似的。
“哈哈,您也搞古幣收藏啊?”
我脸一红:“可说不上收藏,上中学的时候,迷上了攒铜钱。后来,忙高考、上大学、搞对象、找工作、写新闻……淘宝访币的雅事没了,净剩下眼面前的俗事儿了。”
人生简直就是逗闷子:我集币急得抓耳挠腮的时候,无缘得识“伍文”面;不集了吧,和刘先生却成常见面的好朋友了!
人生更是无常,这两位刘老师前几年都已仙逝。
忆苦思甜的银毫子
老电影《红色娘子军》里有个情节,海南岛贫女吴琼花,受尽恶霸地主南霸天的残酷压迫,决心拼死求生。南霸天为了杀一儆百,让手下把她活活打死。命大的琼花醒过来,遇到了党代表洪常青。洪常青赠给她两枚银毫子当路费,让她投奔红军去。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银毫子”。后来,我从姥姥家也得到过一枚银毫子。我这枚银毫子,是伪满洲国的货币,正面铸着“二龙斗宝”的图案和“壹角”二字,反面铸着牡丹图案和“大满洲国康德六年”八个字,左右双星。双面的内圈都有“万字不到头”的纹饰,外廓光滑无齿。
“康德”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年号。1931年,在日本当局的操弄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初期为“共和”体制,立清朝逊帝溥仪为“元首”,称为“执政”,年号“大同”。1934年,溥仪改称“皇帝”,年号“康德”。“康德六年”就是公元1939年。
记得姥爷跟我说,他早年丧母,十几岁就跟着河北同乡闯关东,在一家营造厂当小工。营造厂,就是现在的建筑公司。后来日本人侵占了东三省,他们就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艰难生活。当时,他一个月的工钱,就是一枚一角钱的银毫子。一个银毫子能买什么呢?“能买什么?能买一身儿里外三新的棉裤棉袄,剩下的钱,还能找个小饭馆,进去改善一顿伙食。”好在营造厂包吃包住,否则光指着这一枚银毫子,还真活不下来。
这枚光闪闪的银毫子,成了我们家痛说革命家史的实物教材。我打算把它传给女儿,让她不能总惦记着吃喝玩乐坐汽车,革命传统代代相传,那才有盼儿。
孔方兄的文化味儿
过去,别看小门小户,谁家里也趁几个旧铜钱。只不过,懂得收藏的微乎其微。那些铜子儿,大致有几种用途,一种是做钉子垫圈,就是木门上、柜子上用来固定铁钉子的垫片儿;一种是做卡子,用来固定卷起的竹帘子;还有一种用途是“辟邪”,这就需要用品相好的铜钱,用红绳穿起来,挂在屋门口或者床头床尾,起到“镇宅”的作用……总之,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失去货币属性的孔方兄,仍旧多多少少发挥着“余热”。
除了丢了的那枚秦半两之外,家里还有两枚“五铢钱”。五铢钱自西汉至隋朝,前后用了七百多年,存世量很大。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写《蜀先祖庙》“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的时候,他已经用上了“开元通宝”。在西城区官园市场,我曾淘换过几枚五铢钱,一对比才发现,家里旧有的那两枚在品相上要逊色不少:口大,肉薄,边窄。被我起下来之前,它们一直在我家的旧木门上充当“钉子垫儿”。如此“明珠暗投”,我怎能不出手解救?拆下来一看,果然上面有模模糊糊的“五铢”字样。于是接着作进一步“清理”,没想到,稍一用力,“啪”,薄如指甲的“五铢”,一分为二,惜乎!我这哪儿是“解救”存活了两千年的孔方兄,简直就是送他老人家上路啊!实实悔之晚矣!
从那儿以后,我对这些千八百年的孔方兄开始小心翼翼地伺候。这一细心不打紧,发现古币里的文化气息和它们的珍稀程度、历史价值同样不得了!慢慢了解到:“半两”钱上的两个字,是出自秦相李斯的手笔;唐初废五铢改铸“开元通宝”,这四个字是“欧字鼻祖”欧阳询的墨宝;“咸丰重宝”四字是清代书法家戴熙所书。宋钱里的名人书法就更多了:“元丰通宝”是苏东坡的行书;“元祐通宝”是司马光的篆字;“太平通宝”是宋太宗赵光义的隶书;“崇宁重宝”“大观通宝”是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书……看着这些“金文”,仿佛历史的距离一下子拉到了眼前:手里攥着这两枚“开元通宝”,兴许就能在长安的酒肆里遇到风流倜傥的李太白?又或者揣着几个“大观通宝”,能在清明时节的汴河上来个“一日游”?还是在西湖边的茶寮内,拍出几大枚“元丰通宝”,请杭州知州苏轼喝杯明前龙井?哈哈,虽然咱没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仙气、豪气,也可以放浪不羁地嘚瑟一番啦!
都说钱有“铜臭味儿”,我咋就闻出了“墨香”呢?
上班以后,与孔方兄的交往,不知不觉地搁那儿了。主要是挣人民币的任务比较艰巨,身无长技,卖字为生,靠爬格子挣钱养家糊口,真是玩不起收藏,对收藏的理解,也异于少年时。那陪伴我度过青少年时光的二百铜钱,倒是没舍得易手或者弃于尘埃,而是买了两个钱币收藏册子,把它们一一入册。偶有闲暇,从小柜子里取出来翻翻,看看它们的旧模样,闻闻老味道,追忆一下早已逝去的似水年华。
窃以为,收藏,对于那些千百年留下的老物件来说,不过漫漫旅途中短暂的小憩;对于寿不过百的收藏者来说,不过是对文化血脉保管、传承的阶段性责任。无论是不见经传的古砖石印旧家具,还是价值连城的晋字宋画唐三彩,藏品流转不断,而藏者接力不止,是为常理。我与孔方兄的缘分,也大抵如此。
收藏,其实就是一份人生情感,不必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不必缠绵悱恻一腔幽怨,有些藏家为了一件藏品,或狂喜,或深悲。在我看来,似乎都大可不必。收藏,和大多数人的人生一样,在平平淡淡中过得长长久久,闲时听雨,闷来看花,以平静而欣赏的眼光,来看待物象,来关照内心,才是至道。
特约编辑 蓦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