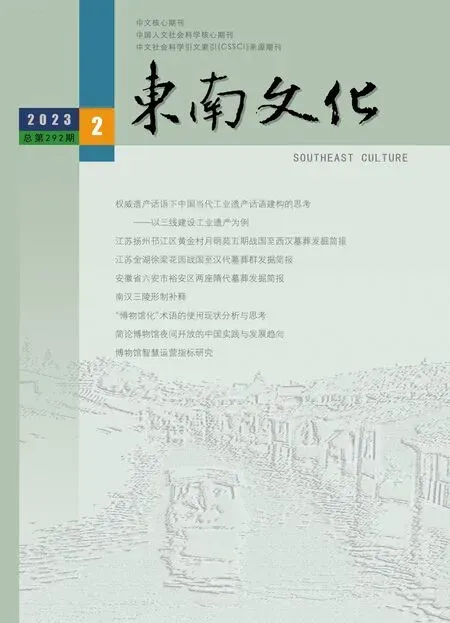权威遗产话语下中国当代工业遗产话语建构的思考
——以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为例
吕建昌 李舒桐
(上海大学历史系 上海 201900)
内容提要:当今在世界遗产研究与实践领域,根植于西方现代史观及价值观的权威遗产话语掌控着遗产的价值与意义阐释权,中国工业遗产的话语声量显得很微弱,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因此面临一些困境。构建符合本土语境的工业遗产话语有助于其摆脱“削足适履”和“丢车保帅”的命运,展现其遗产所凝练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同时三线建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探索,其工业遗产亦是解释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崛起的理想切入点。
当今世界遗产保护领域正盛行一种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理念,以统一的标准影响着文化的多样性,这就是权威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AHD)。它制度化于一系列国际公约,经由官方机构的认证和推行而成为普遍的标准和毋庸置疑的常识[1]。西方遗产观的塑造与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兴起有着惊人的同调性[2],而AHD 正体现了这种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构建的现代史观和文化观,反映了西方文化遗产价值标准的“功能取向”[3]。它排除了遗产概念的不同见解,将遗产的阐释权集中于小部分群体之手。不同国家的遗产本应有着不同的发生与发展轨迹,但在AHD“统摄”全球的遗产话语体系之下,“世界遗产”缓慢演化为西方“精英主义”的价值观、历史观和文化系统内涵的政治、文化输出工具。全世界通用一套标准,遗产被划分为固定的类型和等级,这使得我们的遗产事业很容易陷入两种困境:其一,为迎合国际评判标准而“削足适履”,将未达到“普遍价值”的因素忽视或择出;其二,“丢车保帅”,遗产价值的等级化会使被权威话语认可的遗产因高价值而得到优待,而那些未被权威话语认可的遗产则不得不面对被搁置甚至被忽视的命运。这套标准、这种划分是否适配于我们的遗产?仅依靠这套标准我们能否讲清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与精神?显然不能。因此,我们需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遗产话语体系,推动中华文化和遗产走向世界、面向未来。
一、AHD 体系下的西方中心主义观
现行的文化遗产学发源于欧洲人历史意识和民族主义的觉醒。为了凝聚人心,“民族主义叙事”被国家政体赋予文化合法性,而支撑这一叙述的重要支点就是保护过去的物质证明,因此,遗产话语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话语本质上是相似的,它们都体现着一定社会阶层的体验与审美观念[4]。19世纪的欧洲在世界范围内占据强势地位,其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也逐渐成为全世界的遗产话语,规范欧洲乃至全球的遗产实践活动。欧洲通过一系列话语构筑起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我们”(self)和一切非西方的“他们”(the other)相对立的世界:西方有自我表述的能力,并借由权力表述、建构出了一个“臆想”中的东方;而东方则因缺失这种表述和建构而“长久地处于静寂和危险状态”[5]。
在西方中心主义观下,东方的历史和传统时常被有意或无意地误解,其遗产的价值阐释也无法得到正确的表达,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东方文化对自身的反思也因此受到影响[6]。文化习惯如果全盘接受由西方所制定的话语,会使我们陷入一种险境——以西方的价值观来看待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7]。当我们不再以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无私奉献为荣,转而推崇享乐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时,我们便很容易陷入民族自轻的陷阱中。在如今多极、多文明的世界中,文化能回答人们对“我是谁”的追问与反思,身份认同与归属感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塑形与巩固[8]。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明确提出了两个“加快”,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以便凝聚人心、汇聚民力、促进民族认同、加强文化自信,同时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形成同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9]。
AHD 的重要影响之一在于它通过赋予遗产某种价值界定了“何为遗产”“为何要保护遗产”以及“如何保护管理遗产”等问题,其权威性通过官方组织对国际和国家层面的一系列遗产政策施加影响而不断被强化,并以其强大的媒体宣传引导着国际和国家层面的遗产实践活动。从《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Athens Char⁃ter)、《威尼斯宪章》(Venice Charter)到《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以下简称“《公约》”),受保护对象从“具有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的纪念物”拓展到“具有巨大内在价值的”或“随时间流逝而具有文化或自然价值的较为一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遗产的价值也被逐渐塑造成具有共享意义、支撑集体感的文化价值,甚至是“旨在人类发展”的“普遍价值”。从语义上看,这些文件的相关叙述将“来自文明背景的”与“较为一般的”相对比,虽然二者都是人类重要且宝贵的财富,但显然重要性的来源不同——来自“文明”的物品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AHD 认定其具有巨大内在价值,而“较为一般”的物品的全部价值与意义则取决于其经历的时间足够久远。后启蒙时代的西欧认为自己的文化已进化到一个高峰,这里所谓的“来自文明背景的”实际上等同于“来自宏大的西方背景的”[10]。这种观念延伸到工业遗产保护领域时,所谓的“文明背景”自然要与工业革命相联系。
被视为工业遗产保护领域最权威的国际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和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TICCIH)制定的指导性文件《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The Nizhny Tagil 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以下简称“《下塔吉尔宪章》”)以及之后出台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联合准则:工业遗产、构筑物、区域和景观的保护》(Joint ICOMOS-TICCIH Principles for the Conser ⁃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s,Structures,Areas and Landscapes,以下简称“《都柏林原则》”)在界定工业遗产的定义时都强调了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从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开始直到今天都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历史时期”,此前的“前工业阶段”工业遗存当然也具有研究价值,但研究的重点要放在“和主要工业阶段的渊源”上[11]。“过去两个世纪的工业化全球进程是人类历史的重要阶段”,它“使得其工业遗产对于现代世界变得尤为重要和关键”。2012年TICCIH 发布的《亚洲工业遗产台北宣言》(Taipei Declaration for Asian In⁃dustrial Heritage)中,也强调“亚洲工业遗产的许多关键元素是由殖民者或西方国家引进的”,只有那些“来自文明背景的”亚洲工业遗产才具有内在价值[12]。这种关于工业遗产内在价值及重要性的观点实际上一直反映在世界遗产的评定中: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World Heritage List)的75个工业遗产中,半数以上来自西欧,其中发达国家的工业遗产多与工业革命相关联,那些最早的、能反映启蒙运动气息的、代表行业最高科技水平的、保存最完整的“最”字辈工业遗产则特别受到青睐;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遗产则以工业革命之前反映本国工业活动或工艺特色为主[13]。“具有西方背景的”——更具体来说是“与工业革命有关的”成为划分“文明”与“朴实”、“现代”与“传统”、“先进”与“原始”的分水岭。2015年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是以亚洲首个成功移植西方工业化的表征而入选的,“代表着工业化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的第一次成功转移”[14]。
《公约》提出“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概念,在《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中指出《公约》的目的不是“保护所有具有重大意义或价值的遗产,而只是保护那些从国际观点看具有最突出价值的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所描述的是“罕见的”“超越国家界限的”“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的”[15]。它诚然体现着人类社会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但同时更反映着以西方中心论为内核的“普遍价值”——西方自视为现代文明的起源、现代世界进步的引领者、现代文明意义与价值的界定者,其价值取向和思维路径理应成为自然与社会遵循的普遍法则,在考量不同文化、历史传统、制度模式、价值理念时赋予其普遍意义。中国政府就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产”申遗问题明确指出,日本为宣传西方工业化向非西方国家传播的功劳,刻意避而不谈明治工业遗产中“有多处遗址在二战期间使用了中国、朝鲜半岛和其他亚洲国家被强征的劳工。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至今尚未被彻底清算。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公约》促进和平的宗旨与精神,“将向国际社会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值得深思”[16]。
AHD 通过合理化、科学化、系统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技术问题赋予遗产美学与科学价值,同时也是为了掩盖其文化与政治作用。一直以来,“普遍价值”都在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鼓励那些社会追随西方制度与文明进行合法性辩护,并将其抽象化成客观而普遍的“自然状态”或“自然秩序”,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知识体系由此构建并成为其意识形态的基础[17]。AHD 使这种“普遍价值”延伸到遗产保护领域,坚持“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诸多遗产政策在其实施过程中,实际上是在保护并传播着西方国家特定的价值观与文化意义。
二、AHD 体系下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困境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所面临的问题归根究底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判断主体、情景、标准的不同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西方主导话语权的国际社会组织与遗产所在地的本土国在价值判断上的矛盾正说明了当前AHD 所推崇的这种“普遍价值”实际上是很难成立的。它将文化遗产保护上升到超越民族、阶级、国家矛盾的高度,使之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但遗产保护工作的主体仍集中在少数群体[18]。诚然,AHD 在一定时期有过积极作用,但长期来看,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内核依旧是引发矛盾的根源:首先是部分遗产为了迎合一系列世界遗产标准而矫饰其过去,使其文化灵韵遭到消蚀[19],遗产与个人情感、经历、记忆的连接也被随之掩埋;其次是AHD 语境下对遗产进行价值判断的“权威”与遗产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由于文化差异而引发的价值观分歧。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所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在于:在AHD 语境下,“具有工业革命背景”或“足够古老”成为评判各国工业遗产的重要指标,而三线建设作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开展的以备战为中心,以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设施为基础的大型经济建设活动,既没有体现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技术转移,年代上又不够久远,又因涉及关键技术和国家机密而无法被完整展示,遑论大量厂房设备遭废弃已称不上“恢宏”,其文化意义与价值不能契合AHD 所推崇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其物质存在也不符合AHD 对物质性的偏爱。然而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可贵的并非一砖一瓦、一钉一铆,而是浓缩在其中的民族精神,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与西方在个人权力上追求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是截然不同的,也是秉持着西方中心主义观的国际“权威”所不能理解的。这使得它“走出国门”变得愈发困难,这也是大多数中国近现代工业遗产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一。
其次,AHD 强调“普遍价值”,它虽然统一了遗产管理与保护的标准,但也同时使标准之外的遗产陷入被无视的困境。1985年中国加入《公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由此与世界接轨[20],也同时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这套标准,并愿意以此重新定义、评判本国的遗产资源。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曾因此陷入了被忽视的险境:它作为当代工业遗产,年代上晚于我国的“苏联援建156 工程”,更比不得都江堰、大运河的历史悠久;历史评价方面,三线建设曾一度被视为当时国家对外敌入侵预判失误的产物[21],又因涉及关键技术和国家机密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被官方宣传,这导致其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使得部分厂房、设施被变卖,还有一些遗存则濒临废弃与损毁。虽然如今这种状况已被部分扭转,但已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难以挽回的。
此外,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另一重困难来自AHD 直接界定了哪些人可以称为过去的合法代言人,它对某些重要个体、群体的忽视将直接影响地方感的激活。《下塔吉尔宪章》明确提出,“经过鉴定认为是重要的场所和建筑结构应以立法的方式予以保护”。“政府要拥有对工业遗产保护和维护能提供自主意见的专家咨询库”,要“在所有重要问题的处理上认真倾听他们的主张”;“由志愿者组成的协会、社会组织在遗址的鉴定,促使公众参与保护和传播信息以及调研中将扮演重要角色”[22]。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专家在遗产重要问题的处理上更具合法性与权威性,当地社群和普通大众扮演的则是参与保护者的角色,对遗产的相关活动的决策走向的影响相对有限。在“遗产是什么”“遗产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上,不同个体、群体的理解和评价是不同的,这将直接决定其地方感能否被成功激活[23]。诚然,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价值阐释工作在国内开展良好:既有西方的工业遗产案例作为参考,又有专家的学术研究护航[24],还有三线人主导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实践活动做宣传,四川攀枝花兰尖煤矿社区的“兰尖故事”博物馆、成都莲花社区“川齿记忆”(社区博物馆)等的创立都是三线人努力的成果,这是为打破AHD 桎梏、扩大价值判断主体而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与普通个体的链接并未被完全激活,公众仍是遗产信息的被动消费者:他们被AHD 引导和指示,尚未主动参与到整个遗产的建构、阐释过程中,民众的力量尚未被充分调动。
价值判断是主体基于过往经验的理性思考,遗产阐释问题是公众参与历史、认识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参与和沉浸才能带来切实的认同。一台设备、一座工厂哪怕经受了时光的摧残被废置、被损毁,它仍是设备、工厂。但当它活在某些人的个体化体验中时,它才实际上成为“遗产”,其内涵深深根植于生产生活、语言等事物的展演中、口述史和传统民俗的传承中、经历者的回忆中,只有在价值判断主体与遗产的互动关系(如公众的实际体验)中才能不断更新、代际传递、焕发新生。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不仅仅是国家的、专家学者的以及三线建设者的,更是当代乃至后代普通大众的。如何让公众在一砖一瓦、在或废弃失修或仍能运转的钢铁机械间、在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普通符号间,认识三线建设的意义,相信他们也是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主人,也肩负着保护传承它的责任,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三、AHD 下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话语的建构思路
三线建设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于备战需要,建厂选址以“靠山、分散、隐蔽”为原则,大多数工厂都建在远离城市的偏僻山坳。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三线企业进入军转民的“调整改造”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三线企业遇到生存发展的重重困难,被迫从深山沟里搬出,迁到城市或城市近郊。搬迁后留在原址的大量厂房、生产车间与仓库、设施与设备、办公楼以及生活服务类建筑和职工住宅等,除了少数为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等利用外,大多数长期被闲置或荒废。这些物质遗存“是离我们最近的遗产”,是三线建设最直接的历史见证,承载着成千上万三线人燃烧岁月,在西部这片热土为“让毛主席睡好觉”而忘我工作、艰苦奋斗,追求美好青春理想的记忆;也承载着我国在面临外敌入侵的严峻局势下,党中央作出建设我国西部战略大后方的伟大决策,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开展三线建设的顶层设计的宏观记忆。
1.作为话语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
遗产作为一系列价值和意义的动态集合,是身份认同的符号表征,在民族主义背景下诞生的遗产话语则将这种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高度联系在一起。英国铁桥峡谷(The Ironbridge Gorge Site)和布莱纳文工业景观(Blaenavon Industrial Landscape)因其表征着英国工业革命而被保护和宣传,其动机大多是为了提醒英国公众“这些才是代表国家认同的正统”。在国家话语这一层面上,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与前者有一定相似性:通过这些三线建设时期遗留下来的工业遗存,我们能了解中国当时的工业技术水平、工人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当时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因此它表征着“三线建设”那段历史——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在我国西部地区开展的一场规模巨大的、以国防军工建设为核心的经济建设[25]。更具体的,它呈现着当时中国的工业与科技发展水平和极为不平衡的工业布局,亦表现着中国工业化由东部沿海城市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的历史变迁过程。同时,它还暗示着当时国内与国际波谲云诡的环境:在内,台湾方面时刻准备反攻大陆,而大陆刚经历过连年战乱和自然灾害,亟待休养生息、稳步发展;在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加紧了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围追堵截,中苏关系逐渐恶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战争威胁宛如一把把悬于中国头顶的利剑,没人知道它何时坠落打破这来之不易的和平。这样的备战环境和平衡沿海与内陆工业分布的需求决定了其发展内陆以及“靠山、分散、隐蔽(进洞)”“大分散、小集中”的建厂选址与分布原则,这样的原则也决定了三线建设的条件之艰苦、任务之艰巨、时间之紧迫。正因如此,才更显得三线人的付出与拼搏是多么难能可贵。在物质高度匮乏的大环境下,正是靠着坚定的革命意志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无数党员和群众、各条战线的工农商学兵与知识分子,历经磨难仍不改初心。如今,这些伫立在深山里、荒漠中的工业遗存——无论其破败与否——无不在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峥嵘岁月。透过这些历史信息,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背后所蕴藏的价值内涵也渐渐浮现:一方面,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次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的中国创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是“自鸦片战争后至那一时代我国工业建设的最高成就”[26],并由此延伸为中国摆脱苏联、走上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表征;另一方面,它彰显着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中华民族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勇于创新的民族精神,亦是集体主义精神的具象体现,并可以延伸为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与红色基因的内核[27]。
除了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价值还体现在三线人这一微观层面。任何物质遗产都是过去的物质表征,而过去则由地方感、归属感、社区感所代言。三线建设亲历者是其过去的合法代言人,三线企业原址则被解读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和归属,更多通俗的、不起眼的小物件——三线建设者用过的水杯、阅读过的书刊杂志、获得的奖状奖杯等也随之被纳入“遗产”的范畴。普通符号和日常活动除了能不断地“标记”或提醒人们国家认同的内涵,还会激发个体和集体记忆,群体再通过共享的记忆建构其集体认同。如今散居在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亲历者(包括其二代、三代)仍会自发地相聚于三线厂遗址追忆往昔。原址的空置、废弃、残破改变不了它是三线人“第二故乡”的事实,三线人通过守护、珍视他们的过去而感到荣光并获得精神慰藉,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一些三线人因为退休生活待遇欠佳而产生的失落感。
除此之外,文化意义也流动于公众之中。“遗产是一个文化过程”[28],它通过一些实践活动被创造,在这些活动中,个体与遗产邂逅,并加入价值的建构与阐释过程中。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被开发为三线遗址公园、三线建设博物馆、三线军工小镇等形式各异的旅游目标物,为公众提供体验感和沉浸感。因为记忆不是物件,无法像长辈给晚辈留下传家宝那样简单地由这一代人交予下一代,它需要依附在具体物上,并借助纪念、仪式、交流等记忆过程在代际间重铸。因此,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实际上成为公众获取或参与历史的方式,公众不是任由权威话语灌输信息的“空瓶子”,而成为构建文化意义的主动参与者,他们在感同身受中找寻共鸣、唤醒那份刻于骨血之中的遥远记忆,从而生成并强化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
2.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话语特色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是中国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话语亦是中国特色遗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话语特色的剖析亦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遗产话语的建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实践较西方起步晚,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AHD 的影响。目前在国际遗产界,AHD 掌控在西方手中。一方面,AHD 体系在促进世界遗产认识与保护方面有其积极意义,它使我们的遗产保护管理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另一方面,在AHD下,西方的价值观凌驾于别国的价值观之上,排除了其他文化群体的体验,西方中心主义的内核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历史观、价值观的差异始终存在。如果仅遵循西方的规则而不考虑这种差异,我们便无法准确地展示自己,遑论讲好中国故事。因此,我们要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文化特色——既反映本民族特色,又能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的“普遍价值”,要从规则的追赶者、适应者转变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和引导者,构建一套彰显中华民族文化观、价值观,展现中国特色的工业遗产话语体系。
所谓特色,即是“有人之所无”,而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特色在于其所凝练的三线精神。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探索,三线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其遗产的历史、科技、社会价值无不包含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记忆,从备战时期的军工生产到改革开放时期向民品生产的转型历程,也道明了党和国家的坚持——无论是最初为了国防安全和国内工业布局而发展重工业,还是后来为科技创新、改善民生而转型,中国的发展从不以发动战争、殖民掠夺为手段和目的,而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恰恰力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关注民生的重要特征。
人是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核心要素,三线精神是其价值阐释的重点。透过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我们得以了解三线人乐观顽强的奋斗精神: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成千上万有志者舍弃繁华奔赴蛮荒,在几乎不可能通铁路的西部大裂谷建设成昆铁路,在方圆仅2.5 平方千米的荒山台地上(“弄弄坪”)建设“微型钢城”——攀枝花钢铁基地,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贵州六盘水建设“江南煤都”,在苍穹荒漠上建设核工业基地,在峡深湍急的江流中建设水电站。一些人因此而献身——为铁路架桥、打洞的铁道兵和民兵,为建设煤矿而遭遇塌方、瓦斯爆炸等险情的煤矿工程兵,为保护油井而奋战烈焰的四川石油管理局32111 钻井队,带病在工作岗位献身的好干部亓伟、陶惕成和劳模韩世芳、李忠祥……[29]。三线精神与“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延安精神”“长征精神”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抗争与自强原本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底色。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直观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智慧、信仰与品格,凝结了当代中国人最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也恰恰证明了集体主义宏大叙事与个体追求理想、实现人生价值是相互成就的。如今,当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冲击着我们的价值观时,当个人理想濒临崩塌时,它能给人以启示与鼓舞,在弘扬革命斗争精神的同时滋养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
因此,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话语的特色在于“三线精神”,讲好“三线精神”是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话语建构的核心。以小见大,结合实践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是构建中国特色工业遗产话语乃至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必要前提。
四、结语
AHD 经由国际组织和文件掌握了遗产的价值与意义阐释权,其前置性文化逻辑深刻根植于西方现代史观及价值观。受此遗产话语的影响,三线建设工业遗产难以“走出国门”,也曾在国内遭遇“冷遇”,现在还面临着促成普通公众自觉、自发地投入遗产事业的问题。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工业遗产话语建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三线精神是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特色所在,亦是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话语建构的核心,对民族精神作出适应实践和时代需求的解读是构建中国话语的前提。如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一套自己的话语与世界平等对话,告诉世界中国为了什么、依靠什么从一穷二白发展至今,中国人民何以愿意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若要讲明白这些,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是一个理想的切入点:工业与科技的创新与崛起、社会发展的困难与探索、与自然环境抗争的勇气、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品格、万万中国人的奉献与担当,全都凝结于此。
江苏扬州邗江区黄金村月明苑五期M12及出土陶器

1.M12发掘现场(西—东)

2.鼎(M12∶9)

3.盒(M12∶14)

4.壶(M12∶11)

5.豆(M12∶4)

6.杯(M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