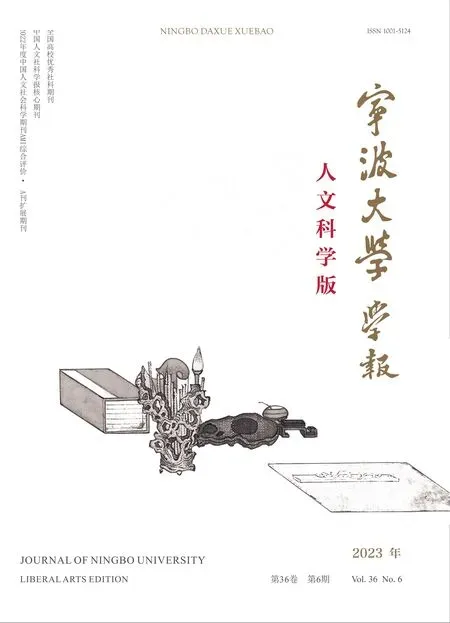张九成之诗学体系及其儒学支撑
左志南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0)
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号无垢居士,又号横浦居士。“其先开封人,徙居钱塘。绍兴二年进士第一人,授镇东军签判,历宗正少卿,兼侍讲,权刑部侍郎。忤秦桧,诬以谤讪,谪居南安军。桧死,起知温州,丐祠归。卒,赠太师崇国公,谥文忠。”[1]924张九成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即问学于杨时,其学术思想的一大特点即是极为重视实践的意义,强调理论的探求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修养工夫中,其《客观余〈孝经传〉感而有作》中曰:“如何臻至理,当从践履论。”[2]296《题晁无咎学说》曰:“学不贵于言语,要须力于践履。践履到者其味长,乃尽见圣人用处。古之人所以优入圣域者,盖自此路入也。”[2]430对自我践行的高度重视,是张九成的理学思想一以贯之的主线,而诗歌创作则承载着书写日常修养之“践履”心得的作用。儒学修养对张九成诗论及具体的诗歌创作影响甚巨,使其诗论及创作呈现出了鲜明的特点。张九成现存《横浦集》《横浦心传录》及《横浦日新》中论及诗歌创作处甚多,张九成对诗歌的论述涵盖了诗歌本质的阐述、诗歌书写内容的界定以及诗歌功能的探讨,这三部分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诗论系统。张九成之诗论在汲取同时代江西诗派理论的同时,又本自其理学理论提出了自我见解,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诗论框架。
历来论者多关注张九成《孟子》学、《书》学、《中庸》学等儒学思想。论者对其儒学思想及在宋代学术发展史中之影响与地位论述颇深,但对张九成儒学思想支撑下的诗学思想少有问津。或有少数涉及其诗歌之研究,亦只是从文学层面关注其贬谪心态与文风,而忽视了其人格修养、生命体验、审美趋向及诗歌创作浑融无间的体系性。寻绎并揭示张九成儒学思想支撑下的一以贯之的诗学体系,不仅有助于补足张九成研究中所缺失的重要一环,亦可从此角度窥见两宋之交诗学观念转变的风向。
一、准则《诗经》,踵武东坡——师法对象的提出与诗歌体裁的选择
张九成认为诗歌应是作者性情之正的书写,《横浦日新·诗》载其言曰:“古人作诗所以吟咏情性,如三百篇是也。后之作者往往务为艰深之辞,若出于不得已而为之者,非古人吟咏之意也。”[3]252张九成一方面认为诗歌的本质是主体性情之正的展现,《诗经》即是如此;另一方面,他指出苦心为“艰深之辞”是不可取的创作态度,因为这会导致诗歌书写内容远离主体之真性情,而沦为虚假的修饰与言说。因此,从创作的角度而言,诗歌不是有意为文的产物,应是主体性情之正的自然流露。其《读梅圣俞诗》中抨击后代之诗时说:“后辈亦有作,岂曰不冥搜。雕琢伤正气,磔裂无全牛。”[2]298其《庚午正月七夜自咏》中亦曰:“文不贵雕虫,诗尤恶钩擿。粗豪真所畏,机巧非予匹。”[2]299
在对雕琢之创作方式提出批评的同时,张九成又用《诗经》作为藻鉴前人诗歌的标准,彰显了其师法《诗经》的主张。其评陶渊明诗曰:“文字雕琢则伤正气,作诗亦然。如陶靖节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此真得三百篇之遗意。”[3]253其赞王粲曰:“王仲宣赠蔡笃有‘瞻望遐路,允企伊伫’,又有‘虽则追慕,予思罔宣。瞻望东路,惨怆增叹’之语,又有‘中心孔悼,涕泗涟洏。嗟尔君子,如何勿思’之语,大有变风之思,杂之《卫》诗中,何有不可。”[3]252又赞刘桢曰:“刘公干《赠从弟》二诗,兴寄幽雅,有国风余法。”[3]252在论及前人诗什缺陷时,张九成亦以《诗经》作为标准:“宣远咏张子房诗有‘息肩缠民思,灵集鉴朱光。伊人感代工,聿来扶兴王。’又曰:‘爵仇建萧宰,定都护储皇。’又曰:‘銮旌历颓寝,饰象荐嘉尝。’又曰:‘飧和忘微远,延首咏太康。’此等诗句皆刻画,殊无三百篇风致。”[2]252上述所列诗句皆生涩拗口,与之前所举之陶渊明诗、刘桢诗之文从字顺大相径庭。将以上两则论诗语录相对比,其诗学宗尚可谓不言自明。而张九成关于其学诗有得的论述,则从正面昭示了其师法《诗经》的事实:“予友施彦执读杜诗,至‘风吹客衣日杲杲,树搅离思花冥冥’而有得。予读毛诗,至‘絺兮绤兮,凄其以风’而有得。”[3]253张氏举友人学杜诗有得与自己学《诗经》有得相类比,正彰显了其多师法《诗经》的事实。不难看出,张九成认为诗歌应是主体性情之正的自然流露,应以《诗经》为师法对象,以妥帖自然、文从字顺为诗美追求。
此外,《横浦日新》中载张九成所评论之诗歌,五言古诗十一首,七言律诗二首,五言律诗一首。同时,其文集中存诗四卷,其中五言古诗三卷,五七言律诗、绝句一卷。五言古体所占比重较大,这一现象不容忽视,因为体裁的选择往往与一定的审美趣味相关联,而张九成对五言古体的热衷,既与其远绍《诗经》的诗学旨趣息息相关,又有着宗法元祐诗歌的因子在内。对《诗经》的重视与极度的熟悉,不可避免地使张九成对诗歌抒写自我心志以达到心理平和的功用极为重视。而张氏所言学诗有得的“絺兮绤兮,凄其以风”,出自《诗经·邶风·绿衣》,亦是独白性质较为显著的一首诗作。这彰显了张九成极为重视诗歌表白心志的作用,重视诗歌可以通过书写心志以使心理归于平和的功用。
在宋代诗学背景下,诗人所探讨的炼字、对偶、用事等等大多是针对律诗创作而言。这些因素与律诗本身固有的格律及用韵限制,使得诗人的创作自由度相比于古体诗受限较多。故而与律诗相比,古体诗相对更容易实现心志表白的功用。同时,五言古体诗在写作传统中形成的追求古拙的审美特点,与七言相比更接近于《诗经》的表述方式。上述因素与五言古体成为张九成所偏好之诗歌形式关系密切。究其原因,既与张氏诗学宗尚有关,又与其特殊人生经历有关。长年受到政治迫害身居贬所的人生经历,使张九成惯常于诗歌中表白心志,以此来缓解因贬谪而产生之心理压力,坚定自我信念。贬所的僻远造成了其交游面的缩小,使其诗歌独白特质鲜明,其《竹轩记》云:
子张子谪居大庾,借僧居数椽,阅七年即东窗种竹数竿,为读书之所,因榜之曰竹轩。客有见而问焉曰:“耻之于人大矣!今子不审出处,罔择交游,致清议之靡容,纷弹射而痛诋,朋友摈绝,亲戚包羞,远窜荒陬,瘴疠之所侵,蛇虺之与邻。谓子屏绝杜门,蔬食没齿,髠头唶舌以祈哀于朝廷,而抱病于老死。不是之务,乃种植垦艺,造立名字,将磅礴偃息,自适于万物之外,知耻者固如是乎?”[2]411
张九成通过虚拟之客的发问,形象地描述了谪居横浦时交游断绝、翛然独处的生活状态。于恕《横浦心传录》亦载有张九成谪居南安时自述之语:“予平生性又不喜游,然终日闭户,倚柱著书度日。”[4]184长年谪居交游断绝的生活状态,使张氏表白心志的咏怀之作较多。尚永亮先生指出:
古体诗是独白方式的最佳载体。与近体诗相比,古体诗无严格的格律限制,无须过度地雕琢刻画,诗体可长可短,自由灵活,最便于抒发深沉、复杂的思想感情……换言之,过于短小的近体诗难以承载子厚极复杂丰富的感情郁积,而其对形式格律的多般讲求也必然会构成痛苦情绪直接抒发的某种障碍。于是,选择较少形式限制的古体,自说自话,抒怀写心,借以减轻精神的苦闷,遂使得古体与独白在这一层面针芥无违地吻合到了一起。[5]55
尚先生之论虽是针对柳宗元而言,但同样适用于张九成。贬谪的经历造成了其交游面的急剧缩小,情感的淤积则使张九成极为重视诗歌抒发心志的功用。远绍《诗经》的诗学旨趣,则又造成了张氏崇古的诗学特点。这些因素遂使张九成的诗歌五言古体诗创作较多。
除此之外,张九成推崇苏轼,学习苏轼古体亦是其偏重五言古诗创作的一个原因。与当时理学家对苏轼之学颇多批评不同,张九成对苏轼之学问人品极为推崇,甚至在其《尚书》研究中直接援引苏轼之论,如其论《胤征》时称赞苏轼曰:“东坡按《史记》及《春秋》传晋魏绛、吴伍员所说,以见征羲和出于羿擅国政之时,非仲康之意,其说详明,信不诬矣……读书如东坡之见,可谓过人矣。”[2]330其论《尚书》时,引苏轼之说有数十条之多,各引程颐、张载之说一条,而其他诸儒之说则并未明确引用,由此不难看出张九成对苏轼的推崇。相同的贬谪经历,使张九成对苏轼的理解更深一层。苏轼诗歌数量众多,各体兼备,尤其擅长古体创作。张九成对苏轼诗歌的学习,亦集中在了对苏轼古体诗的规模追步上,具体的表现即是对苏轼诗歌的次韵追和。张九成《横浦集》中存有张氏次韵东坡之作六首:《鲁直上东坡古风坡和之因次其韵》二首、《读东坡谪居三适辄次其韵》三首、《读东坡叠嶂图有感因次其韵》一首。除此之外,张九成现存诗文集中并无追和他人之作,由此可以看出其对苏轼的倾心与追慕,亦可以见出其对苏轼诗歌的关注较多体现在了古体诗上。
张九成贬谪的经历造成了其诗歌倾向于自我表白,而其远绍《诗经》的诗学旨趣则使其表现除了崇古的诗学追求,其诗歌创作偏重五言古诗。他对苏轼诗歌的推崇与学习集中在五言古诗上,这也是其诗歌偏重五言古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二、践行孝悌,强调力学——诗歌书写内容的界定及其与诗歌境界关系的论说
诗歌中所流露的性情之正应如何体现,张九成亦本自其理学思想进行了界定,认为性情之正应是主体悟得儒学“至理”之后的外在表现。其《客观余〈孝经传〉感而有作》曰:“如何臻至理,当从践履论。跋涉经险阻,冲冒恤寒温。孝弟作选锋,道德严中军。仰观精俯察,万象入见闻。不劳施斧凿,笔下生烟云。”[2]296诗歌应是“至理”的外在表现,而如何臻于“至理”之境,则应是从孝悌等伦理观念的切实践行做起。臻于“至理”,则无意为文而文自妙,即“不劳施斧凿,笔下生烟云”。《读梅圣俞诗》中,张九成在抨击后学之诗失于雕琢的同时,亦指出了后代诗人之所以不能达到梅尧臣之高度,也在于后人未能达“理”:“堙郁暗大理,矜夸堕轻浮。”[2]298其《祭吕居仁舍人》中写道:“圣学不传,何啻千载。吟哦风月,组织文字。转相祖述,谓此极致。正心修身,不复挂齿。孰如我公,师友渊源。文以宣之,诗以咏之。”[2]433张九成称赞吕本中诗文是其高妙精神境界的外在表现,而其高妙境界则是通过理学正心修身等修养工夫所达到的。他的这一观点在《书吕秀才文后》中阐述得最为详细:
文之难久矣,而子之用意不苟,则是欲工其文也。然工其文而不工其意,则固无取于其文。有人焉濡笔布楮,握管下注,以俟喙之出,意迫句窘,则又耳听目剽以幸其成、求其所谓,则牵合散断,脉络不贯,枝分体异,且欲收拾以为一物得于自者,未有不窃笑为戏,此病于工文者之过也。今吾子方且修于身孝于家而得称于宗族乡党,则是子工于意者密矣。工于意者密,则唯意所寓。凡详复而温醇,畏内而舒外者,吾知其得于身也;气和而下,礼曲而缓者,吾知其得于家也;不必而不失,不扬而不坠,不洁而不污,以自适其适者,则知其得于宗族乡党也。是以言不求备而自备,其体昭然。如世之用物可以长久而不废,则古人所谓“行有余力可以学文”者亦以兹欤。文而不为用于世则已,果为世之用也,则用之者必知之,知之者必好之矣。求唯知者之好,则无废其工。故身也、家也、宗族乡党也,可以曲尽其意焉,而吾知唯子之好者必亟矣。[3]207
张九成认为欲工文必先工其意,而工其意则应首先做到“修于身”“孝于家”“称于乡党”,即切实践行孝悌等伦理观念。通过长时间践行与操持,主体自然会达到从容中道的境界,其气质必然庄重平和,举止必然和缓闲雅,故发而为言则必然迥异流俗、高妙典雅。总之,性情之正应是主体内在修养充盈的必然结果,是体味到儒者之道而能践行不渝的崇高操守。
在会得“至理”达到性情之正对文学创作具有决定作用后,张九成还指出了文道相长这一规律,认为学者应注重读书治学与会得“至理”、从容中道的相互促进作用。《横浦心传录》载:“或问:‘学文者多矜,学道者多退,理欤?’曰:‘文至退处,学方有趣,不独道也。然文外又安得别有个道?’”[4]193不难看出其文道合一且递相促进的见解。所以谪居南安时,张九成携册读书,终日不辍,其曾自述:“予老居烟瘴,亲故相绝,赖有文字为乐。”[4]220《横浦心传录》亦载:“或问:‘先生每日耽看文字朝夕忘倦,寝食俱废,颇近乎癖矣。’先生曰:‘使无味亦何必看?吾每看文字但觉其中有味,故所以忘其他。’”[4]192张九成极为重视读书对于精神修养的重要作用,对于读书方式论述甚多。《横浦日新》“涵咏”条曰:“文字有眼目处,当涵咏之,使书味存于胸中,则益矣。韩子曰:‘沈浸醲郁、含英咀华。’正谓此也。”[3]249《横浦日新》“论语”条曰:“凡读《论语》,当涵咏其言,然后有味。”[3]240其所谓“涵咏”即是强调在反复阅读中,获得自我独特的体悟与见解,这样才能实现对古人之意的深刻领悟,进而促进自我修养的进步。故而,张九成又强调在贯穿博取的同时需要形成自我见地。其于《孟子传》卷三《梁惠王章句下》中曰:“学者之观圣王不当泥于一语,局于一说,当取先王之书贯穿博取而读之,必合于人情乃已。”[6]259其所谓“必合于人情”,即是强调读者从自我涵养道德的角度出发,在读书中得出自我见解。《横浦心传录》卷中曰:“或问:‘观文字如何观?’先生曰:‘先自家于所观事理中具一见,不可随其语去,恐古人亦有见不尽处,亦有用意深处,意在语外,则不为语夺。’”[4]192亦是强调读书贵在能有所得。读书有所得,方能获得对世界、人生的深刻认识,方能促进修养境界的提升,由此才能使文章议论超越流俗。《横浦日新·观史之法》曰:“如看唐朝事,则若身预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当时在朝士大夫,孰为君子,孰为小人;其处事,孰为当,孰为否,皆令胸次晓然,可以口讲而指画,则机会圆熟,他日临事必过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当蓄之于心,以此发之笔下,则文章不为空言矣。”[3]251《横浦日新》“文集”条亦曰:
书犹麹蘖,学者犹秫稻,秫稻必得麹蘖,则酒醴可成;不然,虽有秫稻,无所用之。今所读之书,有其文雄深者,有其文典雅者,有富丽者,有俊逸者,合是数者,杂然列于胸中而咀嚼之,犹以麹蘖和秫稻也。酝酿既久,则凡发于文章,形于议论,必自然秀绝过人矣。故经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观也。[3]240
因此,读书当反复涵咏,贵在能获得自我独特体悟。这样不但能实现认识的飞跃、境界的提升,亦能使主体于创作中体现出识见的高妙、学养的丰富,由此使其创作达到较高的层次。
张九成《悼吕居仁舍人》诗曰:“精识高标不世才,泉台一掩怅难回。词源断是诗书力,句法端从践履来。西掖北门聊尔耳,春风秋月亦悠哉。问君身后遗何物,只有窗间水一杯。”[2]316此诗集中称赞了吕本中的文学成就,首联开门见山地称赞吕本中“精识高标”的崇高人格难得一遇,颔联、颈联分别从“精识”“高标”两方面分别赞美吕本中文学境界高妙之所自。“词源断是诗书力”明确指出了吕本中读书治学造就了其“精识”,进而使其文学创作“词源”广大,气局开阔。而“西掖北门”“春风秋月”则代指庙堂与江湖,张九成用“聊尔耳”“亦悠哉”赞美吕本中不以富贵为喜、不以处穷为忧的高妙境界,即“高标”。吕本中的“精识高标”即是其文学境界高妙的缘由。此诗虽是对吕本中的称赞,亦是张九成诗论的一次集中展现,惟有做到“精识高标”,方能诗文秀绝。强调读书治学之方式即是为达“精识”,注重践行伦理观念即是为臻“高标”境地。
张九成从主体内在修养的角度,对如何实现诗歌创作境界的高妙进行了详细的论说,认为读书治学、践行伦理观念则能使主体性情归之于正,从而使诗歌书写内容合乎儒道要求,达到诗歌高妙典雅的境界。
三、意与物遇,诗以咏之——诗歌创作手法的探求
在本自理学义理界定了性情之正后,张九成亦对性情之正如何书写进行了论述。张九成认为性情之正的书写不是单纯的直陈,不是苍白的说教,而应是“文以宣之,诗以咏之”,即应遵循文学创作的规律,用文学的方式表现主体会得儒者之道后获得性情之正的精神气象。《横浦心传录》载:
渊明云“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子美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若渊明与子美相易其语,则识者往往以谓子美不及渊明矣。观其“云无心”“鸟倦飞”则可知其本意。至于水流而心不竞,云在而意俱迟,则与物初无间断,气更浑沦,难轻议也。[4]203
张九成认为此一联杜诗优于陶渊明句,理由在于陶渊明“云无心”“鸟倦飞”过于彰显主体心迹,有着为表露心迹而刻画的痕迹。而杜诗则更好地做到了自我精神与外在景物的融合无间,水流云飞极为贴切地象征了作者内心的闲暇自得、无拘无束,后者完美融合在了对前者的书写中,达到了表现自我精神与刻画外界景物的融为一体,即“浑沦”境界。所以杜诗此句是意与物遇、自然生成的,故而优于陶渊明句。主体本自性情之正,应事接物时遇物感发,则诗歌自然就此生成,张九成认为如此方是佳作。其在回忆与友人刁文叔的一段文字中,正面表述了这一观点:“每忆与刁文叔夏夜清坐僧室,风竹泠泠然有声,遂咏前人避暑诗。文叔笑云:‘诗在言外,意与物遇,则诗已形于吾前。’予不觉失笑,时此趣最难得。予观其言诗,论及言外趣,真有作者风味,又何必于言语间求之?”[4]170作诗欲臻高妙之境,关键在于把握瞬间的感触,将主体精神集中地展现出来,即表现出“作者风味”。在与吕本中论诗时,他亦将此一主张贯穿其中:“尝见吕居仁论诗,每句中须有一两字响,响字乃妙指。如‘身轻一鸟过’‘飞燕受风斜’,‘过’字、‘受’字皆一句中响字也。某平生不能作诗,每读白乐天诗便自意明,但不费力处便佳耳。尝举以告居仁,云:‘不费力极难,用意到者自知。’”[4]171文中所谓“不费力”即是主体平和淡然精神与物相遇之瞬间感触的书写,也就是之前所言之“意与物遇”,自然生成。值得注意的是,张九成所强调的意与物遇、自然生成,是以主体的丰厚学养、高迈境界为基础的,是建立在读书治学、修养明理的基础上的。故而,张氏对读书精博与作诗高妙之关系论述得颇为细致,《横浦心传录》载:
或问:“山谷《与王观复书》云:诗文虽兴寄高远,而语言生硬不谐音律,或词气不逮初造意时,此特读书未精博耳。”或曰:“谓今人往往读书虽精博,而于诗词多不谐音律,或词气不逮初造意者,此病又在何处?”先生曰:“学能通伦类者少,须是达理便自得趣。不然精博自精博,于诗全不干事。颖悟者虽不甚读书,下语便自可喜。又不知山谷当时所见以此理推之否?”[4]174
张九成针对门人的发问,认为有人读书精博却不长于诗词创作,原因在于其未能“通伦类”,即未能“达理”。其意即是批评此等人读书则单纯读书,作诗便单纯作诗,未能打通二者之壁垒。反之,如欲读书精博且诗词高妙,则应读书治学提升精神境界,再于诗词创作中将自我精神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简言之,即是捕捉自我通过理学修养而达到的精神境界在应事接物时的瞬间感触,将其以诗文创作的形式表现出来。《横浦心传录》中另一则资料则更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张九成这一思路:“先生读子美‘野色更无山隔断,山光直与水相通’①,已而叹曰:‘子美此诗非特为山光野色。凡悟一道理透彻处,往往境界皆如此也。’”[4]168杜甫此联诗句本是描写客观景物之作,张九成却用“作者之心为必然,读者之心未必不然”的阐释方式,将其看作是理事无碍后通脱心境遇物感发的瞬间感受。意与物遇、自然生成的诗论,既能实现诗歌表现主体“明道”后之精神,又能为诗歌注入丰富的哲理意蕴,使其平易自然却味之不尽。张九成此一观点,在品评前代诗人作品时亦有流露:“《文选》谢宣远《戏马台》诗造语虽工,然不及建安七子有正气矣。如‘轻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岂曰不工,何如子建云‘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3]252同为写举目所见之天空,《戏马台》诗用字考究,却造成了气骨偏弱的缺陷,而曹植诗直书寓目所见,却气局开阔,刚健有力。张九成认为曹植诗之刚健在于“正气”存于胸中,不难看出他强调意与物遇要以高妙人格境界为基础的诗论特点。
在强调基于自我理学修养而捕捉意与物遇之瞬间感触的同时,张九成亦对具体的创作手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诗歌应是对事物情态及主体自我精神的表现,而不应停留在再现的层面上。《横浦心传录》中载:“吾友施彦执工于诗,一日见其赋柳有‘春风两岸客来往,红日一川莺去留’,不见柳而柳自在其中,语亦工矣。而刁文叔《赋春时旅中一绝》有:‘来时江梅散玉蕊,归去麰麦如人深。桃花只解逞颜色,惟有垂杨知客心。’致思尤远,不止工也。”[4]170张九成所举之施彦执诗,虽未直书柳之情态,却通过“客来往”必折柳相送,“莺去留”必驻柳来去,引出岸畔杨柳婀娜之态的呈现。而所举刁文叔诗,则通过游子漫游在外所见四时景物的变化,来引出身在羁旅、身心疲惫的慨叹。二诗皆是通过景物描写而表现出所咏事物的情态和主体的心境,这种表现手法的运用使诗歌含蓄蕴藉、情致摇曳,避免了直陈式的再现手法所造成的筋骨毕露。其评吕本中诗,亦是着眼于诗句表现手法的准确:“《春日即事》云:‘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倚栏杆未暮时。’②此自可入画。人之情意、物之容态,二句尽之。”[3]248其评杜诗亦是如此:“‘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③,读此二句不问,已知为竹诗,子美过人,正以此尔。”[3]248杜诗此联佳处在于通过侧面描写自我于竹荫下读书、饮酒的惬意,来委婉地表现竹之情态。张九成所提倡的此种诗歌手法,类似于惠洪《冷斋夜话》所言之“诗言其用不言其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④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也。东坡《别子由》诗:“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也。山谷曰:“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又曰:“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见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⑤[7]43
惠洪所推崇的“言其用不言其名”,实质上是强调语言叙述方式上的改变,如惠洪所引之诗句,在所要表达的内容上并无新奇,但言说方式的新变却给读者造成语言上的强烈冲击感。
总之,张九成的诗歌创作论注重诗歌创作的文学规律,提倡用意与物遇、自然生成的方式,书写创作主体遇物感发的瞬间感触。同时,苏轼、黄庭坚等元祐文人认为读书精博对于诗歌创作极为重要,张九成在认同其元祐前辈观点的同时又有所开拓,他以理学思想为本,将读书精博看作是提升精神境界的必要手段,只有将精神境界的提升与自然生成的创作态度相结合,主体的高迈精神才能渗入其诗歌创作,如此才能诗文秀绝。不同于邵雍等理学前辈的朴拙与直露,张九成主张运用表现的手法来书写主体精神境界在应事接物时的瞬间感发。朱熹曰:“张子韶文字,沛然犹有气,开口见心,索性说出,使人皆知。”[8]3316朱熹所云之“开口见心”即是张九成自然生成诗论在具体创作中的体现,朱熹之语可谓准确概括了张九成文论指导下的创作特点。
四、张九成创作论的实践与理学精神的审美表达
理学修养的目的是使主体具备崇高超越的人生境界,实现主体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共存,故而其导向的是主体平和悠游、自在淡然的精神体现。张九成的理学修养使其对此人生境界有着明确的追寻意识,而贬谪经历则从另一个面加剧了他意欲通过“孔颜乐处”的和乐体验,来实现超越当下苦难的意识。此外,张九成“心即理”的理学思想,使其极为关注自我内心状态,有着明确的通过内在修养以实现外在超越的意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遂使其诗歌于吟风弄月中呈现出了心闲气正、优游洒脱的特点。
张九成长期谪居邵阳、南安,交游稀绝的现实和喜好独处的性格使其离群索居,终日倚柱著书,其《竹轩记》一文即记载了其生活的境况。然而,贬所清幽的山水却时时呈现于诗人眼前,以江山之助的形式为诗人提供了诗材,铸就了其诗歌风格秀丽、笔触清新的特色,如下面三诗:
《正月二十日出城》:
春风驱我出,骑马到江头。
出门日已暮,独游无献酬。
江山多景物,春色满汀洲。
隔岸花绕屋,斜阳明戍楼。
人家渐成聚,炊烟天际浮。
日落雾亦起,群山定在不。
江柳故撩人,萦帽不肯休。
风流乃如此,一笑忘百忧。
随行亦有酒,无地可迟留。
聊写我心耳,长歌思悠悠。
《二十六日复出城》:
杜门不肯出,既出不忍归。
借问胡为尔,江山栖落晖。
濯濯漱寒玉,青青入烟霏。
柳色明沙岸,花枝作四围。
玉塔天外小,渔舟云际微。
兴远俗情断,心闲人事稀。
我本江湖人,误落市朝机。
计拙物多忤,身臞道则肥。
所以此胜概,一见不我违。
吟余尚多思,白鸟背人飞。
《十二日出城见隔江茅舍可爱》:
茅屋临江上,四面惟柴荆。
绿阴绕篱落,窗几一以明。
门前滩水急,日与白鸥盟。
不知何隐士,居此复何营。
朝来四山碧,晚际沙鸟鸣。
棋声度竹静,江深琴调清。
终携一尊酒,造门相对倾。
心期羲皇上,安用知姓名。[2]296-297
《正月二十日出城》作者首叙日暮独自出游,接着写沿途所见景物的清新可人:掩映在野花中的茅屋,斜阳辉映下的戍楼。信马而行,人家渐多,袅袅炊烟与日暮丛林所生之薄雾交织在一起,使远处之群山若隐若现。驱马前行时,垂杨枝条拂帽而过,撩人心意。观此景物,则百忧可忘,纵使此处乃为贬所,亦可以对酒当歌,悠游度日。《二十六日复出城》亦是写出城所见,开篇诗人即言说杜门不出之缘由,因为出游则必为清新景物所牵引而不忍归家。接着写触目所见:近处青青翠竹耸入烟霏,杨柳之绿辉映沙岸之白,柳树之下繁花锦簇,一派生机盎然之景;远处玉塔矗立,天际渔舟荡漾。当此之时,作者笔锋一转,转而自述对过往人生的反思,发出了“我本江湖人,误落市朝机”的慨叹,而“计拙物多忤”所造成的远谪此处的现实,却使自己“身臞道则肥”,于儒者之道的体会上精进良多,所以能见此胜景而内心生出淡然欣悦。而作结处则以江畔独吟、目送归鸟之诗人形象的塑造收尾,将主体超越当下而悠游裕如的心境现于言外,此开放式的结尾增强了诗歌语言的张力,给人以无限遐思。《十二日出城见隔江茅舍可爱》则通过想象中隐士形象与生活的书写,表述了其渴望于此归隐的情怀。远谪之处变为了诗人理想生活的居所,其人生境界的超越高迈与心境的坦然平和,于此可见。
在书写自己身居贬所却能本自豁达胸襟悠游自在吟风弄月的同时,张九成诗歌在书写身居贬所时的超越心境时亦以清壮高迈的风格呈现出来。此类诗歌中,主体心闲气正的襟韵与不同流俗的高迈结合在一起,比之一般诗人闲适生活的书写更多了一份嶙峋风骨与浩然正气。
《辛未闰四月即事》其五:
种槿已五载,入门幽径深。
拒霜偶然植,亦解成清阴。
晚凉新浴罢,松风披我襟。
终日岸巾坐,阒无人见寻。
浩然媚幽独,发兴付瑶琴。[2]303
《拟归田园》其三:
所居极幽深,事简人迹稀。
乘兴或登山,兴尽辄复归。
芝术足吾粮,薜萝富吾衣。
一生澹无营,百事不我违。[2]309
《拟归田园》其四:
不必效沮溺,聊与世相娱。
荒山无邻里,人烟在村墟。
所以近城市,幽处卜吾居。
门前草三径,堂下柳五株。
虽无羊酪羹,箪瓢亦晏如。
在我傥知足,清贫乐有余。
子云作甘泉,相如赋子虚。
嗟我懒此学,箧中一字无。[2]309
《辛未闰四月即事》其五,作者无人见寻而无孤独寂寞之感,其与成荫之木槿为伴,当松风披襟之际援琴赋曲,“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作者形象跃然纸上。虽是谪居闲暇生活的写照,但亦彰显出了张九成虽遭贬谪而不愿随时变易的气节。《拟归田园》其三,诗人虽身居贬所却认为此处衣食富足,因此能“一生澹无营,百事不我违”。这种闲暇情怀的书写,实则亦暗含了作者虽被远斥而不改素志的兀傲情怀。《拟归田园》其四中作者诉说了虽居僻远之地,但能本其儒学修养,箪食瓢饮,安贫乐道,耻为司马相如、扬雄之辈,以阿谀之文辞邀人主之欢颜。其兀傲独立之人格精神与超越流俗之高洁品格形诸诗篇,呈现出了心闲气正的崇高情韵。
张九成“意与物遇”的诗论观亦使其即兴而作的诗篇中体现出了心闲气正的风貌,《横浦心传录》卷上载:寄处南安宝戒寺院,终日闭门著书,未始辄出。一日策杖到院门,秋深,芙蓉两行,红翠相映,照耀目光,遂成一绝:“苦无人事扰闲居,赢得终年学著书。今日欣然出门去,秋风吹意满芙蕖。”[4]168
贬谪生活造成了交游稀绝的境况,却使自己在儒学修养上进展颇大,而儒学修养的精进又使自己实现了对当下现实的超越。诗人出门见秋日盛开芙蕖所感到的心神清爽,正是其超越精神移情于外物观照中的表现。此类诗篇在张九成《横浦集》中极为普遍。《秋晴》:“秋空极清快,偶值数日阴。造物果何意,成此三日霖。晚来风色转,天边露遥岑。无言若有得,古人知我心。”[2]308《闻桂香》:“清晨未盥栉,桂香递秋风。不知此花意,何为恼衰翁。举头复何有,燕雁书晴空。景物如此好,谁云吾道穷。”[2]308《秋晴》乃诗人秋日见风起雨停、晴空终现而作,作结之“无言若有得,古人知我心”则与苏轼“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意蕴相似,乃谓清者自清,如同天空终会转晴一般,彰显了张九成虽被贬谪而不改初心的高洁操守。《闻桂香》乃其闻桂香之瞬间感触的捕捉:秋风袭裾,桂香入鼻,矫首远望,雁过晴空。身处此地,悠游终日,无人事之纷扰,更得每日赏此胜景,可见吾道不穷,是为“景物如此好,谁云吾道穷”。由此可见,张氏超越贬谪苦难的豁达胸襟与自得心境。
张九成诗歌虽以五言古体为主,但其超越精神与“意与物遇”诗论的结合,却使其绝句因能捕捉到闲居生活之自得自在的瞬间感触而意蕴悠长。如其《午睡》“深杏小桃暄午昼,游丝飞絮搅长空。觉来一枕轩窗静,燕子双双西又东”[2]317,《夏日即事》三首[2]318,“寂寂柴门可设罗,唯余柳色许相过。重帘半卷鸟声乐,闲看炉烟篆髻螺”;“心莹是非都不入,神清魂梦亦无多。年来借问生何似,梅雨寒塘飐露荷”;“萱草榴花照眼明,冰厅水阁晚风清。萧然终日无人到,帘外时闻下子声”。其绝句或写午睡醒来时所见之游丝、飞燕,或写自己静坐时入目之袅袅炉烟、入耳之清脆鸟声,或写观雨打荷叶之所思,或写听帘外落棋声之所感,皆是以“意与物遇”的创作方式书写自我超越自得之精神,而其信笔直书、不加雕饰的创作方式,不但是其自然生成诗论的具体践行,亦更好地表现出了其内心的自得与超越。
张九成虽连遭贬谪,但其理学修养却使其通过精神境界的提升,实现了对贬谪苦难的超越。张氏这种精神境界的提升与其“意与物遇”诗论相结合,遂使其诗歌出现了惯常表现主体心闲气正之高迈气韵的特点。张氏对其此种情怀的书写,不但使其达到了舒缓情绪、平和心境的目的,亦使其诗歌在平易自然、不加雕饰的同时,具备了意蕴悠长、味之不尽的风貌。
五、结语
张九成对诗歌创作手法的探索与其对诗歌本质的论述、对诗歌书写内容的界定、对诗歌境界关系的论说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张氏之诗学理论及其创作实践,不仅有着强调主体精神修养的理学印记,亦吸收了文苑的诗学理论,体现出了兼容并包的特点,是南宋初儒林文苑合流程度加深的一个缩影。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认为:“北宋中叶以后,理学大盛,尤其到南宋,理学思想渗入各个阶层,不少诗人都濡染此风,许多理学家在视诗为余事的同时又写了大量的诗,形成了独特的理学诗风。”[9]125南宋文学的第四阶段是“以理学诸派为中心内容”[9]210。全祖望云:“龟山弟子以风节光显者,无如横浦。”[10]1302张九成作为宋室南渡之初影响力颇大之士大夫,其诗论与创作实绩不但彰显了时代风习,亦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考察其诗论特点与形成之必然,不仅有助于深化南宋文学的研究,亦可窥见南宋理学兴起之学术语境下诗论观念的发展趋势与发展特点。
注释:
①原作“山光直与水相通”,仇兆鳌《杜诗详注》“补注卷上”作“天光直与水相通”。
②原作“人倚栏杆未暮时”,祝尚书笺注《吕本中诗集笺注》作“人倚栏杆欲暮时”。
③原作“色侵书帙净”,杜诗各本均做“色侵书帙晚”。
④原作“含风鸭绿鳞鳞起”,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作“含风鸭绿粼粼起”。
⑤原作“心知世事等朝三”,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作“心知外物等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