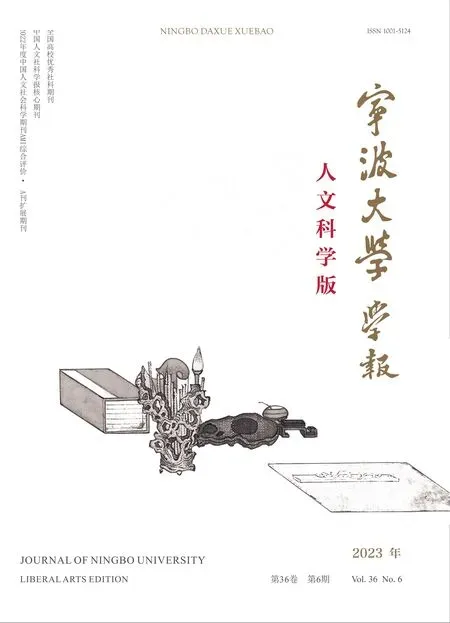精神的迷失与写作的迷途
——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论
侯玲宽
(兰州财经大学 商务传媒学院,甘肃 兰州 730101)
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小说取得了长足发展。它继承20世纪90年代书写之余绪,又呈现了新世纪时代之风貌,真实展现了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困厄、茫然、失落与裂变,从另一层面映照出了知识分子悲剧性的生存形态与精神气象。杂乱斑驳的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也暴露出了作家复杂而矛盾的写作姿态,这之中既显现了一些作家的睿智观察与责任担当,亦显现了一些作家的认识偏颇、价值观混乱与文心缺失。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的成就与不足给我们留下了多重的反思与追问。
一、日常生活:被生存挤压的精神悲剧
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一向承载着宏大而沉重的家国情怀和天下理想,而他们一旦从革命、政治、启蒙的场域走向日常生活的轨道,将会怎样面对日常生活经验与历史惯性的联结与断裂?他们的精神与肉身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人们最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往往蕴含着最深邃的悲剧,这种最深邃的悲剧完全不体现在不幸、伤害、死亡、毁灭或血淋淋的事件中,而体现在人最本质的自由精神遭到损害或丧失,它表面上没有矛盾冲突,人最本质的力量却泯灭了。在城市化和商业化的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所呈现出的灰色、紊乱与沉重,让知识分子在失去了传统的重任与理想之后,无可避免地走向了精神破碎的悬空状态。而对日常生活平庸性的感受和焦虑正是世纪之交文学写作的重要主题之一。
作为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力作的《沧浪之水》,正是从日常生活入手,解构了知识分子一贯秉有的精神神话和终极意义。池大为在父亲的影响下本希望以一种精神性的生存为旨归,以知识分子的内心自足和人格力量在蝇营狗苟的同事中独善其身,却在住房、妻子工作调动、孩子入幼儿园和看病等一系列日常琐事的消磨中,不得不放弃精神的信仰和生命的终极追求,与俗世的浑浊沆瀣一气,痛并快乐着。日常生存的挤压催发了池大为的一次次蜕变,让他看清了终极的虚无与坚守的虚妄,每次蜕变中的自我辩驳和灵魂挣扎都让池大为充满撕裂般的痛苦。义不容辞的使命意识、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流芳千古的缥缈幻想均被更严峻的日常生活击败了。池大为终究还是迈进了现实铺就的轨道,融入了曾被他拒绝过的政治秩序之中,滑向了他力图抗拒过的平庸状态。阎真说:“我力图写出普通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那种宿命性的同化力量,它以合情合理不动声色的强制性,逼迫每一个人就范,使他们失去身份,变成一个个仅仅活着的个体,虚无主义者。”[1]珍存了十年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被池大为在父亲坟前付之一炬,池大为把父亲的遗物终又还给了父亲,这份精神的坚守已成为他日常生活的无法承受之重,坚守了十年的池大为在生活的磨砺和生存的颠覆性中与过去的自己做了最彻底的告别。日常生活是个体存在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但在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上却交织着日常生活的严峻与苦楚,“日常生活的复杂与晦涩,不仅在于它以动态化的方式,承载了人类社会演进与文化变迁的丰富信息,还在于它以无穷无尽的手段,对每个个体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都进行了潜在的文化规约”[2]。那些看似是池大为个人化的生活琐事与工作安排,牵绕的却是一系列微妙繁复的社会关系和潜在规约,城市空间中沉重的日常生活不再是人们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反而成为一个让人全面异化和沉沦的场域,当代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滑向“恶”,但却丢失了理想、放弃了坚守,沦为碌碌人群中的一员。对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本应是他们最具自我空间的日常生活,却成为了导致他们精神异化的强大力量,日常生活的变革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内涵和任务。
对知识分子碎片化生存痛感的书写,呈现了作家们深刻的社会问题意识、难能的锐利和难得的勇气。在许春樵《屋顶上空的爱情》中的郑凡、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涂自强等人的悲剧里,读者真实地看到了知识分子生存的艰难挣扎和苦涩境遇。对黄梅戏研究的激情与城中村居住的恶劣环境在郑凡身上交织出了艺术与生存的现实悖论,也展示了在文化失落与价值转型的年代里知识分子尴尬的生存状况。郑凡可以为艺术的尊严丢掉一份工作,但面对房子的压力和亲情的期盼,他不得不一再丢掉自己的尊严到外面四处兼职,甚至为别人做虚假广告,如所长郭之远所说:“当一套房子成了你一辈子奋斗理想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指点江山、担当天下的妄想了,你就会变得很现实、很老实、很真实。”[3]如果一个社会不能给人提供一种舒适的生存空间,它必然会逼迫着人们以牺牲创造力和消费力为代价而集中全部精力去建构自我保护的壁垒与屏障,因为人首先免除了生存之虞才能从事其他个人活动和社会活动。知识分子在进行人格建构时面临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价值目标,这双重价值目标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互逆背离、冲突交战,映现出的是当代知识分子无法突围的生存困境和孤独悲怆的精神悲剧。作者最后让遍体鳞伤的郑凡放弃为房子和金钱而疲惫奔波的状态,重新回到书斋钻研学术,做一个宠辱不惊安贫乐道的书生,重拾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道统,保持了内心最后的纯净与尊严。这是作者给予尚在生存苦境中挣扎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慰藉,也是作者在揭示与批判之外,给予知识分子的一种可能的救赎方式,这里面包含了作者内心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期望和希冀。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是一部关于希望的作品,可它最后展示的却是彻底的绝望,它让一个出身底层的年轻人通过努力拼搏看到了希望后却又遭遇了必然的绝望。涂自强的悲剧与他的性格全然无关,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这是真正让人悲伤的地方。涂自强的自强、坚韧、刻苦都已达到生命的极致,但却改变不了他凄凉而悲苦的命运,这不仅仅是他出身于贫苦家庭的缘故,更折射了因缺乏公平与公正而引发的时代悲剧。赵同学能凭其家庭背景实现人生飞翔,而涂自强却只能在城市中辛苦辗转地生活。作品写的虽然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但如书封上不无凄凉的书写:“这是一个人的悲伤,更是一代人的悲伤,只有看到平等与公正的希望,人生出彩梦想成真才有希望。”[4]封面 作者方方显然是在借涂自强鞭挞尚存的某种不公和缺陷,并触及到了隐现的“阶层固化”、贫富分化等问题。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也不只是一个底层知识分子的悲伤,正如山村女孩采药所写的,“不同的路/是给不同的脚走的/不同的脚/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4]2,这首诗放在她和涂自强之间,是一种个人奋斗失败与成功的悲壮剧,而放在涂自强和赵同学之间,则是一种人世不公的悲惨剧,这首诗和那个在沙漠中苦苦挣扎着爬行却被骆驼踩踏的梦,形成了涂自强个人命运的深义互文与隐喻。涂自强和郑凡呈现的正是当下年轻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剧性遭遇,不过在涂自强身上方方不但没有给予任何救赎,甚至连丝微的慰藉都打碎了,从而引向了彻底的绝望。
此外,很多作家还以其切身体验展现了高校知识分子日常工作与生活的挣扎与焦虑,坚守者在困厄中的溃败同样呈现出令人触目惊心的难言之痛。史生荣《所谓教授》中刘安定的困境在于日常生活的拮据、科研经费的紧张、课题申报和科研评奖的艰难以及职称评审的无望。对于一个学院知识分子而言,这些是他生存的全部,这种状况令他窒息乃至绝望。史生荣《所谓大学》中的马长有力图在高校中做一个宁静致远、淡泊名利的学者,结果却是如此艰难,在现实生存的逼迫下不得不一再丢弃心中的道德戒律向权力和金钱低头。史生荣《大学潜规则》中的曹小慧和申明理在令人困顿的“衣食住行”中爆发了婚姻的危机,日益窘迫的生活、无休止的家庭纠纷使他们再也无法安然于自己平稳的脚步,于无奈中遽然改变了人生的轨迹。汤吉夫《大学纪事》中的阿满面对宣传与操作时代的大学教育,面对人文精神消失的校园,她只能将自己的苦闷与孤独化作呓语,诉诸另一个世界的丈夫,作为一个欲望喧嚣时代的学者,她能做的仅仅是不同流合污,她无力抗争也无处逃遁。朱晓琳《大学之林》中的老教授尹夕寒面对令人焦虑的学术困境,黯然交出了她倾注了三十年心血的学术期刊,这里面更积满了她的失望和无奈,这位淡泊清雅、治学严谨的老学者对学术的最后坚守被荒诞的现实无声地击溃了。尹夕寒飞赴异域既让心灵找到了最后的归宿,也使九州大学消失了最后一个神话。史生荣《所谓教授》中的宋义仁虽为院系作出了巨大贡献却依然免不了窘迫如丧家之犬、尊严被碾得粉碎的命运,他凄凉的晚景也是坚守者的困境,让人同情与怜悯之余不免感慨万千。这些最后的坚守者成为乱象纷呈的高校中独异的存在,生存的困厄与坚守的艰难让他们在荒诞的现实中透出一种悲怆和落寞。他们在徒然的挣扎里呈现的困窘与尴尬,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信念坍塌和理想放弃,映照出的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溃败,是大学之“道”的改弦更张。现实或诚如评论者所言:“在世纪末整体性的文化颓败氛围里,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精神’再美丽却终究不能使知识分子真正走出他们面临的现实困境。而实际上,知识分子试图以人格的坚守来抵抗和超越世俗的梦想只不过是一个虚妄的神话。”[5]
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更多从日常生存的视角展现了知识分子困顿压抑的精神悲剧,而这些挣扎者也成为了本时期知识分子多元生存形态中精神最为痛苦的一个群体。他们对自己的现状既无法超越又寻求不到救赎之路,他们内心的坚守和对理想的追求在现实面前纷纷溃败,最终只能在精神的迷失中或者走向彻底的失败乃至死亡;或者与浊世同流合污,从中寻求另一种“新生”。他们的惶惑与幻灭映照了我们的时代之痛与生存之殇,“这种突出呈现生活的琐碎、凡庸、惰性与耗损性的文学企图,一方面提供出一种对于日常生活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叙事态度,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说是一种承载着此前的社会文化现实而来的‘文化失望’的产物”[6]。作家们一方面展现了这些挣扎者在生存困厄中左右冲突而始终无法突围的精神危机,另一方面也在试图阐释这些挣扎者向现实妥协、认同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显现了社会转型期与时代的大变革给知识分子,乃至整个文化所带来的创伤与痛楚。
二、人性异化:欲望狂欢下的时代拷问
经过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思想冲击和文化激荡,新世纪以来,有关精神、价值、信仰的乌托邦想象在人们的意识中愈发变得扑朔迷离和虚无缥缈,人们或自觉或被迫地从既往的道德理性、价值体认和人格操守中挣脱出来,趋赴于对各种欲望的狂热追逐中。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和人文理想逐渐失去了向来的公众认同和精神导向,市场经济不仅推翻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话语权,甚至还逼迫着他们不得不反过来应对日常生存的挤压和经济拮据的窘迫。随着知识分子身上曾有的终极关怀的泯灭和人文精神的枯萎,其精神的危机也赫然凸现,“他们再一次面临对于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新想象,对于知识分子职能的重新理解,对于个人道路的重新选择”[7]。话语权丧失后的失落感和精神坚守放弃后的危机感迫使他们开始调整自己的生存状态和人格姿态,并迅速向市场、官场等能够攫取利益的场域靠拢,他们再次试图进入社会的中心,只是这次拿起的武器不再是启蒙思想和精神话语,而是金钱和权力。他们很快就变为市场中“捞金”的商人,官场中争权的污吏,知识分子成为“物化”的人,并在感官的狂欢与人性的异化中演绎着一个时代的悲剧角色。
刘志钊的《物质生活》书写了一曲诗性精神被物质生活击败的悲歌。敏感而脆弱、偏执而富有才气和诗意的韩若东本应该在校园里走一种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并行的教书治学之路,可生存的困境和浮躁的社会已容不下他再安静地写诗。理想与现实、爱情与生活以空前的悖逆性纠结地呈现在韩若东的生存世界里。为了证明爱的能力和自己在商品社会的价值,他不得不走上一条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的下海经商之路。对韩若东而言,这同时也是一条不归路,这条路注定要将他的精神彻底摧毁,甚至连他也一起埋葬。在韩若东的人生裂变中,乔万里是一个关键性的存在:作为导师,他是精神的象征,他肯定了韩若东的才华与诗作,并引导了韩若东的精神走向和思想形成;作为岳父,他却是物质的象征,并最终将韩若东从纯粹的精神世界里残忍地剥离了出来。韩若东的公司是成功的,他拥有了财富和金钱,但他却不再拥有精神,诗和爱情从他的生命中退席了,韩若东由极端的精神生存滑向极端的物质生存,这一过程给读者以极强的冲击力,其人格的分裂和偏执在内外挤压下已经到了极端危险的地步。从一个纯粹的诗人到一个偏执的商人再到一个绝望的杀人犯,韩若东一生的挣扎终究没有避开物质与精神的撞击所酿成的悲剧,物质与精神不是必然冲突与对立的,但它们交织在一个世俗导向出现偏颇的时代里,纠结在一个人格偏执而缺乏理性的人身上,悲剧又是理所当然的。韩若东被作者处理成了理想主义的化身,韩若东与乔其的爱情、韩若东自己的诗歌都是一种精神的礼赞,作者通过韩若东的精神流变书写了理想主义在当代的命运,韩若东所经历的精神蜕变和内心挣扎以及最后的毁灭,使文本触及到了世纪末“诗人之死”的深刻主题。韩若东的悲剧来自于时代与个人的双重作用,但这种诗性的溃败与丧失终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之痛。
如果说韩若东的异化还带有生命被撕裂的疼痛感,那么在另外一些高校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里则充满了精神无法承受之轻的喜剧感。新世纪以后的高校小说大都从与知识分子生存密切相关的事件入手,描绘了知识分子在金钱与权力双重异化下精神坚守的全面溃败和欲望狂欢。在资本和权势横扫天下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伟岸人格、道义良知、责任担当都已不复存在,他们将知识作为换取金钱和权力的资本与筹码,并以自我扭曲、自甘堕落的方式迎合市场的需求和官僚的青睐,映现了一个时代价值观的严重错位。“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问题,不仅是教师在世人的目光里地位下降,就连教师自己,许多人也不再以教书育人为荣,从而对教书也没有了太多的热情。甚至在他们看来,教师也不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书也只是一个谋生的手段。”[8]既然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如果这一职业不能给他们带来世俗的名利,不愿再坚守人格操守与精神高地的知识分子必然会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利用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本疯狂攫取市场利益与社会地位,所以张者《桃李》中的邵景文、邱华栋《教授》中的赵亮、莫怀戚《经典关系》中的茅草根等形象就在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中大量涌现了。“在21世纪,传统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让位给了一个更务实、更讲求实效的人”,“许多知识分子发自内心地接受了与他们的活动相伴的实用主义……把知识和文化仅仅当作实现更大、更高目标的手段”[9]。邵景文和赵亮之所以放弃他们所热爱的中文而改走他途,正因为现实让他们看到中文根本没用场。邵景文每天琢磨的是怎么接收各种官司,怎么得到更多的官司费,怎么更好地周旋于情人与家庭之间。邵景文以打赢每一场官司为目标,所以他充分利用法律的空子并动用金钱和权力的力量,在两场相同的官司中既做此一场的原告代理,又做彼一场的被告代理,并最终在“矛盾之诉”中获得“双赢”。赵亮甘愿充当花花世界中的各种“帮忙”与“帮闲”,每天东奔西走到处做代言人,提出诸多故作惊人、悖逆常识的怪诞“高论”,忙完了各种会议和人际关系就出入高档娱乐场所,约会情人。茅草根也是考虑怎么在公司里兼好职,怎么和情人相处。他们都千篇一律地挣扎于物欲和情欲中,完全摒弃了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和社会担当,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对社会公正、进步、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他们只是兴奋地沉迷于各种世俗的狂欢之中,至死不悟。
在商人型的知识分子之外,本时期还涌现了大量的官员型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本来就立志于官场,有的则是在经受一系列挫折后才深知权力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行政化的高校中,纯粹的教师身份不但让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而且在日常性的各种事务中还经常受到权力阶层的刁难、打压及不公正对待,所以他们不可遏制地产生了冲刺权力的欲望。权力背后的资源和利益让很多高校知识分子无心再专注于教学与科研,转而对权力趋之若鹜。《所谓教授》中的刘安定、《所谓大学》中的杜小春等人本都是安分守己、坚守岗位、对生活没有过多奢求的人,可这个潜规则处处涌动的操作时代让他们发现了现实的残酷与自我命运的无可把握。他们的问题几乎都是通过权力解决的,他们也身不由己地陷入到了权力与欲望交织的泥淖中无法自拔,而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力量,既是他们无法预料的,也是他们无法抗拒的。《所谓教授》中的白明华是本时期醉心于权力并被权力完全异化的典型形象。他是一个官场油条,他能上下逢迎、左右逢源,但这也是一个阴险可怕、人格严重分裂的典型,他是传统“官本位”思想和现代物欲社会双重异化的产物。《大学之林》中的俞道丕和薛人杰同样显现出了在权力面前知识分子的贪婪与狡诈。他们是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这本可形成外语学院良好的学术梯队,可他们却为了院长一职勾心斗角,表面一团和气,背后相互拆台,在对权力的争夺上,两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并无二致。在纪华文的《角力》中,围绕学校的副院长一职,各个有可能提升的中层干部更是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对权力的痴迷让他们丢失了本性,在这一过程中,卑鄙的手段、丑恶的嘴脸、无赖的行径、流氓的习气展现了知识分子一副副邪恶可怕的面孔,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之恶。在新世纪以来的高校小说中,高校几乎变成了一个没任何精神价值的名利场,成了一个欲望泛滥、藏污纳垢之所,大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理念被欲望腐蚀得千疮百孔,学者也都变成了官僚型、商人型的学霸,他们都是为名利而生存,而他们获取了权力之后却是以权谋私,使高校更加腐败黑暗。他们并没有为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公平、合理的秩序与法则、永恒的价值与理念而努力,甚至还成为社会“恶”的推动者。这是高校知识分子最令人感到失望和痛心的地方。本时期的高校小说在对高校内的学术腐败和堕落图景进行深刻而尖锐揭示的同时,也呈现了当代学院派知识分子深重的精神危机和荒芜颓废的绝望灵魂。作家们通过对知识分子个人的审视完成了对当下高校病象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高校小说无疑是深刻而独特的。
新世纪的知识分子小说以最贴近于知识分子现实生存境况和精神状态的方式书写了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存在,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那种苍凉感和惶惑感尤为触人深思。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时代变迁带来的困厄、迷茫、失落与裂变,“他们不得不既要承受传统道德规范丧失因而无所寄托,又要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之下述而难作、徒唤奈何这双重挤压”[10]。在知识分子精神流变的悲剧中,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人性迷失与人格萎缩,以及价值理性缺席后精神的悬空与沉沦,他们逐渐丧失了独立的姿态。在生存的困顿中无法再用人格的力量抗衡强权和世俗的挤压,更无法维护公正、道义、良知等人类的基本价值。困扰着他们现实生存的传统文化理念、世俗价值导向、社会潜在规约等问题还将长期存在,而他们前行的最大困境还在于,在一个精神失守的欲望化时代里,他们能否抵御住日常生活的消磨和世俗利益的诱惑,坚守住精神的家园,不再自我放逐,并建构起自己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的价值信仰和崇高人格。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个艰难的考验。
三、双重反思:写作姿态与文学效果
在对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形态做多元展示与悲剧书写的时候,很多作家都有为时代“立此存照”的意图。阎真曾言:“我的文学理念是零距离表现生活……我表现生活的方式,几乎是照相似的,绝对地忠于现实。”[11]知识分子小说不仅记录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履历,也是整个社会的精神价值标记,深刻呈现了当前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演变。首先,新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对文学控制进一步松动,“主流意识形态……不再运用行政权力直接介入文学,而是……将部分权力让给了民间、社会和传媒”[12],作家的创作环境因而更加宽松自由了,他们更倾向于书写“个人化”与“生活化”的知识分子,尤其在生存的繁琐与重压下,我们甚至看到了知识分子难以言说的挣扎之痛。这也是一个对知识分子“祛魅”的时代,知识分子一贯的博学与睿智、神圣与崇高形象遭到了最彻底的解构与颠覆,其平庸、灰暗、卑琐的一面也都暴露了出来。也许知识分子到现在才是活得最“自我”的一个时代,但在没有了意识形态的支配之后,如果他们不能重建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信仰,这就成为了一个知识分子最容易思想随波逐流、精神陷入平庸、人格走向卑劣的危险时代,而现实正在证实着这一担忧。其次,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渐深化,知识分子从政治中剥离出来之后,又走进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消费主义价值观占据了人们的思想,知识分子的市场化生存状态映照的正是时代生活主题的变迁,所以对欲望的追逐成为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的主要图景,呈现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与缩影。再者,本时期的知识分子小说也凸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变迁。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催生大众文化的繁荣,“毋庸置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姑妄称之为‘大众文化’的通俗、流行文化以愈加有力而有效的方式参与着对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构造过程”[13]。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正是当下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知识分子小说中主人公对世俗的迷恋、对市井里巷的兴趣、从书斋走向广场的真实写照折射了大众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与吸引。知识分子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精神趋向以及知识分子的人格裂变映照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素质,作家们通过知识分子小说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印记和社会转型期的发展轨迹。
随着社会的转型,知识分子也面临着自身的转型问题。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通过不同的书写视角展现了知识分子的世相百态和多味人生,这里面也渗透着作家们的睿智观察和深沉思考。市场经济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并不必然要发生冲突和悖反,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才能拥有独立的精神人格,但在知识分子原有的精神信仰和价值体系逐渐坍塌,而新的精神信仰与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之时,知识分子不但不能再为世俗化的社会提供超越性的精神和道德资源,其本身的苦涩生存、价值迷茫、思想困惑、信仰缺失也使其陷入了转型期的躁动与不安之中。对知识分子来说,转型期也是他们的一个方生方死的考验期,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时代的领路人和代言人,他们的启蒙话语逐渐丧失,而且日常生活的沉重、世俗欲望的诱惑、转型期的社会缺陷都在消磨着知识分子本已岌岌可危的精神坚守。故而知识分子还需要及时走出转型期的阵痛,发挥推动社会演进和文明建设的正能量,尽快建构起自己新的价值信仰和人格理想,重铸知识分子的精神之魂。这也是本时期作家基于现实的人文精神危机所思考的一个沉重话题。
世俗欲望作为一种书写视角,为我们认识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形态和精神生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也暴露了作家复杂而矛盾的写作姿态。欲望书写是一种“双刃”式的文学创作现象,它既是对某种合理欲望的肯定,也对在追逐欲望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道德失范、精神堕落、人性异化予以了警示和批判,暗含了作家对世俗价值体系的怀疑。有些作家的欲望书写表现出了一种严肃的态度和深刻的思考,揭示了欲望生存下知识分子复杂而扭曲的人性、令人喟叹的命运与悲剧。知识分子由时代的“立法者”变为“阐释者”又变为“喧哗者”,他们逐渐丧失了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作家书写背后的失望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从另一层面而言,很多的欲望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市场催发的结果。作家们市场化写作的目的在于以此获得庞大的销量和巨额的利润,故而有的作者在书写欲望之时陷入了渲染欲望、玩弄欲望的狂欢中,有商业时代市场竞卖、媚俗大众之嫌,本时期的欲望书写也因此泥沙俱下。“文学作品一旦与市场相联,就有了‘商品’的意味,就有了去迎合消费者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的欲求,作家的写作就容易在‘市场’的牵引下,去制作小说,形成模式化倾向。”[14]对金钱的贪婪、权力的角逐、情欲的放纵几乎成为很多知识分子小说必备的情节和故事模型。一些作家只看到了知识分子欲望化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形象,却没有真正走进知识分子深邃的精神世界,没有刻画出他们的复杂心理与人性内涵;故使得这些在欲望中沉浮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变成了一种“单向度的人”,他们因缺乏鲜明的个性而显现出同一副人格姿态与精神面貌。知识分子在有些作品中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披着知识分子外衣的“物”,作家只不过是借助这样一个没有灵魂的载体在写欲望。作家因对知识分子的审视缺乏多维观察、深切体验和深度思考,反而将知识分子小说引向难以为继的危机。正如评论者所言:“当代小说的危机,并不在于‘想象的危机’和‘虚构的贫困’,而在于小说家的经验资源的贫乏,在于小说家与‘活的中国’的隔膜。”[15]很多作家在书写知识分子欲望化生存的时候,必然要写到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泛滥与过多婚外情,这导致作品有一种滥情的倾向,消解了转型期知识分子孤独而苍凉的悲剧感,甚至给作品的整体格调造成了败笔。有些婚外情硬加在某些男女主人公身上显得很牵强,这对人物形象和精神造成了硬伤,从而降低了作品应达到的效果和高度,这是作家应该反思的地方。
本时期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生存形态无疑是最让人感到沉重的,多元、庞杂却又令人窒息。现代知识分子在最黑暗的年代里“反抗绝望”的悲怆精神并没有为当代知识分子所继承,甚至连那份孤独和沉郁之气也都不复存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谱系同样也是令人失望的。作家们固然写出了当前知识分子真实的一面,可作家们却也似乎丧失了塑造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这是令人遗憾的,“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自己正面的精神价值作为基础,作为理想,作为照彻寒夜的火光,它的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它的思想艺术的境界,就要大打折扣”[16]。尤其是作家们在书写知识分子沉沦的时候一再写出了这种沉沦的现实合理性和必然性,这就使知识分子的“反抗绝望”不但削弱了力度,也丧失了可能性。而在揭示社会负面现象和知识分子问题方面,作家们更是一拥而上,陷入了一味“揭丑”与“批判”的书写误区中,以致使知识分子小说“成为一种另类的‘官场小说’和‘黑幕小说’”[17]。对社会正面现象与知识分子正面形象建构的忽视,或者说,这种建构能力的缺乏,是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的一大缺陷。这种建构并不是说要粉饰太平、掩盖矛盾,而是作家们应该多元、全面地反映社会现状。一味揭丑只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认识的误区,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知识分子小说还应该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和浩然的正气,这种力量和正气应该能够温润心灵,能够驱散人性的阴暗,让人们在灰色的现实和堕落的人生之中看到希望与信心。文学就是要把人的精神和灵魂从绝望痛苦中拯救出来,重铸民族灵魂、表现人性深度也最应在精神和思想最为复杂的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来。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因缺乏对理想与崇高、价值信仰与深邃人性的深入探寻而在整体上充满颓废和绝望之感,失去了理想之光与延续之力,徒增几多沉重与压抑。
文学创作是作家的生存之道,亦是体现作家生命价值的重要方式。文学的尊严和前景很大程度上是由作家决定的,不同的写作姿态定然产生不同的文学效果。作家用笔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印记,他应对时代负起精神性的责任。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的面貌固然受到当前知识分子真实生存形态和精神境况的影响,但其格调和品位、成就和质量则要受制于作家的写作姿态、文学修养和人格力量。作家以文学的形式来反抗人世的虚无、荒谬和绝望,建构自己所向往、所迷醉的独特话语空间和艺术世界,他们有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作家可以以严肃的态度直面人世的明暗晦朔,亦可以消遣的态度对精神的苦旅避重就轻。“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18]如果作家仍然以寻租或游戏的态度在市场化的写作中以利益为导向,向世俗献媚,那么,他们不但背离了时代的价值导向,也必会被读者所抛弃、被时间所淹没、被历史所淘汰。就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的整体效果而言,它留下的问题要远远大于取得的成就,它在文学想象、语言修辞、叙事策略、美学品格、人性探幽、哲学顿悟、精神气韵等方面几乎都留下了遗憾。较其他题材的创作而言,知识分子小说的危机更为严重。作家们还需端正写作的姿态,潜心艺术,为内心而写作,为生命和灵魂而写作,才有可能实现自我创作的突破与超越。知识分子小说创作还需努力开掘复杂深邃的人性与独异的生命意识,显示出精神的力量和思想的深度,以精美的语言呈现出悠长醇厚的艺术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