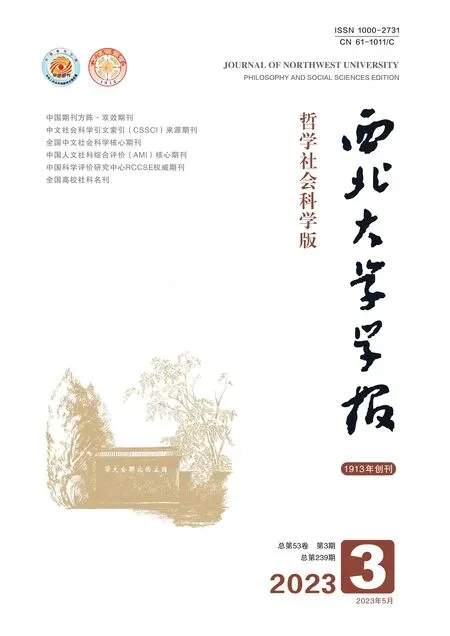天道与人情:先秦儒家礼乐美学形而上之维释证
——以《礼记》为中心
潘黎勇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绪 论
礼乐不仅是华夏文明之根株主脉,亦是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古代生活世界的行动轨范与价值支柱。中国人的政治活动、道德实践、宗教信仰、艺术创造以及据此构造的整个生命经验皆涵融于礼乐之中,贯通为一。从礼乐所涉器物图文、动作仪节、舆服典章、声乐言语以及由这套礼文系统对生命情感之陶养、公序良俗之建构、人文精神之培育等诸种价值实践来看,都与丰富的美感经验活动和独特的审美文化理想具有本质性的关联。唐君毅说:“中国古代……合礼乐于社会、政治、伦理之生活整个皆表现审美艺术之精神。”[1]19这种审美精神成就了中国人充实而富条理、活泼又不失谨严的生命情态,塑造了一个感性充沛却谨严有序、既散溢世俗人情又内具超越精神的生活世界。唐君毅对礼乐文化慧眼独照的体察从一个思想侧面说明,礼乐本身关涉美学问题,礼乐美学实构成中华美学重要的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
如果按照美学的学科视野和知识框架来看,礼乐美学研究至少包含三个论域:其一,礼乐审美形式论,主要分析礼乐活动所涉之名物器具、仪式动作、容姿声采等感性形式的审美特征;其二,礼乐审美经验论和审美价值论,探讨人在艺术化的礼乐活动中面对他人、世界、神灵所生成、绽放的情感体验与生命情态,以及在此过程中不断积淀、创造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其三,礼乐审美本体论,旨在通过探求礼乐的存在本原以揭示礼乐美学的超越性维度,礼乐本体是包括审美活动在内的一切礼乐实践据以开展的终极根据,也是构架整个礼乐世界的最高原则,故亦从根本上塑造了礼乐美学的形而上品格。礼乐美学的三个部分无论在理论观念上抑或现实活动中都很难截然区分,但在我们看来,要深度把握礼乐美学的精神要义,理解其作为一种中华美学思想形态和儒家文化叙事形式的深层价值所在,便不能仅从形式鉴赏和世俗政教层面来认识礼乐美学的意义,而须直探其本,超乎其上,从形上之维切入礼乐文化的终极之思,厘定礼乐美学在哲学上的合法性根基。但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由于学界对礼乐美学作为中华美学之重要理论形态这一思想事实尚未形成自觉的认识,对于礼乐美学本身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往不乏有对礼乐的美学研究,但多数聚焦于作为艺术形式的“乐”,而缺乏对“礼”的美学考察(1)“礼”和“乐”固然可以分置对举,但作为一套融合政治、伦理、宗教多重功能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系统,“礼乐”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乐”实际涵括于“礼”之中,言“礼”已有“乐”在内。,更少有将“礼乐”当作一个整体性的美学范畴来阐释,遑论从形而上学维度对前者进行哲学上的释证(2)笔者检索中国知网发现,明确以“礼乐美学”名篇的期刊论文共16篇,学位论文0篇,其中15篇发表于2018年以后,将“礼乐美学”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有论文21篇,多数与“篇名”搜索结果重合。由于《礼记》堪称礼乐美学最重要的经典,故笔者又以“《礼记》美学”作为“篇名”检索项进行检索,共有论文12篇,9篇是关于《乐记》的美学研究,12篇论文中,4篇是学位论文,其中3篇硕士论文,1篇博士论文。学术著作方面,李泽厚在《华夏美学》第一章对礼、乐审美属性及其文化意蕴的考察应是新时期较早且十分重要的礼乐美学研究成果。王燚的《西周礼乐美学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是目前所见唯一明确以礼乐美学为论题的专著。张义宾《中国礼乐审美文化史纲》(齐鲁书社2016年版)也可视为同类著作。港台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林素玟的《〈礼记〉人文美学探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是较早对《礼记》美学作系统性阐释的专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龚建平的《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专论礼乐哲学思想,其中对礼乐哲学的形而上学问题的阐释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礼乐美学的形而上学问题具有重要参鉴意义。。
作为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论礼的文献汇编,《礼记》是先秦儒家礼学的集大成之作,整书虽编订于西汉初年而难免杂有汉儒的观念,但《礼记》记录的主要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想(3)《礼记》49篇作者不一,各篇写作年代也有较大差异,但多数文献成篇于先秦,起止时间大致从春秋早期到战国晚期。关于《礼记》的成书情况,可参考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李学勤也认为:“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见《郭店简与〈礼记〉》,载《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并且保存了西周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些共识性的儒家礼义观念,其有关礼的起源、本质、功能、意义等问题的思想论述具有基础性和典范性,可谓激励后世两千年礼学发展、演化的源头活水,当中自然也包括礼乐的形而上学问题。本文即以《礼记》为中心文本,通过阐述先秦礼乐美学形而上之维的思想路径和结构特征,于本源处揭证形而上之维之于礼乐美学学术品格和礼乐文化精神旨趣的塑造作用与建构意义。
一、“礼必本于天”:礼乐的形而上之原
众所周知,被称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宇宙万物及一切存在者的终极原因和普遍本质,论证存在物的存在根据和结构原理。在古希腊,形而上学是一门关于Being(是)的学问,其中包含了后来称为本体论的核心内容,本体论在原初的形而上学中实为其应有之义。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与西方形而上学有相类之处,却也存在明显区别。张岱年把中国形而上学分为大化论和本根论。他说:“按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 (Metaphysics)分为Ontology与Cosmology,中国古代哲学中, 本根论相当于西方的Ontology,大化论相当于西方的Cosmology。”[2]92本根论就是本体论,大化论相当于宇宙论或宇宙发生论。显然,这还是按照西方哲学框架来划分的,却也说明中西方原初的形而上学存在着重要的思想交集和共同特征,即它们都涉及万物初始本原和宇宙变化过程及其原因的研究。但同时两者的差异性更为关键,这种差异性来自形而上学在中西方不同的发展路径。概言之,在西方形而上学的演化中,宇宙论逐渐从中分化出来,形而上学便集中于对世界终极根据和存在本原的探讨,变成了一门研究“是之为是”的科学。与此不同,中国的形而上学始终没有明确区分宇宙论和本体论。古人相信,万物本原和初始性质贯穿在宇宙的演化、变易过程中并发挥根本性作用,而对本原或本体的探证必须在万物流变的过程中来把握,甚至认为,发展和变易本身就是宇宙本体。牟宗三在评判中西存有论(Ontology,即本体论)之差异时说:“中文说一物之存在不以动词‘是’来表示,而是以‘生’字来表示。……但是从‘是’字入手,是静态的,故容易着于物而明其如何构造成;而从‘生’字入手却是动态的,故容易就生向后返以明其所以生,……故中国无静态的内在的存有论,而有动态的超越的存有论。”[3]259唐君毅也说:“中国人心目中之宇宙只为一种流行,一种动态;一切宇宙中之事物均只为一种过程,此过程以外别无固定之体以为其支持者(Substratum)。”[4]2两位现代新儒家大哲皆认为,与西方形而上学中那种隔绝于现象的静态性本体不同,中国哲学所谓本体不是固定不变的孤悬的实体,而是表现为一种生化流行的动态过程。
华夏礼乐尽管承担着治政安民、纲纪人伦的政教功能,但其中亦潜含着精深杳渺的形上思想维度和超越性的精神内涵,此关乎礼乐审美的存在本体和先天原理,亦是寻证中华美学之精神境界与价值理想的思想渊薮。显然,礼乐美学形而上之维与古代形而上学紧密交织勾连在一起,其思想特征亦要置于后者的总体视阈中来把握。因此,我们对礼乐美学的形而上考辨就不是像西方形而上学那样径直去追问万物本质、思证宇宙存在的绝对根据,而是希冀在一种自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去把握礼乐审美的形而上特质,而这首先要聚焦到礼乐的起源问题上。在传统礼学中,历史性的礼乐起源问题与哲学性的礼乐本原问题本来就混融不分,对礼乐起源的多重探讨构成了礼乐哲学、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礼记》对礼乐起源问题的思考相当自觉而深入。《礼记·礼器》云:“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5]657《礼记·祭义》道:“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5]1222“反本修古”“反古复始”便是强调探求礼的本初起始,追寻礼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精神动因。而礼之初始究竟为何,无论揆诸儒家典籍还是历代学者研究,皆存在一个基本共识,即礼的产生与祭祀活动或原始宗教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礼乐在华夏文明初期正是以宗教形态——广义上的——存在的。
《礼记·礼运》是一篇讨论礼的运行法则的重要文献,其中就论及礼的起源问题,言曰: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5]586-587

事实上,所谓“事鬼神上帝”正是作为华夏礼乐发轫阶段的殷商古礼的文化功能。《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5]1310而在殷人的鬼神体系中,族群信拜的至上神称为“帝”或“上帝”,上帝支配包括生产、战争、祭祀、婚配、夭寿等一切人间事务,成为殷人日常生活的精神依持和整个族群生存繁衍的终极信靠。无论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祇,他对于殷人来说就是一位神圣的“超验者”,殷人由此享有了一定意义上的宗教生活,这种宗教生活构成早期礼乐活动的具体内容。同理,正是上帝信仰孕育了早期礼乐文化超越性的思想元素,塑造了礼乐哲学、美学形而上精神的最初维度。
到了西周时期,以周公为首的统治集团开启了一场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文化变革,其直接后果是极大削弱了殷商古礼中原始宗教和神巫文化的内容,促使宗教礼乐向人文礼乐转变。礼乐的宗教精神不再表现为对一切人间事务直接的启示、审判和导引作用,却是隐退、转化为由人文礼乐规导的政治、道德活动的超越性本原和价值依据,而其中的思想关键在于周人将与人的主体意志和社会活动更具存在关联性的“天”或“天命”取代殷人的“上帝”观念(4)关于“天”的观念最早出现于何时,学界向来有争议。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指出,殷人称至上神为“帝”或“上帝”,“决不曾称之为天”,“天”的观念是周人的创造(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页)。陈梦家也认为,“‘天’之观念是周人提出来的”(见氏著《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81页)。但傅斯年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依卜辞做出推论,殷人既有上帝及众神,自当有“天”这样的观念总摄一切神祇(见氏著《性命古训辨证》,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13页)。笔者认为,既然“天”字在殷商卜辞材料中极为少见且未发现以“天”为上帝的用法,哪怕“天”至少在殷商晚期已开始指称某些宗教文化观念,但仍有理由肯定,“天”的观念是到西周时期才真正流行并成为周人的一种普遍精神信仰的。,成为两周时期新的精神标识。在思考殷亡周兴的政治规律时,周人更将“天命”确立为王权统治的合法性来源,相信天命的获得和移易与人(统治者)的道德条件直接相关,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8]462,《尚书·召诰》曰:“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8]225“德”的引入使天获得了道德性意涵,周初的“天命”(命运之天)观到春秋时期转变为“天道”说(义理之天)(5)据统计,在记载西周历史的《尚书》和《逸周书》中,“天道”只出现 12 次,而春秋史书《左传》和《国语》援用“天道”就达30次之多。陈来梳理出春秋时期“天道”观念的三种意思:第一种是“宗教的命运式的理解”,等同于西周时期主宰个人、民族、国家命运的“天命”;第二种是“周书中的道德之天的用法”,体现为道德意义的法则和秩序;第三种是“自然主义的理解”,指永恒的自然原理和运行规律。这三种观念“互相扭结,难解难分”,使得“天道”成为一种广摄一切事物的普遍性的宇宙法则,自然、社会、历史都不能逃离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参见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0-88页。。徐复观指出,“春秋承厉幽时代天、帝权威坠落之余,原有宗教性的天,在人文精神激荡之下,演变而成为道德法则性的天,无复有人格神的性质。”[9]47相比于殷商之“上帝”,春秋之“天命”或“天道”已更多显现为一种“无声无臭”“于穆不已”的宇宙法则,超越而神圣。牟宗三在论述孔子天道思想时便说:“天仍然保持着它的超越性,高高在上而为人所敬畏”,因而天道、天命确有形而上的含义[10]36。在这种天道观的支配下,礼与天的关系也被迅速构建起来,《左传·文公十五年》言:“礼以顺天,天之道也。”[11]614天道被视为礼的存在源头,礼必依天而立,顺天而行。
“天”在《礼记》中的义涵十分丰富(6)《礼记》中的“天”主要可分为自然之天、主宰之天、道德之天、形上义理之天,各举一例说明。自然之天:“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礼记·月令》);主宰之天:“鲁哀公诔孔丘曰:‘天不予耆老,莫相与位焉。呜呼哀哉!尼父。’”(《礼记·檀弓上》);道德之天:“子夏曰:‘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矣?’”(《礼记·孔子闲居》);形上义理之天:“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礼记·中庸》)上述例子中多以天、地对举,但儒家以“天”总摄天、地之义而成为最高实体,天、地无论作为自然元素还是创生力量皆本原于天道。,但对于礼乐美学的形而上之维来说,最具思想意义的乃是作为万物存在之依据和人性道德之本原的“义理之天”,这也是春秋时期天道的核心义涵。《礼记》对天道观的宣扬首先表现在其将天作为最高的祭祀、信仰对象。《礼记·祭统》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5]1236祭礼在整个礼仪体系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祭祀对象主要有天地、鬼神、祖先等,而两周尤其是春秋时期的祀神祭祖仪式仍明显保有上古宗教和殷商神巫文化的遗传。区别在于,此时的天在祭祀体系中已处于至尊地位,成为凌越于鬼神、祖先的宇宙创生之原,这也构成殷周之际礼乐精神变革转化的根本关节。《礼记·礼运》道:“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5]615祭“帝”是为了确立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帝”在这里俨然是一个陪衬性的虚化概念,“天”才是真正信仰、思证的对象。《礼运》中的几段材料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其言曰: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5]585
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5]616
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5]616
不难发现,上述三段材料遵循了相同的叙述逻辑,即首先从形上义理层面确证礼的存在根据,然后说明礼如何协和效法自然,运转、落实于现实世界和世俗社会,由此实现自身之功能价值。其言“礼必本于天”,“本”即本原,因天道乃宇宙万物生化、运行之原理与根本法则,故自然也是礼所出、所化之根据。《大戴礼记·礼三本》云:“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12]17一般认为,此中“性之本”应作“生之本”解(7)傅斯年指出,先秦没有独立的“性”字,先秦典籍中的“性”字多作“生”解,参见《性命古训辨证》上卷。《荀子·礼论》中这句话便是作“生之本”。。究其实,“生之本”是侧重于从宇宙论层面昭示天作为礼乐世界和礼仪形制创生之源的意义,此“天”属自然形气之天。“性之本”则从存在论上说明天是礼乐精神和礼义价值的本原,礼乐乃效法天地之道而设,此“天”是形上义理之天,也就是《礼记·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的天,朱熹视为“道之本原”所在[13]20。牟宗三指出,“天命、天道的传统观念,发展至《中庸》,已转为‘形而上的实体’一义”[10]39。可以说,《中庸》中的“天”为《礼记》的礼乐本原论提供了坚实的形而上学支撑。
既然天为“性之本”,礼本于天,则天命之性即为礼乐之性。天命之“性”是天道贯落于人而生成的自然禀赋和人格本性,但天赋秉性必要在礼乐活动中得到涵育和表现以获得其现实性,此即孔子“立于礼、成于乐”的人性生成逻辑。而照《礼记》所论,礼乐不仅是一套人性教化的程式体系,更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它之能教人、成人正在其为人性固有之内涵。《礼记·冠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5]1411《礼运》道:“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5]617故此,礼乐之性、人之性与天命之性在本质上是相通为一的,且都以天或天道为形而上之终极依据。更可强调的是,天作为礼乐的形而上本体与之作为自然万物的存在依据是不同的。礼乐乃“人之大端”而必要关联人性来讲,所谓“本于天”或“承天之道”的这个礼,并非如孔子所批评的徒有“玉帛”“钟鼓”之形制空壳,这样的礼是非人的,而是“本之情性,稽之度数”[5]1000,并“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的人道实践体系。因此,天对礼的形而上规定必然是指向人的,只有通过人这一存在维度,这种形而上规定才能将天道义理下贯到礼乐之中,实现修道立教、人文化成的圣王之业。
照上所述,我们认为,无论形气之天还是形上义理之天,都已脱落了殷商巫礼信拜的“帝”那样的人格神属性而成为创化万物、生产意义的超越性力量,也正是这两种“天”合构成所谓“礼本于天”的形而上之义(8)“礼本于天”是《礼记》礼乐本体论的核心观念,如:“古之制礼也,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礼记·乡饮酒义》);“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礼记·丧服四制》);“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等。。可以肯定,礼乐所本之“天”不只因为直接关联人间生产生活的实际利益才作为宗教活动的最高祭祀对象而存在,剥去了神巫色彩的天道观此时已深度嵌入礼乐精神结构当中,不仅从道德价值上为礼义世界定则立极,亦从哲学上为礼乐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与“帝”向“天”的观念变革相照应,自西周初年始,人文化与世俗化成为礼乐发展的鲜明趋势,礼乐的意义指涉和功能实践超出了“神人之事”的范囿而成为延伸到国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一套制度规范与精神法则。正如钱穆的概括:“凡当时列国君大夫所以事上、使下、赋税、军旅、朝觐、聘享、盟会、丧祭、田狩、出征,一切以为政事、制度、仪文、法式者莫非‘礼’。”[14]41然而,无论礼乐文化的整体功能如何聚焦于世俗政道,礼的终极源头在天,礼作为人间秩序依然有天道作为其超越性的依据。正是这种天道观念一方面赋予礼乐以全新的超越性的精神内涵,同时为礼乐的哲学(美学)形而上学提供了核心思想构件。
二、“天地有大美”:生生之道与礼乐之美
如果确证天道为礼乐之形上本原,那么应该如何立足美学视阈来理解天道之于礼乐的形而上意义呢?礼乐美学的形而上之思旨在探求礼乐审美的存在本体和价值根据,既然天道为万物创化之根本,礼乐制度与其审美形式自然亦由天道所造化,依其而生,循其而行。然如此论说过于空泛,无法准确解释天道何以能够在美学意义上构成礼乐的形上之原。在我们看来,最简易直截的做法便是阐证天道本身即是一种审美化的形上本体,其美学意蕴乃是哲学上的应有之义。而既认定“礼本于天”,便可相信建构人间秩序的世俗礼制在构造形式和功能特征上必然整个是审美化的,这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审美化塑造、支配了礼乐的政教、社会、宗教等文化功能,从而不仅使美学研思成为体证礼乐文化精神的关键路径,更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形而上美学构成了礼乐形而上学的本质要义。
那么,如何理解天道的美学意蕴呢?这就不得不从认识天道的存在特征入手。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形而上学讲求在变易、生化的动态过程中揭证宇宙的本体之义与本原精神,而变易、生化自身即被看作是本体之显现,质言之,中国先哲关心Becoming(变化、生成)更甚于Being,这也典型地体现在作为礼乐形而上之维和礼乐审美本体的天道之中,其关键特征便是充塞宇宙、永不止息的生生之力。《周易》对天道的这种创化力量及其哲学意蕴作出了经典性描述,稍举几例: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卦》)[15]7
天地养万物。(《颐卦》)[15]122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卦》)[15]139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卦》)[15]144
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15]297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15]310
以上材料表达的核心观点是:生育万物是天地的根本功能与特性,这种创生力量永恒不息,它是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生命滋长化育、盛衰存亡的根本,也是宇宙大化流行、发展变易的原理。它不是来自最高主宰者的意志与命令,乃是天地本身如其所是的本原之性与存在形态。这样的天地宇宙充满生香活意,处处生机盎然,“是精神与物质浩然同流的生命境界,在波澜壮阔的创造过程中生生不息”,方东美称这种观念为“万物有生论”[16]117。而支配这样一个恒久不绝的运动、变化、发展过程的是阴阳变化之道。《周易》“观变于阴阳而立卦”[15]324,阴和阳是宇宙中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功能与力量,阴阳二气的流变、聚散、和合构成创化天地自然、推动宇宙流化更新的根本动力,进而产生刚柔、动静、强弱、顺逆、吉凶、祸福、美丑等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所谓“生生之谓易”,“生生”即有阴阳相生相长、相互作用以造无限生机之意,孔颖达疏曰:“生生不绝之辞,阴阳转变,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15]271一阴一阳施受交汇、化合消长的规律便是穷极万物变化的宇宙神机、天道至理,此即“一阴一阳之谓道”[15]268。由是,正如罗炽在总结《易传》道家思想时所说:“天道一阴一阳,相互感应、消长盈虚、自然无为,生生不已。……风雨变化、品物流行、日月更替、寒暑交章, 各因其性而生,和谐共处而长。这里描绘了一幅人与万物以及各种自然现象在阴阳二气氤氲交感、相摩相荡中周流变化、生成发展的美妙图景。”[17]53
《周易》的天道思想和以“天”为中心角色构造的生生宇宙对儒、道两家哲学影响深远,其中也包括《礼记》的天道观。《礼记》及其构筑的礼乐哲学中的形上之天同样不是一种抽象、孤绝的静态本体,亦是在创化万物、鼓荡天地的生生过程中显现存在。试看: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礼记·郊特牲》)[5]1193
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礼记·郊特牲》)[5]707
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礼记·月令》)[5]417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礼记·中庸》)[13]35
天地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礼记·乐记》)[5]1010
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礼记·乐记》)[5]993
无论从内容还是语言来看,《礼记》所述天地生生之道明显是承传于《周易》,同样强调了天道浩荡不竭、造化万物的终极作用,这自然也构成制礼作乐的本始力量。
依上述,天道是宇宙中幽深玄远、流化不息的生生之道,此生生之道即美的根源和美本身,是浸润万物、散发生香活意的天地大美,故生生之道即生生之美。方东美说:“天地之大美即在普遍生命之流行变化,创造不息。……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而生命之美形于创造,在于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16]290在中国古典美学视阈中,美不在比例的和谐,也不在机械的秩序,而必显耀于盎然生意、活泼生命之中,美只能存在于一个气韵生动、万物含生的世界,绝不能寄托于一个干枯死寂的宇宙。天道之为美,就在于它是宇宙生机之本枢所在。如方东美所说:“各民族之美感,常系于生命情调,而生命情调又规抚其民族所托身之宇宙,斯三者如神之于影、影之于形,盖交相感应,得其一即可推知其余者也。”[16]193
然而,之所以认为美涵育、显发于万物生化的过程之中,乃至相信生生之道便是美的始源本根,并不仅仅系于生生之力恒久不息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因为生机勃发有可能是混乱和无序,生力活跃也有可能是野蛮和侵夺,这无论从形式和价值上都无法契合“天地之大德”“天地有大美”的生生之道。事实上,正如宗白华所言:“宇宙是无尽的生命、丰富的动力,但它同时也是严整的秩序、圆满的和谐。……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美,也是人生美的基础。”[18]57-58生生之道之能含章吐华、美耀德彰,正在其能够不断创造、维持着天地位、万物育的和谐秩序。这种宇宙的和谐秩序不是静态的、机械的,而是动态的、创造的,其根本原理是阴阳施受交汇、化合消长产生的无限动机,宗白华称之为“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的生命节奏”[18]438。这种和谐的生命节奏既是天道流行的频率,亦是美的根源和表现,这样一个鼓荡着自由生命节奏的宇宙在庄子看来便是“至乐”的美妙乐章。在这首宇宙乐章中,万物在和谐的自然节律中展现生命创造的无穷妙趣,个体深契宇宙大化而浩然与天地同流,达至善至美之胜境。此种生生的节奏和旋律就是天地大道,而至善至美是天道的本体特征。
如果说充满生生之力的和谐圆满是宇宙创化过程中本然具有的存在秩序,那这样的秩序自然也应该成为人类政治行为、道德生活、个体精神乃至整个文化所追求的理想状态,而儒家无疑是将这样的终极使命托付给了礼乐。“礼本于天”的观念一方面固然表明人间礼乐有其形而上的价值源头和存在根据,但同时也绝不可忽视其潜含的另一层意思,即作为广大无穷的天道流行的一部分,礼乐享有天道的精神特质和价值功能。《乐记》云:“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5]994这样的礼乐就是天道的载行者和代言者,是后者在人文世界的整体表征,“天的性格,也是礼的性格”[9]47,认识这一点对于理解礼乐审美的形式意义与文化旨趣至为关键。
由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天道以创生、护生为作用特征的生生之性同样显著地存在于礼乐的观念与实践之中,可以说,依循天地之道关护、安顿自然万物和现实生命乃是礼乐的精神本旨,也是一切文化创造的价值基础。《礼记》中存在不少有关礼乐创生之义的论述,如《礼记·郊特牲》:“乐由阳来者也,礼由阴作者也,阴阳和而万物得。”[5]674《礼记·乐记》:“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5]1010“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5]994不难看出,礼乐分象天地、阴阳、动静,表明其本原于天道而具有类同于天道的创生化育之力。天道流行最显著的表现莫过于自然时令,故“礼以顺天”的首要原则在于顺时。《礼记·礼器》云:“礼,时为大。”[5]627顺时的目的则在尊生、养生,“天地养万物”乃天道之自然。“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鬼神弗飨也。”[5]625
天地大化流行以其无尽不息的生生之力和由之昭显的生生之美构成天道美学的核心意蕴,礼乐美学的初旨本义首先似应基于如下理解:效天法地之礼乐,无论是为事神致福还是政教德化,目的都是在现实文化活动中激发和养护人的源源不竭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并将之同流合融于宇宙大化之中,这种生命力与创造力不仅是审美创造的条件,其藉由礼仪、礼制的活跃显发本身即是礼乐精神的审美化表达。与此同时,正如天道生生之美在于一阴一阳的生命节奏达成的宇宙秩序与万物和谐,这样的秩序与和谐同样是礼乐本有的一种存在属性和价值旨趣,并成为礼乐美学判断的观念依据。而如果礼乐本身扮演了天道载行者的角色,那仅仅把礼乐当作天道运行流化的产物或天道的制度性摹本就不准确了。事实上,在《礼记》中,礼乐被视为宇宙和世界的存在样态,“世界是通过其自身的礼乐性向人显现出来”[19]167。《礼记·乐记》云:“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5]992天地万物形态各异,品性有殊,却自然呈其所是,相宜而安,似是礼制的秩序安排。另一方面,万物同处天地之间而能和谐共生、聚合融通,在变化不已的过程中吟奏出宇宙的和声谐律。孙希旦据此指出天地自然本身具有礼乐性:“天地定位,万物错陈,此天地自然之礼也。流而不息,而阖辟不穷,合同而化,而浑沦无间,此天地自然之乐也。”[5]992“天地自然之礼”“天地自然之乐”指一种本体意义上的礼乐。如《乐记》言:“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5]988“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5]990“大乐”“大礼”并非现实生活中的礼乐,而是超乎其上、合融于天地大道的至乐、至礼。人间礼乐的现实品格固然以天道为形上本原,但天地宇宙的秩序性与和谐性亦体现了天道的礼乐性内涵,礼和乐由此成为结构世界的方式,“和”与“序”及其审美意蕴则为天地宇宙与礼乐的共同特征。在此意义上,天道(天地宇宙)、礼乐(本体意义的)实质是一种一体同构性的存在。进一步亦不难理解天道之能构成礼乐美学的形而上之维不只因其在存在论、价值论层面上创化万物的绝对性和普遍性,更因天道本身含具一种审美化的礼乐本体(“天地之序”与“天地之和”),故不妨说礼乐审美的形而上本原恰是一种审美的形而上礼乐(天道)。
然而,按照中国哲学体用不二、天人无间的思想特征与显现方式,天道、人道从来不能隔断来看,对天道的领受不是依靠智性的玄思,而是通过政教德化的人事活动与个体的心性修养实践来体证。赵敦华说:“中国形而上学始终面临的问题是,宇宙生成之道如何影响、规定人的行为准则?”[20]换言之,中国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天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故天道的形而上意涵亦只能在人道中把握。在儒家看来,礼乐正是一套交通天人、兼摄圣俗的观念系统和行动规范。王船山叹曰:“大哉礼乎!天道之所藏而人道之所显也。”[21]3天道、人道皆交合同构于礼乐之中,故要深入理解礼乐的天道本原及其形而上意义,势必要将视角下落到现实礼乐中,通过探查礼乐审美活动的一般特质及其潜含的天人关系来进一步把握礼乐美学形上之维的构造特征与价值意旨。
三、“达天道而顺人情”:礼乐美学形而上精神的情感内核
要把握由天道下贯而成且作为“人道之极”[22]347的礼乐,既需要具体而微的历史探证与考索(如对礼仪节文的考察研究),亦须超越具象细节而能对礼乐文化的一般性问题展开宏大深广的思辨。在一系列对于理解礼乐本质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当中,礼与情的关系问题便处于统架整体的核心位置。无论就礼的制度创构、观念演化还是实践形态来看,“情”既作为思想依据也构成行为动力而始终贯穿在礼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检诸先秦儒家礼学文献,对礼与情关系的深刻认识和丰富阐释构成有关礼乐起源、本质、功能等礼学关键问题的观念基础乃至论述核心,而情感恰恰也是对礼乐开展美学阐证的重要义理依据。
在先秦儒家文献中,没有其他经典比《礼记》更能集中典型地反映出礼与情的思想关系和价值纠联。根据李天虹的考察,《礼记》全篇“情”字凡六十六见,涵括了先秦文献中“情”的全部四种用法(9)李天虹在《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一书中对先秦文献有关“情”的用法做了较为完整的归纳,共分为四种:第一,情性之情,具有情感、情欲的内涵;第二,指事物之实,是事物的实际情形,即情实、实情;第三,指人内心之实,是真心、真诚的意思;第四,是指事物的本质或常理,可解释为质性、质实。见氏著第31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欧阳祯人亦在《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研究》中指出先秦儒家的“情”范畴有四个义项: “质实”“情实”“情理”“情感”,与李天虹看法基本相同,见氏著第89-9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相似的分类还可见黄意明《道始于情——先秦儒家情感论》,第34-44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概言之,“情”既指事物的本来情状和实际内容,也含具个体的欲望、情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感情关系和交往状态的意思。无论如何,立足现实生活境域的一种在身性的生命活动与感性经验似是先秦儒家之谓“情”的基本义理,这也构成了因情而立、据情而显的礼乐活动的本质特征之一。,除了事物之情实、实情(共三例)和事物的本质、质实(共七例)这两种意思外,其他用法基本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指涉情感的意涵[23]38-44。然而,相比肯定礼乐之“情”的情感意义这一点,更加重要的应该是准确理解情感在礼乐思想叙事和实践形态中的存在属性与价值内涵,这将是我们本诸天人之际的宏阔视野把握礼乐美学形而上精神的关键所在。
检诸《礼记》文本不难发现,一方面,人情被视为礼乐之本,乃礼之发生、制作的根本依据。如《礼记·乐记》:“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5]1000《礼记·三年问》:“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5]1373同时,又特别强调礼对情的制约功能,主张以礼治情。如《礼记·坊记》:“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5]1281《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舍礼何以治之?”[5]606-607应该说,治情、节情正是展开为社会、政治、伦理等多重价值实践的人间礼乐的主要功能所在。而在由亲亲、尊尊原则主导的传统宗法社会中,包括《礼记》在内的先秦儒家文献所言之“情”很少直接表达生理欲望或物欲的意思,而更多是指以孝悌为本的血缘亲情及由之扩展延伸而来的表现于宗法伦常中的道德情感。在儒家看来,这种基于血缘亲情的道德情感是一种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人类天性,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动力和道德观念的心理基础。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24]74,“欲仁而得仁,又焉贪”[24]210。钱穆论“仁”有言:“道德本乎人性,人性出于自然。”[25]219作为孔子和儒家道德哲学的核心观念,“仁”正是一种带有强烈自然情感(以孝悌为基础)属性的道德情感。行仁、践仁并非出于外在的规范要求,更多是来自人性内在的道德欲求。孔子言“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4]12,其所“欲”者显然不是自然情欲或物欲,而必然包含了某种道德价值目标。
圣人固可从心所欲不逾矩,但对于现实境遇中的普通个体来说,道德情感的表达——某种程度上也是因其自然性——却往往因环境和物欲的干扰而难免有过与不及之患,由此必然陷入荀子所揭示的因欲而求、因求而争、因争而乱、因乱而穷的政治衰败逻辑。于是,无论是个体修养层面的“不学礼、无以立”[24]178还是社会政治层面的“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11]76,礼乐之于道德精神秩序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建构功能与规范意义便被发挥出来,而其功能机理就在于“治人之情”,即情感的教化与涵养。《礼记》中有关道德情感和世俗人情的论述材料十分普遍、丰富,如:“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5]618;“教民相爱,上下用情,礼之至也”[5]1220;“哭泣无时,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5]1352等等。显然,这些材料中的“情”皆要从圣王政治的实践场域和世俗社会的伦理语境来认识,具有强烈的功能化意蕴。圣王通过治人情以化人性,达到治理国家社会的目的,这种情感不是个体的自然情欲,而是表诸君臣、父子、夫妻等世俗伦常关系的道德情感,也就是《礼运》中所说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礼运》道:“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5]607“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是“弗学而能”的自然情性(10)“七情”并非单纯的生理性本能,而必然是个体身处具体的道德情景所产生的情绪反应,既有自然性也具社会性。,“十义”则是修身治情的礼义观念,亦是儒家对十种基本社会角色提出的道德要求,它既是自然情性的人化或道德化,也是道德情感在人伦世界中的具体化,正是这样的道德情感维系了“大人世及以为礼”[5]583的宗法社会与家国体制。十义本于七情,而十义之能治七情恰在于其源于七情。《礼记·问丧》曰:“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5]1354礼乐并非如律法刑政一般从外部强制人性、规训情感,而是尊重人性的需求,遵循情感的规律。礼生于情而能治情,非礼亦无以治情。由是不难理解,从人文价值视角来说,礼乐实是一套藉由涵育、节制情感来培养道德人格、教化社会人伦以合政教之用的形式化(审美化)、制度化的规范系统,这也正是作为“人道之极”的礼乐文化的价值所在。
如果说形而上之天道必然要下贯到人间场域和世俗世界而凝聚为以礼乐为主要形式的人道文化实体,则在儒家体用不二、天人一体的思维模式和精神结构中,包括人间礼乐在内的一切人道实体必然也要反溯天道、回证天命。《礼运》言礼乃“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或谓“达天道,顺人情”。既然作为“天道之所藏而人道之所显”的礼乐可以贯通天人、接合内外,则不得不问的是,礼乐何以能藏天道而显人道?天与人在藏、显之间贯通合一的介质路径是什么?在我们看来,这一介质和通路就是情感。蒙培元曾多次阐发“情可上下其说”的观念,“这里所说的上、下就是形而上、形而下的意思,……从下边说,情感是感性的、经验的,是具体的实然的心理活动。从上边说,情感能够通过性理,具有理性形式。或者说,情感本身就是形而上的、理性的”[26]。这种“理性情感或者叫‘情理’,与天道相联系”[27]。这里对情的上下分判或许失之武断和绝对,但对情的形而上之维的揭证却为我们从情感通路把握礼乐美学的形而上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持。如果人间礼乐的价值依据与功能指向是基于血缘亲情的形而下的道德情感,那么理解礼乐语境中关联于天道的超越的形而上之“情”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先看《礼记·礼运》和《乐记》中几则有关“情”的材料: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礼运》)[5]585
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礼运》)[5]617
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礼运》)[5]614
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乐记》)[5]1006
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记》)[5]1034
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乐记》)[5]1000
细审以上材料可以发现,其所谓“情”或“人情”,确有心理层面“感于物而动”的情欲、情绪的经验性,但更指向一种超越感性活动的恒常存在,包含了“情”作为人之为人本来既有、本来应有的某种价值规定的先验色彩和本质意义,是《乐记》所言“情之不可变者”。这种不可变之情向下展开显现为世俗人情,向上原系于天道性命,是人与人、人与天地鬼神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存在关联,具有一定的本体性内涵与形而上色彩,或可名之曰“本原之情”,而要深入理解此“本原之情”,便不得不将之回置到先秦儒家性情论背景中加以探证。
正如我们所知,“中国哲学里的情,一般都得随性而出”[28]。早在先秦思想中,“情”和“性”就是两个紧密相关却各自独立的范畴,“情”的不同意义多数要在情性的关联语义中获得说明,而“情”之哲学本原正来自它与“性”的结构性关联。《礼记》中的“性”具有多种内涵,但最重要的定义还是《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朱熹注曰:“命,犹令也。性,即理也。……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行,所谓性也。”[13]19简单来说,性得自于天,是人秉受天理或天道而含具的完满和谐之态,是人性圆融未发的原初本体。不能否认,就“性”上说,无论孔子罕言“性与天道”的缘由、孟子性善论依系的天命观还是《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存在论评断,都说明“性”在先秦儒家那里的确具有形而上的思想意义。但与此相对,“情”却并不纯指形而下的道德情感乃至感性的身体情欲,而是具有向人、向天的两个指向。
作为思孟学派重要文献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是先秦儒家论“情”的经典,其年代、内容与《礼记》十分相近(11)陈来就认为,“荆门郭店楚墓所出土的竹简中,《缁衣》等十四篇为战国时儒家所传文献。以现存文献与荆门竹简十四篇相比照,最接近者为《礼记》,这在内容、思想、文字上都是如此。这也是大家所公认的”。见氏著《郭店简可称“荆门礼记”》,载《人民政协报》1998年8月3日。,两者之性情论实可构成互证。《性自命出》所论之“情”,不仅指世俗生活中的真挚情感,更突出强调了超越具体情感的情的抽象的一般性本质,后者集中体现在开篇一段:“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简3-4)[29]3这里展示了一个由天而命,由命而性,由性而情,由情而道的宇宙生化模式。不难看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与《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一句语意切近。性由天所命,情生于天命下降之性,是性之本体原质的显现,如此性情互证,性与情都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再看“道始于情”一句。从同属思孟学派经典并关联整个战国思想语境可以相信,此“道”之义当类同于《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中的道,朱熹注此句曰:“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13]20其当指社会伦常、礼乐政教等人事规律与法则,即人道。但同时,此“道”循天命之性贯落而出,朱熹言“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13]20,其必然指涉天命而内具形上之维。我们从“道”的双重性意涵(《中庸》所谓“合内外之道”)可合理推知,其所源出之“情”同样应是“上下其说”、天人同摄的。很难说这个“情”与《礼记·礼运》“承天之道,顺人之情”“达天道,顺人情”的“情”不是同一个“情”,即情显道,道由情生,即道用情,情从道化,情与道在此意义上可谓相生而在,贯通无碍。程伊川说得明白:“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谓之性善。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30]318
可见,在由天、道、性、命等概念构成的形而上学语境中,“情”绝不会停留于“血气心知”层面,也不仅止于道德情感畛域,而必然要在个体情理互证、身心相得的修养实践中回归天道性命的源头,这种修养实践正是藉由礼乐活动展开的。《性自命出》曰:“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后之序则义道也。或序为之节,则文也,致容貌所以文,节也。”(简19-20)[29]4面对大千万物,要依据事实、义理来安排事物的先后次序,这符合道的价值指向,这种秩序安排的形式化、制度化就是礼仪,而礼仪有此功能的关键在于节制人情。在这里,“礼作于情”之“情”者,确实含有人情、情感的意思,礼的制作是出于节制、教化情感的需要,这是从功能论角度讲。类似说法在《礼记》中同样十分普遍。另一方面,“礼作于情”之“作”者,又有始、生的意思,郭店简《语丛二》亦有“礼生于情”一句。从宇宙生成论角度说,礼是由情生产、创造出来的,这种情自然不是感物而动的心理情绪或日用伦常中的道德情感,而是一种具有始源性质的创生力量,即《礼记·乐记》所言“天地之情”(12)《乐记》原文:“礼乐偩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礼记·丧服四制》道:“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5]1468“人情”与天地、四时、阴阳这些自然元素都是统一的宇宙力量——其内含的原则和规律即为天道——的构成部分,从而也一同成为礼的创生条件。礼固然是为节情、治情而作,但这也正表明情在礼先,情之于礼就存在逻辑言具有优先性。《乐记》云:“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所谓“本之情性”,既是从生成论意义上说明礼乐所出之源,又揭示了圣王制礼作乐的本体依据和价值关怀。而这种先在于礼的“情性”之“情”显然超越了世俗人情的范畴,它既指包括前者在内的自然万物、人间世界呈其所是的本然情态(它尤其表诸人的生命情态),更含有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30]460的天地情怀。本然情态乃宇宙规律和万物原理的自然显现,天地情怀则是儒家个体身心修养和政教实践所企冀达成的生命境界和精神气象。两种“情”虽分言物与我、外与内,却都是本于天而显诸人的,依性质即是前文所说的本原之情。
综上所论,情感不仅是人间礼乐的发生原理和功能依据,它更指涉、含蕴形而上维度而具有超越性的精神意蕴。作为“情之不可变者”,这种超越的本原之情尽管与性和天道紧密相联,但它本身绝非是与经验世界相隔绝的抽象的形而上本体,而是深刻嵌入到人的生命情境和生活境域之中,并藉由礼乐文化实践获得具体表现。在此意义上,情感因能同时涵盖形上、形下之域而成为主体在礼乐世界中接连天人的精神通路,也正是这种基于情感内核所构造的礼乐形而上学与西方以纯粹理性思维考辩存在本体的哲学形而上学区分开来。
余 论
丰富细密的情感主义叙事和对情感价值的高度彰扬,构成了先秦儒家礼乐美学的思想根基,也正是作为体系核心构件的性情论,使礼乐美学的形而上精神与儒家的天人思想一脉相通。其实,在先秦儒家礼乐哲学、美学视阈中,“情”的义涵与用法并非如现代知识学所辨析得如此泾渭分明,情之本原与发用无法判为两截,离却世俗人情更无以言天地情怀。天道与人道、超越与世俗、本体与工夫、已发与未发皆有且仅有在一个“情”上见出,此“情”可谓彻上彻下,道通为一,即凡而圣,应天而从人。礼乐“称情而立文”,实谓礼乐之上下、四方之精神结构和价值世界皆由情而张立而运行,亦由情贯通一体,成其文化之整体。
事实上,无论是天地神人在礼乐活动中的感通交流还是礼乐制构下的政道教化,其本质都是基于日常现实中的人的情感需求所展开的精神叙事和生命实践。由此不妨说,礼乐正是一套以天道为依归、以现实生活为场域、以身心情感为对象、以政治伦理为目标的具有强烈审美风格的人文价值系统,礼乐美学的形而上精神也只有从这样的人文价值视角才能获得准确的理解。在此意义上我们进一步认为,礼乐美学固然不能排斥以礼仪、礼器、礼容等礼乐形式为对象的审美鉴赏、审美分析问题,但其理论叙事根本上应围绕如下问题展开:为实现个体的生命证成,为建构理想的天人关系、政治形态和伦理秩序,礼乐应如何培育与之相应的心性条件?对此问题的回答可以是政治的、道德的、法律的、宗教的,但本质上是美学的,据之发展出的审美修养论(个体生命)、审美教化论(社会政治)和审美超越论(天人关系)则构成礼乐美学的理论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