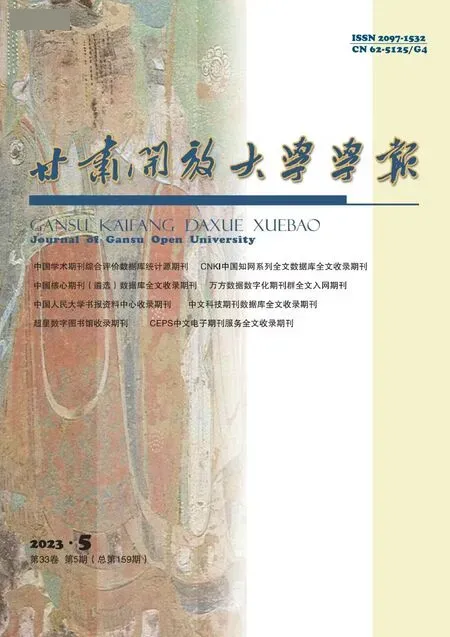文学地理学视野下“脚客”贾平凹的游记散文
陈欣月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地理意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从古至今都引发学者的关注。以往文学中的地理意识都是比较零散的,自20 世纪80 年代起,文学地理学逐渐从萌生了将文学与地理融合的意识过渡到自觉的理论建构甚至是学科建构。从金克木的《文学的地域学设想》、袁行霈的《中国文学概论》、严家炎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到曾大兴、邹建军、梅新林、杨义等人的著作与文章,文学地理学不仅成为一种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方法,更成为一门不断建设发展的学科。曾大兴提出“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1]。梅新林将文学地理学定义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2]。这些都可以看出文学地理学发展为学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经过不同代际学者的努力,文学地理学逐渐系统化、学科化,开辟出迥异于并且互补于时间线索的一条空间路径,有助于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打开新的研究面向,对于贾平凹的研究即可采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及视角。
贾平凹的文学书写受到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风土人情的影响,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通过对不同地域的感知,尤其是从故乡生活获得的“地理感知”与储存的“地理记忆”使贾平凹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基因”,“地理基因”影响着其创作的审美选择与思想表达,其构建的文学世界也时常渗透着地理因素。当前对于贾平凹散文创作的研究,更多是对其散文观念、艺术特色、审美意象、创作意识,如生命意识与禅宗意识等的研究。以空间地理的角度分析贾平凹散文的成果较少,而贾平凹的散文论物、论景、论人、论史、论情,其笔下包揽的万千事物与其行走时见闻之广不无关联。贾平凹曾将其散文集命名为《脚客》,“脚客”亦代表着行走中的贾平凹,他以真实的行走感受世间。因此,对贾平凹的散文研究不得不重视其游记类散文。其游记类散文已经结集为几本散文集,如《平凹游记选》《贾平凹游品精选》《南北笔记》《贾平凹游记》《平凹西行记》以及《脚客》,这包含了贾平凹大多数游记散文。所谓“游记是以描摹山水名胜,记叙游踪风情为内容的散文。它必须具备地理因素和文学因素。所谓地理因素,是指作品中一定要涉及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包括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地形地貌、游览线索等。所谓文学色彩,是指作品不是纯客观地模山仿水,而是进行文学性的描绘,景中有情,事中见理,或者通过山水描绘,透露出作家的思想境界,感情流向。”[3]游记散文兼具地理与文学因素,因此以文学地理学之视角、方法来重新爬梳贾平凹游记散文或许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几个关键词,如“地理基因”“地理影像”“地理景观”“地理思维”等切入作家本人与其文学创作,分析地理环境对作家的形塑作用以及对其审美选择的影响,探讨文本中所选取的重要地理景观,从而进一步挖掘作家的地理思维以及文本中地理因素所蕴含的不同维度的心理指向。
一、“地理基因”影响下的审美选择——农村图景
在学科理论建构中,邹建军教授以关键词研究的方法对文学地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既丰富了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资源,也提供了分析具体文本的“认知装置”。“地理基因”即是其提出的概念之一。“所谓‘地理基因’,是指地理环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痕,并且一定会呈现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4]29创作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家如鲁迅、沈从文、莫言、贾平凹等,他们的作品里都渗透着“地理基因”,尤其是少时地理环境的影响更是挥之不去,成为其创作的根基与贯穿始终的血脉。
贾平凹出生并成长于陕南商洛地区,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十分复杂,“八山一水一分田”便是对商洛地区自然环境的概括。“毛泽东主席曾手书《再宿武关》,其中有‘乱山高下入商州’的名句。清代郑燮有‘云掩商於万仞山’的佳咏。境内北有蟒岭,中有流岭,南有鹘岭,相间丹江及其主要支流银花、武关、老君三河,岭谷交错,呈‘掌状’地貌。山石嶙峋,岩崖嵯峨。”[5]2-3多山的地势影响着交通的发展,形成相对闭塞落后的环境。贾平凹在去西安求学之前长期浸润在商州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早期19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构筑了他最初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成为内在基因沉淀下来。农村的生活环境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基因”,储存了属于乡土的“地理记忆”,使得贾平凹在写作时时刻坚守着自己的农民身份与农民视角。在故乡成长的见闻,尤其是对农村生存及发展的切身体会、对乡人焦苦生活的观察以及对特定地区不同时代氛围的把捉,都使贾平凹能够执守着真情实感来代替农民这一“失语者”群体发言,其农村题材的创作也更加贴近大地与底层人民。成长经验在作家的意识里会形成“先结构”,先在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着后来的文学选择及文学创作。正如贾平凹长期生活于商洛农村的经验形成了自觉的农民意识,这种“先结构”使农村成为其审美选择的重点取向。其小说对乡村图景的构建已无需多言,其游记散文也常常将视角聚焦于农村。《商州三录》作为“商州系列”的奠基之作,移步换景般地记录着商州农村的事事人人,从黑龙口到龙驹寨、从棣花到白浪街,商州这一叙述母题是商州山水及人文环境对贾平凹的长期影响,形成了商州的“地理基因”后所作出的审美选择。虽说商州是贾平凹的一张名片,奠定了其在陕西作家以及当代文坛的重要地位,但贾平凹对农村的审美选择与文学呈现并没有局限于商州,而是通过行走将当代社会不同地区的农村图景纳入其观照视野,如江浙农村、甘肃农村等。1996 年初,受中宣部、中国作协安排,贾平凹前往江浙,写下了《江浙日记》。通过日记中的走访与谈话,贾平凹展现了江浙地区农村的富庶与发达:房屋的豪华、商业的发展、思想的先进,与陕西农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凸显出东部与西部发展的巨大差异。因受“地理基因”地影响,那些贫困的农村更吸引着贾平凹的注意并引发更为深切地思考。贾平凹认为自己由农村走出,生命里或许包蕴着些许贫贱的基因,这使他的行走更倾向于贫苦农村,如陕西韩城、合阳、朝邑以及运城、临汾、陇右等地区,都是其视野与足迹所及的地方[6]4。陕南农村的“地理基因”使贾平凹偏爱着与故乡相似的地理环境,成为其观照异地农村的参照,他对农村的深沉情感与真实表现,也与其实地考察式的行走有关。同样书写故乡村庄的梁鸿就曾指出:“2002 年《中国农民调查》所引起的热烈反响可以说是对作家乡村想象的最大打击,虽然它的成功并非在文学意义上,但是,它告诉作家一件事:乡村现实所蕴含的残酷和苦难远远大于作家廉价的虚构和坐在书桌旁的空乏幻想!”[7]因此,贾平凹走出书房的游记类散文更能真实地反映农村的生存现状。
二、“地理影像”的呈现与生存状态的自审
“‘地理影像’是指文学作品里的与地理相关的图像与意象,以及与地理相关的物质形态的东西。”[4]30“地理影像”包括现实中的物象以及虚构的物象。贾平凹游记散文中呈现的“地理影像”更多的是现实中的物象,其所选择的现实景象并非简单地作为布景之用,更带有深层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现实因素,其背后是对人之生存状态的深刻自审。正如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论述“文学地理景观”时所认为的那样,文学地理学不是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文学作品对地理的描写也不只是记录,还带有对地理及相关因素的思考[8]。游记虽然是对现实的记录,但在文体上仍归类于文学,所以当现实的地理景象进入文学中,就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更包蕴着审美内涵及文学意义。贾平凹游记中所呈现的景象,如房屋、道路等,其存在与变化的形态都与外在的世界相联系,经济的发展、政策的实施、现代化的转变等,诸多因素都影响着当地地理环境与地理景象的变化。贾平凹将种种图景纳入文学领域,在展现现实景象的过程中也夹杂着对世界的思索。
(一)房屋:荒凉与出走
“人之不能无屋,犹体之不能无衣。衣贵夏凉冬燠,房舍亦然。”[9]房屋不仅是物质性的地理存在,更凝聚着人们的精神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房屋意味着家,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亦是情感的寄托,农村人盖房的执着与城市人买房的执着都彰显了中国人特有的房子情结。“农民的一生,最大的业绩是在自己的手里盖一院房子。”[10]163农民将盖房作为人生大事,因此,对于农村地理环境的考察不得不重视房屋这一地理景象。贾平凹在其游记散文中经常描写房屋的外部形态与内部设施,房屋的样式与变化也反映着一个地方的生存及发展现状。《江浙日记》描绘了江浙农村房子的富丽堂皇,从外观到内在设施,都不同于贾平凹见惯的西北农村,单从房屋这一地理景象即可看出中西部与东南地区的差异,引发着贾平凹对中国中西部尤其是其生活的陕西农村的忧虑,反思着影响发展的种种因素,如自然环境的恶劣、内陆环境的闭塞、文化观念的落后等,映照着贾平凹的自审心态。在去甘肃农村时,贾平凹的《定西笔记》又呈现了异于江浙农村的房屋景象:“巷道很窄,还坑坑洼洼不平整,巷道怎么能是这样呢?不要说架子车拉不过去,黑来走路也得把人绊倒。两边的房子也都是土坯墙,是缺少木料的缘故吧,盖得又低又小。……老婆子的脸非常小,慢慢话就多起来,说她家的房子三十年了,打前年就想修,但椽瓦钱不够,儿子儿媳便到西安打工去了,家里剩下她和死老汉带着孙女。”[6]11-12农村的艰苦条件通过又低又小的土坯房以及狭窄不平的巷道显现出来,这种荒凉的景象背后是农村落后的现状。落后与贫穷逼迫着安土重迁的农民不得不选择出走甚至是逃离,留下的是难以流动的老人和儿童。而农村人口的流失又加剧了房屋的破败,形成恶性循环。在《条子沟》里,贾平凹将目光置于村里的一间房子上。“村子模样还在,却到处残墙断壁。进了一个巷道,不是这个房子的山墙坍了一角,就是那个房子的檐只剩下光椽,挂着蛛网。……这院子很大,厦子房全倒了,还能在废墟里看到一个灶台和一个破瓮,而上房四间,门窗还好,却成了牛圈。”[10]48房屋的破败是由于其主人已经落脚于城市,留下乡村的旧房子无人居住。贾平凹以房屋为观察视点,最为直观地展示出农村的生存条件。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使城市像磁铁一样不断吸引着农民迁移至城市,农村人口大量流失,愈加凋敝,更影响了农村建设的发展,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是否还能保存成为贾平凹的心结。不仅是房屋的外部形态,房子的内部格局与设施也隐含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精神寄托。贾平凹在《定西笔记》中展现了甘肃农村房屋的内部景象:很多家庭无论房屋的好坏,都会在屋子的中堂上挂起字画,而且讲究书画家的德行、职位和相貌,定西人还在中堂的柜盖正中央摆放着或多或少的宝卷。对于贫苦地区来说,能体面地摆脱贫困的最佳路径即是升学,因此中堂上悬挂的字画不单是作装饰之用,更重要的是营造一种文化气息,体现着农民对知识与文化的尊重与景仰,其背后是祈求子女能够通过学习之路摆脱当下贫苦命运的宿愿。贾平凹由教育之用的字画联想到行贿倒卖之用的字画,农村对知识文化的纯粹情感不禁让其更反感于当下社会以物行贿的不良之风。房屋这一地理影像既是现实生活中的重要物质存在,也是承载着社会文化意义的关键地理意象。
(二)道路:变动的地理景观
路是人类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它勾连着地方与地方,维系着人类社会。在《周武寨》中,乡人们对路的崇拜已经渗进日常生活,甚至男男女女的名字中都带有路字,或与路相关。道路顺境适应,随地势而变,沟通着物质、风尚、人情的往来,因而周武寨人崇尚着坚韧而灵活的道路。“故在这一带,山民们最崇尚的,一则是天上的赫赫洪洪荒荒的太阳,二该是地上的坚坚韧韧粘粘的山路。”[11]232周武寨人将路与太阳视作同等地位,可见路之于人的作用也是无穷的。自古以来人们就重视开辟道路,就中国而言,陆路如丝绸之路,水路如京杭大运河,这些道路从开建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运输货物、促进交流,如今也成为重要的文化景观。在近现代经济飞速发展的环境下,对于路的开发更是重中之重。贾平凹游记散文中选取了农村中道路这一变动的地理景观来反观人们的心理状态以及农村的发展状况。《黄土高原》中以路映照着圪崂洼里的人们对外部世界的重视。当道路被连天的雨水冲垮后,全村人都会为之担忧,并会齐心协力地背着锄头去修路。不仅如此,道路的开通也带来了现代文明,不断冲击着乡村的原始生活方式。“公路是新开的,路一开,外面的人就都来过。……客人走过,窑背上的皮鞋印就不许被扫了去,娃娃们却从此学得要刷牙,要剪发……。”[12]道路的开辟与变动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影响更为明显。《从棣花到西安》更是聚焦于道路这一地理景观,展现了不同代际下人们从棣花到西安的方式。棣花到西安,途径蓝关,古代韩愈经行此路,发出“雪拥蓝关马不前”之感叹,而从父亲的年代到如今,这条路的面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父辈时代,父亲只能步行上学,而“我”去西安上学时有了公路。20 世纪90 年代初公路又由沙土路改造为宽阔的柏油路,2000年后铁路开始建造,当火车开通不久后,八车道的高速公路也开始修建并通行。[10]65-68路的发展使棣花从闭塞到开放,这个隐匿于山间的村庄逐渐被人们发现并成为旅游景点,由此牵动着其他因素的变更,洋楼老街的修建、汽车的随处可见、房价的飞速上涨,都是道路因素带来的变化。不仅物质层面发生变化,人的心态也随之变化。以往交通不便城乡互通困难,闭塞环境下的农民在走进城市时,由于环境的巨大差异往往会形成自卑意识。但路的变动使城乡之间的各种信息迅速传递,如政策、风尚等,缩小的差距减缓了城市对进城农村人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的自卑。但是,路的发展同时也冲击碰撞着农村原生态的生活,尤其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冲突,使乡民为利益所驱而导致传统道德式微。贾平凹对于农村与现代化进程的心态始终是矛盾的,一方面现代化发展带来便利和逐渐富足的生活,但另一方面路沟通了闭塞农村与外界的联系,也使农村难以保留其原始面貌。贾平凹选取道路这一变动的景观,观察由此辐射出来的时代变化,具体而微地展现了农村里发生的震动与异变。
(三)庙宇:精神寄托的神性空间
据《丹凤县志》记载,商洛从古至今建立了许多寺庙:唐武后年间(684—704)先后在商洛县城南建商山寺,在县城东街建灵光院,在棣花街建昙花庵。唐玄宗大中元年(847)在显神庙村为伍子胥建显神庙,其后在棣花驿建法性寺。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在商州东棣花东街建二郎庙,清代又在二郎庙东侧建风格相近的关帝庙。[5]8-10陕南秦楚交界的地理位置以及多山的地理环境使巫鬼佛道盛行,寺庙的建立既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又强化了巫鬼佛道之风。贾平凹的创作具有鲜明的佛道色彩,这使其超越单一视角而具备了天地人神相贯通的多元视角来观察人间世事。佛道思想的浸染使贾平凹在游历中常常选择寺庙、道观,庙宇也因此成为贾平凹游记散文中的重要地景,如《松云寺》《张良庙记》《灵山寺》《仙游寺》等直接以寺庙名称作为游记篇名,此类游记散文大多独抒性灵,倾述着对历史、人事、自然的感悟。还有一些游记散文虽未以寺庙名称直接作篇名,但都记录了寺庙这一景象,并通过寺庙传达着精神观念。庙宇的建立承载着人们不同的情感,或感激或期盼,如盐井镇的人们因“盐井生民,感念神灵”建立盐神庙。盐作为当地重要产物维系了人们的生存,在现代社会中甚至已成为产业,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当地人们对于神明的感激转化为物质性的存在而建立盐神庙。鸠摩罗什去中原时在天水和定西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在沿途建有很多寺庙。当地人在高考时去庙里祭拜,认为神知道这个地方苦焦,给娃娃剥农民皮哩[6]96。在《又上白云山》中贾平凹分析白云观产生的原因是“生存的艰辛,生命必然产生恐惧,而庙宇就是人类恐惧的产物,于是佳县就有了白云观”[10]116。在农村,艰苦的生活环境加剧了人们的生存难度,对于生存的恐惧以及生产、生活的需要,农民将自己的愿望寄托于神灵,人们去庙宇祈福或为感谢上天的恩赐,或希望摆脱当下的贫苦命运,无论寄托着何种愿望,庙宇都成为告慰人们精神的神性空间。贾平凹思索到:“中国农村几千年来,环境恶劣,物质贫乏,再加上战乱频繁,苦难那么多而能延续下来,社会靠什么维持?仅仅是行政管理吗?金钱吗?法律吗?它更要紧的还是人伦道德、宗教信仰啊。”[6]16庙宇这一地理空间对于人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于生活苦焦的人来说,它给予人希望并赋予这些贫苦之人寄托情感的空间以及情感宣泄的途径,进而支撑着那些生存于苦难之中的底层人民,维持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当时代发展后,生存问题逐渐转变为生活问题,人们到寺庙的心境亦有变化。白云观因佳县人们之于生存的恐惧而建,现在已门庭若市,怀揣着不同愿望的人都来这里祭拜,穷人和富人来这里焚香敬神,求取功名、学业、健康。贾平凹在游历中关注着不同时代下的不同景象,并展现着种种景象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时代特征以及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变动,如由庙宇可见生之艰难,亦可见形色各异的欲望。
三、多重视镜下的深度思索
贾平凹的主要居住地有两个:一是本籍,即出生成长之地陕南商洛地区。二是客籍,即贾平凹走出商州后定居的西安。本籍地的文化即商州文化对于贾平凹来说是“文化母体”及创作之“原色”[13]。70 年代贾平凹到西安求学、工作,继而定居于西安,西安成为贾平凹第二个故乡,城市生活亦牵动着贾平凹书写观念的变更。“空间的流动,往往可以使流动主体的眼前展开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化区域和文化视野,这种‘双世界视景’,在对撞、对比、对证中,开发了人们的智慧。……两个世界的对比,可以接纳、批判、选择、融合的文化资源就多了,就可能开拓出一种新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深度。”[14]西安的城市生活经验与故乡的农村生活经验对撞,城市与乡村的双重生活经历使贾平凹具备了杨义所说的“双世界效应”。所以贾平凹在观察农村时,增加了城市视野,在城乡的比对中更能发现乡村的优长与落后之处。不仅如此,贾平凹的一生是流动的,陕西、甘肃、新疆、川渝、江浙等地区的行走经验使其精神世界更为丰富多元,所以其游记散文中对农村的自审更为真切深刻。
首先是理性与情感的背反。“我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从农村到西安的,几十年里,每当看到那些粗笨的农具,那些怪脾气的牲口,那些呛人的炕灶烟味,甚至见到巷道里的瓦砾、柴草和散落的牛粪狗屎,就产生出一种兴奋来,也以此来认同我的故乡,希望着农村永远就是这样子。……但我也明白我所认同的这种状态代表了落后和贫穷,只能改变它,甚至消亡它,才是中国农村走向富强的出路啊。”[6]16理性视域下,原始的农耕状态意味着落后与贫穷,城市化的过程将改变发展落后的局面,逐渐实现更为均等的发展,但在感性的情感中,贾平凹对传统乡村持有眷恋的态度,乡村纯净的山水、仁义礼智信的乡风,都是其难以割舍的对象。一方面期盼着农村向前发展,抛却苦难,另一方面又对发展中农村发生的异化失落、无奈,这两种矛盾的情感在贾平凹的思想中不断搏斗着,无论小说还是散文,对于社会时代的关切,对于道德信仰的关注始终如一。作为知识分子的贾平凹直面农村种种问题,尤其在长篇游记散文《定西笔记》中,对于农村发展及农村政策存在的弊病更是直言不讳。如耗尽家庭供养的大学生更多的选择留在外面,不仅农村的财物被掏空,人才也不断流失,如此恶性循环更难以摆脱贫苦境遇。还有农村中存在危险性的水泥预制板房、公路沿途体现地方政府政绩的搪了统一白灰的房墙,而在鲜亮的背后仍是破败灰黑,如此问题都是农村真实存在的。贾平凹没有遮蔽真相只顾表现农村光鲜亮丽的一面,而是发挥着文学的“公共性”能力,深度思考着农村制度、发展的种种,体现了当代作家的责任与担当。其次是对时代氛围的把握,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生活方式与精神气度的变化。贾平凹一直重视对流溢于社会中的时代氛围的表现,通过所在时代的原生态样貌,如人们真实的生存境遇与生活变动呈现时代精神与时代氛围。贾平凹小说如《浮躁》《废都》《高兴》都追踪着社会现实并抽象出时代特征,他始终关注时代并书写时代。不仅小说,其游记散文也是如此,时刻展现着社会时代下人们的生活状态。正如《商州再录·题记》所阐述的随着时代的嬗变,居住于此的山民既保存了古老的传统遗风,又渗进了现代的文明时髦。在对待土地、道德、婚姻、家庭、社交、世情的诸多问题上,夹杂着不同时代的观念,呈现出美丑善恶交互的状态[11]228。时代的变迁牵动着人们生活的变动,冲击着既往的物质存在和精神信仰。对于闭塞的农村来说,外来风气的渗透影响着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经济政策的推行使农民不再拘囿于土地而开始经商,吃穿住行都与时代发展相联系,人们的精神面貌也逐渐改变。贾平凹对时代的把握,正是通过诸多的生活细节来展现,细致地描摹出时代洪流裹挟下的人生百态。贾平凹的游记散文包含着对不同地域地理景观、风土人情、历史传说的记录,他不仅将种种地理要素纳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还由此引发着对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思考。
四、结语
“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如漫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15]150贾平凹时常提起自己的农民身份,可见故乡这一地理环境,包括内在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贾平凹其人其文的形塑作用。少时的“地理感知”形成着离开故乡后的“地理记忆”,多重记忆的叠加又凝结为更为内在也更为持久的“地理基因”,如此种种促进了贾平凹“地理思维”的形成与深化,并输出为文学文本。贾平凹之所以在小说和散文中都以乡村为重要的取景图像,是浓重的恋地、恋乡情结引发的对故乡命运的深度思考,并由故乡推及整个中国乡村。在急剧发展变动的时代,乡土空间不断被冲击甚至被蚕食,原有的社会结构与传统的精神向度难以为继。贾平凹文学世界的建构带有文学地理的意识,一方面实现了对农村发展的记录,凸显着时间维度下的空间变迁,另一方面也是对乡土记忆的强化,物质性存在的乡土空间已逐渐成为过去式,为了保留对乡土空间的记忆与想象,贾平凹乡村主题的小说与内含乡村因素的散文是十分有价值的。商州是贾平凹的文学发迹地,但他并没有拘囿于一时一地,而是传达着对中国农村普遍命运的关怀。游历的见闻使贾平凹在对故乡书写的基础上具备了更加开阔的眼光,他不是苦坐于书房内闭门造车,而是走出书斋回归大地,所以更能超越地域的限制,以历史性、现代性、普遍性的多元视角重审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