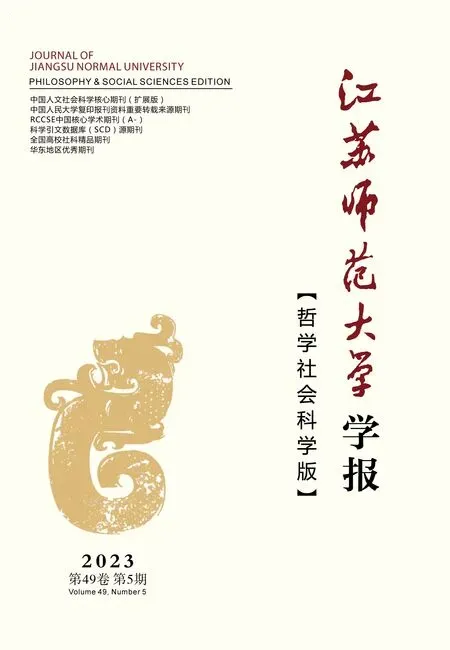宋代“宣医纳命”说考论
肖红兵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官员病卒之际皇帝或亲临视疾或遣使视疾,比较积极地开展视疾临问活动,甚至针对部分大臣的病卒皇帝生发出“未能视疾为恨”的追悔之情。在官员病卒之际,无论是皇帝亲临视疾还是派遣中使(内侍)视疾,一般都会宣诏医官随同前往诊视病情。这种宣医诊视疾病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礼遇,体现的当是皇帝关心、优待、体恤臣僚的特殊眷遇情怀。宋代官员病卒之际的临问视疾待遇主要分为亲临问疾、遣使视疾、宣医诊疾三种类型,呈现出“降中使以抚存,命大医而诊视”(1)(宋)杨亿撰:《武夷新集》卷17《代参政王侍郎陈乞状》,《四库全书》第108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70页。、“降医走使,不绝于道”(1)(宋)杜大珪撰,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15《吕文穆公蒙正神道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336页。的皇帝“临问”患病臣僚的政治生态和文化意蕴。皇帝看望臣僚疾病一般被尊称为“君问臣疾”,所谓的“疾”包括官员日常身体疾病(能够治愈之疾)和生命死亡疾病(导致生命终结之疾),本议题探讨的“臣疾”专指官员病卒之际生命即将死亡期间的疾病。从宋代的政治礼法来看,与皇帝临问宗室亲属疾病不同,皇帝亲幸官员宅第临问视疾臣僚属于皇帝的特恩眷顾和政治优待,临问视疾的对象多为大臣、重臣、勋臣等人,而不是一般臣僚所能够获享的普遍的政治礼遇。宋代皇帝针对异姓官员病重的宣医诊疾待遇的施行主要分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伴随着皇帝探视临问病重臣僚时宣召医官同行;第二种是在皇帝遣使探视病重的臣僚时宣召医官同行;第三种是单纯的宣召医官前往官员宅第探视和诊治病重的官员。从宋代官员病卒之际的临问视疾实践来看,宣医诊疾是皇帝关心、探视、体恤臣僚生命健康的主要形式,这种宣医视疾行为随着诏葬制度在北宋中期式微而逐渐异化,最终与诏葬制度一起演绎出“宣医纳命,诏葬破家”的宋人眼中的特殊文化意象。关于宋代官员病卒之际宣医探视和诊治臣僚疾病的议题,学界尚未有直接专题成果,部分学者在探讨宋代官员疾病、医疗与卒葬问题时,涉及对“宣医纳命”谚语的引用和解析,但是侧重点多在“敕葬破家”层面,较少论及“宣医纳命”谚语产生的政治因素和文化意蕴(2)除了本人《宋代诏葬制度初探》(《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5期)一文对“宣医纳命,诏葬破家”谚语进行初步分析外,涉及引用宋代“宣医纳命,敕葬破家”谚语的相关成果如熊恩剑《宋代民间的话语——以笔记小说为中心的考察》(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5月,第36页)、孙朋朋《宋代谣谚与政治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6月,第40页)、徐战伟《宋代归葬问题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6月,第49-50页)、孙丰琛《礼制下移与习俗上行——北宋墓葬形制所见礼俗问题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9月,第72页)、张雅娴《宋代护丧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6月,第59页)、赵笛《宋代皇帝问疾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6月,第73页)等。其中,方燕《〈宋诗纪事〉时政谣谚论略》一文指出:“‘宣医纳命,敕葬破家’道出百官表面上沐浴皇恩,实则有性命之忧、财产之险的无奈。皇帝宣太医诊视罹病的臣僚以示恩宠,太医用药急于收一时之效,结果适得其反,病者往往性命不保。”(《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75页)。张嘉文《宋代时政谣谚研究》指出:“宋代官员生病,皇帝会宣太医诊视罹病的臣僚以示恩宠,这种情况下太医往往不敢擅自开药方,用药需向皇上禀报,然后按照皇帝的药方治疗,但皇帝大多并不会治病,其所开的药方多数时候不但治不好病,甚至还会威胁患者的性命。”(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11月,第20页)。韩苹硕士学位论文《宋朝文官就医研究》第四章在引用“宣医纳命”相关文本后指出:“医官秉承皇帝旨意,又急于成效以便升迁,因而以当面为患病大臣投药为功劳。在这种环境下,病家则处于相对的被动地位,因慑于皇帝权威,难以较为准确的向医官陈述病情,又怯于抵抗医官所开之药方,而只好听从医官嘱咐,服下不对病症的药,故而造成宣医治病无效、反致死亡的情况出现。”(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6月,第54页)。。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从官员身后待遇视角对宋代宣医诊视病重臣僚所衍生的“宣医纳命”谚语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
一、宋代官员病卒之际的“宣医诊疾”实践
皇帝临问探视臣僚疾病时即宣医诊治,这种及时“宣医诊疾”的对象一般为宗室近亲或大臣、重臣及勋臣。对于普通官员患病至于“疾亟”,大多数情况是先遣使视疾,皇帝根据奏报病情再决定是否亲临视疾,一般官员难以获享皇帝亲挟太医诊视的待遇。因此,“中使挟医诊视”是宋代官员病卒之际朝廷宣医诊疾的主要形式,这种“中使挟医”诊疾行为涉及中使和太医两类人员的酬劳报谢,加重了患病官员家庭的经济负担,中使以皇帝使者的身份“彰显”皇权威仪,迫使患病官员用药,难以避免地导致了“宣医纳命”现象的出现。此外,就病卒官员所在地点而言,医官的派出地分为京师和京外,朝廷遣使挟医赴京外诊治重病官员,常常出现医官初至而官员即已病卒的情况,给人以“宣医纳命”的想象。这里的“医”一般被尊为太医或国医、御医、上医、尚医、内医等,因为他们除了诊治皇帝、后妃、宗亲等人员疾病之外,还主管供奉医药和承诏诊疾。例如,医官局“掌以医药入侍及承诏诊疗治众疾”(3)(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9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938页。,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4)(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9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0页。,表明医官局或翰林医官院医官本身就承担有诊治百官疾病的重要职责。
(一)单纯的宣医诊疾
在宋代官员病卒之际的宣医诊视活动中,最直接的视疾行为是皇帝听闻臣僚病重信息之后直接宣召医官前往官员宅邸诊视,这种宣医诊疾方式显然是一种只有医官参与的单纯的诊疾行为。从礼法程序来看,一方面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皇帝出于关心或担心患病臣僚的生命健康而“急忙”宣召医官前往诊视,是皇帝关心和体恤臣僚的一种本能体现;另一方面,皇帝不便轻易前往患病官员宅第,需要了解官员病情之后才能决定是否需要亲临视疾,一般会在宣召医官之后再派遣中使前往了解情况。与之相对应的是单纯的宣医诊视臣僚疾病的事例并不多见,如太平兴国三年春高怀德被病,“诏太医王元佑、道士马志就第疗之”(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50《高怀德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822页。,道士马志参与病卒之际官员的诊治当是实施“金丹”服用之术。同州、鄜州等缘边都巡检使侯延广被病,“遣太医随侍”,其后病发“上遣御医驰驿视之。医至,疾已亟”(6)(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53《侯延广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885页。,很快病卒。雍熙四年宦官王仁睿被疾,“遣太医诊视,卒”(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66《王仁睿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01页。。咸平元年冬,宋湜便殿奏事,“疾作仆地”,内侍掖出,“太医诊视,抚问相继,以疾亟闻”(8)(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87《宋湜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645页。。杨徽之属疾,“遣尚医诊疗”(9)(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96《杨徽之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867页。。景德元年七月,李沆疾作而归,“诏太医诊视,抚问之使相望于道”(10)(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82《李沆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40页。。皇祐三年秋,夏竦以疾请归于京师,“天子方忧思公,饬太医驰视。又以肩舆往迓之,而公疾寖剧矣。既就第,未几以薨闻”(11)(宋)杜大珪撰,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22《夏文庄公竦神道碑》,《四库全书》第4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453页。。熙宁二年三月,唐介“遽寝疾不朝,上遣太医日夜视公疾”,四月乙未神宗幸其第临问,“公寖剧不能言,上泫然出涕”(12)(宋)杜大珪撰,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19《唐质肃公介墓志铭》,《四库全书》第4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869页。。端明殿学士孙永“病不能朝,神宗遣上医调视,六命近侍问安否”(13)(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42《孙永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902页。。元丰二年十一月孙洙被病,“累日不朝,上驰遣太医诊治,内侍就问所苦者再”(14)(宋)杜大珪撰,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25《孙学士洙墓志铭》,《四库全书》第4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977页。。元丰八年四月丞相王珪感疾,“诏国医诊视,遣尚宫数就问,赐以御膳珍药”(15)(宋)杜大珪撰,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8《王太师珪神道碑》,《四库全书》第4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72页。,五月已酉薨于位。又如刘延让“以疾闻,帝遣内医诊视”(16)(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59《刘廷让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003页。。孙何被疾,“遣医诊视。医勉其然艾,何答曰:‘死生有命。’卒不听,是冬卒”(1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06《孙何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00页。。孙何对待医者“勉其然艾”的救治态度,反映了他“死生有命”的生命理念,但是该事例或许与当时“宣医纳命”的谣俗影响有关。又如,陈恕病重,“诏太医诊疗”(18)(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67《陈恕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203页。。孔维被病,“上遣太医诊视,使者抚问”(19)(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31《孔维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812页。。范纯仁寝疾,“遣国医往视”(20)(宋)杜大珪撰,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11《范忠宣公纯仁世济忠直之碑》,《四库全书》第4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27页。。
以上举引是官员病卒之际单纯的宣医诊疾的代表性事例,虽然“宣医诊疾”相关事例不多,但是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北宋官员病卒之际皇帝宣医诊疾的大致状况。皇帝获悉官员患病信息后,首先考虑和实施的是宣医诊治。这种宣医诊疾行为本身是太医代表皇帝前往臣僚之家救治患病官员,直接彰显了皇帝关怀生命、眷顾臣僚的恩典礼遇。与下文所要探讨的派遣内侍宦官代表皇帝挟押医官前往患病官员宅第诊治疾病不同,上述纯粹的“宣医诊疾”行为中,皇帝派遣的医官基本不受宦官的干扰,能够比较客观地发挥医官的医术水平,真实有效地开展诊疾和救治,对症性地开方下药,从而最大程度地尝试挽救患病官员生命。
(二)遣使“挟医诊视”
正如前文所论,单纯的“宣医诊疾”事例较少,一般都会在医官派出之后再派遣内侍官员前往了解官员病情。常态的程序是派遣内侍官员与医官一同前往患病官员宅第视疾诊治,同行的内侍宦官被唤作中使。此类中使与医官同行探视诊治官员疾病的行为,从最初的“带领”“护送”演变为“押送”“挟送”,呈现的是中使在“宣医诊疾”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中使“挟医诊疾”事例较多,如开宝八年李谦溥“以疾求归,肩舆抵洛”,太祖“遣中使领太医就视之”(2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73《李谦溥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39页。。淳化二年刘继元疾,“遣中使护医诊视”(22)(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82《刘继元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941页。,卒封彭城郡王。淳化二年臧丙被疾,“遣中使及尚医驰往视之,逾月卒”(23)(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76《臧丙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99页。。咸平三年天雄军、邢州二钤辖符昭愿“以疾求归京师”,诏“遣中使、尚医驰传诊视”(24)(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51《符昭愿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841页。。景德三年冬王显被病,“诏中使偕尚医疗视”(2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68《王显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233页。。景德五年杨亿以疾在告,“遣中使致太医视之”(26)(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05《杨亿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82页。。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丰州防御使王承美被疾,“遣中使挟太医视之,令日候其起居,附驿言状”(27)(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9,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甲戍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8页。。大中祥符六年三月,河北转运使、右谏议大夫卢琰被疾,“诏遣中使挟太医往视,及卒上甚悼之”(28)(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0,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三月丁酉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19页。。天禧元年陈彭年被疾,“遣中使挟医诊疗,旦夕存问”(29)(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87《陈彭年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665页。。天禧二年陈知微以疾闻,“遣中贵挟太医往视之”(30)(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07《陈知微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15页。。治平二年六月,贾昌朝告疾,“中人将太医问视相属”(31)(宋)杜大珪撰,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6《贾文元公昌朝神道碑》,《四库全书》第4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32页。。治平二年十月戊子,贾黯“病且革”,“天子遣使挟太医,日夜临视之”(32)(宋)杜大珪撰,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9《贾翰林黯墓志》,《四库全书》第4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722页。。元丰二年四月宋敏求被病,“遣使挟医疗治之,仍诏其子官于外者归省”(33)(宋)杜大珪撰,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16《宋谏议敏求墓志铭》,《四库全书》第4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827页。。元丰八年七月王拱辰寝疾,“诏遣中使挟国医临视”(34)(宋)刘敞撰:《公是集》卷51《王开府行状》,《四库全书》第10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57页。。又如凌策疾甚,真宗“累遣中使挟医存问,赐名药”(3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07《凌策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29页。。卢琰被疾,“诏遣中使将太医诊视”(36)(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07《卢琰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26页。。曾公亮被病,“上遣中使挟太医诊视”(37)(宋)杜大珪撰,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52《曾太师公亮行状》,《四库全书》第4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534页。。吕公弼得疾,“上遣中使将御医诊视”(38)(宋)王安礼撰:《王魏公集》卷7《吕公行状》,《四库全书》第110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0页。。
以上举引的是北宋时期官员病卒之际朝廷派遣内侍“挟医诊疾”的代表性事例,大致呈现出了遣使宣医诊疾的基本面貌。一是太祖、太宗时期表现为派遣内侍率领太医诊疾、遣使护送太医诊疾;二是真宗大中祥符以后开始出现派遣中使挟送太医诊视、遣使将太医诊疾,这种变化表明遣使“宣医诊疾”经历了从遣使视疾、宣医诊疾转变为遣使挟医诊疾。从各种事例中“挟医”称谓来看,真宗大中祥符以后已经形成了太医受制于中使的局面。其结果是所宣太医失去了诊治官员疾病的主导权,从而难以客观有效地开展医药救治,尤其是作为皇帝使者的宦官会要求或监督患病官员当面服用御赐丹药等,加之部分太医医术水平确实有限,以至于被时人视为“庸医”,部分官员可能在服用御赐药物后死亡,最终导致了“宣医纳命”谚语在京城的形成、传播和影响。
与北宋时期相比,南宋时期官员病卒之际“宣医诊疾”事例少见记载。如韩世忠初得疾,“敕尚医视疗”(39)(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64《韩世忠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367页。。绍兴二十八年王纶肺病,“上遣御医诊视,且赐白金五百两”(40)(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72《王纶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536页。。大将吴玠在蜀被病,朝廷遣内侍奉亲札以赐,“至,则玠病已甚,扶掖听命”,“帝闻而忧之,命守臣就蜀求善医,且饬国工驰视,未至,玠卒于仙人关”(4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66《吴玠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413页。。刘拱属疾请致仕,“孝宗遣中使以医来”,疾革草遗奏言“皆以未能为国报仇雪耻为恨”(42)(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86《刘珙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183页。。咸淳二年,王爚“以疾乞祠”,“帝遣尚医视之,且赐食”(43)(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18《王爚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526页。。南宋时期这种宣医诊疾事例的少见记载,或许跟北宋中期以后形成的“宣医纳命”的谚语传播和文化影响有关,即南宋时期患病官员大多辞避朝廷的遣使宣医诊疾待遇,这一点在南宋时期有丧官员之家纷纷辞避皇帝临奠和诏葬待遇上可以得到印证。
(三)“宣医诊疾”的特殊情况
前述官员病卒之际宣医诊疾只是临问视疾的常态情况,在宋代官员病卒之际的宣医诊疾实践中,一般是官员发病以后朝廷派遣太医前往诊治,虽然经过太医一定程度的积极救治,但是患病官员最终都无法逃脱生命因病消逝。在宋代官员病卒之际的宣医诊疾实践中尚有两种特殊情况,导致宣医诊疾待遇无法真正实施或诊治没有效果,从而削弱了官员病卒之际宣医诊疾的政治效用。
其一,朝廷宣派的医官尚未到达,而患病官员已经去世。例如,大中祥符七年五月折惟昌疾亟,“上遣使挟医诊视,弗及”(44)(宋)陈均编,许沛藻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8,大中祥符七年五月,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0页。。嘉祐二年三月狄青属疾于镇,“诏遣国医驰视,未至以薨闻”(45)(宋)余靖撰:《武溪集》卷19《宋故狄令公墓铭并序》,《四库全书》第108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8页。。嘉祐五年八月李端懿疾亟,“命中贵人驰国医往视,未及行而以薨闻”(46)(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33,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91页。。又如杜衍病革,“帝遣中使赐药,挟太医往视,不及,卒”(4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10《杜衍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92页。。熙宁五年春邵亢疾作,“敕太医驰视,既发而讣至,上闵伤之不胜”(48)(宋)杜大珪撰,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19《卲安简公亢墓志铭》,《四库全书》第4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882页。。
其二,朝廷宣派的医官已经抵达患病官员住所,但是医官的救治已经不起作用了。例如赵逵“以疾求外,帝命国医王继先视疾,不可为矣。卒年四十一,帝为之抆泪叹息”(49)(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81《赵逵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752页。。又如章得象暴感疾,“诏遣太医驰视,已不可为”(50)(宋)杜大珪撰,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4《章丞相得象墓志铭》,《四库全书》第4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632页。。大中祥符二年杜守元属疾,“诏遣其子殿直惟庆,挟太医乘驿诊候,既至而卒”(5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63《杜守元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39页。。再如霍端友被疾,“亟遣内侍邓忠仁挟国医曹孝忠三辈等驰视公病,病益急,不可为矣,上恻然”(52)(宋)孙觌撰:《鸿庆居士集》卷42《宋故通议大夫守礼部侍郎致仕赠宣奉大夫霍公行状》,《四库全书》第113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57页。。
上述两种宣医诊疾而无效的特殊情况,虽然未能真正起到宣医诊疾的实际效果,但是却比较真实地彰显了皇帝、医官关怀与诊治患病官员的恩典或礼遇,其中皇帝面对宣医诊疾而不能救治的“抆泪叹息”和“恻然”态度,正是从生命关怀视角呈现了宋代皇帝主导的宣医诊疾的政治初衷和文化意蕴。
二、北宋“宣医纳命”谚语与内涵
宋初官员病卒之际的宣医诊治,最初是医官单独奉敇前往患病官员宅第进行疾病探视和诊治,内侍官员随后前往了解病情奏报,进而出现中使护送太医诊疾的双重视疾待遇,这一时期的中使主要是代表皇帝探视官员病情和宣赐财物等,医官多能担负起诊治疾病的主要责任。但是到了真宗大中祥符时期开始出现了中使挟医诊治的“合二为一”的特殊视疾现象,医官们逐渐受制于中使。这种“受制”在宣医诊疾的文本记载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即所谓“遣使挟太医”“遣使将太医”“遣使宣押太医”等。例如,刘拱以疾请致仕,“诏遣内侍省西头供奉官陆彦礼,宣押翰林医痊诊御脉周昭眡治公疾”(53)(宋)朱熹撰:《晦菴集》卷94《刘抠密墓记》,《四库全书》第114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9页。。此类“挟”“将”和“押”等语词,或表明被宣派去给病卒之际的官员诊疾并非太医们所情愿,因为在常理上官员获患重疾基本都是“疾亟”状态,生命即将消亡,此时对大部分患病官员的医治都是无效的,医官可能会因此担上一种“医死”官员的“罪名”,成为时人所谓“宣医纳命”中的“庸医”或“罪魁祸首”,而遭受皇帝的惩罚或官员亲属的咒骂。
(一)宋人笔下的“宣医纳命”谚语
所谓“宣医纳命”谚语出自宋人的笔谈之说,最早见载于北宋孔平仲《谈苑》卷一:
京师语曰:“宣医丧命,敕葬破家。”盖所遣医官云:“某奉敕来,须奏服药加减次第。”往往必令饵其药,至死而后已。敕葬之家,使副洗手帨巾。每人白罗三疋,它物可知也。元祐中,韩康公病革,宣医视之。进金液丹,虽暂能饮食,然公老年,真气衰,不能制客阳,竟以薨背。朝廷遣使问后事,病乱中误诺敕葬,其后子姪辞焉。(54)(宋)孔平仲撰,王恒展校点:《孔氏谈苑》卷1《宣医丧命诏葬破家》,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22页。
上引文字所谓“敕葬破家”之谚,笔者在诏葬制度相关议题中已经作了详细论述(55)肖红兵:《宋代诏葬制度初探》,《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5期。,这里仅就“宣医纳命”谚语略作分析。孔氏通过“京师语曰”的方式揭示了“宣医纳命”的说法是在“京师”传布,是太医强制患病官员服饮御赐药物所致,既未点名患病官员身份,也没有提及是“中使挟太医”的问题,所举引韩绛服用御赐“金液丹”而死的事例亦未见诸史载。文献记载所见,宋人有关“宣医纳命,敕葬破家”的记载尚有两处,只是在文辞表述上略有差异。
其一,叶梦得《石林燕语》卷第五:
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礼厚者多宣医。及薨,例遣内侍监护葬事,谓之“敕葬”。国医未必皆髙手,既被旨,须求面投药为功,病者不敢辞。偶病药不相当,往往又为害。“敕葬”,丧家无所预,一听于监护官,不复更计费。惟其所欲,至罄家资有不能办者。故谚云“宣医纳命,敕葬破家”。(56)(宋)叶梦得撰,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5,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7页。
叶梦得将宣医的对象描述为“大臣及近戚”,并进一步指明了“宣医纳命”的原因是“国医未必皆高手”以及太医奉命诊疾“须求面投药为功”。
其二,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亦详细载录了“宣医纳命,敕葬破家”的谚语:
贵臣有疾宣医及物故敕葬,本以为恩,然中使挟御医至,凡药必服,其家不敢问,盖有为医所误者。敕葬则丧家所费,至倾竭赀货,其地又未必善也。故都下谚曰:“宣医纳命,敕葬破家。”(57)(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9,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117页。
陆游的表述比孔平仲的记载当更为合理,却没有叶梦得的细致。陆游直接突出的是“中使挟御医至”的问题,将“宣医纳命”的原因归结为中使监督服药所致。由于中使代表的是皇帝,对于中使的决定,官员及其家人不敢违背,而太医大多受制于中使。这是因为北宋中期以后官员病卒之际的宣医诊疾基本上都是“中使挟医携药”的模式,患病官员要服用中使携带的御赐药物和太医诊断后开列的药物。
上引三种有关宋代“宣医纳命”谚语文本的记载,涉及三个宣医诊疾问题:其一,中使监督患病官员服用御赐药物,该御赐药物是否对症有效问题;其二,朝廷所宣派的太医是否医术高明,所开药方是否对症有效问题;其三,朝廷(皇帝)对“宣医纳命”现象是否有所认知和应对问题,皇帝并非医生且对疾病和药材也不了解,但是御赐药物却必须服饮。这三个问题涉及的是宣医诊疾的主导者皇帝、中使和太医,后二者亦代表着皇恩圣意,患病官员及其亲属自然是均“不敢问”,其结果可能就是“药不对症”而导致患病官员速死。如此,宋代官员病卒之际宣医诊疾待遇中的“宣医纳命”现象,可以解释为皇命难违和“医工不精,药石未效”(58)(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9,仁宗嘉祐八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833页。,加之中使监督服用御赐药物所致。
但是上述三种“宣医纳命,诏葬破家”记载并未言及谚语出现或形成的大致时间。孔平仲《谈苑》所举韩绛服用金液丹“纳命”事在元祐中,这已经是北宋晚期。结合笔者所论“诏葬制度”异变的大致时间,可以推测“宣医纳命”现象的出现也应在真宗、仁宗之际。试举引一段材料聊作参考:
(真宗景德四年八月)巳亥,诏自今两省五品、尚书省四品、大将军、刺史已上、知杂御史、诸司使,被疾请告三日已上者,入内内侍省遣使将太医诊视之。旧制,文武官属疾,咸遣医疗治,颇有自陈微恙,请不命国医者,上不欲恩例有异,故定制焉。(59)(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真宗景德四年八月巳亥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78页。
这份诏令针对的是在京臣僚“托疾不朝”问题,虽然已经明确指出“请不命国医者”是因为“微恙”,但是官员有疾“请不命国医”诊视是否与“宣医纳命”现象有关,尚有待结合相关资料作进一步考察。
(二)从中使“挟医诊疾”待遇到“宣医纳命”谚语
从皇帝派遣内侍宣医诊疾的初衷来看,在官员病卒之际派遣中使挟医诊疾,原本是中使作为皇帝身边的内侍近臣代表皇帝宣押护送医官救治患病官员,但是随着中使参与事务的日益宽泛和官员家属对所谓“代表皇帝”的中使的尊重或忌惮,出现了中使对官员家庭索取无度的违法行为。诏葬制度正是由于中使索取无度和宣扬政治威仪导致丧家无力承担丧葬费用而遭纷纷辞避,与之一致的是宣医诊疾也是在中使的参与下导致了病卒官员家庭面对中使索取和酬医费用的双重支出,加之宣医诊疾时医生携带有皇帝御赐金丹等药物,中使一般会监督甚至强迫患病官员当面饮用御赐药物才能算是完成皇帝赐药任务,这样的结果是可能由于“药不对症”而导致官员病情加重乃至很快死亡,于是才衍生出了与“诏葬破家”意蕴相似的“宣医纳命”的京师谚语。
但是,就官员病卒之际遣使宣医诊疾本身来说,实施救治任务的是享有国医称号的太医,但是如何服饮御赐药物等常常须由具有中使身份的内侍决定,因为中使代表的是皇帝。于是医官奉命救治患病官员,救治成功则可能会受到皇帝褒奖,但是救治失败则可能会面临皇帝的惩罚。例如,太祖建隆二年春正月,宰相范质、王溥相继卧疾在告,“上命翰林医官王袭、米琼视之,质、溥皆瘳。上喜,于是以袭为光禄寺丞,琼为都水监主薄”(60)(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太祖建隆二年春三月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页。。王袭和米琼显然是幸运的,因治好了两位宰相疾病而获得升迁。但是,雍熙二年三月,翰林医官使刘翰责授和州团练使,原因则是“时武成军节度使刘遇疾,遣翰候之,复言必瘳,未几而卒。太宗怒,送中书簿责降职”(61)(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9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0页。。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二月丙寅,步军都虞候、英州防御使袁贵被病疾亟,“诏遣太医诊视,晨奏稍损,及暮而卒。上责医工无状,并黜其官”(62)(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7,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二月丙寅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58页。。七年舒王元偁薨,“医官并坐视疾无状谴责”(63)(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2,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夏四月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72页。。这种“视疾无状”的结果是患病官员在宣医诊治后病卒,故而成为“宣医纳命”的谈资。到了皇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仁宗专门下诏“医官之属,今后有阙递迁,不得额外差置”,即医官不能随便去给患病官员等诊疾,其中一个原因是仁宗认为“医官愈人之疾,乃其职尔,而每治后宫及宗室愈,辄侥幸以迁”(64)(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9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1页。。除了“侥幸以迁”官职外,医官诊疾之后还能从官员之家获取丰厚的医费酬谢,于是下诏“条约之”。
从“宣医纳命”谚语生成的历史背景来看,宋代太医的医术水平值得探究。理论上太医主要是给皇帝、后妃、皇嗣、宗室近亲等人员诊治疾病,医术多能代表着国家医术的最高水平。但是翰林医官院医官们的医术水平显然是有高低之分的,至少有普通太医和御医的区分。例如,韩琦在地方任职期间患病,曾专门奏请派遣御医齐士明给其看病,显然这位齐士明的医术是大臣们知道和认可的。又如,赵奎疾亟,“力上章请外,弗许”而病重,皇帝向朝臣询问赵奎“疾状”,“论方剂甚悉,且曰庸医恶知此,遣侍医视之,而疾不可为矣”(65)(宋)周麟之撰:《海陵集》卷23《中书赵舍人墓志铭》,《四库全书》第11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0页。。由于赵奎在京城做官,给其诊治看病的医生或为普通医生或为普通太医,但是因为未能治好赵奎的疾病,在皇帝眼中就是“庸医”,故而派遣医术高超的随身“侍医”视之,但是赵奎疾病已经严重到“不可为矣”。
上述庸医所误和良医不足的现象并非孤例。至道二年宋太宗就曾颁布过“全国寻医令”。至道二年正月丁卯,礼部侍郎兼秘书监贾黄中卒,“疾复作,上亟命太医诊视,劳问旁午”,然而贾黄中很快病逝,年仅59岁。贾黄中的病逝应当引起了宋太宗对翰林医官署国医们医术水平的怀疑乃至否定,史称“先是黄中之卒,上悼惜之甚。念翰林无良医,因遍令索京城善医者,得百余人,悉令试以方脉。又诏诸道州府,令访能医者,乘疾置阙下。俾近臣各得荐所知,以隶太医署”(66)(宋)钱若水撰,范学飞点校:《宋太宗皇帝实录》卷76,至道二年正月丁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50、651页。,太宗此举显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将全国医术高手召集在京师之内。类似“悬榜募医”行为在真宗时期再次出现,大中祥符四年惟吉疾病复作,“不能朝谒。车驾屡临省之,或亲视其灼艾。日给御膳,为营佛事,设科醮,令开封府揭榜募能医者”(67)(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五月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70页。,当然此次“悬榜募医”也许是真宗皇帝求医心切的特殊举措。
事实上“悬榜募医”只能是一种偶然为之的特殊行为,从理论上来说,京城的太医们还是能代表国家的医术水平的,故宋代大臣对太医们的医术一般比较认可。前述至和元年十二月,知幷州韩琦“以疾乞太医齐士明”,而翰林医官院言“士明当诊御脉,不可遣”,但是仁宗皇帝“立命内侍窦昭挟齐士明往视之,以示优宠也”(68)(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礼47之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5页。。
(三)宋代“宣医诊视”中的“馈赠”“酬谢”
在宋代上层社会中,无论是御医还是普通太医,给官员诊治疾病一般都不是“义诊”,即便是奉皇帝敇命诊疾的太医也会象征性地接受病卒官员之家的医费“馈赠”,具体礼法或政策尚未见知。文献所见典型事例有二则:一是元祐五年六月,司马康被病,“诏遣内侍挟御医三人诊视治疗,以君清贫,命医毋得受馈,俟疾损取旨”(69)(宋)杜大珪撰,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23《司马谏议康墓志铭》,《四库全书》第4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950页。,明确要求所宣太医“毋得受馈”,表明“宣医诊疾”接受官员之馈赠是常态行为。到了八月,司马康提举嵩山崇福宫,“诏曰勿药有闻,即膺吾用”,“遣内侍谕旨,俾留京师就医药,赐钱三十万。九月丙寅,以不起闻”(70)(宋)杜大珪撰,顾宏义、苏贤校证:《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23《司马谏议康墓志铭》,《四库全书》第4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950页。,在司马康病卒之际“赐钱三十万”显然是用作医药费用,那么“宣医诊疾”之费也应当由内府承担了。二是范纯仁归许昌养疾后,徽宗“遣上医视疾”,“疾小愈,丐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医。诏赐医章服,令以冠帔与族姪”(7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14《范纯仁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92页。。范纯仁择以“冠帔”作为“酬医”之物,皇帝知晓“酬医”实情后并未责罚所遣太医,间接表明患病官员之家酬谢“宣医诊疾”费用已经是普遍的常态现象。此外,范纯仁病重之际,“仍遣国医诊视,医药所须,并出内府,一钱不得取于公家”(72)(宋)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14,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6页。,这里的“公”指的是范纯仁,即范纯仁不需要给付任何医药费用,而由徽宗专门诏令医药费用等“并出内府”,应当是包含了可能的“宣医诊疾”费用。
除了上述两则馈赠“宣医诊疾”的太医事例,笔者尚见有一则馈赠挟医诊疾的中使事例。刘谦从幸大名被疾,“俾其二子随侍,仍挟尚医以从,御厨调膳以给之。疾瘳,毁所服鞍勒以遗中使。上闻,赐白金二百两”(73)(元)脱脱等撰:《宋史》卷275《刘谦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82页。,刘谦“馈赠”的对象是“中使”而非“尚医”,馈遗方式为拆卸“所服鞍勒”“以遗中使”,该鞍勒当是贵重之物。而作为从幸在外的刘谦身边显然不会带有较多金钱财物,只能从随身物件中选取“贵重”之物作为酬谢之资,足见宋代官员病卒之际中使挟医视疾过程中接受馈赠的恶劣风气。
三、宋代“宣医纳命”谚语的文化意蕴
从馈赠中使和酬谢医费的视角来看,宋代官员病卒之际遣使挟医诊疾中的“宣医纳命”现象,并非是宣医诊疾的常态行为,当只是个别病重官员服用御赐药物或太医所开药物后“药不对症”所致,故叶梦得“偶病药不相当”、陆游“盖有为医所误”当属实情。然而“宣医纳命”谚语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内涵——中使视疾和宣医诊疾行为本身所象征的皇权制度下的政治威仪,潜在地要求患病官员及其亲属对视疾中使和诊疾太医抱有尊敬乃至畏惧的态度。
具体而言,官员病卒之际的中使视疾和宣医诊疾,属于皇帝主导的一种特殊政治活动。一方面官员或其亲属在中使视疾或宣医诊疾之后,需要及时向皇帝奏谢关怀之情和救命之恩。另一方面在视疾、诊疾之前、之中或之后,官员或其亲属需要向视疾中使和诊疾太医表达馈谢之意,甚至为了不得罪中使或者冀望太医能认真有效诊治疾病而可能刻意地给予丰厚酬谢。从一些零星的酬谢中使和太医事例来看,酬谢中使和太医不仅是一种常态的乃至病态的“宣医视疾”现象,也是国家礼法所允许的政治行为。这种酬谢视疾中使和诊疾太医的“正常行为”,与诏葬制度中中使索取无度的“非正常行为”,一同引发了部分病卒官员之家对中使宣医诊疾和中使监护葬事的抵触和忌讳心态,加之部分病重官员在中使挟医诊疾之后可能因为“被迫”服用相关药物很快“纳命”,于是时日长久在京师官员群体中就产生了所谓“宣医纳命,诏葬破家”的特殊谚语。
从上述分析来看,宋代“宣医纳命,诏葬破家”这一谚语反映的是病卒官员之家对中使挟医诊疾和中使监护葬事两种特殊皇恩优待的心理抵触和政治避讳,其背后所隐含的是宣医诊疾和诏葬制度因中使的贪婪腐败而逐渐异化为皇权制度下的特殊“虚恩”。
与诏葬制度最终流于形式化的辞避结果不同,宋代官员病卒之际的遣使挟医诊疾待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宣医纳命,诏葬破家”谚语的影响,但是作为皇帝关怀、眷顾和体恤臣僚生命的一种特殊政治待遇,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实施着。南宋时期有两则宣医诊疾的特殊事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宋代官员病卒之际遣使宣医诊疾待遇的文化内涵。其一,周必大《谢宣医札子》:
臣积为寒气所薄,有妨拜跪。初误信医,先投刚剂,转觉腰背疼重,不能转侧。仰蒙圣慈,宣遣王懋诊视,宣通熨烙,遂获安愈。再生之恩,实逾天地。臣昨日已曾奏谢,伏缘王懋连日至臣私第,取效甚速。已依例薄送药材之费,欲望特降睿旨,令懋收受。臣无任感恩,荷圣激切,惶惧之至。(74)(宋)周必大撰,王蓉贵等点校:《周必大全集》卷128《谢宣医札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0页。
这份札子在讲述了宣医诊疾的过程和效果后,直接点明了“依例薄送药材之费”,并奏请诏令王懋“收受”,正说明馈赠太医诊费药费是朝廷的礼法政策,官员之家应当积极奉送诊费药费。只是可能由于周必大特殊的身份,王懋不仅没有额外索取诊费,还不肯依例收取“药材之费”,结果造成周必大“惶惧之至”而请求圣裁。
其二,吕颐浩《乞致仕札子》:
臣辄具忱诚,仰干天听。臣于今十六日因治事之际,忽觉两臂沉重,言语蹇澁,疑是风疾。遂召医官陆近评脉,系是风证。调理两日不效,遂召医官王继先看视,亦云风证所作,与臣灵宝丹及袪风散煎服之。又令医官杜楫,点穴灼艾,灸十余处,未见如旧。今则思虑不宁,心神恍惚,少有劳动,疾疢増加。臣自料虚风所中,必不能日近平复,伏望圣慈检会臣前后累奏,乞收还旄印,除臣一近下阶官致仕。(75)(宋)吕颐浩撰,徐三见等校:《吕颐浩集》卷3《乞致仕札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吕颐浩的“劄子”讲述了三次宣医诊疾过程,相继给予诊病、赐药和艾灸治疗,但是医官诊治效果不佳,于是积极请求给予致仕。
以上举引的两则南宋时期宣医诊疾事例,十分具体地呈现了医官诊疾的过程和效果,医官们诊疾态度积极认真,既非庸医也未对患病官员造成伤害,医患关系较为和谐,表明两则事例中的宣医诊疾是十分正常的诊治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两则宣医诊疾事例中均未提及中使,表明在南宋时期的宣医诊疾活动中太医或是单独奉敕前往诊疾,或是中使仅仅是“传宣医官”而不再是“挟押医官”,即中使在宣医诊疾活动中无法参与或干扰医官的诊治疾病。
从传统的礼法制度来看,官员病卒之际的宣医视疾是宋代官员病卒前的一种特殊政治待遇,也是视疾临问待遇中主要的、常用的视疾方式。只是宣医诊疾通常伴随着君临问疾或遣使视疾进行,最终形成中使挟医诊疾的特殊视疾方式,在视疾活动中皇帝派遣的中使一般会携带御赐药物。由于内侍宦官在官员病、卒、葬系列活动中扮演着“皇帝”派遣的“中使”角色,从而主导着官员生前用药和死后葬事,在彰显圣恩眷顾和政治威仪的心理推动下,中使监督甚至强制患病官员服用御赐药物,造成宣医诊疾待遇逐渐异化为病卒官员家庭抵触和力求避讳的社会现象。从这一视角来看,“宣医纳命”隐含的当是病卒官员之家对宣医诊疾行为中的中使或医官监督强制患病官员服用御赐药物的抵触和避讳心态。至于庸医导致“宣医纳命”发生的概率相对较少,当然人们对“庸医纳命”始终是深恶痛绝的,苏轼就曾发出“勿使常医弄疾”之警语,陆游认为苏轼之语是“天下之至言”而“读之使人感叹弥日”(76)(宋)陆游撰,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卷27《 跋东坡〈问疾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三册,第176页。。因此,官员病卒之际传宣诊疾的一般都是常医,而非像齐士明那样的名医,常医的首要职责是诊治疾病,对于重病官员救治无方实属正常现象。在宣医诊疾的实践层面,或许会有偶发性的个别“庸医”误诊或御赐药物不对症而直接导致患病官员快速死亡,这才是真正的“宣医纳命”。总之,官员病卒之际的“宣医纳命”谚语,并非宋代宣医诊疾政治实践的历史常态,更多的是宋人因憎恶作为中使的内侍宦官的“胡作非为”而衍生的士宦之家对中使挟医诊疾行为的“戏谑”之辞。
四、结 语
在封建帝制社会中官员病卒之际,由皇帝主导的视疾临问活动是早期中国上层社会中“臣疾君问”“臣丧君吊”仪礼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官员病卒不仅仅是官员生命的终结,还会涉及朝政和人事的变迁。从皇帝的角度来说,在获得大臣患病信息后,皇帝需要通过宣医诊治等视疾方式抚慰病者、了解病状、开展救治,以冀望官员疾病痊愈而继续为君为国工作。从臣僚的角度来说,病卒之际能够获得皇帝视疾临问则是一种崇高的政治礼遇,凸显的是皇帝对患病官员的认可、优待、关怀和眷顾。从国家礼法制度来说,官员病卒之际的宣医诊视待遇,是帝制国家表达优待抚恤病卒官员的特殊政策,藉此激扬生者为君为国的忠义情怀。因此,以宣医诊治为主要形式的视疾对象虽然是即将病卒的官员,但是视疾临问活动呈现的是国家优待、抚恤、关怀臣僚的圣恩与情怀,这种视疾临问待遇的实施足以激励其他在世官员坚定忠君爱国理念。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看,在宋代复杂变动的政治生态下,官员病卒之际的视疾临问待遇与临奠、诏葬待遇一样,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逐渐从尊耀的恤逝皇恩异化为避讳的饰终虚恩,以致出现了宋代特有的“宣医纳命,诏葬破家”的戏谑谚语。南宋名宦刘克庄有诗云:“乍可裸尸仰药,勿求敕葬宣医”(77)(宋)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 46,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 2408页。,所表达的正是对宋代宣医、敕葬两种特殊皇恩的抵触与避讳之意。清人许瑶光针对宋代出现的“宣医纳命,诏葬破家”怪异现象,更是生发感叹说:“宣医丧命,敕葬破家。乃知虚恩不可受,使人望古增咨嗟”(78)(清)许瑶光:《雪门诗草》卷14《衍古謡谚·宣敕篇》,《续修四库全书》第154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