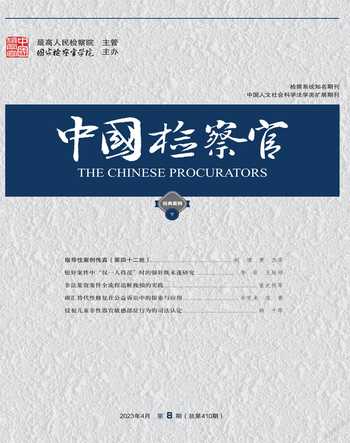论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
雷知仁 胡松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侵犯著作权罪中将信息网络传播与复制发行并列,经此修订,对“复制”行为的认定,应当坚持在物质载体上固定作品的要求,对“发行”的认定则应坚持以转移所有权的方式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且“发行”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包容,从而协调刑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之间的关系,消解司法实践中民事裁判和刑事裁判的冲突,维护法治体系统一。
关键词:侵犯著作权罪 复制 发行 信息网络传播
一、网络环境下“复制发行”的认定争议
[基本案情]2018年1月至案发,梁某某以营利为目的,成立相关公司,组织人员开发“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及移动客户端,将境外网站下载的未经授权的电影作品,翻译后压制、上传至网络服务器,通过网站和客户端向用户提供在线观看和下载服务。期间,梁某某等人以接受“捐赠”、收取广告费、销售含有盗版电影作品的硬盘等方式获取经济利益。经审计及鉴定,“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及移动客户端内共有未经授权的影视作品32824部,会员683余万人,经营额总计达1200余万元。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梁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15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1]
有观点认为,本案涉案人员实施了复制发行行为,完全符合侵犯著作权罪客观要件。[2]但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盗版影视作品,是否能被解释为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并非毫无争议。本案尚需就三个焦点问题进行分析:一是涉案人员通过境外网站下载未授权电影后,组织人员翻译,添加字幕后上传至网络服务器的行为,是否构成“复制”;二是通过信息网络向他人提供在线观看和下载服务,是否构成“发行”;三是刑法中“复制发行”,是否应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相关术语的内涵保持一致。有观点认为,网络时代,复制从占有转变为感受,发行也突破了有形载体的束缚转变为无载体发行,对刑法概念的解释不必以民法的规定为前提。[3]2004年《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4年解释》)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视为“复制发行”,2011年《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11年意见》)再次明确网络传播属于发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单独入罪后,前述观点是否合理、司法解释相关条款是否依然有效值得探讨。
二、网络环境下“复制”行为的认定要点
2020年11月《著作权法》修改,在印刷、复印等典型的“复制”行为之外增加了“数字化”方式,而“人人影视字幕组”未经授权“数字化”再生产电影作品的行为能否被法律评价为“复制”进而构成犯罪,需要从复制权的构成要件出发进行分析。
(一)“复制”必须借助物质载体再现作品
法院将梁某某等人借助互联网下载、翻译、压制、上传盗版电影的行为定性为“复制”,这种网络复制与传统的实物复制具有显著差异。我国《著作权法》所列举的典型“复制”行为,印刷、复印、拓印都会形成作品的复制件,录音、录像、翻录、翻拍都会将作品固定在物质载体上,复制的本质是在有形载体上稳定地再现作品。[4]是否在有形载体上再现作品,是《著作权法》上的复制权与表演权、广播权的根本区别之一。[5]这一要件在域外法律中也有体现,《英国1988年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第17条就规定,与文学、戏剧、音乐或艺术作品相关的复制是指以任何物质形式复制作品,也包括通过电子方式将作品存储在任何介质中。[6]借助物质载体重现作品,则必然产生作品的复制件,《美国1976年版权法》第101条明确,复制件就是用来固定作品的有形物,并且可以通过该复制件传输、复制、感知作品。[7]美国国会曾在立法报告中强调,复制件包括固定所有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的物质载体。[8]实践中,美国法院也曾指出,法院以前没有解决过通过互联网未经授权传输数字音乐文件是否构成版权法意義上的复制的问题,但当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固定在新的物质材料中时,就会发生复制。[9]因此,要构成“复制”,必然需要通过物质材料再现作品,并形成一个复制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如“人人影视字幕组”这样的网络复制行为数量剧增,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复制”的要件?前文案例中,电影等数字作品虽然是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看似无形,但其存储的基础是硬盘等物理硬件,对电子数据进行复制依然需要借助物质载体,下载和上传电子作品都不可能脱离物质载体而单独进行,前述英美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互联网的发展,并未改变复制权借助物质载体再现作品的要件,只不过是载体从传统的实物载体转换为了数字载体。那种认为网络时代的“复制”体现出非物质化的观点,违背我国《著作权法》的文义解释,误解了计算机运行的底层逻辑,不具有合理性。
(二)“复制”必须使作品“固定”
“复制”是借助物质载体再现作品的行为,但是,并非所有再现都能称为法律上的“复制”,如借助投影仪播放电影。这就涉及到认定“复制”行为的第二个要点,即作品必须被“固定”在物质载体上,这种固定是相对稳定和持久的。[10]《美国1976年版权法》第101条就明确规定,作品以有形形式“固定”,需要足够持久或稳定,使它能够被感知、复制或以超过短暂长度的时段被传输。[11]美国国会的说明中也指出,对“固定”一词的定义,从概念上将那些纯粹转瞬即逝或暂时的复制品加以排除,比如短暂地投射到屏幕上,在电视或其他电子显示器材上显示,或者在计算机内存中短暂存储。[12]互联网环境下,这一要件依然成立。将作品数字化后上传到互联网,将导致在网络服务器的硬盘中固定作品,这种“固定”是相对稳定且持久的,只要不人为地擦除硬盘数据,常见的外部存储器如普通固态硬盘理论寿命可达20年[13],数字作品可以长久地保存在存储装置中。
前文案例中,“人人影视字幕组”下载和上传电影的行为,都借助计算机存储装置这一物质载体对数据作品进行了再现,且这种再现是持续而稳定的。只要服务器上的数据不被人为擦除,这些电影就可以“固定”在存储装置中。因此,即使《著作权法》未将“数字化”列为“复制”的方式之一,该行为也完全符合“复制”行为的构成要件。部分学者将关注焦点放在该案的字幕翻译行为是否构罪上,在刑法未将盗版翻译这种民事侵权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前提下,借道共犯理论论证翻译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14]笔者认为这是误读了案件争议焦点,因为本案的复制行为不是发生在翻译环节,即使是合法翻译,也不影响字幕组下载和上传未经授权作品属于非法“复制”的定性。另外,认为网络时代对刑法第217条“复制”的解释可以突破《著作权法》的规定,扩大为非物质化复制的观点,既不符合刑法文义解释的一般规则,还会导致刑法和《著作权法》适用上的冲突。因此,网络环境下,对刑法第217条“复制”行为的解释,还是应当坚持在物质载体上固定作品的要求。
三、网络环境下“发行”行为的认定要点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网络传播与复制发行并列规定,完全改变了《2004年解释》和《2011年意见》的规定。对“发行”概念的解释,既涉及到对刑法条文关系的理解,还涉及到刑法与《著作权法》衔接的问题。
(一)“发行”应当提供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
前文案例中,争议焦点之一是梁某某等人实施的网络传播行为是否应当被视为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发行”行为,因为网络传播并未像传统的发行一样向公众提供诸如书籍等实物产品。根据我国《著作权法》,构成“发行”需要提供作品原件或复制件,这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规定一致。《美国1976年版权法》第106条就将发行权定义为向公众发行有版权的作品的复制件或者录音制品,而第101条将复制件定义为“有形物”。[15]《英国1988年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第18条规定,“發行”是将先前未在英国投入流通领域的作品复制件投入流通领域。[16]《欧盟版权指令》将发行权定义为成员国应就其作品原件或其复制件,赋予作者授权或禁止以出售或其他方式向公众发行的专有权。[17]欧盟法院在判决中也指出,欧盟立法者在发行权中使用有形物的用语,是为了使作者能够控制体现其智力创作成果的有形物的初始市场。[18]《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6条也明确指出,发行权是作者向公众提供其作品原件和复制品的专有权。关于该条约的议定声明指出,条约第6条所用“原件和复制品”,专指可作为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的复制品。[19]结合我国《著作权法》及其他国家和国际条约的规定,可以发现,发行权的对象是作品的物质载体,即原件和复制件,并非作品本身,构成发行必须提供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
厘清了发行权是向公众提供作品的物质载体,即原件或复制件后,再来观察前述案例所谓“网络发行”就很清晰:梁某某等人将电影上传到网络服务器,数据本身构成作品,上传行为是“复制”行为。数据上传到网络服务器后,当然也有物质载体,那就是服务器的硬盘,此时,行为人通过网络向公众提供电影下载和在线观看等服务,传播的是数据,即“作品”本身,而非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即存有该“作品”的硬盘。因其传播的是“作品”本身,并非在向公众提供原件或复制件,这种网络传播行为不符合“发行”的要件。
(二)“发行”必须转让作品所有权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发行”只有出售或者赠与两种方式,不论是出售还是赠与,均会导致作品物质载体所有权的转移。在采纳狭义“发行”概念的国际条约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中,发行必然导致作品所有权转移。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6条规定的发行方式就是通过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形式,《欧盟版权指令》也强调发行需要通过销售或其他方式进行。欧盟法院曾指出,发行的概念,仅适用于转移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所有权的情形。因此,不论是给与公众使用受版权保护作品的权利,还是向公众展示这些作品而不给予他们使用的权利,都不构成“发行”。[20]我国《著作权法》将出租等转移占有形式单独列出,规定为“出租权”等权利,很明显也采取的是狭义“发行”概念。事实上,我国法院也早就意识到网络传播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行”。1999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曾在王蒙等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将其作品上网传播侵犯著作权案中指出,通过网络传播作品,是作品使用的方式之一,与出版、发行、表演、播放等有不同之处,并认为网络内容服务商未经授权通过互联网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21]《著作权法》增加信息网络传播权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曾在源泉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诉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数字世纪网络有限公司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案判决中认为,发行权显然需要转移作品载体所有权或占有,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侧重点和范围并不相同。[22]可见,构成“发行”需转让所有权,在域内外司法实践中是必须条件。
既然发行需要转移所有权,网络传播行为与发行行为的界限就更加清晰,如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就曾借助音乐作品网络传播的过程来区分二者:电子传输通常涉及在A点读取数据并在B点复制该数据。由于在A点的数据并不一定被读取数据的过程所销毁,在A点的人可能仍然享有原始数据,因此并未发生销售或以其他形式进行的所有权转移,通过网络传播音乐作品也不构成发行。[23]前述案例中,“人人影视字幕组”通过服务器将电影数据提供给社会不特定公众下载,电影被使用者下载后就存储在使用者的设备中,数据读取过程中“人人影视字幕组”服务器上的数据并未被销毁,依然享有原始数据,保留电影数据的存储装置(作品原件或复制件)也没有发生所有权转移,其结果是电影在新的物质载体上固定,形成了新的作品复制件,也就是作品复制件绝对数量的增加,这种并未导致所有权转移的传播行为,并不符合“发行”的构成要件。从法律的文字含义和我国的司法实践及域外规定都可以得出,在解释“发行”时,应当坚持提供作品原件或复制件和转移所有权两个要件,对于“人人影视字幕组”这类网络传播行为,不能将其定性为“发行”行为。
四、“发行”与“信息网络传播”相互独立、互不包容
如前述案例般将网络传播定性为“发行”的刑事裁判,实务中认为网络时代“发行”体现为无载体、所有权无须转移的观点,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视为“发行”的规定,都非新鲜事物。早在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缔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进行外交磋商时,美国代表团就建议在条约“发行权”中增加“通过传输提供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表述。[24]美国法院也认为,版权法规定“发行”需要转让所有权,但在电子传输过程中这个要件可以被突破。[25]也许是受美国实践的影响,我国有学者就认为只要意图转让复制件,就构成网络发行。[2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代表团希望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条约发行权中增加信息网络传播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相关专家曾指出,议定声明对条约“原件”和“复制件”定义的澄清,是为了将任何形式的数字传输从两个条约规定的发行权以及发行权用尽的范围中排除出去。[27]而美国法院之所以对“发行”作出扩大解释,源于其版权法上并没有规定类似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因此通过对发行权的扩大解释来对此类行为予以规制。
在我国刑法和《著作权法》都已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如果今后仍将网络传播行为解释为“发行”,会产生以下危害:一是会导致刑法第217条内部不协调。既然《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了“复制发行”与“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是并列的危害行为,从刑法文义解释上看,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包容关系,而是相互独立的行为,如依然把信息网络传播解释为发行,那么这二者之间就完全重合,《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该处的修正也就成为具文。二是会导致严重的刑民脱节。《著作权法》早在2001年就增设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刑法一直未作修订,反而是《2004年解释》和《2011年意见》将信息网络传播视为发行。曾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对刑法中“复制发行”的解释,不以《著作权法》的规定为前提,二者的含义可以不一致,即在特定情形中,即使不构成民事侵权或行政违法,也可以构成知识产权相关犯罪。[28]这造成司法审判中严重的刑民脱节现象。如前所述,民事法官早就明确指出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范围并不相同,但刑事法官却只能依据司法解释将“人人影视字幕组”通过网络传播的行为认定为“复制发行”,这种刑民裁判的不协调,不利于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也会损害司法公信力。在我们推进知识产权三合一改革进程中,前述观念只会导致参加“三合一”审判的法官裁判时自相矛盾。[29]因此,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已对侵犯著作权罪进行修订的情况下,今后在办理类似“人人影視字幕组”这样的案件时,应当坚持刑民衔接的基本观念,在解释“复制发行”概念及其与信息网络传播之间的关系时,应当以《著作权法》相关术语的内涵为前提。同时,应当明确司法解释中将信息网络传播视为发行的条款已经失效,才能实现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协调一致。
五、结语
近年来,司法系统大力推行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审判职能“三合一”改革,以综合司法保护助力创新驱动发展。而以“人人影视字幕组”为代表的案例则显示,推动改革向深里走、难点攻,不仅要重组机构、重塑机制,更需建立起以民事救济为常态、行政处罚为主体、刑事惩治为补充的递进式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保持部门法之间法律概念的一致性,促进实现法律适用统一、裁判结果一致、保护效果最佳,织密知识产权的法治保护网。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100875]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四级检察官助理[430079]
[1] 参见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沪03刑初101号。
[2] 参见高卫萍、王思嘉:《“盗版型”侵犯著作权罪司法实务问题探析——以“人人影视字幕组案”为研究对象》,《中国版权》2022年第4期。
[3] 参见李小文、杨永勤:《网络环境下复制发行的刑法新解读》,《中国检察官》2013年第6期。
[4] 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81页。
[5] 参见王迁:《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6] 参见《英国1988 年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http://ipr.mofcom.gov.cn/hwwq_2/zn/Europe/UK/Design.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3月6日。
[7] 参见裴安曼:《美国版权法》,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4页。
[8] Se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port,No.94-1476,94th Congress 2d Session,1976,p.53.
[9] See Capitol Records, LLC v. ReDigi Inc,910 F.3d 649(2th Cir.2018).
[10] 同前注[4] ,第81页。
[11] 同前注[7] ,第5页。
[12] 同前注[8] ,第53页。
[13] 参见吕新平、王丽彬:《大学计算机基础》,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年版,第201页。
[14] 参见王萤:《字幕组的恩怨江湖与相关知识产权犯罪分析|评“人人影视”字幕组涉刑案》,中国法律评论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kiHgpHUnHwNFeQ8Ljwx_Sw,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3月6日。
[15] 同前注[7] ,第24页。
[16] 同前注[6] 。
[17] See 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May 2001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rticle 4.1.
[18] See Art&Allposters International BV v. Stichting Pictoright,Case C 419/13,22 January 2015,ECJ.
[19] 参见《关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的议定声明》,WIPO网https://wipolex.wipo.int/zh/treaties/textdetails/12741,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3月6日。
[20] See Peek & Cloppenburg KG v. Cassina SpA, Case C-456/06, 17 April 2008,ECJ.
[21]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海知初字第57号。
[22]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23号。
[23] See London-Sire Records, Inc. v. Doe 1, 542 F. 2d 153(D.Mass.2008).
[24] 参见王迁:《网络著作权专有权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15页。
[25] 同前注[23] 。
[26] 参见何怀文:《网络环境下的发行权》,《浙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27] 同前注[24],第119页。
[28] 参见《上海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会议综述》,上海审判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Rz8lIhkOH3k2RYuWw0ac5A,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3月6日。
[29] 参见王迁:《论著作权保护刑民衔接的正当性》,《法学》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