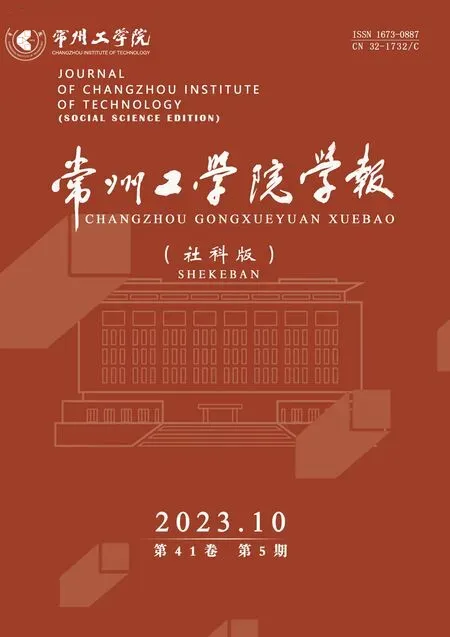暴力叙事与创伤书写
——论莫言《蛙》的叙事策略
曾安菁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莫言的小说《蛙》以叙述者“蝌蚪”的视角,讲述其姑姑万心作为妇产科医生、计划生育工作者,前后跨度约50年的故事。尽管文本以妇产科医生为主要人物,以高密东北乡计划生育执行前后50年为时间背景,但文本并没有停留在对50年乡村生育史的书写上,莫言的写作目的不在于铺陈历史的长度,而在于表现计划生育执行过程中国家意志与民间伦理产生的冲突,叙述其中发生的暴力行为以及暴力带来的创伤记忆,由此达到对人心灵的叩问。
一、温和的暴力叙事
“暴力”是莫言得心应手的写作成分,《蛙》也存在对暴力的书写。《蛙》的暴力与《枯河》中隐晦、含蓄地以主人公小虎的心理活动表现父亲的暴力行为不同,也和《檀香刑》中直露、具体地书写行刑场面不同,《蛙》以一种相对平实、温和的方式来叙述暴力。
(一)暴力书写的具体呈现
《蛙》选择叙述者“蝌蚪”的姑姑作为主要叙述对象,文本涵盖了姑姑的出身、情感、工作以及晚年境遇,在姑姑的人生经历中伴随着数次暴力行为,例如姑姑受男友王小倜叛逃台湾的影响,在“文革”时期遭红卫兵暴力批斗,这里的暴力书写为姑姑后来的表现提供了逻辑支持,采用了一种平实的叙述方式。而在对姑姑作为计生干部期间的叙述中,莫言对暴力叙事作了温和化处理。莫言收敛起以往泥沙俱下、狂欢化的书写姿态,变得克制、温和,这种温和的书写方式影响着他对暴力的表现。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后,姑姑对政策绝对拥护,这种狂热与姑姑当年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政治清白并无二致,目的都是为了寻求组织信任与认同,同时也反映姑姑对政策出发点的肯定。“计划生育不搞不行,如果放开了生,一年就是三千万,十年就是三个亿,再过五十年,地球都要被中国人给压偏啦。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人为全人类做贡献!”[1]123在农村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姑姑面对的是上级下达的指标与村民超生的矛盾,在双方的压力之下,姑姑只能采取所谓的土政策:“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1]121耿秀莲、王仁美、王胆就是土政策之下的牺牲品,文本以这3位女性为例证,在姑姑与她们的追与逃之中展开一系列的暴力叙事。
姑姑与超生者的追逃就像猫捉老鼠,耿秀莲为逃避姑姑的追捕藏匿在水下,姑姑开着计生专用的机动船在水上与孕妇展开你追我赶的“游戏”。人的肉身终究无法战胜机械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悬殊最终造成了耿秀莲一尸两命的结果。这段追捕的结果是悲惨的,然而在莫言笔下,这却如同游戏一般,作者以意识流的手法,通过叙述者的视角将船下耿秀莲的奋力逃生与对王肝和小狮子肢体接触的旖旎意淫混杂在一起。这种情欲的想象与追捕超生者游戏化地交织在一起,消解了实际追捕过程的残酷,只有耿秀莲的死无声地控告着这一暴力行为。
躲着生,是超生者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无奈选择。王仁美为躲引产手术藏于地窖,袖珍的王胆也冒着风险怀孕,试图离开高密东北乡分娩。姑姑不仅摸清超生者的类型,并且针对个体差异还形成了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对躲藏在地窖里的王仁美,姑姑并不直接闯入其家中,而是将邻居的树推倒,甚至还要推倒邻居的房屋来胁迫王仁美“自首”。在这段对峙中,莫言对推树这一系列过程的书写可谓具体:
“链轨拖拉机发出一阵震动耳鼓的轰鸣,钢丝绳绷成一条直线,嗡嗡地响,绷紧,绷得更紧,绳扣煞进了大槐树的皮,渗出汁液。”“钢丝绳已经深深地煞进树干,剥去了一块树皮,露出了里边白色的纤维。”“拖出来了,嘎嘎吱吱地响,有的树根折断了,越拖越长,好多条大蟒蛇一样的树根……细小的树根频频折断,地下升起一些尘土。众人搐动鼻孔,嗅到了新鲜泥土的气味和树枝的气味。”[1]128-129
扎根在土壤中的槐树没有反抗与逃跑的余地,只能在机械的震怒下被抽去生命。在槐树被暴力推倒后,王仁美主动走出地窖接受引产手术。文本以叙述者在手术室外的视角记录,手术室传出的金属碰撞声与拖拉机的轰鸣声交汇,正如槐树在拖拉机面前的无力与渺小一般,王仁美年轻的生命在手术刀下戛然而止。对槐树推倒过程的具象化描写和对王仁美引产的过程略写,可以说是莫言的有意安排。他并非不擅长书写血腥场面,一部以刑罚为题材的《檀香刑》就足以证明他对暴力书写的熟稔,而这里正是他有意回避直面暴力的写作策略。
姑姑向超生者们施压招致了人民群众的反向暴力。耿秀莲的3个女儿对姑姑进行分工明确的攻击。王仁美死后,其母亲在失控之下将剪刀捅进姑姑的大腿里。这些反向暴力的情节正如施暴动作本身一样短促,在文本中只有寥寥几句,但这些暴力的表现与血的代价是不容忽视的,它们的存在提醒着我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者与被执行者都会遭遇暴力。
除了游戏化暴力、有意略写暴力或是缩短暴力时间之外,莫言还用一种平衡的方式来削弱暴力的力度。文本有意交代耿秀莲患风湿性心脏病、王仁美因体质问题在引产中失血过多、王胆因体型袖珍不适合生育的情况,这些人物的疾病与残缺并非偶然,是作为3人死亡的根本原因来削弱死亡结局的残酷性,为可能带来的争议寻求自洽的逻辑支持。此外,在抢救耿秀莲与王仁美时,姑姑都有过为她们献血的行为。王胆早产,姑姑则放下计生干部的任务,以医生的仁爱之心接纳了这个新生儿,并且在陈鼻对孩子弃之不顾时,无私地照料孩子。这些细节的补充平衡了姑姑暴力追捕超生者的“恶”,弥补了执行者暴力行为下的后果,淡化了暴力的色彩。
在《蛙》中,莫言通过对暴力游戏化、略写化、缩写化以及平衡化的方式,将暴力书写的力度大大降低,从而使该文本表现出与其以往作品对暴力的狂欢化书写不同的特点,这是一次温和的暴力叙事。
(二)温和暴力的写作缘由
作者在创作中扬长避短无可厚非,但反其道而压抑自己擅长的写法,就不得不引人疑问,莫言为何削弱书写暴力的力量呢?
从莫言以往的作品来看,他一直致力于对文本形式的探索,例如《红高粱》中“我爷爷”的叙述视角,《生死疲劳》的六道轮回结构,《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的复调叙述方式等。在《蛙》中,莫言再次从文本形式入手,文章由5部分构成,第1到第4部分是叙述者“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书信,第5部分是“蝌蚪”所写的剧本。但从严格意义上来看,第4部分书信只有每一部分开头与杉谷义人的问候称得上是书信体,其余部分以小说的形式承载姑姑的故事。尽管莫言不时地以叙述者向杉谷义人诉说的姿态添上“先生”的称呼,但回归文本就可知道这一称呼的冗余:“先生,匆匆忙忙讲述大爷爷的故事,是为了从容不迫地讲述姑姑的故事。”[1]15这里的“先生”就算略去也不妨碍故事的推进,但莫言毫不吝惜对“先生”的使用,坚持以“先生”的称呼来维持整个文本的书信氛围。写信人的身份是一位作家,收信人同样也是作家,知识分子之间的话语交流是内敛的,当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书信的书面化特点并置,就决定了文本将不再是莫言以往粗犷、狂欢的风格。此外,写信人自称是收信人的学生,师生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叙述口吻的尊敬与节制。莫言以往信马由缰的书写方式也不得不规矩起来,暴力色彩也随之淡化。
在《蛙》后记中莫言吐露了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他从2002年就已开始动笔,采用“以一个剧作者在剧场中观看舞台上正在演出自己所写话剧时的诸多回忆联想为经纬”[1]342的结构方法,但他的自觉写法又在重复荒诞夸张的旧套路,且结构方法有刻意之嫌,于是暂时搁置这份书稿而构思起《生死疲劳》。一直到2007年,莫言才重拾书稿,将原来的结构改为书信体,为了避免平铺直叙,加入了第5部分的话剧与正文互补。由莫言的自述来看,《蛙》的结构方法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斟酌与选取,这与作品的取材有一定的关系。《蛙》以计划生育为切口,可以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计划生育一方面被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步事业’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则成为90年代以来主旋律乡土文学突出乡村基层政治尴尬现状和困境的点缀性情节”[2]。计划生育题材尴尬的写作状态是由其敏感性带来的,用何种方式来叙述计划生育,关涉政治与道德的正确性问题。莫言的《蛙》虽以计划生育为题材,但臧否政策的功过并非其写作的目的,计划生育政策只是他探讨人性的背景。倘若过度书写计生过程中的暴力手段,作者的写作重心容易落在政策评价上,不免喧宾夺主,因而莫言选择了有限度地书写暴力,以较为公正的姿态来呈现国家意志与民间伦理之间关系的张力。
莫言巧借书信私密性的特点,构成私人话语空间,“讨论的虽然是属于公共领域的生育问题,却不是对它的公开检讨,而仅仅是亲密朋友之间的个人交流。这种公共话题的私密化表达,无形中为小说可能出现的价值偏差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障;即便有什么尖锐意见,也仅仅是对公共问题的私人性意见,不必过度解读”[3]。书信体的私密性为文本提供了大胆讨论的保障,不失为一种策略性的选择。与此同时,叙述者的知识分子身份也为反思与赎罪意识创造了可能。
倘若暴力书写不能作为文学思考的辅助工具,而只是为了满足猎奇心理与商业利益的话,那它只能削减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暴力现象,这是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无法忽略的。如何在不破坏文学真实性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地把握好暴力书写的限度,莫言用《蛙》的书信体结构交出他的答卷。
二、深刻的创伤书写
由《檀香刑》狂欢式的暴力叙事转向《蛙》温和的暴力叙事,这种转变是否减弱了《蛙》的表现力?事实上,莫言借助暴力后的个体创伤书写,从侧面更突出了暴力的残酷。通过莫言的《蛙》,我们看到了政策执行的难度,超生者对新生命的渴求,这些都是政策之下的隐痛,《蛙》将这些疼痛集中在作品中的小人物身上,为这些宏大叙事下的个体发声。在深刻地展现个体之痛后,《蛙》超越了莫言以往创伤叙事对宏观历史的批判,将反思对象聚焦到个体身上,乃至将解剖刀转向自我,审视自我的罪恶。
(一)疾病隐喻下的精神创伤
创伤书写是莫言在《蛙》中对个体之痛的呈现方式。创伤叙事用口头或书面的方式对创伤记忆进行讲述,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对创伤体验进行重现。创伤叙事受到创伤主体记忆偏差的影响,从而产生错位、遗漏,这与文学的虚构性相结合,生发出不同形式的文学创伤叙事,有时是对创伤事件的直接呈现,有时会经过重新编排、再造。尽管其真实性常遭质疑,但它能为人们提供认识与想象历史的途径,感受亲历者的无形疼痛。
以往文学的创伤书写多是战争、政治、灾害等主题,但《蛙》的计划生育主题为创伤书写提供了新的叙事维度。“创伤源于现代性暴力,渗透了资产阶级家庭、工厂、战场、性/性别、种族/民族等个体和集体生活的多层面,是现代文明暴力本质的征兆。”[4]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者与超生者在孩子“去与留”之间博弈,双方在对抗中的摩擦、冲突甚至暴力行为,都会给二者留下创伤记忆。这些暴力行为引发的个体精神创伤,在莫言的创作中得到了文学性的表征。
如果说《蛙》的暴力叙事是以一种温和、平实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暴力之后的创伤书写则因小说与戏剧的拼贴呈现出荒诞的色彩。在文本第4部分,叙述者从青年人变为退休人士,高密东北乡经济腾飞,升级为“朝阳区”,但人们的精神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态,尤其是在计划生育时期受挫的群体。
姑姑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同时又兼具高度的政治热情,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人口控制手段显然与其对生命的珍视相违背,历史将姑姑摆在计生干部的尴尬位置,注定要她作出选择。无论选择哪一方,她都会因放弃另一方而痛苦。在文本中,莫言以“蛙类恐惧症”将姑姑无以名状的痛苦具象化。“蛙类恐惧症”源自姑姑一次荒诞的臆想,在退休当天,姑姑喝了假酒,意识不清,在一片洼地里她先是听到凄厉的蛙鸣,后来便遭到成千上万的蛙的猥亵与攻击,险些丧命。自此姑姑对蛙有了应激反应,蛙成为她最惧怕的生物。蛙群攻击显然和姑姑喝了假酒产生幻觉有关,尽管莫言诉诸听觉、触觉、视觉等感官上的细节描写,为姑姑的幻觉搭建真实感,然而蛙群非正常的攻击行为依然提醒着读者这是作者想象的结果。“蛙”与“娃”谐音,作品题目为《蛙》,内容却围绕着“娃”。叙述者在介绍自己的剧本《蛙》时说道:“暂名青蛙的‘蛙’,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娲’。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我们的泥塑、年画里,都有蛙崇拜的实例。”[1]308“蛙”与“娃”在文本中构成一种象征关系,对蛙的恐惧实际上来源于姑姑对被手术流掉的娃娃的愧怍,计划生育时期的记忆俨然成为姑姑的梦魇。
经历被遗弃、毁容、掉入代孕公司陷阱的陈眉是文本中悲剧性最强的女性,她是王胆计划外生育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代孕产业链中被利用的一环。莫言将陈眉塑造成单纯善良、坚强孝顺的独立女性,又将她放置在金钱至上、正义体制失序的现代都市。经历容貌乃至精神的毁灭,陈眉最终精神失常,在孤独、痛苦与虚无之中以一己之力对抗着社会的不公。
姑姑的“蛙类恐惧症”与陈眉的精神失常并非闲笔,小说并非只是为了表现她们在病理学上的种种症候,而是通过人物疾病凸显暴力带来的残酷,将潜藏在内心的痛苦通过人物的异常举动来表征,以此隐喻历史前进过程中人们遭遇的精神创伤。姑姑与陈眉的病态是创伤亲历者痛苦的外化,这种病态放置在正常运作的社会当中,是互斥、失序的状态,在文本中以叙述者的视角呈现,想更好地体会创伤者的痛苦,创伤亲历者的自述是最好的证词。
(二)创伤言说下的真实经验
如果疾病隐喻是由叙述者转述的创伤叙事,那么亲历者的创伤言说更显得尤为直接。姑姑、陈眉、秦河、陈鼻等人物的非正常状态都是以叙述者的话语表现的,这些人的非正常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被建构的,需要回到创伤主体的言说中辨认。以姑姑和陈眉为例,二人非正常的行为表现是在小说部分完成的,是被言说的他者。第5部分则借助剧本形式让姑姑、陈眉脱离叙述者的代言,自由地吐露内心的痛苦:“最近,我的失眠症又犯了,那个讨债小鬼带着那群残疾青蛙每天夜里都来吵我,我不但能感觉到他们凉森森的肚皮,还能嗅到他们身上那股子又腥又冷的气味。”[1]336“实话告诉你们,最近,我经常想到死。”[1]337“老虎,豹子,狼,狐狸,对这些常人害怕的东西姑姑是一点不怕,但姑姑被这些蛙鬼们魇怕了。”[1]338在姑姑的自白中,有着对失眠、蛙群的恐惧,以及由此衍生的死亡念头,这些都是创伤引发的个人真实体验,只有创伤经历者能体会,这是他人无法代替的痛苦。
小说部分交代了陈眉毁容和陈耳殒命的遭际,在剧本部分则以陈眉的自述托出她内心的痛苦。对陈眉而言,要回被抱走的孩子成为她的执念,而这一执念正是文本中多方极力阻止的,个人的执念与多数人的意志对立,个人就容易成为被质疑、唾弃的异类,于是陈眉成了“疯子”。当姑姑深省自己欺瞒陈眉的罪过时,“蝌蚪”却认为:“不管怎么说,陈眉是疯子,而且是个严重毁容、面貌狰狞的疯子,我们将孩子交给她抚养,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1]337陈眉真如“蝌蚪”所言是疯子吗?陈眉向警察小魏、判官高梦九陈述的事实有条有理,而这些正义机构却为维护非法组织的利益站在了真相的对立面,把掌握真相的人归为“疯子”。“蝌蚪”也为了说服自己接纳代孕而来的孩子,将陈眉视作“疯子”,企图为自己剥夺陈眉抚养权的行为确立合法性。
对于自己被动地成为“恶人”,姑姑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反省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因而不断遭受创伤记忆的攻击,这种勇气是罕见的。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力逐渐下降,生育乱象频现,体制外的人在流动地生、秘密地生,甚至出现代孕产业链,政策早已被无视。在良心泯灭与道德淡薄的时代,姑姑的痛苦显得尤为突兀和讽刺,也更加珍贵。陈眉遵循着公平、正义的准则,怀抱赤子之心看待世界,但社会的非正常状态却将她的信仰击溃,将她生的希望掠夺。姑姑和陈眉这些良心未泯的“狂人”是真正单纯、善良的正常人,她们象征着自然的良知与道德,那些为了金钱利益丧失道德、公正、职业操守的人才是非正常的人群。这证明了姑姑和陈眉的“失常”是被非正常的社会所建构的,反思和质疑精神的稀缺让拥有这些精神的人成为他者、成为“狂人”,莫言以疾病隐喻与创伤言说完成了这一叙述。
(三)受害者亦是加害者
文本以疾病隐喻、创伤言说的方式表现人的创伤体验,但创伤的展示不是莫言最终的写作目的,这从莫言对创伤主体赎罪行为的表征中可以推知。如果仅仅只是展示创伤,那么赎罪行为的呈现就显得节外生枝,因而创伤书写是莫言为指向最终写作目的的叙述策略。赎罪意味着心中带有罪恶感,文本中多数创伤主体的痛苦在于他们自觉自己既是受害者亦是加害者。
叙述者给杉谷义人所说的最后一封信件里写道:“先生,我原本以为,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赎罪的方式,但剧本完成后,心中的罪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沉重。”[1]281叙述者是受害者,但他为了仕途顺利将妻子推上手术台,最终导致一尸两命,从这一意义上说,叙述者也是加害者。
叙述者对杉谷义人所说的话在姑姑身上同样适用。为了逃脱剥夺生命的罪恶感,姑姑不断地寻求赎罪的方法,甚至从唯物走向了唯心,嫁给救命恩人郝大手,并让郝大手捏泥娃娃还原被流产的孩子,日日供奉泥娃娃。此外,为了弥补对“蝌蚪”的愧疚,她与“蝌蚪”夫妇合伙欺骗代孕者陈眉,称她的孩子是小狮子所生,但这些自欺欺人的“瞒和骗”无法安抚姑姑内心的罪感。戏剧中叙述者为姑姑解释剧本:吃青蛙的人最后都变成青蛙,而姑姑是保护青蛙的英雄。但姑姑矢口否认:“不,姑姑手上,沾过青蛙的鲜血。姑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们蒙骗,吃过青蛙肉剁成的丸子。”[1]310鲁迅小说中“吃人”的文学传统在这里得到延续,姑姑被历史推上加害者的位置,在无知无觉中伤害别人,当历史的浪潮落下,姑姑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时,才发现自己也“吃过青蛙肉剁成的丸子”,从此饱受精神折磨,她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
叙述者与姑姑的痛苦来源于他们回溯过往时的反思,这种反思精神引领着他们获取审视自我、承认错误的勇气,也为他们带去无从赎清罪过的痛苦。在《蛙》的后记里,莫言的一句“他人有罪,我亦有罪”为二人的痛苦作了注脚。文本中虽然以暴力叙事呈现出了政策带来的国家意志与民间伦理之间的矛盾,但最重要的是莫言并不止步于暴露问题,而是更进一步将解剖刀转向人的内心,发出了人人有罪的声音,以此增强反思的力量。
回溯莫言往期的创作,创伤叙事并不鲜见,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莫言对饥饿体验的创伤书写。其小说《粮食》《铁孩》《四十一炮》《丰乳肥臀》等作品中均有对饥饿的描写。对饥饿重复书写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莫言童年时期的经历,“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5]。饥饿带来的巨大痛苦已成为一道疤痕烙印在莫言的内心深处,这种疼痛无法随年岁的增长而消解,只有重复书写才能纾解饥饿体验的创伤,因而童年对抗饥饿的经历都成为莫言创作的原料。在《丰乳肥臀》和《粮食》中,出现了同样的情节,母亲为了养活孩子,偷偷将做工时接触到的豌豆吃进胃里,到家再呕吐出来做成食物。2000年,在斯坦福大学作的《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演讲中,莫言谈到了童年吃煤充饥的体验,这一体验在《蛙》里得到了表现,在饥饿感的驱动下,孩子们主动吃煤,甚至从煤里吃出滋味与乐趣。《丰乳肥臀》中的乔其莎不仅为粮食委身于人,更在饥饿感的作用下暴食豆饼胀死。莫言对饥饿的重复书写,是童年创伤记忆在创作中的投射,而这种创伤叙事并不仅仅为再现特殊时代下个人的苦难,记录饥荒时代的集体记忆,更是借以反思造成苦难的根源。如果说饥饿的创伤叙事最终指向的是对宏观的时代与政治的批判,那么《蛙》中的创伤叙事不再拘泥于对宏观世界的指控,而是将个体拉回到微观视野进行审视。
《蛙》将创伤亲历者放置在受害与施害的双重处境之下,丰富了创伤叙事的维度,使文本的创伤叙事不仅具备再现历史、治愈创伤以及反思苦难根源的功能,还增加了创伤亲历者的自我拷问。这种自我拷问突破了莫言以往创伤叙事对历史、政治的质询,回到思考人本身的罪过上。“关心创伤及其再现,不仅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了解,也是重新揭开过去的伤口,审视那曾经的疼痛,并完成(work through)心理重建的过程。”[6]《蛙》的创伤书写借助疾病隐喻,将计划生育执行过程中一些人遭遇的精神创伤具象化,以此表现这些群体的创伤程度。此外,作者还在文本的剧本部分将言说的权利归还创伤者,以创伤者的自白对那些被言说的“狂人”指控进行反击,从而还原创伤者的真实创伤感受。小说走向人内心的幽暗之处,从创伤中审视自我,凸显反思自我的力量。
三、结语
面对计划生育史这样一段敏感又不容忽视的记忆,莫言选择其擅长的暴力叙事来呈现,然而《蛙》中的暴力叙事在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之下,已不再是夸张、变形,而是以温和的力度来书写。文本中暴力的主要实施者姑姑,在退休后饱受罪恶感的煎熬,赎罪无门的她,陷入创伤记忆之中无法抽离。莫言借个体的创伤让我们思考如何化解国家意志与民间伦理矛盾,这一书写放置在中国文学史的视域下是可贵的,对于唤醒人们的反思意识是有效的。莫言以暴力叙事展露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艰难与强硬,以较为中立的姿态书写超生者与执行者两方的难处,文本中也并未评判政策的对错,仅在后记中才表明其本人对政策的肯定,这说明文本写作目的并非在于评价政策本身,而是着眼于政策执行中超生者与执行者两方的肉体与精神创伤,进而达成反思的目的。此外,作者在后记中“他人有罪,我亦有罪”的观点,更是将解剖刀朝向自身,反思的范围从外部世界一直延伸到内在心灵,是其文学思想向深处开掘的体现。
在一次访谈中,王尧问及莫言中国作家缺少什么时,莫言回答:“我觉得起码缺少这种叩击自己灵魂的勇气。”[7]在《蛙》中,莫言以向内转的姿态对人的内心进行解剖,得出“他人有罪,我亦有罪”的结论,从而揭示自我反思的重要性。可以说,这是莫言叩击自己灵魂的一次写作实践,他在创作中拾起正视自我内心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