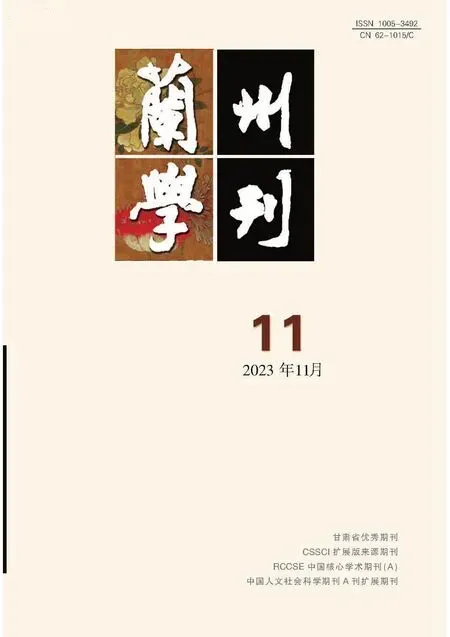孔子死后弟子们的“心思”
——从《论语·子张》看
陆建华
《论语》所记多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事迹,其二十篇中,唯有《子张》篇没有“子曰”或“孔子曰”,不记孔子所言,只有弟子“曰”,只记孔子弟子之言论。究其因,此篇所记,很可能是孔子死后,孔子弟子之言论。(1)黄朴民也认为《子张》篇所记孔子弟子的言论,“显然为孔子去世之后”的言论,不过,其未作论证(黄朴民:《文化生命的永恒:〈论语·子张〉绎义》,《中华读书报》2017年10月18日,第15版)。除此之外,此篇出现“子夏之门人”,载有“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载有子张、子游对子夏的批评,以及子游、曾子对子张的批评,也是证据。试想,在孔子生前,子夏、曾子还不及而立之年就聚徒讲学,曾子弟子阳肤就学业有成而去做官,是不太可能的;在孔子生前弟子就公开“争执”,批评对方的学术,甚至从道德的维度否定对方,也是不太可能的。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子张》篇所记孔子弟子之言论可以说反映了孔子弟子在孔子死后的“心思”。这“心思”涉及孔子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理解和宣扬,以及在继承、理解和宣扬孔子思想的过程中出现学术分歧时所显示的学术层面的“争执”;孔子弟子内部对同门的负面的道德评判,所显示的人际关系层面的“紧张”;孔子弟子对于孔子形象的维护,以及对于儒门的守护。“紧张”,反映了批评者以正统自居的心理。
《子张》篇所记孔子弟子之言论,涉及孔门十哲中的子贡、子游、子夏三人的言论,按照顺序来看,先后有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等的言论,都很集中,并且是连续的,因而对于研究孔子死后弟子们的“心思”,具有代表性。下面,我们将依次分析之。
一
《子张》篇前三章所记,皆是子张的言论,其中,第一章论及士,第二章论及信守道德,第三章涉及子张对于子夏的交友之道的批评,不过,不属于主动批评。
我们先来看第一章:“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以矣。’”这一章论述士。在子张看来,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重道德,重道德践履,轻个人利益,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祭思敬,丧思哀”,重情感,重礼之内在本质,轻外在的礼节仪式,为此,追求礼仪背后的情以及礼仪背后的礼的本质。这里,“见危致命,见得思义”,是对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等思想的继承和阐发,强调士对于仁义的追求;“祭思敬,丧思哀”,是对孔子所反对的“为礼不敬,临丧不哀”(《论语·八佾》)的警惕和反思,是对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等思想的承继和发挥,强调士对于礼的本质以及礼的背后的情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子张从德与礼的维度理解士的品质,是合乎孔子的观点的。 此外,子张的“丧思哀”,与子游的“丧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也是一致的。
子张之所以论述士,与其重视士,力求以士为标准要求自己,是分不开的。在孔子生前,子张就士的问题请教过孔子:“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颜渊》)从上述子张与孔子的对话可知,子张一开始以为士之所以为士在于名声,士所追求的是名声,孔子告诉之,追求名声并没有真正得到仁、践行仁,而是徒具仁的外表,士之所以为士乃是由于其求仁而得仁,士所真正追求的乃是道德、礼义、谦让,也即德和礼。基于此,子张在得到了士的真谛之后,才能在孔子死后正确的理解士。
接下来,再来看第二章:“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这一章论述信守道德。在子张看来,一个具有社会价值的人应该是持守、弘扬并信仰道德的人。这是对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等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抓住了孔子弘道、信道、学道、守道的思想精髓。联系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强调士对于仁的终生追寻与实践,可知,子张所谓“执德”“信道”者其实就是士。这么看,子张此章和上一章所论述的都是士,只是此章侧重于从德的维度论述之,而上一章则是从德和礼的双重维度论述之。
最后,再来看第三章:“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一章论述交友之道,但是,并不是子张主动说的。从子张“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来看,“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应出自于孔子,代表孔子的交友思想;子张“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是立足于孔子的“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而对子夏“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的批评。在子张看来,既然孔子认为君子尊重贤人、宽容普通人,赞美善人、同情能力不足的人,那么,子夏的“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就是错误的。因为依照孔子的意思,如果自己是君子,就能够宽容普通人,不仅与君子相交,而且也与普通人相交;如果自己是个普通人乃至小人,想与别人交友,也会被别人所拒绝,自己就没有拒绝别人的机会。
这里,子张对于子夏弟子的求教的回答是谨慎的,首先弄清了子夏的观点。如果子夏的观点跟自己的观点一致,子张是不会说出自己的观点的。由于子夏的观点跟自己的观点不一样,并且不同于自己所理解的孔子的观点,不是对孔子观点的宣讲,子张于是批评了子夏。子张对于子夏的批评是站在师门的立场上的,仅限于学术的层面,而且还是被动的。这可以看作是被动的学术批评。
由上可知,在孔子生前,子张虽然问为官之道、问治国之道、问仁、问礼,涉及孔子思想中的内圣与外王两个方面,但是,在孔子死后,子张所关注的主要则是修身、是士的品质,强调士对于德和礼的坚守、信仰,仅仅涉及孔子思想中的内圣的方面。关于交友之道,子张谨守孔子的“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对子夏提出批评,有其合理性。
二
《子张》篇第四章至第十三章所记,是子夏的言论,论及交友之道、“小道”、为学、修身、君子、节操、学与仕的关系等,其中,第十二章涉及子游对于子夏的批评以及子夏对于子游的批评的回应,子夏的回应属于被动发声。此外,子夏的言论还存于第三章。
我们先来看第三章中子夏的言论:“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这是在论述交友之道。在子夏看来,交友要有选择性,具体则为,与可以相交的人相交,拒绝、远离不可以相交者。这是对孔子“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毋友不如己者”(《论语·子罕》),“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等思想的继承、概括和发展。孔子就是认为交友是有选择性的,只能与比自己优秀的人相交,与士之中的仁者相交,与正直、诚信、博学的人相交。简言之,只能与德或才超过自己的人相交,只能与优秀的人相交。不过,相比于孔子对于交友条件的明确限定,子夏是灵活的,未作硬性规定。
接下来,我们依次来看第四章至第十三章中子夏的言论:
第四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这一章论述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的技艺的价值及其局限性。在子夏看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的技艺作为生产、生活的技艺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毕竟不是君子之道,不能据此成就远大目标,所以,君子不能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联系“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可知,子夏曾想学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的技艺,孔子以“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分告诫子夏,道、礼是君子之道,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的技艺是小人的技艺,学道、习礼才能成为君子,学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技艺只能成为小人,真正的君子、真正的儒者是不屑于学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的技艺的。子夏的上述言论是对孔子的教诲的牢记与体悟。不过,不同于孔子从“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分的维度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的技艺作全盘否定,子夏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的技艺本身的价值的维度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的技艺还是有所肯定,这一点不同于孔子。
孔子轻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的技艺是一贯的。他自己因为年少时贫贱,精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的技艺,可是,他并不以此为豪,反而说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认为真正的君子是不应该通晓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的技艺的。他的学生樊迟想学农圃方面的技艺,被他批评:“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农圃方面的技艺只是小人谋生的技艺,礼义道德才是君子修身、为政的根本。
第五章:“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这一章论述学习,涉及学习方法以及学习态度。在子夏看来,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就是时时刻刻学习,做到既天天学到新的知识,又时时通过复习的方式记住已经学会的知识,而不至于学了新知识就忘了旧知识。这是对孔子“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论语·述而》)等思想的准确把握和体悟。
从“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来看,子夏还试图以“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来理解“好学”。这是因为孔子本人就特别强调“学”,不仅评价自己好学,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还认为颜回是自己所有弟子中唯一好学者:“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这么看,颜回能够成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好学。
子夏对于“好学”的解读是否合乎孔子之意呢?从上述孔子谓其好学时将“好学”与“忠信”并举,孔子认为颜回好学时将“好学”与“不迁怒,不贰过”并举,可知,孔子以上所言的学是不包括道德修养、道德实践的,是关于知识方面的学,其“好学”也就是对于知识的孜孜追求。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孔子在德与学之间是从学的维度解读“好学”的。不过,孔子本人另有对于好学的直接解读:“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此处,孔子在德与学之间又是从德的维度解读“好学”的,孔子此处所言的好学乃是指君子对于道德追求、道德实践的勤勉努力。这么说,孔子关于“好学”有两种解读,一种是从学的维度解读,一种是从德的维度解读,子夏对于“好学”的解读合乎孔子从学的维度对于“好学”的解读。
第六章:“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一章论述学习,也论述道德修养。在子夏看来,从学习的维度看,学习包括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等四个方面,既要广泛地学习各种知识,又要在学习过程中有坚定的志向,善于提出并思考问题。从道德修养的维度看,道德修养也包括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等四个方面,既要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广泛地学习道德知识,又要有坚定的道德志向,还要善于提出并思考道德问题。从学习的维度看,子夏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是对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等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将孔子的学思并重、学问结合等熔铸于一体。从道德修养的维度看,子夏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是对孔子“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等思想的体会和发展,将孔子为学与为道、为学与修身相结合、相一致的思想作了进一步阐释。这里,孔子所谓的“学”是广义的“学”,是包括子夏所言学与思等的。此外,子夏“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涵括学习和道德修养两个方面,这与孔子所谓学主要是指“学道”,其所谓“学道”也指修道,强调为学的道德性、实践性有关。理解了孔子为学的秘密,“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将修道、行德理解为“学”,就容易理解了。
第七章:“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一章论述学习,专论君子所学。在子夏看来,君子学习的目的是掌握“道”,而不是工匠们的技艺。即是说,工匠们所拥有的技艺是小人的技艺,君子所应该拥有的则是“道”,所以,君子所学应是“道。”这同其所云“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一样,也是对孔子“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的教诲的谨守和体悟。
第八章:“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这一章论述小人对待过错的态度。在子夏看来,小人对于自己的过错所采取的态度是掩饰,而不是公开并改正,与小人相对,君子对待过错的态度就应该是公开之、改正之。这是对孔子 “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的自述的深思,以及“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论语·子罕》),“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顺便说一下,这里,孔子把主动公开自己的过错说成是自己的过错被别人发现,可见其君子之德。基于过则改之的思想,孔子赞扬颜回“不贰过”(《论语·雍也》)。
第九章:“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一章论述君子,具体论述君子的外在形象。在子夏看来,君子带给人们的外在形象是庄重、温和、严厉。这是对孔子“君子不重则不威”(《论语·学而》),“君子矜而不争”(《论语·卫灵公》),“色思温,貌思恭”(《论语·季氏》),“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论语·尧曰》)等思想的传承和运用。孔子认为君子具有庄重、温和、谦恭等特征,子夏将其运用到君子外在形象的刻画方面。
第十章:“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这一章同样论述君子,具体论述君子是如何对待民众和君王的。在子夏看来,君子无论是面对君王,还是面对民众,都要以“信”为先,因为“信”乃君子之德。这是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把“信”列为教育的重要内容的回应;对孔子“敬事而信”(《论语·学而》),“谨而信”(《论语·学而》),“主忠信”(《论语·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把“信”作为人追求的目标,作为君子之德,子夏不仅将之作为君子之德,还讨论其政治价值。
第十一章:“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这一章论述节操,论及权变及其界限。在子夏看来,大节是不可以违背的,小节是可以有所违背的,权变只能局限于小节的范围之内,不能超越根本的原则。这是对孔子权变思想的准确把握。孔子曰:“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强调权变;又曰:“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认为大信必须固守,小信不必拘泥,从而以“信”为例,明确说明权变的限度、界限。为此,孔子还以管仲为例讨论了权变的限度、界限。我们来看孔子所言:“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在此,子路、子贡拘泥于小节,认为管仲没有做到仁;孔子从大节方面看待管仲,认为其做到了仁。这意味,孔子所主张的,就是子夏所总结的“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第十二章:“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这一章论述君子之道的传授问题,涉及子游对于子夏传授君子之道的方法的批评,以及子夏的回应。可以说,子夏的观点是子夏在回应子游的批评时表达出来的。在此,我们只讨论子夏的观点。从子游所言“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来看,此章的君子之道应是指礼。在子夏看来,君子之道也即礼有本有末,对于礼的传授应该循序渐进,先传授其末,然后传授其本,也即先传授礼之仪,后传授礼之质,而不应该直接传授礼之质。这是对孔子传道方法的归纳、总结。比如,“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这里,林放问礼之质,孔子虽然反对舍本逐末,反对人们只重视礼仪而忽略礼的本质,但是,依然从礼仪的维度予以回答,认为只有认识礼仪,而又不拘限于礼仪,才能真正把握礼仪背后的礼的本质。这意味,在孔子看来,学习礼,既不能局限于礼仪的层面,又必须从礼仪入手进入礼的本质。孔子教育学生以君子之道,可是却对曾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认为自己所谓的道有一个核心,可见其一开始给学生传授的是道之末,在学生沉湎于道之末时,他才告诉曾子,其所谓的道有其“本”,应该从道之末入手进入道之本。这么看,子夏才是得到了孔子传道之精华。
第十三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一章论述“学”与“仕”的关系。在子夏看来,当官而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而有余力就去当官;当官而有余力就去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当官,学习而有余力就去当官,也是为了更好地当官。从内圣外王的维度看,“学”属于内圣,“仕”属于外王,子夏在此强调的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内圣的目标是外王。这是对孔子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等思想的发挥。
由上可知,在孔子生前,子夏虽然问孝、问礼、问政,涉及孔子思想中的内圣与外王两个方面,但是,在孔子死后,子夏所关注的主要则是交友之道、“小道”、为学、修身、君子、节操、学与仕的关系等等,主要涉及孔子思想中的内圣的方面,兼及其外王的方面。具体来说,子夏强调交友要有选择性,强调“小道”也有其相对价值,强调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对于“好学”与修身的重要性,强调君子的形象与品格,以及君子对于节操的守护,强调内圣以外王为目标。在子游质疑其关于君子之道的传授方法时,又辩护其君子之道的传授方法的正确性。
三
《子张》篇第十四章、第十五章所记,是子游的言论,论及丧礼、孝,论及对于子张的评价。此外,子游的言论还存于第十二章,涉及子游对于子夏的批评。
我们先来看第十二章中子游的言论:“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这一章论述君子之道的传授问题,系子游对于子夏传授君子之道的方法的批评。在子游看来,君子之道是礼,礼有本末,对于礼的传授应该先传授礼之本,后传授礼之末也即礼仪,学生所学最重要的是学到礼之本质。这是对孔子面对礼崩乐坏,重视、持守礼的本质的思想的深刻体悟的结果。在孔子看来,“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服、礼仪虽然可以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但是,不可以影响礼的本质;礼也不是礼器以及礼器所表征的礼节仪式,而是礼器和礼仪所体现的、礼器和礼仪背后的本质。既然孔子在礼仪与礼的本质之间看重礼的本质,子游便认为对于礼的传授,首先要传授的就是礼的本质,所以其批评子夏先传授礼节仪式是错误的。
接下来,再来看第十四章:“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这一章论述丧礼,也是在论述“孝”。因为孔子认为孝就是“无违”,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包括“葬之以礼”,也即包括正确的实行丧礼。在子游看来,办理丧事、举行丧礼要尽哀,要体现生者对于死者的哀痛之情,而不要在意礼仪的周到完备。这与子张的“丧思哀”(《论语·子张》)的主张是一致的。也是对孔子所反对的“为礼不敬,临丧不哀”(《论语·八佾》)的警惕和反思,以及对孔子“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论语·子张》等思想的承继和发挥,强调礼的本质以及礼的背后的情感因素。
最后,再来看第十五章:“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这一章是对于子张的评价,是从道德的维度加以评价的。在子游看来,子张虽然是自己的朋友,虽然努力践行仁,致力于道德境界的提升,这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但是,客观地说,依然没有做到仁。由于孔子曾言:“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认为仁是君子与小人区别之所在,是君子之为君子的本质之所在。这意味,在子游的心中,子张只是比普通人的道德品质好一点,并没有达到君子的境界,并不是个君子。
由上可知,在孔子生前,子游虽然问孝等,所涉及的仅仅是孔子思想中的内圣的方面,但是,在孔子死后,子游所关注的主要虽是君子之道的传授方法、丧礼,同样仅仅涉及孔子思想中的内圣的方面。此外,其对子张作过评价。关于君子之道的传授方法,其与子夏不一样;关于丧礼,子游强调丧礼背后的亲情,强调礼仪背后的礼的本质;关于子张,子游认为子张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不能被看作君子,这是对于子张人格和学问的否定。
四
《子张》篇第十六章至第十九章所记,是曾子的言论,其中,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是引用孔子之语的言论。这么看,真正表达曾子观点的言论也就只有第十六章和第十九章,分别论及对子张的评价和法官的为官之道。
我们先来看第十六章:“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这一章同第十五章一样,也是对于子张的评价,也是从道德的维度加以评价的。在曾子看来,子张虽然仪表堂堂,但是,难以和他一起做到仁。这意味,在曾子的心中,子张也没有达到君子的境界,也不是一个君子。这里,曾子并不像子游那样,把子张看作“友”,而是直接将子张的仪容与品格相对照,通过肯定其外表而否定其内心的方式评价子张。
接下来,再来看第十七章:“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这一章是曾子引用孔子之语的言论。曾子言其听孔子说过,人们平时是不会充分暴露自己的感情的,只有在父母去世时才会这样。这表明,孔子认为子女之于父母的感情应该是至深的,子女对于父母的孝体现在父母去世时所表露出来的对于父母的哀痛之情。这与孔子所反对的“为礼不敬,临丧不哀”(《论语·八佾》),所提倡的“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是完全一致的。
再往下看第十八章:“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这一章也是曾子引用孔子之语的言论。曾子言其听孔子说过,孟庄子的孝,在其他方面别人能够做到,可是,在不撤换父亲任用的官吏、不改变父亲的为政之道等方面是别人所难以做到的。这与孔子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观点是一致的。
最后,再来看第十九章:“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这一章论述法官的为官之道,即应当如何对待罪犯,但是,又不是曾子主动要说的。在曾子看来,天下无道,为官者胡作非为,民心因而早已散了,在此情形之下,民众犯罪,实乃为官者之过,如果能审出其真情,应该同情、怜悯之,而不应该喜悦。联系孔子所言“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可知,在孔子看来,天下有道,礼乐盛行,民众得到教化,才不会犯罪,相反,天下无道,礼乐崩坏,民众无所适从,才会犯罪。这么看,曾子的观点是与孔子一致的。
由上可知,在孔子生前,曾子虽然言及修身、孝、君子、士等,将孔子所谓的道归纳为“忠恕”(《论语·里仁》),阐述孔子的“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2)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论语·泰伯》)。这是对孔子“不耻下问”的阐述。,但是,几乎没有问过孔子问题,所涉及的仅仅是孔子思想中的内圣的方面;在孔子死后,曾子所关注的主要是孔子关于亲情、孝的思想,同样仅仅涉及孔子思想中的内圣的方面。此外,其对子张也作过评价。其虽然论述法官的为官之道,但是,这不是其所关注的。关于孔子对亲情的论述,曾子引用了孔子“亲丧”而“哀”的思想;关于孔子对孝的论述,曾子引用了孔子“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的思想;关于子张,曾子像子游一样,认为子张没有达到仁的境界,因而不是君子,这同样是对于子张的人格和学问的否定。至于其认为法官要有同情、怜悯之心,只是回答他人之问时所说。
五
《子张》篇第二十章至第二十五章所记,是子贡的言论。其中,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论及君子,第二十二章至第二十五章论及孔子。子贡此处所论孔子主要是对孔子的评价,不过,都不属于主动评价。
我们先来看第二十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一章论述君子。在子贡看来,纣之坏不像现在传说的这么夸张,是人们因其坏而把一切坏的名声加在其身上的结果,因此,君子厌恶处于下流,从而使天下之坏的名声都归于自己身上。这很可能属于子贡独创的思想,因为孔子不曾有类似的思想,孔子所谓君子“恶居下流而讪上者”(《论语·阳货》),也与子贡上述思想没有关联。
然后,再来看第二十一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一章论述君子对待过错的态度。在子贡看来,君子光明磊落,从不掩饰自己的过错,不仅公开自己的过错,同时还积极改正自己的过错;君子不是一个不曾有过过错的人,而是一个敢于暴露过错、改正过错的人,这也是君子的魅力之所在,以及君子被人们所敬仰的地方。子贡的上述观点,同子夏所谓“小人之过也必文”一样,是对孔子“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的自述的深思以及“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论语·子罕》),“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接下来,我们依次来看第二十二章至第二十五章中子贡对于孔子的评价:
第二十二章:“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这一章论述孔子的学问的来源以及学问的主旨,不是子贡主动言说的,乃为了回答卫国的公孙朝所问,维护孔子形象而不得不说的。面对卫国公孙朝通过质疑孔子没有明确的师承、专门的老师,来质疑孔子的学问,子贡首先指出孔子所学乃文武之道,因而其学问主旨乃三代之礼,然后才指出孔子虽然没有明确的师承,但是,并不意味就不能学到文武之道,因为文武之道存在于人世间,并不为少数人所专有,其中,贤者知其本而不贤者知其末,孔子并不需要专门的老师,其正是因为学无常师,从贤者和不贤者那里学到了文武之道之本末,才完整地掌握了文武之道。这里,子贡的回答既维护了孔子作为文武之道的继承者、宣扬者的形象,又认为其学无常师,符合孔子对于自己的认知。由于孔子自己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认为自己的学问来源于“学”,所以,当卫国的公孙朝问“仲尼焉学”时,子贡没有吹捧孔子是“生而知之者”(《论语·季氏》),而是认为其是“学而知之者”(《论语·季氏》)。由于孔子确实没有固定的、著名的老师,并且还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所以,子贡言其学无常师,不仅向贤者学习,也向不贤者学习。关于孔子所学的内容,从孔子的“好古,敏以求之”,可以看出,其所学乃是古代文化,具体而言,则为三代礼乐文化;从孔子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可以看出,在三代之礼中,其最看重周礼。再加上孔子一生研习礼、捍卫礼,梦想恢复礼治。由此,子贡认为孔子所学的内容是文武之道,可谓准确之至。
第二十三章:“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这一章论述孔子的伟大,也不是子贡主动言说的,是子贡在反驳鲁国大夫叔孙武叔故意以抬高自己来贬低孔子时说的。面对叔孙武叔的蓄意挑衅,子贡直面回击,以围墙的高低为喻,用围墙低,人们可以在围墙外就能看见围墙内的房屋的美好,而围墙高,人们只能在通过大门进入围墙之内,才能看到宗庙的华美和房屋的繁多,说明自己的优点人们容易看到,而孔子的伟大人们不容易看到,这正是自己远远不如孔子的原因之所在。这也说明,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不懂得孔子就不知道其伟大。
第二十四章:“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这一章也是在论述孔子的伟大,同样不是子贡主动言说的,是子贡在反驳叔孙武叔对孔子的诽谤时说的。面对叔孙武叔的诽谤,子贡直接回击,先说出孔子是诽谤不了的,任何诽谤都无损于孔子的伟大这样的结论,然后运用比喻的方式,给出理由:别人的贤能犹如山丘,是可以超越的;孔子的贤能犹如日月,是无法超越的;诽谤孔子,对于孔子没有丝毫损伤,只会表明诽谤者不自量力。
第二十五章:“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这一章同样是在论述孔子的伟大,同样不是子贡主动言说的,是子贡在回答陈子禽的疑问时说的。对于作为孔子弟子的陈子禽居然也怀疑子贡胜过孔子,子贡不得不首先告诫陈子禽谨言慎语,因为君子一言即可显示其有知或无知,然后,告诉陈子禽,孔子是不可以超越的,犹如天的高不可攀,自己和孔子的差距犹如天地之间的距离,接下来,才说出孔子不可以超越的原因,在于孔子具有治理好国家的能力,能够教育、引导、安抚民众,使之极力向善、齐心协力。此处,子贡告诫陈子禽谨言慎语,与孔子“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强调说话谨慎,是一致的。不过,孔子要求说话谨慎,是在言行一致的意义上提出的,子贡要求说话谨慎,是在认知的意义上提出的,这是二者的区别之所在。从子贡从外王的维度论述孔子的不可超越来看,陈子禽认为子贡胜过孔子也许也是基于外王的维度,不过,子贡给出的理由属于“假定”性质,并不是孔子所取得的实际功绩。
由上可知,在孔子生前,子贡虽然问君子、问士、问仁、问友,所涉及的仅仅是孔子思想中的内圣的方面,但是,在孔子死后,子贡所关注的主要则是君子,同样仅仅涉及孔子思想中的内圣的方面。子贡认为“君子恶居下流”,又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当别人在其面前诽谤、贬低孔子时,其又维护孔子形象,并通过这种维护将孔子塑造为三代礼乐文化的拥有者、传承者,不可以诽谤、超越的伟人,从而开启了后世对于孔子的“神化”。
六
从《子张》篇来看,虽然在孔子生前,子张、子夏问及孔子思想中的内圣与外王两个方面,不似子游、曾子、子贡仅问及或提及孔子思想中内圣的一面,但是,在孔子死后,子张、子夏和子游、曾子、子贡一样,主要就孔子关于内圣的思想加以守护、弘扬和发展,涉及修身、节操、为学、践仁、守礼、行孝等方面,以及君子、士等理想人格。其中,子张、子夏、子游、子贡着力于对于孔子内圣思想的弘扬和发展,曾子着力于对于孔子内圣思想的守护。曾子守护孔子的内圣思想,体现在其宣扬孔子内圣方面的言论而不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孔子关于外王方面的思想,都没有作解读甚至提及。
在对于孔子思想的弘扬和发挥方面,子张与子夏、子游与子夏有明显不同。子张与子夏的不同,是在交友之道方面,其中,子张对于子夏的批评,更是搬出孔子的“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直接以孔子之语批评子夏。其实,子夏所言的交友之道,也是根据于孔子的思想的。子游与子夏的不同,是在君子之道的传授方法方面,子游对于子夏的批评以及子夏对于子游的批评的回应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据。子张与子夏、子游与子夏在对孔子思想的理解方面各有不同,又都合乎孔子的思想,究其因,一方面是由于孔子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学生的具体情况,对于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甚至可能是差别很大的表述,造成弟子们所接受的知识具有“片面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弟子们对于孔子的思想在认识上各取所需,各有偏差。从子张、子游都对子夏提出批评来看,子夏在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上应是比较独特的,也许也是有较大的偏差的。这种独特、偏差也造成了其弟子的困惑,否则,“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这类事就不可能发生。由弟子们对于孔子思想的理解的不同,显示了孔子死后儒门在思想上的分化的倾向;由弟子们看似站在师门的立场、孔子的立场,实则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从学术层面去看待、批评对方的观点,而不是选择包容和理解对方,显示了这种思想上的分化的不可避免和进一步加剧,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弟子们在学术层面的“争执”。尤其是子游对于子夏的主动批评,显示了这种“争执”是人为的。而这种人为的“争执”,表明在孔子死后有的弟子有以正统自居的“心思。”
子游、曾子对子张均有评价,而且都是主动的评价,都是以仁为标准,从道德的维度对其所作的评价。对于子张来说,这种评价又都是负面的评价。从子游的“吾友张”来看,子游把子张不仅看作是同门中人,还看作“友”,以示自己和子张在个人感情方面的“亲密”,或者说,以“友”来确认自己对于子张的评价的准确性。这么看,子游的评价应该是比较客观的。由于曾子对于子张的评价和子游对于子张的评价是相同的,所以,也可以说曾子的评价也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当然,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子游、曾子对于子张的道德维度的负面评价是出于嫉妒。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评价伤害了子张。由弟子们对同门中人的、主动的负面评价,可以看出,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在人际关系层面的“紧张”已在所难免,儒门的分化除了学术的因素,还有人为的因素。儒门的分化,体现为同门中人从思想的分歧,到彼此关系的决裂。
其实,在孔子生前,孔子和子贡对子张就有评价,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评价:“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孔子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先进》)。从子贡“师与商也孰贤”来看,在子贡的心里,子张和子夏不仅比自己更优秀,在师门之中也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他才将二者作比较,问孔子谁更优秀;从子贡“然则师愈与”来看,即便孔子批评了子张,子贡却以为子张更优秀。这里,孔子虽然对子张作出批评性评价,指出其缺点,但是,孔子也同样批评了子夏,并指出子夏的缺点。再说,孔子对于弟子的评价,多是负面的,主要是为了指出其缺点,促使其改正之,比如他对子羔、曾子、子路的评价也是如此。即便对于自己最喜欢的弟子颜回,孔子也说过:“回也非助我者也”(《论语·先进》)。更何况,孔子对弟子的评价多是从性格、为学等维度加以评价的,并没有从道德的维度加以评价,从而不涉及弟子的人品。(3)王毓珣论述孔子评价弟子的原则,认为孔子评价弟子,均不涉及“道德”。王毓珣:《论孔子评价弟子的原则》,《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年第4期。所以单从孔子对子张的性格维度的评价,是看不出子张的人品的。另外,从子贡的角度看,子张是优秀的。这么看,子游、子夏对于子张的道德维度的负面评价就很难说是客观的,很有可能是出于对于子张的嫉妒。而嫉妒,乃是出于想“上位”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子游对于子夏、子张分别从学术和道德维度加以批评,其“上位”的心情更加迫切。
子贡对于孔子形象的维护和神化是被动的。叔孙武叔、陈子禽都认为子贡比孔子更优秀,其中,叔孙武叔还诽谤孔子,子贡对此作了坚决的回击,极力论证孔子的伟大及其不可超越,但是,其论证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属于类比、假设之类,显得较为苍白。这也说明子贡很可能至少在某些方面确实比孔子更优秀,以致于子贡言谈之时都找不到孔子比自己优秀的证据。再说,陈子禽是孔子的弟子,不太可能当着子贡的面乱说。
子贡的优秀,孔子生前是看出来的。“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这里,孔子对于子贡的评价不仅是正面的评价,而且还是很高的评价。“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这里,孔子因为担心子贡与颜回争斗,居然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这说明,在孔子的心里,子贡未必比颜回差,虽然孔子表面上只赞扬颜回,还有时批评子贡。子贡对孔子的提问心领神会,就顺着孔子的意图,说自己不如颜回,并从智力的层面加以论证。关键是,孔子一时激动,竟然说其自己也不如颜回,以此来压服子贡。既然孔子也认为子贡非常优秀,甚至不比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差,叔孙武叔、陈子禽都认为子贡比孔子更优秀,就至少有一定的合理性了。
既然叔孙武叔、陈子禽都认为子贡比孔子更优秀,子贡为什么不但不认可,还坚决予以回击?原因不仅在于孔子是自己的老师,二人存在着师生的名分,更在于子贡对于孔子的深厚的情感和子贡本人的高尚的人格,虽然孔子生前对待子贡并没有特别的地方,有时还当面批评子贡,有的思想没有传授给子贡,导致子贡有“怨言”。比如,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公冶长),批评子贡。再如,“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抱怨”孔子不曾将“性与天道”方面的思想传授给自己。
子贡对于孔子的深厚的情感和子贡本人高尚的人格,不仅体现在孔子生前,更体现在孔子死后。比如,“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子贡为了抬高乃至神化孔子,将孔子的圣人人格和“多能”归结为天意,连孔子本人都不好意思,而是将自己“多能”归结为“少也贱。”再如,孔子死后,据《孟子·滕文公上》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只有子贡一人为孔子守丧了六年。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就《子张》篇所载来看,在孔子死后,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等都主要从内圣的维度继承和弘扬孔子思想,这是他们共同的“心思”,其中,子张、子夏、子游、子贡主要是通过阐释孔子思想的方式继承、弘扬孔子思想,而曾子主要是通过引用孔子之语的方式继承、弘扬孔子思想。在弘扬孔子思想的过程中,子张、子游与子夏有明显的不同,并因此都批评子夏,显示了孔子死后子夏“受到同门的批评最为激烈”(4)高专诚:《子夏的思想成就和历史贡献》,《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第49页。,显示了儒门最初的思想分化,以及同门中人在学术层面的“争执”;在对同门中人的评价上,子游、曾子都从道德维度对子张作出负面评价,显示了孔子死后同门中人在人际关系层面的“紧张”以及彼此关系的决裂。这种“紧张”,反映了子张、子游、曾子在孔子死后都有以正统自居的心理,其中,子游先后联手子张、曾子,分别打击子夏和子张,以正统自居的心理最为强烈。由此也可以看出,儒门的分化有着客观与主观、学术与人为的因素。至于子贡,作为颜回之后,孔门最优秀者(5)辛安亭:《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最杰出的人物》,《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极力批驳叔孙武叔、陈子禽对于孔子的贬损,显示了其维护孔子的形象、守护儒门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