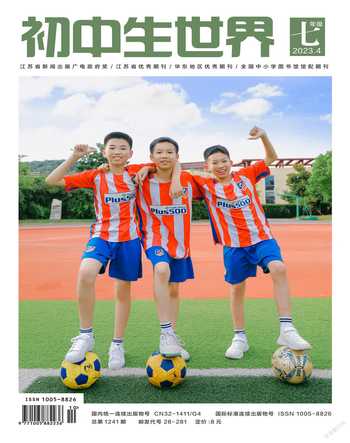百岁杨苡的翻译人生
刘梦妮
2023年1月27日20:30,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去世,享年104岁。杨苡首创了《呼啸山庄》的译名,并翻译出多部经典作品,得到广泛认可和赞誉。让我们重温杨苡的人生故事,缅怀先生。
杨苡,安徽盱眙(现属江苏)人,生于1919年。翻译家、作家。先后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翻译、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师。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著有儿童文学作品《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文字游戏,它使你夜不能眠,但最后你尝到了它的甜味。”刚刚过完103岁生日的杨苡,将翻译称为“游戏”,足见她的个性,事实上,“这是一种玩法”是她现在的口头禅。女儿赵蘅有时甚至觉得母亲就像一个小女孩,“并不是她的样子有多年轻,而是她仍然思维活跃,活力四射,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都好奇”。
常跟着哥哥杨宪益去书店
“我的命不好,因为我没有爸爸。”2021年5月,一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九零后》上映,影片最开头响起的是百岁杨苡的声音,将她的身世娓娓道来。赵蘅说,杨苡出生两个月时,她的父亲就去世了。“我外公是当时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我外婆很要强,也重视教育,对自己的三个孩子,她不分男女,都要求他们好好读书。”
三个孩子后来都学有所成。杨苡的哥哥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英译了百余种经典名著,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杨苡的姐姐杨敏如毕业于燕京大学,师从顾随,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杨苡小学和中学上的天津中西女校,在那里,她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中英文基础。
杨宪益是杨苡一生最崇拜的人。《九零后》纪录片中,杨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最欣赏的男性当然是我哥哥。” 小时候,杨苡总拽着哥哥的衣袖跟来跟去,买书、看电影、逛市场都要跟着,以至于杨宪益的同学开玩笑说杨苡是“小巴儿狗”。在杨苡的回忆中,哥哥总能满足她的各种心愿。
1937年,杨苡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南开大学。没想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的轰炸让南开大学沦为一片焦土,师生被迫南迁。于是,杨苡和几个同学一起坐船从天津到香港,再绕道越南,最终抵达昆明。
“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
在赵蘅看来,母亲杨苡走上翻译之路,除了受杨宪益的影响,还有沈从文与巴金的推动。杨苡到了昆明后,与同住在青云街的沈从文相识。她本想上中文系,但沈从文了解她的情况后,力劝她进外文系。“他说我妈妈英文底子那么好,不适合去读线装书。他很有预见性,是我妈妈人生大方向的指路人。”赵蘅说。沈从文常常鼓励杨苡多读书,不要荒废时间。晚年杨苡仍然记得,当年,夜里自己要睡觉了,对面楼上沈從文的房间里还亮着灯。
巴金一直通过书信影响着杨苡。在天津读中学时,杨苡就开始与巴金通信。这样的通信伴随着两人境遇的起起伏伏,持续了一生。大二那年暑假,杨苡与赵瑞蕻结婚,生下大女儿。之后,她应在重庆避难的母亲要求,到重庆中央大学继续学业。1942年6月,巴金写信鼓励杨苡:“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1943年底,巴金在信中谈到了翻译:“你有空,我还是劝你好好翻译一本书……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巴金是直言不讳的。1950年代初,他看了杨苡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俄罗斯性格》后也曾说:“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从那时起,杨苡下决心,“我的译文或译诗必须为读者着想,要经得起行家对照原文推敲”。
杨苡第一次接触《呼啸山庄》的故事,是在天津读中学时。她看了由小说改编的电影《魂归离恨天》,就被深深吸引了。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借读时,她在图书馆读到《呼啸山庄》的英文原著Wuthering Heights,萌发了翻译这本书的念头,还写信告诉了巴金。巴金得知后很高兴,回信鼓励杨苡并提出要帮她出版。
在杨苡之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本书,他的英文很好,却把书名译为《咆哮山庄》。“妈妈对这个书名不以为然。”赵蘅说。
1954年春,杨苡翻译这本书期间,恰逢丈夫赵瑞蕻被外派到民主德国教书。一天晚上,窗外狂风呼啸,雨点打在窗户上,此情此景,犹如亲临《呼啸山庄》的故事中。“就这样,妈妈的灵感突然来了。”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杨苡确定了“呼啸山庄”这一书名。
巴金也没有忘记十年前的承诺。1956年,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由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1980年,这本书再次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的40多年里,这一译本多次再版,至今仍然畅销。
“等待与希望”
在南京定居的杨苡,晚年总惦记着要去北京看哥哥。“妈妈一般年末来北京,因为舅舅的生日是在冬天,她要陪舅舅过生日。”赵蘅还记得,2009年春天,杨苡离开北京前在杨宪益家聚会,“我妈妈还像小妹妹一样倚着舅舅。分别时,舅舅笑着,妈妈已经哽咽了”。这是杨宪益和杨苡最后一次见面,半年后杨宪益去世。哥哥不在了,杨苡再也没有去过北京。
2022年8月之前,杨苡生活仍都基本自理。“她自己洗漱,保姆只是在旁边看着,避免她摔跤。她在家里都是用助步器自己走。”赵蘅说,杨苡喜欢靠在床头看报看书,还是电影电视剧的热心观众,“有喜欢的电影,她还会让保姆打电话叫我看,常常我在北京,妈妈在南京,我们看同一部电影”。杨苡家中充满怀旧、艺术和童真的气息。沙发靠背上和柜子里摆着可爱的玩偶,大多是亲朋好友送的,还有一个玻璃柜专门放各种各样的猫头鹰,有布的,有瓷的,有金属的,赵蘅说:“妈妈视猫头鹰为智者。”
杨苡一直记得1997年最后一次见到巴金时的情景,那时巴金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他坐在轮椅上,仍使劲对杨苡说:“多写,多……写!”1998年,杨苡与人合译完成《我赤裸裸地来——罗丹的故事》后就停止了翻译,但这些年来,写作一直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对笔下的每一个字,杨苡一如既往的认真,用她的话就是文章写出来要“摆一摆”,放上几天,再反复修改好几遍,直到满意为止。
1937年冬天,18岁的杨苡在读完《基督山伯爵》的英译本后,非常喜欢故事的结局,“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待和希望”。当时,南开大学被日本侵略者炸毁,她只能待在家中。在给同样身处沦陷区的巴金的信中,她写道:“我记得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书里的末一句话:Wait and hope,我愿意如此。”巴金在公开发表的《感想》中引用了这段话,并说“这wait自然不是袖手等待的意思”。40多年后,1980年底,听说巴金腿受伤后,61岁的杨苡在给巴金的贺年卡片中又写上“Wait and hope”。巴金在回信中聊到了1937年的那封信,又说,“我相信我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又是40多年过去,“等待和希望”仍是杨苡最爱的句子,不断出现在她的题词、文章和采访中。
(选自2022年9月16日《新华每日电讯》,本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