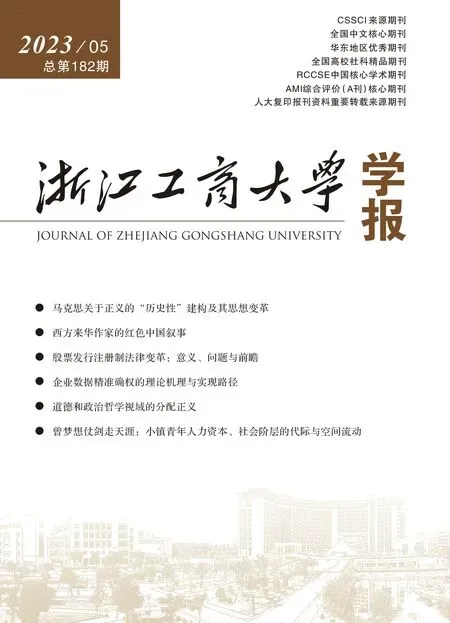“其美有如音乐”
——谈宗白华的艺术批评中的音乐思想
张 生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一、 绪言:“德国音乐本来深刻而伟大”
在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中,对音乐的看法或者运用音乐的法则来对艺术进行批评是其艺术批评的核心方法之一,也是其美学思想的重要特点。因为他不仅热爱音乐,还将音乐作为衡量所有艺术及美的重要标准。他称英国文艺理论家佩特(W.Pater)的“一切的艺术都是趋向于音乐的状态”是“最堪玩味的名言”[1]98,而这句话更是他在进行艺术批评时念念不忘的座右铭。更重要的是,他在对中国艺术的批评中,不管是对书法、绘画、舞蹈,还是对建筑,都引入了音乐性的批评,并且将具有音乐性作为最高的艺术境界予以揭示和表扬。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音乐性的批评不仅是他的艺术批评的独特之处,也是他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别具只眼的发现和建构。他还因此认为“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将自己所发现的“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用于建构礼乐的生活,同时表现于艺术之中,“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2]400-403。可以说,音乐性的批评是宗白华艺术批评的真正的“秘密”或“法宝”。
宗白华之所以对音乐如此重视并且将其作为艺术批评的至高法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1920年赴德留学之后的生活体验。他在出国前很少在文章中谈到具体的音乐,这当然与中国已非音乐的国度有关,但这种反差恰好使得他到了德国后对其生活中弥漫的浓烈的音乐气氛印象深刻:“我在德国两年来印象最深的,不是学术,不是政治,不是战后经济状况,而是德国的音乐。……德国音乐本来深刻而伟大。Beethoven之雄浑,Mozart之俊逸,Wagner之壮丽,Grieg之清扬,都给我以无限的共鸣。尤其以Mozart的神笛,如同飞泉洒林端,萧逸出尘,表现了我深心中的意境。”[3]414宗白华对德国音乐的热爱也由此而生,同时这也让他对叔本华和尼采等哲学家的音乐思想的认知变得更加深刻。与之同时,他接触的瓦格纳等音乐家和费希纳(G.Fechner)等美学家有关音乐方面的论述,也在不同程度上加深了他对于相关音乐理论的理解,从而也给他此后运用自己对音乐的深度认识来对艺术进行批评奠定了基础。
当然,宗白华将自己对于音乐的喜爱转化为对艺术的批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首先,他在1925年夏回国于东南大学暨其后的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后即专注于美学及艺术学的研究及教学,在理论上将音乐作为艺术形式的构成要素;之后,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转向中国书画的批评,开始将音乐的表现作为其中的重要因素;40年代初,他又提出中国艺术意境说,将音乐性尤其是舞蹈作为最高的境界。最后,他在50年代又专门对中国古代的音乐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他的音乐思想。
二、 艺术的“形式的结构”:“节奏”与“音乐”
宗白华对音乐的理论认识最早见于其1925年回国任教后为相关课程撰写的讲稿中,如《美学》(1925—1928)、《艺术学》(1926—1928)等。他在系统探讨美学及艺术学的过程中,涉及对音乐的特点及其与其他艺术的关系的认知,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他在这些讨论中将音乐的节奏与艺术形式相关联。虽然他对音乐精神的整体理解有歌德、尼采、叔本华等人的影响,但是对具体的音乐艺术特征的把握和转化却主要与他在柏林大学留学时的老师德索(Max Dessoir,1867—1947)的艺术理论的影响有关。德索作为德国艺术学的建立者和推动者,他的美学及艺术学思想对宗白华的影响很大。宗白华在《美学》和《艺术学》讲稿中不仅多次提到他的名字,还多次引用他的观点。如宗白华对于美感阶段的划分、对于艺术的分类等,都是直接来自德索的观点:“艺术学本为美学之一,不过,其方法和内容,美学有时不能代表之,故近年乃有艺术学独立之运动,代表之者为德之Max Dessoir,著有专书,名Ae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颇为著名。”[4]496这本书即出版于1906年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其中的思想对宗白华的艺术理论及音乐观点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首先,宗白华认为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的特征为其节奏与和谐。这个观点主要来自德索,后者认为审美对象因为有其一般性的特征,才得以让人产生美的印象,而音乐主要靠节奏予以表现。德索指出,审美对象的特性就是可以让人“愉悦”的相互关联的“因素”,“审美对象最为规律的特性包括一种呈现出直观必然性并引起愉悦的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属于同一秩序序列并同时被认识到。涉及品质时,这种联结关系就称为和谐;涉及数量与尺度时,便称为匀称。声音之间,颜色之间均可产生和谐”[6]97。审美对象的这种“最为规律的特性”共有三种,除了“和谐”与“匀称”外,还有和音乐直接相关的节奏,“节奏与节拍是富有审美价值的过程中所具备的两个客观特征”[5]109。此外,还有“大小和程度”,“在一件艺术品中,所有的特性都少不了大小和程度,而大小和强度在任何情况下又是与性质联系在一起的”[5]118。但宗白华并没有照搬德索的说法,而是对他的这个看法进行了概括,将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特征概括为“形式”上的“复杂一致”:“艺术上基本形式之美,即在所谓复杂一致也”[4]515。他进而指出,所谓的“复杂”(Mannigfaltigkeit)与“一致”(Übereinstimmung),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宗白华把德索的审美对象的三种特性“和谐与匀称”“节奏与节拍”和“大小与程度”转化为“复杂一致”的三种“美”的基本形式,即Eurhythmic,节奏的协调;Proportionality,大小的相称;Harmony,配合的和谐。在这三种美的形式中,他对音乐的节奏与和谐尤其重视,并且认为其不仅突出表现在音乐中,也表现在绘画、建筑等艺术之中,“Rhythm,本为音乐上的节奏,但斯审美对于大作品,如图画,不仅为空间的问题,亦带有时间性质,如中国之手卷画,即觉其波浪起伏,另有节奏也”[4]518。
其次,宗白华认为节奏是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并且节奏不仅是艺术的形式,也是生命和宇宙的形式。宗白华根据德索对艺术特性的概括把艺术的形式分为音乐的“节奏”、建筑的“比例”与绘画的“和谐”三种主要类型,虽然这三种“形式”均启示出“精神”“生命”和“心灵”的奥秘,但是他认为音乐是更为本质的一种“形式”:“音乐不只是数的形式的构造,也同时深深地表现了人类心灵最深最秘处的情调与律动。音乐对于人心的和谐、行为的节奏,极有影响。……但我们看来,音乐是形式的和谐,也是心灵的律动,一镜的两面是不能分开的。心灵必须表现于形式之中,而形式必须是心灵的节奏,就同大宇宙的秩序定律与生命之流动演进不相违背,而同为一体一样。”[6]54宗白华不仅对音乐的节奏推崇备至,更将其与人的心灵律动乃至宇宙的“秩序定律”相联系,这与希腊哲学的影响有关。他谈到希腊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等以艺术家的观点来探索宇宙的秘密,把所发现的音乐的法则扩展到宇宙的法则,从而将艺术与宇宙关联起来。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希腊大哲)以“数”为宇宙的原理。当他发现音之高度与弦之长度成为整齐的比例时,他将何等地惊奇感动,觉着宇宙的秘密已在面前呈露:一面是“数”的永久定律,一面即是至美和谐的音乐。弦上的节奏即是那横贯全部宇宙之和谐的象征!……艺术家是探乎于宇宙的秘密的[6]54!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对于毕达哥拉斯这种将“宇宙的原理”或“数的永久的定律”与“至美和谐的音乐”相联系和贯通的思想的赞叹,宗白华后来在批评中国艺术时才产生了“以道贯艺”或者“道艺合一”的想法,而不是很多人所认为的受庄子的“庖丁解牛”等篇中所表示的“道”“技”合一或“道”“艺”合一的思想的直接影响。相反,宗白华对于作为审美对象和艺术形式的音乐的节奏与和谐的重视,却深深地影响到了其中国艺术批评的方法及评价。
三、 中国艺术的“音的境界”:“绘画”与“书法”
宗白华因为在德国受到音乐的至深影响,又接受了德索对于音乐的节奏与和谐在艺术形式中的根本作用的观点,所以,在他之后转向中国艺术批评时,遂着意研究绘画、书法的音乐性的表现及特点,而他对艺术的音乐性的“赋值”,也使得人们对中国绘画和书法的认识进入“音乐境界”。他还给予谢赫的“六法”之第一法“气韵生动”以音乐性的解释,将其所表现出的音乐性的节奏看作中国绘画的最高境界。
首先,宗白华对于中国艺术的音乐性的批评,或者将音乐性作为考察绘画与书法等艺术的重要形式因素,既与德索的审美对象的特性理论有关,更与其对德国音乐在艺术中的“泛化”或“深化”的认识有关。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很快就发现了德国文化中音乐影响的无所不在,不管是文学、哲学,还是绘画、雕刻等别的艺术,都可见到音乐的特质的表现。
德国全部的精神文化差不多可以说是音乐化了的。他的文学名著如G.Keller等等的杰作,都是一曲一曲人生欢乐的悲歌。叔本华的世界观化入Wagner的诗剧,尼采的人生观谱成R.Strauss的《超人曲》,哲学也音乐化了,画家如Bocklin,Schwintters,Thoma等等,都谱音乐入山川人物之中。雕刻家Max Klinger的最大杰作,是音乐家Beethoven的石像。我常说,法国的文化是图画式的,德国的文化是音乐式的[3]415。
宗白华对德国音乐的这种认识不仅仅为其独有,与他同在德国留学的好友王光祈对此也印象颇深,王光祈认为自18世纪起,随着巴赫、亨德尔、贝多芬及施特劳斯的出现,德国开始“执欧洲音乐界之牛耳”,且被世人认为是“听的民族”[7]527。但是,与其后专业从事音乐研究的王光祈主要专注于音乐在其自身领域的研究有别,宗白华对德国的文化的“音乐化”精神的深入体验与认识,不仅使得他对于音乐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异常重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启发,就是音乐在艺术中的各种“化入”,这也使得他开始以音乐性的表现来评价文化的价值,或者用音乐的“眼睛”来审视艺术的意义。对他来说,这就是艺术所表现出的“生命的节奏”:“世界上唯有最生动的艺术形式——如音乐、舞蹈姿态、建筑、书法、中国戏面谱、钟鼎彝器的形态与花纹——乃最能表达人类不可言,不可状之心灵姿式与生命的律动。”[1]99这“生命的节奏”不仅是音乐的节奏,而且是宇宙间生生不息的节奏。
其次,宗白华基于对艺术的音乐性的认识,在对中国艺术尤其是对中国绘画与书法予以批评时,有意强调其音乐性的表现。尽管他认为建筑、音乐、舞蹈“乃最能表现吾人深心的情调与律动”,但是因为中国的建筑土木结构难以保存,雕刻又不够发达,封建的礼乐生活也已经消失,所以对音乐性的论述集中在以“笔墨”为基础的书法和绘画上。宗白华对于中国绘画的音乐性的批评,侧重于其“形线”所产生的美:“中国画是一种建筑的形线美、音乐的节奏美、舞蹈的姿态美。”[1]99-100形线的流动与飞转给人以音乐的节奏感和类似舞蹈的形象美,其实,舞蹈本身也是音乐的节奏的形象化,“中国画,真像一种舞蹈,画家解衣盘礴,任意挥洒、他的精神与着重点在全幅的节奏生命而不沾滞于个体形相的刻画。画家用笔墨的浓淡,点线的交错,明暗虚实的互映,形体气势的开合,谱成一幅如音乐如舞蹈的图案”[1]100。宗白华认为正是中国画的“形线”及由其“跳跃宛转”构成的“花纹线条”的“交织”与“融合”,使得中国画产生了有如“交响曲”一样的美。因此,与西洋绘画以“色调”表现个人心灵及世界的“色彩的音乐”不同,中国画是“点线的音乐”。但宗白华指出两者各有所长,他特地引用佩特的名言以说明,“虽然‘一切的艺术都是趋向音乐’,而华堂弦响与明月箫声,其韵调自别”[1]108。
对于书法的音乐性,宗白华更是给予不同凡响的评价,他认为书法不仅表现出了音乐性,甚至其本身就是音乐,“故中国书法为中国特有之高级艺术:以抽象之笔墨表现极具体之人格风度及个性情感,而其美有如音乐”[8]。他认为书法与画法一样,都可表现生命的节奏和心灵的情韵,尤其是对于中国画来说,其与书法联系紧密,不可分离。中国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引书法入画”,因为画中的各种点线皴法都来自书法;第二是“融诗心,诗境于画景”,各种线纹跳动飞舞表现了心灵的节奏,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国乐教失传,诗人不能弦歌,乃将心灵的情韵表现于书法、画法。书法尤为代替音乐的抽象艺术”[1]101-102。因此,宗白华不仅对书法的音乐性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还把书法直接作为音乐的替代品来看待。书法之所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是日常的写字工具外,还有就是其共有音乐的特性,或者说它就是一种特殊的中国音乐,既可以“演奏”也可以“观看”,触手可及又触目“惊”心,从而与人们的生活不可分离。也因此,宗白华在评价好友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绪论》时,将书法作为中国的“中心艺术”来看待:“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能表现人格,创造意境,和其他艺术一样,尤接近于音乐底,舞蹈底,建筑底抽象美(和绘画,雕塑底具象美相对)。中国乐教衰落,建筑单调,书法成了表现各时代精神的中心艺术。”[9]203
因此,宗白华将音乐作为书法和“也是写字”的绘画的共通之处,“书境同与画境,并且通于音的境界”。[10]不过,他将书法视为音乐或者与音乐相通的观点,他的朋友李长之却并不完全认同。李长之对书法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中国的一切艺术,几乎都以纯粹形式美的书法为目标。所谓纯粹形式美就是不问内容只问形式,但在形式中已显示了内在的意义”[11]330。但是,他并没有认为书法是音乐的化身,中国艺术以书法为目标,只是以其书写的“纯粹形式美”为目标,而并非以其所表现的音乐的节奏为目标,如他指出“天地玄黄”这四个平淡的字,由赵子昂或颜真卿写,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和美感,而其美观也并非由所表现的音乐的境界获得。相反,他认为西洋艺术倒是以音乐为目标,所以,“如果西洋的一切艺术,都憧憬于音乐的话,则中国的一切艺术,都憧憬于书法”[11]330。当然,宗白华对于书法音乐性的评价并非孤立无援,朱光潜就有着和他相似的见解,并且表述得更为明确:“再举我们中国的书法为例。其实中国书法就美来说,最近于音乐,可以说是有形的音乐。”[12]这显然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宗白华更将谢赫的“六法”之首的“气韵生动”予以音乐性的解释,他曾引入西方美术史家对气韵生动的解释作为其现代释义,认为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律动”[1]103,或者说是“生命的节奏”以及“有节奏的生命”[1]109。他还强调,“气韵生动,这是绘画创作追求的最高目标,最高的境界,也是绘画批评的主要标准”[13]465。宗白华将气韵生动理解为“生命的律动”或“生命的节奏”,目的是为了更为具体地把握其在绘画中的表现,这就是由中国画特有的线纹的流动、笔墨的浓淡变化等所形成的节奏。所以,气韵生动的核心就是其音乐性的“节奏”。
气韵,就是宇宙中鼓动万物的“气”的节奏与和谐。绘画有气韵,就能给欣赏者一种音乐感。……明代画家徐渭的《驴背吟诗图》,使人产生一种驴蹄行进的节奏感,似乎听见了驴蹄的的答答的声音,这是画家微妙的音乐感觉的传达。其实不单绘画如此,中国的建筑、园林、雕塑中都潜伏着音乐感——即所谓“韵”。西方有的美学家说:一切的艺术都趋向于音乐。这话是有部分的真理的[13]465。
因此,宗白华通过对气韵生动的音乐化的处理,给予了中国绘画的最高境界即音乐的境界以深化。同时,他也将这种音的境界扩大到中国的建筑、园林与雕塑中。当然,更不用说本来就是绘画基础的书法所具有的音乐性了。或因如此,汪裕雄等学者认为宗白华对中国艺术的音乐境界的批评来自对秦汉人“律历融通”发展出的“律历哲学”,由此“为传统美学思想探求出宇宙论的依据,发现我们先人的艺术心灵深处,原本振响着浩茫深邃的宇宙音乐”[14]。这个说法显然与宗白华受国外音乐理论的影响而对气韵生动等的音乐性的认识相悖。相对而言,胡继华的观点较为中肯,他认为宗白华引入了德国“生命哲学”对气韵生动命题予以改造,“发挥出‘生命之节奏’、‘生生而条理’、‘至动又和谐’的形上哲理——此乃中国艺术所呈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精神”[15]。但他更多地从生命哲学的现代性影响来阐述,而并未强调宗白华的这一改造中所蕴含的音乐特质。
四、 中国“艺术境界的典型”:“舞”与“道”
宗白华不管是谈论中国的绘画还是谈论中国的书法,在指出其音乐性的表现时,都将其接近于舞蹈作为最重要的特点。他认为虽然舞蹈与音乐有共通的地方,如舞蹈亦有音乐性,但后者为听的艺术,前者为视听合一的艺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更具综合性。他对于舞蹈的推崇,除了因为舞蹈本身即具有音乐性,也与尼采的酒神精神的影响有关,因为酒神精神即音乐与舞蹈之神。所以,他将舞蹈作为中国艺术之最高境界。同时,他又将舞蹈作为贯“道”之代表艺术,以此建立了自己的“道”与“舞”统一的境界,亦即“道”贯于“艺”或“道艺合一”的思想,最终揭示了中国文化将形而上的宇宙的“道”即生生不息的旋律贯穿于生活及艺术的富于音乐节奏之美的精神。
首先,宗白华在批评绘画和书法的音乐性时,都将其与舞蹈相通作为一个重要的特征。他尤其关注艺术家的身体姿态,从艺术家创作的角度出发,对其创作时心意与身体的“姿态”或者“用笔”的“姿态”予以舞蹈化的描述,认为不仅画家作画时身体与舞蹈相似,书家写字时身体也与舞蹈相通。所以,宗白华不仅以雷简夫闻江声潮涌波涛翻滚而写之于笔下如“通于音乐的美”,更以书家观舞作书等来指出其与舞蹈的共通之处:“唐代草书宗匠张旭见公孙大娘剑器舞,始得低昂回翔之状,书家解衣磅礴,运笔如飞,何尝不是一种舞蹈?”[9]203当然,“运笔如飞”表面上来自身体的姿态的舞蹈,实际上是来自生命的节奏,最后表现于绘画和书法之中,从而呈现出生命的节奏与韵律。这正是宗白华推崇舞蹈的原因。
其次,宗白华将舞蹈作为中国艺术意境的最高表现,与尼采的酒神精神有关。他认为在艺术家创造意境之时,既需要“活泼泼的心灵飞跃”,也需要“凝神寂照的体验”。这两种艺术生活的不同的“最高精神形式”,就是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他特地以中国画家黄公望(字子久)与米友仁二人“体验生活”的不同的方式予以说明:“黄子久以狄阿理索斯(Dionysius)的热情深入宇宙的动象,米友仁却以阿波罗(Apollo)式的宁静涵映世界的广大精微,代表着艺术生活上两种最高精神形式。”[16]361宗白华认为正是由于这两种不同“心境”,使得艺术呈现出一种“空灵动荡而又深沉幽渺”的境界,也即用日神的静照来涵映酒神的生命的律动。朱光潜曾对此有非常恰切的解释,认为尼采的酒神即为叔本华的“意志”(will),歌舞即是其艺术表现,日神则为“意象”(idea),造形艺术如图画与雕刻为其艺术表现,而希腊悲剧则是静观的阿波罗的意象与狂歌曼舞的酒神的结合:“这两种精神本是绝对相反相冲突的,而希腊人的智慧却成就了打破这冲突的奇迹。他们转移阿波罗的明镜来照临狄俄倪索斯的痛苦挣扎,于是意志外射于意象,痛苦赋形为庄严优美,结果乃有希腊悲剧的诞生。悲剧是希腊人‘由形象得解脱’的一条路径。”[17]宗白华同样认为艺术意境的构建如同希腊悲剧,由酒神与日神相结合而成,并且具有音乐性的酒神精神的舞蹈则是其“典型”:
因为这意境是艺术家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它不是一味客观地描绘,像一照相机的摄影。所以艺术家要能拿特创的“秩序、网幕”来把住那真理的闪光。音乐和建筑的秩序结构,尤能直接地启示宇宙真体的内部和谐与节奏,所以一切艺术趋向音乐的状态、建筑的意匠。
然而,尤其是“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在这时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16]366。
因此,宗白华直言,“‘舞’,是中国一切艺术境界的典型。中国的书法、画法都趋向飞舞。庄严的建筑也有飞檐表现着舞姿。……天地是舞,是诗(诗者天地之心),是音乐(大乐与天地同和)”[16]369。他对于中国艺术的“舞”的特质的强调,就是对于音乐性的强调,因为舞蹈的精神就是音乐的精神的具身化或者可视化。
最后,宗白华从舞蹈出发,通过对庄子的“庖丁解牛”的解读,指出其由“道”进于“技”,而“技”又合“舞”,最终则为道艺合一,因为二者本质上为一以贯之的音乐精神,即宇宙之生生不息的节奏所表现出的形而上的“道”,与表现出这种节奏的艺的契合无间:“道的生命和艺的生命,游刃于虚,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音乐的节奏是它们的本体。”[16]365这也使他得以将“道”贯于“艺”,建构出道艺合一的理论。但是,宗白华的这个看法的产生并非来自庄子于“庖丁解牛”等寓言故事中所体现出的道艺合一的观点,他在此只不过是用“庖丁解牛”来阐明自己的这个看法而已。因此,他坦承是荷尔德林的诗句“谁沉冥到/那无涯际的深,/将热爱着,/这最生动的生”给予他直接的启悟:
他这话使我们突然省悟中国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的特点。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16]367。
这就是宗白华的贯道于艺或道艺合一的由来,这种观点的诞生既与希腊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等人把艺术的发现推广到宇宙的做法的影响有关,也与尼采的酒神精神所表现的舞蹈艺术给予他的启发有关。汤拥华虽然也认为宗白华把舞作为中国艺术意境的典型并且将其拓展和深化为“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的化身是个创举,但却认为其未能像尼采那样做到尽善尽美,“宗白华看到了舞在言说艺术本体时的价值,但是他找不到很好的方式,可以像尼采解说古希腊悲剧那样解说舞与中国意境的关系”[18]。他的这个观点不尽合理,实际上,宗白华强调的是舞所具有的内在的节奏及其具身化,而这与他对中国意境的节奏的强调正相一致。因此,他才从庖丁解牛的“舞”引申出艺道贯一的思想并进而推广为“道器合一”,把宇宙之“道”即生生不息的节奏,贯穿于礼乐文化以及日用之器皿,同时表现在艺术之中,从而将整个中国文化笼罩在音乐的节奏之中,“使我们一岁中的生活融化在音乐的节奏中,从容不迫而感到内部有意义有价值,充实而美”,而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也是“宇宙的旋律”和“生命的节奏”的秘密[2]402。
五、 对中国音乐的批评:“不能发扬人的灵魂”
正是因为宗白华在德国所受到的音乐的深刻影响,使得他不仅在艺术批评中把音乐性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还非常重视音乐在生活中以及文化中的作用。他也因此对中国的音乐在生活及精神文化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批评。这其中既有他对中国音乐现状的不满,也有对中国音乐传统的衰颓感到悲伤,还有对中国曾有的传统礼乐文化的赞叹,以及对当时中国文化精神的缺憾的惋惜。
首先,就是宗白华对中国的音乐现状不满。他在1920年赴德留学前很少关注音乐问题,但德国生活中弥漫的浓烈的音乐气氛与国内的音乐现状所造成的强烈的反差,还有随着他对于德国音乐的深入了解,使得他对中国现代音乐的不足的认识也更为深刻。他以为音乐是民族精神的表现,而中国的音乐现状却让人体味到了一种“消极”的情绪,只是一种神经的“刺激”,却不能像德国音乐一样“发扬人的灵魂”。
中国现代社会上的音乐,听了都使人消极生悲感,能刺激人的神经而不能发扬人的灵魂,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以这种音乐表现这种民族精神,中国现在文化的地位可想而知了。中国旧文化中向来崇重音乐,以乐为教,则中国古乐之发达可知,然而,现在社会上音乐品格如此低下,真不是好现象。所以,我想中国的新文化中极需要几多谱乐家呢[3]415。
宗白华出于对中国社会的音乐现状的不满,而音乐又对人的精神生活有着深入的影响,为改善民族精神考虑,他自此开始力主更新和加强中国的音乐艺术。而他的好友王光祈虽然也有着与之相似的看法,但是他却更多地为中国音乐的特点进行辩护。他从西洋人和国人的“习性”与“民族本性”的不同出发,认为与西洋人因“习性豪阔”,“性喜战斗”,音乐又与宗教密切相关,所以其音乐有“壮观优美”的“城市文化”,“激昂雄健”的“战争文化”和“宗教国民”的“宗教音乐”的特点;与之相较,中国人因“恬淡而多情”,“生性温厚”,音乐与宗教关系不大,故音乐有“清逸缠绵”的“山林文化”,“柔蔼祥和”的“和平文化”与“哲学民族”的“陶养性灵”的特征[7]550。这是与宗白华不同的地方。因此,抗日战争期间宗白华主编《学灯》时,就特地编发介绍德国音乐家的文章,以激励和深化人们的精神:“现代中国人需要悲壮热烈牺牲的生活,但也需要伟大深沉的生活,音乐对于人生的深沉化有关系,我预备发表几篇音乐家的故事。”[19]在这些音乐家中,有肖邦、巴赫等。后来,在介绍巴赫时,宗白华尤其感慨其音乐在哥特式教堂里演奏时给予人的神圣与充实,以及对生命的“深沉化”。
哥谛式大教堂,塔峰双插入云,教堂里穹庐百丈,一切线条齐往上升,朦胧隐约,如人夜行大森林仰望星宇。这时从神龛前乐座里演奏巴哈的神曲,音响旋律沿着柱林的线丛望上升,望上升,升到穹宇的顶点,“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整个世界化成一个信仰的赞歌。生命充实,圆满,勇敢,乐观。一个伟大的肯定,一个庄严的生命负责。中国现代生活里不需要这个了吗?[20]
宗白华对中国音乐现状的不满,并不意味着对中国音乐传统的不满,他在谈到中国音乐的传统时,既为其曾经有过的辉煌而激动,也为其突然的衰颓感到悲伤和困惑。这也许是他竭力在自己的艺术批评中提出书法是音乐的替代的重要原因。或许,这其中也含有他对中国音乐为何消失的一个解释,那就是书法的出现。因为书法形线之美既可以让人有视觉的愉悦,也可以让人产生节奏的律动,而且更易普及,所以终取音乐而代之。但是,这并不能让他为中国真正的音乐的消失释怀。抗战时期,他在与朋友华西大学哲学教授郭本道闲谈时,对其从文艺角度谈到中西民族的特性的不同的观点非常赞同。郭认为中国的民族性近于“诗”,是“内向”的,是“悒郁多愁”的,而西洋民族则是“向外发扬”的,是“雄壮欢乐”的;宗白华则将中国的诗性与音乐性沟通,强调其同样是一种音乐性,只是与西洋的音乐性不同而已。
所以中国的“音乐”也近于“诗”,倾向个人的独奏。月下吹箫,是音乐的抒情小品。西洋的诗却近于音乐,欢喜长篇大奏,繁弦促节,沉郁顿挫,以交响乐为理想。西洋诗长篇抒情叙事之作最多,而西洋民众合唱的兴致和能力也最普遍[21]。
让人惋惜的是,到了宋代以后,随着诗的消失,即使是“月下吹箫”的音乐“小品”也消失了,因此宗白华很希望中国可以恢复唐朝时那种“诗歌音乐兴趣普遍”的状态。不仅重新恢复为“诗的民族”,也重新成为“音乐的民族”。当然,他不仅希望中国的音乐传统可以复兴,同时也希望可以吸收西洋音乐之所长,如同他对中国绘画的批评,希望变“明月箫声”般的“点线的音乐”为西洋绘画的“华堂弦响”般的“色彩的音乐”[1]108。
不过,宗白华认为中国音乐虽然宋以后不彰,但其精神传统却并未消失,那就是把“宇宙生生不已的节奏”,即天地创造与时间运行的伟大且“和谐”的“节奏”与“旋律”,贯彻到生活中去,使其礼乐化,并将其运用到日用的器具之上,以造成艺术之美。
中国人在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就是一切现象的体和用。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最能表出中国人这种“观吾生,观其生”(易观卜辞)的风度和境界,具体地贯注到社会实际生活里,使生活端庄流丽,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但这境界,这“形而上的道”,也同时要能贯彻到形而下的器。器是人类生活的日用工具。人类能仰观俯察,构成宇宙观,会通形象物理,才能创作器皿,以为人生之用。器是离不开人生的,而人也成了离不开器皿工具的生物。而人类社会生活的高峰,礼和乐的生活,乃寄托和表现于礼器乐器[22]。
这就是宗白华所说的“道器合一”,即将“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贯通。而这“道”就是一种音乐的节奏,“宇宙的旋律”。他认为,正是有了对于这种天地之道的体认和生活的贯通,使道艺得以合一,艺术因此而发扬,才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音乐的节奏,精神融化在音乐的旋律里,因此获得如孟子所言之“充实之美”。
宗白华认为这种独具特色的中国音乐精神有利也有弊。虽然中国找到了“事物旋律的秘密”,使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音乐的节奏,但却未能像古希腊和西洋近代的人一样,努力用逻辑,数学和物理去“把握宇宙间质力推移的规律”,也即找到“科学权力的秘密”,这导致了近代以来备受欺凌,成为西洋用“科学权力”武装起来的“霸权”的“牺牲品”,美丽的文化不能保存,本来就已衰落的音乐也彻底丧失了。
中国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因而轻视了科学工艺征服自然的权力。这使我们不能解救贫弱的地位,在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受人侵略,受人欺侮,文化的美丽精神也不能长保了,灵魂里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我们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我们丧尽了生活里旋律的美(盲动而无秩序),音乐的境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斗争)。一个最尊重乐教、最了解音乐价值的民族没有了音乐。这就是说没有了国魂,没有了构成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的高等价值。中国精神应该往哪里去[2]402-403?
因此,宗白华一方面对中国音乐精神的丧失感到忧伤,另一方面又因为音乐是“国魂”,是与“生命的意义”和“文化意义”相关的“高等价值”而又对其表同情之感。
六、 结语:“和而不同”
宗白华因为受到德国音乐及德国哲学家的音乐理论的影响,将音乐及其节奏作为艺术的形式结构的重要因素,并以此为据,在对中国艺术进行批评时将音乐或者音乐性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因此,无论是他对中国书画的音乐境界的发现,还是对中国艺术境界典型的舞蹈的推崇,以及对中国音乐及文化的批评,都别开生面。但这只是他对音乐的借用,或者以音乐为批评的方法,并不是他对音乐的专门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他才在《中国古代的音乐寓言与音乐思想》等文中对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进行了研究。在这些观点中,他除了在谈到自己的音乐思想时引入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使其观点更为丰富之外,并无大的变化。
不过,这其中的变化也并非不重要,那就是宗白华在解释中国音乐精神的发生和衍变时减弱了之前所具有的宇宙论的神秘化色彩,而更多地从唯物主义角度来解释。他依然认为中国的音乐精神就在于对自然节律的感知与广泛应用,“中国人早就把律,度,量,衡结合,从时间性的音律来规定空间性的度量,又从音律来测量气候,把音律和时间中的历集合起来”[23]427。在谈到中国的这种音乐观念的产生原因时,他也更多地从当时的自然环境和劳动条件出发作出解释。
希腊半岛上城邦人民的意识更着重城市生活里的秩序与组织,中国的广大平原的农业社会却以天地四时为主要环境,人们的生产劳动是和天地四时的节奏相适应。古人曾说,“同动谓之静”,这就是说,流动中有秩序,音乐里有建筑,动中有静。
希腊从梭龙到柏拉图都曾替城邦立法,着重在齐同划一,中国哲学家却认为“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记》)。更倾向着“和而不同”,气象宏廓,这就是更倾向“乐”的和谐与节奏[23]432-433。
当然,宗白华对音乐的重视也依然没有发生改变。他认为“哲学的智慧”就是音乐的智慧与数理的智慧的结合,数学和音乐就是西方和中国古代哲学的“灵魂”,所以,如同对于西洋哲学来说,必须理解数学和几何学,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则必须理解中国的音乐的思想。但是,他认为无论是中国的哲学还是西洋的哲学,都未能处理好音乐和数理的关系问题,所以导致各自的发展都不尽如人意:
中国在哲学发展里曾经丧失了数学智慧与音乐智慧的结合,堕入庸俗。西方在毕达哥拉斯以后割裂了数学智慧与音乐智慧。数学孕育了自然科学,音乐独立发展为近代交响乐与歌剧,资产阶级的文化显得支离破碎。社会主义将为中国创造数学智慧与音乐智慧的新综合,替人类建立幸福丰饶的生活和真正的文化[23]433。
宗白华在60年代的希望不可谓不美好,只是在今天似乎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这样美好的愿望都还未曾实现,所以,也只能期待在未来某个时刻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