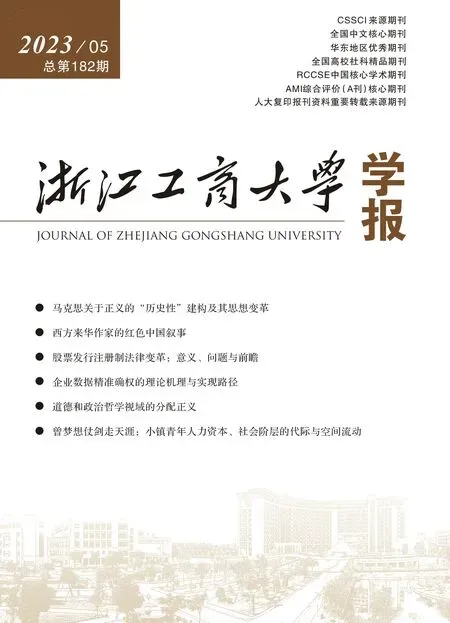西方来华作家的红色中国叙事
——以斯诺、史沫特莱与白英为中心
汪云霞,戴思钰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一、 引 言
二战前后,不少西方记者和作家来华,他们奔赴延安地区考察,撰写关于红色中国的新闻报导、报告文学、日记游记等作品。其中,三位作家尤为值得关注,即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与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这三位作家居华时间长、中国经历丰富,且他们访问延安的时间恰处于二战前后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透过其代表作品《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1937)、《中国的战歌》(BattleHymnofChina,1943)和《红色中国之旅》(JourneytoRedChina,1947),我们可以管窥二战时期西方来华作家如何叙述红色中国并建构中国形象。
斯诺是第一个深入延安地区采访并向世界报道红色中国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他于1928年来华,在华游历十四载,并于1936年6月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下大量通讯报道。他创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在海内外引发强烈反响,使当时“基本上不了解情况的外界大为惊讶”[1]。《太平洋事务》书评指出:“斯诺此书的出版,不仅开创了他记者生涯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人们认识当今中国的新纪元。”[2]
在斯诺造访延安后数月即1937年1月,“杰出的记者、女性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3]史沫特莱受邀到陕北苏区考察。她于1928年来华,在华生活十二载,创作了《中国人民的命运》(ChineseDestinies,1933)、《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RedArmyMarches,1934)、《中国在反攻》(ChinaFightsBack,1938)等多部中国题材作品,对宣传红色中国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国的战歌》被誉为二战期间最好的报告文学之一,着重刻画了她在延安的经历。吉原夏纪认为,史沫特莱的中国书写与美国的东方主义话语形成断裂,她没有试图替他者说话,也没有企图利用他们的声音达到自己的目的[4]。弗洛伦斯·豪(Florence Howe)强调,史沫特莱的延安书写是在为中国的普通百姓发声,“她把自己的艺术献给那些通常没有时间、空间和工具发声的人”[5]。
距斯诺与史沫特莱访问延安近十年之后,白英乃奔赴延安。他于1941年来华,先后在重庆英国大使馆、战时复旦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工作。1946年6月,白英前往延安和张家口访问,历时两个多月。以在华生活经历为基础,他创作了大量中国题材的小说、诗歌、日记、游记等作品,并编译出版多部中国文学选集。其中,《永恒的中国》(ForeverChina,1945)和《觉醒的中国》(ChinaAwake,1947)以日记体形式展示了二战时期中国人尤其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与精神面貌,及时地向西方社会传递战时中国声音。《红色中国之旅》是白英记录延安和张家口之行的游记作品,同日记《觉醒的中国》部分内容有交叉重合之处。有评论指出,白英是“美的永恒力量的信徒”,其“文学才华与高产的作品震惊了文学界”[6]。
从斯诺、史沫特莱到白英,三者承前启后、相互补充,共同塑造了二战时期西方观察者眼中的红色中国形象。三位作家有着不同的跨文化经历和中国想象,他们相继跨越太平洋来到中国,深入延安地区。他们观看延安风景,采访中共领袖,与延安知识分子及民众交流对话。对这三位作家而言,延安不只是充满异域色彩的地理名词,还是中国情感和中国记忆的存储之地,更是一个承担着表达审美诉求、历史思考和中西跨文化交流愿望等多重功能的象征符号。
二、 “神圣的风景”:红色中国景观建构
米切尔(W.J.T.Mitchell)曾提出“神圣的风景”的概念,“神圣的风景,就是这个词让人想起了天堂,想起那流着奶与蜜之地,赐福之岛,应许之地,极乐净土”[7]。人类对“神圣的风景”的想象与建构,不仅是现实需要,也是终极的精神追求。在三位作家笔下,延安堪称“神圣的风景”,它是超越战时中国现实苦难的精神家园和理想世界。他们以延安为中心,从自然景观、社会景观与文化景观来建构红色中国形象。
在斯诺与史沫特莱的笔下,红色中国的自然景观带有超现实主义的奇幻色彩。“景色无穷无尽,奇异而诡谲……那些神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有时甚至吓人的景象,好像一个由疯狂之神塑造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一个奇异的带有超现实主义美感的世界。”[8]27“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却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9]61斯诺与史沫特莱惊叹于延安共产党人领导的红色革命,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正是基于此种信念,他们洞悉延安风景的神圣性,认为其“像毕加索一样触目”,并试图揭示延安军民是何以在“疯狂之神塑造的世界”中坚韧生存的。延安奇美的风景与延安军民的崇高性相得益彰,“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9]作者序。在斯诺看来,延安军民面对“有时甚至吓人的景象”,显得乐观昂扬,充满激情。总体来看,在斯诺与史沫特莱的延安书写中,纯粹自然景观的描写篇幅并不算多。其风景描写往往是大而化之的粗线条勾勒,鲜少细腻描摹、工笔勾画。
相较而言,白英更加钟情于延安自然景观的细致摹写和诗性表达。其《红色中国之旅》中的延安“是个可以歇脚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深深地扎下根来,静静注视着四季更替”[10]10。在白英的体验中,延安是诗意的桃花源,又恍若一曲扎根于土地的民间歌谣。他凭借诗人的敏感,将嗅觉、视觉、触觉多角度联动,以饱满的色调与有温度的笔触,富有神韵地传递出延安诗化的自然风光。“这里有薄荷、欧芹、芬芳的花朵与清新的山间空气。……这是一种独属于中国北方的柔和、甜美、灼热的空气。”[10]7“山谷是黄土的色彩;远远望去,田野里的茅屋、石桥、商店、偶尔被灌木覆盖的小山全是淡淡的黄色。”[10]7此类诗化描写在《红色中国之旅》中比比皆是,构成了其红色中国叙事的重要内容。
白英着重营造了延安山谷这一神圣化的诗歌意象。其诗作《朗姆谷与延安谷》将延安山谷与阿拉伯朗姆山谷相比较,强调二者都具备古老的神性,是被众神眷顾的神圣空间。在诗中,抒情主人公与毛泽东三次会面的经历被置于黄色幽谷的远景中。“山谷静静悄悄,寂寞无声/只有一条涓涓细流,那就是延河/慢慢淌过这片黄沙/流过黄色的山间,这里有黑墨般的阴影/那是我们生活过的窑洞:空气是纯洁的/夏日的窑洞就像每片湖泊、每条溪流般清凉。”[11]全诗以毛泽东为中心,将领袖人物的内在精神外化为自然景观的诗性表达,延安山谷即诗人寻找的延安精神的“客观对应物”。在《红色中国之旅》的“风景”一章中,白英以白描与写意交融的方式,细致描摹延安的如画景观。“这是梵·高想要画的风景——灰尘像火焰般升起。生活还在继续,一辆装着大轮子的农家小推车沿河而下,几家铺子开着,人们在街上慢慢走着,踢起明亮的黄色尘土。”[10]64白英笔下的延安风景具有印象主义绘画的视觉冲击力。他将人与物共同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实现人景合一。“在这些松软的黄土山谷里,所有的土地都必须被翻耕。……你会看到一个人在远处的高地上干活,或一辆小车从你身边隆隆驶过,但车夫却藏在一捆捆干草里。在这些晴朗炎热的夏日里,延安的四周弥漫着一种奇异的空旷。”[10]77这个场景犹如一幅正在徐徐展开的画卷,视点不断移动,由黄土山谷转到远处的高地,再拉回到近景即身边的小车与农夫,进而由实到虚,从描摹到写意,延安的日常景观由此获得诗性凝视。
“景观具有多个面相,构成一种记忆形式,这种形式储存着人类于时间延展中在地球上活动的历史。”[12]景观与人类社会活动密不可分,社会成为风景叙事的重要维度。从社会景观来看,三位作家均感受到红色中国之“新”这一突出特质。延安作为“神圣的风景”,不仅在于黄土地和黄色幽谷承载的坚韧和希望,还在于延安青年身上所具有的蓬勃热情与生命力。斯诺讶异于红军的低龄化,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9]44。史沫特莱关注到小战士“多数是二十岁刚刚出头,但在红军中已经有了四五年或五六年的军龄”[13]110,并引用常听到的一位外国记者对小战士的评价来说,他们“不是中国人,而是新人”[13]129。白英聚焦于青年学生,看到“他们在古老的土地上建造了一些在中国全新的东西”[10]11。他甚至在《红色中国之旅》中专辟一章“学生”,强调延安“是个正在形成的世界,也是个你能感到它将会持久的世界”[10]135。三位作家对红色中国之“新”的观察超越了东方主义式的猎奇,呈现出一种对全新历史主体的期待和对中国未来的希望。
三位作家对社会景观的观察各有侧重。斯诺聚焦于革命青年、军队将领与政治领袖的书写。他指出,《红星照耀中国》中记录的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9]作者序。斯诺以单个革命人物的成长史为线索,串联起红色革命发展史,从而勾勒气势恢宏的革命景观。史沫特莱更重视对战区医院与延安伤兵的关照,呼吁外界对延安的医疗救助,“我们的第一篇战争报道将会是关于中国伤兵处境的。我会努力争取外国医疗资源救助与志愿工作的救护者”[13]132。在《中国的战歌》中,史沫特莱浓墨重彩地描摹了野战医院、医学图书室、卫生学校等,并通过对伤兵个体的采访,收集了大量伤员事迹,借此传递战时中国的医疗状况。白英《红色中国之旅》“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延安人民的——将军、地主、学生、游击队员、教授、商人、政府官员——这些人已与日军作战了八年,依然还在为解放事业而斗争”[10]1-2。相比较而言,斯诺和史沫特莱描绘的社会景观具有宏大的史诗效果,而白英散点透视的描写方法则仿佛抒情绝句或小令,有利于捕捉宏大历史罅隙中的吉光片羽。
除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之外,三位作家还注重文化景观的体察。延安古老神秘的土地孕育了辛勤耕作的人民和他们淳朴美好的歌声。史沫特莱曾以“凄凉的歌声”为题回忆其在中国村落听到的民谣,“那音乐就像中国一样古老,我并不理解歌词,但是我能感觉到,在这些古老民谣的内部编织着人们的希望和忧伤”[13]261。民歌民谣是中国古老民族的文化积淀,也是红色中国的重要文化景观。白英说,“在陕北,每个人,无一例外,都会唱这些民歌。……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比我们从书上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因为民歌是“未经研究的、自然的、从大地和他们的生活中迸发出来的”[10]156。白英指出,他在采访延安艺术家时,他们无不提到民歌的重要性。诗人柯仲平当面为他吟唱家乡民歌,“他吟唱着,好像在那个时刻悲伤侵袭了他,他用一种尖利的调子,双眼紧闭,表情极度痛苦。……他用低沉的嗓音唱得很慢,但在最后一行,以一种深重的悲伤的腔调吟唱出来:‘太阳下山,花儿褪色/蜜蜂飞来品尝花朵/蜜蜂飞来,花儿褪色/哥哥呀看着妹妹敞开的坟墓。’”[10]113在白英看来,这首民歌既“简单”又“繁复”,很好地诠释了爱与悲伤的主题。它不仅与中国《诗经》传统相联,还可以在世界文学中找到相似处,“就像哈姆雷特曾在奥菲利娅墓前吟唱一样,英语诗歌中也有这样的典型表达”[10]113。
白英对延安文化景观着墨甚多,远超斯诺与史沫特莱。他不仅详细记录了与毛泽东的三次见面,还积极建构毛泽东作为诗人的形象,叙述其诗歌创作轶事、手稿《风尘集》,并译介毛泽东《七律·长征》《沁园春·雪》等多首诗词作品。他还塑造了延安多位艺术家形象,包括“吟唱诗人”柯仲平、“中国的惠特曼”艾青、“鲁迅之后最好的小说家”丁玲、“圣歌演奏者”冼星海等。他还亲临延安文艺表演的历史现场,欣赏秧歌剧《兄妹开荒》、京剧《三打祝家庄》、交响乐《黄河大合唱》,并关注中国书法、版画、木刻艺术等。除此之外,他还介绍了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大学,着重谈及图书馆的英文藏书情况。白英试图通过展示延安的文化景观,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红色中国及其文化特质。
概而言之,斯诺、史沫特莱和白英从自然景观、社会景观与文化景观三个维度来建构中国形象。三者相比,斯诺和史沫特莱偏重社会景观的透视,白英则注重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塑造。“风景”恰能呈现意义的缝隙:借助延安风景叙事,三位作家共同建构了西方观察者眼中的红色中国形象。
三、 历史、记忆与诗性:红色中国叙事方式
“风景一般都被视为环境因素,属于空间范畴,但是在叙事活动中,风景被时间化了。”[14]三位作家的红色中国叙事具有强烈的时间性特质。在建构红色中国景观过程中,他们对延安这一地理空间的描绘逐渐让位于时间的叙述:立足于“现在时”的空间描绘,将“现在”视为包容过去和未来的存在标识。从现实的空间场域回溯红色中国的革命历史,考察延安的“历史性”意义,想象红色中国“未来时”的全新景观。斯诺曾详细记录了自己从北平到延安的复杂内心感受:“我之所以激动,是因为展现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与中世纪富丽堂皇的紫禁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在空间上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探险:我要到‘红色中国’去。”[8]9斯诺等人意识到,这条从北平到延安的道路,不仅连接了过去与现在,更串联了过去与未来,暗含了新旧中国命运不断更替的过程。三位作家聚焦于延安这一特定场域,在“历史—现在—未来”的多重维度中相互穿梭与转化,从而将个体与历史、记忆与情感、真实与想象加以融合,构成其红色中国叙事的张力和诗性。
斯诺的红色中国书写采用了典型的历史叙事方式。他以个体人物为中心,梳理其人生轨迹与革命经历,以小见大,以点带面,通过个人成长史勾连起红色中国革命历史的基本轮廓。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曾将历史叙述分为“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等类型[15]。斯诺的红色中国叙事表现出高度的历史敏感性和惊人的洞察力。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他对中国革命的现状与未来做出了许多精妙的分析与预判,并对开篇提出的“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做出了明确回应,具有“论证模式”与“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的叙述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斯诺的历史叙事并非沿着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线性延展,而是采用了现在与过去两大时空并置的模式,历史与现实互相穿插,不断进行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与腾挪。在探寻中国革命历史轨迹时,斯诺谈及自己目睹汉代皇城遗址所深受的震撼:“我无法向你形容那一时刻在我感情上引起的奇怪冲击——由于我们所在的环境而这么强烈,又是这么奇怪地富有预兆性质,这么奇怪地超脱于我、超脱于中国的那部分变化无穷的历史。”[9]26他将延安现代革命战士与二千多年前强盛的汉王朝士兵并置,历史与现实深度交融,在抚今追昔中思考人类历史的宏大命题。斯诺擅长以革命者个人成长史推进对中国革命史的叙述。如以专章讲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中共领导人的个人故事,这些“故事”文本镶嵌在宏大历史主线之上,彼此构成互文性关系。诸多互文性文本的插入,既拓展了历史叙事的深度,也增加了叙事张力。另外,斯诺非常注重历史叙事的客观性。他以理性手段克制作者权威,努力摈弃先入为主的看法与私人化叙述声音,还借助直接引语来增强叙事的客观性和非个人化效果。斯诺强调:“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9]作者序
如果说斯诺的红色中国书写强调历史叙述的客观性,那么史沫特莱则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渗透了强烈的个人情感和记忆,可称之为记忆叙事方式。“历史和记忆交互影响,历史(客观发生的历史)塑造着记忆,记忆重构着历史(事后阐释的历史)。”[16]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既是中国革命与战争的历史,也是作者个人的成长史。全书以时间为线索,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了1928—1941年作者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虽然史沫特莱同斯诺一样重视个人生命史与中国革命史的镜像式呈现,但较之斯诺不同的是,她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渗透了较强的个人主观情感和漫长琐细的记忆性话语。或者说,《中国的战歌》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它既见证了中国的“战歌”,也表现了传记作者自我成长和蜕变之歌。史沫特莱在自我与中国、历史与记忆之间建构了时空双重距离,由此使笔下的延安化为一种“模糊远景”。这个“模糊远景”既折射出作家回忆的景深,也隐藏着其情感的分量。史沫特莱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她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并把自己在中国度过的岁月称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13]365。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指出:“故乡之成为‘故乡’,亦必须透露出似近实远、既亲且疏的浪漫想像魅力。当作家津津乐道家乡可歌可记的大事时,其所贯注的不只是念兹在兹的写实心愿,也更是一种偷天换日式的‘异乡’情调。”[17]由此可见,对于作家而言,即便是真正的故乡,在时空阻隔后,也会产生审美距离甚至“异乡”情调,而只能趋于浪漫化的想象。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隔着时空的双重滤镜回望延安,其记忆化叙事不免涂抹上抒情和想象的光晕和气息。
白英的红色中国书写可称为诗性叙事方式。如前所述,白英《红色中国之旅》与此前出版的日记《觉醒的中国》有相互重叠的内容。《红色中国之旅》沿袭了日记体的散文化和诗性特征。它没有斯诺和史沫特莱作品恢宏的史诗结构,并不以历史线性逻辑展开叙述,而是以横断面方式散点透视延安的“神圣的风景”。其文本结构宛如“花瓣”,以延安为花蕊,而描写延安的风景、人物、学校、艺术等章节如同一片片花瓣,向心而聚,各章看似随意而松散,但彼此有着内在关联,形成统一的有机体,共同折射出延安的诗性景观。白英以二战刚结束的特殊历史时期为背景,巧妙地将延安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相融合。虽然笔墨所到之处难免触及中共政治和眼前一触即发的国共内战,但他更热衷于表现的是革命与战争之外的延安日常生活图景。例如,同毛泽东、朱德等人一起用餐,在剧院看戏,与艾青、丁玲等人谈论诗与生活,他从战争的残酷性之外看到了日常生活恒常的诗性。其笔下的延安“没有坟墓,没有死者”,甚至连死亡也带有诗意的色彩。“在山脚下,在嶙峋的岩壁间,在最贫瘠与未开垦之地,有一些铅灰色的尖尖的小基座。有时上面刻着一颗红星,更多的时候,除了一个死去农民的名字,什么也没有。”[10]77-78白英的延安书写能够将“现实、象征、玄学”融为一体,其诗性叙事中蕴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关切与探寻。《红色中国之旅》有大量关于爱与和平的诗性呼唤,还有对中国未来的知性思考。“这场战争或许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这场社会革命仍将席卷中国……长远来看胜利依然为中国人民准备着,他们自从1911年以来遭受的剧烈痛苦从未被遗忘。”[10]198
虽然将三位作家的书写方式分别界定为历史叙事、记忆叙事和诗性叙事,但不可否认,这几种方式并非相互排斥、非此即彼。它们在三位作家的文本中其实相互交叉与融合,只是表现程度各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斯诺长于述史,其叙事具有历史客观性和纵深度;史沫特莱长于抒情,其叙事饱含主观热情和个人记忆色彩;白英则擅长意象营造,注重将内在情思与客观对应物相融合,建构富有诗性空间的历史情境。
四、 历史语境、文化立场与中国经历
三位作家来华的不同时代语境潜在地制约着其对红色中国的观察与叙述,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与中国经历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中国叙事方式。
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R. Isaacs)曾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以时间为序分为崇敬时期(18世纪)、蔑视时期(1840—1905)、仁慈时期(1905—1937)、钦佩时期(1937—1944)、幻灭时期(1944—1949)与敌视时期(1949— )[18]。斯诺与史沫特莱分别于1936年和1937年先后来到延安。按照伊萨克斯的界定,此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恰处于仁慈时期到钦佩时期的转捩点,西方开始试图了解中国,对红色中国充满好奇。此阶段正是世界局势大转变的开端,中国即将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也即将开启。此外,当时“正值边界战斗和区域内各种政治活动的间歇,共产党领导人有充裕的时间同他们满怀期待的来访者进行交谈”[19]45。斯诺与史沫特莱作为来华的美国新闻记者,在华生活多年,具有对历史事件敏锐的洞察力和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追求精神。他们关注到延安军民“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9]作者序,都对苏维埃、红色中国等理论问题做了深入思考和阐发,具有较强的政论色彩,较好地奠定了二战时期红色中国形象海外传播的舆论基础。
白英前往延安的时间较前两者晚了近十年。彼时延安已进入西方的传播视野之中,不再是神秘朦胧的未知之地。因此,白英的红色中国书写更加重视文化层面的交流与传播,希望在中西文化之间搭建交流互通的桥梁,增进彼此的理解与认同。在国统区生活四五年的白英,抱着对中国真诚的热爱奔赴延安考察,其延安之行“主要的兴趣点在于看看能做些什么来阻止内战的爆发”[10]1。由于历史处境的不同,其关注的焦点已由抗日战争转向国共内战。此一时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已趋于幻灭时期。白英努力向西方展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试图改变西方人对红色中国的刻板印象。白英身为英国传记作家、诗人和学者,一直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充满丰富想象。因此,他注重从自然景观、社会景观和文化景观等多重维度建构红色中国形象,其诗性化的叙事方式一定程度上与来华记者的新闻报道形成互补,有利于推动红色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
三位作家独特的文化立场与中国经验也对其红色中国书写产生了较大影响。斯诺虽接受了西方正统教育,但十分厌恶金钱至上的美国社会。他认为,在全美弥漫的社会文化风气中,存在“有毒的,危险的东西”[20]。他自知无力改变,故远走他乡。在进入延安以前,斯诺遍访中国主要城市,见证了中国的严酷现实。肯尼斯·休梅克(Kenneth Shewmaker)认为“这是一次形成自己性格的经历”[19]41。长时间在华生活的经历奠定了斯诺理解红色中国的可能。他曾自陈,“如果我不是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而是刚刚由我的祖国来到中国而访问红区,则我的感受也许会打折扣,不但如此,反倒可能认为共产党人是美国原则的敌对者”[21]。在华期间,他在中国作家的协助下编译了《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了鲁迅、柔石、茅盾等左翼作家的短篇小说。在此过程中,斯诺对现代中国有了更深的体认,对延安的红色革命有了独特判断,在《红星照耀中国》开篇之初即提出了诸多颇有深度的有关红色革命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政治问题,并表现出富有见地的理解和思考。
史沫特莱是一位来自美国社会底层的作家。她幼年居于科罗拉多棚户区,生活贫困,少女时期,其骨子里便萌生强烈的阶级仇恨与反抗意识。她于1928年来华,先后抵达北京、上海等地,对国民党统治下中国人生活的苦难与沉重感同身受。她与鲁迅、茅盾交往的经历也加深了其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并最终在延安找到了精神归属。延安人民的生活唤醒了其在科罗拉多矿场棚户区的童年记忆,作为一个“被强烈的激情所支配的人”,史沫特莱“比中共的党员更激进和更富于理想主义”[19]246。她深入抗战前线,不断增进对红色中国的情感认同,并将之化为《中国的战歌》中热烈激扬的文字和对延安真诚的颂歌。她对中国延安怀有炽烈的情感,在离开中国后仍时时挂念,故以自传体回忆录的形式书写隔着遥远时空距离的中国,既寄托着对中国的深切情感,也是其自我人生的审视与反思。
白英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结。早在幼年时期,他便幻想身边有一条象征中国形象的青龙伴其成长,每当困难来临,他都可以召唤青龙化险为夷。他以此为据创作了长篇史诗《西尔维娅的冒险,丹麦和中国的王后》(TheAdventuresofSylvia,QueenoftheDenmarkandChina),诗歌驰骋着白英的中国想象,为其中国情缘奠定了基础。1941年,白英来华,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并与梁宗岱、闻一多、卞之琳等知识分子过从甚密。这构成了他观察和理解中国的重要基础,也使其对战争语境下的中国社会有了更广泛的了解。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大学学术氛围之中,白英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热爱远在斯诺与史沫特莱之上,因而《红色中国之旅》更加凸显延安的文艺实践活动、延安文人及其艺术创作。他还大力介绍和翻译柯仲平、艾青、田间、何其芳等延安诗人的作品,有力推动了延安文艺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三位作家在二战前后相继来到中国。虽然三者个人身份、文化立场有所不同,在华生活经历也各有差异,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是知华友华的国际人士,都对中国抱着理解之同情。他们以各自的话语方式,积极传递红色中国声音、建构红色中国形象。
五、 结 语
基于价值取向的不同,叙事者的观察视角可分为“隔离观察”与“楔入观察”。其中,楔入观察者可以自由选择一套价值系统进行观察;而隔离观察者则不具备这种评价自由,“他采用的价值系统不能过于离谱,至少要能为作者所处的时代与文化所接受”[22]。同期中国作家的延安书写受限于政治因素,多采用“隔离观察”视角。而斯诺、史沫特莱与白英却因域外作家的身份,得以对红色中国进行“楔入观察”,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他们并非远距离地遥望中国,概念化地演绎中国,而是亲临中国历史现场,深入红色中国中心,观察、谛听和体验延安生活的多重面相。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斯诺、史沫特莱与白英外,以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来华作家也创作了诸多有关红色中国的优秀作品。他们广泛介绍红色中国情况,澄清西方社会对延安的妖魔化传闻,加深了西方世界对红色中国的理解与认同。例如,冈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红色中国的挑战》(TheChallengeofRedChina,1945)立足于抗日战争后期延安人民斗争的经历,从人口、经济、军队等多角度入手对比重庆与延安,并高度称许延安的民主制度建设。斯坦因采取较为客观的叙事立场,相对疏离延安革命话语,主张要在“强烈而惊奇的印象后面去探取真理”[23]。其作品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信度,但在文学性和美学价值上却相对缺乏。另外,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的《中国震撼世界》(ChinaShakestheWorld,1949)出版后也获得了较大反响,堪与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媲美。它以解放战争语境下的延安农村为聚焦点,以农民为切入口,描摹出战争参与者的切身体会,以小见大地思考中国革命的未来。贝尔登注重以丰富的细节和大量的数据客观呈现事实,“虽折服于中国人民的力量,但较少情感投射,他态度超然,是独立于中国故事之外的观察者”[24]。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大多数成员短期观光式的体验不同,斯诺、史沫特莱与白英有着更长久的旅居中国的经验,写作风格更鲜明,对问题的剖析更有深度,因而也更具代表性。从时间线索上看,斯诺与史沫特莱率先打破新闻封锁,后者向西方记者广发邀请,由此促成了西方记者访问延安的热潮;而白英则于内战前夕访问延安,其作品衔接了二战期间和之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西方作家对于红色中国的观察与书写。相较于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和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等作品,白英的《红色中国之旅》观察视角更加多元,它在社会景观之外,还着重凸显了延安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从斯诺到史沫特莱再到白英,三位作家由西方到东方,他们不仅突破了空间的限制,还超越了国族以及文化的藩篱,以其广阔的胸襟、超迈的精神和超凡的胆识观察和书写中国,由此创造了红色中国叙事的经典之作。这些诞生于二战前后的经典作品今天依然值得重视,它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历史与面向未来,启发我们思考在当前历史形势下,如何增进文明互鉴与跨文化交流,推进东西方之间的理解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