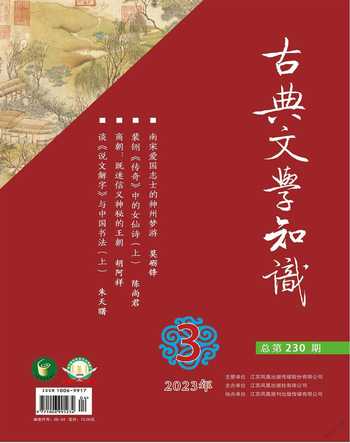《诗经》中的赠玉与爱情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较早反映当时的玉文化,为后来有关玉文化传统的叙述开启了先河。《诗经》中玉文化的政治内涵已被多次探讨,而玉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尚未得到还原,尤其是私人赠玉行为背后隐秘的爱情观念值得发掘。
我们发现在《诗经》中有关“私人赠玉”的诗歌共有以下四首:
《国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毛传》云:“琼,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瑶,美石。”“玖,玉黑色。”《诗集传》释:“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辞,如《静女》之类。”目前学界多沿用朱子之说,将此诗释为男女相好而相互赠答。
《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毛传》云:“杂佩者,珩、璜、琚、瑀、冲牙之类。”《诗集传》释:“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历来诗说虽对其主旨的诠释互有参差,但对夫妻关系是明确的。
《王风·丘中有麻》:“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此处“玖”应与《木瓜》的“玖”同义,也是玉名。
《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历来对“彤管”的解释“未详何物”,或为女史的笔管,或为与茎类植物相关。据后文女子再赠荑草,男子反应更为热烈惊喜,前者应不再是草类。而“有炜”之貌也绝非植物和笔类所有,由此推测“彤管”应为管状玉器。
可见,私人赠玉多见于民间,发生于男女之间的偶遇幽会,事由以求爱为主。通过分析私人赠玉的行为特点,结合玉的特质,我们可以发现玉与人类情感表达的天然亲和性,从而探究这一物媒深处积淀着的情爱观念及其存在的关联。
择偶标准的兼容
选择对象,外形条件往往是首要标准。《诗经》时期的择偶审美也多重“色”的现象,许多诗歌都十分注重男女身形的具体描绘。但从赠玉行为我们可以发现其审美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并驱性,做到了外形美与品行美的兼容。
《说文解字·释玉》云:“玉,石之美者。”周人对玉,首先是爱其形美。陈性在《玉纪》中概括玉的特点为“体如凝脂,精光内蕴,质厚温润,脉理坚密,声音洪亮”,可见玉具有与人相似的审美效应。因此《诗经》中诗人们常以玉来形容自己的求爱对象,“有女如玉”(《召南·野有死麕》)是山野之民以玉的通体晶莹、质地细腻来形容自己的心爱之人,“彼其之子,美如玉”(《魏风·汾沮洳》)是采桑女对思慕之人相貌的赞美。而这里的“美如玉”已不限于外表之美,更是指对方“殊异乎公族”的人品。“将翱将翔,佩玉将将”(《郑风·有女同车》)既是衬托孟姜的美貌,更是赞她美好的品德。可以清楚看出,玉中还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审美内涵,这是当时人们更为推崇的。因此赠玉予人既是对对方玉貌的肯定,也是对对方玉德的体认。以玉相授,不仅是为了增进感情,更是通过所赠之玉将自己的精神世界传递给对方,含蓄地表达自己“有玉”。
婚姻审美的预设
《诗经》时代的爱情,尽管处处显露着远古年代的古朴痕迹, 但它早已不再是人类童年时期纯生理的本能需求了。它还注重情爱的长期发展,对情爱的归宿—婚姻生活有了初步的预演,并将这种婚姻设想寄于玉中。
玉形美质坚、机理清澈,逾千年而不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与美好感情的内在特质相契合。人们将自我情感投射于玉中,以玉作为美满婚姻的依托,倾注了风情男女纯洁恒久、坦诚深挚的情感预期。这也形成了周人初步的婚姻审美观,即建立在双方真正的爱情基础之上,有子孙为依托,婚后家庭和睦幸福,双方能够同心同德、白头相守。人将其情移玉,再以玉赠人,玉的精神与人的情感相结合将馈赠双方联系在一起,玉成为牵系两情的定情纽带与情感见证。他们将彼此的婚姻蓝图注入玉佩之中,以赠玉的形式缔结婚姻关系。
情爱巫术的渗透
叶舒宪指出:“最初,玉中潜含的‘德’并非伦理道德之德,而是神圣生命力崇拜之德,即与‘精’或‘灵’同义,相当于人类学所说的‘马那’或‘灵力’。”(叶舒宪《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因此最初原始先民崇玉,并非玉被赋予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内涵,而是认为玉具有超自然的神力与灵力。从馈赠玉石的行为我们可以发现先民对玉原始的物灵观念及这种特殊观念在情爱意识中的渗透。
原始社会的先民认为万物皆有灵,对神灵的崇拜主宰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他们认为玉是集山川之精华汇集而成,有通天之灵气,“玉璧、玉琮、玉璜、玉龙正是作为中华先民首选的通天、升天顶级灵物而走上历史舞台”(杨伯达《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上》)。而玉也因其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成为情爱关系中的巫术物媒。《诗经》中赠玉诗篇都隐约彰显了这种巫术心理:《木瓜》中男子多次赠玉以加强关系的意图;《丘中有麻》中女子特意“冀其有佩玖以赠己”;《静女》中玉管是首份贈礼。这些都说明当时人们对玉有着非同寻常的珍爱之情,而玉本被视为灵性之物,是人们的护身符,具有异常的灵力。于是借助玉的灵力流入婚俗,赠玉成为加强和稳固情爱关系的巫术手段。人们将贴身佩玉赠予对方,是希望能通过相互接触的感应魔力,使双方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能长久保持联系,以期永以为好。
礼乐约束下的相对自由
由于当时礼法的阶级性及上古遗风的留存,民间婚嫁的观念意识并未因为经济形态的迭变而骤然消失,而是不断地积极渗透,融入新的文化形态中,仍影响着先民的深层心理。在经历过几百年“厚别致远”的婚姻后,男子不禁发出疑问:“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取妻,必宋之子?”(《陈风·衡门》)可见在民间男女心中,身份地位的分庭抗礼并没有真心实意的两情相悦重要,表现了当时民间自主自由的婚恋意识,“两姓”关系回归到“两性”关系的爱情本身意义。通过赠玉诗歌中部分言语暗示,我们也可以发现赠玉的男女往往不是通过父母同意、媒人介绍的私相授受。它们还将“闺房燕妮之情谊”直接载于篇章,静女故意藏而不见的撩拨、士子留恋枕衾贪睡的慵懒。这些由衷的自我情感表达,完全没有把“情”强附“礼”的外衣,与“礼”的“非受币,不交不亲”形成鲜明对比,再次印证了赠玉双方情感的诚挚与关系的纯粹。
不过,它们同样传递出这样一条信息:“情”之“乐”必须以“礼”的控制为前提,需达到真正的“礼乐合一”。所以《静女》中少女才会俟于城隅、避而不见,直至情郎出现方敢缓缓现身;《木瓜》中他们用象征性物件寄寓情谊,将热烈的爱意用含蓄的方式来表达;《丘中有麻》中女子才会多次催促男子能赠玉给自己,以正式确立情侣关系。这都说明他们的“情爱”仍受制于社会文化语境的潜在规约,最终都需“反纳于礼”。赠玉代表的是婚娶之聘、纳征之礼,玉的道德因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礼的传达,这在《女曰鸡鸣》篇表现得尤为明显。诗中夫妇在房中雅乐之余,也能乐而有节、爱而适度,各自做好分内要务:丈夫勤奋劳事、亲贤乐善;妻子勉夫以勤、助成其德。可见,他们虽对情爱有坦然的心态,有放纵原始情欲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仍是需要归结于礼的,是礼乐制度下的相对自由。这种礼制承认男女之情的天然本性,否定情欲声色的过分放纵,认为情爱必须受到礼节理性的规约。其最终目的是希望将男女两性关系纳入一个正常的轨道,从而正夫妇以成人伦。这也表明当时的民间情爱观已受到正统婚恋观念的冲击,过渡至民主性与封建性的双重形态。
《诗经》时代赠玉行为已经走进民间,成为风情男女示爱结情的普遍方式。温润、坚贞、永恒的特质是玉之风骨的折射,潜移默化地浸染着人们的情感认知和爱情审美,同时人们也在用自己充沛的情感、真挚的爱意不断丰富玉的内涵。他们真诚大方地表达自己的情与爱,张扬自己的个性与欲望,还具备初步的现代婚恋意识。这些意识最终也凝结成先民对情爱问题认识的价值内核,对后世的情爱观念及爱情书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桃夭
桃之夭夭①,灼灼②其华。
之子于归③,宜其室家④。
桃之夭夭,有蕡(fén)其实⑤。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zhēn)⑥。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小桃长得真姣好,红红的花儿多光耀。
这姑娘要出嫁了,家庭的生活定美好。
小桃长得真姣好,红白的桃儿多肥饱。
这姑娘要出嫁了,家庭的生活定美好。
小桃长得真姣好,绿绿的叶儿多秀茂。
这姑娘要出嫁了,家人的生活定美好。
——凤凰出版社《诗经全译》
【注释】
①朱熹:“夭夭,少好之貌。” ② 陳奂:“《广雅》:‘灼灼,明也。’《玉篇》:‘灼灼,华盛貌。’盛与明同义。” ③朱熹:“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妇人谓嫁曰归。”
④马瑞辰:“宜与仪通。《尔雅》:‘仪,善也。’”朱熹:“室谓夫妇所居,家谓一门之内。”
⑤于省吾《双剑誃诗经新证》:“蕡、坟、颁与贲古通。……颁、贲并应读作斑。……然则有贲其实,即有斑其实。桃实将熟,红白相间,其实斑然。” ⑥毛亨:“蓁蓁,至盛貌。”陈奂:“《广雅》:‘蓁蓁,茂也。’”
陈馨怡 扬州大学文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