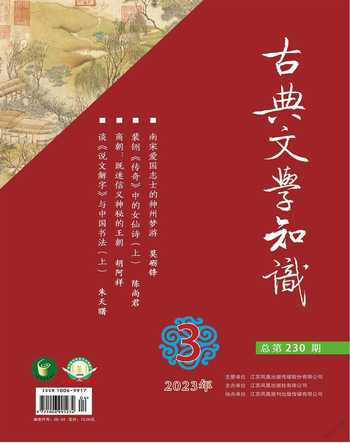说书大师施耐庵与同时空的共鸣者
袁世硕 孙琳


《水浒传》现存最早刊本署“钱塘施耐庵的(dí)本,罗贯中编次”,或“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如实表明小说前大半部分是整合施耐庵演说的话本编次而成,这一部分叙写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等人的人生转折经历,保持了施耐庵说书口语叙事特色,最明显的是在叙事行文中频频插入说书人的话语,也多保持了宋代社会人生实相,鲜活生动,以及自然流淌出来颇为明显官逼民反的倾向性。
由宋入元的说书大师
小说第八回叙述林冲遭高俅陷害,刺配沧州的一段情节,有三处叙述人的插话:一是“原来宋时的公人都叫端公”;二是“原来宋时,但是犯人徒流迁徙的,都脸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唤作‘打金印’”;三是“这座猛恶林子,有名唤做‘野猪林’,此是东京去沧州路上第一个险峻去处。宋时,这座林子内,但有些冤仇的,使用些钱与公人,带到这里,不知结果了多少好汉在此处!”
第二十二回叙宋江怒杀阎婆惜,县府捉拿,宋江躲进自家的地窨子,有段解释性的插话:“且说宋江他是个庄农之家,如何有这地窨子?原來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往来,却做家私在屋。宋时多有这般算的。”
以上情节多提及“宋时”,带有较明显的说话人口吻,说明这些情节都是源自“施耐庵的本”,施耐庵应当是由宋入元的著名说书大师。
《水浒传》基本上是整合施耐庵的本作成的前七十回,从京中禁军教头王进为免遭主管官僚高俅的迫害出走开头,鲁智深是为救助遭到供应官家肉食的郑屠欺凌的卖艺女子金翠莲,三拳失手打死“镇关西”,受到官府追捕,被迫出家做和尚避难的。禁军教头林冲是为防护妻子不受欺辱,得罪高衙内,遭到高俅陷害追杀,濒临死地,无奈投奔梁山的。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事,由家仇诛奸,杀嫂祭兄,斗杀西门庆犯罪,到仗义助友夺回快活林,遭到地方武官张都监陷害,必置之于死地,情不可遏,暴力犯禁,遂“血溅鸳鸯楼”。做郓城县押司的宋江明知晁盖等人劫夺地方高官梁中书送往京都高官蔡京的生日贺礼财宝是“罪灭九族的勾当”,却通信放走“智取生辰纲”的主犯,自己因此被阎婆惜要挟不得已杀人,也沦为官府追捕的逃犯。打劫官僚的财宝,本是主动暴力犯罪,在《宣和遗事》里只是一件历史琐事,而在小说中却增加了事发前“吴学究说三阮撞筹”,对穷苦民众真实生活和心理着意书写,将官员之恶由政治权力的随意滥施,扩展到经济财富的过度占有,故称作“不义之财”,依《孟子》“行而宜之谓之义”的观念,就把打劫官员的巨大财物,赋予了合乎情理的正义性,也就扩大了宋江知法犯法私放“犯了弥天大罪”的晁盖等人的社会价值。由此,叙宋江逃避官府追捕和被判罪两度流徙中发生的故事,一方面是受到社会多类人物间接的爱戴,一方面是屡遭官僚中人的陷害,自然而迂回地酿出宋江浔阳江头“醉”题反诗,形成朝内外官僚勾结制造的所谓“谋反”要案,引出“梁山泊英雄劫法场”大规模的抗法,“宋江智取无为军”对助恶的官僚中人过度残忍的血腥报复,以及李逵要“杀去东京,夺了大宋皇帝的鸟位”的悖伦话,都无疑宣泄出编创者对封建官僚的愤恨心情。
《水浒传》这部分由“智取生辰纲”引出宋江流徙江湖,将多方好汉聚集到宋江的故事中,形成梁山聚义的基本规模。这在宋末元初人“钞撮旧集而成”的《宣和遗事》里,有“杨志筹押花石纲阻雪违限”“杨志途贫卖刀杀人刺配卫州”“石碣村晁盖伙劫生辰纲”“宋江通信晁盖等逃脱”“宋江杀阎婆惜题诗于壁”“宋江得天书有三十六将姓名”“宋江三十六将共反”,连续几节所叙,“遗事”与小说所叙情节大体一致,差异是除掉叙事文的简括,没有鲜活的细节,也没有宋江潜遁青州清风寨和刺配江州的苦难遭遇,“宋江三十六将共反”便没有了现实人生的来龙去脉。
《宣和遗事》节录稗史小说成书,文体不一,研究者发现数本,为之校订。书中叙徽宗宿李师师家故事,类似话本,当据话本节录。叙晁盖伙劫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事,更无疑是节录小说话本,阎婆惜事或有所改编,不能确认即为据《水浒传》采录之施耐庵“的本”,《水浒传》特别是说书大师之“的本”,意味着当时流传的还有别本。或者说在南宋末,如龚开《宋江三十六赞并序》所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士大夫亦不见黜”。“街谈巷语”自然主要是指市井瓦舍的讲说,“士大夫亦不见黜”也自然是指士人的稗史笔记。《宣和遗事》可谓兼容并包,所以前后文体不一,意旨亦有士论与“民情”的差异。就其书内容来看,题名《宣和遗事》,旨在揭露宋徽宗之昏庸荒淫,蔡京、童贯等媚主误国,这是偏安东南一隅的士人心中历史遗恨,节录话本中宋江聚义始末,只是作为那个朝代“遗事”中的插曲,没有关注到社会状况与舆情。
邓牧《伯牙琴》之思想共鸣
与施耐庵大约同时的同城人邓牧的相关政论,与其说话文本的官逼民反基本思想倾向及其“乱由上作”的基本精神息息相通,甚为吻合。邓牧(1247—1306),钱塘人,亲身经历了由宋入元时元兵侵袭掠夺之难,自称“三教外人”“大涤隐人”等,抗节不仕,隐居大涤山中。经时事巨变,他的某些思想从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一般文士的遗民心态,作政论文完全无所顾忌,不单对元统治者表示不满,还振聋发聩地提出对君主制度的讨伐,激烈抨击当时社会至上至尊的帝王,称:“彼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治久安,得乎?”(邓牧《伯牙琴·君道》)揭露统治机构:“小大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数万;小者虽无禄养,则亦并缘为食,以代其耕,数十农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于其间,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岂可得也!”“夫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竭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邓牧《伯牙琴·吏道》)
邓牧揭露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即如三百多年后黄宗羲改题《原君》文中所说:“君为天下之大害”“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后两句引自《周易·系辞》,意谓随意占有财富便是启人为盗,精致美容便教人淫乐,个中就蕴含必招动乱的意思。《吏道篇》揭露大小官吏压迫剥削人民,“夫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直接道出了人民怒怨,起来抗争暴乱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其抨击的对象不再只是“暴君”“赃官污吏”,而是帝王和官吏压迫剥削罪恶的本性,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社会伦理的价值观,所以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被视为“异端”。邓牧从政治经济的实处,揭示君主专制社会的本质为社会动乱之源,具有中国中世纪人道主义启蒙精神,由之也就可以站在历史维度上理解《水浒传》的意旨表达,特别是整合其中的“施耐庵的本”的社会实相的现实主义书写和塑造人物性格的文学特色。
袁世硕 山东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
孙琳 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