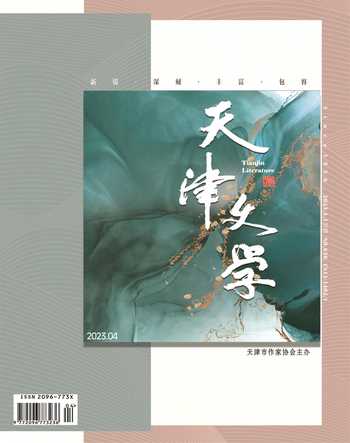从长安出发·甘南行记
总想从长安出发,沿着张骞、玄奘等先贤的足迹,用自己的脚步丈量那满载辉煌的甘南大地,以致敬岁月里的孤勇者。一路走来,歪歪斜斜的履痕,印满生命里不寻常的邂逅。
从人类诞生初始,人们一代代直立着、孤独地不断前行着,离生命原质的土壤越来越远,于是窝穴变成了房子,群落变成了城市,火把演化成诱人的霓虹。大自然是我们最先也是最终的归宿之地。每每回到浮华、喧嚣的城市,穿行在弥漫着躁动气息的大街小巷,我又总会听到甘南那撩魂拨魄的召唤。
为什么“甘南”总让我挥之不去?为什么我的内心总是充满纠结充满矛盾?究竟是什么让我魂牵梦绕、心驰神往,为之欢笑、为之哭泣、为之忧伤、为之痴情、为之忘怀?
——题记
一
火车从关中平原驶出,过秦岭,频频在隧道里穿梭,一路渭水相伴,与我的家乡陕南地貌类似。只是流经陕南的汉水清澈如明镜,而渭水浊黄似泥浆。想起唐代诗人贾岛的两句诗:“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从诗句中可以揣度,那时,即便是秋天,渭水水位也是很高的,水流量更不会小,不然无从得来“秋风吹渭水”的意境。但如今,我们只能看到空旷的河床,仿佛一位有着无限往事却什么也记不起来的临终老人。
陡然一片绿洲,树木葱茏,花草明媚,便到了甘肃最为富庶的天水地区,天水不同陕南的温婉沉静,也有别于陕北的粗犷豪放,独具韵味。关于天水命名有两种说法,都跟汉武帝有关:一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上)曰:“五城相连,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故在汉武帝元鼎三年,改为天水郡。二是源于“天河注水”的美丽传说:相传秦末汉初,邽县遭逢大旱,民不聊生,突然一天夜里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干涸的土地上裂出一条大缝,天上河水倾泻而下注入缝中,形成了“天水湖”。后来这个传说被汉武帝知道了,他就在元鼎三年下令把新设的郡建在邽县北城的湖边,命名“天水郡”,天水便从此得名。
在中国,但凡名山大川,定有名寺,麦积山也不例外。因其形似麦捆堆积起来的巨型麦垛,若鹤立鸡群般屹立于陇南大地上,宛如接引仙人登天的阶梯,又如玉帝在人间的都城,故后秦皇帝姚兴命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此主持凿山修建千崖万像,后转崖为寺,历经千年风雨,乃成秦州胜景。
这个用泥和棉花、头发、蛋清雕塑的石窟高挂在半天半地的山腰间。如此规模宏大的崖阁、摩窟、摩崖龛、山楼、走廊,都是凌空凿建于几十米高的悬崖峭壁上。从远处眺望,异峰突起众峰环,有睥睨万物,舍我其谁之气概。周围层峦叠嶂,云海泛波,依鳞次栉比的佛龛而建的栈道蜿蜒曲折,恰逢雨天,雾霭朦胧,忽隐忽现,宛若游龙,又如玉带般缠绕在山腰,如梦似幻。有人说,它是佛从遥远的西域走向中原时留在秦川大地的一个巨大脚印,是佛的遗迹,是时间、心灵和手艺的遗址。
二
车行景移,山上的植被渐渐由灌木变为草丛,由深深密密的草变为疏疏淡淡的草。车出天水,进通渭,很快就到了兰州。为了赶路,我们没在兰州做过多停留,直接前往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的刘家峡。抵达刘家峡库区时,已近黄昏,太阳在西边高悬,挥洒最后的辉煌。水库碧水万顷,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嵌于赤红的山间。曲折的公路一直沿水库绕行,让我们有机会见证这高原明珠的全貌。
刘家峡地处黄河上游,含沙量很高的支流还没有在此汇入,黄河饱含了高原清澈纯净的雪水穿过千岩壁立的深邃峡谷,在这里成就了万马奔腾般的倾泻,直到汇入水库归于平静,宛如处子卧享群山的怀抱。
曾经读到一段文字:“禹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海。”后来才知道这里的河特指的就是黄河,而“积石”就是炳灵寺石窟所在的积石山。说的是大禹治理黄河,从积石山这一段开始疏浚,经过河南洛阳的龙门,最后流入渤海湾。而地处“积石”附近的刘家峡,正是大禹导河的开端。奇的是,所谓天下黄河向东流,偏偏大禹劈开的刘家峡这一段,却由于地势的原因,转头向西流去,其下又劈开盐锅峡、八盘峡这几个关隘,过五关斩六将才一路向东汇入海,刻下了中华地质、地理史上不朽的一刀。
历史的烽烟随着黄河的滚滚涛声流走了许多辉煌往事。当年,禹王在刘家峡劈开的锋利如刀削般的巨石坚壁,经受了寒冰利水冲刷千百年,依然锐利如初。到20世纪70年代,他的后裔们又在他劈开的三道峡谷上筑起了一座伟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可以想见,在如此坚硬的石山石岭中劈开三道峡谷,其工程何等浩大艰巨,这就不仅仅是神话传说,而是现实中的惊人力作。
夕阳渐渐钻入云中,在天空铺开大片绫罗的地毯,迎接夜的天神下凡。
水库在落日的映照下变幻出千般姿态,一切语言的描写似乎多余,此刻只待大自然随类赋彩。“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此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要去甘南,就是为了那诗和远方!
三
山水之美,古来共谈。
康熙十九年,陇西秀才王荷泽到炳灵寺游玩,写下了名篇《灵岩寺记》:“突兀险仄,总不可名。而漓水之七星岩,大轮之罗汉峰,与湘楚之浯溪,姑苏之虎丘,据余所见,咸皆不屈,而苍莽则番境也。”以盛赞炳灵山水风光,另有一番西部审美意象。
炳灵寺石窟的造像始于西秦,那一尊尊面目清秀的佛像和大大小小的供养人,明确地提示着繁忙的古丝绸之路年代。从地理坐标来看,炳灵寺石窟是古丝绸之路的要津,前秦乞伏氏在此修建的“黄河第一桥”,使得这里一跃成为古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后历经风雨,桥自然是踪迹全无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但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他用信仰哺育着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先辈,为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们保佑祈福。遥想当年,车水马龙,隋炀帝走过,文成公主走过,玄奘走过,进入吐蕃和西域的无数边塞诗人也走过,而络绎不绝的商人更是鱼贯而行。
炳灵寺是藏语“十万佛州”的译音,这是多么漂亮的名字。十万佛居住的地方,一定不是一座寺院,不是一座院子,而是佛的村庄,佛去佛来,在天上人间往返。
由无数大大小小的石窟组成的炳灵寺,分布在大寺沟两岸的红砂岩上,挤挤挨挨的石窟里有很多眉目慈善、衣袂飘飘的佛端坐其中。像凡尘的房舍,像佛的村庄,就算十万佛都居住在这里,也不会拥挤,依然宁静。在原始社会,凡尘之人也住在洞穴里,也是这样栖居在石崖之上。可见天上人间,总有相通的地方。
我不是个真正的佛门弟子,并不能真实领会奥义晦涩的佛理,因缘际会近年来与佛家三宝略微地亲近了些。当面对这无数的佛,我此时好像有无可名状的静谧滋生,自己仿佛穿越到了千年前,我在洞窟内虔诚地看着工匠雕琢他心中佛国他乡的神话故事。
微风轻拂石林,我们走出石窟。仰望姊妹峰与河对岸的万笏朝天群峰,山对着山,崖对着崖,山高可倚天,面前滔滔黄河水,滚滚向东流去。
回望炳灵寺,遥想那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古人,他们袭着一身风尘拖着疲乏身体路过这佛境时,在这些石窟中礼佛,思考着何谓万法皆空。佛曰放下,唯有放下才能脱离六道轮回的苦厄,此间一切已与前人毫无瓜葛,去者已去,唯有这些大大小小的佛窟成为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穿越着岁月的沙盘,默然凝视着大千世界。
信徒们跪拜完毕,从泥土中爬起来,掸去身上的浮尘,头也不回踏上数千公里的远行之路,也许几十年都不会回到家乡,只有佛的信念还在梦中萦绕。
远行,伴随着驼铃声声,马蹄嘚嘚。直到穷尽岁月的余生,方知芸芸众生里的繁,苍凉大地中的小,百里红尘内的孤独。
四
一座以大夏河命名的城市,安详如生命的渡口。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声,仿佛在耳畔萦绕。我自纷繁都市走来,沐浴在大夏河睿智的灵境里。桑烟袅袅,哗哗夏河水伴着拉卜楞寺的真经在耳边流淌。我绕着这城,这寺,如绕佛塔,如绕佛身。隐秘的真言从心头涌起,穿山渡水,穿云裂月而来。
空中,浮动的雪花伸手可触,吉祥的经幡与风儿耳语,佛陀的光芒把慈爱洒满苍穹。地上,院墙巍巍挺立,垒起佛音阵阵。白土垣稳稳扎根,串起经文声声。古树翻墙而出,诉说悠远的繁盛。石板平整延伸,铺就转经的平坦。
红衣僧侣随处可见,或结伴而行,或围坐闲谈,或独坐沉思。还有随处可见的年少的僧人背负书卷米粮行装,穿街过市,嬉戏打闹,举动与高校的学生并无两样。他们穿着僧袍相互追逐,矫健如豹。擦肩回眸时,双眼明亮如星,笑意闪闪发亮。一位年纪幼小的僧人,离群蹲在院墙一角,低头咬牙沉思,双眉紧锁心事;又不时抬头看看来来往往的人群,茫然寻找什么。这身影和眼神更是令人内心柔软起来。
无人、寂静,伴着他们的是一方院墙。独坐、静候,直至天色昏暗。
大夏河在拉卜楞寺前蜿蜒流淌了三百余年。晨钟暮鼓,一代一代的僧人诵经声,持咒声,汇入了流水之中,凝聚成不朽的真言。这河亦如恒河,见证着无数高僧大德的自我砥砺和证悟之路。
出院落,爬上对面的凤山,俯瞰拉卜楞寺,金光闪耀,气势恢宏。龙山脚下,有一处白色房屋,一红衣喇嘛手持念珠,步履悠然。夹杂在风雪中的诵经声,转经声,声声虔诚,仿佛雄鹰从高空飞过,带着风声。
藏民也是这里最重要的风景。长长的辫子、黝黑的皮肤、深邃的眼窝、高挺的鼻梁、鲜艳的服饰。在雪地里、甬路间、殿堂边,总有他们虔诚祈祷的身影,渲染着佛境神圣的氛围。人们把虔诚转进了经筒,将希望留在了心中。还有一众在积雪中匍匐前行的善良灵魂,一步一长头,五体投地,将内心对佛法、神灵的虔诚全投到那一丝不苟的跪拜中去。
证悟的人,睁眼望去,这烟火迷离的人间,不过是一场盛大的孤独,充斥着虚妄的狂欢。爱与恨两两相望,美与丑并道而驰。我们用尽一生气力将自己从人世剥离出来,又再融入进去,如此才完整无憾。
此情此景,万转思绪渐渐清晰起来:藏民们苦苦追寻的,就在他们追寻的路上,就在他们心中。可是,本来通往本心宽阔而直接的路,被尘世间的杂念和欲望引得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辨认。
僧侣也罢,藏民也罢,生于斯,长于斯,一切自然天成。对于看客,处处是风景。于他们而言,皆是生活。
五
别了拉卜楞寺,继续西行数十里,桑科草原近在眼前。
这是个令人心胸开阔得望不到尽头的高山草原。路边一处湖畔,云悠悠,草萋萋,水映群山,在这里天高却不云淡,云朵都是浓浓厚厚地飘荡在湛蓝洁净的天际之上,大得似乎都可以随手扯下披在肩上。我们顾不上高原反应,在草原上尽情跳跃、欢笑,平日里的斯文和矜持都一扫干净。可俯身低首间,耳边仿佛又听到了格萨尔王的战马在桑科草原上啾啾嘶鸣,眼前仿佛又看到了格萨尔王在桑科草原的远山上矫健驰骋。
目的地是迭部县,而桑科草原距离迭部还有二百余公里,一路海拔基本都在三千米以上。时已不早,牧民开始驱赶牛羊归巢,袅袅炊烟召唤着离家晚归的人们。为了不走夜路,我们一路飞驰。
六
扎尕那不是寺庙,但始终保持着一颗普度众生的心。
用再多的语言都无法修饰走进扎尕那时内心的震撼。在秀峰环拱之北,在牧歌漫洼之上,巍峨恢宏的光盖山石峰嶙峋峭拔地插入天穹,突兀地打断了人间生活的绵续,决绝地隔离了尘世流音华韶的干扰,无私地安放着众生漂泊的灵魂。
挺拔的云杉一层层沿着山脚极富层次地向上延伸,或许是生命畏惧神灵的威严,快到山顶时,就只剩下白色的岩石。大神涅甘达娃就住在那里,在顶峰铺开了银白色的双翼。既然是神的栖息之地,则无须以什么固定的形象出现,或者以任何一种形象出现都是那样顺理成章。
山脚下,鳞次栉比的藏寨被对面山谷豁口穿透出的几抹金色霞光拂过。房前、屋顶、村前、村后被早起村民点燃的缕缕桑烟与和煦灿烂的霞光一抹,顿时变得缠绵悱恻,似梦似幻。
梯田层层叠叠,嘛呢经幡迎风猎猎,寺庙白塔在这飘飘欲仙、如泣如诉的桑烟缥缈中朦胧似雾,若隐若现。成群的牦牛绵羊,在田间地头悠闲地觅食吃草,还有那悠远的鸡鸣狗吠划破天地的岑寂,在村庄上空荡漾。眼前的一切,让每个置身现场的人有种时空穿越之感。这祥和的画面,虔诚的信仰,无不展露着这片被誉为现世桃花源的隐逸旷美。
扎尕那的天空是湛蓝的,蓝得让到过这里的人重新理解蓝色的定义。扎尕那的天气更是无比随性的,转瞬之间的风起云涌,幻化无穷,巨峰在瞬息万变中时隐时现,使得烟云与山在这里恒久地缠绵。
一场急雪突袭,让嬉游的云烟瞬间就消逝得无影无踪。雪霁过处,一座直插云天的山峰进入视野,这座神山耸立在皑皑白雪之上、蓝天之下,山巅皓白如银,闪着奇异的寒光。在众山环抱中,这座擎天拄地的高峰就像一位冷峻威严的白发君主,他傲然挺立,昂首向天,在光芒的洗礼中接受众臣的朝拜。
他肯定知道,尘世间又有一群身份复杂的人来到这里了;但他也早已习惯,所以直到我们住进了山脚下的藏族民宿,他依旧冷冷地矗坐。
我想,这次的到来,恐怕又要在魔幻和现实之间徘徊了。
当晚霞余晖普照大地的时候,在湛蓝的天幕下,反射出一条金色的光带。苍穹间剑气飞舞,劈开山巅的一角,一层层,一缕缕,一道道,在山腰雪雾间与藏寨炊烟映衬下变幻出瑰丽的神秘景象,透露出莫测的古老玄机。
恍惚间,我听到一种声音,一种让心灵得到抚慰从而归于宁静和肃穆的声音。是风的微歌?水的细语?还是色彩的吟唱?光的竖琴?抑或是由这一切天籁合成的自然之圣乐?这声音来自烟云迷漫的远方,来自重门掩闭一般的山峦沟壑。我茫然四顾,却又凝神倾听。我被这安宁祥和的氛围笼罩着,犹如沐浴着清风和阳光,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幸福和感动。
我仿佛看见,在那高远深邃的天空里,在那飘逸的云雾中,飞翔着无数快乐的神灵,是他们御龙而行,在浩瀚的苍穹里牧歌。这样纤尘不染的天,这样纯净无瑕的云,这样潺湲清澈的溪水,这样直插云天的山峰和宁静的村落,不正是神灵们居住的地方吗?
扎尕那是心和灵魂的居所。扎尕那的人们朴实勤劳,与世无争,没有太多欲望,平平淡淡地生活着,这就是生活的最好状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不同的时节,重复着昨天的故事,相同的环境下,重复着昨天的自己。质朴的人民,重复着上一辈人的足迹,将自己最优良的传统一直延续下去,将扎尕那的神秘,神山的祝福,自己的故事一直流传下去。
扎尕那的自然美是缄默的,但这种美建构了一个开放、大气而智性的高塔,我们须仰视才得以窥见。再回首,扎尕那云霭迷离,峰峦叠翠,锁住了那条幽深的秘境,也关闭了那个蕴藏了无限寓意的神性所在。
猛然又想起徐志摩的诗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扪心自问,我带走了什么?我在那神性的所在留下了什么?
我只知道,扎尕那以及扎尕那的众多生灵,值得我在灵魂深处日日面对,阅读并思考。
后记
走进甘南,顿时就会感受到这片精神高地充满了诱惑,一旦掀起它面纱的一角,就会让人九死不悔地投入它的怀抱,就会本能地流泻出潮涌般的激情,虔诚地向着博大圣洁的皇天后土顶礼膜拜。
甘南,是英雄的土地,是睿智的灵境。那里曾上演了无数的悲欢离合,凝聚了无数的梦想;那优渥的土地,埋藏着最伟大的英雄的尸骨,也埋藏着最温柔的爱情和浪漫;那众多的寺庙、佛窟,是多少美好的化身;那西去的商队,东来的驼铃编织成了文化融汇的七彩丝带。
当我仰望着甘南的那些文化、自然遗存时,一切喧哗与骚动,一切纷争与困扰,一切争夺与倾轧,一切欲望与贪婪,一切失落与懊恼,人生的一切一切,包括光荣与梦想,就会在一种灵魂的悸颤中全然消隐无踪,瞬间失色。
当我在甘南之旅中饱览精美绝伦的景致的同时,眼前总会晃动着桑科草原上行走的那些或沉凝或活跃的影子,耳边总是回映着他们吟哦的跨越、踏破幽冥的绝响,也就刻骨铭心地理解了关于创造的价值,关于生命的神圣和尊严。于是我便为之情动,内心深处就不停地咀嚼着挥之不去的一切,试图找出那些先贤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循着前人的履痕以及破译历史奥秘的逶迤足迹,我由长安出发,一路走向了拒绝委顿生命的山地高原,走向了欣然接纳一切的大夏河,走向了诞生英雄、传唱英雄的桑科草原,走进了抚慰灵魂的栖居地扎尕那。于是便捕捉到在中华民族繁衍不息的那束审美冲击波。
我清晰地感觉到,内心那由城市挤压的一个潮湿发霉的角落,正冲着甘南大地敞开,正向着甘南的高原阳光暴晒。晒得我阵阵作痛也兴奋无比,脑海里就不由得涌现出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一支支商旅跋涉于甘南大地,高山、古道上留下串串足迹,声声驼铃打破了一路的寂寥。于是久闭的心界缓缓打开,许多历史中的情景和细节一一重现,甘南之行的点点滴滴,沿途的人与自然、历史便在我的指缝间汩汩流淌。
释一尘,原名刘忠涛,陕西旬阳人,陕西国画院理论家、陕西画院联盟执行秘书长,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现挂职于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长期从事中国画创作与美术史论研究工作。陕西省人文社科类重大学术研究项目——陕西美术考察研究系列丛书·长安风格《唐·王维研究》《北宋·范宽研究》《华山研究》《大写意研究》等书籍执行编著。
责任编辑:王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