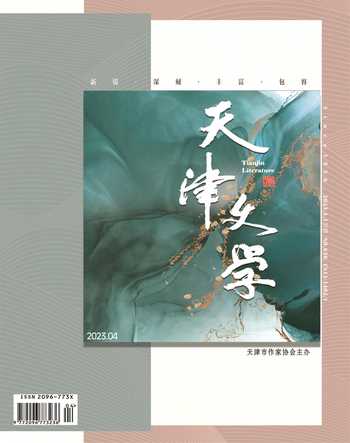写书难,出书更不易
一
从1978年至今,44年当中,我连写带编的书已有一百多本了。这只是如实陈述,丝毫也没有炫耀的意思。记得1958年12月20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读了“孩子的诗”》,其中有两句是:“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郭老当年66岁,比如今的我小16岁。郭老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人,据有关专家粗略估计,他一生写的诗应该有五六千首。他这样调侃自己,表现的是一种谦虚和自信;而我说自己出的书“虽多好的少”,却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不过人的能力有大小,学识有高低,我尽力做了,也就没有完全虚掷光阴。民间有一句鄙薄文人的话,叫“天下文章一大抄”。我想,完全剽窃他人的著作,是一种学术不端的恶行,属品质问题,予以揭露和谴责是应该的。但任何人著书立说,都离不开汲取前行的研究成果,如同想跨越前人,就只能踏在前人的肩上。网上搜索,男子100米短跑世界纪录是9秒58,这世界上能跑出10秒成绩的运动员应该不少,但如想提高到9秒,那就成了奇迹的创造者,虽然差距只有一秒之遥。写文章亦然。我们虽然鼓励在学术领域创新,但我一直认为,一篇文章能有三分新意,就应该得到鼓励,而不能被视为学术垃圾。我是南方人,老了仍乡音未改;当过14年中学教师,至今不会拼音,我仍手握圆珠笔,一笔一画地写字,从未用过电脑。所以,我常常想,像我这样笨拙的人,即使是一个誊抄工,字字抄袭,句句剽窃,要抄出几百上千万字,那也得磨秃无数笔芯,付出几度春秋吧!这就是我说“写书不易”的意思。
二
我在国内的出书经历都是让我难以忘怀。如参与编注1981年版《鲁迅全集》,2005年版《鲁迅全集》,1992年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忝列为2009年出版的《鲁迅大辞典》的编委和主要撰稿人员之一。这部辞典近364万字,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研究鲁迅的必备工具书。2022年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78卷本,是当代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举,我也列名为专家委员会成员和定稿组成员之一。我自知个人渺小如水珠,但不积滴水,就能有浩瀚的江河吗?
还有一些出版社给我带来了受之有愧的荣誉。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聘请我为2005年版《鲁迅全集》编辑修订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林默涵,因病无法做具体工作,实际上的编辑工作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李文兵及其他编辑做的。经作家出版社申报,我写的《搏击暗夜——鲁迅传》获得了两个奖状:一是被评为2016年大众最喜爱的五十种图书之一,二是被评为2016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的三十种图书之一。虽然奖状是颁给作家出版社的,但作为该书的作者,我也与有荣焉。最让我感到温馨的是福建教育出版社。由于我是该社出版的《许寿裳遗稿》主编之一,曾多次到福州定稿,受到了该社的盛情接待,许多美好的记忆都珍藏在心里。福建教育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他们还给我颁发了一张“功勋作者”的奖状。我的名字跟“功勋”二字联系在一起,此生尚属首次,虽然觉得夸张,但仍心存感激。
同样感到幸运的是,凡我或编或写的书,都是应出版社之约,走的正常流程。我没有因为出书对任何社的任何编辑搞过私人公关,我也没有科研经费可以作为个人出书的专用津贴。在出书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不少编辑,他们都成了我的朋友和老师。从这些编辑在审读、校对、画版式直至参与装帧设计的过程,让我懂得了什么叫“为他人作嫁衣”的无私奉献精神,这成了我人生的楷范。
小不痛快的事件发生在跟某编辑的个人之间。这位编辑跟我有过多次合作,仅我应他之约编辑的书籍某一版次印刷总量记得就有20多万册。而最后一次跟他合作时,他职位已有迁升,让助手给我结算编选费时,坚持按电脑显示的汉字数以量计酬,而不按此前的版面字数计酬。当下编选费的标准众所周知,即使去掉标点符号,也省不了多少钱,但却让我想起了鲁迅1934年12月6日致孟十还信中的一段话:“稿子是该论页的,但商人的意见,和我们的不同,他们觉得与萝卜白菜无异,诗的株儿小,该便宜;全篇塞满文字的文章株儿大,不妨贵一点:标点,洋文,等于缚白菜的草,要除掉的。脑子像石头,总是说不通。”这件事后来惊动了出版总署的领导。这位领导跟该社的社长直通电话说:“对于这些老作者,不妨宽厚一点。”后来当然还是按版面字数结清了编选费,不过犹如在墙上钉了一颗小钉子,虽然拔掉了,仍会留下一个小坑。
三
这后记越扯越远,必须“悬崖勒笔”,回到这本《我观现代文坛——陈漱渝近作选》本身。所谓近作,是指我退休之后——主要是近两三年的文章。所谓“选”,当然不是我近作的全部,而是跟书名比较贴切的文章。附录《生有确日,死无定时》一文,是因为表达了我撰写这批近作时的一种真实心态,那就是时不我待,要赶快做!“近作”与“少作”孰优孰劣,这也是一个复杂的创作现象。鲁迅虽不悔其少作,但却把少作比拟为“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集外集·序言》)。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开头就夸奖“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表达了诗人对南北朝时期宫体文学代表人物庾信的评价。不过还有一些作家创作的起点就成了一生的高峰,如:郭沫若的《女神》,曹禺的《雷雨》。鲁迅的“少作”与后期之作如何评价,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谁也不能否定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的艺术价值和时代意义,但也没有人说这部小说的成就能超过他的奠基之作《呐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七年,学术界对鲁迅早期文言论文的评价是有“历史唯心主义”的成分;后来又有学者说这些“少作”如何之高明,反倒是后期杂文出了问题,应该把其中的某些文章从《鲁迅文集》中抽掉。这就是学术界的见仁见智,观点是永远不可能完全统一的。至于我个人的文章,仅从文章学的视域观照,应该是“近作”比“少作”老到一些,这是自己跟自己比,如同“积跬步”往前挪动的蜗牛一样,因为世故日深,顾虑渐多,所以行文远比“少作”谨慎。由于马齿日增,知识面当然也比青年时代略显开阔。至于立场,观点,方法,几十年我自认为没有调整变化,不存在学术转型问题。因此有人夸赞我有学术的一贯性,也有人认为我多俗见,跟不上时代。我在写作方面的追求也是一贯如此,希望自己的文字比纯史料多一点理论,比论文又多一点文采。我是教中学出身,所以按胡适的要求,力求言文一致。自己没弄懂的新潮学说,我从不敢在别人面前卖弄,只讲一些自认为明白的话。知我责我,那是读者的事情。文章公开发表之后,那就基本上跟我脱离干系了。
四
对于出版这部拙作的天津人民出版社,我还是要讲几句掏心掏肺的感激之言。我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在校期间不仅喝了五年的海河水,还曾三下海河修堤筑坝。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的学术发祥地。我也可以说是《天津青年报》《天津晚报》《天津日报》扶植的作者,是这些报纸让年仅十八岁的我将手写字變成了铅字。早在1978年和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我的《鲁迅在北京》和《许广平的一生》这两本小册子,让我在新涉足的鲁迅研究领域站稳了脚跟。前不久一位在出版社的忘年交坦诚地告诉我,他们社当下只对三种书感兴趣:一是文宣读物,有固定销路;二是教辅读物,家长都愿购买,生怕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三是合作出书,因为国家投入了大量科研经费,高教和专门学术机构都能申请到数额不菲的科研费,这笔经费又是专款专用,所以跟出版社出书是双赢之举。然而我退休已久,个体笔耕,哪来的分文补贴?前两类书我又写不出来,所以从不抱出书的奢望,生怕麻烦那些偏爱我的出版社和编辑。当天津人民出版社表示欢迎我编写一本书时,我并不当真,只将在手机上保存的一些近作杂乱无章地发了过去。不久就有一位编辑室主任跟我联系,认真商量书名和选目,这让我在欣喜的同时,又深感愧疚。因为我此前从没有将未经“齐、清、定”的文稿发给出版社,给对方在百忙之中平添许多麻烦,对此我深感自己行为的孟浪。在对天津人民出版社表示感谢之前,需要先诚恳地表示我真心的歉意。
在我撰写这篇后记时,窗外是社区反复响起的喇叭声,身旁是瘫痪四年病妻的呻吟声,楼上是邻居装修的尖厉噪音……在这些声音的包围下,我在斗室灯下勉力写完了这篇后记,以增添生命的定力和活力。今后还能写类似的后记吗?今后还会有出书的机会吗?我不能悲观地说没有,也不能盲目乐观地说有。只能说:祈望会有!祈望能有!因为“生有确日,死无定时”。
陈漱渝,曾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南社及柳亚子研究会顾问、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艾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