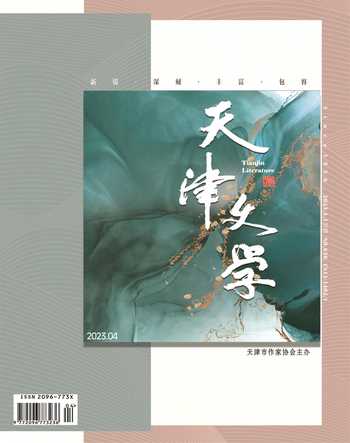鲸
我在网络地图上点选了出发点A和目的地B,AB两地相距四百米。这是我下班回家会走过的一段路。出了地铁站的西南口,从A地走到B地,从东到西,走过三百米,右手边有一棵杨树,树干的侧面看起来像半扇房门那么宽,大概四十厘米的样子。杨树头齐平锯断。
我还记得杨树新锯断的样子,像是一根崭新的、青白色的柱子,有两层楼那么高。
第二年,杨树长出一头新叶,叶片很大,摘下眼镜看去,杨树像粗壮的绿头火柴,半身揳入泥土。
我从来没有在安静的时候听过风从叶片间吹过会发出什么声音。
第三年,仍能看出杨树曾被锯断。
第四年,杨树像以前一样繁茂。我已经忘记杨树以前是什么样子。
再往前走二十米,又有一棵同样粗细的,同一年被锯断的杨树。
两棵杨树的北面,再往北一些,有巨大的、正方体的楼群,下午的阳光常常使楼群反射出金属的光泽。
再往前走三十米,是一个十字路口。汽车的声音长年不停,即使在深夜,没有车辆经过的时候,也有汽车的声音。声音是波,像湖面的水波,或是宇宙里的电磁波,从来不会停止。
站在十字路口东北,视线以一条从东北到西南的斜线穿越路口,抬起头再往前看,能看到一座六层高的建筑。它像一个巨大的、标准的长方体,坐落在马路西侧。
黄昏前的阳光从西方而来,先后穿透了六层建筑西面和东面墙壁的玻璃窗,落在马路东侧的B地。
我从A地走到B地,这段路已经走了八年或者九年或者十年。年的具体数字在记忆和经验里摇动。所有摇动的事物,都像随风摇动的杨树叶子一样没有声音。
这一次从A走到B,并不是下班回家。是一次日常的散步。在两棵杨树北面,巨大的反光建筑里,有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房间,布置成练舞室,我的女儿在里面练习芭蕾。她每周会花两个小时,压腿,跟随音乐做出老师教给她们的动作,听老师高亢的口令,喝水,压腿,看窗外,看同学。这两个小时,对我来说不太漫長,乃至过于短暂,不够用来从容地散步。我像赶场一样把女儿送到练舞室门外,看她放好水杯,走进舞室,像小青蛙一样趴在地板上开始压腿,我就下楼离开。走过舞蹈教室的前台,我会再看一眼监控电视,电视里分出六个俯视镜头,多半是空教室,有一间教室里有孩子正在练习静止的动作,我看不清谁是谁。我出了门,快速地走到A地与B地的中点,在这个位置,往右前方看,正好能看到近处和远处的两棵大杨树。
我计算着时间,估测在赶回舞蹈教室之前,我能走到哪里。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分钟,由于要回来接女儿,能走出去的路程长度还要做一个对折。大概四五十分钟的步行,我并不确定每小时能走多远,但我知道在这样的步行范围内,并没有一个可以称为目的地的所在。
这时是下午两点,太阳尚未降落到足够低的位置,在B地还看不到阳光穿越那座长方体建筑。于是我直行穿过了十字路口,继续往前走。
我每周都可以这样散步,没有目的。或者说,目的不在空间中,目的在时间中,我需要度过两个小时的光阴。有时我用这两个小时在手机上看一会儿电影,我总是没完没了地拖回重放,两个小时只能看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情节;有时两个小时用来清理聊天记录,清理聊天记录的最好方式是彻底清空,但彻底清空后的一段时间,总是会面临不期而遇的工作压力,这件事也不会常做;有时可以听两个小时音乐,音乐偶尔让我感受到世界的质地,但这些感受连再次重复都难以实现,那情境,就像有一个陌生人从空地上走过,他走过之后,我无数次回到那片空地,却再也见不到那个陌生人,但我常常想要回到那片空地上。
古时候,有一个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或许是韩非,韩国的一个王室后裔,韩非像苏格拉底一样,在狱中服毒而亡,比苏格拉底晚生约二百年。
我会在这样的胡思乱想中散步,经过一个多小时,就开始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疾走——去接我的女儿,下课回家。我总是因为走出去太远,而没能在两个小时内回到舞蹈教室。我说的“远”,并不是真的远,只是在徘徊中恰巧走远了,没法准时返回舞蹈教室。
舞蹈教室所在的楼群,构成了一个新建的小区,这个小区由五六个近似正方体的建筑围拢而成,每一个建筑都有大量的空房间。这或许是一座商住两用小区,小区里的地上车位和地下车位都收费不低,停车费按小时来算,每小时收三四块钱。因此住在这个小区里的人,常常把私家车停在小区外面。
几年前,我刚拿到驾照,还不怎么会倒车入库,于是我开着借来的车,在那个空旷的地下停车场练习停车。停车场里常常整排整排地空着,也没有保安。我驾驶着小汽车在地下两层停车场里来来回回地倒车,停车,驶出车位,转向,开雾灯,关雾灯,开雨刷,雨刷变速,关雨刷,倒车,停车,熄火,启动,开远光,关远光,调后视镜,看后视镜,开门下车,看车轮,熄火,关灯,听音乐,开窗,关窗,上坡,刹车,坡起,驶出停车场。
2006年,我做过一个梦,并且记录了下来,记录如下:
漂移的车
2006-09-06
我表弟曾经为一个大公司做间谍。他的任务是窃取对手的商业机密。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窃取对手商业机密的)事。因为他所在的公司在他报到那天就倒闭了。
但是表弟依然要到对手的公司去,因为他的一个朋友被关在那里。关在地下室里。
一天晚上,我的表弟潜入了(对手)公司内部。他走在地下错综复杂的走廊里,毫无头绪,几个小时之后,他看到早已看过多次的门牌。
并且,似乎是某些错觉在作怪,他在来往的工作人员中仿佛看到了他朋友的身影,这样的经历在几个小时内一再重复,直到他确信他没有一个朋友被这家公司扣留。
我的表弟开始迷惑,他想不出自己(起初)潜入这个不可理喻的公司的意图。
于是我表弟离开了,他寻找出口,但情况并不乐观,当他终于走到走廊尽头时,他看到一扇窗,窗外是繁星点点。那时我表弟站在五十层楼的窗口。夜风袭来,表弟低头看了一下,发现他脚下是一个工厂或者是一座废墟,没有灯光,只有各式各样的车纷乱地绕弯狂飙。有小汽车,有卡车,有自行车,还有坦克。
表弟想走回去,找到来时的路,但是一种(即将)陷入迷宫的恐惧使他无法回头。
后来,我的表弟从包里掏出一根有钩子的长绳,他从五十层楼上溜了下来,在下来的过程中,他发现所有的窗户里都开着灯,穿着各种衣服,神态各异的人都在看他。最终,表弟艰难地来到了一楼。于是他陷入了车海,没有一辆车是静止的,表弟找不到走进大楼的门,也找不到走出车海的路径,那些车实际上开得很慢,好像老人散步一样,但是它们总在试图作出漂移动作。
(上文括号内文字是出于工作习惯刚刚添加的,添加后,内容似乎更清晰,但语感不好;此外改了几处“的、地、得”的误用。上文中的人物——我表弟,是一个虚拟形象,他是梦里的第一人称,也就是我。)
2006年做梦的人,并不知道十几年后,他成为他梦中出现过的,一辆近乎荒谬地行驶着的汽车的驾驶员。
当那辆借来的小汽车开到地表,停在地上的某个车位后,我忽然想,为什么不再把车开到地下,这样到时就可以和女儿乘电梯下到这个地下车库,在迷宫里寻找小汽车,再载着她,打开车灯,在空旷又昏暗的地下车库行驶。那里很安静,但和上面一样,路上只能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在想象的声响中,有时还能听到封闭空间内传回刹车的回声。另外,从昏暗阴凉的地下,驶入白亮刺眼的地上空间,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电影《潘神的迷宫》不就是那么开始的吗?
这么一折腾,时间就过去了太久。舞蹈班里的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跟着大人们离开了练舞室。我猜我的女儿并不着急,我看她一点儿也不着急。即使同学们一个个离开教室,她还在更衣间仔细地换着舞蹈鞋,并没有焦虑地向外张望。她知道爸爸经常晚。
三岁时,早上下小雨,她去幼儿园。爸爸早上把她送到幼兒园,看着班主任把她接到怀里,就转身骑车上班去了。她跟着老师进了教室,问老师:“爸爸什么时候来接我?”
老师说:“爸爸买雨伞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接你。”
“一会儿”是什么意思呢?一会儿就是很久的意思。到了中午,爸爸还没回来,她问老师:“爸爸什么时候来接我?”
老师说:“爸爸买到雨伞就回来了。”
买雨伞要去很远的地方,用很长的时间,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些雨伞,爸爸走进那个有雨伞的房子,说:“我要买雨伞。”
黄昏时天晴了,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被大人们接走。幼儿园教室的紫色消毒灯点亮了。老师把她带进办公室。爸爸在老师下班前买雨伞回来了。
爸爸没有给她看新买的雨伞。爸爸也并不知道自己去买了一整天雨伞。
——他们走出舞蹈教室,在回家的路上,女儿讲了这件事。
有几次,他们驾驶借来的车回家;有几次,他们驾驶租来的车回家;有很多次,他们骑自行车回家;有几次,他们步行回家。他们每次都会经过B地对面的建筑。光线从建筑东西两面的窗户中穿过,越过他们的头顶,打在B地旁边的墙壁上。
那道墙大概有四米高。围着一块十几年未曾动工的土地。每年春天,都有人从墙下挖一个通道,钻到那片空地里,种玉米、辣椒、大葱、芸豆、秋葵、向日葵、薯葵,这些人还在空地上搭起窝棚,用砖头和木板摆成桌子和凳子,窝棚外面放置几个大矿泉水桶。
我们在秋天快过完时,也从围墙下钻了进去,走在收获后的土地上,看到了春天劳动的影子。站在空地上,能看到北面舞蹈班所在的大楼,能看到B地对面的大楼,如果楼上有人,他们往这片空地上看,就能看到春天播种和浇水的人,也能看到他们搭起了窝棚,夏天坐在窝棚里。
时间留下想象的痕迹。
两棵杨树北方的一群正方体建筑下面,始终没有足够的车辆填满地下车库。路边换过几次的招牌没有继续换下去。整排的门面房天长地久地挂着最初的招商广告。直到有一天,舞蹈班也退掉了他们租用的练舞室。
有一天,我和女儿再次从地铁站西南口出来,走到A地的时候,我听到大风从我们上空经过,又从远处的树林上空经过。风没有惊动树梢。女儿骑上了自行车,我不知道她是否感觉到快要下雨了。或者她还有什么事儿,她骑上自行车,很快就骑出去很远。
经过这么多年,两棵杨树没有长得更粗,又或者它们已经长了很多,我没有看出来。那是下午晚些的时候,透过B地对面建筑的窗户,橙色的阳光穿过楼内的空间,落在女儿的脸上和她骑的蓝色自行车架上。这让我意识到,这么多年过去了,那里面竟然一直空着。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些房间里有什么。
我们决定进去探索一下。
我们绕着楼转了一圈,所有的大门都上锁了。金属的U形锁上有不规则的锈斑。果然是没有人住过的,至少现在没有人住在里面。我们又绕了一圈,试图找到一扇没有关上的窗户。所有的窗户都关着,没有一块玻璃有裂痕。
再次回到正门前,女儿推了一下门,想试一试能不能推出一道我们可以侧身出入的缝隙。我觉得这个想法有些异想天开,如果能推出一个让人进出的门缝,那锁还有什么用。人似乎总是愿意做这类尝试,有时尝试本身会变成一些有趣的事。我们又退回了B地。从B地往南走,再经过四百米,就能走到我们居住的小区。
回去的路上,我和女儿说:“你猜那栋楼是干什么用的?”
女儿看了我一眼,说:“我知道你又要编故事了。”
我说:“它是用来养鲸鱼的。”
从第一次见到阳光穿透东西两面墙壁的窗户,我就觉得那里面养着一条鲸鱼。一条安静的蓝鲸。
蓝鲸是体型巨大的哺乳动物。它的体长可以超过三十米。当它被饲养在一座建筑里,这座建筑至少要有五十米长。而那栋楼的长度,或许并没有达到五十米。一条蓝鲸被饲养在其中,它没有办法转身,如果它不小心翻一个身,也许整栋楼会因为水的摇晃而崩裂,巨大的水流会从破裂的墙壁间涌出。
为了安全,蓝鲸会安静地在水的空中漂浮,让自己的鼻孔稍稍露出水面。它始终没有用力呼吸,因为呼出太多的空气,它就会下沉,而它并不能有力地摆动尾巴让自己上升,那么做,巨大的水浪会冲破楼房。长久以来,它习惯了轻轻地呼吸,它习惯了忍住因为干燥或寒冷的空气而时常带来的喷嚏。由于不能充分地交换空气,蓝鲸的身体里长久地积存着陈旧的气息,它慢慢地适应了那些陈旧的感受。
蓝鲸并不需要运动,它的能量消耗很少,它当初吃下去的食物,一直在它的胃里。蓝鲸曾经想要消化掉它们,但是它担心那些食物一旦消化掉了,没有人来给它投喂新的,它会饿死。还有一个问题,一旦它把那些食物都消化掉了,就需要排泄,而在这么小的空间里,一旦排泄,水就会变得很脏,变得奇臭无比。蓝鲸担心这样一来,它的一次排泄,会把这一片区域的空气都污染了。而更糟糕的是,它会因为无法忍受脏水,想要逃离,从而破坏掉整个建筑,水会流走。没有了水的浮力,蓝鲸的内脏、肌肉和骨头会被巨大的体重压毁。它会死去。一旦死去,腐烂的过程会十分漫长。
“一间房子里如果非正常死掉一个人,这间房子就会变成凶宅,凶宅没有人想买,这个房子就会贬值。如果一栋楼里死了一条鲸鱼,整栋楼都会卖不出去了。”我说。
“你不是说这个楼已经被蓝鲸毁了吗?”女儿问。
“是啊,楼毁掉了,蓝鲸会死;楼没有毁掉,蓝鲸也有可能死啊。如果楼没有毁,蓝鲸非正常死亡了,这栋楼也会变成凶宅。”
“蓝鲸能活多久?”女儿问。
“我记得和人差不多,人能活多久,蓝鲸就能活多久。”
“这条蓝鲸很有钱,它买下了一栋楼给自己住。一栋楼要多少钱啊?”
“这也不一定,”我说,“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穷鬼,因为有钱的都住在海里,那里多自由。”
当我说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一不小心落入隐喻的陷阱。我讨厌隐喻,讨厌任何形式的隐喻。但是讲述故事的时候,似乎有一个奇怪的表达惯性会把我扯到隐喻中去,这很油滑,就是鲁迅说过的油滑——“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起初,我看到阳光穿过一栋空楼,空楼内部那么大的空间,这让我想到楼体内如果全是空的,如果有一条鲸鱼在里面缓缓地游动,会是一个很让人驻足出神的画面,可我并没有认真想过,那样的生活会让鲸鱼不适。
油滑是创作的大敌,而考虑鲸鱼的生存状态,这难道不是很务实的事吗,怎么会是油滑?没错,鲸鱼的生存是务实,但由此而引出的隐喻感,就显得油滑了。这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这的确是创作的大敌。
鲁迅在“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之后,就在小说《补天》中“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既然明知油滑不好,鲁迅何不把这个小丈夫擦去呢?鲁迅是向来主张下功夫修改作品的。不好的东西,何不擦去?
真实的事,怎么能擦掉?怎么能假装不曾有过?
这的确是一件让人悲伤的事,就像那条鲸鱼要忍着不打喷嚏。
麦尔维尔在《白鲸记》的“语源”一章中引用到:“鲸,更其直接地来自荷兰文和德文的Wallen;古代英语Walw-ian,滚动,打滚的意思。”
鲸非但要狠狠地打喷嚏,鲸还要打滚。就像犀牛会在泥浆里打滚。忍住,它就不再是鲸。因油滑不好而擦掉小丈夫,就不再是鲁迅。
一头鲸——而非一“条”鲸“鱼”——为什么要住在一栋不足五十米长的楼里?
我没有和女儿说这么多。
我仅是每次经过B地对面的楼栋时,时常想象着一头鲸,缓慢移动,或者似乎在缓慢移动,显然,那栋楼里没有什么空间给它移动——这里没有任何隐喻的意思,如果要说隐喻,何不直接说出本体?本体本是乏味的,这才是隐喻令我厌恶的根本——那么,就可以有阳光照在鲸的沉默的身体上,于是在黄昏,经过它的时候,光线不会空洞地穿过两层窗户,鲸的身体会留下巨大的投影。人们也会从四面八方走来,观看这一头巨大的蓝鲸。(我当初这么想,是因为生活中缺少奇观吗?)
我也曾更为现实地想象过,这不可能,怎么可能在一栋楼里养一头鲸呢?找不到合理的理由。那么,就简单地做一个灯光幕墙,甚至只是一个粗劣的投影——从B地的高处发出一束光线,打在建筑的墙壁上。
这过于真实的想象让我感到丧气,因为一旦想象到,一头真实的鲸变成了一面投影,那么更为真实的情境就是,有什么理由在一面墙上投射出一头近乎静止的蓝鲸?就算能投射出来,由于那只是一栋普通的楼房,没有平整的墙壁,没有淡色的墙壁,到处都是反光的玻璃,也没有挂起一面巨大的投影布,楼前还有纷乱的树枝。在那么寒伧的条件下,往墙上投影一头蓝鲸,会是多么破碎和败落的场面。
但是有些想象的画面,一旦出现了,就难以驱散。
我总是在从A地走向B地的时候,在走到第一棵杨树的时候,看到B地对面的楼房,我总是无法克制地看到一头不知种类的、无名的鲸,安静地栖居在那栋并非空洞的,实际上已经有人居住、办公的楼房。
人无法驱赶这些顽固的念头。庄子也曾顽固地想象着,在北方的大海里,有一条巨大的鱼,它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鹏”,飞走了。“鹏”是什么东西呢?“鹏”是一个想象中的动物。它从来没有真实地存在过。
“鹏”在宇宙里飞行。
如今人们读《庄子》,也许想象中的“鹏”,从北冰洋飞出,落到了南极洲。南极洲并不小,但对于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鹏”,或许南北两极的距离有点近,这不免令“鹏”的努力略显失落。那么“鹏”会从海王星飞出,落到太阳上吗?那似乎“鹏”又有点小,路程过于渺茫。又或者,“鹏”不大不小,从海王星飞出,扇动巨大的翅膀,经过远近适中的旅程,落到了太阳上。
看过科普读物的,都知道这个比例差是难以弥合的,从海王星到太阳的巨大的空间,海王星和太阳的巨大的体积差,面对这样的距离和悬殊的比例,“鹏”应该有多大的尺寸才合适呢?如果“鹏”大到可以和太阳匹配,那么海王星,乃至这一路经过的七大行星,恐怕都要被“鹏”扇动双翼飞过时产生的巨大引力波动毁灭。毁灭太阳系所有行星,最终降落在宇宙中甚为微小的太阳之上的“鹏”,也会成为望洋兴叹这个故事的主角。
但即便“鹏”如太阳系那么大,在巨大的银河系中,它也太小。如果它像银河系那么大,在宇宙中,也太小。如果它跨越宇宙如同孩子跨越卧室,这样的想象,则变成了疲惫的、乏味的文字游戏了。
几天前,我读完一篇小说,问它的作者:“你在写这篇小说时,是否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形象?”
他说有,并向我讲述了那个场景的形象。
我当时挺想和他说,我也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形象,我一直想把它写成一篇小说。但我没有和他说这个事。人至少要认真地想过一件事,再和他人讨论吧,有时候。
我曾多次想到这个形象,但我想不到一个能让我接受的理由——在一栋楼里漂浮着一头鲸。
我还能记得它最初怎样进入我的脑海。
起因是我想写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写的是我正身处其中的生活。我想着这些关于写作的事,经过了那栋楼房,日落前,阳光正好穿透那栋尚未竣工的建筑。我看到一头鲸安静地漂浮在楼的体内。透过空洞的尚未安装玻璃的窗口,现出了鲸的局部。
很多年。这是一篇无法完成的小说。虚构让我感到沉重。在另外一些未完成的练笔片段里,我写下的角色身处不同的世界,他们在小说完成之前逐一走向深渊。也可能,这是楼栋中那头鲸的神秘起源。鲸落入虚构的深渊,鲸的影像在我的生活里闪烁。
(完)
后记:并没有“完”。小说写完后,我发给几个人看,有人没有回复,有人回复说有寓意,有人说看不懂,有人试图解读出我要表达什么。作为写作者,我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以编小说为职业的。
你如果注意到我在括号里加入了“在现实生活中”,就不免产生联想:写作这件事,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吗?
当然不是!
如果能分出一个“现实生活”,那就有可能分出一个“不现实生活”,或“虚构生活”,或“虚假生活”,的“想象生活”“幻想生活”“梦幻生活”“理想生活”“超现实生活”“亚现实生活”“现实背面的生活”“真现实生活”或“现实工作”“现实梦境”“现实阅读”以及“超现实工作”“幻想写作”“不可靠的AI”“廉价的手机”“错字”“糖水”……
赵文广,1982年生于辽宁瓦房店,2008年起从事小说编辑工作至今,业余时间创作中短篇小说。作品发表于《福建文学》《黄河文学》《草原》《四川文学》《大益文学》《滇池》《山花》以及《新青年》周刊等,出版有小说集《空中鱼》。曾获滇池文学奖。
责任编辑: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