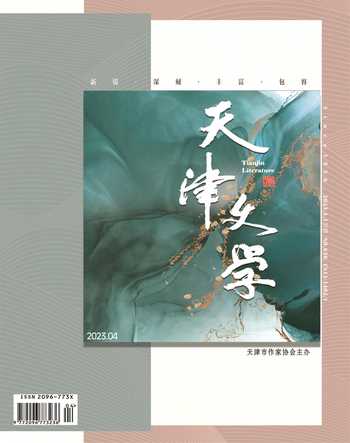快跑啊思甜
1
那一年我十五岁。一到部队连长就带我去炊事班报到。大家见了我没什么好气,上来就问我光板长毛没?说着要扒我裤子,吓得我大叫。
大伙哈哈哈说着怪话,咱是铁道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怎么改幼儿园了?
连长一看这阵势高喊一声“立正——”,奶奶的,老子还没说话你们倒抱怨,师长老战友的孩子敢不收吗?派他去施工班风枪都扛不动,塌方砸死咋办,都给老子看好了,否则有你们好瞧的!
这么一来没人爱搭理我了。其实我很想去施工班,办手续时师长还问,胖子你到了连队会走吗?我说不会,我要做真正的铁道兵战士。没想到还是分到炊事班,真不如走呢。所以每天跟着混,人家也不怎么招呼我,拉粮卸车从不叫我,搞得挺没劲的。
这天我看大伙围着个老乡叽叽喳喳,上前一看是一窝小狗。老乡问我们要不要。班长说部队不许养狗。他话音未落,一只小灰狗“呼”地翻过筐边扑进我怀里,明亮的眼睛盯着我不放。
我犹疑着,班长,昨晚库房又闹狐狸,我亲眼看见叼走一块咸肉,咱得养狗看家护院吧?这句话触动了班长的软肋,最近老闹狐狸,一丢肉施工班就破口大骂。
奶奶的,是狐狸偷的还是你们偷的?班长点点头,就一只啊,你养着,胖子。
先喂米汤再喂剩饭,狗咣啷长大,竖耳朵一身灰,极其聪敏。当时报上常出现“忆苦思甜”字眼,便唤狗为“思甜”。班长夸我名字起得好,胖子你很有板眼呀,要牢记过去的苦,才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小时候……他发现我和思甜都傻愣愣盯着他,话没说完转身走了。思甜在营房长大,对部队气氛情有独钟,比如早上跑操,集合号一吹它就亢奋,围绕我的床低声呼唤,真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按规定炊事班不需要出操,让思甜这么一弄我也只得爬起来,好好好,起来还不行?炊事班就我一人狼狈地跟在队尾,一二一,一二一……思甜怕我掉队,一会儿跑前一会儿断后,好像我是它的狗。
还别说,自打思甜管用以来,狐狸就没再出现。当地山民说这叫一物降一物,防狼靠驴,治狐狸就得用狗。至今我没弄懂为啥狼怕驴,但狐狸怕狗似乎在理,他们说只要闻到狗的气味狐狸就不来了。我把思甜带到库房,让它闻闻咸肉又闻闻被狐狸掏的洞。
都清楚了吧思甜,你守住库房,只要看到狐狸就叫,我非毙了它不可。
说“毙了它”是开句玩笑。炊事班不出操不站岗,连枪都不发,拿什么毙人家?但毙不毙另说,狐狸跑了咸肉保住了是真的。
我自鸣得意,跟班长臭显摆思甜的“丰功伟绩”——说什么来着,狐狸没了吧?
班长面色持重,你这熊孩子啥都不懂,啥也不是,你没看连长一见思甜就拉个脸,躲着他点知道不?
班长这么一说我缓过闷来,当初连长质问过养狗的事,奶奶的,你们还敢养狗?班长说如果再丢肉,施工班要割我屁股。
你让他们立字据不割我屁股,否则就得养狗。
为此连长对思甜鲜有好脸色,那天我正蹲厕所,思甜外面守着,思甜的确很黏人,到哪都跟着我。正赶上连长打此路过,我听他远远地在训思甜,奶奶的,好狗不挡道,给老子滚远点!我怕思甜吃亏没擦就往外跑。可思甜这家伙不是凡狗,见连长就躲,它能闻出连长的味,早蹽了,喊半天才出来。
连长这种态度搞得连里很少有人亲近我。其实他们喜欢思甜,跟它挤眉弄眼,想逗它玩又不敢大逗,做个表情意思意思。我又少不更事,心说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对红尘滚滚毫不在意。比如周六下午组织活动时间,花归花叶归叶,是人就有个群,群主招呼大家坐一块儿聊天,好像还要交什么费,不交就挨批评。我和思甜没群,没人招呼。
有一回搞错了,一个小组长冲我喊,胖子,你怎么瞎溜达,赶快参加组织活动去。
旁边马上有人纠正他,你弄岔了,胖子不是。
不是,真的假的,咱们连还有不是的?
这种事多了,连里新兵都不知道我叫什么,一说就“那个狗的”,差点成“那个狗日的”,我大无所谓,眼不见心不烦,有思甜在,爱特么谁谁。
2
我和思甜常去后山。山前为阳,山后为阴,我们住在山前,南房朝阳。但山里人都知道,山阳石陡土薄,土质干燥不宜耕种。而后山相反,坡缓土厚,湿度容易保持,山区的水井都在后山,戏里说“女人在山阴,战火发山阳”,后山才是栖息之地。往大点讲,农耕文明最早种植的是粟,即小米。小米原产山阴,老祖宗先在后山种粟,然后下山来到平原,种胡人传来的玉米小麦。我和思甜穿过一片谷地,钻进长满各种果树。柿子、核桃、沙果和梨的美味天堂,思甜一会儿在前一会儿断后,又好像我是它的狗。
虽说炊事班不愁吃喝,一天吃五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五钱饿不死炊事员,可你放那么多辣椒干吗?每次炒菜半筐辣椒下去,谁受得了,大葱大蒜还凑合,辣椒根本顶不住,一口也吃不下去。我求他们少放点,人家不屑一顾,说思甜能吃凭啥你不能吃,不吃辣椒算什么铁道兵?当年在大兴安岭修林区铁路,零下四十多度,铁道兵就靠吃辣椒战胜严寒保证施工进度,这才到哪啊,胖子,慢慢学吧。
得,又我不对,老我不对,我就纳闷了,都一帮什么人呐这是,凡事遇到铁道兵全不一样了,生活中的种种极限,吃辣椒根本不算事,恨不得连地心引力能量守恒都通通作废,天兵天将啊?那次十渡二号隧道鼓风机坏了,洞内高温五十二度,没有一人言退,还超额完成任务,这种事比比皆是。再往细说,我亲眼看着五班长把三个生鸡蛋顶对顶摞起来,这是人干的吗,不服你来来?现在流行吉尼斯纪录,铁道兵天天破吉尼斯纪录!
也罢,你们天兵天将我大俗人行了吧?问题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是真吃不饱,老想找东西垫垫。不是吹,我有重大发现,水果跟人差不多,都有早熟者,比如柿子,你慢慢找,众绿之中总有几个黄黄熟透的,不涩且甜。柿子可以充饥,我姥爷当过北洋政府的兵,他说当年打吴佩孚就发柿饼子做军粮。可早熟之果往往在树梢之巅很难够到,就像身处铁道兵艰苦环境发育也快,我光板上的毛日长夜长,都有点扎了。不过采集这种果实我很在行,我体轻如燕,一米五五不到九十斤,能攀至极高处用树枝荡秋千。但上去容易下来难,这就显出思甜的作用,它能于很远处发现山民的身影并迅速预警,给我足够时间撤离。思甜与人的区别是它不假正经,不认为偷水果是坏事,也不告密,我跟思甜“同甘共苦”“坐地分赃”,根本无须解释,偷个水果算啥,又怎么样嘛。
直到那天失手。
那次是摘梨,梨同样有早熟的。我摘的是“京白梨”,顾名思义北京白梨,多汁肉厚非常爽口,可不知何时开始改叫韩国沙梨了,有偷专利的,有偷隔壁老王的,还有偷土特产的?我正在树上饱餐,只听思甜叫我。思甜报警从不汪汪叫,这样会把山民招来。它是吹气,用气压冲两边腮帮子,发“呜呜”声,动静不大穿透力强,我立刻就能听到。待我衣衫不整从树上跃下,“砰”地两脚着地,猛抬头只见一个老汉站在面前,相距不盈两尺。我刚想责备思甜,怎么搞的你,预警晚了?可望着老汉的样子却说不出口。那是张被岁月精雕细刻出无数皱纹的脸,他对我殷殷微笑,皱纹打开时发出“嘎嘎”的响声。我情不自禁用心灵为这张面孔拍照,这种照片是任何相机无法获取的。多年后看到画家罗中立的成名作《父亲》,说真的,跟眼前这位老汉不好比,没他脸上那股仙气。
老汉雕塑般站在我的面前,对襟的马甲敞开着,赤色胸膛上的骨骼肌肉一排排清晰可见,让我想起小时候四舅教我拉的手风琴,我会拉《杜鹃圆舞曲》,“米倒,米倒,米搔搔米倒米来,法西,来扫,来发发米西来倒”。老汉望着我无言,我看着他无语,思甜也沉默着,就这样六目相视好一会儿。
老汉问,娃,多大了?
我默默低下头说,十五。
他伸手抚摸我的头发,静电一样刺刺啦啦作响。娃,回吧,回吧。说着他缓缓走过我们,消失在山谷之中。
回营房路上我没责备思甜,这个老汉有仙风道骨的味道,我都无话可说何况思甜呢?可思甜自己很失落,它不看我,不肯跟我对眼,我看它时它还故意扭过头,又好气又好笑。臭思甜,我还没说你呢,你倒来劲了。
事情至此并未结束。两天后中午,连队夏季有两小时午睡时间,对我来说,两小时躺床上睡不着会无比难熬,很无聊。突然,一阵紧急集合哨铺天盖地响成一片,像卤水点豆腐,把空气凝结成一块琥珀。怎么回事,大白天搞什么紧急集合?思甜在我床前不安地走动,发出“呜呜”的咽呜。我心存侥幸,色厉内荏,炊事班也参加吗?
只听班长大喊着,胖子,你怎么还不动?紧急集合不知道吗?
当我跑出门外全连已排成长长的一列,望不到头。连长脸色铁青,释放出无尽的愤怒。我排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思甜。这时连长从连部请出一位老汉,他肩上的挎篮里不是柴草,而是一堆早熟的柿子和京白梨。我暗自吃惊,虽说任何时候都有早熟的水果,可一下弄这么多很不容易,他这么大岁数,就算找到又如何采下来呢?老汉站在连长身边局促不安,手都没处放。
连长吼道,有人偷老乡的果子,老子今天非处分他不可!老大爷您帮我认认,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是我的兵,绝饶不了他!
连长话音未落,思甜的鼻子喘起粗气,它抬头看看我,又死盯着老汉不放。
老汉眼里冒出水花,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星光。他说,连长你搞岔了,我是给你们送果子的,解放军这么辛苦,凭啥不能吃几个果子?
连长不以为然,您咋知道有人想吃果子呀,您肯定看到当兵的偷果子了对不对?
没有!老大爷斩钉截铁。
连长却不依不饶,老大爷您听我说,帮我认出这个人,就是给我们上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军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铁的纪律,您就帮我这个忙吧。
老汉满脸无奈,只好跟在连长身后缓行。我下意识拉低帽檐,早认出他正是把我堵在树下的老汉,这下可惨了,刚当兵就挨处分,亲娘知道该多难过啊。我心怦怦跳,咬牙坚持最后一秒,希望不被认出来。没想到老汉刚走近我,离我还好几米呢,思甜就紧张得叫起来,一声声对他狂吠,怎么劝都不听。它这么一叫全连都笑了,哈哈哈哈,连长也忍俊不禁,立正——,胖子留下,解散!
是他?
不是。
真不是?
真不是。
说着老汉把整篮水果倒在地上扭头就走。他走得很快,沿弯弯的山梁,像越摇越远的船,风扬起他的小褂,似挥动的手臂,深情对我呼唤着。思甜“噌”地追上去,跑到一半又回来,我知道它想为我送送这位老人。
入夜,月光下我取出一只老汉送来的京白梨。连长说,既然不是胖子偷的大家就分了吧,糟蹋了可惜。刚咬一口眼眶一热,我让思甜也吃,你吃,思甜。它舔舔梨,又舔舔我湿润的面颊,不说话。那晚我彻夜无眠,好像一下长大了不少,我恨自己不懂事,离开母亲的呵护,生活竟如此狼狈,若不是老汉心肠好,处分算背定了,以后还怎么混哪?思甜望着我,它一直陪着我,眼睛时睁时闭,不忍睡去。
3
可十五岁,一个懵懂不羁的尴尬年纪。我心中的世界充满幻想,任何挫折都无法淹没。这次处分躲过了,躲过的灾难不算灾难,不足以唤醒青春的荒唐。我最感压抑的就是与世隔绝,外面的世界到底什么样,我充满好奇。连队周末常去公社的广场看电影,朝鲜的,阿尔巴尼亚的,罗马尼亚的,我最喜欢阿尔巴尼亚的,刘广宁、邱岳峰的配音非常讲究,中文说得像外语似的,外国人就像另一种中国人走近我。你看人家的衣服,毛衣领子那么高围着脖子,多起范。还有《宁死不屈》的台词“外面阳光明媚,人们享受着生活的无比乐趣”,让我情不自禁。明天一定去把军装裤子改细,三号军装是最小的,我穿着还大,窝窝囊囊像缅裆裤,一定改细点。
山下的供销社是这一带的“商业中心”。一排长长的砖房,不仅卖牙膏香皂烟卷糖果,还有个梳辫子的女人踩缝纫机,改细应该找她。第二天正好周末,早饭吃完我和思甜沿下山的小路往前跑,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像我的心情起伏不定,到部队后心情就没定过,总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说不清也道不明。思甜今天不知哪根筋搭错了,走着走着不走了,在背后“呜呜”叫我。我一再跟它解释,保证不偷果子,偷果子也没见你像今天这么磨叽,是不是又犯骚了,想去找小黑?小黑是后山一条小母狗,最近时不时出现在营房四周,远远朝这边窥望。它一出现思甜就消失几小时,回来又满脸歉疚的样子,我还得替它清洗,黏黏糊糊的。其实我自己也偶尔有这种时候,我写信问过亲娘,她说偶尔不碍的,得想办法补补。没想到一提小黑,思甜还急眼了,“汪汪”朝我叫,然后又一会儿在前一会儿断后,认定我是它的狗。
可真到梳辫子女裁缝面前我又犹疑了,好像连长说过军装的每个纽扣都是鲜血换来的,人家给改吗?会不会报告啊?我攥着军装不知如何开口。
女裁缝问,解放军同志,小解放军同志,你有事吗?口气明显逗我玩。
我望着她的大辫子满脸通红,这裤子太大想改细点,可以吗?
她干脆利落接过去,量量裤子量量我,哎哟太大了,这可怎么穿哪,我给你改小点,五毛一件两件八毛,你先旁边转转一会儿就得。
她这么一说我如释重负,长长舒了口气,原来是可以改的,什么事不试不知道,是我想多了。
我和思甜沿长条柜台来回溜达。每月六块津贴费是太少了,可亲娘时不时给我寄来包裹,内衣袜子藿香正气水,涂手的蛤蜊油。那次跟她说“黏黏糊糊”后,还给我寄来一瓶“肾气丸”,刚吃一天就流鼻血,不敢再吃了。所以我花钱的地方不多,兜里总能摸到几块钱。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柜台里有个东西很像半导体收音机,香烟盒那么大,标价三块钱。那个年代民众娱乐两大件:第一打扑克,现在的“斗地主”就是那时开创的;第二当属半导体收音机,最热门的牌子有“熊猫”,“东风”,还有“环球”,据说“环球”最灵敏,有两档短波,可以听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广播,只是卖六十多块太贵了。
我问,这是半导体收音机吗?
是啊。
给我看看。
售货员递给我时一再强调这是新货,总共才进两台。我惊讶地发现这么便宜的半导体居然还带短波。我先调试着中波,只听一片片声音闪过,“大海航行靠舵手……”“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当试听短波时,出现很多杂音和听不懂的话。售货员大惊失色一把夺过去,脸色大变,“啪”地将收音机关掉。我环顾四周,幸好没有别的人。这时思甜冲我“呜呜”叫起来,搞得我很烦,你不骂人家就敢骂我,犯浑是吧?
这个卖吗?
当然卖了。
我买一个。
售货员说得并不错,半导体虽然可卖,但当时偷听不该听的频道却是严重问题,轻则处分重则判刑,不是开玩笑的。我四舅有个“环球”,他当年考上音乐学院指挥系,后来停招了,只得赋闲在家。他就偷听过,尤其是《夜半歌声》,沈湘的原唱:“在这茫茫的黑夜里,谁同我等待着天明……”我都听会了,好听死了,难过死了,我想起小时候在姥姥家温馨又压抑的日子,亲娘亲爹分别同时再婚,起哄啊你们,把我扔在姥姥家,我好多余哦。姥姥善良可出身不好,四舅有才又个性太强,那个日子啊。当时太小什么都不懂,就想变回去,爹娘怎么做的我就再把我怎么做回去,我不要这样活着。
心底的“暗伤”死灰复燃,这是成长对往事的叛逆,也是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情不自禁挥之不去。有人管这叫情结,情结是定时炸弹,比如恋母或艺术情结,构起我情感表达的本能。我明知偷听一旦败露将不堪设想,不光我自己,思甜都明显察觉到了,回营房路上它贴紧我,不断“噗噗”打着响鼻,仿佛要把我带回供销社,让今天重来一遍。我认真对它说,思甜你看到了,裤子是可以改的。至于半导体,我保证只听中波,如果听短波我是你儿还不行?然而我想不到的是,启蒙的冲动会多凶猛,好奇心比性欲都更强烈,那时我已有性意识了,思甜找小黑都让我产生幻想,青春的骚动像一记致命扫堂腿,将平淡的生活打翻在地。加上我不谙世事的浮躁任性,一切来得过于急促,连思甜的行为都发生了改变,我一碰收音机它就往门口跑,鼻孔发出打喷嚏似的噗噗声。
开始我坚持只听中波,像对思甜保证的那样。其实“建制式”节目也很好听,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有段序曲,“啊……百鸟啼叫不停息,满腔怨恨向谁言……”,颇具俄罗斯风味。还有一档节目叫“电影录音剪辑”,就是放电影录音片段,《海岸风雷》中有段父子对话令人难忘,当风雨将至海涛翻涌,马上就要变天:
撒网吧孩子们。
爸爸,马上暴风雨了?
你们撒网好了!
一切像诅咒又像宿命。时间一久我日渐焦虑,当夜深人静在被窝里,我会把半导体攥出汗来,恨不得吞进肚子,在肚子里听。我开始借上厕所半夜往外跑,连队的岗哨设在大门口,这边没有。还有一点很巧,厕所旁边有根电话线,把天线搭上,耳机就加倍清晰。我不惜熬到后半夜,后半夜人睡得最死,趁万籁俱寂戴上耳机,伴着心跳,聆听遥远的“心灵悸动”。我只喜欢音乐节目,其他的不听,听也听不懂。我沉浸在莫名的亢奋中,一般顾不上思甜给我的种种暗示。
然而,最刺激的时刻往往也是命悬一线之际,那根悬挂“达摩克利斯剑”的马鬃,终于绷断了。
那夜没有月亮黑成一团。我又起来上厕所,思甜显得格外躁动,凌乱的步伐像悲情的鼓点围着我转。我像往常那样躲到旁边挂上天线,开始聚精会神地调整频率。还没调准台呢,只听“嗷”一声,思甜不见了!紧接着在不远的黑暗中,竟爆出连长的惊叫与狗吠声响成一片。思甜最怕连长,怎么敢咬他?没等我反应过来,连长的惨叫声再次证实了这点,狗日的你敢咬我,奶奶的,你真咬啊,“哎哟哟”咬到老子了!我一把扯下天线,将收音机和耳机统统丢进化粪池。黑暗中连长觉出附近有人,大喊道,谁在那,是你吗胖子,奶奶的,快把狗拉开呀!原来连长也来上厕所,若不是思甜,肯定跟我撞个满怀!
你不睡觉搞啥鬼?
我起来上厕所。
这狗咬人必须杀掉!
不行,绝对不行!
你懂个屁,它以后见谁咬谁。
那也不能杀。
必须杀,这是命令!
长夜未尽。我的泪水和悔恨在黑暗中狂舞,既恨连长冷血又恨自己没用。思甜浑身打哆嗦,在我怀中瑟瑟发抖,从没见过哪只狗这样恐惧过,我的思甜啊!我对它说,连长要杀你听到了吧,快跑啊思甜,去找小黑,跑得越远越好!我怕它听不懂,还特意做出杀的手势。思甜望着我满眼泪水,突然转身,消失在夜幕中。
4
当晚我就发起高烧,陷入半醒半睡之中。醒是我怕思甜回来,强撑着等它消息。睡是实在撑不住,逐渐失去了意识。
迷蒙中我好像听班长在说,情况不好啊连长,大小便失禁了,这样下去会死人的,咋办呀连长?
接下来是连长的声音,还能咋办,卫生队太远指不上,奶奶的,抓到了吗?
抓到了抓到了,连长你太准了,还真悄悄回来看胖子,被我一把拿住。
那就下家伙吧,按我说的偏方试试。
这行吗连长?
废话,皇上老儿都靠这个救命,奶奶的,不行也得行。
不知多久我才苏醒过来,只觉得天是白色的,雪白雪白。班长见我醒了高兴得大叫起来,醒了,胖子醒了,哎哟你总算醒了小祖宗,还是连长有板眼,一碗狗血下去就活过来了,胖子你差点过去了知道吗,多亏连长的偏方……
陈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经系、美国俄亥俄大学国际事务系及纽约石溪大学信息管理系,硕士学位。长期从事跨文化文学创作。代表作有小说选《挫指柔》《卡达菲魔箱》,散文集《纽约第三只眼》《野草疯长》及诗选《漂泊有时很美》《窗外是海》等。作品获第十四届百花文学奖,第四届《长江文艺》完美文学奖,第五届中山文学奖,及第四届三毛散文奖。
责任编辑: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