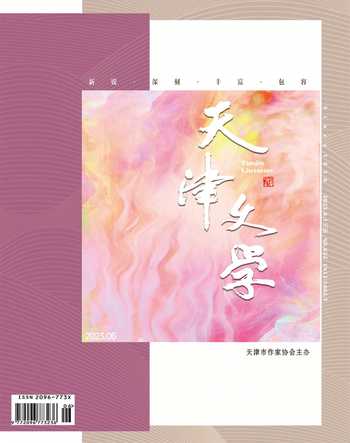大暑
一大早,一个陌生电话把我从一个女人身上拽下来,陌生电话让我挪车。女人昨晚就来了,不陌生。
路两旁塞满了汽车,长短胖瘦不一,里出外进,犬牙交错,像老人残缺不全的牙齿。在路中间,我小心驾驶着汽车缓慢穿行,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不但要避免剐蹭到旁边的车辆,还要防备不定从哪儿突然窜出的自行车或行人。可我还是剐蹭到了一辆车。一辆黑色别克公务舱。它突兀地撅着右后屁股,稀里糊涂的,我的左前大灯和它右后屁股吻在一起。我下车查看,很幸运,只浅浅一道划痕,不严重,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天尚早,人不多,没人看到,我回到车内继续往前开。
我住九层,可我得走步行楼梯,电梯不能用,所有按键指示灯睡着了一样,眼睛全闭着。我下到一楼,全身湿透,衣服黏糊糊贴在身上。好多人站在楼下,往楼里张望,议论着什么。昨夜,地下室的消防水泵坏了,水灌满地下室,全楼停水停电正在紧急抢修。
今日大暑。
我的车停在楼下的院子里。有人要开车出去,我的车挡住了人家的出路。我坐在车里,感觉钻进了蒸笼,热浪瞬间把我淹没。屁股潮乎乎,好像汪了水。我匆忙下楼,眼角有眼屎,眼睛膀肿,睡眼惺忪。我还有点儿迷糊。我穿一双拖鞋。这种情况剐蹭到别克公务舱的右后屁股,我能原谅我自己。
我开车在小区转了一圈,没找到停车的地方,又回到楼下的院子。我的车比原来的位置靠里一点儿,还是横在狭窄的通道上,挡住别人的出路。刚才让我挪車的那辆车在我里面,它出去了,我停在它的位置上。我上楼时,又有一辆车开进院里,停在我车的后面,挡住了我的出路。
我爬回九楼。女人走了。屋子凌乱空荡。我把衣服脱了,背心和短裤,赤条条站在屋子里。不能洗脸刷牙,空调电扇不能用。我擦汗。毛巾干涩生硬砂纸般在身上摩擦。我还很困,得接着睡觉。我把凉席铺在客厅,卧室通风不好,客厅窗户直对着我,没有风。楼下嘈杂声不绝于耳。
嘈杂声与我渐行渐远,我可能睡着了。
楼下停满了车,偶尔有个空位,眨眼工夫就填补上,像坏了一颗牙齿,刚拔掉,露出黑洞洞的缺口,须臾不耽搁镶上了牙。我从外面回来,刚进院门,见一个黑洞洞的缺口,调车屁股往里倒,倒了一半,又开了出来,里边塞着一辆电动三轮车。我把车横在狭窄的通道上,没办法,只能这样停,原路退出去也无济于事,小区道路两旁停满了车。通道上横了两辆车,我的车停在他们后面。
我再一次被电话叫醒,是另一个陌生电话,仍然是让我挪车。电话里的声音已经不耐烦了,问我怎么半天不接电话,有急事都给耽误了。刚才,我随手把手机扔在卧室的一堆衣服上,调成震动了,响了半天,才听到,有三个未接电话。我慌忙穿衣服往楼下跑。让我挪车的是个中年女人,矮胖,站在我车前,脸红彤彤的,直勾勾盯着我,盯着我从楼里出来,走到车前。女人不好惹,中年女人更不好惹。我连忙道歉。矮胖女人的车在我车前,我挡住了她的出路。我车后是空的,人家早就挪出去了。我以貌取人了,中年女人并未不依不饶,她怕是真有急事,没工夫搭理我。我往外倒车,中年女人开车紧随我往外倒,很近,几乎贴上了,技术不错。出了院子大门,中年女人调正车的方向,一溜烟不见了。
我没有马上把车开进院里,而是沿着中年女人的车辙也向前开,在小区里转悠。我想碰碰运气,如果有停车的地方,直接塞进去,就踏实了,一劳永逸,还把车横在院子里,谁的车出去,还得叫我下楼挪车。但我的运气不好,转了一圈,没有找到停车的地方,只好再回到楼下,把车继续横在院子狭窄的通道上。在小区转悠的过程是顺畅的,除了路旁边停的车,没见到其他车,更没见到人,我不知道这会儿怎么这么安静。
我还是爬回九楼。我应该继续睡觉。我也想继续睡觉。天儿还早,我没有理由不继续睡觉。楼上楼下又跑了一趟,又出了一身汗,不洗洗就躺下,难受极了。我撒了一泡尿,马桶冲不了,底部一圈全是黄色的尿液,泛着浓烈的尿骚味。地下室传来“咚咚”的声音。杯子剩半杯水,我喝了。喝完冒了一层汗。我以前没注意,喝进去的水,难道从汗毛孔渗出来吗?我继续躺在客厅的凉席上。我把双手枕在脑后,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
一只蚊子落在腿上,吃得脑满肠肥,身体鼓胀得血随时要喷出来,动作都有些笨拙了,我没太费劲就把它拍死了。血溅了一手,腿上也是。
我可能又睡着了吧。
我上楼梯,长长的楼梯从脚下延展开去,望不到头,楼道灯光幽暗,空无一人。我肯定有什么急事,三步并两步,“咚咚”的脚步声在楼道回响。很快,我就气喘吁吁了,头上身上都是汗。我扶着楼道的墙,继续往上走,我总觉得就快到了,再走几步就到了,到了,就可以喘口气歇歇了。可楼梯好像没有尽头,越走越长,我的体能明显下降,开始一阶一阶上楼梯。我有些气馁,坐到了台阶上。正在这时,好像情况出现了变化,我再站起往上走,觉得不那么费力气了,而且越来越不费力气。我不明就里,站在狭长的空间茫然四顾,小心地往“上”走。楼梯还是那样,长长地向上延展,角度一点儿没变,我却如履平地,顺畅得很,后来,简直就是走下坡路了,需控制速度,不然有可能人仰马翻地滚下去。
又一只蚊子在我耳边嗡嗡,我挥手把它轰走。蚊子是我最痛恨的动物,恨得咬牙切齿。拍死一只蚊子,我的成就感和舒适感能延续到第二天。我是疤痕体质,蚊子叮一口,奇痒无比,用手一挠,立即破溃,然后结疤,我的双腿到处是红色或暗黑色的疤痕,看着很不雅观。
手机又响了。手机就在我枕边,立刻接听,还是让我挪车。这次要出去的车在院里的停车位里,通道的车不挪,他的车出不去。挡住人家出路的有三辆车,一辆在我前面,一辆在我后面。我下楼时,已经有一个人出来了,可能也正在睡觉,站在车旁打呵欠。我的车在他后面,我不挪他动不了,我后面的车主还没下来,他不下来挪车,我们都动不了。我们都盯着楼的出口,出来几个人,不是挪车的,径直走出院子。要出去的车主掏出手机拨打电话,表情不耐烦,口气还客气,您什么时候能下来啊?我们都等着呢。对方说,很快,很快。又过了一会儿,一个人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拎着刚买的早点,用塑料袋兜着,豆浆包装不严,一路滴滴答答。这个人往楼里跑,我拿钥匙去,我拿钥匙去。
四辆车几乎同时发动了引擎,烟雾缭绕,把院子弄成了仙境,尾气的味道有点儿甜。我第三次挪车了,把车从楼下的院子倒出去,是第三次了,今天,早晨。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第四次。第一次挪车,尴尬得很,狼狈得很,心情自然烦躁。第二次本应更烦躁,可那个中年妇女催了我那么多次,我把她的事都给耽误了,有什么理由烦躁呢?第三次我没有烦躁的感觉了。我躲开了那只令人痛恨的蚊子。屋子又闷又热,还有一只嗡嗡叫的蚊子,正好下楼透透气。
车位里的车出去后,我前面的车近水楼台,屁股一扎倒了进去。我可以停在他的位置上,还是在通道上,只是往里挪了一个车身。可我还是想碰碰运气,开着车在小区里转悠,希望找到停车的地方。转了一圈没找到车位,不甘心,转第二圈。不是我死心眼,固执,有时还真能发现“新大陆”,但这样的概率极低,大多是白费工夫,狗追猪——瞎转悠。
一辆大车堵在路口,是每天都进小区的垃圾车。我停在它后边。我后面是一堆自行车和行人。我后悔多转一圈,没找到车位,还堵在这里。没想到情况更糟。垃圾车半天不动,后面的人引颈高喊。垃圾车动了,不是往前,是往后,有个人跑过来指挥垃圾车往后倒。没有倒车空间,那个人双手用力挥动,仿佛十分费力地推一个巨大的物体。后面的人开始叫骂。那人说,没办法,过不去,半个多钟头了,前面的路挡住了。
一辆黑色奥迪堵住了垃圾车的出路,车上没留电话,问了半天,得知是附近一个工地包工头的车,包工头坐飞机去外地了,早晨刚走,连车钥匙一起带走了。包工头的车和一辆小车并排停着,中间的路更窄了,但停车处是一个封闭的大门凹陷处,比其他地方宽一些,小车可以通行,包工头没觉得碍事。身形巨大的垃圾车一早空车进小区,还勉强蹭进去,装满垃圾出来就被堵在里面了。我不明白,垃圾车往回倒是什么意思,小区共两个口,另一个口更窄,根本出不去。
后面的车和人流像一块黏稠的“淤泥”,开始缓缓后移。我的车技本来就稀松二五眼,这样的路况,往前开还行,倒车真让我头疼。我倒得很慢,小心翼翼。但还是遭到四周人的怨怒。前面的嫌我倒得慢,两边的喊着说我刮到他们了,后面的嚷嚷着说我撞到他们了。有人“砰砰”拍打车窗玻璃,拍得我心烦意乱。
我想从车里钻出来,把车一锁,然后一走了之。可周围的车和人像铁箍一样把我困在车里,无法开门出来。我像动物园里的一只猴子,被牢牢关在笼子里,供游人观赏、戏耍、嫌弃和嘲弄。我没有任何辩驳的权利和反抗挣脱的能力。我的使命只有一个,取悦别人。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发现处境似乎也没那么糟糕。我从车里往车外看,产生一种新奇的陌生感和隔阂感,像从另一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乍看,外面的人形态各异,表情丰富。再看,所有人的形态都一样,焦躁;表情也都一样,呆滞。我怀疑观察力和判断力出了问题,贴近车窗仔细看,确实如此。我错愕。只错愕了一瞬,就坦然了。两个世界之间是有差别的。
我发现了一个机会(不管是不是机会),觉得应该尝试一下,这种情况下必须做出改变,改变才能摆脱窘境。旁边有个空当,在两树之间。心中窃喜。运气到底还是来了。我高兴早了,这个空当还是窄了点儿,停不进一辆车,都精明得很,贼得很,这样的好机会没人能错过。空当平时被电动三轮车或自行车填满,没人注意它。我觉得无路可退了,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我踩着刹车轰油门,车后炸了窝,轰鸣声、叫骂声一片,遮天蔽日的浓烟散去后,现出一块干干净净的空地。我迅速向后倒车。不是我死心眼,愣要把车塞进那个进不去的空当里,我当然不希望车磨损、挤扁、变形,丑陋得不成样子。
两棵树不是平行的,一前一后岔开着,这就是机会。
我斜着车身往里倒,左边的车屁股先进去,情急之下,我的潜能被开发出来,一把进去,严丝合缝,几乎贴着树皮,只一个钢镚的缝隙。平时停车入库腻歪得很,有时还得下车看一眼,才勉强塞进去。车停稳了,还没见有人这样停过,探出小半个身子,突兀地昂着头,傻乎乎地观望着什么。垃圾车轰隆隆从我前面过去,“撮”着车后那堆“淤泥”。我觉得垃圾车与我车头的距离是一张纸币的宽度。
我松了一口气。没我事了。垃圾车倒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能出去,怎么出去,我不操心了。我回家了。楼下院里停满了车,通道都停满了。我庆幸没回到院里,回来也没地方停了。
我应该继续上楼睡觉。我不知道这会儿我还应该做什么。可我现在一点儿都不困了,那辆堵在小区里的垃圾车,耗费了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已经销蚀尽我的困意。地下室伸出一根帆布管子,向外排水,水浸过停在院里车的轮胎,慢慢流到院外。从楼里出来的人和从院外进来的人,选择水浅的地方,踮着脚尖一跳一跳地走。
是情况本就严重,还是情况变得严重,地下室的动静越来越大,人也多了,来了一辆面包车,车上装着不少工具。面包车斜着扎在门口,只进了半拉身子,太长,进不去,能进去也没地方停。
面包车像座小山,横亘着,碍手碍脚,遮挡视线,堵心。
我侧着身子从面包车旁挤进来,面包车堵住门口,只有通过一个人的缝隙。我上楼进屋,撞上门,再次把自己脱光,坐不是,躺不是,站不是,在屋里来回溜达。有敲门声,声音很轻,和地下室的声音裹在一起,声音更轻。我一惊,眼睛盯向刚刚关上的门。敲门声重了些。我紧张地站在门里,通过猫眼瞄向门外,一个陌生男人。谁?我问。是我。外面的人回答。我没开门。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开什么门。敲门声又重了些。我生气了,打开门,冲陌生人喊,你想干什么?陌生人一步跨进门,随手把门撞上。我的心提了起来,下意识地退后一步,想一定遇到了不测。陌生人说你别紧张,我只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仍然警惕地问,你到底想干什么?陌生人说,别急,听我说。我站在原地不动,没有请他往屋里進的意思。陌生人就在门那里站着说话。他说他停在小区里的车轮胎总被扎,有好几次了,案子都是半夜发生,有一个人嫌疑很大。我听着觉得不对劲,没好气地说,我又没扎轮胎你找我干什么?他用手往旁边一指,说他怀疑的人就住在我隔壁。他难道想在我家埋伏下来,守株待兔,等嫌疑人回来立刻抓住扭送派出所?我说,我一会儿要出去办事,你抓紧吧。这时,他说出了他的意图。兜了这么大圈子,现在才说到正题。陌生人说要在楼道装一个摄像头,再用我家wifi密码上网,和摄像头连在一起,他用手机观察嫌疑人。我说,我凭什么要协助你?你这是监视他还是监视我啊?我对陌生人的无理要求非常反感,我说,你少跟我扯这个淡,你这是非法监视。我连推带搡把陌生人轰了出去,“砰”地把门撞上。
我一点儿没有困意了。我气得够呛。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肚子饿了。打开冰箱,只有一个馒头,一个鸡蛋。锅里放上水,点着燃气灶热馒头煮鸡蛋。水开了,掀开锅盖,白色的气体升腾开来。伸手拿馒头,刚拿在手里,馒头像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子,颠来颠去,烫得扔了出去。低头找,满地找,整个厨房找遍了,没找到。从卫生间拿了扫帚,倒握著在橱柜下扒拉,都扒拉遍了,没有。横不能跑到厨房外面去吧。在客厅里找,也没有,用扫帚在沙发下扒拉,馒头真跑到厨房外面了,竟从沙发底下滚出来。真是活见鬼了,怎么跑到客厅沙发下面呢?难道馒头真是只会蹦会跳的兔子。馒头已经面目全非,黑不溜秋,沾满灰尘,尘土上全是头发,长头发,短头发,长的是女人的,短的是我的。看到馒头上蜘蛛网似的头发,我心里一阵发紧发麻,像有无数只虫子爬,极度不舒适。我把煮鸡蛋吃了。我把细碎的蛋皮以及沾满灰尘和头发的馒头一起扔进垃圾桶。
我开始扫地。我平时很少扫地,实在看不过去了,才象征性地比划两下,算是一种心理安慰。我没把扫地看成生活中多么重要的事。生活中比扫地更重要的事有的是,得抓紧时间做。我住的房子是两室一厅,不算大,也不算小。我从卧室开始扫,床上的头发似乎更多,特别是枕头下,一层,长的,短的,她的,我的。然后书房,然后厨房,然后客厅,最后把扫的垃圾堆在卫生间门前,竟有一大团,有一个皮球大小,什么都有,灰尘、瓜子皮、花生皮、栗子皮,还有一枚硬币,主要还是头发,密密麻麻一团。得有上千根儿吧。每个人都掉头发,这是自然的生理现象,我看过一篇文章,说一天只要掉头发不超过五十根就算正常。这密密麻麻一团头发得掉多少天啊。我把头发撮进簸箕倒在坐便器里,实在不愿再看到它,一冲了事。可我把没有水的事忘了,头发就那么硬生生地塞在里面,黑乎乎的。突然,“咣”的一声,吓了我一跳。厨房的门撞上了,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谁把门关上了?我紧张地向厨房走去,手里握紧扫帚把,随时准备挥打出去。一阵狂风,卧室的门也撞上了,来不及反应,昼如黑夜,暴雨倾泻。窗帘掀到房顶,啪啪响,阳台地面雨水纵横。我急忙关窗,外面烟雨蒙蒙,混沌一片,楼下和小区目力所及的地方,所有车溜光水滑,闪着耀眼的光。狂风仍不甘心,继续撞击窗户,哐哐!哐哐哐!单薄的窗户随时会炸裂散落。远处正在行驶的汽车,开着大灯缓慢移动着,像一只只病恹恹的猫,瞪着无神的眼睛寻找安身之处。连续几个闪电,滚过几个闷鼓般的雷声,紧接着一个闪电,天地一片银白,雷声炸响,汽车报警声此起彼伏。
手机又响了。雷声淹没了手机铃声。我看到了手机屏幕急切焦躁地闪动着。我不担心挪车电话了,我的车妥妥地停在两棵树之间,不碍任何人的事了。大树总不会找我的事了吧。再说,这电闪雷鸣的天气,谁还开车出去呢,除非不得不办的事情。电话那头不容我说话,开口就喊道,你赶紧过来吧!我听出是父亲的声音,这个时候这么急切的电话肯定出了大事,父亲还能打电话,声音洪亮,应该没事,那就是母亲有事。我来不及多想,拿上房门钥匙、车钥匙跑向楼下,跑向小区停车的地方。刚跑出门,忘拿伞了,又跑回去拿了一把伞。刚出楼门,我全身就湿透了。跑到停车的地方,我傻眼了,车还在两棵树之间,一棵树连根拔起,斜歪着身子倒在车上,前挡风玻璃已经破碎,车里灌满了雨水。我跑到大街上打车,哪儿有出租车啊,边跑边打,跑出一公里才打上车。
我想象的情景没有出现,母亲没躺在床上,父亲也没急得在屋里团团转。两人一个在客厅,一个在卧室。屋子里安静得很。外面的雨还哗哗下着。我问出什么事了?都不说话。我又问了一句。两人看了我一眼,还是没说话。我肯定像个落汤鸡。我站的地方全是水。父亲说话了。父亲说你把她接走吧,我不想跟她过了。父亲话音刚落,母亲就说,我还不想跟你过了呢。我问,为什么不过了?父亲“呼”地站起来吼道,我早就跟她过够啦!父亲的手抖得更厉害了,连带身体一起抖,都站立不稳了。父亲帕金森很多年了,越来越严重,吃饭喝水都成问题,碗里的东西,送不进该去的地方,基本都灌在脖子里。母亲的嗓门也不低,虽然说话已经含混不清。母亲是中风,到医院抢救多次,每次都能顺利回家,吃饭喝水影响不大,腿脚不行了,整天坐在轮椅上。母亲说,都老棺材瓤子了,还这么不要脸,我都替他臊得慌。父亲和母亲年龄都不小了,一个八十五,一个八十四,都是老棺材瓤子了。我站在客厅和卧室之间,不知道该应对谁,父亲和母亲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向我喷来口水,一浪接一浪,我身上更湿了。
听了一会儿,我明白了。父亲的手越来越抖,做不了饭了,想找个保姆。母亲不让找,嫌费钱,说你能凑合就凑合,好几千块钱白扔。母亲坐在轮椅上,做不了饭,吃现成的。后来父亲炒菜把油洒在火上,差点引起火灾,母亲勉强同意找保姆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来家里“面试”,父亲给她端水,刚沏的茶抖得剩不下多少,剩下的抖到妇女手上。妇女“啊”了一声,父亲抓住妇女的手,说烫着了吧。母亲见状,把手里的茶杯扔了过去,砸到父亲头上,砸了一个包。进门的时候,我看到父亲的左前额肿了起来。
中年妇女“嗷”的一声跑了。
我说,把户口本给我。父母同时问,要户口本干吗?我说,拿来吧。父亲哆哆嗦嗦把户口本翻出来,递到我手里。父亲和母亲互望了一下。我说,好,明天我开车过来接你们。父母问,去哪儿?我说,民政局。
雨怎么越下越大啊,天连着地,地连着天,分不出个层次,成了一个气团。我从父母家出来时,又忘拿伞了,没拿没拿吧,反正全身已经湿透了。马路像一条河,水流湍急,河中停满抛锚的车,高矮胖瘦颜色各异,甲壳虫似的露着光滑的车顶。我不可能坐公交车或打车回家了。我在雨中奔突。雨水没过小腿快到膝盖了,还在往上涨,我必须用力扭动身体摆动双臂才能艰难前行。我呼吸非常困难,不得不间断停下来大口喘气,除了体力消耗过大,还紧张恐惧(这种精神压力,体力消耗更大),雨水兜头盖脸,像水闸泄洪,我什么都看不清,如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洞中行走,比黑洞还恐惧,手触不到岩壁,摸索着往前探,随时担心掉进深不见底的深渊。
我为什么不找个地方避一避雨呢?
手机提醒了我。手机的震动让我有触电般的感觉。在大雨滂沱的雨中,手机竟然有如此巨大的魔力。我“游”到离我最近的一个公交站接电话。仍是个陌生电话。陌生电话让我挪车,说树刮倒了,横在路上,影响交通,得把树锯掉,我的车碍事,得挪走。我说我在外面回不去。把电话挂掉了。我非常失望,我以为是刚刚跟我同床共枕的女人的电话,她走了,又回来了,我不在家,进不去,给我打电话。我想见这个女人,我想她也想见我。我认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无论世界发生什么事,哪怕山洪暴发,哪怕大坝决堤,哪怕海水倒灌,哪怕天崩地裂,我们都会在一起,永不分离。我们相识不久,很快就非常亲近了,难舍难分,可见,相识时间与关系亲疏没有相关性。我不认为她不打招呼,就会离我而去,她一定有充分的理由,暂时出去,但很快就会回来。所以,我得马上赶回去,以免她在门口焦急地等待。对了,我忽然想起,昨晚我们一起开车出去,她买了一双鞋,忘在车上,现在还在车上吗?泡汤了?冲跑了?我想给刚才那个陌生电话拨回去,让他帮我在车里找找那双鞋,一双白颜色、细高跟儿、三十八码的高跟鞋,我跟他说,找鞋最重要,车咋挪都行。
可手机不能用了。黑屏。被雨水浸泡了。
雨住了。汽车喇叭声渐起,像雨后青蛙的聒噪。我在精疲力竭之时,到了小区路口。我看到了天上有一道彩虹。一辆吊车正在作业,吊臂慢慢升起,移动,挂钩上好似一条刚从海里捕捞上来的巨大的乌贼,汤汤水水,稀里哗啦。忽然,我脚下的水没了,瞬间就没了,抬头看去,整个小区水都没了,刚才路边所有汽车的半个身子还淹在水中,现在裸露出来,像有一块巨大的海绵,一下把水吸干了。
吊臂停在半空,那辆前挡风玻璃损毁严重的汽车,与彩虹叠映在一起。
从林,北京人。北京作协会员。曾在《啄木鸟》《青年文学》《创作》《特区文学》《天津文学》《芙蓉》《厦门文学》《短篇小说》《山西文学》《鸭绿江》《地火》《星火》《阳光》《北京作家》《延河》《都市》《佛山文艺》《北京晚报》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等若干。
责任编辑:王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