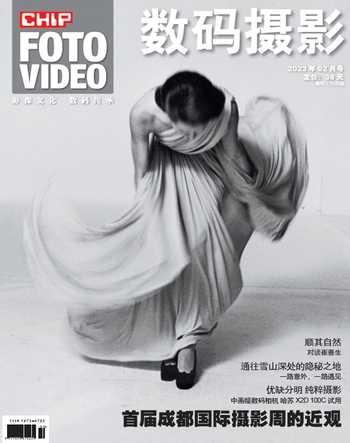顺其自然



从19世纪初期到现在,摄影逐渐从记录性的工具演变成为一种文化,而作为一种文化,探索和实验是其发展的重要手段。从探索与实验的角度出发,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与年轻摄影师群体的合作——“锐像”便是一个专门介绍中、外年轻摄影师的栏目。《数码摄影》杂志通过对他们的深入采访,将他们和他们最具实验性、探索性的作品介绍给广大的读者群体。面对这些年轻人的“新锐”作品,也许很多人没有办法能够立刻接受,但是我们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好与坏、对与错并不是由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来盖棺定论,因为这是一个过程,一个事物发展的过程。本期的“锐像”栏目,向大家介绍年轻摄影师崔善生,他喜欢从文学和电影中汲取创作灵感,从日常生活中捕捉某种神秘的共鸣。他也一直持续地坚持文字和影像的创作,同时也经营着一家叫谜雾舍的冲扫店。
崔善生这个名字源于《莲花》中的一句:“来,善生,跟我来。”崔善生喜欢从文学和电影中汲取创作灵感,从日常生活中捕捉某种神秘的共鸣。他一直持续地坚持文字和影像的创作,同时也经营着一家叫谜雾舍的冲扫店。
从传统的胶片到实验影像,崔善生的作品运用了各类媒介的创作形式,他认为除去社交媒体里愈发高效的图片呈现以及传统的画廊展出外,如今的摄影艺术市场也应该通过调动更多的媒介去参与创作,在网络中构建和探索更多呈现方式的同时,并与线下形成一种呼应,比如《城市谋杀案》中的实验短片与其展出现场、装置和画册的联动,《岛屿变奏曲》与音乐的联动等等。虽然摄影作品的价值和接受程度依然面临着一定困境,但影像作为新世纪的语言必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个良性的市场机制会助推摄影创作的健全化。“因为我热爱摄影,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创作的价值能够得到尊重。”
——张隽
崔善生
生于1991年,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10级编辑出版专业毕业。诗人、摄影师、谜雾舍主理人。作品有:诗集《账单》,摄影集《城市谋杀案》系列、《忧心忡忡的美梦》《岛屿变奏曲》等。曾担任直播节目《写真食堂》策划、顾问。
QA
对话崔善生
FOTO:你的本科是在北师珠学习的编辑出版专业,而现在主要转向了摄影行业,那能否介绍一下你的学习背景以及创作路径?(比如对你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艺术家。)
崔善生: 我从小比较有探索的欲望,喜欢乱写乱画,就很疑惑为什么拍照只是拍摄集体合影,而不是其他的一些空镜头——比如天上的云朵。这是我对图像的最早认知,也是对影像产生兴趣的原因。所以,我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转专业的说法,也并不是因为大学才开始对于摄影产生兴趣,而是在我之前的人生中没有接触到摄影这个选择。
2010到2014年,我在北师珠学习编辑出版专业,课程的门类很杂——现当代的中外文学、广播制作、新闻采写和编辑、各种设计软件、市场营销课程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出版课每年都要做出一本出版物——第一年印刷青年杂志,最后一年印刷小学一年级教材书。这是每年课程中的必选项,需要以小组的形式完成,每次分派的任务都不同,策划、编写、编辑校对、打印展示等步骤我都全程参与过,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作品创作帮助很大。毕业后在北京上了一个半月的暗房课程也对我之后的拍摄有很大的影响。
我的创作方式受到很多艺术家的影响——不只是纯粹摄影的领域,我把这些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创作方式。最开始,我在邮件里看到了一张清晨时分在甲板上披着一条蓝色毛毯的男人,这是一个忘记名字的玛格南摄影师拍摄的,它让我下决定要通过摄影开始创作,我特别希望能拍出这样的作品。
在文学上,从安妮宝贝到海子、杜拉斯、三岛由纪夫、太宰治、王小波、木心再到芥川龙之介、卡尔维诺;在电影上,从各式港片到姜文、杜琪峰、王家卫、娄烨再到各类小众片子,这些作品激发了我的很多创作感觉。在摄影上,最开始接触的是杂志上的照片,大学时候接触了豆瓣,在上面认识了许多目前仍旧活跃的摄影师——吃土豆的人、松本南国、张剑等等,也接触到了很多國内外的知名摄影作品,其中二战后的那一批日本摄影家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最大,像是森山大道、中平卓马。
FOTO:你的作品都是在旅行中拍摄的,你很喜欢旅行么?你觉得旅行和你的摄影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崔善生:我喜欢旅行,旅行可以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事,经常会让我有一种新奇的体验,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能让我跳脱思维的局限性。每次无意识的旅游总会激发我的灵感。
对我而言,作品和创作者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妙,与其说是作品被创作者生产出来——如同母体受精的生产方式,不如说这是双方的选择,摄影和人生一样是一种选择,而这样的选择不完全是主观的,而是受到很多来自命运的影响,人和他的作品之间也有微妙的缘分。
FOTO:你如何看待日本摄影,它给你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崔善生:日本摄影,其实我了解的也不够多,可能是都从属于东方文化,而近现代的日本又是东西方结合的典型代表,与我们当下所处的环境有不少相似之处——甚至有些情况他们比我们更早遭遇,所以我能从日本的创作者身上汲取到很多力量来促使自己的思考。
我最欣赏的是他们在创作上的生命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真的一直拍摄至死去,这种力量感也是我觉得当下的创作者非常缺失的。
FOTO: 《东欧空难》《城市谋杀案》《忧心忡忡的美梦》《地狱变》这些作品的名字都带有悲剧色彩,你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命名?
崔善生:这种命名方式是我受到当时的遭遇和状态的影响,根据我对于人生经历的思考,试图用文学化的方式在作品层面上反思自己的人生。
FOTO : 那这些作品的取材来源是什么?可以描述一下你的创作思路吗?平时的状态是怎样的?而创作的过程又是怎样的?是先做好拍摄计划还是后期进行整理?
崔善生: 我作品的取材范围不固定,大多数是在生活里拍摄的素材。很多时候遵循着潜意识的拍摄欲望,或者依靠当时所在场域里的忽然冒出的灵感去拍摄。这些素材对我发出了某种召唤,那些被拍摄下来的照片总有一种想要被表达的欲望。比如作品《忧心忡忡的美梦》是我在日本探望朋友时候拍摄的;《地狱变》是我在日常出门闲逛时拍摄后再整理纹理类素材时产生的作品;《城市谋杀案-Vietnam》是我2018年初在越南旅行时拍摄的,旅行末段在胡志明市遭遇了抢劫,让整个旅程的素材完全有了不一样的走向,这些都是个人思考和生活结合碰撞出来的灵感。
目前,“城市谋杀案”是我之后一个很重要的创作母题,其中已经完成系列的取材分别是在越南、上海和珠三角地区。
一般来说,我的创作很少有提前计划的,几乎都是先去拍摄,再一遍遍地审视它们,这时候有些线索就会自己冒出来,有些则会继续潜伏。譬如《城市谋杀案-Vietnam》这组作品,是我遭遇抢劫后回看照片时,才注意到照片中早已显露出当时脑子里没有想到的线索。通过我的调查和越南房东的讲述,以及我结合生活和历史的推断,这个谋杀案才逐渐浮出了水面。这可能就是之前自己想到的“城市谋杀案”这个名字所要表达的内容。我在这场“谋杀”中,是凶手、帮凶也是受害者、旁观者。越南这个地方,本身发生的故事和城市谋杀案这个名字发生了连接,这都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我平时除了参加活动,基本就是在家里整理作品,冲扫胶片,阅读书籍和电影。有时候会写些东西,偶尔和朋友们电话交流想法和创作。
创作上,近三年和之前有了比较大的区别。首先,我之前有机会就会出去拍摄,而现在因为疫情影响出行没有之前便利了;其次,我一直在思考自己创作风格的发展,如何更好地通过作品表达这个在自己眼前复杂铺开的时代。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思考时期。
FOTO:此外,作品和作品之间会有关联么?比如,《城市谋杀案-Shanghai》和《城市谋杀案-Vietnam》它们之间有联系么?如果有,是什么?
崔善生:作品之间的关联,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城市谋杀案这个名字。即,在当下的全球资本化的时代中,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很多事情都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以及在大环境之下每个受影响的人之间也在彼此发生着关系,这种社会的驱力和人性的驱力相结合,共谋出了城市谋杀案。其次的连接是创作者,即我的参与。我并不是很在意是否要隐去作者,而更在乎作品蕴藏的能力,以及时代的关联,任何创作者都很难完全剔除这个部分。我希望我的创作最终能形成一个自己的“宇宙”,它们彼此关联,又时时呈现着世界的不同侧面。
“城市谋杀案”系列的各个作品之间必然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仍旧想让观众自己去阅读感受。挑一点讲的话,就是它们都呈现着人们生活的部分真相,尤其是人的挣扎与异化。
FOTO:作品《城市谋杀案-Vietnam》是通过档案夹和纸上电影的方式呈现,十分特别,能否分享一下当时的创作想法?作品的编辑/整理是一种怎样的逻辑?以“城市谋杀案”系列作品为例,如果在实际的展览中,你会进行怎样的安排?
崔善生: 这组作品,我最初想好的呈现方式就是视频,一个由照片、日记、旁白、音乐和声音采样组成的视频。因为考虑到摄影作品在互联网上的呈现方式太过单一,有很多类型的作品不能体现出它们的特质,而展览更多是展出的方式,它需要和观众有一定的互动性,我希望呈现不一样的方式,让观众的体验感不一样。
后来, 我开始尝试制作纸质书籍,因为书籍的质感、设计不同于电子作品,其本身的气质(生活表面下潜藏的、略带悬疑的、零碎易被忽略的)能更好地呈现出来。这种展现手法来源于我对看过的侦探剧、黑色电影的拙劣模仿。
但我必须指出,形式上目前可能存在不完备之处,但作品企图呈现出的“谋杀案”是真真实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FOTO:摄影,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死亡的语言,在“城市谋杀案”系列作品中,你用了一种死亡的语言来讲述一种死亡的可能,你如何看待这种矛盾性。
崔善生:举个例子,就像我用一首《城市谋杀案-Vietnam》 诗来解释另一首诗,用一个谜语解释另一个谜语。生与死并不是一个很确定的说法,我们其实是处于它们的叠加状态中。就拿攝影作为死亡的语言来说,用死的语言是为了好好地活,在创作里,有的时候死的东西能复活,而且能激发出更多生的力量。所以这种矛盾性可能是一种源自生命、生活本身的张力。
插句题外话,之前一个朋友问:你们摄影师在很清楚自己拍摄什么东西的情况下为什么还在自己的讲述中总表达出一种超出物外的感受?其实我想说很多时候摄影师并不清楚他拍摄的到底是什么,一株植株仅仅是一株植物吗?一个人一瞬的表情姿态仅仅是你所看到的样子吗?显然,我们并不能肯定地做出回答。
FOTO:作品《湿铁锈》是对自己记忆的一种讨论么?在其中,你用了很多海岸的影像,它对于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么?
崔善生:湿铁锈,这个词语是我对童年生活的一种印象。它对我来说,是一种味道,当时还写下了“布满绿色水垢的鱼缸的气味”。我在一遍遍地观看堆积在硬盘中的影像时,忽然想起了这种味道,它来源于逝去日子里的某些场景意象的闪现。海岸的影像没有过于特别的意义,主要是我这十几年都生活在广东珠海,所以海的影像比较多,而它们也逐渐沉入到记忆的潮水中,偶尔向我涌来。
我在童年时候的确憧憬大海,但第一次看到海的时候却是令人失望的灰突突。所谓的让人心胸开阔不过是一种感动。对于这种印象以及它所引发的思考,我确实曾经想过拍一部短片来呈现,但目前这个想法仍旧搁浅在岸上。
FOTO:在不同的作品中,你选择了不同的照片尺幅,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崔善生:照片是有边界的呈现,而不同的尺寸也带来了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观看方式。有的尺寸比例是为了更好地呈现其本身,而有的作品因为尺寸的限制,反而成就了它。这些都是机缘巧合带来的。我在创作中并非将自己置于全知全能的角色,更多的是乐见其成。
FOTO:作品《忧心忡忡的美梦》中的图片十分生活化,像是对于日常的记录,你的作品在呈现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顺序?
崔善生: 我摄影中的日常感比较强,因为我在拍摄中时常处于一种既兴奋又放空的状态,没有思索那么多形式感的东西。目前这组作品有三种呈现顺序——一种是在展览上的,一种是在视频中的,还有一种是在新印的画册中的呈现。不同的场景形式下其他形式上的呈现可能又有新的变化。
这部作品的画册中, 我是按照音乐专辑的感觉划分了章节:第一章的“海”作为引导观者进入一种忧郁的氛围,第三章的“孤独的霍普”则将城市中的现代孤独掀起一角,第五章的“碎浪”是在游历中平卓马焚烧底片的逗子海边以及江之岛时拍摄的,阴天下的海更能调动人的愁绪,人们如同碎裂的浪花,匆匆消逝。明媚和阴雨的光影基调交织出现,也让阅读者感受到了一种矛盾变换的心绪。
FOTO:相较于其他作品,作品《地狱变》的色调和展现方式有一种暗房特殊效果制作(如色调分离、中途曝光、浮雕效果)的感觉,你是通过什么技术手段完成作品创作的?为什么会想要采用这种创作方式?能讲讲它的来由和创作过程么?此外,它在你所有作品中,处于一种怎样的位置?
崔善生: 《地狱变》这组作品,是我通过调色和素材之间的互相叠加而制作的,这组作品算是一个创作上的探索,因为这不是我熟悉的胶片制作流程,是数码拍摄的,我其实不会或者说不太喜欢用过于复杂的创作方式,这跟我的性格有关。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拍过类似的东西,但是并没有太在乎。但是闲来无事时拍下的那些引起我注意的素材们总是达不到我当时捕捉到它们时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后期的时候对它们进行反复实验,在众多版本中有了现在的样子。
它拍摄的几乎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东西,譬如瓷砖、墙面、油漆渍、划痕、锈迹等等。名字是因为在实验过程中的初始图片让我想起了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地狱变》给我的感觉,而这个名字又来自于佛教,于是我开始在幻想地狱角落的样貌上展开了探索。地狱也许并非是遥不可及的某处,也可能就躺在触手可及的日常中。当然这个想法和城市谋杀案又有一些连结的地方。
FOTO:未来,你的作品将偏向研究哪个领域?最近有计划出新的作品吗?
崔善生: 最近,我一直在整理旧的作品,前些年没有好的方式把那些作品呈现到大众的面前。接下来的两年,我希望慢慢整理出书和做展览。目前,作品《忧心忡忡的美梦》已经印制完毕,计划下一部是《东欧空难》,然后是《城市谋杀案-Vietnam》和《岛屿变奏曲》。“城市謀杀案”这个系列,我会尽量持续创作下去。关于创作领域问题,最近我也在思考创作的问题,很难给出确切的答案。只要我感兴趣的方向,可能都会涉猎,譬如“城市谋杀案”系列中就会有项目制的作品形式以及装置、行为艺术的呈现方式。
艺术总有这样便利的错觉,你不用很专业地了解每一个事物,而是捕捉到了某种“神”。
关于新创作的作品,仍在拍摄的有PUZZLE 《岛屿变奏曲》《乌鸦的臼齿》这些。可能也有要做一些视频影像、装置这些呈现方式的想法,一步步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