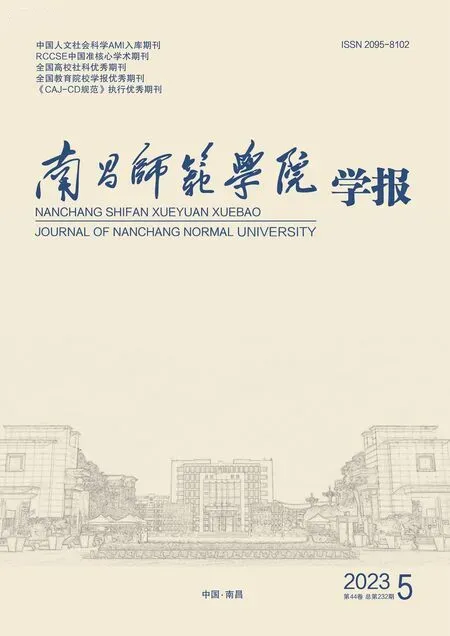传统与现代的会通
——再评都市新淮剧《金龙与蜉蝣》
陈丽芬
(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西南昌 330032)
1993年5月,罗怀臻的都市新淮剧《金龙与蜉蝣》在上海首演,它打破了传统淮剧的乡土气息,以现代大剧场的格局为中国戏曲注入了浓厚的古希腊悲剧意味和莎士比亚风格,成功实现了传统淮剧的现代化再生,为处在“萧条期”的中国戏曲整体带来了惊奇,被誉为“当代戏曲改革与创新全面冲刺的代表作”,它也因此成为一部向古希腊悲剧致敬的经典作品。1993年,上海剧坛更是因《金龙与蜉蝣》一剧将当年称为“罗怀臻年”。它也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热议,众多评论对其现代化的品格作了深刻的分析,不仅从主题、人物、风格上阐释其现代化品格,更是阐发了此剧与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风格的横向借鉴与关联。然而,都市新淮剧《金龙与蜉蝣》的现代化品格并不是脱离本土文化的抄袭和引进,恰恰相反,是脱胎于传统的创新与再造,处处体现出现代艺术对传统艺术的继承。三十年后,当我们再次回看它,会发现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沟通了传统与现代,对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从而使之成为现代的一部分的努力。
一、淮剧剧种本色与现代悲剧的契合
中国戏曲的文学创作,内容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偶尔也写写文人式的失落,民族的审美定势总是在悲欢离合式的团圆中自觉煽情。而作为地方戏曲的淮剧更是以擅长演绎苦情戏著称。淮剧起源于盐城建湖,最早是以“门叹词”的形式出现,即贫困人们的乞讨词,受“香火戏”的影响演变为“盐淮小戏”,在吸收徽剧、京剧的艺术特色后逐渐形成一种新艺术——淮剧。由于淮剧发展形成于苏北,使得淮剧的整体风格气质具有浓厚的苏北地方特色,古朴粗犷、高亢辽阔。而特殊的形成环境与发展历程,又使得淮剧总是和苦难联系在一起,观众人群也是最底层的百姓,演出的内容则是底层观众爱看的“哭”戏,妻离子散、万里寻亲等内容构成了传统淮剧的基本情节。[1]
后来因为苏北发大水,淮剧艺人逃荒又把淮剧带到了上海。淮剧流传到上海以后,受都市文化的影响,渐渐丧失了古朴、粗犷的苏北地方特色,风格趋向越剧、京昆,变得温柔抒情,演剧也趋向写实。淮剧最终也因其剧种的泛化逐渐没落,至80年代后期在上海几乎无立锥之地。
罗怀臻的都市新淮剧《金龙与蜉蝣》一剧,把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做了全面嫁接。在内容上,它延续了淮剧擅长演绎苦情戏的特色,讲述了一个宫廷政变、王权导致人性异化的悲剧故事。故事的核心情节也有妻离子散、万里寻亲的内容,但是这个故事却并没有局限在封建家族聚散合离、儿女情长弯弯绕绕的悲情叙事中,而是将其上升到了古希腊悲剧的高度。
在《金龙与蜉蝣》的叙事中,皇帝被杀,身为王子的金龙流落在孤岛上,与渔家女玉凤成亲并生下一子,过了三年平凡而快乐的日子。但在对王权的渴望下,他毅然抛妻弃子,走上十年的复仇之路。十年后,他终于成功登上皇位,人性却一步步走向异化和变态:先是杀死有功之臣牛牯;继而因误以为千里寻父的亲生儿子蜉蝣为“牛牯之子”,而残忍地将其阉割;最后为延续子嗣,强抢民女入宫,不想抢来的竟是自己的儿媳。蜉蝣也由一个天真的寻父少年变成一个身心变态的宦官,在这种生存环境的影响下,年幼的孑孓刺杀自己的亲生爷爷金龙。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金龙被自己的亲孙子所杀,竟能倍感欣喜地称赞:“孙子像我”!
在这个故事情节中,由于金龙“阉子占媳”的情节与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的情节相似,金龙为王权的延续而杀死亲生儿子的情节更是《美狄亚》的翻版,从而使这个悲情故事成为贯穿古今中外的人性悲剧,带有浓厚的古希腊悲剧风格。故事结局以父亲杀儿子、孙子杀爷爷的人伦悖反与扭曲变态行为模式来完成悲剧的惨烈效果,更是超越了传统戏曲的悲欢离合模式,激起观众心灵的震撼和哲理的思索,带有悲壮苍凉的历史感、宿命感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悲剧。剧作不仅在情节、手法上借鉴了古希腊悲剧,更重要的在于借鉴了它的精神。在中国是苦戏泛滥悲剧少,苦戏是在世俗的道德中纠缠,悲剧则是命运的必然与个人意志的矛盾。《金龙与蜉蝣》一剧中,金龙不知有子而日日盼子,儿子就在身边却误将其阉割,为了求子又误将儿媳强占,为了祖先的基业延绵子孙,却又亲手残害子孙受到先灵的谴责。这其中处处体现出金龙悲剧命运的必然与个人意志的矛盾,生发出对人性、人生的思考,使其具有了古希腊式的悲剧力量和人格力量,成为一个向古希腊悲剧致敬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金龙与蜉蝣》一剧借鉴的只是古希腊悲剧的风格与精神,而这种古希腊式的悲剧风格与精神却是从民族文化中根植出来的。具体表现为:其一,从情节设定来看,金龙的亡国、玉凤与金龙、玉荞与蜉蝣的夫妻分离、蜉蝣的寻父、玉凤、玉荞的寻夫等等情节,都能找到观众喜欢的“老淮调”的“悲剧因子”;其二,剧作中,金龙的悲剧命运并没有像古希腊悲剧那样处处有神旨和预言的召唤,没有支配命运的上天的存在,而更多体现出权欲与人性的悲剧冲突。剧作通过金龙、蜉蝣、孑孓祖孙三代人性的异化来纵向揭示专制的残酷性和对人性的摧残,使剧作更多呈现出中国专制王朝下,自相残杀、代代不息的历史长河的共同图景;其三,蜉蝣这个人物更是体现出中国式的悲剧,宦官是中国历史的隐秘角落,是封建等级文化下产生的畸形现象。剧作重点表现了蜉蝣被阉割的巨大痛苦,以及阉割后人性从异态走向变态的心路历程,是现代意识对畸形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其四,为了重新找回传统淮剧古朴粗犷的剧种特色,剧作在故事背景、人物形象、情节设置上处处与淮剧古朴粗犷、刚健有力的剧种风格相契合。剧作将其故事背景设定在父死子继的宗法世袭制完备的“西周以降”,模糊在西周到东周漫长的六百余年间。远古时期的生存环境处处透露着古朴粗犷的气息,人物形象则透露着荒蛮、残忍与坚韧的原始古朴与粗犷豪放。故事以父亲杀儿子、孙子杀爷爷的人伦悖反与扭曲变态行为模式完成的惨烈悲剧,形成全剧恢宏的气势和刚健的风骨;其五,剧作在深挖金龙孤独精神和蜉蝣裂变心理的同时,并没有导向金龙与蜉蝣做是生还是死的灵魂拷问,也没有提供场面挖掘蜉蝣想要复仇杀死金龙的痛苦与纠结,而是极力展现金龙权力至上的孤独情感以及蜉蝣从异态到变态的惟妙惟肖的心理外化情态。这就使得剧作没有导向李尔王的独白、哈姆雷特的叹息式的西式处理方式,而更多呈现出儒家文化、老庄文化中那种“天地悠悠”“乾坤浩荡”“逝者如斯”“人生若短”的感叹。
总之,《金龙与蜉蝣》在情节上并没有像传统戏曲那样用波折横生、旁逸斜出的冗长结构来叙事,而是把时间的线性叙事以跳跃性的场景出现。在充分发挥戏曲表现时空自由特征的同时,充实了戏曲文学的情节容量和内涵表现。大场景中重点表现了金龙自由意志与权欲召唤的矛盾冲突以及蜉蝣被阉割后的痛苦情感与精神裂变,将传统戏曲的悲情叙事演绎为人生人性的哲理思索,使中国传统戏曲淮剧意义中的“苦戏”上升为现代悲剧的品格。
二、传统戏曲程式与现代人物塑造相结合
中国传统戏曲的人物根据角色扮演的不同类型及表演的不同,形成戏曲人物的行当。淮剧的行当有生、旦、净、丑,“生”指“老生”“小生”,“旦”指“老旦”“小旦”,“净”指“大花脸”“二花脸”。“大花脸”一般都扮演较有身份的帝王将相角色,人物可忠可奸,一种专演白脸的奸臣,淮剧界称之为粉脸。“二花脸”一般都是扮演较有武功的人物。“三花脸”亦称小花脸,即小丑。由于传统戏曲表现的主题往往是在人物的忠奸善恶对立中作道德式的评判,传统戏曲表现的人物普遍呈现出扁平化的特征,传统戏曲行当也因此形成类型化的特征,忠奸善恶一目了然。角色只要依据自身扮演的类型选择行当对号入座即可,然后依据行当规定的表演程式表演即可。
都市新淮剧《金龙与蜉蝣》打破了传统戏曲忠奸善恶的人物塑造方式,人物向复杂立体方向发展,并尤其注重对人物复杂性格的刻画以及深层心理的描绘。金龙、蜉蝣在剧中都呈现出复杂人性的多面。金龙在流落渔岛、与渔家女玉凤度过的三年时光里,呈现的是一个对自由平静生活向往的理想金龙,但在其自由理想的形象表层之下,潜藏着一个对王权渴望并受其召唤的野心勃勃的金龙,由此形成理想金龙与野心金龙的心灵搏斗与撕扯。最终野心金龙战胜理想金龙,促使他抛妻别子走上十年复仇之路,最终坐拥王权。为了维护王权,他开始了人性扭曲的不归之路:杀功臣牛牯、误将亲生之子蜉蝣当作牛牯之子阉割、认子后为维护帝王尊严将已为阉人的亲生儿子蜉蝣杀死……在求子与杀子、保障祖先基业又亲手摧毁的矛盾行为中,呈现的是一个遭遇灵魂拷问与人性冲突的纠结而痛苦的金龙,王权至高无上的孤独感在金龙身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相比金龙,蜉蝣的人物形象则更为丰富复杂。传统戏曲舞台上的宦官(太监)形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宫廷里的近臣,大都属于龙套角色,这类人物通常起着传旨接驾的职事,形同摆设,无戏可做;再一类就是刘瑾、魏忠贤一类坏到极点的脸谱化人物。”[2]而蜉蝣这个人物形象却呈现出人生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寻父之前的“常态”,呈现的是一个健康俊朗、天真活泼的少年形象;第二阶段是被金龙阉割后的“异态”,呈现的是一个不生不死、痛苦纠结的常人与非常人的过渡形象;第三阶段是八年宫廷生活之后的“变态”,呈现的是有点阴险和玩世不恭的变态形象。
《金龙与蜉蝣》的人物形象已经大大超出传统戏曲人物的类型化,呈现出现代人物的复杂与深刻。值得称道的是,剧作在塑造金龙与蜉蝣的复杂性格、描绘其深层心理时,依托的仍然是淮剧的戏曲程式。虽加入了许多现代表演手法,但都如盐入水般地“化”到了淮剧的戏曲程式中。具体表现为:其一,在角色行当方面,金龙的角色基本套用淮剧戏曲行当的老生,妆容上以凸显人物气质的现代妆替代了原先脸谱化的大花脸,表演时加入了演员细腻的面部表情动作来刻画人物。在几次表现金龙心灵搏斗与撕扯时,运用了人物心理外化的手法,让金龙受权力召唤的内心以先王的形象幻化出来,并配以画外音来呈现。蜉蝣的角色用的也是淮剧的行当,虽进行了程式重组,将生、旦、丑行当融为一体,来表现蜉蝣不同人生阶段特征,但生、旦、丑行当的基本表演是不变的。其二,在身段表演方面,金龙基本沿用的是老生的身段表演,但是加入了一些表现远古时期人物形象的生活动作。蜉蝣的表演则按生、旦、丑的身段依次表现人物的三个阶段。并在原有行当身段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现代化的造型和细节动作,如“他成了太监还欺侮女孩的拽女孩子的动作、他吃完东西剔牙后一唾的动作、为皇上按摩的动作等都有一种扭曲的、报复的诡秘心态渗透出来。”[2]并且,为了表现蜉蝣被阉割后的复杂情感与心理,还创造出了许多新的戏曲身段。如,“行步的不规则,身体的扭曲摇摆、笑声里藏着阴冷、哀痛中透出疯狂,对金龙明显唯唯嗒咯,暗中却诅咒唾骂、喜怒无常、瞬息多变、不可捉摸、充分表演出人性异化后的非常人性态”,[2]处处表现出一种扭曲的美。这种扭曲的美不是通常小生表演一惯用的身形,也是传统戏曲动作中所没有的新的语汇。这些生活化的动作、现代感的造型、贴合人物的新的动作语汇都渗透进传统戏曲的行当身段中,水乳交融,处处彰显出淮剧艺术的美。其三,在音乐唱腔方面,《金龙与蜉蝣》也保持了淮剧的原汁原味。淮剧曾被称为“唱不死的淮剧”,[3]由此表现出淮剧“长于唱”“工于唱”的“以唱为先”“以唱见长”“以唱为重”的鲜明文化审美特征和独特艺术个性。一出淮剧演到最后,如果主要演员没有一段大板唱(所谓的核心唱段),观众是不会满足的。”[4]传统戏曲音乐都有一个基本属性,即剧种音乐本色问题,这就为整部剧预先设定了一个音乐框架与基调。《金龙与蜉蝣》一剧的音乐唱腔做到了“变中求同”,使之既不失淮剧风味,又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其音乐唱腔在创作风格上虽然有新的探索,但都能建立在传统淮剧音乐的基础之上。为更好地塑造人物,它打破了传统戏曲曲牌成套的音乐唱腔,采用以调性音乐为主的自由组合。音乐唱腔的细节方面也做了创新,如调整了调性音乐的节奏结构,时快时慢,有整有散,在原本锣鼓开场中填满演员的身段表演等等。但“全剧音乐素材的摘取,不难看出是来源于淮剧音乐中‘淮调’‘拉调’‘自由调’的音调。”[5]“蜉蝣受刑后的一段‘大悲调’荡气回肠,如述如泣;玉凤责骂金龙的‘马派自由调’悲愤交加、酣畅淋漓;金龙与蜉蝣父子相认的一段‘淮调’层层叠进、峰回路转。”[5]充分展示了淮剧所独有的魅力。
三、传统戏曲美学与现代审美的融合
传统戏曲美学讲究写意性、虚拟性、抒情性及程式性。写意性是指戏曲的舞台上不能太实太满,讲究抽象神似,通常要求在形象之中有所蕴涵和寄寓,让“象”具有表意功能或成为表意的手段。虚拟性则指演员表演时多用虚拟动作,依靠某些特定的表演动作来暗示出舞台上并不存在的实物或情境,比如借用马鞭的动作虚拟骑马、借用竹篙撑船的动作虚拟行船。安葵指出,“在舞台的时空处理上,以虚写实、虚实相生更是戏曲的重要特征。传统戏曲用一桌二椅可以代表居室、客厅、军帐、宫廷等不同空间。”[6]抒情性则指剧情到了“人物有深刻的情感、复杂的人生况味的地方,则不让他唱个曲尽其微、痛快淋漓就不能罢休。”[7](P91)戏曲的程式性则是一种规范,“戏曲的程式化,不仅仅是指在表演过程中的那些固定的一招一式。戏曲的程式化特征渗透在戏曲舞台的所有方面,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它们分别通过唱腔、身段、行当、脸谱等等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8]《金龙与蜉蝣》一剧从舞台处理、服饰造型、舞蹈动作、灯光技术等方面处处体现出以现代审美意识对淮剧各个艺术环节的创新,并力求将传统戏曲美学与现代审美相融合。
首先,从舞台处理来看,由于剧作表现的时空的大跨度,“导演把大量铺垫性和衔接性的情节叙事若即若离地推向幕后,而使直观场面用以表现命运突变性。”“剧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皆从云中龙似的虚实相生中表现出来。”[9]“舞台体现不追求形似,只要求传神,使象征性成为主要手段,如王位的不同位置、高度和变化。”[10]整体的舞台布置呈现出肃杀、冷漠、旷寂、惨阴的生存环境氛围,处处透视出写意的观念,充分运用了传统戏曲时空自由转换的特点,使整个舞台在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叙事中彰显着诗意的光辉。但在时空的转换中,跳跃的快节奏、强烈的对比等现代审美因素都融入到了剧情、舞美与表演中,丝丝入扣。同时,在这种诗意的叙事中,重点铺排了蜉蝣被阉割后、认父后等几个灵魂大搏斗的场面,把悲剧性的冲突提高到历史的和美学的特定情境中来体认、感知,既强化了现代审美意识,又给人物表达情感留了充分的表演空间,充分展现了戏曲的抒情美。
其次,从服饰造型来看,传统戏曲的服装造型被简化处理,水袖、髯口、厚底靴、翎子等被用作技艺传情的服饰都没有了,而是从戏的格调与力度出发,从人物性格出发,服饰上追求一种远古感,古朴、粗犷、有力度,并强调现代审美追求的色彩的夸张。造型上,融入了日本歌舞伎的东西,将“戏曲程式的相对稳定性语汇和相对雷同性、风格化语汇作一些调整和改造,以创造这个戏独具特色的形体动律总谱。”[10]是戏曲传统风格基础上的现代创新。
再次,从舞蹈动作来看,加入了许多现代舞蹈,如宫女的群像、战士的群像、武士的舞蹈。“特别是武士的舞蹈,带有宗教的特点,又有木偶式的夸张变形,对造成戏剧场景对比起着重要作用。”[5]宫女的群像、战士的群像、武士的舞蹈,带有强烈的展示性,在增强现代视觉审美的同时,又很好地营造出古典的、阳刚的、粗犷的远古氛围,与淮剧古朴粗犷的剧种风格相得益彰。不仅如此,现代舞蹈语汇很好地融合进淮剧戏曲的舞蹈程式中,扩充了淮剧戏曲舞蹈的表现空间,增强了戏曲程式的表现效果。如,表现蜉蝣刚刚被阉割后的一段表演中,采用了淮剧惯用的手法,先是一段锣鼓导人,锣鼓声后,人物便开始大悲调唱。为了增强剧场效果、符合现代审美,原先演员无戏的锣鼓声中,导演让演员填满身段动作。于是,这段舞蹈动作就在生活基础上提炼出一个用双手和双袖掩遮小腹的动作,再加上淮剧技巧上踢褶子、抖动等动作,就使得这段打击乐里注入了人物的情感而有了灵魂。再如,演蜉蝣母亲玉凤闯宫冲开卫兵刀架的一场,有一段表达人物情感的大悲调唱段,一张嘴就是一百多句,把“唱不死”的淮剧精髓发挥到了极致,原本也是先一段锣鼓导人,然后开唱的。导演仍然将这段锣鼓声中加入了身段舞蹈,这段舞蹈动作也是在淮剧技巧上加入了生活提炼动作,使其更贴合人物。同时,还成功地融入了兵士的现代舞蹈,让演员与兵士的现代舞配合着随着戏曲节奏动了起来。
最后,从灯光技术来看,《金龙与蜉蝣》一剧的灯光尤其精彩,不仅能跟随着戏曲的节奏、锣鼓音乐的节奏来,强弱、对比、色块都有分寸,而且起着转换时空、塑造人物、营造氛围的关键作用。在转换时空方面,从金龙潜逃、被渔家女救起、金龙与渔家女玉凤三年快乐的夫妻时光、金龙抛妻弃子十年征战、二十年后蜉蝣寻父入宫、蜉蝣被阉割后在宫中生活的八年……种种时空中的大跨度均由灯光的强弱、色彩的转换来过渡。在塑造人物方面,灯光会随着人物的情绪、心理而变换,并以心理外化的方式来呈现。如,蜉蝣受宫刑后回忆起自己的妻子、母亲的一段戏,为了呈现三人交叉思念形成情感交流,舞台以灯光的方式切换出三个表演区域,蜉蝣的主表演区灯光较强、不同时空的妻子、母亲的表演区灯光较弱,三人交叉表演,形成了电影“叠印”的效果。在营造氛围方面,灯光或温馨浪漫表达金龙与玉凤在渔岛快乐生活的画面,或宏大壮观表现征战场面,如“一段表现征战场面的仅有三分钟的舞蹈中,灯光变换了四次,投之以红光、白光及白色圆柱形顶光。瞬间十六道光束组成了一道光幕喷泻而下。表现了武士们血战中的悲壮形象。”[5]或亦真亦幻呈现人物的心理等等,灯光营造的氛围为戏剧叙事延伸了诗意的抒情空间。
四、结 语
《金龙与蜉蝣》一剧将传统戏曲的悲情叙事演绎为人生人性的哲理思索,使得中国传统戏曲淮剧意义中的“苦戏”上升为现代悲剧的品格,使淮剧的悲怆深沉的古楚遗风与古希腊悲剧意味、莎士比亚风格融合在一起,是学院派戏剧在中国戏曲中的再生。它的成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本土文化传统对于当代戏曲发展的价值与意义:其一,传统戏曲的现代化进程总是在横向借鉴多种艺术手法来实现创新,但各种借鉴来的艺术手法能不能糅合到戏曲艺术中去,使之成为自然融合的整体,是戏曲现代化成功的关键所在;其二,任何戏曲改革最终都要回到本剧种的特色上来,创新同时也是一种返本,戏曲艺术价值想要在世界艺术中立足,必然要通过个性的强调、通过对民族性的强调而影响深远。
——江苏省宝应县泾河镇中心小学“淮腔今韵”文化项目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