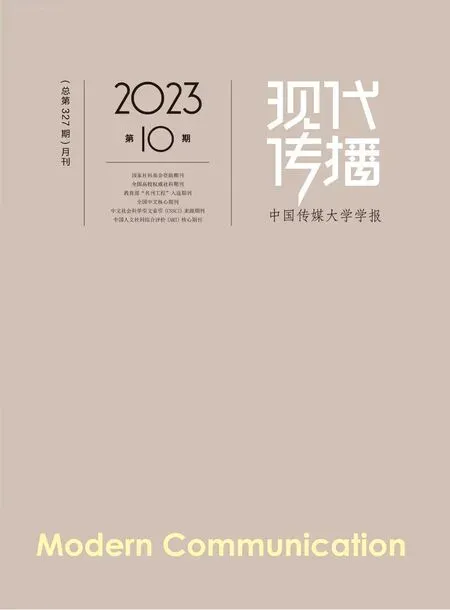“形象迭用”与中国电影的表意观念*
—王海洲 吕培铭—
一、“形象迭用”与中国艺术传统
美国学者浦安迪(Andrew H.Plaks)在研究中国明清小说的结构问题时,认为“中国思想上所谓的‘循环’观念,着重在表现不断周旋交替中的意义,而与西方小说的追求直线性的发展迥然不同”①。他基于中国文化中“多项周旋”的哲学见解,认为“形象迭用”手法是“奇书文体”的重要特征之一。②所谓“形象迭用”是指一种有意而为之的行文重复,如一系列人物、事件、场景、物象等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其在传统小说中的运用之广泛“有时甚至到了令人厌烦的地步”③,但恰是在这些看似繁琐的重复操作中,隐藏着深刻透视传统叙事美学的关键密码。这一问题在国内诸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回应,如林岗认为,“反复迭用是评点家们指出的最基本的手法”④。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基于“道”与“技”的“双构性”,着重探讨了“重复”在明清小说中得以实现的具体方式,并尤其关注到了“重复中反重复”的叙事操作。⑤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这一问题是基于明清小说而提出的,但传统诗词、戏曲等艺术往往也隐含着“形象迭用”的创作规律,它不仅与中国文化哲学息息相关,同时也形塑着中国艺术传统的民族面貌。正因如此,梳理“形象迭用”得以产生的文化哲学背景,归纳其在艺术传统中的表现方式,并将其与中国电影的创作实践结合起来,分析两者间的继承关系,是推动中国电影民族化发展、建构中国原创理论话语的有效路径。
从文化哲学观念来说,“昼夜更替”“四时轮转”等自然现象感性直观地形塑着华夏初民对事物规律的朴素认知,无数次经验的重复与镂刻,促使人们产生了事物“周期性变化”的循环观念,自此线性时间化为了循环之“圆”,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圆道”思维模式。这一观念最早可追溯到《周易》中,其所阐释的“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⑥,正是宇宙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变化观的展现。从既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以“圆”为内蕴的循环意识是先秦不可忽略的重要思想,无论是老子对“道”“周行而不殆”(《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的规律阐释,抑或是庄子“枢始得其环中”(《庄子·齐物论》)的形象描绘,均受到了此种思维的影响。“易的运行和道的运行,具有相似的圆形轨迹,这就是中国人宇宙论和生命论的动态原型。”⑦战国末期,《吕氏春秋》广泛吸收先秦诸子思想而专列《圜道》一篇,并将“‘圜周往复’视为天道的特质和人主治道”⑧,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是中华民族的特色之一。
独特的文化观念造就着民族化的审美追求。受此影响,中国传统艺术也形成了“绵延复沓”的审美意识。诚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人的意趣“不是一往不返,而是回旋往复的”⑨。如《诗经》中常出现大量的重章叠句,在重复的回旋交叠中释放着含蓄朦胧的情绪张力。广为流传的《关雎》以河畔的关雎起兴,“窈窕淑女”的形象循环复现;“参差荇菜”作为重要的意象重复又略有变化,从“左右流之”到“左右采之”再到“左右芼之”,呈递出了一种曲折婉转的复沓之美。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的《楚辞》同样具有这种曲折回环的审美节律,“每一顾三回首,每一语必以三语复之”⑩的特有体式形成了一唱三叹、缠绵悱恻的美感。诚如朱良志先生认为,中国艺术中有一种独特的“眷顾意识”⑪,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楚辞》所奠基的。戏曲艺术中,虽然“传奇关目极忌犯重”是创作者们的普遍共识,但诸多戏曲艺术家也运用“迭用反复”的方式建构全篇,如李渔《笠翁十种曲》中,“重复性情节如同有着一定动力节奏的马达,引领着人物在其跌宕起伏的喜剧命运中不断前行”⑫。明清小说方面,金圣叹最早注意到了这一手法,在点评《水浒传》时将其概括为“草蛇灰线法”。《金瓶梅》《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叙事文本中,均可看到此种手法不同程度的体现,“中国最伟大的叙事文作者并不企图以整体的构架来创造‘统一连贯性’,它们是以‘反复循环’的模子来表现人间经验的细致的关系的”⑬。从另一方面来说,“形象迭用”也契合着华夏民族以儒家礼乐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在“乐从和”的情感规约下,中国艺术特别注重提炼艺术的纯粹形式,“着意形式结构的井然有序和反复巩固”⑭,这同样也是“形象迭用”得以贯穿于不同艺术门类,并产生持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中国电影“形象迭用”的分类
电影在中国的发展创新,必然要受到中国文化艺术传统的滋养,“民族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进来,赋予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理论以民族特色”⑮。无论从文化哲学观念还是中国艺术传统来说,“形象迭用”均是一种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审美创造方式,它不可避免地内化于中国电影的创作思维当中,成为其叙事表意的关键所在。相较于文字媒介而言,电影视听综合的影像表现更具直观性,这就使其在运用“形象迭用”手法时具有了天然的广阔空间。另一方面,蒙太奇能够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融合与再造,由此,时空关系可以被打破、重组,甚至循环。正是电影本体性艺术特点与“形象迭用”传统的深层契合,才使得两者间“跨媒介”化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结合电影艺术的特点,我们可以从“典型化场景”“情景交融画面”“功能性物象”三个层面来加以讨论。
(一)“叠韵绵延”:典型化的场景重复
叙事场景是人物活动与事件发展的空间环境。当它们循环往复地出现在作品中时,常隐含着作者巧妙的构思与深意。明清小说中,场景的迭用是重要的叙事策略之一,如《金瓶梅》中,“一道一佛”两院寺庙的反复出现埋藏着西门庆家族命运起伏的密码。“狮子街”同样是出现次数较多的街坊,根据学者杨义的分析,这一场景不仅写尽了人物的荒淫与浪荡,同时也指涉了西门庆家族的鼎盛与危机,强化了叙事的哲理意蕴。⑯《三国演义》中,作者以行文重复的手法成就了“三顾茅庐”的历史佳话,此类明清小说中大量存在的“三复情节”⑰,往往是通过场景的重复来实现的。
电影艺术中,叙事场景的迭用不仅强化了故事空间的稳定性,还能够使作品在“叠韵绵延”的形式美感中实现表意作用。如在陈凯歌的《黄土地》中,黄土飞扬的场面循环往复地衬托着陕北高原环境的恶劣与贫瘠,加之固定机位和写意化构图的渲染,凸显着导演厚重的文化哲思。此外,“黄河”作为重要的叙事场景也实现了重复迭用,片中翠巧去河边打水的情景反复出现了三次,每次均采用了类似的机位与景别,伴随着翠巧浅吟低唱的山歌,传递着她对自由的憧憬与向往。遗憾的是,这一朴素的理想最终仍旧无法实现,当翠巧被黄河的旋涡无情吞噬后,深情的山歌戛然而止,此时画面“出现了六次黄河水的叠化镜头”⑱,滚滚而流的黄河之水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表征,也暗喻着历史文明的接续与传承,导演正是通过对这一场景的“重复化操作”,强化着他对中国文化命脉的审视与思索。最后,作品开头的“迎亲”场景在结尾“同机位、同景别地重复表现了一遍”⑲,传达了特定时代下悲剧性命运的重复与循环。在吴天明执导的《老井》中,“枯井”“荒山”等叙事场景的迭现彰显着中国独具特色的地缘景观,成就着其作为“中国西部片”的苍劲之气。导演同样地多处运用了“形象迭用”的方式来叙事表意,如“倒尿盆”的场景在剧中反复出现了三次,它与主人公孙旺泉微妙的心理变化息息相关。迫于经济的压力和长辈的承诺,旺泉放弃深爱的巧英而入赘到喜凤家,根据当地的文化习俗,清晨“倒尿盆”是男性作为“上门女婿”的重要标志,影片首次出现这一场景,便代表着旺泉对命运的让步与妥协。在丈母娘无休止的唠叨与指责下,旺泉曾选择过反抗(拒绝再倒尿盆),但此时喜凤已怀有了身孕,面对这种既成的事实,我们又看到了旺泉在清晨对这一义务无可奈何的依循。影片最后,虽然旺泉与巧英在井下重燃了爱情之火,但现实的压力已然无法让他卸下生活的枷锁去追寻自己的爱情,于是这一场景再次出现,无声地传达了作者对人物的怜悯与悲切。
(二)“即景入咏”:情景交融的镜语复现
在构建中国原创电影理论话语的进程中,电影与意象、意境等传统美学范畴的互动关系是不可忽略的分析视角。这方面研究较早可以追溯到李玉华的《诗与电影》中,作者从中国传统的诗词出发,探讨了文学描写中“渲染与陪衬”的方法与电影蒙太奇手法相嫁接的可能性。⑳此后,徐昌霖、林年同、刘成汉等学者均在此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极大地推进了电影民族化的理论层次。通过分析发现,中国电影中那些“即景入咏”的镜头画面往往是以“局部”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之中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叙事的“断裂”,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它们为什么会在叙事的进程中突然出现? 只有锚定这些情景交融的镜语在叙事进程中的定位,才能够更好地指导中国电影的创作实践。而想要解决这一问题,除却将电影与诗词等抒情艺术结合起来外,还可以在中国传统以叙事性见长的文本惯例中寻求答案。结合明清时期评点家们的论断不难发现,这一现象与“闲笔”密切相关。
与西方“史诗性”见长的叙事传统不同,诗歌曾一度占据中国文学的主导地位,由此奠定了我国源远流长的抒情传统,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具体来说,传统叙事艺术往往不以建构严密的因果链条为旨趣,而是更加注重事件的自在呈现,由此确立了“闲笔”的重要地位,这是抒情文学与叙事艺术相交叉融合的结果。所谓“闲笔”与“正笔”相对,主要指那些“游离”于故事主线之外的、与叙事进程无过多关联的刻画描写,“情节的严谨整饬与非情节因素的有机融合是中国古典小说结构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和特征”㉑。电影艺术对“闲笔”的继承与转化,则体现为对情景交融画面的运用,它们之所以被创造、保留,甚至通过迭用反复以实现浓墨重彩的渲染,往往是出于抒情表意的需要,这既体现了中国电影对传统叙事文学的自觉继承,同时也是对意象美学的有效转化。
学者张宗伟指出,电影中的意象可分为单一意象与复合意象,而影像的流动叙事需要在一定的长度内进行,“因此需要有‘情节上的贯通能力’和‘意义上的穿透能力’的复合意象,从而起到贯穿影片主旨和风格的作用”㉒。如上所述,电影中的“闲笔”往往是情景融合的镜语,除却局部的运用以外,它们常以复现的形式来建构影片兴味十足的表意系统,成就着中国电影诗情画意的美学风格。如在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月亮这一意象充分践行着“形象迭用”的手法。当张忠良和素芬结合时,高空圆月是他们感情的见证;二人相隔两地时,月亮又代表着素芬对张忠良的牵挂与思念;张忠良抛妻弃子之后,“圆月”变成了“弯月”,加之“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哀唱,悄无声息地传递着素芬期望的破碎。沈浮导演的《李时珍》被誉为民族化的典范之作,影片中多次重复“逆水行舟”的镜头来强化主人公的坚毅品格。当李时珍少时放弃科举考试而毅然从医时,面对父亲的劝告,他眺望着江水上拉船的纤夫,坚定了“生如逆流船”的决心。影片中段,面对父亲的离世和重修《本草》的阻碍,“逆水行舟”的画面再次出现,由此剧情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拐点,李时珍决定以一人之力完成《本草》的修订。影片最后,白发苍颜的李时珍耳边再次响起了纤夫拉船的号角,此时“逆水行舟”的画面已内化为了他虚实相生的“心象”,伴随着“生如逆流船”的低唱,使故事在寓意深远的意蕴中落下了帷幕。总的来说,当情景交融的镜语以“复现”的形式穿插于叙事中时,其能够在作品中建立起一套抒情表意的、带有浓厚中国色彩的影像密码,为中国电影注入更多的传统文化基因。
(三)“草蛇灰线”:功能性的物象贯穿
“功能性物象”是指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与情节等层面“起贯穿性连缀作用的具体物品”㉓。金圣叹最早注意到了这种手法的运用,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到,“有草蛇灰线法。如景阳冈勤叙许多‘哨棒’字,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字等是也。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㉔。在《水浒传》对武松的描写中,“哨棒”这一物象出现了十九次,它不仅成为武松身份与性格的标志,也为“武松打虎”的高潮营造了强大的“势能”;此外,“帘子”出现了十六次,对于武松来说,“帘子”是保护家庭的“屏障”,对于潘金莲来说,它是女子“遵从妇道”的象征。㉕《金瓶梅》也很注重物象周期性地复现与迭用,如鞋袄、宠物等物象均伴随着季节更迭而出现,是揭开作者叙事表意之“道”的关键密码。
电影艺术中,物象的重复也是重要的策略,当它们“草蛇灰线”般贯穿于叙事的进程中时,既构成了推动情节变化的关键之处,也成了情感外化的重要体现。如早期电影《故都春梦》中,烟斗、花等物象的运用充分展现了“形象迭用”之于中国电影的巨大价值,诚如当时一位影评者指出,“开幕时朱家杰啣烟斗,王蕙兰替他点火……第二次朱家杰偶尔返家,王兰蕙忙取烟斗给他,他早已啣着雪茄……末次幼女在把弄烟斗时,朱家杰已蹒跚到家了”㉖。导演巧妙地通过“烟斗”的迭用表现了朱家杰境况的变迁,并与片名产生了呼应:感受过物欲横流的奢华之后,一切又仿佛回到了从前,真恍如春梦一般! 同时,影片中的“花”物象也反复出现了三次,表现了人物不同的心境。第一次朱家杰尚未离家,此时幼女“摘花”象征着一家其乐融融;当朱家杰抛弃蕙兰后,幼女再次“摘花”并为母亲戴上,“花”的鲜艳反衬了蕙兰的“悲痛”情绪;影片结尾时,幼女摘下的花枯萎在地上,引发了莹儿好花难再开、青春一逝不返的感慨。㉗电影发展进程中,我们能看到诸多电影作品自觉以此策略建构全篇,通过物象迭用建构“连环细笋伏于其中”的影像血脉。如根据导演谢晋的回忆,他在创作电影《秋瑾》时,便已经在有意识地思考如何以重要的细节来塑造人物,通过“秋瑾的珠翠,一直到她的武器的贯串,她的诗词贯串,她的主要道具——宝刀的贯串,还有钟的贯串”㉘等建立起了人物生活起伏的坐标。在谢晋导演另一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作为重要物象的“银毫子”反复出现了四次,摄影师沈西林每次均给予特写来进行强调。从叙事线索来说,它是琼花在革命中由稚嫩到逐渐成熟的见证,从主题来说,这四枚“银毫子”既是共产党拯救人民于水火的体现,同时也是革命理想的有力证明,尤其当这四枚“银毫子”最后变为琼花上交的第一笔党费之时,实现了导演对特定年代“英雄主义精神”的赞美与讴歌。此外,物象迭用也常用来承载男女间微妙的情感关系。电影《知音》中“琴”共出现了“五次”,它是蔡锷与小凤仙交流的桥梁,也是推动二人情感递进的枢纽。在张艺谋早期作品《我的父亲母亲》中,“青瓷碗”总共出现过“四次”,导演为了强调这一物象每次均使用了小景别镜头,它成为“父母”二人关系的重要表征。这些均显现了“形象迭用”之于中国电影的强大生命力。
三、“形象迭用”与中国电影的表意观念
“形象迭用”虽是一种刻意而为之的“重复”,但它却并不意味着机械地复现,作者的深意往往存在于“重复”的细微变化中。在此基础上,“意”之深远能够在“复”之表现中得以言说,这充分契合了中国传统的含蓄表意观念,成为影像建构“象外之意”的重要手段。最后,中国电影的表意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而“迭用与反复”的普遍运用则代表着其整体性表意观念的确立。
(一)“犯中求避”:同中见异的思想传达
如上所述,金圣叹最早注意到了“形象迭用”手法,并将其概括为“草蛇灰线法”。在此基础上,他又主张创作应当遵循“犯中求避”的原则。“犯”即是说要敢于“求同”,敢于“重复”,而“避”则是在此基础之上有所创新。这一观点得到了诸多评点家的回应,如毛宗岗认为,《三国演义》“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惟犯之而后避之,乃能见其避也”㉙;张竹坡称赞《金瓶梅》“妙在于善用犯笔而不犯也”㉚。由此可见,“重复”并不代表机械复现,“周期叠现的文本成分当有细微的差别”㉜。电影艺术也不例外,除却导演刻意而为之的重复照搬外,多数“形象迭用”均是以“同中见异”的策略来实现表意的,这不仅可使观众从形式上的复沓转移到对作者意图的追寻,还能巧妙地规避反而复之所滋生的“枯燥感”和“扁平性”。在谢晋的《芙蓉镇》中,胡玉音被批斗后不得不与同作为“右派”的秦书田共同劳动,两人周而复始地扫地、挨批,那条扫不完的青石板路仿佛昭示着二人苦难悲剧的永续。随着剧情推进,秦书田“扫街的身体运动化作了求爱的舞蹈”㉜,两人也终从陌生走向了结合,此时扫街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逐渐从“各扫一头”变为了“齐头并进”,为晦暗的街道增添了一抹温暖的气息。导演谢晋正是在“同中见异”的场景变化中实现了表意,传达出对黑白颠倒世界的无声控诉。电影《乡音》以“散文化”的影像风格展现了乡村“日复一日”的生活流动,根据导演的阐释,“实现《乡音》多层空间结构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重复”㉝,全片陶春及女儿为丈夫木生“洗脚”的场景共出现过“五次”,这代表着伺候丈夫已然成为她日复一日的习惯。当陶春生病住院之后,女儿龙妹自觉模仿起母亲的行动,当她学着为父亲端洗脚水时,导演刻意使用了与之前完全一样的镜头语言,“我们在拍摄龙妹端洗脚水时,无论景别大小、镜头角度、场面调度、人物的端水动作都与陶春端洗脚水的情景一模一样”㉞。导演恰是在这样一种变化当中凸显了命运的循环,使观众在“蓦然回首”中收获了理性的认识与思考。此外,当陶春生病住院后,龙妹在哄弟弟睡觉时也不自觉地讲起了那个海鸟“衔石填海”的故事,这“说明龙妹也默默地走着母亲走过的那条可悲的道路”㉟。不难发现,中国电影常以这种“重复中反重复”的方式来表现苦难的循环与命运的轮回,如在谢飞导演的《湘女萧萧》中,影片的开头是萧萧作为童养媳跋山涉水来到杨家坳村结婚的场景,自此涉世未深的萧萧成为人妻,承担起了本不属于她年纪的责任与义务。然而,岁月无情的冲刷与洗礼却使她从封建制度的“受害者”转为了纲常礼教的“卫道士”,影片结尾处结婚的场景再次上演,此时萧萧已经娴熟地扮演起了“婆婆”的角色,悄无声息地展现出人间悲剧的重演。
(二)“隐以复意”:含蓄婉转的情感言说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道: “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㊱按照一般的理解,“复意”是指作品在自身意义之外的弦外之音。此外,“复意”还可以视作“重重复复,含蓄蕴藉的审美意味”㊲,这即是说,“重复”也是建构艺术作品深远意味的关键手段,只有通过相似意象间不断地反复强化,才能使作品在相互映衬交织中展现出意义的丰富性与朦胧感,进而达到“意在言外”的审美效果。与此同时,“重复”手法也是“关联思维”的显著体现,所谓“关联思维”即一种注重事物间共生互动的认知模型,“在关联结构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其前后相继、首尾循环的性质,构成了阐释之圆满的流动性”㊳。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六十四卦的循环互通等均是此思维方式的体现。众多明清小说评点家所探寻的那些精微的重复照应,也正是叙事文本在整体关联中所隐含的构思与深意。
在此影响下,中国电影表意中也极为注重意义间的相互关照,创作者常通过场景、意象、物象的循环往复,甚至将其作为结构全篇的布局策略,使观众在“蓦然回首”的复沓与回旋中获得“秘响旁通”的意义统摄。如吴贻弓《城南旧事》以“艺术的重复”来建构全篇,通过主人公小英子的视角结构了三个不同的故事,它们单个看来可能并无深意,但恰是在不断地重复中传递出绵延不尽的韵味。电影《小城之春》中,“城墙”段落出现了“五次”,它既代表着周玉纹安常守故的心理,也暗喻着她冲破藩篱的期盼,成为全篇重要的空间意象。章志忱的突然出现激起了玉纹压抑已久的情欲,两人每次去城墙幽会都代表着暧昧气息的升温。然而,正在他们的情感喷薄欲出之时,章志忱却最终选择了离去。影片的最后,玉纹在城墙散步的场景再次出现,经历了一番痛苦与徘徊后,理智终究克服了欲望占据了上风,玉纹无可奈何地让生命留下这一页空白,不想再挣扎反抗。㊴此外,破败不堪的“庭院”也是极具寓意的空间场景,它与“城墙”一起在循环复现中编织出了“家国同构”的历史寓言,这使得整部作品在男女情爱之上,又增添了时代历史的厚重感,以含蓄婉转的方式完成了一场“不可言说的言说”㊵。
夏衍先生曾谈道: “不特别讲出来而让它自然流露,这就是含蓄。”㊶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复”之手法恰能够让“隐”之深意得以言说,以不断堆积的“密度”为作品带来“伏采潜发”的意蕴,这是具有浓厚中国色彩的表意观念之一,值得深入研究,并可以进一步指导中国电影的创作实践。
(三)“迭用与反复”:整体性表意观念的确立
“整体性”一直是中国叙事美学的自觉追求,但这里所说的“整体”并不是呆板而机械的功能框架,而是以一套流动的运作系统吐纳着世间万物,使整个叙事文本成为“血脉贯通”的有机整体。金圣叹认为,“《水浒传》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两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㊷;毛宗岗认为,《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㊸,这些评点家们所道出的,正是创作者匠心经营下作品浑然天成的整体效果。“形象迭用”也是此种观念的产物。当我们将这种“整体性”追求与电影艺术诗情画意的表意方式结合起来观察,不难发现,中国电影的“意象”表意也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诚如罗艺军先生认为,“一部影片的意境既可以表现在某个场面、段落,也可能渗透在整个影片之中”㊹。纵观百年影史,中国电影表意方式也恰好呈现出此种递进式的发展轨迹,它与民族影像观念的成熟进步息息相关。
电影传入中国时被称为“影戏”,“戏”之观念为本、“影”之表现为末的观念长期占据影坛主导地位,因此早期中国电影的表意方式多是从戏曲创作技巧中派生而来的,如人物间强烈的善恶对比、故事中传奇性的误会巧合等,以此来达到“教化社会”的作用。20 世纪30 年代,随着苏联蒙太奇以及诸多经典理论陆续被译介到中国,先进的电影观念给予了广大电影工作者全新的启示,人们开始认识电影独特的造型语言,逐渐摸索出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实际、又贴近电影创作规律的叙事表意之路。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对蒙太奇的借鉴和吸收更多是“普多夫金式”的象征隐喻,而非“爱森斯坦式”的对撞与冲击,注重“从现实环境中吸取造型因素构成人物心绪与环境交融的蒙太奇段落作为情节链条上的华彩乐章”㊺。也正因如此,传统的“赋比兴”手法与电影蒙太奇得到了深层的应接与延承,产生了一系列诗情画意的经典之作。然而,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意象抒情表意多数是作为“局部”段落来实现的,“两种物象可能仅仅是因为某一表面属性的相似而被归到‘想象的类’中”㊻,即便一些经典之作如《小城之春》等通过意象的叠加反复来建构全片,但这种策略始终没有被中国电影人很好地保留下来。20 世纪80 年代,日益密切的国际交流推进了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启示下,中国电影最终确立了以“意象造型”为核心的表意方式,此时民族影像的意象风格也开始突破了局部意义而呈现出整体性的效果,“有别于传统电影中隐喻、象征性的蒙太奇段落,意象造型直接以视觉造型表意,而且是整体性的”㊼。这种整体性的突出表现之一,便是意象的“迭用反复”成为铺陈于整部电影的风格表征。如张艺谋早期作品中,《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多数作品直接以贯通全篇的意象来命名。近年来,我们也能看到大量以此策略建构全片的作品出现,如电影《长江图》以长江图景的循环迭现、诗歌意象的不断反复造就影片含蓄多义的美学风格。男主高淳逆流而上的同时,安陆“形象迭用”般地出现在每一个渡口。随着高淳航行的路线越来越远,安陆却变得越来越年轻,导演正是在这样相向而行的时空错位中,用表面的数次相遇来建构二人情感与精神的背反与矛盾,使整部作品氤氲着深厚隽永的“象外之意”。总的来说,中国电影的民族意象风格应从局部的修辞手段转换为一种整体性的表意观念,而“迭用与反复”是其有效的实现路径。自此,中国电影独具民族色彩的诗意化风格才能够真正得以彰显。
“一个国家的电影在某个时期有所突破,往往是在自己传统基础上的突破。”㊽本文从“形象迭用”切入,梳理了这种审美创造方法得以形成的文化哲学基础,以及在艺术传统中的表现方式,并将其与民族影像的创作经验结合起来,归纳了中国电影对“形象迭用”手法的依循与转化,并借此总结出了其独具特色的表意观念,试图为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创新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注释:
①②③⑬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96、88、90、97 页。
④㉜ 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44、149 页。
⑤⑯ 杨义:《中国叙事学》(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版,第74、75 页。
⑥ 陈鼓应、赵建伟注译:《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第665 页。
⑦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517 页。
⑧ 孙进:《先秦“圆道”观念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2 页。
⑨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15 页。
⑩⑪ 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83 页。
⑫ 卢旭:《李渔戏剧情节重复方式的喜剧价值》,《韶关学院学报》,2021 年第11 期,第57 页。
⑭ 李泽厚:《华夏美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年版,第34 页。
⑮ 罗艺军:《中国电影理论研究——20 世纪回眸》,《文艺研究》,1999 年第3 期,第200 页。
⑰ 转引自赵莎莎:《〈金瓶梅〉数理批评》,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第29 页。所谓“三复情节”是指做一件事要重复三次才能成功的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在先秦典籍中大量存在,而在叙事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中最为著名的应是《三国演义》之“三顾茅庐”,刘备三请诸葛亮,构成“三复情节”。
⑱⑲㉝㉞㉟ 罗艺军主编:《20 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年版,第651、657、640、640、641 页。
⑳ 李玉华:《诗与电影——学习札记》,《中国电影》,1957 年第1 期,第43 页。
㉑ 杨爱君:《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叙事结构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第12 页。
㉒ 张宗伟:《〈周易〉美学与中国特色电影美学的建构》,《当代电影》,2020 年第8 期,第150 页。
㉓ 李鹏飞:《试论古代小说中的“功能性物象”》,《文学遗产》,2011 年第5 期,第119 页。
㉔ 〔明〕施耐庵著、〔清〕金圣叹评、刘一舟校点:《金圣叹批评〈水浒传〉》(上),齐鲁书社2014 年版,第21 页。
㉕ 张香竹:《移云接月·草蛇灰线·势能——由武松的故事浅议〈水浒传〉叙事艺术》,《小说评论》,2011 年第2 期,第144 页。
㉖㉗ 長夏:《〈故都春梦〉漫评》,《影戏杂志》,1930 年第7/8 期,第42 页。
㉘ 谢晋:《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 年版,第162 页。
㉙㊷㊸ 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11、16、18 页。
㉚ 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219 页。
㉜ [美]尼·布朗、吴晓黎:《社会与主体性:关于中国情节剧的政治经济学》,《世界电影》,1998 年第4 期,第13 页。
㊱ 〔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553 页。
㊲ 皮朝纲:《中国美学体系论》,语文出版社1995 年版,第489 页。
㊳ 任鹏:《中国美学中的关联思维——基于秦汉美学的反思》,《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 年第1 期,第139 页。
㊴ 莘薤:《〈小城之春〉:一首清丽的诗》,《大公报》(上海),1948 年10 月14 日,第7 版。
㊵ 顾春芳:《诗性电影的意象生成》,《电影艺术》,2022 年第2 期,第4 页。
㊶ 夏衍:《电影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 年版,第50 页。
㊹㊺ 罗艺军:《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5 年版,第142、17 页。
㊻ 王海洲、虞健:《“兴”之所致:电影“赋比兴”的新思辩》,《电影新作》,2021 年第6 期,第6 页。
㊼ 罗艺军:《第五代与电影意象造型》,《当代电影》,2005 年第3 期,第5 页。
㊽ 林年同、古苍梧:《关于当前中国电影创作问题的意见》,《电影》,1980 年第18 期,第29 页。